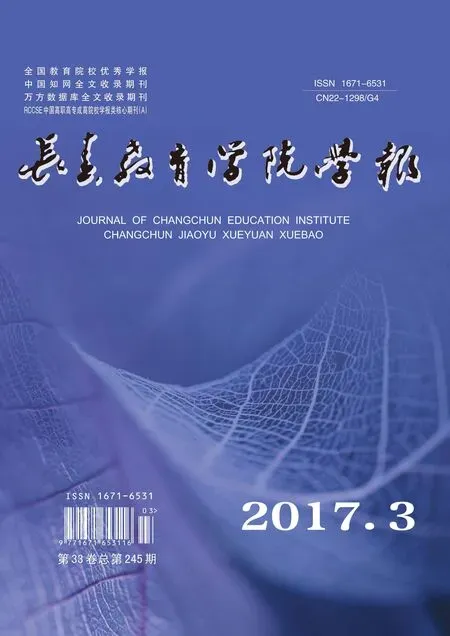乡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的社会环境支持策略*
冯玲玉,冯晓花,曹晶瑜
一、研究背景
关于乡村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研究,关注点最多的是培训话题,乡村教师被生硬地对照各种专业标准进行各种培训,然后再去考评培训应用效果,最终因为培训效果不佳备受批评,他们对各种继续教育和学习培训感到越来越疲惫、焦虑,甚至厌倦和麻木。针对这一问题,笔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教师教育从职前的师范教育到职后的培训培养,更多关注的是学校内部、课堂教学情境,而较少关注非学校情境的,尤其是忽视教师作为社会性成员的普遍的、一般性的特征。对于乡村教师,仅仅把信息化教学能力作为研究对象,显得有些“小题大做”,甚至有些奢侈。乡村教师,首先是社会学范畴的人,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活处境、基本生存问题,其次才是专业能力发展与提高问题。信息化教学能力对于乡村教师来说属于精神追求,是一种自我实现层次的高级需要。
信息化教学与一般的教学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也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双方共同活动。[1]信息化教学是对传统教学的改进与发展,而不是全盘推翻后的替代或否定。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应当是其基本教学能力的一部分,是以基本的教学能力为基础的扩充和发展。
脱离了教师的基本教学能力,孤立、片面地将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及其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则是脱离了信息化教学的本质,既不能揭示信息化教学手段对于目前乡村教育教学改革的意义,也不可能真正找到乡村教师能力发展的途径。因此,对于乡村信息化教学及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的主题研究,应该将其放到乡村社会的大平台上加以观察和思考。鉴于此,本文将着眼于乡村教师的基本生活状态和乡村社会信息化的现状,提出有利于乡村教师信息化能力的环境支持策略建议。
课题组以甘肃省Q县X镇、L镇、Y镇为例,采取访谈法、观察法和实物收集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分别在不同类型的完全小学、中心小学、教学点蹲点,实地观察,采取听课、参加集体教研活动,与一线教师进行深度访谈,和学生一起上课、一起玩、一起聊天等方式,获得第一手自然真实的信息。
二、乡村教师的生活处境现状
(一)教师严重缺编、工作量超重
在走访中发现,乡村教师严重缺编,导致日常工作量超负荷的问题十分突出。如Q县Y镇中心小学,全校共有教师、管理人员26名,每人平均代3门课,每周23节课。镇中心小学相比来说条件较好,教学点师资更加短缺。在L镇某教学点,只有一个代课教师,50多岁,承担校长、门卫、教师三职。今年有走教教师一名,是该地区师范学院的顶岗支教大学生。在甘肃农村小学,教师短缺是较普遍问题。正如姚晓迅等认为的那样,“当种种改革落实到乡村教师身上的时候,他们被期望做一个全能的、不计成本的‘教书匠’,他们成为承担改革成本的工具”。[2]
(二)乡村教师社交范围狭小,社会资源贫乏
衡量一个人的社会资本,很重要的维度是看他遇到困难时是否有较多的人可以提供帮助。乡村教师交往圈子小、社会资源贫乏,他们日常交往对象首先是同事、学生家长、学生、领导。交往的时候,多数与学校工作有关,即“公事”,私人的密切交往不多,职业化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积累社会资本。其次是亲戚、邻居。这些交往对象在社会资源上与自己趋同。受访教师认为,遇到麻烦时可以依靠的人是邻居、最近的亲戚、同事和领导,生活中缺少安全感。最担心家人生病,最难为的是求人办事情。狭小的生活环境、单调的信息互动影响教师的生活质量,也使他们的思想视野、精神追求受到限制。上课按部就班,学生不出安全问题就好;下班回家干家务、看电视、手机上网。这种生活惯性影响教学能力的发展,从而也影响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
(三)乡村教师受到多方排挤,社会地位边缘化
乡村教师收入来源就是工资。一个教龄5年的本科生,到手工资大约3000元。他们在物质财富、政治影响、社会声望甚至赖以生存的文化资本方面,受到体制、市场、道德三个方面的排斥,朝边缘流动。从日常生活空间看,乡村教师的边缘化还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消费、人际交往、精神追求与工作场所(学校)、学校所在社区的分离,在乡村环境中主动或者被动地边缘化,乡村教师成为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3]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揭示了人的需要首先是生理和安全,其次是社交和尊重,最后才是自我实现。乡村教师最迫切的需要是生活工作待遇的改善、教学工作的减负、社会地位的提升。现实中的乡村教师由于社交和尊重的需求难以满足,自我实现的欲望受到遏制。因此,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基本上是纸上谈兵。
三、乡村社会信息化现状
(一)家庭信息化现状
大家熟知的城市家庭场景是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家里有无线网,教师与家长建立QQ群、微信群,布置作业,及时交流。在乡村,以L镇的为例,家庭信息资源匮乏,家校之间信息化互动呈现很大程度的空白。以下通过案例说明。
留守学生A:母亲在邻县打短工,父亲长期在兰州打工。家里爷爷奶奶只有一部老年机,爷爷识字,奶奶不识字。主要是爷爷用老年机和爸爸妈妈打电话。家里有电视机,没有电脑,孩子从小没有接触过网络社交媒体。这样的留守儿童家庭很多。乡村家庭家长文化程度低,信息装备单一、数量少、功能单一,这是普遍现象。在非留守儿童的家里,情况稍微好点儿。以N Q小学一年级为例,18个学生家庭中有4个家庭有电脑、8个家庭有无线网、12个家长有智能手机。电脑主要用来看影视娱乐节目。在这样的情形下,教师与学生家长的信息化互动处于空白状态。
一个良好的信息化互动系统应该是教师、家长、社会、学生之间多向互动。乡村学生从家庭、父母长辈那里获得的信息化体验和影响不多,甚至为零。与此同时,师生之间信息化活动缺失成为乡村教师信息化能力发展的阻碍之一。
(二)乡村社会信息化现状
由于缺少获取外界信息的手段,乡村信息化进展比较缓慢。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带来了信息工具,比智能手机。但如前文所述,信息工具用来娱乐的多,用于家校合作、提升孩子信息素养的少。值得思考的是,信息化工具也带来了变味的文化。有个别家长购买电脑、手机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娱乐,模仿城里人玩游戏、追剧,家长没有将使用手机作为学习工具和方式的媒体运用意识,没有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四、思考和建议
(一)合理布局乡村学校,提升教师的成长性动机
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班级授课制,优点是几十个年龄和知识程度相近的学生互相交流沟通、互相帮助、互相竞争。与城市学校大班额、超大班额现象对比鲜明的是,乡村学校学生数量少、教学环境十分封闭,即使在完全小学的课堂上,一般都不足20人的班额,在教学点上,有时一个班级只有三四个学生,协作学习、讨论学习、比赛、竞赛、表演等教学组织形式因为人数太少受到限制。在这样单调的环境里,学生和教师严重同质化,缺少新鲜信息的刺激,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与交往量少质低。教师数量少,缺乏合作与竞争,缺少成就感,职业效能感降低,专业化成长动机不高。乡村教师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才能激发教学热情和教学能力发展的动力。
(二)重视农民的信息素养教育,鼓励教师参与乡村信息化建设
城市人口相比农村来说,受教育程度高,信息化环境优越,有较强的自学能力,接受信息的渠道丰富,在信息化教育推进中能够家校配合,积极互动。乡村社会受自然条件限制,环境闭塞,乡村人口接受信息的渠道来源单一,信息资源贫乏,信息素养普遍较低。在信息化进程中,究竟谁应该承担起农民的信息素养教育,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一大批教育家开展过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他们非常重视农民的教育。如,晏阳初提出将学校式教育和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结合的主张和实践。梁漱溟探索过举办乡农学校,陶行知更是提倡乡村教育、兴办乡村学校的先行者。[5]有鉴于此,可以针对乡村社会的特点举办乡村学校,专门针对农民进行文化、科学、信息技术知识教育。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在传统社会中,教师从来都是最为重要的社会精英之一,与村社耆老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仅是道德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乡村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日常秩序的维护者。显然,如今教师在乡村社会的威望和地位下降,处于边缘状态。作为乡村的文化人,政府应该重视教师这一宝贵资源,把乡村教师纳入乡村信息化建设、文化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中,成立家长学校、农民学校,给学校教师提供举办讲座、讲演、讲课的机会和平台。让教师融入乡村社会之中,有利于提升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提高乡村教师的地位和威望,也有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
第一,政府应该重视信息化建设,把其纳入到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计划中,让信息网络与广播电视一样,走进家家户户。
第二,成立家长学校,专门培训家长。教会家长掌握家校沟通的手段和应用技能,合理应用社交软件。同时,教师兼职教育农民,引导农民正确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引领农村文化健康发展,引导农民学会健康的信息化生活方式。
(三)对乡村学校撤点并校的思考
2001年起国家对农村学校进行撤点并校。目的是资源优化整合,提高教学质量。然而,怎样合理布局调整乡村学校?显然不能一刀切。
以笔者生活的F村来说,现在道路宽阔平坦,房屋崭新。乡亲们生活富裕了,农闲之余在树下聊天乘凉、打牌娱乐,晚上跳广场舞。可是,原来就读过的学校几年前撤并,如今这个人口2000多的村庄没有小学、幼儿园。村庄里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孩子们上学有的去1公里以外的镇中心小学,有的去3公里以外的县城小学,起早贪黑赶路上学、做作业。
振兴乡村,经济与文化要同步,发展乡村教育刻不容缓,撤点并校必须认真研究、科学策划。配置合理的教师数量,完善学校建制,让学生就近入学,让教师成为乡村社会有尊严的体面人,让他们在信息化发展的大潮中拥有施展自己才华的大舞台,这是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动力所在,也是乡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的根本策略。
:
[1]南国农.信息化教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3.
[2][3]姚晓迅,元昕.边缘化的打工者——中西部地区乡村教师工作和生活调查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冯玲玉等.乡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现状分析——以秦安县陇城教育园区为例[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1).
[5]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54-459;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