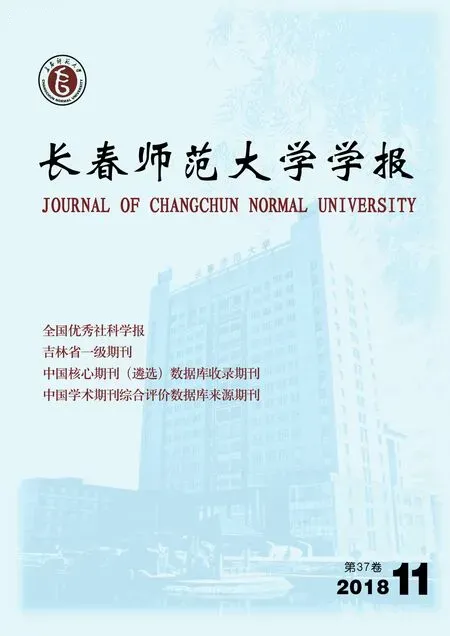论吕韵清短篇言情小说的现代性
许文伯,杨 萍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小说界革命”推动了小说文体地位的提升,一些政治活动家、士大夫等视其为救国救民的工具,对小说推崇备至。客观来讲,小说本身并不具备变革社会的能力,相反,自民国成立后,百姓的生存环境仍然处于“歧路仓皇,血膏原野者,尤难仆数”[1]的惨淡局面。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民初小说家慨叹:“呜呼!向之期望过高者,以小说之力至伟,莫可伦比,乃其结果至于如此,宁不可悲也耶”[2]。现实境遇与心理期望之间的落差促使小说家的创作心态发生改变。
民初小说家的创作心理向游戏消遣的趣味回归,在创作理念上向通俗、媚俗靠拢,积极迎合市民阶层的阅读需求。《申报》“自由谈”栏目主笔王钝根称:“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3]。以市民阶层为中心的读者群更青睐描写男女爱情的故事,他们将小说视为消闲的佳品,小说家们便乐此不疲地创作言情小说。这种创作风气使得“民初言情小说形成中国小说史上继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之后的又一高潮”[4]421。受此影响,吕韵清开始创作言情小说,并在报刊上发表。
吕韵清,字逸初,笔名“韵清女史”“韵清女士”“韵清女史吕逸”等,清末同治年间生于浙江石门县城(今桐乡市崇福镇)。“她天资高厚,有才学,善诗词,喜丹青”[5]20,积极投身于女学教育和文学创作之中。1914—1916年,她相继发表了八部短篇言情小说,分别为《凌波阁》(1914年载于《七襄》第二期)、《白罗衫》(1914年载于《七襄》第五、六期)、《秋窗夜啸》(1915年载于《女子世界》第三期)、《蘼芜怨》(1915年载于《繁华杂志》)、《彩云来》(1915年载于《小说丛报》)、《金夫梦》(1916年载于《春声》第二期)、《红叶三生》(1916年载于《春声》第五期)、《我之新年》(1916年连载于《申报》第15436-15438期)。其中小说《我之新年》在1916年2月《申报》“自由谈”栏目发起的“我之新年”悬赏征文活动中荣获第三名,获得八元酬赠;小说《白罗衫》《凌波阁》又分别易名《血绣》《情殉》并转载于《香艳杂志》第十期、第十一期。
20世纪初女性小说家群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无女性小说的纪录,它为‘五四’新文学女性小说家群的出现提供了文体样板”[6]101,标志着女性作家开始自觉选择小说体裁进行文学创作活动。以吕韵清为代表的女性小说家不再局限于诗词题材创作,不再满足于闺阁之中的吟咏传播,而开始向大众靠拢,所关照的视角也一并延伸到社会风潮之中。这一群体的创作实践顺应了中国近现代小说文体地位提升、女性启蒙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一、主题的现代性
民初言情小说,普遍设定在尽管传统婚姻制度动摇,但现实的壁垒使追求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难以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困境之中。“从社会现实和思想要求出发,小说作者就侧重描写哀情,引起共鸣”[7]272。因此民初小说家往往借助社会背景增强作品的真实性,深化“良缘难成”的悲剧色彩。
言情与社会相交织的创作模式在晚清的写情小说中就有所体现,“将个人情感放置到国家动乱的大背景下来表现的写情小说不在少数”[8]95。清末写情小说借助男女的“私性情”宣扬家国天下的“公性情”,站在维护礼教的立场上把私性情看作情的异化,视其为痴与魔的代表。与清末写情小说相比,民初言情小说肯定私性情的合理性,在创作层面回归言情本体,这是进步的一面,但二者的共同局限性表现在对礼教的维护。一些民初言情小说家在男女之情与礼教发生冲突之际,固守“发乎情止乎礼”的观念,没能深入探讨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
吕韵清的小说《白罗衫》《金夫梦》和《红叶三生》采用言情与社会相交织的主题模式,以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为背景,深刻地反映出男女之间在动荡的社会冲击下所造成的不幸结局。《白罗衫》中男主人公赵武,在辛亥革命之际革命军攻入金陵之时投笔从戎,以某军书记的身份加入北伐团。共和告成后,他与许贞媮结为夫妻,二人情投意合,但不久“风雨飘摇,国基乍定。干戈同室,杀运重开”[9]。二次革命失败后,赵武落入假革命者柳萍的圈套,最终死于乱党枪下,许贞媮随后也殉情而死。《金夫梦》女主人公佩秋与同念私塾的蓉哥“并肩问字,联臂踏歌,两小无猜,相爱愈于手足”[10],双方家长早已为二人定下终身大事。随后私塾先生病辞,佩秋辍学照顾双亲,蓉哥则离乡求学,不得不承受别离之苦。在时局与家事的干扰下,双方极尽所能来维护真情。武昌起义暴发后,战争不断,“警信纷至,城人出奔益众,舟车之价骤增”[10],百姓纷纷逃离家乡。蓉哥本欲携佩秋一起奔走,但她掩泪曰:“深感厚意,惟父垂死,母又卧床,为人女者,安忍暂离,惟君亮之”[10]。紧张局势与侍奉双亲之间的矛盾,击碎了二人双宿双飞的夙愿。后来佩秋在母兄干预下嫁给假革命分子李起文,却终遭抛弃。“儿女何关家国事,姻缘偏误乱离中”[10],佩秋的悲剧命运与动荡的社会紧密相联。《红叶三生》则继续深化《白罗衫》言情+社会的主题模式。“岁辛亥,义旗四起,海内骚然,清社以屋。迨民国肇基,又苦中原逐鹿,二次之变作矣……呜呼,今非昔是,功罪模糊,何莫非时命使然欤”[1]。作者对社会现实有清醒认识,共和所期许的和平安宁愿景破灭,百姓的生存环境与清末别无二致,恩爱夫妻洪生与叶氏落得阴阳相隔在所难免。吕韵清在惨淡的社会环境面前怀有悲怆之感,对复杂的时局具有深刻的认识与批判,并将心中的悲悯融入创作之中,使作品富有哀情基调。
与同时期在作品中直接加入“宣传性”口号而不顾文学艺术个性的一些“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相比,吕韵清能够意识到小说的独立价值。她对时局描写坚持以服务情节为中心,将社会背景视为导致婚恋悲剧的重要因素,增强了婚恋悲剧的现实性。同时,她更注重矛盾的复杂性,家庭的变革、礼教的压迫、人物独立意识的缺失等多重因素丰富了悲剧意蕴,这使得其言情小说具有“现代性”特征。
二、女性形象的现代性
近代女学堂的创办、女权运动的发展等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吕韵清曾在浙江石门公立文明女塾与上海竞雄女学担任教员,是清末民初在女学堂有过任教经历的小说家代表之一。《石门公立文明女塾简章》设立“修身、识字、文理、算学、手工、卫生”[11]六门课程,培养女性的独立生存能力。以启蒙女性为己任的吕韵清,能够站在女性立场上进行人物塑造与文本创作。她的言情小说不局限于哀情氛围的营造,而是进一步呼唤女性寻求自由婚恋、培养独立意识。
刘思谦教授认为,“只有在人类历史由传统的母系制到父权制再到近代由传统的封建父权社会向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才有可能出现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12]3。清末民初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女性的觉醒对封建父权社会形成挑战。吕韵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她们在礼教压迫与渴慕自由的矛盾中必然要面对的困境与遭遇。
这些处于复杂矛盾中的女性,如《蘼芜怨》中的畹君、《彩云来》中的絮才,她们所接受的教育大多属于旧式教育范畴,具有闺秀女性的特征。科举制的衰落使得封建家长的择婿观念发生改变,失去功名庇佑的才华品性沦为附庸,开始赤裸裸地转化为对财力与权势的追逐。才貌端妍的畹君和絮才不可避免地沦为牺牲品,她们所嫁的夫君大多目不识丁,才女与拙夫的结合难以达到琴瑟和谐的境界。在夫妻间不平等的婚姻关系中,女性内心中存有的自由期许逐渐化为泡影。畹君的丈夫荷生贪慕妓女迟云,执意纳妾,触碰了她坚守“一夫一妻制”的底线,在抗争无望后选择以死来维护个人的尊严。畹君的情爱观容不下“第三者插足于两好之间”[13],她的殉情不是为了维护礼教,而正体现出她反叛礼教的精神。吕韵清笔下的闺秀女性在顺从与反抗传统礼教的矛盾中挣扎,女性意识有所显露。
同时期大多数女性难以成功地反抗礼教,类似畹君遇人不淑的遭遇比比皆是。但吕韵清在《凌波阁》中设置了一对自由恋爱男女在阴间得以团圆的情节,女主人公史凌波与周涵秋一见钟情,因史母嫌弃周家家道中落执意不允,而周母知情后也勃然大怒,双方家长横加阻挠。涵秋南下后在母亲干预下娶大家女田氏为妻,凌波则“病骨缠绵,心事难医,和缓束手”[14]。当得知如意郎君另嫁他人后,她弥留之际疾呼:“生时束缚,死幸自由,魂兮有知,终偿宿愿”[14]。后涵秋携家眷归乡,凌波托梦于涵秋,涵秋因此患恶疾而终,二人在阴间得以永结连理。这样的情节安排,表明作者认识到自由婚恋在现实社会中面临诸多壁垒,但她期望女性能够奋不顾身地为自身幸福同强大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
在传统礼教与婚姻制度面前,以《玉梨魂》为代表的民初言情小说中的男女婚恋大多以悲剧收场。吕韵清在创作中希望女性勇于走出闺阁,摆脱不幸的婚姻。在她看来,女性只有具备独立意识,才能摆脱宿命的桎梏。传统女性在封建纲常伦理的灌输下,不自觉地屈从于男权,依附男性而生存,这一点在她塑造的具有自觉意识的闺秀女性身上仍存有烙印。佩秋闻听李起文对自己美貌的赞誉时,竟觉得“故妾生十六年,未闻有加予赞美者,究之貌之美恶,自亦茫然……不图天壤真赏,乃得斯人,知遇之感,不能自已”[10],在潜意识中认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必须得到男性的认同才能获得满足。《红叶三生》中的叶氏,体貌“翘入束笋的纤足,轻躯细骨,弱不禁风”[1],因而“凡饮食洒扫等事,在在需人”[1]。身体的柔弱决定了叶氏这类“大家闺秀”式女性并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她们必然依附男性而生存。小说《秋窗夜啸》中女主人公去凤因事母至孝,无法答应梅友鹤的爱慕与追求,于是设计举家迁徙,斩断爱根,不愿破坏倾慕对象的家庭。颇费心思的举动体现出她在性别平等的进步观念支配下,力所能及地处理好情感欲望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含有对男权中心话语的离心倾向”[15],进一步突出了作者呼唤女性独立、树立平等性别观念的意图。
女性的独立意识,主要表现为摆脱对男性群体的过分依赖,培养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自主能力,在社会交际中彰显自我价值。小说《彩云来》塑造了一位勇于走出闺阁、寻求独立的女性形象,作者塑造了一对性格鲜明的姊妹——絮才与影娥。前者与畹君相类,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结局;而影娥受姨母傅氏的教诲,深知“人不能处常无变,犹天之不能使四时皆春也”[18]。这样的独立精神,鼓舞她在傅姨的督促下勤练女工,技艺精湛。婚后,影娥同样遇人不淑,在面对丈夫的污蔑与羞辱时自缢未遂。种种遭遇促使影娥走出闺门,凭借自己非凡的苏绣工艺卖售蚕扇,自食其力。后来影娥不但出资安葬了死去的丈夫,而且承担了抚养丈夫与小妾儿子的义务,展现了民初时代变革下自力更生的新女性形象。
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吕韵清的女性意识也在不断地进步与发展。她早期创作的《凌波阁》和《白罗衫》期望借助佛教的因果观念来消解矛盾,存有一定的视“情”为“孽”的色彩。作者在不断的创作中逐渐认识到女性悲剧的现实意义,因而不再满足于对“有情人难成眷属”结局的浅层揭示,而是转向对女性如何培养独立自主意识、如何走出礼教与时代枷锁的深入探索,这对启蒙闺秀女性、呼唤时代新女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创作手法的现代性
民初“小说家在创作层面与晚清不尽相同,有着比晚清更强的‘拟古’色彩,似乎向传统小说回归”[4]416,这从民初文言小说数量远胜白话小说便可见一斑。但民初小说家普遍接受了清末小说家对西方叙事手法的借鉴与模仿,并自觉地运用到创作中,体现出“现代性”特征。
吕韵清小说中的叙述者,通常以女性为主体,使得叙述者与作者在性别上形成统一,进一步表明作者以女性为中心,在情感态度与道德立场上倾向于对女性意识的呼唤。
吕韵清小说中的叙述者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小说《我之新年》[17]以第一人称展开“自叙式”叙述,叙述者“予”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琴姑。在除夕之日,“予”与俾女蔻蔻依照风俗上供祭祖,当蔻蔻指向一俊秀少年的遗影(男主人公芹哥),并询问此为何者时,十余年的旧事涌上“予”的心头。“予”与蔻蔻虽名为主仆,但情同骨肉,不觉将隐藏在心中的秘密与痛楚向蔻蔻倾述,将自己与芹哥相识、相恋以及最终分离的过程娓娓道来。小说通过“予”讲“予”的故事,流露出自己错过良缘的无奈。在一个庆贺新年的喜庆日子里,叙述者“予”向倾听者“蔻蔻”道出自身的悲情遭遇,增添了感伤氛围。
民初的短篇小说主要以报刊杂志为载体,作者在创作时更注重情节给读者带来的真实感,见闻述录式叙述成为惯用手法。《金夫梦》中的叙述者包含两个“予”,即客观叙述者“予”和主观叙述者“予”(佩秋)。客观叙述者“予”在拜访亲戚机缘下,发现了一位容貌不凡、面容悲戚的女工,顿觉好奇,终于寻求到详谈机会。主观叙述者“予”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向其倾诉,并在叙述末尾感叹:“呜呼,一念虚荣,六州错铸。此妾两年来痛史,今之忏悔录也!愿君著成篇什,以告当世闺人,毋蹈妾之覆辙也噫”[10],并在与客观“予”接触时发出“君真自由神,较妾之寄人篱下,其苦乐不可同日语”[10]之感慨。与传统小说由全知叙事者在文末发出劝解、警世之语相比,由主观叙述者亲自道出忏悔与感悟,更能给读者带来震撼。
此外,吕韵清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能够巧妙运用倒叙、插叙等手法,增强了故事的曲折性。她善于设置悬念,如小说《白罗衫》以一件珍稀的绣品引发客观叙事者“予”的好奇,来到钵罗庵向了公探寻隐情,但了公以实情凄惨而不忍向女士道出的缘由拒绝面陈。“予”在仔细摸索绣品的过程中,发现了主人公赵武的绝笔书信,通过这一封书信才知与赵武和许贞媮的凄惨爱情有关。“予”进一步通过追问知悉内幕的宋媪探得事件真相,并将赵武因何被害、许贞媮归乡后殉节等情节和盘托出。作者通过第一、第三人称的交替运用,逐层推动情节开展,通过插入书信体引入中心情节,并借第三人称叙述者将事件补充完整,达到“醒阅者之目”的意图,展现出在叙事时序层面求变的欲望。
从运用浅近文言,惯于在小说中插入诗词来看,吕韵清的小说“还是比较接近传统小说的特征”[18]232。即便在叙事模式层面,也不乏类似“韵清曰”的全知评述,体现出作者在限制叙事与全知叙事之间游离的特征。从叙述者多元化、追求叙事时序变化角度来看,吕韵清在创作手法层面具有革新意图,体现出“现代性”特征。
四、结语
吕韵清在《七襄》《申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八部短篇言情小说,表明作者站在女性群体立场上审视转型时期闺秀女性在婚恋与生活中面临的重重困境。作者在一幕幕的悲剧书写中,认识到独立意识对于女性的重要价值;而言情与社会相交织的主题模式运用,印证了20世纪初女性小说家不再满足于反映封闭的闺阁生活,开始关注更为广阔而复杂的现实社会;创作手法的革新意识体现出“自觉意识”,论质论量都堪称20世纪初女性小说家群的代表之一。她的小说创作并非单一地进行“模式化”复制,而是不断在思想主题、艺术手法层面寻求突破,所展现出的“现代性”符合近代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