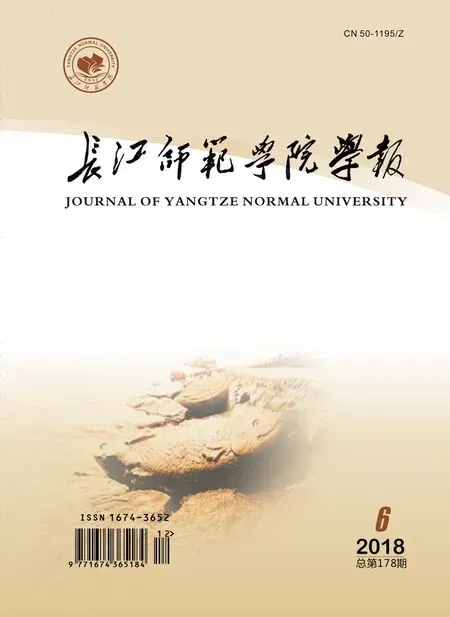倾听与理解:隐性知识视角下的师生交往审视
孙发有
(广州工商学院,广东广州 510850)
交往是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的现象,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在教育领域,交往更是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叶澜曾提出教育的“交往起源说”:“人类的教育活动起源于交往,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人类一种特殊的交往活动。”[1]把教育界定为一种交往活动,彰显了教育的本质,揭示了教育的本真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教育活动中“目中无人”的现象导致师生交往品性的迷失。在主客二元对立观念的影响下,教学活动常以直接传递显性知识为任务,教师掌握着课堂的话语权,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学生则成为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以致教育活动沦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控制和训练,师生心灵之间交往的路径遭到阻隔。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素质教育的推进,“将课堂还给学生”的呼声高涨,以扭转教师话语霸权过度压抑学生精神空间的现状。但这种主张又容易走向“学生中心”的极端,消解教师在教学中应有的作用和责任,导致师生关系走向放任自流。
无论是“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都是主客二元对立思维观念下的产物,忽视了交往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导致师生关系的对立和异化。从交往的观点来看:“交往是作为主体的人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行为,以客体的性质所参与的交往不是真正的交往。”教育在本质上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特殊交往活动[2]。教育活动中师生关系的和谐构建必须回归到交往的本质。那么,何以达成这种交往?隐性知识理论启示我们从倾听与理解的角度出发,以师生彼此的隐性知识为基础,重构师生间的交往关系,回归教学交往品性的本真。
一、倾听:隐性知识的存在期待师生交往中的倾听
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与显性知识相对,又称为缄默知识、默会知识或意会知识[4],这一概念是英国物理化学家、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首次提出的。波兰尼指出:“人类有两种知识。通常所说的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地图、数学公式来表述的,这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例如我们有关自己行为的某种知识。如果我们将前一种知识称为显性知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后一种知识称为隐性知识。”[3]有学者指出,显性知识为“表、形、毛”,隐性知识为“里、意、皮”,两类知识构成“表里”“形意”“皮毛”关系[4]。在人的知识结构中,显性知识可以说是“冰山的尖端”,隐性知识则是隐藏在冰山底部的大部分。具体到师生交往领域,隐性知识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个体性。学生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已经具备了彼此各异的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与他们个人的生活经验、知识储备、情感态度、兴趣爱好等密切相关,构成其独特的认知资源。二是相对性。师生双方是不同的交往主体,其隐性知识的差异性构成了交往主体的异质性,从而使得交往成为必要。三是不可教性。隐性知识不同于显性知识,它不能有效通过教师讲解、书本学习等方式直接传递,而只能靠个体的主动建构与沉淀。四是情境性。隐性知识关涉个人的经验、情感、知识等,往往是在具体的情境中不自觉地获得的,只有当类似经历的情境再现时,其隐藏在脑海深处的隐性知识才可能被激活。五是先导性。用波兰尼的话说,隐性知识是显性知识的根源,是显性知识的“向导”和“主人”,没有这个“向导”,人的思想就会迷失在大量的显性知识的“丛林”中。在教学中,显性知识的学习只有与学生自身的隐性知识相契合时,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隐性知识在教学活动中是大量存在的,且对人们的行为实践发挥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已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但由于隐性知识的上述特征,它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隐蔽性,在现实教学中隐性知识虽然无处不在,但教师一般很少能主动意识到并重视这些隐性知识。相反,显性知识则可以被清晰地表达和快捷地传播。在我国,由于显性知识与应试教育的某些要求相契合,一直成为课堂教学的主宰。在这种知识观的影响下,我们对教学的认知仅局限于显性化知识的传授与获取。在应试教育观念下,这些显性化的知识被进一步浓缩为一个个“知识点”,强化为学生获取分数的外在符号,知识本身的意义和学生成长的关系被忽视,致使师生之间的交往沟通也因此日益萎缩而仅依附于应试性的知识传授之上,彼此虽共为教学一体,但心灵却相距甚远。
教师不能仅关注学生接受显性知识的多寡、分数的高低、课堂秩序是否整齐划一、学生的回答是否符合标准答案,更要认识到隐性知识的存在价值及其对显性知识学习的引导和影射作用。教师要关注每一位学生,真诚倾听学生的心声,探寻学生的隐性知识状况。首先,隐性知识是学生与生俱来的,与学生的个人成长经历、价值观、兴趣喜好等紧密相连,对学生来说有着无比的亲和性和深刻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根据头脑中已有的认知主动获取知识,并对新学习的知识进行自我建构和加工。学生原有的知识多来自日常生活中无意识获得的隐性知识,它是新知识学习的基础。若教师在教学中能主动意识到这一点,在课堂中认真倾听学生的思想和言说内容,帮助学生打开“话匣子”,激活学生内在的隐性知识,并与新知识学习相结合,教学将取得更好的效果。其次,关注隐性知识意味着对学生“整体人”的关注。学生都是带着自己的知识储备进入教育活动之中的,他们在课堂上的言说和行为表现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行为背后就有一套系统知识基础的存在”[5]。教师若能真诚倾听学生,听其言,观其行,思其想,在倾听中洞察、把握学生的隐性知识,不仅能够了解隐藏于学生言行背后的知识状况、真实想法,以整体的视角去了解学生,而且能够打破师生之间的心灵阻隔,拉近彼此之间的情感距离,营造一种宽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二、倾听与理解:师生交往中的意义创生过程
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影响下,教师掌握着课堂的主动权,“独白”取代了“对话”,充斥在师生交往过程中的是教师的话语霸权和独白表演,学生只是配合演出的“群众演员”,是教师指令的服从者、接受者和执行者,师生之间缺乏理解,教育交往的本真意义被消解。因此,搭建师生之间沟通的桥梁,重构师生之间的交往本真,实现师生交往从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交往的转变尤为重要。
“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我与你)的对话与敞亮。”[6]对话是教学交往的具体样态,唯有对话才能架起师生之间沟通的桥梁,直抵师生的心灵深处。教学对话“不仅体现在教师对于知识的讲解和灌输上,更体现在教师对于学生思想及言说内容的倾听上”[7]。通过倾听,教师可领悟到每个学生首先是一个生命的存在,不是物质或观念的存在,相应地就要施之以对应于生命而不是对应于物(如机器)的教学方法[8]。也就是说,倾听使得师生双方的主体地位得到凸显,彼此开始以生命理解的视角考量,这迈出了倾听的第一步。
倾听是对话的前提,是通向理解的路径。由倾听达成理解需经历两个阶段。一是隐性知识的激活,二是新的隐性知识的生成与获取。隐性知识的激活离不开彼此的真诚倾听,只有在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每个人身上所潜藏的隐性知识、认知情感及态度立场才会伴随着他自身的语言系统显现出来。因此,教师作为倾听者应提供给学生言说的机会,倾听学生的心声,让学生从“失声的集体”中解脱出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我见解。教师在激活学生的隐性知识前提下,洞察出学生已有的知识、观念、习惯、兴趣等与新的学习活动的联系,及时了解学生欲求,并根据了解到的情况适时对教学活动作出调整和改善。
新的隐性知识的生成或获取既是学生根据自身的隐性知识对新知识进行评价、吸收的过程,也是丰富自身隐性知识并使之显性化进而实现认知发展的过程。达克沃斯认为:“课堂教学必须基于每一个学生的独特性之上,而学生的独特性集中体现在每一个人的观念的独特性,教学的目的或价值就是帮助学生在原有观念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更精彩的观念。”[9]前言在课堂教学中,由于学生生活阅历的缺乏以及思想观念的认知偏差,对事物的认识有时是零散、片面甚至幼稚的,但正是这些不成熟的片段思维构成了他们未来成长的基础。因此,教师作为倾听者要认真倾听学生的表达,不仅要倾听学生的言语,领会其思路,更要洞察学生的非言语行为,善于捕捉每一个细节,把握学生的弦外之音,帮助学生实现认知上的改变和意义的生成。例如,语文学习中的语感就是一种典型的隐性知识,学生在长期的语文学习和生活积累中不自觉地习得了这种知识。在语文学习中,一旦对“语感”有了“顿悟”,自然会产生“本来如此”的感觉,仿佛不用解释的数学中的公理。但此时的语感尚处于缄默的状态,对学生而言“说不清道不明”,此时,教师如能及时倾听学生,在学生原有语感的基础上,给予引导、点拨、升华,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像99℃的水需要多一点火候才能沸腾,教师在倾听中的点拨与启发的价值就在于此。
三、隐性知识对师生交往的启示
(一)深化对隐性知识的认知
学生在进入新知识学习时已经是具有一定阅历、知识储备和思维能力的个体,具有表达自我的意愿和能力。以往我们习惯将学生的心灵视为一片白板,而将教师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角色来固化教师形象。这固然缘于人们对教师形象的敬仰与期待,因为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在师生关系中更是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但这种惯性思维也导致学生对教师的盲目崇拜和顺从,遮蔽了学生丰富的生命形态,泯灭了学生的自我见解和思想创见,引发学生集体的失声和思维的懈怠。
隐性知识论认为,个体都包含着大量难以言说的隐性知识,犹如大树之根,根植于个人内心深处并深刻影响个人的认知行为。在教学中,教师应当转变教育观念,不能狭隘地认为书本知识、可教的知识才是知识,而把隐性知识看作无关紧要的东西予以忽视。教师应在理念上和行动中把隐性知识纳入到教学的视野,并给之接受、尊重和理解;教师不应把隐性知识当作干扰教学活动正常进行的障碍而忽视,应将隐性知识作为学生思维的出发点和师生交往的认知基础,并使之成为一种有重要价值的课程资源加以充分利用。因此,教师应当设法创造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给予学生足够的话语权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思维空间,使学生的思维和想象能够自由驰骋。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的隐性知识才可能被激活并参与到师生的对话交往中来,这不仅有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更能拉近师生之间的情感距离,达成教学中我们所期待的师生之间“认识的深化、思维的碰撞、情感的共鸣”的状态。
(二)构建“倾听型”的教学情境
教学中的倾听是师生展开本真交往的前提,但在以显性知识至上为原则统摄下的教学中,师生之间的倾听是单向的,隔断了彼此心灵沟通之桥梁,导致师生关系的异化。一方面,学生摄于教师或教科书的权威不敢有自己的“异见”,不敢对学习的知识加以审视、批判,沦为等待知识灌输的“容器”;另一方面,教师为了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无意中放弃了对学生个性化认知的关注以及对教学的反思,课堂成为习惯性的搬运知识的场所。这样,反映学生真实认知的隐性知识这一宝贵的教学资源不但没有得到充分地利用,有时反而无意识地成了教学的障碍,因为,只有与新的学习活动对称且契合的隐性知识才会被教师认可与接受,而那些不对称的、背离的隐性知识很可能被视为对教学活动的干扰而被排斥在教学交往活动之外。
隐性知识论从一开始就将矛头指向“显性知识至上”的认识论教条,力图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启示我们以倾听作为沟通理解之途径,消除师生交往路径的迷失。因此,革新传统教学方式,构建“倾听”的教学情境尤为重要。首先,倾听是一种平等的行为。师生人格上的平等是倾听展开的人本基础,教师对学生的关注与尊重是倾听的情感基础。教学中教师要认真、耐心地聆听学生的言说,善于发展学生言语中内含的隐性知识,并给予积极的反馈和鼓励,使学生意识到自己是被尊重、理解和信任的,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平等的、受重视的个体参与到对话中的。这样,学生才没有心理负担而乐于与教师交往,从而敞开自己的思维、情感,使得对话流畅、有效地进行下去。其次,倾听是一种主动的行为。一方面,受传统学习习惯的影响,学生一般不主动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教师应主动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创设学生轻松、愉快表达的氛围和机会。另一方面,倾听也需要学生主动的作为。课堂上虽然大多数学生能做到认真的“倾听”,有些学生甚至认真地做着课堂笔记,但他们大都追求的是能“记住”或“复制”教师所讲的内容,没想甚至不敢对听来的内容加以思考和判断。主动的倾听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不仅在于听到了什么,更在于倾听者对内容的理解和思考。课堂教学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师生之间围绕某一文本或主题展开的交流对话,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如果教师只倾听学生,而没有有效的反馈,师生交往必将无法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也会弱化学生表达的信心和勇气;如果学生不主动敞开自己的心扉,并对教师的反馈进行自我加工、理解和判断,师生的对话交往也只能是低层次的,难有深层意义的隐性知识生成。
(三)追求“理解型”的教学交往
传统教学认识论中无论“教师中心”还是“学生中心”,都有一方压制另一方、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并没有使师生关系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教师中心说”以教师直接传递显性知识为己任,学生被认为是等待接受的知识“容器”或等待加工的“标准零部件”,教学中忽视了对学生的倾听和关怀,“对学生的影响往往也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心灵之间却隔着遥远的距离”[10];“学生中心说”怀着彰显学生主体性的目的却容易导致教师的教学主导作用被严重弱化,在课堂呈现出“多者言说”的热闹景象中,造成“假说”“假听”现象的盛行。
教师面向的不是抽象的学生群体,而是向着当下教育情境中的具体个人[11]。毕竟“知识的学习最终乃是为了成就个体生命的健全,而非让个体沦为知识的奴隶”[12]。教学活动应关注的是对学生灵魂的唤醒和鞭策,从而把知识学习的过程变成“敞亮个体生命,也即开启个体智识空间、启迪个体探究欲望、进一步激发个体求知热情的活动”[12]。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说:“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在它是一个人格心灵的‘唤醒’”[13]。教育不仅是一门知识之学,更是一门成人之学,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教师的职责不仅在于“教书”,更在于“育人”,不仅在于“传道”“授业”“解惑”,更在于成为学生的“精神导师”。我们对教育的理解离不开对个体人的理解。教育活动不仅仅指向师生间知识信息的简单传递,而是一种对话性、理解性、创造性的活动,是师生之间言语、动作、思维、情感的多维互动,并最终指向的是师生之间精神的相遇、人格的感化、情感的共鸣。教育活动中只有教师不再把学生看作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作为具体情境中的具体个人来看待时,他才可能与学生发生“相遇”,进而去用心去认识理解一个真实、鲜活的个体。这就要求教师要认识、尊重并重视学生的隐性知识,和学生建立一种“学习共同体”关系,在这种“学习共同体”关系下教师不再以自己的判断代替对学生的理解,教师在教学中不再是“独奏者”而是“伴奏者”,教学成为师生双方精神世界的相互敞开,理解与接纳过程。它最终指向的不仅是理解他人,更是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进一步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样,教学中师生它不要求一方把观点强加于另一方,更不要求卑微地接受对方的观点,而是双方“以辩证的思维、积极的心态使双方实现自身立场的改变,进而获得一种共同理解”[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