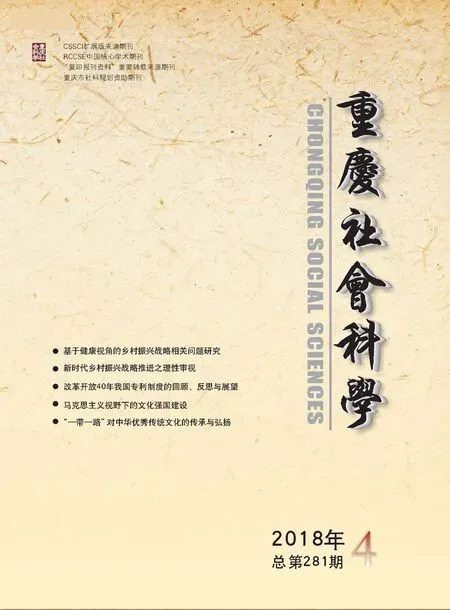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功能
李淑蘋 周昭根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 510632)
任何政权都具有一定的功能,而不同的政权,其功能也有所不同。在旧政权被摧毁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对诸如镇压人民反抗、以封建伦理道德约束人民行为等功能予以坚决的摒弃。同时,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还努力使自己肩负起更多的责任,给政权赋予了新的内容和使命,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调动一切力量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此,从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四个方面探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所具有的功能。
一、组织群众抗战、保障人民权利的政治功能
旧有政权的政治功能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对下实施控制。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功能则是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战,对汉奸反动派实行专政,保障抗日群众的各项权利,并增强民众关心国家、参与政治的意识。
(一)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战
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正式建立之前,华北地区已有抗日救亡团体对民众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和动员。他们“尽量把亡国亡种、沦为殖民地的可怕前景告诉民众,唤起民众的爱国情绪”[1]。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第二战区半政权性质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也曾担负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紧急任务。然而在日军大举进攻、旧政权土崩瓦解、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要真正做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首先得安定人心稳定情绪,使群众摆脱无政府无依靠的恐慌和不安。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就“如同树起一面大旗,使人民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聚集在这面大旗之下”[2]。这就为更好更有效地动员组织群众提供了前提条件,因为“政府——在老百姓的眼里,是很有权威的”[3]。
与国民党旧政权拒绝动员民众参加抗战不同,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后,为使千百万民众投身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滚滚洪流之中,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响应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号召,规定县区村各级政府主要官员皆负民众动员工作之责,从组织上为动员民众提供保证。第二,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将政府施行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合理负担、废除苛捐杂税、改善民生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同抗日战争的大局联系起来,同“打鬼子求生存”[4]联系起来,以此调动群众抗日救亡的积极性,使“拿起武器,保卫家乡”的口号成为群众参加抗战的自觉要求和行动。阜平县的农民就喊出了要打日本、要吃饭、要下租子(减租)的口号,冀西地区七八个县一下子就有15 000多人参加游击队,减租的结果比空洞的宣传更有效地动员了广大农民参加抗战。第三,通过扶持群众团体,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曾明确规定:一切抗日人民有结社自由,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负有掌理社团事宜的责任。陆续成立的工、农、妇、青、童、文各界抗日救国会“以争取民族的解放为宗旨”[5],成为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直接承担者,政府的职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们来实现的。可以说“晋察冀边区一切工作的计划和布置都要经过他们的两手,通过了他们而传达到一千二百万民众,推动一千二百万民众”[6]。
(二)对汉奸反动派实行专政
晋察冀边区政权的抗日民主属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对汉奸、特务、反动派实行专政。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初,旧的警察制度以及机构被取消,辖区内各县普遍成立人民武装自卫队,临时担负惩治汉奸、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1939年6月,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成立,随后各行署、县、区、村先后设置了相应的公安局、公安科、治安委员等机构和岗位,冀西部分农村还一度建立了政治警察制度。各级公安机关是政府的职能部门,除依照边区施政纲领有关“肃清一切破坏团结抗战,破坏边区的特务、奸细,打击妥协投降派”和“对死心塌地的汉奸,严于惩处”的规定,严格履行对汉奸、特务、反动派实施打击的职责外,还注意发动依靠广大群众合力锄奸。1941年4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制定颁布了《公安局暂行条例》,对边区公安局的性质、行动、工作、权限和机构设置等做了明确的规定。此后,边区公安部门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保障抗日群众的各项权利
在对汉奸特务实施专政的同时,抗日民主政权还对抗日各阶级各阶层群众的各项权利予以保障,并尽可能地给人民提供参政议政的机会,提高群众对国家命运的关注程度。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缺乏鲜明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他们本能地起来进行了一些抵抗,但还不可能把这种抵抗的意义上升到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高度,更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的一分子有参战的义务,更有参政的权力。直到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的事例才逐步提高了广大群众对国家命运的关注程度,增强了其参政议政的意识。
二、协助抗战的军事功能
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政权必须肩负起一定的军事职能。在晋察冀根据地,正规战役由八路军充当主体,但补充部队兵源、组织地方武装、进行战事协作等任务则由政府来完成。
(一)补充部队兵源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战事紧急,八路军主力部队兵源又严重不足,因此在扩军过程中,旧军队的散兵游勇、兵痞流氓、亡命之徒等均有混入八路军的。而普通老百姓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下,很少主动参军。随着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征兵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1940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双十纲领》中明确提出:“扩大边区人民子弟兵,充分保障其给养和经常的人员”[7]。
为了保证兵源,边区政府首先在组织上予以高度重视,在各级政府中设立相应的部门分管兵役工作。边区由民政处分管,各县有专门的人民武装部掌理,村归人民武装中队部负责。除专司兵役的各部门外,晋察冀各机关各部队各群众团体实际上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兵役工作。其次在兵役制度上进行改革,逐渐废除旧的封建募兵制,推行志愿义务兵役制。1942年1月,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志愿义务兵役制度实施暂行办法》,规定:凡本边区之男子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者,均有服兵役之义务;志愿服兵役者,应依本办法报名登记,听候征召入伍。新兵役制的规定不仅有利于杜绝拉兵、买兵、派兵等不良现象,而且从群众心理上提高了当兵入伍者的地位,因为应征者在志愿的前提下,还得通过一定的审查,“听候征召”,这就在保证兵源数量的同时保证了兵源的质量。最后,结合新兵役制度,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利用墙报、壁画、报告、演剧、开会等各种形式,深入广泛地进行宣传,形成群众动员的热潮,以保证动员计划的完成。
(二)组织地方武装
除了动员群众参加主力部队外,晋察冀边区政府还组织了自己的地方武装,主要有属于各县公安局的警卫队、正规化的地方军、接敌区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产的人民武装自卫队。警卫队人数不多,主要活动在城镇,以协助公安局清查户口,除奸缉匪,从事敌工,维持后方治安。地方军和游击队均为脱产的武装组织,地方军较游击队规模更大,裝备更好,机动性更强,与正规军配合作战较多,后期多转化为正规军,如初期的马本斋回民支队等。游击队多是以县为组织单位,区域性较强,以定期集合与分散活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游击作战,同时也在本县区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地方军与游击队是主力部队的重要助手,人民武装自卫队则是乡村性自卫组织,最为普及,建制也最完善。1939年9月颁布的《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自卫队暂行组织条例》规定:边区“凡年在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之人民,无残废疾病者,不论男女均得参加自卫队”[8]。16至23岁的队员编为青年抗日先锋队,是自卫队中的骨干力量和特殊力量,24至35岁的队员编为模范队,另外还有专门的妇女队。
在组织系统上,边区设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专署设区队部,县设总队部,区设大队部,中心村设中队部。最初,各级自卫队隶属于各级政府,各级自卫委员会由各级行政长官、群众团体之武装部长及其他代表组成。制度日益健全后,各级自卫委员会设队长、政治指导员、军事干事、政治干事、妇女干事、总务干事,由各级自卫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各级政府指挥下进行工作。到1941年,边区人民武装自卫队已具相当规模,其中以青年抗日先锋队和模范队为主体的民兵总数达30万人。再行整顿后,民兵的军事性和集中性大为加强,成为活跃在广大乡村田间的劳武双料能手。每当有战事时,民兵在各级政府的组织下,随军担任向导、侦察、破路、运输、联络、救护、转送伤员等任务,以各种方式配合主力作战。
(三)进行战事协作
在战斗中,各级政府还组织广大群众协助作战。1938年春,平汉、津浦线的大破击战时,就有好几县的群众都参加了破路和搬运战利品。百团大战更是军政民配合的典范,仅晋中区就动员了10万余群众参加破路,冀东区动员了8万群众,同时破坏七八个县的公路和电线,正太沿线动员了2万多民兵,编成50个大队,在前线与主力部队并肩作战。可以说,晋察冀八路军取得的所有辉煌战绩,都是晋察冀军政民合作的结果。
三、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功能
最早出现于敌后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国民政府虽然承认了边区政府,但在经费、枪支、弹药和物资方面,边区政府得不到任何接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由于自身经费的短缺,客观上也不可能大力帮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本着既要有利于抗战又要有利于民生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保障军政供给
晋察冀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伊始,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保障军政供给。虽然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时,根据地内的八路军只有几千人,各级政府机构人数也不多,但随着八路军队伍的迅速壮大和各级政权的进一步完善,军政供给的数额越来越大。除了有限的外援和少量的缴获日、伪敌产以及自力更生外,新生的抗日民主政府主要靠合理负担的办法,取之于民,解决供给问题。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最早实行合理负担的当推晋察冀边区。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阎锡山就在山西提出了合理负担的主张。根据地初创时,晋东北18个县先后在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实施合理负担。1938年3月,边区行政委员会按照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废除一切苛杂的间接税,建立合理的直接税”的建议,公布了《村合理负担实施办法》及相关政策,对合理负担做了严格的规定,废除战前近30种苛捐杂税,统一各种赋税,一律按村户“分数”负担。每家每户的负担额是根据其财产、收入和消费的情况,依照统一标准进行计算,再经村评议会审核确定,每年两次进行征收。这种富者多出,贫者少出或不出的办法,使负担面扩大到50%左右,既消除了过去穷人既出钱又出力的不合理负担现象,大多数贫农、雇农负担减轻或免于负担,又纠正了部分地区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富户负担”、擅自摊派的偏向。在村合理负担普遍推行并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平山、唐县等地又开始实行县级统一合理负担,1941年进一步发展到全边区实施统一累进税,使各阶层负担更为合理。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初,抗日军队的给养是就地筹划,全边区并不统一。边区财经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后,边区政府开始承担各抗日部队军费统一发放任务。在粮秣问题上,边区政府先后采取过县级合理负担、公债购军粮、发给军队现款自行解决等办法,但由于战时的特殊情况和边区内各县经济发展不平衡,上述办法实施起来均存在诸多不便。为从根本上解决抗日军队的粮秣问题,边区行政委员会于1938年秋公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条例》,规定以合理负担的原则在晋东北和冀西征收救国公粮,“用以供给军食,优待抗属,救济灾荒,有余作为政府收入之一部”[9]。征收办法以各家的全部收入(包括农业、副业、畜牧业、工商业、放贷业等)折米计算,按百分比递增累进。救国公粮作为一种税收,与一般税收最大的区别在于征收之后的储存保管不是集中于政府手中,而是分存于各村各户。军队如需用粮,可随时随地用边区行政委员会所发之军用粮票,通过区公所军用代办所向各村领用救国公粮。这种独特的财经制度是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创举,它妥善地解决了坚持敌后抗战的军粮供给问题,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兵马任动粮草随行”,既方便了军队也便利了群众。
(二)组织发展生产
晋察冀边区政府是边区人民的政府,因此在适当征收赋税、取之于民的同时,还特别注意以政府行为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尤其是发展边区支柱经济——农业。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实施减租减息,帮助农民从繁重的地租和高利贷盘剥中解脱出来。至1940年6月,仅北岳区两个专区就减租614.5万斤,四个专区减息32.6万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
第二,把握住生产的关键环节,不失时机地组织并协助农民的耕种与收获。从1939年起,晋察冀各级政府便按季节成立春耕、护麦、护秋等专门机构,统一组织生产。每到春耕时节,边区政府或是召开联席会议,或是制定有关条例,直接推动群众生产。对种子、农具、耕畜有困难的农户还贷款帮助。1940年春,边区政府对北岳区20个县提供种子借贷4767石,补充耕牛6 921头。夏收和秋收往往是敌我双方田间地头非军事对峙最激烈的时候,边区政府就将各级政府机构的干部分配下基层,组织群众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武装保卫夏收秋收,并指定干部负责收获后的坚壁工作。1943年秋收时,完县地方政府动员了500名民兵,七天中抢收了1 300亩庄稼。
第三,鼓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垦荒单行条例》《垦修滩荒方法》,规定新荒地和连续两年未耕种的熟荒地,农民可以无租耕种,土地所有权归承垦农民所有;滩荒地垦修先考虑土地所有人,土地所有人不能垦修者,则由地方政府招人垦修。在政府的积极鼓励下,广大农民及部队和政府机关人员纷纷垦荒,使耕地面积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春耕时边区共开荒3万亩,1938年至1939年仅平山等9县就垦荒15 000余亩,1943年新熟荒共开垦53万亩。抗战八年晋察冀边区共开荒120余万亩,修滩地25万余亩,耕地面积的扩大直接增加了农业生产总收入。
第四,在巩固区大力提倡和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并改进农具,在条件容许的情况下,还组织科学实验,以增加粮食产量。如晋察冀农林牧植局就曾通过实验使小麦产量增加了10%。
第五,民办公助兴修水利,有计划地凿井、开渠、修堤。1940年春,边区政府通过银行向五台、盂县、定襄、忻县发放水利贷款,共修水渠20条,灌溉农田13 385亩。1941年4月冀中滹沱河长堤工程竣工,河间等14县水患威胁大为减小。1944年平山一县就开渠65条,第一、三两区的8个县凿井4 046眼。水利的兴修,水浇地面积的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第六,通过拨工互助和合作社的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中国农民历来习惯于分散的个体生产方式,但在战争造成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这种分散的力量往往无法保证生产。在后来的生产实践中,农民们逐渐意识到要克服战争造成的劳动力困难,就必须组织起来。在1943年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阜平等地出现了拨工互助形式,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到1944年,边区许多群众组织起来,全区20%的人口参加了 28 000个拨工组,劳动效率一般都提高了 30%。在实践中,农民还将拨工互助的规模扩大,由小组而分队而大队,再至劳动互助合作社。在游击区和接敌区,主要是劳武结合,民兵掩护和协助群众生产。农民组织起来后,解决了部分地区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提高了劳动效率,节省了劳动时间,还互助互学,提高了生产技术。总之,在边区行政委员会的领导和帮助下,晋察冀边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既改善了人民生活,又为抗日战争提供了丰厚的物资基础。
(三)进行灾荒救治
古今中外皆有灾荒,因此救灾赈荒就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人民除了遭受战争的创伤外,还倍受自然灾害的侵扰。据不完全统计,自1939年始,晋察冀边区共发生特大重大的水、旱、蝗、雹、震等灾害十几次。1939年特大水灾时,日军还趁机在冀中决堤128处,使灾情加重,累及30余县,近万村庄,灾民300余万人。1945年,冀东同时遭遇旱、水、雹、蝗、震数灾,100万亩土地绝收。另外,由于日军在根据地内散布毒菌,喷射腐烂性毒瓦斯,致使霍乱、伤寒、鼠疫、疟疾等疫病流行,军队和老百姓罹毒染疫而死亡者甚多。1939年8月,一个月内华北地区因霍乱伤寒而死亡者就达四五万人,晋察冀边区死亡者也不在少数。所有这些灾害对于生产力低下且正在遭受日军“扫荡”包围的晋察冀根据地人民,尤其是极端贫困的北岳区人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为了帮助灾民战胜自然灾害,度过难关,恢复和发展生产,晋察冀边区政府认真履行政府职责,根据《双十纲领》第十一条,各级政府都相应地成立了救灾委员会,积极采取各种救灾措施,减免灾荒所造成的损失。第一,灾荒发生后,县区两级干部立即深入调查灾情,根据情况减免灾区公粮的征收额。第二,“在‘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下,进行救济活动”[10],在重灾区无偿发放救济,分设粥厂以济灾民,政府拨款赠医施药。如1939年特大水灾发生后,边区政府当即拨款10万元紧急救济,次年又赈济100万元帮助灾民度春荒。1943年大旱之后,边区政府发放了60余万元救济款,4 000大石救济粮,进行紧急赈济。同时拨出300万元专款修建被毁房屋,数十万元添置灾民衣被,300万元为灾民购置药品。第三,为灾情较轻的地区贷粮贷款,解决种子、肥料、牲畜,帮助灾民恢复生产,修复被洪水冲毁的农田。如1940年春,边区政府仅为头年遭水灾的北岳区就贷款300万元,借贷种子4 767石,补充耕牛6 921头、驴2 902头、骡1 127头,帮助灾民完成春耕。据不完全统计,北岳区20个县修复滩地14万亩,恢复被冲毁土地的94.5%。第四,号召军政机关节约,提倡群众互助。1939年8月,边区行政委员会曾对军政民每人每天节约粮食数做过如下规定:部队官兵1两,政府和群众团体工作人员4两,一般民众2两,特别劳动者1两。节约之粮均用于灾民。1942年至1943年的大旱中,边区人民自动募集互助,仅冀西群众就募集粮食8 377大石、糠1 693石、米200余石、菜3 004斤、边币20余万元。有的开明绅士也主动募捐,1941年繁峙县20余名开明绅士组成“募捐救灾委员会”,带动全县地主富农捐出小米300余石、边币300余万元、麦种50余石,对解决春荒起到了一定作用。
以上临灾而救的措施虽是必要的,但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因此边区政府在救灾的同时,注意引导群众生产度灾,生产自救。1939年水灾时,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了“灾民工作介绍所”,安插灾民参加地方工作,从事生产劳动。1943年,边区政府贷款210万元,帮助重灾的冀西三个专区发展家庭副业和运销业,组织群众割荆条、挖药材、打猎等,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灾民的衣食问题。另外,边区政府还注意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力争防患于未然,如禁止开垦超过三十度以上的荒山,以优惠政策鼓励修梯田,提倡植树造林,筑堤治河兴修水利,耕三余一、以丰年备荒年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民灭蝗。近代历史上也曾以“灭蝗”作为人工除害的手段,但实际上对于“蝗灾”的救治根本无济于事。然而,1944年和1945年发生在晋察冀根据地的蝗灾却有着与近代历史上的“捕蝗”完全不同的结果。边区政府调动军政民力量齐动员,对群众灭蝗还给予奖励。阜平县长亲自带头,冀西14县约有60万人参加打蝗队。1945年冀西3个专区灭蝗38万余斤,挖蝗卵4万余斤,基本控制了灾情的发展,减少了蝗灾的危害,从而也就稳定了人心。
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灾荒救治措施,因此晋察冀根据地虽灾害不断,农业生产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但并没有导致人口锐减、农业生产凋蔽、民变骤起、社会动荡的严重后果。相反,政府的帮助不仅使广大灾民的生活得到妥善安排,生产迅速得到恢复,1940年个别地区还超过灾荒前的水平。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形象因此更加完美,根据地更具吸引力,甚至连一些敌占区的灾民都到根据地参加生产自救。
四、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功能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教育是与抗战建国密切联系的。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时,教育处作为四大处之一被单独设置,以后随着各级政府的建立健全,教育机构也日益完善。行署有分管教育的干事,专署和县有教育科,大县还设有督学,区有教师助理员,村有教育委员。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正是通过这一套完善的教育行政系统加强了对边区教育事业的领导和管理,发挥着特有的教育功能。
(一)为抗战培养各种人才
早在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决议案》中就特别规定了战时文化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加强抗战力量;造就专门技术人才,建设抗战时期的各项事业;培养热情的新青年,扩大民族革命的基础力量。而晋察冀根据地抗战建国的急需人才,主要是通过包括高等学校、中学、各类干部学校和培训班等各种形式的干部教育来培养。
在晋察冀的土地上,先后有过四所战时非正规高等学校:1939年2月,由延安迁至河北灵寿的抗大二分校主要是培养敌后抗日军事人才,到1943年初共培训了10期学员。1939年7月在延安成立后转到冀西的华北联合大学是边区的最高学府,主要培养适合敌后工作的、有坚定的政治方向、高尚的革命品质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党、政、文教、民运各方面的高级干部。华北联合大学在1941年2月与抗战建国学院合并,鼎盛时期下设社科、文艺、工人、青年、师范、法政、群工等学院,教职学员4 000多人,截至1942年底培养了3 000多名干部,并先后为边区七所中学配备了主要干部。1939年秋,边区政府创办了抗战建国学院,主要是轮训在职干部,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前,共培训了区政助理、税收、银行、合作事业、财政、秘书、妇女等各类行政和经济建设人才1 000余人[11]。1945年5月,冀中行署还曾开办过行政干部学院性质的五一学院,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700余名学员中有不少人参加了后来的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为了解决失学青少年继续学习和基层干部培养提高的问题,晋察冀边区政府从1939年开始,先后在各专署开办了9所民族革命中学和抗属中学以及抗大二分校附中。此时边区中学的目标已“不是为了升学”[12],而是为了在以后能补充边区政府、军事部门以及生产单位对人员的需要。此外还有白求恩卫生学校、军政干部学校、群众干部学校、农业职业中学、蒙藏学校等中等学校以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晋察冀边区的干部教育在华北敌后根据地中成绩最为显著,不仅解决了基层干部短缺的问题,还为边区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专门人才。1939年至1940年,北岳区和冀中区通过专区和县办培训班以及在中学附设培训班的形式,共培训了1万余名教师,补充了边区师资,推动了晋察冀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扩大教育面
晋察冀边区多是贫瘠的山区,历来文化落后。冀西山区许多村庄甚至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冀东文化稍发达,但农村中仍有80%的文盲。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后,本来就很少的学校,或是校舍被毁,或是教师被杀,晋察冀边区的学校教育几于停顿。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后,曾以行政手段要求各级政府帮助不直接遭受敌人炮火威胁的小学校迅速恢复教学,并一律免除学费,对贫苦学生还给以必要的书籍和纸笔等日用品,使穷人的孩子都能上学。经过一年的努力,各县小学大部分恢复,有些文化落后、原本就没有学校的地方还建立了一些学校。到1939年,全边区小学校已发展到7 063所,入学儿童达36万余人,占学龄儿童的60%。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第二年制定的《双十纲领》又进一步规定,“在提高国民文化水准及民族觉悟的目标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建立并健全学校教育,至少每行政村设一小学,每行政区设一完全小学或高小,每专区设一中学”[13]。同时,边区政府还进一步建立教育行政领导体制,改善教师生活,基本完成了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小学教育任务,推动学校教育向正规化发展。1941年以后,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边区小学有所减少,边区政府开始对全边区小学进行整顿改革,并在游击区和接敌区创造了巡回小学、隐蔽小学、两面小学等适应战争环境的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顽强地坚持学校教育。1944年教育会议之后,晋察冀边区推广小学民办公助,使边区小学教育进一步普及和发展,从而广泛地提高了国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
(三)进行教育改革,开创新民主主义教育
晋察冀边区的教育是在战争环境下坚持的教育,因此不可能按部就班维持旧的教育秩序。同时,晋察冀边区政权的抗日民主性质也决定了其教育必定会在坚持抗战发扬民主的要求下有所改革,有所创新。
首先是教育结构上的改革。传统的教育多局限于学校教育,而晋察冀边区在坚持和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更重视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这种教育结构上的改革,完全是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因为广泛的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 “是当前深入动员群众参加与坚持抗战培养革命知识分子与干部的重要环节”[14]。干部教育主要是通过各种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以及各种干部培训班来完成,群众教育则是通过各村建立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夜校、识字班以及各中心市镇的民众教育馆等形式,掀起广泛的全民的学习热潮,从1938年冬天开始的“冬学运动”便是这种热潮的主流。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北岳区各县冬学有4 000余处,1939年增加到5 379处,1940年达到8 373处,学员约52万余人。巩固区和部分游击区几乎村村有冬学,在提高广大群众文化水平的同时,也增强了群众的民族抗战意识。
其次是教育内容上的改革。晋察冀边区的教育不仅仅是传播一般的文化知识,更不是着力灌输儒家的伦理纲常,而是以新民主主义为基本内容。1940年,随着中学教育正规化的提出,中学课程设置被要求为基础文化课占40%,政治课占30%,军事课占20%,艺术课占10%。政治课所占比例并不是绝对大,但实际上文化课的课文内容是以抗战、民主为主,军事和艺术也是服务于抗战的。小学课程除一般的国语、算术、史地、唱歌、运动等外,还有自然、社会、劳作、公民、常识,就是一般课程的课本也多是配合抗战建国而编写的,因此政治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占课本60%强”[15]。另外,基本生产技能的传授也占一定比例,尤其在1943年以后,小学生的生产成绩被列为评定学生成绩优劣的标准之一,这就使小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有了新的含义。
(四)新开社会风气,推动根据地的社会变革
在边区政府的提倡和组织下,各种各样的学习运动前所未有地深入到晋察冀边区的每个角落。教育不仅使晋察冀人民逐渐扫除了文盲,也使他们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不曾认识到的自我,教育给他们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教育还推动了晋察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由于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女子入学受教育的很少。晋察冀边区政府通过广泛宣传,动员女童入学,几年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如1941年冀西的阜平县小学生中女生所占的比例达到了43%。1938年冀中各县小学女生总数仅为22 410人,平均占小学生总数的13.15%,1941年增加到197 157人,平均占小学生总数的43.44%,最高的县达到50%[16]。不仅如此,在群众性的学习运动中,广大农村妇女前所未有地冲破束缚,走出家门,参加识字班。1940年仅冀中第八专区7个县的统计,参加冬学识字班的女学员就占学员总数的47.38%[17]。男女拥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这就在最大的范围内实现了最基本的男女平等,成为许多妇女干部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是最早在敌后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统一战线政权的典范,从其发挥的有效功能来看,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具有不同于旧政权的特点:第一,旧政权总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对多数人实施统治,而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是代表根据地内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对外组织抗日战争,对内实施对少数汉奸卖国贼的专政。第二,作为抗日民主政权主要工具的常备军已不是统治者的特殊武装,而是人民的子弟兵。此外还有特殊武装——游击队、全民武装——自卫队,共同肩负保卫政权、保卫家园、维持治安等重任。第三,工农群众已经把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积极参政议政,联合抗日的其他各阶级各阶层共同管理政权,这说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已经发生了不同于旧政权的质的巨变,事实上成为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形。
参考文献
[1][3]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383.
[2]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215.
[4][6]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M].北京:三生活·读书·新知联书店,1979:19.
[5]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345.
[7]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89.
[8-9]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M].北京:三联书店,1979:128,107.
[1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华北治安战·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65.
[11][16-17] 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2[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07,201,215.
[12]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N].解放日报,1944-04-07(1).
[13]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1.
[14]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12.
[15] 李公朴.华北敌后一晋察冀[M].北京:三联书店,1979: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