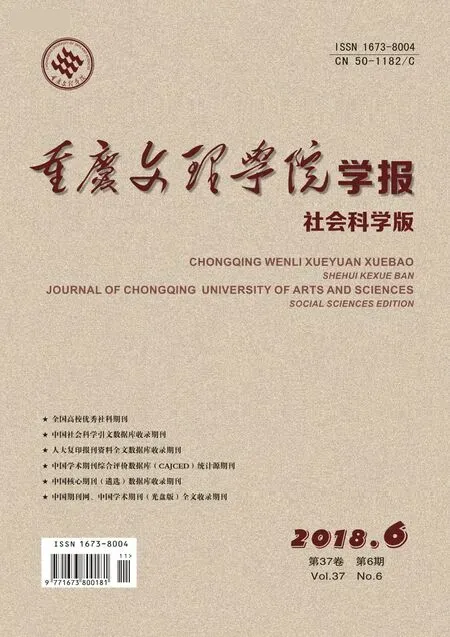《普宁》的话语空间解读
阳丹丹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20世纪著名的小说家和文体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曾将绝妙的文学比喻为“狼来了”的故事,因为在草丛横生中凸显狼的身影和文本故事中夸张的狼之间存有重叠空间的多义性,类似一幅棱镜,光线的射入产生出迷幻般的效果,就是在这种对照重叠中,文化的差异实现了某种结合,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的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象性建构。他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文学创作观,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世界,因此,他摒弃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而追寻一种多义的后现代话语建构,在其中,僵死的形式话语因宏大叙事的破裂而溢生出众多的话语空间,而意义从中生发。《普宁》则是典型地代表了纳博科夫的这种创作意图。或许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普宁》绝不能算纳博科夫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因为它既没有《洛丽塔》的名声,也没有《微暗的火》的纯艺术文体特色。但在我们看来,它却是这样一部标志着纳博科夫单一的文学叙事话语撕裂后,直视双重对立空间中人物身份建构焦虑的经典作品。
在众多学者对纳博科夫的研究中,《普宁》的结构一度是大家争议的焦点,小说在诞生之初更是因其结构的“松散”而遭到出版社的拒绝,但这也正是决定其小说价值的重要内核所在,在这几年聚焦于对《普宁》研究资料的梳理下,大多也是对其结构技巧分析为主,这以王青松的《论〈普宁〉的内在有机结构》[1]和张鹤的研究[2]为代表,他们从结构的螺旋形到内在机构的有效过渡出发,在纵横两个维度的重复往返中深入分析了《普宁》的叙事结构,由此而扩展的王海丽的叙事和修辞技巧[3]以及王安[4]等人的空间叙事视阀的挖掘。其次是对小说主题的解读,在《论纳博科夫的小说主题》[5]中,刘佳林将文本视作作家“生命主题”的延伸,即“文化流浪者的精神创伤”,王丹在《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和文化立场》[6]中,则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从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深入探究了多元文化带来的“差异性”。再次则是对普宁主体性身份的阐释,如李楠的《流亡者剪影》[7]、张素娟的《乌托邦梦幻的破灭与希冀——论纳博科夫长篇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宿命》[8]等,主要分析普宁作为一名流浪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可见,《普宁》的结构差异性和由此引发“他者”的思考成为小说永恒探讨的意义所在。但从整体来看,这种结构和多义性在《普宁》中留有的争议却很少有人将其纳入话语的范畴考察。我们知道,话语关乎主体的自我指涉,而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背景使得人们开始将关注点转向各种文化意义领域与语言学或其他指意符号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也深刻影响到当时的小说创作,被喻为“反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锋”的纳博科夫如何不受其影响呢?1958年创作的《普宁》正是处在这一革新时期,可以说,作为一位追求多义的后现代话语建构的纳博科夫来讲,话语的构建绝对是在《普宁》中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且它结构的多义性也正隐藏在这一话语空间的建构中,而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鉴此,《普宁》结构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正是寄托着作者将话语空间的一种断裂滑移植入其中的结果,并由此将它作为导向对现实社会身份困惑深切关怀的隐喻的代表之作,这对于我们当下思考他者话语对身份的建构毋庸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话语的间断性与空间感
索绪尔将人的语言划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层面,并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9],即概念和音响,并用能指和所指来分别指称。语言成了一种发现差异的存在,而在以关系作为基础的语言状态下,空间的配合又帮助语言符号建立联想关系。于是话语成了一种图式化的符号,它在向我们展示事物时是将表意单位集聚起来。这样的组织结构必然会导致话语的能指与参照对象的分离,并将这种分离置放在一个独立于说话者或环境的位置上。正如利奥塔所说:“言语本身就是以某种空间化为前提条件……我们不是通过声音特性来定义音素,而是通过它在一群分散的单位中的位置来定义。”[10]能指会在不同的说话者部分产生不同的意指效果,因为它的结构本身就是比喻性的,它在一个层次的所指中指向另一个所指。
因此,我们会发现,语言结构与组成其本身记号的质料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作为纯社会性对象的规约系统,而言语则是具有差异的重复的心理现象,它具有个体性和多变性。我们这里探讨的话语就展开于言语的那个空间,并且这一空间不是同质的,而是一个间断性的空间,它是以言语形式呈现出来的一个片段组合。我们知道,语言学中的所指指代的是一种“现实性”,是该事物或事件的“心理表象”,“通过声音传递的概念信息必然有别于包含在这些声音和节奏的连接中的前概念信息。这两者有时会重合,有时会分道……”[11]因此,所指只能是在意指过程的内部来加以定义,是能指与另一能指反复的建构过程。这样一来,能指所指称的空间围绕着话语就使得所指沿两个平面展开,一是组合段平面,另一个则是联想层平面,它们彼此构成了参照对象的延展性和聚合性。正是以这种方式,所有的言语都是在一个话语空间内构筑着与现实相关联的事物,并在自身边缘处使隐匿的东西呈现。正如皮尔斯注意到的那样,所有符号都具有向他者开放的特性,言语通过叙述和描写让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在场的可见物,正是这种话语中意义和他者产生了分裂,由此,文本不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清晰度,而相反是对某种具有厚度的空间的建构,在这一空间中演绎为两种能指功能之间的位移游戏,成为承载行动进程的记录和在空间中展开隐匿之物的在场。这种空间给予了意指中断功能的转移,话语的这种双重空间性,通过间断的片段组合与话语图式建立新的关系而生发出超验性的空间意义。
这一可见化的文本空间在其建立背后是通过两者相互交叉的差异性而产生意义的,只有在一方对另一方的重叠建构中,文本的内涵才能生发出改变原生在场意义的效果,而不再作为话语物质的一面。这主要表现为话语空间之间的转化,以及它们之间不可逆的异质性,而文本的组织结构就是处在话语和视觉图式空间的差异中,乃至于两者都以不同的名义在话语活动的空间结构中扮演自己的角色,这一秩序的功能将两者的不平衡状态纳入到一个结构性系统而将对立空间转变为一个中立的空间图式,借助这一效果,文本被留下一个有待解释的剩余部分,或者读者被迫参与到进一个被建构文本的部分。海德格尔说过“艺术作品的真正存在就是为了揭示生命的存在”,因此作品的意向也体现在文本世界的建构中、在于人对文本的直接体验,而这一体验则是由一系列能指元素的整体对不可见形式进行的图式组合,而且这一体验通过空间与所指领域的差异被领会到。这类似于朗西埃所谓的“行为与形式的即时同一性”,它在消解话语僵死形式特征的同时,又消解了读者搁置心理解读的能力,这样,话语的意指与空间形式的变化才得以交织在一起,它既具有向自己表现正在形成的自身过程,又表现了空间的外延性,从而具有一种动态感。它通过可视性与所指意义的关系建立,打破了故事传统的秩序,并自动形成一些联结,而作品的意味正是通过结构话语的差异性而呈现于图式空间之中,它涵盖了所有想象之物。话语具有可见现实的力量,但是只有话语与图式空间相互缠绕时,才能指示出感性的表现和意指行为的力量,从而让一个世界背后的世界显现。
话语空间作为一套能指转化所形成的形式系统,它们之间的断裂与重叠性造成了文本一种弯曲的空间感,使其独立于文本的内容以及约定俗成的参照体系。呈现于话语中的差异作为“意指空间”和形式空间而成为另一差异场,它属于某种生命能动性的领域,它凭借自己在组织成系统的空间内被置于了它们的缝隙处。这类似于科瓦雷所说的无中心无极限的空间概念,感性话语在其中具有了一种空间,并且它出自于隐匿言语的文本。因此,在文本中,话语和故事的展开共同构成了多重空间,在其中,空间的重叠性造成了直接话语表面的隐退,意味着空间的不透明性或模糊感,在这种阅读过程中,我们处在书面语链和语义场组织结构的那些裂缝中,就像在棱镜的观照下观看它们,它将话语的空间安排赋予读者对多个空间的嵌合,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所指间的安排方式和能指图式的空间投影造成了作品中感性与知性关系的不稳定,同时,艺术形式也与生命形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二、《普宁》的话语图式
由此,在纳博科夫的《普宁》中,能指不再像传统文本那样书写,而是根据话语空间的重组规则进行了重构,它越出了叙事的逼真性或推论的可能性的界限。伊利格瑞曾说,物质作为书写的场所,无法被明确地主题化(the matize),而“一种书写文本的结构,经过其他文本的循环,不断回到这种文本……”[12]这种东西在此被称为一种“替补之链”。因为书写的场所与空间是一种物质性,但是它又不同于“物质”的范畴,后者的表达明显受到前者的制约与推动,例如风、雨、情感等“前概念”都实质上被一整套感知代码所概念化了,也就是说文本话语世界的物质性变成了一个话语空间性的存在。在这个空间中,有一个实在的关联在起作用,即通过能指材料的操作使信息指向了一种补充的意指效果,它们与图式共同建构着有机体的产生。可以说,《普宁》体现了纳博科夫对话语空间结构的缜密思考。
首先,语言的结构具有连带关系,而能指的线条特征使得它的价值往往与要素的组合有关。我们在一个话语空间里感知到事物在于它们之间组合的顺序,只有在话语空间词序的排列中,才能创造一个空间实体被我们感知。纵观《普宁》,整篇小说的明线是按照普宁的生活琐事来进行叙述的,这构成了小说的横向组合层,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空间结构,但这横向组合却不断地遭受断裂的命运。这种话语空间的塑形在能指与所指之间以及能指的线性法则中使得文本《普宁》成了一个特殊的话语领域,一个不再受到线性法则支配的能指是为了让人们体会另一种语言操作的可能。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种种话语空间支配着《普宁》的整体组织结构,它体现在小说各个章节的片段性上。全书以七个章节的形式将各个分离的部分以十分精准的范式组合成了一个多维空间,小说的每一章可以说是自成一个完整的空间体系。除了主人公普宁外,每一部分讲述的人物和地点都呈现出断裂性特征,而且,每一部分的故事都自成多个向度,这也成了纳博科夫小说的“谜”,纳博科夫“用延迟信息制造了一个不易猜度的悬疑”[13],而这正是它话语空间制造的效果所在。除却小说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作为了解普宁的进出口外,中间的五个章节都朝向普宁的外部世界,并且通过并置情节线索,以回溯和闪回等手法中断了文本的空间建构,取得了复合的空间效果。在普宁的外部世界里,读者无法进入普宁真正的现实,所有话语的分布方式好像都置身于普宁之外,它们通过话语的能指而获得区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了解到的普宁是不固定在任何地方的,作家所叙述的关于普宁的故事就像虚无缥缈的话语一样,后者作为一个语言事实从属于一个社会系统而非个体,而作为个体的普宁在其中却缺场了,他在被书写的双重空间中被虚化,这就构成了话语及思想的空间构造。
小说中,普宁人物的塑造是能指与所指关联的结果。全书围绕着对普宁人物的塑造,通过普宁坐错车、租房事件、婚姻恋情和工作等事件形成一个环形结构,每一结构自成一个话语空间,由此组合并指向我们对普宁人物的整体认识。第一章一开始就叙述了普宁教授上了年纪的外形以及他自作聪明坐错车的事件,但是他坐错车的结果是通过叙述者直接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主人公并不知情,直到列车员的查票,普宁教授才得以了解,读者先于主人公的进程,这一阅读效果是由叙述者的叙述话语造成。在文本构成的过程中,话语明显的意思无法被穷尽,它不是将意义完整地汇集在所指中,而是由一个外在的决策者或说话人,即将你的言语作为第三人称来加以把握,在此过程中,话语的空间性油然而生。我们从普宁的现实状况一下子跌入叙述者给我们营造的另一个空间环境,即普宁教授的基本信息以及普宁授课时的滑稽表演,瞬间又移步到他坐错车的事实,这一切都源自于话语的安排造成的语义的能动性。通过他者的叙述,我们进入了普宁的世界,在叙述者的笔下我们不约而同地将他视为迂腐可笑的读书者。因为概念是通过体验而得到的,叙述者在能指的过程中有意刻画了普宁滑稽可笑的形象,但是在下一部分叙述普宁的爱情时,我们又看到了为爱矢志不渝的普宁。看着丽莎对普宁无情利用,我们只能推翻原有的认知而对普宁的命运感到可悲。第四章里,在普宁与维克多相见的漫长的等待时间里,从普宁礼物的挑选、两人之间的通信,在此的话语营造出了一幅温馨浪漫的画面感,就在我们以为普宁终有幸福的时候,话语却突然转向了那被扔弃在阴沟里的排球以及辗转的失眠这两幕,能指的迁移将这一切瞬时瓦解了。如同第五章普宁在驾车前往库克城堡的途中,话语空间虽呈现出一幅宁静的英格兰乡村风光,尽管我们看着普宁在同胞中游刃有余的周旋以及他尽情展示着他的魅力,却感受不到欢愉之情,相反,能指的转移让我们直面普宁的悲剧命运。在普宁开始他乔迁之喜的时候,他的“朋友”正洋洋得意地等待着他的失业,而他却浑然不知,这一刻,他的悲剧达到了高潮,读者的心情也五味杂陈,很不是滋味。
在对普宁人物形象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将对普宁几个生活部分的塑造视为体系中的几个部分,它包含了用几个故事来揭示普宁形象,这些组织单就对人物的塑造而言是同形的,但是深入文本中我们会发现,能指的反复移动成了《普宁》结构的常见形态,并且每一个部分中都有着对普宁形象不对称的他者的塑造。这是文本所具有的能指与所指横向层的替换所导致的。从一种空间过渡至另一种空间,这种整合使之构成了一个互为关联的整体,构建了一个“世界”,因为我们从一个叙述单元走向另一个叙事部分进行建构的时候,我们将会远离被前一部分所隐藏的潜隐文本,而新一部分的潜隐部分将会引导我们接近真相。这种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空间结构是引发文本意义的根源,因为这种衔接相反地酝酿着一些侧面的、实质的东西。我们会看到,在《普宁》中,这种话语空间并没有直接在个人与现实之间起连接作用,而是涉及对个体起中介作用的瓦解,这是话语空间横向断裂的结果。
其次,小说空间的纵向组合又加深了这种差异性。我们看到,《普宁》中场面的突然连接和断裂成了小说结构的一个常态,并且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我们被突如其来的状况“抛入”在作者描述的时空里,没有原因,如同有“心脏阴影”的普宁一样,瞬间坠入至过去、梦境甚至他者的视野中。这一系列的纵向组合构成了小说话语空间的另一纵深面,这些情景线索不断地被并置在他者对普宁的建构中,但它们之间呈现出来的空间指涉意义又在不断地互相消解。这种纵深性最明显的体现在于对普宁超验现实的描绘,现实成了主观化的空间建构,我们在话语空间里,来回游离在现在、过去甚至梦幻中,话语的主观现实构筑成了“现实”的话语空间,两段现实之间被割裂,从中生发出的主观现实成了读者了解普宁思想的动态反映。
普宁第一次幻象的出现是在惠特彻奇公园的长椅上。“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注意到生活当中的一大特点就是离散状。除非有一层薄薄的肉裹住我们,否则我们就会死亡。人只有摆脱他周围的环境才真正存在。”[14]15正值他思考着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时,回忆突然而至,童年里四扇式的木屏风,满是落叶的马道……话语空间在这里被撕裂,我们跟随普宁坠入他的幻象。可以说,连贯的故事情节在这里消失殆尽,而第二章则直接跨越第一部分情节转入到他因租房而与克莱门茨一家的相处,后又坠入梦境……这种幻象造成的断裂空间在《普宁》中随处可见。丽莎的突然造访使他对过去婚姻的追溯、居无定所后的定居对家庭生活的幻想……总之,在每个独立成型的章节中总有这样幻象的出现打破文章能指链。话语给予了这种回忆以形象的表现,在形成小说空间纵深度的时候,它的功能在于在读者身上唤起能指空间的那个所指,将其变换为一个意义,一个关于普宁形象的信息或命运的建构。于是,我们会看到,话语图式在能指功能上指向了不在场的言语的所指,文本获得了它自身的坚实性乃至它的繁衍性。
《普宁》的空间纵深性还在于它呈现出事件的重复性特征。它通过能指的重复构成了一个彼此解构的空间,其中能指的滑移和故事反复被断裂的所指效果化,加强了话语空间的纵深感。当一个故事呈现出不同性质的重复时,彼此造就的话语空间在重叠的过程中赋予了文本第二种存在方式,它是对原始材料的一种消散和肢解,这样的变形是对能指滑移,它们四处流浪,又以这种消散使得文本内部的流通成为可能,文本中出现的火车、讲稿、童年和心脏病等在小说中被反复提及,恰恰在于它们相对于所指的不确定性,是通过在话语空间中解构相似性而形成,从而创造第三空间。在书中他三次吟咏普希金的诗句来表达他的爱情悲剧,这三次吟咏分别出现在普宁给学生授课时、走路差点摔倒时以及梦中时刻来进行叙述,但是在重复性中,我们看到了因能指滑移而导致的意指的不稳定而造成的重叠性差异。话语的意指功能指向何处,这就逼迫读者去关注文本中不同的话语空间以及反复出现的话语应该指向的所指。唯有此,普宁身上的特性以及他所遭遇的情形才能有一个背景,“次生之文”才能被生出,而话语空间的厚度也由此获得。
可以说,构成《普宁》空间性的超现实性的东西是言语的结果,而话语具有可视的空间性特征。在纳博科夫笔下,小说不是现实的再现,而在于现实的虚构,并在虚构中给予读者一种超现实的意义。这就意味着话语的空间性侵入了话语并使得文本中的连续性行动遭到了瓦解,于是在话语的断裂性空间中,此时的意指具有了一种模糊性,产生了一种新的空间,它们依据相互补充的细微感知的逻辑来进行表达。由此我们会发现,《普宁》的描写是优先于行动的,这种描写就是空间的可见性。这是一种属于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所在,它将不可见的东西转变为可见的。话语的世界是一个可见的世界,也是一个多重话语空间的世界。它之所以为整体,是因为它是局部的,并且,它将这种拥有伸展到存在的各个方面,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超越的空间。《普宁》的所指既是具体的,又是一般的,它在逻辑上同时涵盖了肯定和否定。在《普宁》所指的空间中,非存在与存在两者以相互纠缠的方式共存在文本中,这个由双重语义结构构建出来的空间里,恢复对现实的感知理解。在话语空间里面,读者进行的是一种空间性的过渡综合,这种视域的过渡与扩展不会终结,但它们又完全融入一个世界里,即在相互牵扯的状态中内外两部分彼此互相促进。
三、话语空间隐喻下的普宁
话语是心理意识的外现,更是一种自我认知的确认。因此,小说中文本的意指活动的语言是受到语言学支配的现实的语言,在话语空间的法则下,各个话语空间都是展示现实生活的一个窗口,我们在其中是为了交换词语并获得意义价值,它成了意义的生成方式。不同的话语空间提供了不同的身份建构,王丹《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学立场》更是以跨民族的立场深入分析了纳博科夫文本中对文化边界的突破和多元文化的思考,“纳博科夫的世界主义思想是将自我与世界空间进行关联的结果,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自我建构”[6]。因此,在《普宁》文本里能指与所指的滑移中,在话语空间的重叠和排斥中,我们都应该明白一件事,即在普宁人物的塑造上,普宁俨然成了一个言语隐喻的存在,窥视《普宁》话语空间建构的背后,隐藏的是普宁形象的现实特殊性。我们的意识是一种心理现实,而言语则是这个心理现实的象征并通过它得以强化塑造,话语空间的整合是对现实的认同和拒绝的过程。普宁在文本中由于能指与所指的滑移而造成的一个事实就是让我们意识到现实社会对他的否决,这体现在他对自我身份确立的迷失上。
语言的能指被记录在一个表现空间,这种表现空间寓指的是一个文化环境。普宁作为一名流亡的俄国知识分子,历经挫折来到美国立足,但是却因带有浓重俄式的美式发音而遭到周围环境的排斥,他与周围人的关系是在美国的话语背景下建立的。在第二章中普宁与他的同事交流时说道:“不出两三年……人家也会把我当作美国人啦。”[14]35很显然,这是一个入“局”而不成的“局外人”,身处异地的普宁,却无法彻底融入美国的文化环境,他被分裂、质疑和排斥,话语空间的弯曲是一种主体身份的不确定性。当语言与表现空间指向两种文明,那么意义统一性就会遭受瓦解,而普宁深陷这种异质文化中。位居在两者空间下的普宁形象正是这两种文化差异在某种程度上的象征,所以在《普宁》的话语空间中才会有如此多的异域空间的呈现,这也正是其意义所在。
首先是美国文化形成的一个话语空间,这几个场景主要由前往克莱蒙纳的火车、惠特彻奇的公园、温代尔学院、克莱门茨夫妇的家以及昂克维多小镇等组成,普宁形象的建构依据叙述者对普宁在这几个话语空间中的活动,而这个空间是通过活动的断裂形成,在跟随普宁生活境遇的变化以及与主人公保持一定距离的叙述者的视角交叠中,我们不断地体验着话语空间的多维立体感,读者借助视角图像的不断呈现来感知普宁形象。在对普宁形象的表征中,我们看到了普宁形象是一个遭遇了叙述者黑化的形象,一个被挖苦的对象,读者和叙述者都得意扬扬地看着他自作聪明“坐错车”的窘态,甚至他被视为“俄式幽默”的“病态”的教授。而叙述者“我”与普宁同为俄语教授,更是构筑了一个个普宁教授的出丑空间,言语里充斥着对他的讽刺挖苦。在这个文化里,文化的障碍和语言的不精通,使得饱学之士的普宁成了胸无点墨之人嘲弄的对象,最后甚至连工作都失去了。但是在其中穿插的故事中,我们又看到了普宁对待朋友的真诚,对待前妻孩子的爱,即使他在背后被人无情地嘲弄。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美国话语环境下失去根基的飘零之人与本土文化的冲突。
其次是穿插在文本中的俄罗斯生活情境的叙述,这形成了普宁身份构造的另一文化空间,在其中,与美国文化空间下普宁的滑稽怪异相对照,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位失去故国的流浪者,他知识渊博,对妻子忠心不二,但却只能生活在回忆和梦幻之中,他企图靠戴着东正教的十字架来认识自己,无奈在美国社会背景下却成为一种情感负担,“我什佛(么)也没由(有)”成了普宁飘零一生的总结。俄美文化导致的冲突共同刻画出普宁身份的二重性,纳博科夫用话语空间的转换展示了主人公身份认同的外在压力,希冀在现实话语的断裂空间中寻找一丝安慰,但这种身份困却伴随着普宁的始终,普宁最终“头戴一顶有耳扇的小帽,穿一件风衣”,驾着一辆寒碜的堆满箱笼的小轿车,继续他的模糊身份的流亡之旅。
正是普宁无法摒弃俄国文化,又徘徊在对美国文化的肯定之间,普宁成了异质文化悲剧命运的象征。可以说,普宁话语空间受制于自身的环境,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碰撞,因此,纳博科夫在塑造普宁的时候是通过话语空间的转换来表达作家的话语意图的。只有建造出多样的话语空间场域才能尽可能地实现话语的多元性,突破单一的话语文化来塑造我们主人公身份的双重性,并引申出文本的多样性和现实性,使得文化差异的冲突得到审美效果的最大化,而普宁的形象则是在边界模糊的话语空间中得以深化。
身份话语的差异造成了普宁的悲剧,这是文本敞开的侧面凸显,并由其各个部分组合成一个多话语空间的差异存在,于是,我们在纳博科夫的《普宁》的话语空间中看到的是文化话语的空间交叉,是俄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交流与对立、异质与排斥,它典型地体现在普宁每一个不同的片段组合。在《普宁》中,话语的建构是通过空间的断裂形成的,这种独特的话语空间形式是作家为塑造普宁这个人物形象而独具匠心的结果,我们说过《普宁》文体的特殊性在于在话语空间下横纵两方面的组合以及它们的重复和断裂,这就构成了小说一个链式的构造,在每一链之中,都有与其他链相重复的其他链。可以说,每一空间自成一个体系又环环紧扣普宁的生活境遇,在环与环相扣的重叠之处,塑造这普宁的形象,形成了它独特的话语空间,并且,这多个空间混而不杂,相反有着清晰的脉络迹象,它们彼此交错着,以语言经验、组合和聚合为凭借,从而使我们去发现普宁的象征性,每一个空间像影子一样紧随着“我”身份的确认,以此揭示永远属于客体的自我想象领域。纳博科夫多样的话语空间解构了传统,实现了突破单一话语的文本形式,正是在肢解和摧毁单一话语空间的基础上,语言才能与多元的文化恢复联系,这才是《普宁》中话语空间的意义所在,它以多元的意识形态进行着对生活的思考。话语空间能够自我诠释,因为它具有一种自我关涉的结构,而纳博科夫在《普宁》中显示出来的多维度空间的消解,则是对丧失自我身份的恐惧的表露。
四、结语
在《普宁》的话语空间里,作者制造了许多意义矛盾的能指与所指的混乱,这种混乱反过来加深了话语空间的分裂,所指本身是虚拟的,类似米兰·昆德拉所谓的“梦幻般的真实”,运用话语空间审视纳博科夫的《普宁》,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梦幻就在于纳博科夫是通过言语的棱镜创造了一个迷宫般的世界,而真实即在于我们在跟随作家故事能指时体验的空间流动感,我们不断发现与重组,也不断地在体验自身现实的处境,文中的虚构空间正如张鹤的叙事解说一般,“生命的真实就潜藏在现实生活与艺术生活相结合的刹那”[2]。纵观文本的建构,普宁是处在一个他人视角下“异类”存在,他身上充满了矛盾性、混杂性和不确定性,“文化主体已经难以辨别到底他者是受到同化使然还是对自我主体身份进行恶意的暗讽与戏仿”[15],这是通过文本中话语空间的间断性而表现出来的。抽象的概念背后是阶层背后的价值取向,言语空间打开的是我们所处现实社会身后的生活观,它是社会思想观念的精神显现,并作为读者的运思工具的。“普宁的成功在于他的虚拟”[16],作为在模糊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人物形象,一个在文本各个话语空间建立起来的中心人物,他的存在体现了现实社会中的真实环境、身份的流动与质疑性,这种话语身份的困境在当代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在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左右,纯艺术被设想为将思想直接实现为自我满足的一种感性形式加以表达,或是在自我消解中彰显自身,它消解了文字图式产生的空间距离感,而将话语的断裂等同于某个整体处在行动中的一个生命形式。对于纳博科夫而言,这种时代语境带给他一种全新的创作体验,话语空间成了他文化身份的能指,并散居在文本的流动中。他将文本的线性联系割裂,使其成为各个单一的话语空间,以作为主体身份的渗透。当一个文本的整体框架被拆散分裂的时候,那么文本本身也就是僵死的表达,类似一幅图画被拆分为几个部分,而我们却盯着这几个残缺被打乱顺序的画面,犹如大家企图在脑海里恢复一致的全貌一样,这无疑是荒诞的,框架失去了表现,并不再受到现实世界对它原有概念的裹挟,从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会生发出不同意蕴,结构的多义性也由此而来,并使得普宁他者身份的冲击与威胁显得越发紧张和迫切。纳博科夫在话语空间的技巧下,使其作品脱离了僵死文字的表面化,从而成就了普宁流动鲜活的总体形象,《普宁》也得以成就“纯艺术”的称号,这种全新的言说凝结着他对身份的深刻思考,在王丹的论述中,纳博科夫是以跨越民族形式的写作方式来获得超然的文化立场。那么,这种超然的立场则是纳博科夫立足于对多元文化语境下身份的质问而获得的,并以动态的话语空间构筑出艰难知识分子的异域身份定位困境,而这种先锋性正是其小说经典的活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