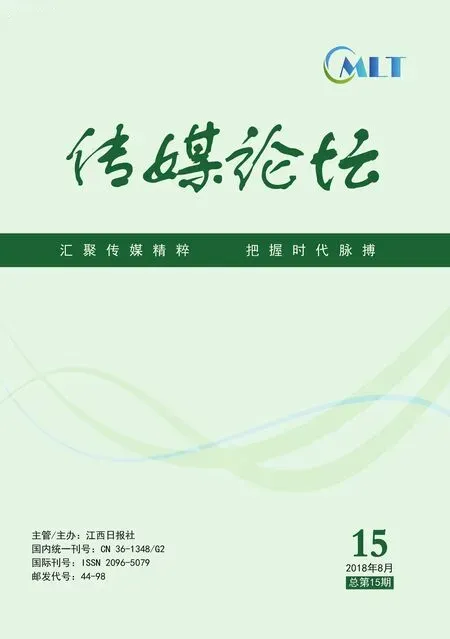自我塑造或地位固化
——美国肥皂剧对女性观众的满足与剥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肥皂剧是诞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的一种电视节目形式,其基本定义为“一部连续的、虚构的电视戏剧节目,每周安排为多集连续播出;它的叙事由错综的情节线索组成,聚焦于某个特定社群中多个角色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肥皂剧满足了女性观众观看与想象的欲望;另一方面,因其模式化制作与消费主义的渗透,女性形象的单一化呈现使现实中真正的女性被更深地压迫在荧幕影像中。这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女性观众的观剧愉悦与电视剧中父权制意识形态控制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女性对幻想情节与现实生活加以区分,充分认识到肥皂剧依受众需求为导向的制作方式,以自觉抵抗渗透于“现实情节”中的无意识的父权中心的意识形态。
一、欲望与幻想:肥皂剧满足观看的方式
(一)情感的倾泻
肥皂剧首先满足了女性对情感的需求。肥皂剧中大部分情节展开与戏剧冲突都围绕着女性探索自我情感、追寻自我欲望而展开。在复杂而牵扯不断的人际关系中,女主角与不同的人物建立各样的联系,链接起情感纽带,故事的冲突则往往来源于感情纠葛或人际纷争,并且这一进展过程被不断延长。肥皂剧中每一件事都会产生后果,而最终的结局则被无限拖延,很少达到叙事高潮。相反,不断有障碍和问题需要解决,叙事的兴趣点在于人们面临障碍时所产生的情感与反应,它们带来了一系列世俗的近乎老套的满足感。
当肥皂剧作为类型化电视剧销售给女性时,它的目标群众是这样预设的:女人忙于家务劳作,亲子关系与夫妻关系是全部情感来源,社交仅限于邻里关系,社会性与外向程度低。这就造就了肥皂剧以“抒情”为主要内容的故事构成方式,既能提供给女性幻想性的逃离现实的情感满足,又因其“现实主义”的背景贴合女性的日常生活,使其像是平淡生活中的白日梦,消磨琐碎且无趣的家庭生活。
(二)欲望的诉求
“凝视理论”下女性作为被男性观看的对象这一论点无需赘述,但在肥皂剧中,男性成为荧幕前女性观众观看与评价的对象。女性从这一“幻想性的男性”身上得到了两方面的愉悦,一是对情感关系的想象,从虚构的男性人物身上找到满足自我情感的特征(尽管这些特征可能并不存在);二是对肉体的想象,肥皂剧中常有让男演员赤裸上半身展示肉体的美好与强壮的镜头,这似乎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男性化”的快乐,以补充剧中展现情感关系的女性欲望。
肥皂剧的女性取向直接影响了电视剧中的性场面的描写。正因为女性对男性的幻想不仅仅表现在他的身体上,还进入了他的感情关系与人际交往风格,所以肥皂剧中的“性”是情感纠葛的一部分,它所带来的快乐在于情感体验,而非肉欲结合。因此“性”往往作为表现人物激烈热切的情感的方式。在女性审美之下的肥皂剧中,以一种新的女性化的方式来建立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关系。肥皂剧削弱了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地位,因此,至少从女性视角出发,肥皂剧的内容确实满足了女性观众精神与想象上的满足。
(三)想象的呈现
肥皂剧中的女性形象有别于现实生活,她是女性观众对“生活在别处”的幻想,女性观众跟随女主角体验不同的人生,使一些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想象在观剧过程中得到显现,令想象的内容具象化。
男性角色作为女性幻想关系的一部分,承担了大部分“非生活化”的形象塑造。他可以是全能型的男主,以上帝般的姿态出现解决女主角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他可以是深情的配角,只出现于女主失落的种种时刻予以她安慰;他也可以作为阴险的盗贼,在故事平和进展时偷取美好事物令主角坠入深渊。这些想象中的形象离现实过分遥远以至于成为标签和符号化的人物。
肥皂剧给女性观众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修正型的日常生活。我们都知道它有别于日常生活,但依然令人沉溺,因为它在现实世界的骨骼上填充幻想的血肉,在漫无边际的琐碎剧情里,在家务劳作与激情消退的婚姻生活里,肥皂剧里想象中的“障碍” “困难” “危机”既是对冒险刺激的渴求,又是对安逸生活的顺从。
二、颠覆与破坏:肥皂剧对男性话语的冲击
(一)破坏父权模式的家庭结构
在以人际冲突为主要戏剧矛盾的肥皂剧中,要想追逐情节刺激不可避免的方式就是对关系造成破坏,肥皂剧婚姻中往往埋藏着毁灭的种子。因为幸福美满、风平浪静的婚姻不具备戏剧性。肥皂剧对婚姻生活的描绘给了人们另一种解读婚姻的方式——一种不为男权社会所青睐的解读。例如,在妻子的婚外情行为,可以解读为对伴侣的不忠与对婚姻契约精神的背叛,从另一方面解读则可以是女人的独立性与她的性权力。
女性越轨的故事摧毁了文本的意识形态核心:家庭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对破坏的认同,也用来对现状提出质疑——婚姻是否是必要的?家庭关系破灭的界限在和何处?观看肥皂剧的快乐也在于她们所感受到的对男性权力的蔑视。打破传统家庭结构,大量出轨、越界行为的出现造成了脱敏效果。在这里,男性只作为符号式的人物出现,他所代表的是女性身边“未能解决的问题”。
(二)创造自我表达的新方式
肥皂剧的收视群众主要是女性,对她们来说,收看肥皂剧是一种反抗情绪,对自身文化空间的创造可以自发产生女性的认同感,女性对这一节目产生了文化占有感——这是她们的文化,而男性则没有。
“闲聊”一词显然出现自男性中心话语,其潜藏的含义是闲言碎语和“女人气”,女性对肥皂剧中问题积极的参与,是她们以自身生活有关的方式解读这些问题的愿望。通过闲聊很容易在肥皂剧与口头文化中建立联系,产生的是为特定观众群体才知晓的意义。所以闲聊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它生产出观看者的观影体验,二是它建构起使这一体验流行开来的群体。肥皂剧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象征性体验和一种共同的话语,女性的私人观影感受和通过闲聊建立联系的其他女性建筑起独立的女性话语空间,它给予了观众一套新的解读系统,纯依赖于女性观感的解读系统,从意义生产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积极的。
三、加深与固化:肥皂剧对女性形象的压制
(一)压制生活方式:关在既定形象中的女人
“可能电视剧强烈地暗示出的是一种女人的文化形式特征,妇女都能在其中发挥一种社会委派给她们的专长和施行其特殊关怀的所有的社会舞台”。早期肥皂剧把女性形象固定为“家庭主妇”,女性通过观看肥皂剧中女主角的生活方式而加深了自我形象认同。
而后来展示“女权”观念的电视剧中,女性“离经叛道”不受男权文化的控制,性观念的解放和对身体禁忌的消解,似乎令女性朝向更自由的方向前行,然而另一个问题是:肥皂剧对女性的规训真的消失了吗?如果说早期肥皂剧是教导女性贤良淑德才能幸福美满,那么现今的电视剧是否在教导女性用女性特质来伪装自己?女性主义是否成为一种新的消费品?身体解放是女性主义的诉求之一,但身体的自由、欲望的袒露是否令女性进一步沦为更“具吸引力”的观看对象?影像中的女性在消费物质与性,电视前的观众在用眼睛“窥视”与“消费”女性身体,女性观众甚至模仿电视剧中女性形象,从而落入消费文化的陷阱。
(二)压制理性表达:沉溺感情与琐事的女人
肥皂剧的充满情感的情节叙述方式受人诟病,“情绪化”通常被认为是女人标签与特质,在肥皂剧中女人把情感关系看作生命的制高点,尽管这是女性书写中难以避开的命题——描绘私人情感和自我体验,然而肥皂剧的情感的滥觞让人不得不怀疑,难道女性的自我价值就是建立在与他人缔结情感之上?
肥皂剧中那些相似的故事,类型化的女性形象、局促的女性生活场景无不昭示了女性的文化地位,女性的文化身份认同也在这样的框架下得以完成。她总是以情感为中心,难以逃脱“软弱”的魔咒。同时,肥皂剧中女性形象不仅受到来自男性的贬损,也受到女性观众的贬损。在承认对肥皂剧的热爱时不可避免地用上轻蔑的语气以掩饰对“低级”文化的趣味。如福柯的观点,性别的结构与权力的结构是相等的,权力在性别区分中是因而不是果。因此对肥皂剧全然否定的非理性评价,是主流精英文化对大众娱乐的权力压制。
四、结语
肥皂剧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从最开始描述20世纪50年代家庭主妇情感纠葛的电视剧,到现在描绘都市女人日常生活的电视剧,始终不变的是以女性观众为导向,满足女性观众的情感与观赏快感。面对肥皂剧,女性观众既可以把它当作白日梦的副产品,在消费电视剧的同时生产出自我的女性意识,也可以通过肥皂剧中的角色关照自身,确认自己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地位。然而隐藏在肥皂剧幻想泡沫之下的是它对女性形象的压制,把女性塑造成剧中要求的形象,再寻求女性观众的认同,以至于在观影过程中女性就这样被“询唤”,将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刻入社会形象之中。所以尽管肥皂剧提供给女性观众快乐同时也剥夺了女性个体经验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