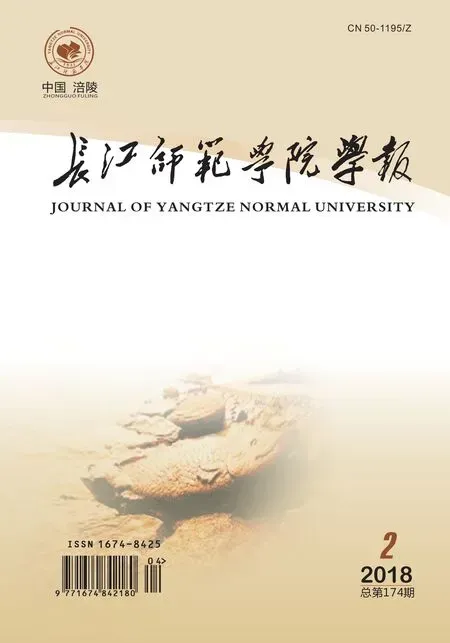“乡村振兴战略”下发展农业合作社使然的两个视角
——基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何晓琼,钟 祝
(1.河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2.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党的十九大对“三农”发展的新举措无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并将“乡村振兴战略”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重点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吹响了建设美丽幸福乡村的“冲锋号”。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体系,都离不开各类专业农业合作社发展壮大,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特征决定的[1]。农业合作社作为农民个体规避经营风险采取灵活合作方式建立的经济组织,是弱质、分散性农业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有效举措。
一、现代农业合作社的兴起及“罗奇代尔规则”
(一)现代农业合作社的兴起
一般认为,现代合作社诞生于1844年的英国,一个名叫罗奇代尔小镇建立以自己小镇名字命名的协会——罗奇代尔先锋协会。会员们筹集本金,构建了合作社经营和管理规章,建立起一个消费者合作社,获利颇多,大获成功。为了纪念这一创举后人称之为“罗奇代尔规则”。随后数十年间在英国建立了1 000多个合作社。罗奇代尔先锋协会经历了160年的发展,也历经多次收购、兼并、重组,于2007年发展为以曼彻斯特为基地的全国性合作集体。而美国的合作社发展后来居上,成立于1752年火灾保险合作公司——费城房屋火灾保险合作社,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合作社,由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发起建立。1875年美国成功的农业合作社始于“农庄”(The Grange)的全国性农场协会组织,拥有85.8万成员,涵盖了美国32个州。为了促进农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农庄组织派人到欧洲合作社“取经”,于是“罗奇代尔规则”的精髓开始在美国大地生根开花,在1902年成立了“农场主联盟”和“美国公平社”两大组织。其中“农场主联盟”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具有工会性质的农场主协会,通过庞大的组织力量影响着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支持农业合作社的发展。1922年,美国国会通过“合作社大宪章”——《帕尔·沃尔斯太德法》,最终确认了合作社最基本的规范和合法地位。美国政府在1930年通过一项规定,将每年的10月份设定为合作社月。截至2012年的数据显示:全美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总数为2 200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有440多万,约占农业人口的90%,合作社农产品的加工占全美农产品总量的80%,销售总额已经达到2 350亿美元,提供了18.5万个全职和兼职就业岗位。全美最大的100个农业合作社销售总额达到1 620亿美元[2]。通过对英美合作社发展历史的回顾,我们可全面了解欧美农民合作化发展历程,也窥见了西方发达的现代农业合作体系。
(二)“罗奇代尔规则”的主要内容
根据“罗奇代尔规则”基本要求,合作社在决策中采取民主投票的方式,一人一票(民主决策);会员自由参加(自愿原则);合作社资产由会员提供(所有权);会员所出资产股份、股份红利有一定限制(限制性原则);净收入以“惠顾金”的方式返还会员(分配方式);不设立任何高风险的项目(风险原则);会员权利平等(平等原则)。“罗奇代尔规则”包含的基本理念和诸多原则,无论合作社从民主决策到会员权利平等,还是科学管理到合作精神培育都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西方合作社发展到今天,经历170多年经营调整,合作社的运营模式才日臻完善。与西方合作化道路相比较,我国农业合作社起步相对较晚,在实际运营中存在对合作社性质、规章、管理等诸多问题,对合作社用经济纽带形成的同舟共济“共同体”的作用也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二、厘清我国农业合作社内涵及其分类
2006年10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农业合作社是农户通过农产品的交易而设立并按照交易额度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营利性社团法人。我国的合作社和欧美国家合作社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法律地位的不同,造成的混乱是将“社团法人”与“企业法人”划等号,即要求社团按照企业的模式经营。“社团法人”应该是建立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在同类农副产品的生产、销售、采购、消费、服务等环节展开合作的一系列农业商业活动中的联合,实行自愿互利、民主管理、规范经营的原则,是可有效规避市场风险、保障经营效益的一种互惠共享性经济合作组织。一般来讲,我国农业合作社是特殊经营法人,从价值取向上讲具有公益性;从承担财产责任上讲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从所有权上讲入社社员具有财产所有权;从管理方式上讲实行社员民主表决等,这些属性都不同“企业法人”的法律规定内涵[3]。合作社在法律界定方面的模糊,导致在实践中某些合作社和成员利用“特殊法人”的地位,钻了法律的空子,以不法的手段谋取个人私利,损害合作社集体利益。因此,有必要厘清我国合作社的科学内涵,消除营利性社团法人“后门”过大的问题。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农业合作社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大。按照农业活动可以分为生产、销售、采购、消费和服务专业合作社;按照市场领域可分为地方合作社、地方延伸合作社、区域合作社、全国范围合作社、国际合作社;按照所有权结构可以分为单一合作社、联盟合作社、混合型合作社等类型。按照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合作社多集中于生产和销售环节,合作形式单一,规模不大,区域地方性特点明显,处于整个产业链下游,农产品加工销售附加值难以提升,利润维持在较低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就必须加快现代农业合作体系建设步伐,形成各级各类专业合作社,突破所有权限制,开展跨地域和跨产业的大合作,形成区域性乃至全国的各类合作社联盟,为农业增效、农村振兴、农民致富提供组织架构。
三、发展农业合作社使然的两个现代化视角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有必要重新认识农业合作社在边际效益日益降低的农业、“空心化”的农村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实现从经济组织“利益共同体”到村庄“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性转变。
(一)农业现代化视角
第一,从宏观上讲,农业合作社可以帮助疏通农业生产的内部系统,实现生产要素聚集和合理流动。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4]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经营体系的延伸,都需要合作社搭建起个体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桥梁和平台,提升生产、销售、采购、消费和服务整个产业链的专业化程度。从国外经验可看出,任何国家的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特点都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构建多元化的农业合作社发展模式是满足当今经济发展的需要[5]。以建立各级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社为纽带,大力培育农业经营主体,实现传统农业升级、改造、重组,促进现代农业各个生产要素聚集和规模流动,以及打造“乡村振兴”的现代农业升级版都有重要意义。
第二,从中观上讲,农业合作社可以有效延伸农业价值链条,提升竞争力。受制于农业的细碎化经营和小块土地经营效率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农业产业化、商品化水平较低,抵御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能力较差,农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弱质产业。农业合作社是作为个体会员的“避风港”和集体利益的“蓄水池”而存在,合作社可通过专业的市场信息收集,主动调整农业合作社内部的种植结构,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在销售农产品、采购农业生产资料、提供服务方面,农业合作社可以实现“抱团取暖”,也可以通过合作社之间的合作,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和先进的技术指导和帮助农民,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6]。农业合作社可以集体的力量拿到数量折扣及其他优惠,也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到高品质的农资产品和优质服务,甚至在农产品供大于求或者是个体农户急于出售农产品而形成买方市场时,通过合作社集体力量联合销售农产品,建立内部价格同盟,旨在改变在市场价格谈判中处于劣势的处境,通过“抱团”的方式适当降低农业风险系数,或集体分担商业风险。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中,公司和农户必须签署相关合同条款,共同维护双方利益不受侵犯,促进双方合作的顺利进行[7]。农业合作社在与公司或市场直接博弈过程中,通过为农户“代言”,维护了农业产业利益链条顺畅,既保证农业合作社的利润,也保障整个农业产业链向更深领域延伸。
第三,从微观上讲,可以实现个体农户利益的最大化,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经营效率。通过加强个体农户在合作社内部生产要素的联合,农业生产要素如资金、劳动力、土地都可以通过合作社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减少个体农户收益的不确定性。合作社作为互惠共享性经济组织,通过市场化模式运营,科学有效的管理和规模效应为合作社带来利润,而利润又以“惠顾金”的方式返还给会员,避免了个体农户间的恶性竞争,防止了中间商在农户和市场两头赚差价的的现实。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除了依靠个体农户自愿在劳动力、土地、资金的联合,更需要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地方政府可以帮助合作社完善规章制度,加强业务指导和人员培训,增强农民合作社防范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提供各种金融信贷等各项服务,当好合作社利益的“调解员”和市场规则的“仲裁者”。
(二)农村现代化视角
第一,有利于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对于农业合作社,人们很自然地理解为有合作意愿的农户组织。个体为了规避经营风险,自愿加入合作社组织,实现“抱团取暖”,这既有利于个体利益的保障,又可以促进集体经济力量的壮大,形成一个组织内的利益共同体。按照农民本身合作的意愿来讲,合作的积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内驱力就是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致富奔小康,就是通过组织内合作,共同分享经济成果,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按照对国家、集体、个人“三有利”的思路来看,只要有利于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有利于农民致富奔小康,一切符合农业农村现代化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都可以拿来为“三农”服务,而农业合作社就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最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之一。在现代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视域中,农民依靠建立自己的经济组织,通过积极劳动改善生活,这是劳动者应有的价值观[8]。合作社这种互惠互利的经济组织,保障了农民的经济自主权,是农民组织内部经济地位平等主体间的对话,彰显了对劳动、创造、管理的尊重。这样的现代价值观必然对阶层固化的农村治理产生积极的正效应,逐渐弱化农村守旧势力对农村治理的不利影响。
第二,有利于政治上的民主治理。我国城镇化单向度的推进,导致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日益严重。在基层农村治理中,多数“原子化”的农民受制于经济地位比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家族宗族势力弱的影响,话语权和影响力将逐渐丧失,乡村的基层治理将出现“马太效应”。而西方的农业合作社通过农场主的联合,或聘用专业的游说者到国会游说,或者选出自己的代表和议员通过沟通等方式来影响政策的制定者制定出有利于农场主的政策法规。随着我国各类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其经济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农民的政治权利意识也逐步提高。这种政治要求不仅增进了合作社成员之间的联系,也增加合作社参与外部经济活动的机会,拓展农村经济发展的外部空间。随着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合作社和成员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政治民主参与意识日渐增强。合作社的发展也吸引那些拥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农业产业精英回流农村,夯实农业发展的后劲。以农村经济的振兴带动为切入口,可以逐渐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扎根乡村,带动基层政治生态的根本好转,推动村干部逐渐从“为民做主”向“让民做主”转变,由“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推动基层政治民主发展,为基层的民主治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有利于农村文化上的文明引领。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的某些消费文化与流行时尚的精神“鸦片”不断侵蚀着乡村文化固有的“根脉”,不断改变着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影响着农民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引起乡村社会的文化裂变。而农业合作社是互惠共享性经济合作组织,基本遵循民主、民办、民受益的自治原则,既是一个经济实体,又兼具文化组织的功能,可以弥合乡村文化出现的裂痕。合作社在管理组织机构中,一般采取会员一人一票民主的投票方式来决定重大事宜,建立合作社的运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建立合作社自己的运行原则,从原先的单一的经济行为到转向整个村庄的未来发展,形成同舟共济的“利益共同体”。这种从经济“利益共同体”到村庄“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转变,浸润着农民渴望摆脱“原子化”的生产困境,实现集体合作“文化共同体”的重构。在合作社内部,合作、共赢、共享的理念扎根于每一个成员,成员的合作和意愿能力日益加强。村庄随着经济活力的增强,必然带来村庄公共性文化的重建,并逐步恢复在外来文化冲击下日益失落的文明乡风和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杨娜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基于湖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172.
[2]唐珂.美国农业——发展中的世界农业[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238.
[3]崔晓红,张玉鑫.浅析新型农业合作社的性质与法律地位农业经济[J].农业经济,2017(1):56-58.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5]胡红斌,戴波.国外农业合作社运营模式的比较研究[J].世界农业,2017(5):158-161.
[6]黄海啸.中美农村合作社的比较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09(9):94-95.
[7]薛建改.日本农业产业化运营的经验与启示[J].农业经济,2016(8):12-14.
[8]李亮,柏振忠.国外农业合作社典型模式比较及中国借鉴[J].理论月刊,2017(4):17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