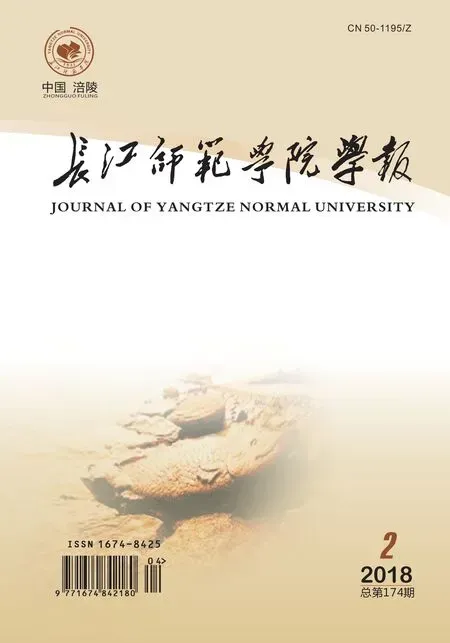“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立场与民众认知水平
——基于“五四”启蒙的反思
冯 阳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
“五四”运动距今已有90多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沉淀,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再看“五四”或许能看得更清楚些。“五四”运动也是一场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启蒙”所指认的有两个对象:一个是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一个是作为被启蒙的民众。对于前者,我们要重新去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只有弄清“何谓知识分子”之后,我们才能明白“知识分子何为”;而对于后者,我们则要反复去追问“‘五四’到底启蒙了谁?”这样一个问题。
一
首先我们来看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在西方,人们常常将知识分子笼统地称作“社会的良心”;本雅明用近乎于诗人的浪漫情调称知识分子是“眼睛在鼻子上,秋天在心中”;英国学者斯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将知识分子称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生的勒代特”;列宁则视知识分子“等于常识渊博者和民众的导师”。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历来不一,以至于让知识分子这一头衔太过于容易摘得。在我国,知识分子有大小之分,比如,如果钱穆、屠呦呦等人可以被称为“大知识分子”,那么随便哪个中小学老师、职场白领、网络写手、杂志编辑都可以算是“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变得毫不清晰。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知识分子的概念加以范围上的限定。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找出一种类型,称呼他们为“知识分子”不会有损他们身份的完整性。以钱穆先生为例,我们将他称作“大知识分子”当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称他为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极为恰当的。同样的道理,把屠呦呦说成药学家或是“发现青蒿素第一人”,比起空泛的“大知识分子”称呼更能概括其成就。中小学老师或杂志编辑亦然,两者已经包含了足够清晰的名称指向,没有必要再用“小知识分子”一词来画蛇添足。汪曾祺也可被称为“知识分子”,但以“散文家”来称呼他更为准确,正如舒婷最为合适的称呼是诗人,尽管她的诗歌创作,尤其是诗歌《致橡树》曾经引起了一个时代的关注,并激发起一大群知识分子关于女性地位的热烈讨论,但是仍不能改变她作为诗人的身份。所以可以明显确定的是,那些大多数称作“大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的个体,并未由于“知识分子”这一称号而限制了他们的职业属性和工作特点,将他们的“知识分子”称号放弃掉,不会造成混乱或歧义。
那么知识分子究竟该如何定义?笔者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走出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1],而且思维方式要尽量符合基本的公共理性,在言语表述上也要力求做到与大众一致。这样无论其之前的身份是编辑、诗人、教师还是一名普通公务员,他都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来重新审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不管是李大钊、陈独秀,还是胡适、周作人,他们在“五四”时期都走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了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上,他们在思维方式也是尽力合乎公共理性,但问题就出在“表述方式上力求贴近大众”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人所大力倡导的“白话文”主张,其背后暗含着一种旨在拉近“精英”与“民间”距离的主观努力。胡适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启发,将“文学革命”的目标确定为重新打捞“民间”文学的价值,他指出:“中国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只因为无人敢公认主张用白话文学等来替代古文学,所以白话文学始终只是以民间的‘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不能取死文学而代之。”[2]按照胡适的说法,“白话文学”并非是什么新鲜事,它在古时就已经出现过了,只是当时居于“庙堂”的文人将它看作是一种俗气的“民间文学”,故而使得其应有的价值受到了埋没,所以“五四”提倡“白话文学”,明显是带有为“民间文学”伸冤翻案的意图。而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又指出:“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而是要致力于提升“平民文学”的精神品格[3]。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于“平民文学”是要求其能“脱俗”并且尽量达到“高尚”,这其实就体现出了“五四”知识分子所持的一种启蒙的精英意识。通过上述对胡适和周作人等文学主张的简单陈述,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分别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阐述了“五四”新文学的非“民间”倾向。
胡适在谈到“旧文学”的缺陷时说,其“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成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文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仍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扔块骨头给他们吃去吧。这种态度是不行的。”[4]胡适的这番话似乎预示着“五四”时期精英将要毫不犹豫地抛弃“我们”而融入“他们”,但是细致考察胡适与周作人的相关文学主张又可以发现,他们所持的“民间立场”并非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全盘接受与盲目认同,而是带有条件的,即在形式方面吸收“民间”的“精华”,而在内容方面舍弃“民间”的“糟粕”,这看似非常的客观公正,其实质却凸显出“五四”知识分子的功利心态:认同民间文学的创作方式,但是并不认同民间世俗生活的文化价值。“民间文学”极其庞大的受众群体,才是他们为启蒙“民间”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四”那代知识分子大力推行白话文,其目的就在于使他们在“表述方式上力求贴近大众”,这表现出了强烈的“民间”倾向,比如鲁迅的“乡土小说”、刘半农的民歌体诗,它们贴近生活现实描写底层民众的苦难,确实给新文学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甚至一度出现了从“庙堂”走向“广场”的新趋向,但是“民间”并不等于“广场”,“广场”只不过是为知识精英重回社会政治中心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其本质还是知识分子“教化”民众的意志体现。“五四”新文学一方面倡导“民间”,另一方面又批判“国民性”,这就使得它自身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民间”是“国民性”孕育的土壤,“国民性”隐藏于“民间”之中,否定“国民性”也就意味着对于“民间”的否定。
回顾“五四”,我们可以发现那时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其实远不如古代文人那种“感同身受”的思想境界,因为无论是柳永、关汉卿还是罗贯中、曹雪芹,他们对于“民间”都有着深厚的了解,他们熟悉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与生活情趣,他们的创作是真正的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反映“民间”,所以得到了大众的一致喜爱。相比之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持的“民间”立场就立马相形见绌,他们所持的利用“民间”的功利心态使得他们始终都没能在“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真诚有效的沟通机制。所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推行白话文并非单纯地想在“表述方式上力求贴近大众”,他们只是借白话文为自身创造出一种适于表述“知识分子意识”的“广场”话语,而“广场”最终遮蔽了“民间”,使得“五四”的启蒙并未真正走向民众。
二
其次,我们再来看作为被启蒙的民众。“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不管是推行白话文,还是创作新式小说,其目的就在于想通过文学的手段来启蒙民众,但是这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不能被忽视,即普通民众应具备起码的文化知识,他们有能力阅读文章,有能力理解知识分子所传达的思想内涵,但是现实恐怕并非如此。
对于“五四”时期民众的识字率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表1所反映的是1906-1923年全国的学生人数,从中可以看出在1919年学生人数大约在4 000 000左右,占当时总人口(约4亿)的1%,学生人数所占比重当然是推断民众识字率的重要依据,但是表1所统计的学生数仅仅是官方的公立学校在读的学生数,而当时中国的学校类型丰富,不仅有公立学校还有私立学校、乡村的私塾等,所以这一数据难以准确说明“五四”时期民众识字率的水平。

表1 1906-1923 年之逐年学生数(教会学校学生数未列入)[5]
根据章开沅等人的考证,清朝末年识字的人只有4 000万左右,仅占当时总人口(以4亿计)的10%[6];到了1930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开展了民众教育程度的调查,结果如下表2:

表2 定县7岁及以上人口文盲与识字者人数统计表[7]
定县是当时教育发达的地区,表2的数据包括了县城居民和农村居民,如果单就农村来看,识字率可能更低,而且表中17%的识字者绝大多数只是能够认识几个常用的基本汉字,能读书写信的是极少数;来自当时南京的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显示:1929-1933年,中国华南地区文盲率为80.7%,华北为85.2%[8]。从这些数据我们大概能够推测出“五四”时期中国人整体的识字率应该是不足20%。
识字率会对启蒙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情况。美国文化史学家彼得·盖伊在他的《启蒙时代》一书中探讨了欧洲各国识字率的上升是如何影响启蒙运动的,他认为,“文人共和国繁荣昌盛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广大的阅读公众”,因为作家能够自由地去决定自己要写什么、怎样去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自己拥有一个人数众多的读者群,这样,作家才能因有自己的“粉丝”而摆脱赞助商而生存的困境。而处于启蒙时代的欧洲,就已经形成了广大的读者群体。盖伊举例说:“在日内瓦和荷兰共和国等加尔文宗国家,民众求知欲旺盛;在英国,朝气勃勃的清教徒在17世纪时即已成为庞大的读者人群。在休谟和伏尔泰时代,这些国家的读书风气日益浓厚。”而根据彼得·盖伊的统计,仅在当时的法国,“成年人识字率从1680年的40%上升到1780年的70%”[9]。毫无疑问,社会整体识字率的提升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而在1919年的中国,有超过4/5的民众尚还处于文盲阶段,我们不禁要问,对于连字都不识的人,启蒙对于他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五四”知识分子所持的“启蒙”立场几乎没有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过痕迹。也就是说,封建专制制度长期赖以延续维持的最为深厚土壤——广大农民——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因知识分子的启蒙而站了起来,得到了一次深刻的觉醒,他们甚至连启蒙的声音都没关注到。正如胡愈之所说:“吾国内地农民,殆全系不识字者,其智识之蒙昧,尚未脱半开化时代。因此吾国一切文化事业,与大多数之农民阶级,竟若全不相关。”[10]
在“五四”时期,对于中国不识字的芸芸民众而言,他们从封建时代走来,身上带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他们大多是穷苦的农民,祖祖辈辈的种田耕地使得他们深受自给自足的小农思维影响,他们只关心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发生关系的事情,比如日常的吃饱穿暖、生儿育女。对于所谓的“国家大事”在他们那里是空洞的,无论这个社会怎样变化、王朝怎样更迭,只想安安心心做一个顺民,兢兢业业将祖宗传下来的伦理道德维护好。因此,普通民众理解不了现代启蒙者对他们开出的那套思想上的“药方”,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呐喊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启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东西。鲁迅小说里未庄的百姓所关心的绝对不是大革命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无非是像阿Q那样,一心想着钱家的桌椅、赵家的床,等等;祥林嫂到死也不会去思考自己是如何被封建社会的仁义道德所杀死的,她所关心的一直是人死后是否还有灵魂,是否会在阴间被劈成两半;成年后的闰土没有去反思自己贫穷麻木的根源,而仍是将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向“我”讨要的香炉和草灰上;华老栓最为关心的并非是为他们的美好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党人,而是自己“十世单传”的儿子在吃了人血馒头后是否能恢复健康。“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句话在他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除此之外,王鲁彦《菊英的出嫁》里为死去的女儿操办“冥婚”的母亲,台静农《拜堂》里在深夜偷摸着拜堂的一对叔嫂,蹇先艾《水葬》里那些在刑场边看热闹的村民,甚至是老舍《骆驼祥子》里的人力车夫祥子,这些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愚昧、麻木,他们对于造成自身悲苦命运原因都浑然不知,都与整个时代的“启蒙”主题相去甚远,他们的物质精神诉求与知识分子的启蒙呐喊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契合点。
回到我们开始提出的问题,对于大多数都不识字的民众而言,启蒙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五四”究竟启蒙了谁?在启蒙者对民众进行启蒙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事后的结果表明,民众并非如启蒙者所期望的那样获得了一次深刻的洗礼,思想上也并未得到空前的解放,但是对启蒙者自身而言,他们似乎才是这场启蒙运动的最大受益方,他们获得了最大的启蒙。在这场运动中,启蒙者对中国的封建制度、伦理纲常、文化传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们努力挣脱传统思想上的束缚,通过汲取西方思想文化的资源,从而获得了一次思想上的彻底解放。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喊出了传统文化对人精神的戕害,撕毁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假面:“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11]5,“我翻开历史一查……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1]7所以,“五四”的启蒙可以肯定的是启蒙者对自我进行了启蒙。
三
反思历史,是为了用历史的铜镜来照见现实,同样的,我们反思“五四”的启蒙也是为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吸取教训。有人会说,当前是一个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任何价值的获取都没有了门槛,比如一个人想获取知识不再需要有钱、有地位,互联网可以让你在短期内就获取大量知识。一个人想有影响力也不需要有权或读书读到博士,一个网红就可以轻松办到,这样社会现实状况就使得以前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从高位被拽了下来,启蒙本身也逐渐式微。当今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时代的感受应该毫不亚于康有为那代人当年所感受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需要说的是,作为启蒙两端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他们之间的界限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被打破这对于启蒙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当界限被打破,知识分子直面民众时,他们就必须重新寻找一种新的言说方式来与民众沟通,重新调整他们与民众的关系。而旧有的“五四”式的那种带有孤傲的姿态、凛然的眼神或是不屑流俗的手势的知识分子启蒙形象在这个网络化的时代大都可会被民众当作可以用“表情包”嘲弄的东西,这样或许能够逼迫知识分子更换原有的认知或者固有的待人接物的“姿态”,并催生出一种新的更为平等的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关系。在各种文化思潮日益交汇的当下,这一点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反思“五四”启蒙的原因。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7.
[2]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35.
[3]周作人.平民文学[M]//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11.
[4]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M]//胡适.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2.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928-929.
[6]章开沅,马敏,朱英.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660.
[7]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49、182、234.
[8]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291.
[9]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下)[M].王皖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59.
[10] 罗罗.农民生活之改造[J].东方杂志,1921(7):4.
[11]鲁迅.狂人日记[M].赵延年木刻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