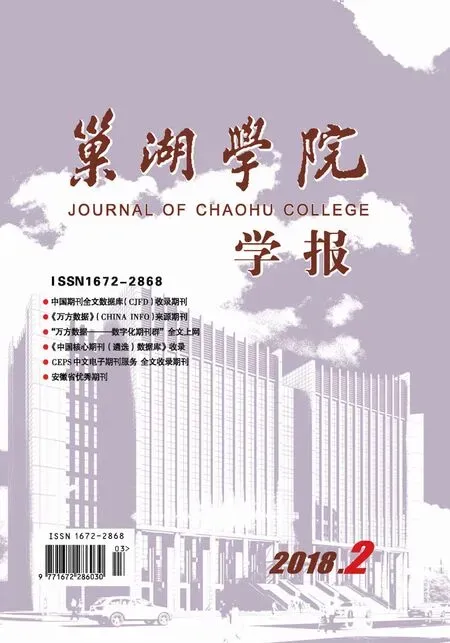论徽州审美文化“徽派”的精神内涵
洪永稳
(黄山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安徽皖南的古徽州,是名冠海内外的徽州文化的发祥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诞生了曾辉煌一时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华夏文化经典代表的安徽地域文化——徽州文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徽州文化的研究热,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以来对徽州文化的研究存在一种不平衡的态势,研究大多集中在历史学、民俗学以及徽商等方面,对于徽派审美文化的研究较为薄弱,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以“徽派艺术”为代表的徽州审美文化无疑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徽州文化独特魅力的重要表现。在古徽州,审美文化异常发达,著名的“徽派建筑”“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书法”“徽州文学”“徽派篆刻”“徽派版画”等都是盛极一时的徽州审美文化的代表,它们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学艺术、审美等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追求文化自信的新形势下,在振兴安徽文化走向全国的战略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对徽州审美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徽州审美文化的“徽派”特征及其根源,总结徽州审美文化“徽派”的精神内涵,对当下推动安徽文化事业的繁荣兴盛以及走向全国,促进中国审美文化的建构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所谓“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包含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什么是徽州审美文化“徽派”的内涵?至今还是一个不够明确的概念。一提起“徽派”,我们就会想到徽州建筑中黑白分明的“粉墙黛瓦”,“五岳朝天”的马头墙;雍容华贵锦绣辉煌的徽班演出;意境深远清俊峭拔的新安画风;个性张扬表情达意的徽州书法等,这些都是具体的审美文化形态所显示的美学风貌,它们是彰显“徽派”内涵的表征,是徽州审美文化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的显现,与“徽派”内涵密切相关,而不是内涵本身。为了对徽州审美文化本质作理性的把握,我们试图沿其美学风貌进一步探索徽州审美文化“徽派”的精神内涵,以求教于方家。
1 伦理至上的道德理性和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并重
众所周知,徽州被誉为“程朱故里”“东南邹鲁”,徽州文化的哲学基础就是程朱理学;同时,徽州也是徽商的诞生地,徽商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因素。程朱理学是中国先秦以来儒家哲学的深化和总结,它从“内圣”的经世路线和“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强调通过道德的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操守的传统,具有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徽州诞生了著名的地域理学流派:新安理学。新安理学继承了程朱理学的道德理性诉求,坚守人格主义的道德标准,同时也注入了徽商文化的血液,表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倾向,具有求真求实、儒商结合、重义也重利、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精神。这些精神品性渗透在徽州文化的精髓里,当然也深刻地融进了徽州审美文化里。徽派艺术就突显出这种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二重诉求。
这种诉求最明显地表现在徽派建筑、徽州雕刻等艺术中。就徽派建筑来说,徽派古民居建筑体现了宗法制伦理社会的价值理念,《黄帝宅经》曰:“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贤,无能悟斯道也。”[1]明确地表达了儒家的住宅观,宅者“人伦之轨模”,徽派建筑继承了这一儒家的住宅观念,体现在建筑的格局和形式上。在整体格局设置上,徽派古民居建筑,遵循同族而居的规则,大多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同姓同族而居,不掺杂姓;在住宅的内部设置上,严格遵循宗法制家族的孝悌伦理和礼乐秩序,“按照男女长幼、房系嫡庶有序排列,营造出主次分明、内外有别、尊卑有序的多元聚合”[2]。内部的设置也体现儒家的象征观,如古民居中的“天井”有“四水归堂”的说法,象征着敛财聚宝,“肥水不流外人田”;“天井”也象征着家族的兴旺昌盛,“家有天井一方,子子孙孙兴旺”,这种伦理道德理性是徽派建筑艺术的精神灵魂,它也体现在宗祠、牌坊等建筑中。
此外,徽派建筑也体现了徽州审美文化实践理性诉求。我们说徽派建筑是一种生态美学的艺术典范,除了伦理的诉求外,还有实用的、环保的生态观念。比如,徽州古民居的选址,因地制宜,依山傍水,突出顺势而为实用观;“马头墙”除了美好的寓意外,还具有挡风防火的功能;“漏窗”既有通风采光的功能,也有透景的作用,所谓漏窗得景,介于幽、旷之间,半遮半露,可望而不可及,给人以幽深的审美的感受;“天井”也有防盗、采光、通风、消防等实用的功能等。
总之,徽州审美文化在儒家文化和徽商文化的二重作用下,展示出伦理诉求和实用诉求的二重性,这是“徽派”的精神内涵之一。
2 崇尚锦绣辉煌的宏富之美的审美取向
在中国美学史上,有两种鲜明对立的美的范式:清水出芙蓉式的天然之美和错彩镂金式的雕饰之美,前者表现为简易质朴、自然清新,后者表现为宏博锦绣、富丽精工。这两种美的范式在徽州审美文化中都有不同的表现。支撑徽州文化的两大支柱程朱理学和徽商文化是徽州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根源,也是徽派艺术的“徽派”风格的内在依据。徽商文化是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徽商是儒商,亦商亦儒,但不管对儒学钟情到什么程度,他们身上的商业气息还是很明显的,作为商人,其审美趣味也就打上了职业阶层的烙印,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3],审美趣味是审美意识的一部分,也与审美主体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相联系。徽商少年离家外出经商,历经千辛万苦,获得商业成功,荣归故里,当然免不了有追求奢侈、讲究排场、崇尚豪华的审美心理,精美的“徽州三雕”可以明证,从徽班的庞大阵容也可看出。
在徽州的审美文化中,“徽州三雕”是“徽派”风格的一个代表。“徽州三雕”是指有徽派风格的砖雕、石雕、木雕三种传统民间雕刻工艺,它的审美风格体现徽商“亦儒亦商”的特征,在表现的内容上,大多反映儒家“忠”“孝”“仁”“义”的思想,如“岳母刺字”“卧冰求鲤”“苏武牧羊”“孔融让梨”等;在艺术的风格上,精雕细刻,细腻繁复,错彩镂金,集平、浮、圆雕于一体,镂空层次多重而清晰,具有精妙的艺术效果。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的木刻花雕艺术就是一个佐证。“三雕”在明清鼎盛,与徽商关系极大,同时也反映了徽商的审美趣味,所以,有学者说:“明中叶以后,随着徽商财力的增强,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浓厚,木雕艺术也逐流向精雕细刻过渡,多层透雕取代平面浅雕成为主流。入清以后,对木雕装饰美感的追求更痴迷,涂金透镂,穷极华丽,虽为精工,但有时反而过于繁琐”[4]。这是对“徽州三雕”兴盛以及审美风格的精准概括。
这种崇尚宏富之美的审美取向也表现在徽班的演出上,徽剧作为安徽的地方戏,是在徽商的支持下发展和成熟的,徽剧的演出特征,阵容庞大,可以用雍容华贵、气势雄伟来形容,徽剧“排场宏大,气派不凡,行头服装富丽堂皇,角色行当齐全,演出时讲究三十六顶网巾会面,十莽十靠,八大红袍,载歌载舞这种气势恢宏”[5],这是徽商审美趣味的表现,反映他们追求一种华丽堂皇的富丽精工之美的审美心理。因此,徽州审美文化的“徽派”内涵应包括这种反映徽商审美趣味的审美取向。
3 追求宁静致远、淡雅高古的意境之美的艺术风格
这是徽派艺术的重要特征,也是徽州审美文化的重要内涵。走进徽州的艺术世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这种淡泊高雅的徽州气派的艺术风貌,这种风貌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所追求的一种人生的高远境界,用艺术去表达人生。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之乡,向来不乏文人雅士,徽州的知识分子继承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传统,秉承儒家的人格理论,如朱熹提出“圣贤气象”的人格境界,程大昌高举“高明博厚”人格操守等;同时,徽州的知识分子也崇尚道家“道法自然”和佛家“法界藏身,万物同一体”的思想,沉醉于山水风林之间,淡泊名利,与自然山水为伴,用自己的艺术天才描绘徽州大好山水的美景,借景抒怀,体现出儒道释文化融合。反映在艺术上,形成一种宁静致远、淡雅高古的意境之美的艺术风格。这方面最明显地表现在“新安画派”的绘画艺术和徽派书法艺术中。
“新安画派”是诞生于徽州明清之际中国著名的绘画流派,此派画家善用笔墨,描绘徽州的山水,借景抒情,表达自己心灵,在理论上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其画风继承元四家的遗韵,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士人的逸品格调,给人以淡雅高古的意境美。如“新安画派”的创始人渐江(1610—1663),师承元代画家倪云林、黄公望等的风格和笔法,意境苍茫,笔画瘦劲,气韵峭拔,风格冷冽,他的《松溪石壁图》,被誉为“山水笔法介于倪、黄之间,而自具面目”,代表作《西岩松雪图轴》是他人品和画风的表达,体现出远离尘世的夙愿。再如:“新安四家”中的主将査士标(1615—1698),绘画笔墨疏简,格调清远,风神懒散,气韵荒寒,给人意趣深邃之感。现藏于扬州博物馆的《仿米山水轴》图,笔墨简化而疏放,有天机逸趣之美。
在徽州书坛上也体现出这种审美风格。徽州书法兴盛于明清,随着徽商经济的发展、徽州文化的繁荣,徽州书法异军突起,出现了众多著名的书家。近人许承尧在民国《歙县志》中就列举上百名书家,像草书大家詹景凤,金石学书家程瑶田,书印俱佳的巴慰祖,新安画派的査士标、戴本孝,“扬州八怪”的汪士慎、罗聘等都在中国书法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徽州书法的书风承接中国书法自宋以来开创的“写意”书风,重视书写主体的胸怀情志。如草书大家詹景凤论书以“劲”“古”“逸”为尚,推崇北宋书家苏、米、黄,评苏轼的《寒食帖》为“神来之笔”,论山谷书法“莽苍深郁,奇古而雅致厚致不俗”;再如:“新安画派”中的书家,他们的书风和画风一致,重视人品与书品,用书法表达内心的情怀。“新安四家”中的渐江、査士标都是著名的书法家,他们不满清朝的统治,面对江山易主的事实,无力回天,愤然遁世,退隐山林,寄情山水,书风与画风一样,风格傲然有骨气。总之,这种淡雅高古的艺术风格是徽州审美文化“徽派”的重要精神内涵。
4 尊崇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天然之美
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不仅表现在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上,还表现在对中国古代众多优秀文化的融合上,具有一种包容性和多元性。反映在审美文化领域,徽州人的审美观念表现出融合的趋向,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也吸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尤其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在徽州审美文化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从徽州人的来源构成看,徽州人主要是由当地土著人和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战乱迁徙到此处的人构成的。“土著人过着刀耕火种、渔猎樵耕的生活,尚武勇猛,栖息于山林,与大自然结为一体,大自然成为他们的生存依托,和自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6]。因战乱迁徙来的人看重的也是这里的大好山水,“汉越融合后的古徽州人生活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融进自然,亲和自然,崇尚自然美成为他们精神上的诉求”[6]。这种对自然美的崇尚渗进徽州审美文化的基因里,徽派艺术中有明显表现的是徽派建筑艺术中的古民居和徽派园林艺术。
徽派建筑是徽州审美文化中的经典代表之一,表现出徽州人多重的审美祈求。在崇尚自然美方面,徽派古民居建筑的选址、布局和设置都体现出徽人崇尚自然的祈尚。依山傍水,随坡就势,因地制宜的选址,突出了和自然的顺应关系,和自然结为一体,使住所成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古民居的建构布局上,突出和自然的亲和关系,如天井、漏窗、花墙等的建筑手法,使徽州古民居和自然沟通,让自然之风、月、光、影、景能透进室内,达到人与自然的妙合无垠之境;在古民居的内部设置上,徽州古民居一般都是宅内庭院铺设鹅卵石或青石板路,修筑花圃,添饰林木盆景等,这是徽派古民居建筑形态的普遍基调,反映出徽州人热爱自然、依赖自然、亲和自然、融合自然的精神品性。
徽派园林是徽州建筑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园林建筑的一个流派。大凡园林建筑都是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集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于一体,供人们憩息游赏。徽州园林别开生面,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赋予自然以文化的底蕴,同时,使文化与自然相容,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徽州园林建筑类型较多,如私家园林、庭院园林、衙署园林、寺观园林、水口园林等,不论哪种类型都与徽州的自然山水环境相一致,以自然山水为背景,靠山采形,傍水取势,顺其自然,天然而然。在园林的建材上,大多以徽州本土的材料为建园素材,以徽州本土的动植物来装点,最常见的是以徽州的松、竹、梅、石等作为素材,以求得园内建筑与园外大环境的和谐与统一。这是“师法自然”的道家思想在建筑艺术中的运用,体现出徽州人崇尚中国古代文化“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
5 拥有“勇于进取,敢于创新”的开拓精神
徽州人素有“徽骆驼精神”之称,这是徽州自然条件的限制,山多地少的艰难生存环境造就的。徽州人在长期的谋求生存发展的斗争中养成了坚毅不拔、吃苦耐劳、勇于进取、敢于创新的精神品质,纵横明清三百多年的徽商的成功正是这种“徽骆驼精神”的有力确证。在徽州审美文化领域,“徽派”的精神内涵同样具有这种“勇于进取,敢于创新”的精神品质,这可以从“新安画派”的发展历程和徽剧的成功演变看出。
“敢于创新”是“新安画派”驰名明清画坛几百年的一个重要原因。“新安画派”在创作题材上,主要以黄山、齐云山以及徽州的大好山水为主要题材,属于风景画题材,画风秉承元四家的倪云林、黄公望等,用笔简淡疏放,而意境深邃含蓄。但是,他们并不是一味地秉承与模仿,而是力求创新。从明代的程嘉燧到民国的黄宾虹,创新发展始终是此画派不变的旨归。在描摹事物上,“新安画派在吸取前人的绘画法度时,不师古泥古,古而不化,重在表现不同事物各自具有的外部形体特征的逼真程度的量感和表现不同物质各自具有的本质特征的逼真程度的质感的有机结合”[7]。在构图上,超越了倪云林构图模式化的缺陷,“讲究疏密相衬,山水相生,在动与静、远与近、清晰与苍茫的结合上给人以一种主体的感受和审美的张力。”[7]在绘画的立意上,大多注入了作者的社会认识和人格追求,在对山川的描绘中寄寓着画家对社会历史的心理观照,主体精神的强化,把中国的文人画艺术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敢于创新”在徽州戏曲中也有充分地体现。徽剧是由皖南山区的民歌小调和从江西、浙江等地传来的弋阳腔、余姚腔等声腔结合逐渐形成的一个民间剧种。由于她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使她最终走向全国,进驻京师,演变成中国的国粹——京剧。她的创新精神表现为:在声腔上,随着时代的步伐,吸纳不同类型声腔的优点,如昆曲、秦腔等,革除其弊端,如在弋阳腔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改变其戏剧叙述的方式,产生了“滚调”,“滚调”的诞生对于戏曲的完善与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乐器伴奏上,改变了弋阳腔少伴奏的状态,增加了“曲笛”“唢呐”“先锋”“徽胡”“竹筒板胡”“大筒”“板鼓”“月琴”等一整套乐器,完善了戏曲的伴奏体系;在舞台设计上,从服饰装扮,化妆脸谱,到灯光布景都有新的创新。行头齐全,服饰华美,脸谱丰富,色彩寓意的成功运用都体现出徽剧的创新精神。尤其是徽剧富有创造性地加入徽州历史遗留的武术因素,重武打,便时有“昆山唱,安徽打”之称,形成了徽剧的表演重武功、重场面、重气派的审美特征。总而言之,徽剧和徽商一样,是徽州人“徽骆驼精神”的生动体现,勇于进取、敢于创新是其重要的精神品质,也是徽州审美文化“徽派”的重要精神内涵。
综上所述,徽州审美文化的“徽派”内涵大致包括这五个方面。它是徽州宗族社会、地域文化和自然环境在审美领域里的体现,是徽州人精神世界的诗性表达,是徽州审美文化的精髓,也是徽派艺术审美风貌呈现的内在根源。在今天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强调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下,对此研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老根,编著.黄帝宅经[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1.
[2]李道先,侯曙芳.简论徽派古民居建筑的审美特征[J].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1):5-8.
[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
[4]杨建生.徽州木雕与徽州古民居室内装饰[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9,(2):169-170.
[5]洪永稳.从马克思“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互动关系”理论看徽剧发展的内在机制[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7,(5):101-104.
[6]洪永稳.从徽派建筑的角度论徽州人审美精神的诉求[J].池州学院学报,2012,(5):70-74
[7]姚邦藻.徽州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19、320.
——以安徽蚌埠“湖上升明月”项目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