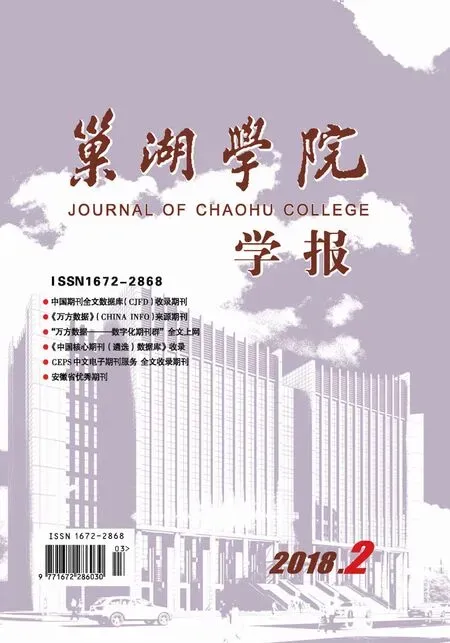《道德经》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宋 怡崔兰海
(1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1)
(2 安徽医科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2)
前人研究《道德经》①本文《道德经》的版本依据: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下标章节。的廉政思想多从个人品性着眼,强调从政人员的廉政品格。本文立足于道家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的学术根基,突出《道德经》廉政观下理想的行政模式和政府行为,更多关注老子廉政思想的行政哲学色彩。
1 道法自然:老子廉政观的哲学根基
《道德经》的政治哲学以宇宙本源论和辩证法为根基,前者关注万物产生的根源及其存在状态,后者关注事物运动的规律,此两者也是《道德经》廉政观的哲学根基。
1.1 《道德经》的宇宙本源论
《道德经》宇宙观首先从宇宙本源论说起,《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这是老子对万物之母的“道”衍生万物的过程性描述。这个本源意义上的“道”有两大特征。
第一,“惚恍”。《道德经》解释为“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为‘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若有如无的状态就是道存在的常态,而在若有若无中又偏向于“无”,老子说“复归于无物”;而于有的层面,老子说“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这里“有”“无”均是道的存在状态,不过二者中“无”更具本源性。冯友兰说“道、有、无虽然是三个名,但说的是一回事”[1],不可名状的道、无,是无形的,是本源性的。有、名是可以认知的,是本源体的外现,属于知识的范畴。冯友兰说《老子》有“为道”和“为学”的不同[1]。大致可以说“为道”就是体会“无”的应用,《道德经》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无”代表空虚,空虚方能容物,也就是说有了“无”的应用才能发挥“有”的便利。在政治上发挥“无”的用就是要“无为”。
而获得外在知识“有”需要借助“名”。《道德经》说“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二十一章》)。我们之所以能认识“道”,就是因为我们掌握了道的 “名”,但这一思路在 《道德经》中并没继续展开或延续,相反,《道德经》更多的看到了名与实之间的不确定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二十章》),也可以说《道德经》对外在的知识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怀疑立场代表着老子对所处时代强烈地不认同,胡适说“老子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2],胡适这里提到的“革命政治哲学”就是指老子对知识,外在“名”的不认同。《道德经》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惠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昬乱,有忠臣”(《十八章》)。如果人们能恢复到“道”的状态,即使没有这些大名词,人们仍然会很幸福,老子说“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诈,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章》),与通行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不同,陈鼓应据郭店简本修订的“绝智弃辩”“绝伪弃诈”,这里并没有排斥仁义、圣德的意思,只是否定了背离了“道”的虚伪、巧诈。在没有巧辩、诈伪的世界,即使没有仁义、圣德这些词,但人们复归孝慈,天下太平,人们处其实而忘其名,但忘其“名”不等于没有“名”。老子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三十八章》)。这里“彼”就是现有“礼”制文明,在老子看来它是浮华、伪善的。“此”就是皈依道的新政治,它是敦厚、笃实的。这种依“道”建立的制度文明似乎也要靠“名”方能让人遵循,《道德经》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三十二章》),这里提到万物开始就有的“名”,似乎未经过后世的“有为”政治的污染,是老子认可的,所以有了这个依“道”而立的“名”,人们的行为就有了一定限度,行事有了限度,即可没有危险。老子质疑与反对的是现有“有为”政治扭曲的“名”,而不是事物本来就有的 “名”。
第二,“周行”。老子说道的存在是“周行而不殆”(《二十五章》),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这两段话一是强调“道”运动的广博与永恒,一是强调“道”运行的效果;但都说明了《道德经》的宇宙观是动态的,变化的,陈鼓应说“‘道’乃是一个变体,是一个动体,它本身是不断地在变动着的,整个宇宙万物都随着‘道’而永远在‘变’在‘动’”[3]。不过笔者认为老子宇宙观中“变”论从根源上可能是来源于老子的天道观。《道德经》说“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天道成为人间理想政治模式的楷模。当代学界有种本末倒置的理论,认为重视天道自然的顺时理论是《道德经》之后黄老学派才有的特征,但从文献看,顺时行政思维产生可能更早 ,它应该是《道德经》“无为”政治学说的理论根基之一,不过后来的黄老学派更加扩大了这一理论的应用。
1.2 《道德经》的辩证法
《道德经》的辩证法以对立物的运动为根基,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万物在阴阳互动中产生均衡和谐状态。但《道德经》中和谐状态的产生不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而是阴阳二气相遇自然产生的结果,外力的作用只能起到破坏的作用,《道德经》在辩证法说实现了四大突破。
第一,他认识到事物存在对立面,事物只有在对立面的比较中才有意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髙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基于对事物“相反相成”的认识,《道德经》廉政观上提出了两点廉政实践思路。
(1)事物对立面皆有其存在价值。《道德经》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二十七章》)。在《道德经》理想的政治生态中,“无弃人”“无弃物”,万物各因其性,各本自然的发挥着价值。尊重多元、异己力量的存在,蕴涵着包容性行政的理念。
(2)万物皆存在对立面,故而理想的人格不可太偏执与专断。《道德经》称之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二章》)。矛盾的对立也造就了万物的差异,承认差异就要包容而不能偏执。《道德经》说“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培或堕,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这里提到理想的政治人物一定不要偏执、侈靡、过度,应允许差异与特质。
第二,他认识到矛盾双方存在着转化的可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五十八章》)。《道德经》警告人们事物是变化的,提醒人们要预防事物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做到“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五十八章》)。这实质上已经触及到事物变化的“度”的界定问题。
第三,他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过程性以及过程的渐进性。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是关注事物发展渐进性的辩证思维。在实践上,有两层意义。
(1)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六十四章》)。
(2)要慎终如始,不可急于求成。老子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六十四章》);又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六十三章》)。
第四,他认识到事物发展的周期性问题。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老子注意到事物发展的周期性,他称这种规律(常)为“复”。“复”这一周期规律的认识是《道德经》开展“德性修持”的哲学依据,每个人天性是“静”的,后世的欲望与有为扰乱了其本来的“静”,故而“德性修持”的理想状态就是复归于静,也就是所谓“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这是一种通达理想廉政品格的修持方法。
2 《道德经》廉政观的内涵
老子目睹政治的黑暗与统治者的暴政,提出了自己的廉政观,并试图通过这种廉政思维构建一个理想的政治新模式。
2.1 寡欲:廉洁政府建设
欲望是罪恶的源头,寡欲是预防与远离灾祸的最佳方案。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 令人行妨”(《十二章》),“五色”“五音”“五味”“无度田猎”“难得之货”这些东西无时不在诱惑人们,而不加节制的追求会导致 “目盲”“耳聋”“口爽”“心狂”“行妨”等不良结果。老子呼吁人们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抱朴即为守真,寡欲则可乐生。质朴、寡欲是老子提倡的一种理想人生状态。老子认为理想的政治家在面对外在诱惑时,要做到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林语堂说“‘腹’指内在自我(theinnerself),‘目’,指外在自我或感觉世界”[4]。
老子让人放弃追逐物欲的外在自我,持守内在自我的虚、静状态,这也是人生的本然状态,老子称之为“归根”(《十六章》)。虚、静的状态就是接近于“道”的状态,《道德经》说“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二十章》),这里的昏昏、闷闷的状态就是虚、静的淡然状态,它深邃如海,飘逸若无止境。众人纵情声色、名利,而我独甘守淡泊,与道为养。老子给“寡欲”找到了哲学上的依据:“大道”。老子说“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三十四章》)。这里的“不辞”是种担当,而“不有”“不为主”则是“寡欲”的境界;有功而不居功,以此来消解主政者的占有欲与支配欲。
2.2 慈爱:民本政府的构建
《道德经》对生命的珍惜是通过其反战言论展开的,它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三十一章》)。
消除战争的方法就是要弘扬三种品格:一是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四十九章》),二是慈(“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六十七章》),三是谦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六十一章》)。老子这种基于理性与慈爱的政治哲学散发着人文主义气息。
老子呼吁主政者要关注百姓生存状态,慈爱对民。他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二十七章》),主政者要对百姓冷暖感同身受,做到“无狎其所居,无压其所生。夫唯不压,是以不厌”(《七十二章》)。在老子理想社会里民众应该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的桃源牧歌式生活。老子对民众的基本需要在这里给予充分肯定,童书业说老子的政治态度基本体现了“小土地所有者的隐士的态度”[5],此论甚佳。而对于小土地所有者而言,最大的威胁就是“苛政”,故而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七十五章》)。
小私有者要乐生,除了物质条件和外在政策保障外,尚有精神层面的要求,老子提出“愚”的精神追求。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六十五章》),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觉得老子是中国历史上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二程遗书》卷十五说“秦之愚黔首,其术盖亦出于此”),然从《道德经》全书看老子的“愚民”思想与秦代“焚书坑儒”愚民政策在内涵上实不一类。“愚”是老子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精神状态,老子说“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二十章》)。可以看出,这里的“愚人”是一种质朴、纯真的状态,也是老子刻意保持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这种状态就是“沌沌”“昏昏”“闷闷”,是一种皈依于“道”的大智慧。而老子所要抛弃的“智”乃是背离“道”的诈伪之术,这种诈伪、巧智即是“昭昭”“察察”“皆有余”的不循自然的状态。
2.3 无为而无不为:社会自治与高效政府构建
“无为”是老子政治哲学的核心,通过“无为”既要达到社会自治,约束政府,也要达到“无所不为”的效能建设。
第一,无为与社会自治:“无为”是老子廉政观的核心。老子说“法令滋彰①郭店简本作“法物滋彰”,陈鼓应本未据改。河上公注:“法物”,好物也。此与《管子·牧民》“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含义相通。“文巧”即为老子所言“法物”。,盗贼多有”(《五十七章》),又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七十五章》),老子对当时诸侯王国政令、赋税繁苛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深有认识。故而希望通过“无为”政治的提倡来约束政府的行为,也可以说老子的“无为”首先是针对当时诸侯暴虐之政的反动。其次,老子“无为”政治是基于对社会自治的认同,老子相信群众能够自我治理,老子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老子对社会自治能力充满信心。但这里老子所谓的社会自治,不等于无政府主义,它只是要求政府少干预、少贪欲,给人民自治的合理空间,或者我们可以说老子的社会自治是建立在其有限政府思想框架下的。
老子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培或堕。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社会神圣在于社会本身的复杂性,政府不可能完全照顾到各个层面,故而政府不要干预太多,许多事情政府“不可为”,勉强去为,只能导致“败之”“失之”的恶果,这里实质上是主张政府权力应有所止。老子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三十二章》),老子提出政府行为应该有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名”,不过老子说“名”,是“始制”之名,也是就依道而兴的名,也就是“朴散为器”(《二十八章》)的“器”。我们可以看出老子有限政府理论实质上就是让政府遵循依据“大道”而确立的名物制度。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 “涤除玄鉴”(《十章》),做到 “虚其心”“守中”,这样就可以 “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准确把握社会动态。
第二,无不为与高效政府。“无为”的目标是达到“无不治”“无所不为”的效能建设,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我们称其为高效政府,是因为老子的“无为”实质是主张以极小的行政成本来换取极高的行政效果,也就是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为了实现政府的高效运作,老子提出了一些施政的具体思路。
(1)抱柔、守雌。柔、雌代表“静”的一面,“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思路与其抱柔、守雌的为政举措是一致的。但老子的高明之处在于把这一思路构建在辩证法的基础上,实现事物由“柔”“雌”到“强”“雄”的转变。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二十八章》),圣人之所以能都成“官长”,就是因为他善于应用“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的辩证思维。
(2)用啬。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五十九章》)。爱而惜之则为啬。这里蕴涵着节约型政府建设的意味。国家治理中减少政府的开支,就是节省民力,达到藏富、蓄精于民的目的。我们今天说只有政府过苦日子,老百姓才能过富日子也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七十八章》)。这里就是要求政府要善于担当责任,而不是贪图享乐,这样的政府才能有威信,才能有效能。
(3)不盈。政府的威信不是来自暴力与压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而是来自政策的对路以及施政者的品格。在 “无为”的廉政框架下老子描绘了其理想的施政者品格:“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十五章》)。作为施政者应该谨慎敬畏,释然洒脱,质朴谦虚,豁达随和;而最主要一点就是要“不盈”,只有不自满,才能去故更新,永葆活力。
3 《道德经》廉政思想的当代价值
《道德经》廉洁政府建设主张用“寡欲”“抱朴”来消解为政者的私心,为政者在“与道合体”的状态下自觉排斥物质利益的诱惑,来保持内心的虚、静。这种虚、静的状态不仅是保持自我安足的需要,也是保持客观、公正施政能力的需要,《道德经》“见素抱朴”的主张对推进党员思想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方面仍有其鲜明的时代价值。
《道德经》民本政府构建理论充满中华人文气息,其关于“德善”“慈爱”“谦下”的论述,闪动着人性的光辉。与老子大致同时代的哲人中,管子与孔子皆是现实政治的合作者与改良者,老子与他们不同,《道德经》更多的体现出与现实政治决裂的色彩。与对现实政权决裂相反,老子对生活在动荡中的人民抱有浓烈的悲悯。老子设想把政府置于“道”的制约下,来重现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秩序,这一新的社会秩序基本否决了现实政治中的各项名物制度,而是“依道”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体系。在如何实现社会秩序的转化中老子把希望寄托给他理想中的“圣人”,而“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他遵循了老子的“道”。尊道的政府要做到“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这实质上是要还原政权的社会性质。
《道德经》高效政府构建理论,闪烁着对社会自治的认同,以及基于这种认同下的有限政府理念。社会的进步不能以国家政权掌握财富与资源为标准;而要看这个政权维系下的社会自治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自治能力所给予人们的安全度和幸福感。《道德经》勾勒的理念蓝图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老子在这里并没有否定物质文明,而是更多的关注物质文明的社会化给群众带来的精神感受。社会自治能力越高,政府的运作成本就越低,政府也就越高效。
《道德经》廉政观的不足在于过高的估计了“无为”廉政体制下人民的“自化”意识,彻底地否定了“他化”,也就是政府的教化责任。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9、224.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9.
[3]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5、135.
[4]林语堂.老子的智慧[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90.
[5]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