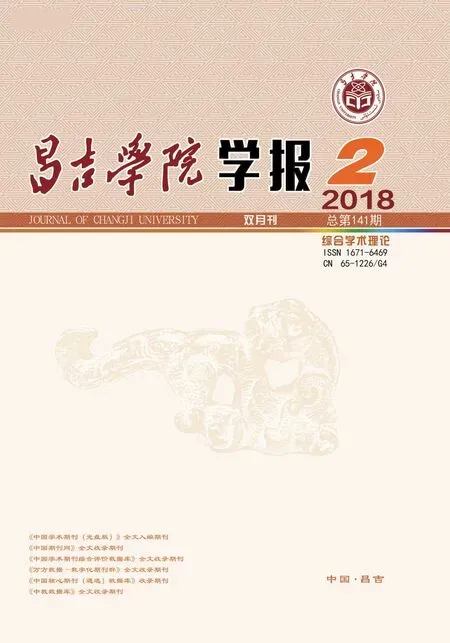战争背景下女性身份的想象与建构
——重读《炸弹与征鸟》《冲出云围的月亮》《色·戒》
梁小娟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作为生命存在的根本性物质形式,身体具有属己的、私人性的特性。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战争场域中,身体往往会超越自身的物质特性而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女性的身份也因之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在战争背景下,女性常被纳入到国家、民族、革命的视域,被当作国家、民族、革命的表征与符码,身体通常成为女性介入战争的武器与工具。“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是女性界定自己的身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自我赋权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和组成部分。”[1]本文试以《炸弹与征鸟》《冲出云围的月亮》《色·戒》三个典型文本来探究文本叙事中女性的身份与身体的书写与建构,以期发掘特定历史时空下女性的生存处境与女性解放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一、战争背景下的女性身体书写
白薇的《炸弹与征鸟》(1929年)以余玥与余彬两姊妹在“五四”时期至大革命失败后的命运来刻画知识女性在国民革命走向低谷后所做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自主选择。余彬素以“炸弹”自称,自视为摧毁旧世界、革命到底的“炸弹”,在军阀混战、国民革命陷入低潮后,在武汉当起了交际花,流连欢场,周旋于各种男性之间,为证实自己对男性的诱惑力,屡屡施展女性的魅惑,让吴诗茀、赛颖、沈铭石、哲学家、柯青等男性跪拜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余彬的革命意志已被腐朽的现实所击溃,她不再相信革命与爱情,认为男女之间只有性,玩起了爱情游戏而忘却了革命的要义与投身革命的初衷。余彬自觉接受了交际花这一社会角色——“当时的男性社会给女性规定的女性角色之一”[2],并完全沉湎于这一角色,在众多男性的争风吃醋中享受男性的膜拜而无法自拔。与余彬不同的是,姐姐余玥在挣脱封建婚姻的桎梏后,抱着投身革命的宏愿,来到武汉参加革命。余玥未重蹈妹妹的覆辙,主动远离沦为交际花的危险,在混乱中坚守自己的革命理想。为达到革命的目的,余玥答应革命者马腾的要求,决定放弃与马腾的恋爱,牺牲自己的身体与G部长相好,色诱部长以探听军事秘密。本着革命的要求,女性可以牺牲自己的身体与爱情,可以毫无顾虑地放弃自我,全心全意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余玥与余彬两姊妹的人生出发点极其相似,都富有争取个性解放、反抗旧社会的反叛精神,但革命失败后二者的不同选择代表着挣脱父亲桎梏后的“五四”一代女儿走向社会后所面临的尴尬身份:要么充当交际花,向传统的男权社会俯首称臣;要么扮演大无畏的革命者,泯灭个性与性别,为革命牺牲小我。无论是交际花还是革命者,都无法完成女性对自我身份的确证与认同。
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1930年)刻画的同样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知识女性所面临的生存抉择与历史命运。女主人公曼英在男友柳遇秋的召唤下,来到一所军事政治学校就读。入校后,曼英在着装上改变自己,“穿上了灰色的军衣,戴上了灰色的帽子,俨然如普通的男兵一般”,“而且她有时照着镜子,恐怕也要忘却自己的本相了”[3]。在环境的影响下,曼英渐渐完成了自我改造,克服了女性的柔弱、娇气,成长为一个男性化的、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与希望的革命战士,“几乎完全忘却自己原来的女性了”[4]。但在革命男性眼里,风姿绰约、娇艳欲滴的曼英潜意识里流露出来的女性魅力仍充满吸引力,“无论如何曼英是怎样地忘却了自己的女性,在一般男子看来,她究竟还是一个女子,而且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子”[5]。革命陷入低谷后,曼英在南征路上被贪恋美色的陈洪运收留,后借机逃到上海。在曼英看来,肉体能够征服男人、摆布男人,在陷入只剩下惟有肉体能够由自己自由支配的境地后,曼英决意用身体作为最后的武器来反抗社会,以此实现自己对社会的报复。在与钱培生的性事中,曼英一改传统女性被动的处境,用各种方式捉弄他,用“雪嫩的双乳”“鲜红的口唇”来驯服他,尽情践踏男性的尊严。与钱培生、周诗逸、四十岁左右的小官僚、资本家的小少年、柳遇秋等男性周旋时,曼英完全模拟男性对女性的蹂躏方式,变被动为主动,以付费方式来获取自己嫖男童的心理平衡,自欺欺人地实现自己的报复。当革命的浪漫主义走向虚无时,曼英不愿正视妓女的身份,而以自己在男性面前的主动,在性事过程中以调戏、驯服、驾驭男性等方式来实现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确证。但曼英的这种确证经不起任何追问,一旦面对单纯无邪的小姑娘阿莲和爱恋着的李尚志时,曼英用身体复仇的哲学根基就开始坍塌,尤其是在身体不适、误以为身染梅毒时,曼英万念俱灰。曼英在革命者李尚志面前自卑、犹疑与悔恨相交织,认为自己不洁的身体已经失去爱与被爱的权利。心灰意冷的曼英决意自杀,但田野的新鲜空气与初升的朝阳给曼英带来了新生,曼英与妓女生活彻底告别,蜕变为一个革命女工。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曼英经历了女学生-妓女-女工的身份转换,思想上对于革命的信念也经历了坚定-动摇-幻灭-重新坚定的过程”[6]。身份转换一经完成,身体上的疾病也自然痊愈,曼英也就具备与李尚志爱恋的权力了。在同时期以“革命+恋爱”为主题的左翼小说中,曼英的身份转换与蜕变富有时代性,曼英也被视作因爱情的引导而投身革命的典型。
与《炸弹与征鸟》《冲出云围的月亮》相比,《色·戒》①虽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但小说同样也演绎了女性在战争、革命背景下对于身体、情感与革命的抉择。小说女主人公王佳芝活动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中汪伪政权时期,她出场时的身份是来上海跑单帮的生意人麦太太。小说虽然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但并未直接描写中日双方残酷的正面交战,而是巧妙地将国家、民族间的战争转换为汉奸与革命青年个体间的心智较量与周旋。王佳芝刻意掩盖大学生的身份,凭借一时的抗日热情的支撑来用美人计色诱汉奸易先生。为达到锄奸的革命目的,王佳芝不惜牺牲处女之身,与同学发生性关系以获取性经验。一步步接近易先生之后,王佳芝的身心渐渐被他所俘获,在刺杀的关键时刻因一念之差而错失良机,为此将自己与同学的性命一并葬送。《色·戒》在讲述革命故事时,开篇还是遵循了“革命+恋爱”小说中千篇一律的模式,即知识分子女青年在革命的引领下,改造自我寻求新生的故事套路——年轻貌美的王佳芝为刺杀汉奸而宁愿将自己的身体贡献出来,将性与爱、性与革命毅然分离。与余玥不同的是,王佳芝在为革命献身后并未坚持到底,在与易先生的身心纠缠中,革命信念最终输给了女性的肉身体验。此为,张爱玲为“革命+恋爱”模式下的女性成长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在革命与身体的双重变奏中,放弃宏大的革命理念而遵循身体的寻唤。
二、女性身份的想象与建构
《炸弹与征鸟》中的余彬在喧闹的男欢女爱中无法找到心灵的栖息之所,只能于落寞寂寥处叩问革命与生存的意义何在。余玥虽满心欢愉地同意为革命奉献自己的身体,但真正面临身心分离、灵肉分裂的考验时,仍难逃心灵的空虚与苦痛。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处境中,女性是接受传统的社会角色,自甘沦为男性的玩物,还是反抗女性既定的社会角色,投身革命继而充当革命的螺丝钉,放弃女性角色而转向中性甚至是男性化,这种两难选择是摆在当时的知识女性面前无法逃避也无法逾越的现实。小说借叙事来书写女性对身体的两种不同的安置方式,刻画女性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犹疑与尴尬,流露出作家对革命能否最终引导女性走向自我解放这一问题的真诚思考与追问。虽然在文本中,白薇将赞赏的目光毫不犹豫地投向了表征革命力量的余玥,但小说也借余玥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对革命进行反思,字里行间传达出她对革命女性命运的无限担忧。鉴于小说下卷已经遗失,我们也无法推断余玥未来将面临怎样的生活,但在小说上卷最后一句已有些许暗示:余玥受困于胃酸问题,“她将开始过异常刺激的生活了”。知识女性何去何从,不得而知。
蒋光慈以革命的乐观主义书写了曼英的身份转变,文本中曼英的蜕变看似并未经历多大的痛苦,轻而易举就获得了革命的新生。曼英、余彬与余玥,她们生存的时代背景、教育背景、生活追求与革命理想极为相似,单从文本来看,曼英好似比余彬、余玥姊妹更能适应革命的需求,实则是曼英内心的分裂与挣扎被作家有意悬置与延宕。曼英受过“五四”初期的新时代教育,自甘沦为妓女却无法接受“妓女”这一带有侮辱性的身份,反倒是总能够以复仇哲学来为自己开脱。以身体复仇,尤其是在男女两性的博弈中,当女性只剩下身体这一最后武器时,女性的悲哀处境已不言而喻。作为“革命+恋爱”模式的践行者,蒋光慈为女性设定的身份是男性主动下的革命同盟者,是男性革命者的坚定追随者。曼英在柳遇秋与李尚志之间的感情抉择实际就是这一写作模式在文本书写中的实践。
从写作时间来看,《炸弹与征鸟》《冲出云围的月亮》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这一时期正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中国革命走入低谷之际。许多革命青年受压抑的时代环境影响,在思想上陷入困顿之境,不少人开始放弃革命信仰甚至走向革命的对立面。这一时代烙印在这两篇小说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书写。余玥、余彬、曼英作为“五四”一代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代表,她们所经历的思想与革命的困惑、肉体与灵魂的分裂,她们所走过的革命成长道路,都是以情爱的方式来加以呈现的。可以说,情爱成了这些女性确证自我与实践革命的有效方式。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情爱成为涅槃于旧家庭、旧道德的新一代‘狂人’们最具政治价值感的革命性诉求,因而也是现代社会革命具有诱惑力和火药味的叛逆性的政治行为。”[7]正是这种时代语境催生了革命与情爱的结盟,以“革命+恋爱”为主要叙事模式的左翼小说风靡一时。从写作实践来看,这一写作模式无论是在男性还是女性作家笔下,都呈现出同一的吊诡性:女性追求个性解放、投身革命的方式最终都离不开男性的引领,并最终难逃以情爱的名义与男性共筑革命同盟的宿命,情爱与革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胶着在一起。“在社会革命程式之下,恋爱一经与革命遇合便被进行了赋以新质的改写,彰显出了不同寻常的意味,而红色恋人们的革命经历与恋爱过程也在一种奇异的同构关系中透射出了独特的意义。恋爱与革命交织谱写成的是一场上演在革命政治语境中的特殊言情故事。”[8]在《炸弹与征鸟》中,余玥、余彬都强烈追求个性解放,在反抗旧社会、旧体制的时候都以各自的方式来对待一己肉身。她们投身革命后的不同选择与走向,在安置身体这一问题上只是在程度和方式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余彬将对社会的失望、对革命的质疑转化为糜烂的私人生活,余玥则将个体的新生与对革命的追随化为对革命的奉献——以肉身为诱饵获取信息以达到革命目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曼英,同样也经历了混乱不堪的私生活,以妓女的身份来向男性社会复仇。遇见革命者李尚志之后,曼英的灵魂得到净化,进而身体也得以走向洁净,与李尚志结为革命伴侣共赴革命前程。可以说,曼英将余玥、余彬这两个人物角色合二为一,既体现了女性偏离革命、悬置肉身的游离,又反映了女性探索革命真谛、重返革命正途的艰难。《炸弹与征鸟》发表之际,左翼作家联盟虽还未成立,但该小说已然流露出浓厚的“革命+恋爱”的思想倾向。身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的白薇,在2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思考女性与革命、身体与政治权力间的关系,小说虽描写了余玥在大革命失败后思想上的困惑,但文本体现的更多的是作家从女性的立场设身处地对女性身份与身体的思索。《冲出云围的月亮》作为“革命+恋爱”小说的代表作,蒋光慈意在借曼英的革命成长与情爱抉择来体现女性可以借助革命与社会解放的力量从而获得自身的解放,但从文本却不难读出曼英的解放成功与否全系于男性革命者身上,曼英对男性的选择决定了她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命运。背叛革命的柳遇秋与忠于革命的李尚志,二者对待革命的立场与态度先验地决定了他们在曼英情感中的地位。可见,女性对革命的追随,是将自己的身体、情感与革命坚实地绑缚在一起,是在男性的引领下奔赴美好的革命前景。
不同于“革命+恋爱”小说的是,张爱玲并没有盲目地遵循“普罗小说”将革命的乐观主义进行到底的写作模式,而是对这一模式进行了改写——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让王佳芝背叛了革命同志与革命信仰,王佳芝对易先生一时的感动,彻底泄露了女性的自我与身体对革命、战争的犹疑与疏离。幼稚的王佳芝一时兴起加入革命队伍,在并不清楚革命的真实与残酷的懵懂中,逐渐陷入易先生编织的“爱情”罗网。两人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爱情,暂且不论。单看王佳芝主动委身于同学梁闰生、汉奸易先生的动机——刺杀汉奸,就不难把握她对自我身份的定位——随时为革命奉献一己之肉身。与曼英、余玥一样,王佳芝同样是无条件地响应革命的感召,并以自己的肉身去践履革命行动,女性的肉身都自觉地被革命收编,不同的是她的肉身最后却在性爱面前溢出了革命意志,个体情感浮出地表并最终击溃了革命理念。以往的“革命+恋爱”小说倾向于简单而粗暴地将女性的情感与肉身之间的冲突消弭于无形,在伟大的革命面前,女性的身体与灵魂能够轻而易举地合二为一。而张爱玲却以女性的敏感质疑了革命女性身心的双重对立,书写出女性在身体、灵魂间彷徨而无所皈依的、尴尬的历史处境与身份。
三、女性自我解放神话的反思
《炸弹与征鸟》《冲出云围的月亮》《色·戒》这三个文本,虽然写作时间不同,写作空间也迥异,但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文本中的女性都有着姣好的外貌,从被众多男性顶礼膜拜、紧紧追逐的交际花余彬到玩弄各个阶层男性于股掌间的妓女曼英,从以革命为自我实现的最终目标的余玥到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王佳芝,这些女性在外形上都拥有傲人的外在资本,或性感或妖娆或端庄或娇艳,都不同程度地吸引着男性的目光。虽然在《炸弹与征鸟》《色·戒》中,文本已对女性的身体与革命间的关系展开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与《冲出云围的月亮》一样,都是将女性置于物的、被看的、被消费的位置。这三个文本对女性在革命中的地位的处理上如出一辙:无论是在国共革命的洪流中,还是在抗日战争的硝烟里,女性参与革命的方式无一例外是依靠美貌,至于智慧、胆识、勇气、谋略、才情等等均被一一悬置,唯一重要的是女性一定要漂亮,一定要能够激发起男性的性欲望。对于女性而言,革命演化成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方式,参加革命就等同于将自己的身体与灵魂交付给了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力量,循着这一逻辑进而可以推演出女性为革命奉献肉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女性的身体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被所谓的“进步”革命加以编码,被纳入到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来。女性的身体唯有紧随革命的步伐,在男性革命者的引导下亦步亦趋,才有可能企及革命的顶峰,与男性共享革命成功后的盛宴。一旦稍有逾矩,女性就将面临余彬、王佳芝般的命运,或一蹶不振或香消玉殒,从而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这些文本中,由女性的身体所谱写的革命“神话”,彰显出了浓郁的时代气息与强烈的男权气质。无论是像白薇、张爱玲这样带有较为强烈女性意识的女性作家,还是自觉为女性代言的男性作家蒋光慈,他们都自觉赋予了女性身体以被动的、被压制的、有待唤醒的处境,不同的是张爱玲在书写女性身体与革命时,流露出更多的疏离与质疑。
对于男女两性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就曾指出:“性是人的一种具有政治内涵的状况”[9],而“政治”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10]。波伏娃在《第二性》当中也指出女性在父权制统治下的他者地位:“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11]在强大的父权制笼罩下,女性很难跳出男权制度所预设的种种陷阱,只能任由男性操纵与摆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性别身份并没有一个本质的、原始本真的样貌,可供人们去模仿与认同。一切皆文本,是文化与话语建构的文本。”[12]从这一意义出发,曼英、余玥、余彬、王佳芝这类知识女性只不过是作家书写与想象革命、战争的建构对象而已。在作家笔下,这类女性自觉接受革命与战争的权力规训,将个体的身体改造为适合于履行和完成革命需求的“守纪的身体”。福柯就曾在《规训与惩罚》中表明,身体并不单单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实体,身体更应理解为社会文化的建构物。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书写与建构女性的性别身份时,更能够从女性的体验出发,注重挖掘女性隐秘而复杂的内心冲突,在革命、战争、国家等宏大主题之外力图重返女性自身。
《炸弹与征鸟》《冲出云围的月亮》《色·戒》这三部描写女性在战争中生存处境的典型文本,虽在女性身体与身份的书写与建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文本的故事最终都诉诸同一个事实,即在价值的等级制里,女性永远都无法摆脱被革命、战争与男性物化的处境,女性的身体永远都只能蛰伏于战争的帷幕下,将物质化的身与精神性的心双重交付给所谓的国家、民族、革命战争等宏大却空洞的符码,任由摆布。女性看似被革命理想与革命理念所收编,究其实质最终却是被男性所改造,被以国家、民族之名的男性所驯服。“女人在婚姻里被赠送、在战争中被掳走、被用来交换恩惠、被作为贡品献出、被买进、被卖出”[13]的命运很难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女人的交换”在男性间不停地上演,有时会假以革命、战争、理想、牺牲等诸如此类的“正义”口号,有时甚至是直接赤裸裸地上演。文本中的女性无一幸免被卷入战争漩涡,自觉选择用身体来对抗时代与战争,对抗另一阵营中的男性。但是,等待女性的结局并不是伴随战争胜利而来的鲜花与荣耀,女性要么迷失在虚假的、盲目的革命乐观中,要么在自我营造的牺牲幻象中沉醉,要么在革命梦醒后身心俱疲。女性在贞女、妓女、交际花、革命斗士等多重身份间穿梭流转,个体的“女人”已无从寻觅,取而代之的是纳入革命、战争、国家等宏大背景下已经被改写、建构与规训的女性。被革命建构与书写的女性已很难与一般意义上的女人划等号,女性身心的自我觉醒显然也只能是对特定时代背景下女性生存命运的奢望。面对这些文本,我们难免要进一步追问:在动荡的历史处境中,女性参与到历史与时代的唯一通道是否只有革命这一种方式?是否只有牺牲身体这一招而别无他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女性的自我解放是否永远都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美好愿景?
注释:
①张爱玲在《惘然记》的序言中所提到的,《色·戒》写于1950年间,70年代末期发表之后又添改多处:“这三个小故事(《相见欢》《色·戒》《浮花浪蕊》)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但一般将该小说的写作年代定于1950年。
参考文献:
[1]苏红军,柏棣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1.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58.
[3][4][5]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2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22,24,25.
[6]梁小娟.革命想象与性别表述——论左翼小说中的女性成长叙事[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4):131.
[7]周仁政.创伤体验与早期左翼小说的革命叙事[J].江汉论坛,2013,(8):46.
[8]叶李.红色恋人的天路历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3):229.
[9][10][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7,36.
[11][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3.
[12]柯倩婷.性别身份的认同、戏仿与操演——从三位英国女作家的图文互涉策略谈起[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19.
[13]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A].女权主义理论读本[C].佩吉·麦克拉肯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