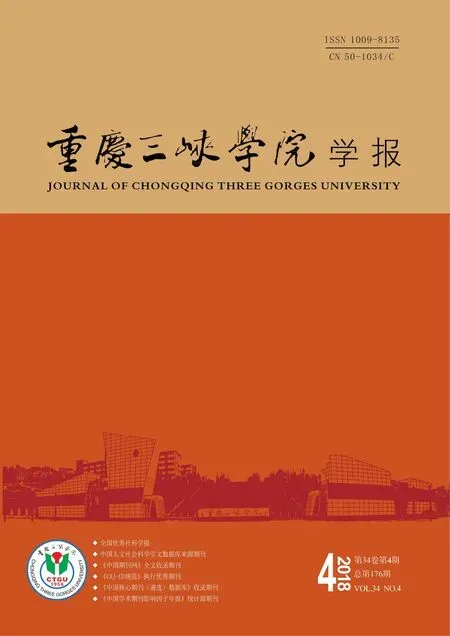论《变形记》中家庭权力网的动态平衡
胡秋冉 邹淑君
论《变形记》中家庭权力网的动态平衡
胡秋冉1邹淑君2
(1.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2.安顺市西秀区民族中学,贵州安顺 561000)
弗朗兹·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记》中格雷戈尔的变形不可避免地带出家人的“变形”,这不是个体的是非善恶问题,而是权力关系流动的本质属性所致。《变形记》明显运用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创新手法,却也从未抛离“现实主义”的肌质而显得抽象化、泛化。卡夫卡作品的复杂性在于他试图书写在一个不乏温情的家里,当养家人变为“异类”,恐惧与同情、嫌恶与愧疚、暴力与爱相纠葛的悲剧故事。梳理萨姆莎一家在家庭剧变中的权力关系流转之始末,揭示卡夫卡如何呈现家庭权力网与亲情之间震撼人心的遭遇。
《变形记》;卡夫卡;权力;动态;亲情
《变形记》(1915年)问世百年来,国内外最有影响力的解读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围绕人变虫形这个中心主题,我国卡夫卡研究专家曾艳兵用传记批评、心理学方法直接地(而非隐喻地)给出作家创造“变形”这个情节的一些现实根源[1];当代美国叙事学家麦克黑尔也以充分的理由将《变形记》列为后现代小说的一个经典文本[2]75-76。《变形记》石破天惊的开头为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赢得了连绵不绝的评论和后现代主义写作这个超越其时代的赞誉。半个多世纪后,当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形式实验的热情渐渐冷却下来,可以发现这种毫不夸张的盛誉似乎遮蔽了卡夫卡小说中看起来不那么“先锋”却极其深厚的笔力。
倘若换个角度,不把格雷戈尔看作唯一的主人公,而将家庭成员群像从一般默认的背景位置推至前景(foreground),那么对于格雷戈尔变形后家人的“变形”则鲜见系统、深入的讨论。毕竟,“人变虫”这个看似最戏剧化的情节在开头作为既成事实摆出却仅止于此,文本从未交待格雷戈尔是如何变成虫的、为什么变成虫的,且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故事中竟无一人追问这些再明显不过的问题。不妨反向思考,“人变虫”这个发生于本故事之前的“后台”事件本身或许没那么重要。开头只是设立了一种特别的情境,中篇小说的主体部分则是在这一情境下展开人与人(“虫”)的关系,篇幅安排即为明证。面对这场灾难,对家人的道德评价毫无意义,毋宁说家庭成员间具有彼此牵制与依附的关系,强弱者间的制衡是一场权力此消彼长的运动。正如福柯所言,“权力应当作为流动的东西,或作为只在链条上才能运转的东西加以分析”[3]27-28。本文拟梳理萨姆莎一家在家庭剧变中的权力关系流转之始末,揭示往往为评论者所忽视的这个先锋文本根基上的“现实主义”肌质,试对经典给出一种新的诠释。
一、父权及“重生”
纵观全文,父亲在家中的表现最为强硬,对儿子更是如此。他出场的显著形象是拳头,“在敲侧面那扇门了,轻轻敲,但用的是拳头”[4]48,“轻轻敲”和用“拳头”并置意味某种隐而未发的威力。虫形的格雷戈尔费劲地开门后,父亲要把他赶回房里(第一次),“还远远地用手杖尖端不时指挥他转身的动作”[4]57,野蛮地帮他摔进房间。小说的第一节即第一个高潮告终,结束这一切的是父亲,确切地说是他操控的手杖。手杖是父亲拳头的延伸,即父权的物化表征:操起手杖,是权力赋予宣言;以手杖指点儿子旋转,是用权威去引导;用手杖砰一声关门,是发挥权力的决定作用——作为“异类”的格雷戈尔不得越雷池半步,即“遭囚禁”①。“囚禁”的规训作用是惊人的,两个月后格雷戈尔听到母亲反对搬家具时才“清醒”:难道自己真希望让房间变成“洞穴”,可以任意爬行而忘掉人性?[4]66-7不过此番反省稍纵即逝,格雷戈尔最后正死于这间父权分配的囚室。
格雷戈尔一度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掌权的却一直是父亲。事发后父亲提及一笔不为人知的急救款,这笔钱本可以还掉父亲的一些债务从而使儿子早日解脱职务(格雷戈尔若非为父母计早就想辞职[4]46,这里叙事重复强调令人厌倦的推销工作)。父亲独揽大权的现实昭然若揭,儿子甘愿放弃最重要的个人权益,认同父亲的财政政策。随着儿子变成弱势之虫,父亲在外貌和精神上也“变形”了。之前,父亲疲惫不堪、举步维艰;如今父亲是一名银行杂役,身板挺直、神情专注、头发油光[4]69-70,这种变化并置于一段而非分布于前后文两处,是叙事的刻意标记。与卡夫卡的另一篇小说《判决》相似,本故事的扔苹果事件“跟判决儿子的死刑实质上是一样的”[8]29。此外,父亲总是妻女矛盾的裁决者(见下文)。
鉴于该小说的自传性已是公认的事实[9]209-10,将卡夫卡的书信《致父亲》(写于1919年)与《变形记》对读不无裨益。卡夫卡在信中说,“如果人们能够事先估计到我这个慢慢长大的孩子和你这个成人之间将怎么相处,就会想,你会一脚把我踩到地底下去,使我一点都不能露出地面的”[5]470(值得一提的是,格雷戈尔即将遭苹果袭击时小说确实从虫的视角描述过父亲的鞋跟,从字面意义上表达了对父权的感受)。可以说,《变形记》是《致父亲》的小说版②。卡夫卡唯一的对抗方式是写作,“在这方面,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走了一段路,尽管这有点让人联想起一条虫,尾部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5]496。父亲在卡夫卡“心中产生了一种神秘的现象,这是所有暴君共有的现象:他们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思想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人身上”[5]473。“暴君”的威权在小说中则以监禁、暴力及受害者的自我规训等形式呈现③。
总之,父亲始终是家中的最高权威,体力重生后更如君王:掌控经济,施用暴力,审判裁决。拳头—手杖—苹果,后两者均是前者即父权之手的延伸,且延伸得越来越远,对儿子的伤害愈来愈大。格雷戈尔变形前作为家庭支柱多少握有的几分权力被收回,它换来父亲体力和精神的重生。父子二人的权力回收与滑脱之间达成某种新的权力平衡。
二、妹妹的“新生”
葛蕾特是家中变化最大的人,从她接手照料格雷戈尔起。起先她准备了他喜欢的牛奶,承认其兄长身份。但开门张望后,她从惊吓到后悔自己的惊吓,到重新开门、小心进屋,显明其同情与恐惧交织的心理。不过妹妹仍坚持食物测试,观察动物习性,尽量满足其需求,不可谓不体贴,但清扫的动作说明她急于划清人虫界限。一个月后她撞见格雷戈尔眺望窗外吓得关门,不复有耐心,与前一次关门形成对比。格雷戈尔用床单罩着自己,而妹妹从未撤走这很不舒服的床单,“他甚至于相信在妹妹的眼神中捕捉到一点感激之情”[4] 65。随着格雷戈尔的动物习性(食物、气味、排泄物等)越发明显,葛蕾特的自我觉醒越发肯定,同情渐少,厌恶增长,最后那丝感激之情可谓她“变形”的预兆。
妹妹是唯一进出格雷戈尔房间的人,掌握后者起居的一手信息,便有了对格雷戈尔及其房间的“管辖权”。父母表示“认可”,而从前他们认为女儿“没用”[4]65,妹妹的欲望遂在父母的肯定下发展。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妹妹不顾母亲的异议及其对格雷戈尔恢复的希望,执意要搬走他屋内的家具以方便其爬行。她“已惯于摆出一副专家的姿态”,或许她“想把格雷戈尔的情况弄得更令人害怕,借此可以为他做更多的事”[4]67,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巩固自己的管辖权。搬家具时母亲因看见格雷戈尔而晕过去,妹妹给父亲的不完全解释导向苹果事件及格雷戈尔的致命伤。而文本交待得清楚,格雷戈尔是因搬家具的骚动才爬到隔壁房间,谈不上逃离“囚室”之意。固然不能说妹妹有意为之,但她于激动的情绪中事实上促成父亲的误解。妹妹工作后很忙,不再考虑格雷戈尔的饮食卫生问题,后者的暗示也无用。同时她的管辖权不许他人干涉,一次她发现母亲打扫了格雷戈尔的房间就向父亲告状,导致家中伤心的争吵。总之,妹妹已不抱格雷戈尔恢复的希望,利用自己的管辖权与“专家身份”压制母亲的愿望,并找到父权这个有力靠山。
妹妹在小说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第三节的小提琴事件。格雷戈尔听到琴声爬出,房客遂提出解约,混乱相对平息后葛蕾特郑重其辞,“在这怪物面前我不愿意说出我哥哥的名字”,她觉得全家仁至义尽,“得设法把它弄走”。父亲虽同情却有些犹豫,妹妹则愈发决绝,“它必须离开”[4]79。此前父亲用苹果做出象征性判决,但真正用言语宣告残忍“判决”的是妹妹。格雷戈尔想转身回屋时(第三次),因葛蕾特的“大叫”又引发一阵骚动。格雷戈尔忙不迭进门,父母都没有动,“只有妹妹站了起来”,急速扣门[4]79-80。格雷戈尔死后,一家人坐电车去郊外,父母发现女儿的美,认为是时候为她找丈夫了。
总之,葛蕾特在家中崛起是人性使然。格雷戈尔变形前,兄妹俩的家庭地位都很低。此后葛蕾特照顾他,一是因为哥哥一向对她很好,二来两个共同受制于父权的人必然生出一种相怜之心。葛蕾特受到父母肯定后,欲望逐渐膨胀,当意识到牺牲格雷戈尔并依附父亲更易满足她对权力的要求时,她的行为和性格越发特出,一跃成为后半部分最显著的人物。
三、母亲的失语
格雷戈尔变形一个月后,除妹妹不得不进入他的房间外,母亲第一个提出要去看儿子,这是对权力层提出的第一次异议。搬家具时,小说第一次提出格雷戈尔会不会恢复的问题,母亲对该问题的审视是第二次异议。最后在苹果事件中,母亲是唯一为儿子求饶的人,这是第三次异议。两个“第一”和一个“唯一”构成母亲对权力层的三次质疑。三次抗争两次受挫,母亲的清醒带来伤痛。前述打扫房间问题上的争吵亦可见母女的地位差距,萨姆沙夫人遭丈夫训斥,还得努力平复丈夫的心情。她渴望拯救儿子却身单力薄,夹在夫女之间唯以心灵的煎熬换取家庭的表面安宁。
给母亲造成最大伤害的莫过于小提琴事件。格雷戈尔爬出后母亲受到惊吓,但这同葛蕾特提出设法摆脱格雷戈尔的建议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父亲对女儿表示赞同后,“母亲仍一直喘不过气来,她用手捂着脸低声咳起来了,眼睛的表情像精神失常”[4]79。“精神失常”(“a wild look”[6]37)是感情色彩极重的词,是无声无力的恐惧和抗议,但母亲异常的神态未引起丈夫和女儿的足够重视。之后,女儿绕开母亲直接向父亲提出拯救家庭的那个可怕的“唯一的法子”。而母亲一直失语,格雷戈尔看母亲的最后一眼,她已完全睡着了。
格雷戈尔死后,母亲无需再徘徊于两个阵营之间。为证实虫之死,女佣用扫帚捅了捅,“萨姆莎太太动了一下,好像想挡住扫帚,但她没那么做”[4]81。尽管终究不忍女佣对格雷戈尔的粗鲁,她也只是跟随丈夫感谢上帝并画十字。一家三口去郊游时,母亲似乎也忘却了儿子。她曾在与权威的妥协中看着被禁闭者经历苦难,自己也从怜悯、痛心落向对现实的接受。卡夫卡在《致父亲》中提及自己的母亲总是在孩子与丈夫间力图调和,受尽折磨,萨姆沙夫人的命运大约与之相仿。
四、家庭权力网与亲情的遭遇
本文无意说明父亲、妹妹变得“恶”了(那样就成了一个通俗的伦理教化故事),卡夫卡作品的复杂性在于他试图书写在一个不乏温情的家里,当养家人变为“异类”,恐惧与同情、嫌恶与愧疚、暴力与爱相纠葛的悲剧故事。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场前所未有、骇人听闻的家庭剧变。眼见儿子变形后的第一瞬间,父亲握紧拳头似乎要把他赶回房间,“接着又疑惑不定地看看起居室,然后用手遮着眼睛哭了起来,哭得他壮实的胸膛也颤动起来了”[4]54。这是文本唯一一次直接描述父亲哭④,可见小说并未将父权的中心人物做恶魔化的简单处理。
小说的情节主体即格雷戈尔三次出屋、三次返回,不仅对格雷戈尔而且对家人来说都是极痛苦的经历;亦即,小说的三个小高潮均伴随家人心绪复杂的三次“退潮”。第一次被手杖赶回屋后,格雷戈尔据灯光推测家人在起居室守到深夜,读者亦不难推知这个沉默的夜晚充满哀伤⑤;格雷戈尔还注意到家人食欲不振、酒饭不思。父母在格雷戈尔的屋外等候女儿的报告,焦虑之心溢于言表。第二次,格雷戈尔被苹果砸伤后,父母意识到他是家庭一员,应忍住厌恶情绪并给予他“补偿”[4]71(这是否暗含父亲的悔意?):起居室门开着,格雷戈尔可以看见、听见家人。语调单一、冷静的叙述者显然不是不可靠的,因此隐含读者需注意其间一些显明的叙述干预,将其当作真命题来接受:“事实上他们已经够痛苦的了”[4]61;“阻碍家人搬家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完全绝望了,他们认为在所有的亲朋好友们中间,没有人像他们这样遇到如此的不幸。世界对穷人所要求的一切都最大限度地落到了他们的身上……”[4]73家人在一起常常泪眼相向或欲哭无泪。考虑这些无比真实的痛苦境地,格雷戈尔第三次爬出后妹妹的哭诉就不能不令人同情。处在这样的灾变中,父亲还试图与格雷戈尔有个协定,而妹妹终于说出“你只有设法不去想它是格雷戈尔,可我们一直相信它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幸”[4]79,这种求生本能几乎有了存在主义的况味。在格雷戈尔因伤残而异常艰难的返归途中,“全家人现在沉默而忧伤地看着他”[4]80,不再有前两次的激动情绪,深刻的痛楚在家庭骚动平复后现出。格雷戈尔死后,妹妹“一直看着尸体”:“你们看,他多瘦啊,他已有那么长时间什么也没吃了。放什么东西进去,拿出来的还是那些东西”[4]81。妹妹不再用人称代词“它”而改用“他”,其怜悯不能不说是真切的。
在书信、日记中,卡夫卡多次表达了对《变形记》结尾的不满⑥,或许正是因为该结尾过多表现了一家三口在春天的“舒适”[4]83和希望,似乎摆脱掉格雷戈尔是一种慰藉⑦,从而容易让人陷入一种较为简单的道德批评⑧。令人遗憾的是,大量关于家人不堪、亲情冷漠的论述就紧紧抓住这个结尾作证据。此类解读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本节述及的诸多重要细节,不免断章取义,将卡夫卡深刻的笔力大大简化了。
诚然,福柯认为“权力更属于‘政府’的范畴”⑨,未将其权力观应用于家庭,本文需要面对家庭权力网与亲情的遭遇这个不能完全照搬福柯的理论来解释的复杂问题。一方面在权力网中,“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个人是权力的一种结果……权力通过它建构的个人而通行”[3]28;易言之,是权力“建构”了“新生”的葛蕾特并通过她而“通行”。正是经妹妹“判决”后,格雷戈尔认为自己应该消失的想法比妹妹还坚决,当夜即死去。这似乎暗示是通行在妹妹身上的新兴权力直接导致格雷戈尔之死。另一方面,小说呈现了在权力关系流转遭遇亲情的途中,得势者与失势者共同而深切的悲痛。格雷戈尔时常回想家庭温馨的美好画面,临死前还“满怀感动和爱意地回想着家人”[4]81;按照叙述者及隐含作者的倾向,三个月来家人对格雷戈尔也确实尽力而疲惫不堪了。换言之,格雷戈尔变形后作为囚室的房间毕竟不同于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监狱,有爱的家庭中的权力关系流转更不是咄咄逼人的政治权力斗争,反过来,亲情也不可能人为地阻断家庭权力网的动态平衡,这注定是一个有关家庭真相的尖锐、悲伤的故事。“《变形记》则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但它也是人在发觉自己一下子变成动物时所经验的那种骇异感的产物。”[14]104-05加缪在此未及阐发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大约就是指家庭权力关系流转与亲情之间的巨大张力,此句中的“自己”若换成“家人”则更显意味深长。
五、结 语
现代主义作品最先打动人们的往往是其先锋特征,《变形记》前瞻于魔幻现实主义的文体风格和“人变虫”的特殊主题使其成为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短篇小说之一。但其经典性不仅在于这两点(进入文学史的缺点是易形成刻板印象),本文通过重返《变形记》的文本肌质,揭示了“人变虫”这个“后台高潮”之后,舞台上正在上演的是这部中篇小说真正的三次“变形”高潮——家庭成员之间(而非集中于格雷戈尔一个主人公变形前后)的等级关系在家庭权力网中的三次分布与流动。概而言之,父亲无论实力如何,始终是最高权威;妹妹一跃而为新兴权力及后半部分的最主要人物;母亲一直是权威的附庸,关键时刻往往陷于失语的晕厥状态;“异类”格雷戈尔则落于底层。一家人有权力的释放、接收,地位随之起伏,保持着权力网的动态平衡⑩。格雷戈尔的牺牲换来父亲的重生、妹妹的新生,顺便将母亲推回权威身边,一家三口得以开启新的(或恢复)中产阶级生活。易言之,格雷戈尔的“变形”不可避免地牵连出家人的“变形”,这不是哪个个体的是非善恶问题,而是权力关系流动的本质属性所致。《变形记》明显运用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创新手法,却也从未抛离“现实主义”的肌质而显得抽象化、泛化⑪。集先锋与深厚于一笔的卡夫卡独创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伦理的、存在的困境,从而得以通过家庭权力网与亲情的震撼人心的遭遇呈现其间的复杂性、尖锐性和悲剧性,其深度堪比古希腊悲剧。
[1] 曾艳兵.为何变形——卡夫卡《变形记》解析[J].名作欣赏,2006(7):44-51.
[2] McHale,Brian.Postmodernist Fiction[M].New York: Routledge,1989.
[3]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 弗朗兹·卡夫卡.变形记[M]//韩瑞祥,仝保民.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谢莹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5-84.
[5] 弗朗兹·卡夫卡.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M].张荣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6] Kafka,Franz.The Metamorphosis: The Translation,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Criticism[M].Trans.and ed.Stanley Corngold.New York: Norton,1996.
[7]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8] 叶廷芳.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
[9] 罗纳德·海曼.卡夫卡传[M].赵乾龙,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
[10] Beicken,Peter.Transformation of Criticism: The Impact of Kafka’s Metamorphosis[M]//The Dove and the Mole: Kafka’s Journey into Darkness and Creativity. Eds. Moshe Lazar and Ronald Gottesman. Malibu: Undena Publications,1987; excerpted and reprinted in Short Story Criticism[G],Vol. 35,ed. Anna Sheets Nesbitt. Detroit: Gale,2000: 259-69.
[11] Zilcosky,John. Samsa war Reisender: Trains,Trauma,and the Unreadable Body[M]// Kafka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Eds.Stanley Corngold and Ruth V.Gross.Rochester: Camden House,2015: 179-206.
[12] 范劲.格里高尔的“抽象的法”:重读《变形记》[J].外国文学评论,2015(4):44-63.
[13] Duttlinger,Caroli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Franz Kafka[M].Cambridge: Cambridge UP,2013.
[14] 阿尔贝·加缪.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G]//叶庭芳.论卡夫卡.刘半九,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3-13.
[15] Deleuze,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M].Trans.Dana Polan.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2003.
[16] Robertson,Ritchi.Kafka,Goffman,and the Total Institution[M]//Kafka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Eds.Stanley Corngold and Ruth V.Gross.Rochester: Camden House,2015:136-50.
[17] 弗朗兹·卡夫卡.卡夫卡口述[M].雅诺施,记录;赵登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8] Blanchot,Maurice.The Work of Fire[M].Trans.Charlotte Mandell.Stanford: Stanford UP,1995.
(责任编辑:郑宗荣)
①谢莹莹译为“被困”[4]62,张荣昌的翻译“遭囚禁”[5]58似更贴切,英译本作 “imprisonment”[6] 20。关于囚禁可联想福柯对疯癫的论述:古典时期疯癫被看作人身上的兽性,只能用纪律来驯服;“疯癫在人们的直觉中是异常(差异):因此,不是医生而是神志正常的人们的自发的集体判断要求做出禁闭一个疯人的决定”[7]66-8,另见第106、220、239页。卡夫卡的文本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对立模式:人不是疯了(以福柯之言,“疯癫借用了野兽的面孔”),而是在字面意义上变成动物(甚至不是福柯所谓的野兽,而是备受欺凌的弱小的虫),仍遵循这一社会逻辑;格雷戈尔虽无害却也因是异类(异常/差异)而遭囚禁。本文所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②转引自[10]265,该文简略引介了Heinz Hillman德语专著的观点:“Hillman将《变形记》看作是对普遍存在于掌权者和受害者头脑中的权力主义结构(authoritarian structures)的批评”。这句话可能与本文的关注点较为相近,不过未及展开。
③虫形的格雷戈尔第一次回屋受权杖的威胁,从此被监禁;第二次遭苹果的暴力袭击;第三次他依然如前两次一样真心希望尽快爬回去,但文本两处强调实际上他既无威胁亦无危险:“当然并没有人来催他,一切都随他自己的意愿”,“他一心想爬快点,根本没注意到家人并未用话语或喊声来干扰他”[4]80,突出了权力不再以暴力而改为以自我规训的模式运作。
④小说另有一次间接写到父亲哭:格雷戈尔死后,一家三口在卧室里谈话后出来,“他们三人眼睛都有点哭过的样子”[4]82。
⑤卡夫卡曾写信给出版社,强调《变形记》的封面图案绝不能画虫子,而建议“父母和代理在锁着的门前,或者更好的是,父母和妹妹在亮着灯的屋里,而隔壁完全黑暗的房间是开着门的”[6]70(出版社显然领会了作家的意思,首版封面是一个抱头痛哭的男子,他的背后是半开的门——这应该就指上段所述父亲的痛哭)。卡夫卡最中意的插图正是小说第一次“退潮”的情境,可见它有绝对重要的意义。
⑥卡夫卡一向对自己的作品苛刻,因一次突然的出差打断其写作而对该小说的结尾尤为不满。参见1912年12月6—7日他给女友Felice Bauer的信,又如1914年1月19日的日记,“不忍卒读的结尾”[6]68, 69。
⑦一家人去郊外的途中,文本只在搬家问题上提及一次格雷戈尔,“现在的房子还是格雷戈尔选的呢”[4]83。
⑧ Zilcosky总结说批评界几乎一致同意结尾的讽刺性,并注出德语、英语界6位重要的卡夫卡研究者对结尾的评论[11]196, 205-06,笔者的观点与之近似。范劲也认为卡夫卡的不满“可能是因为新生和死亡的对照多少还带有人工的痕迹”[12]。Duttlinger的意见不同,她推测卡夫卡对结尾的不满是因为它“打断了文本的有机整体性”,“叙述焦点不再系于格雷戈尔,而是穿梭于人物和地点之间”。尽管一家三口有哭过的痕迹,但“我们确实只亲眼见到他们对格雷戈尔之死更镇静的反应”;妹妹用的人称代词“它”也“仅仅在他死后”才能改为“他”[13]42-43。此番读解也调用了笔者论及的诸证据,但论述逻辑相反。
⑨《言与文》第3卷,238,629,转引自[3]263。
⑩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批判俄狄浦斯情结解读的基础上提炼出卡夫卡小说中另一种形态的“权力动态关系”(尽管他们未用这个词):一边是父—母—子的家庭三角关系及其他三角关系(即由代理引入的官僚三角关系和由三位房客引入的经济三角关系),以此教育孩子它们的驱力都是屈从,且从家庭扩展至社会;另一边是人变动物这一孤独的逃遁路径[15]14,另参第11-12、47、54页。Robertson具体观照了权力关系如何从家庭衍伸至社会机构:卡夫卡“对机构的理解”源自家庭的压迫之始,但他并非在写作中“抱怨父母的不善或虐待”,“孩子,依赖父母、陷于爱的联系而默默接受统治他们幼小生命的权力,内化这些行为标准,并将传之后代”[16]140-42。
⑪ 卡夫卡的写作观可予以佐证:“虚构比发现容易。把极其丰富多彩的现实表现出来恐怕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17]109。布朗肖看到了卡夫卡如何以悖谬的方式实现他的这一追求:“虚构叙述在作者身上塑成一段距离、一条裂缝(其本身亦为虚构),无此他就无法表达自己……他被卷入其中(implicated),在这个模糊之词的双重意义上[即“implicated”的多义性]皆如此:他质询(questions)自己,他也处于故事当中(in question in the story)——尽管他几乎被抹去”[18]21, 22。简言之,布朗肖认为卡夫卡小说中的超常故事、神话等其实是抵达现实的特殊方式。
On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of the Family-power Network in
HU Qiuran1ZOU Shujun2
In Franz Kafka’s novella, Gregor’s transformation inevitably leads to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family members, which is not about good and evil, but a consequence of the immanent nature of the dynamic flux of power relations. Apparently a modernist and postmodernist text, the story by no means loses its “realistic” texture or appears abstract. Kafka’s complexity is that he writes a tragic story of a loving family in which after the breadwinner metamorphoses into a different species, the other family members’ fear and compassion, detestation and remorse, violence and love, get entangled. Borrowing Michel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 this essay traces the dynamic flux of power relations in the family during the disaster and reveals its appalling encounter with familial love.
; Kafka; power; dynamic; family
I106
A
1009-8135(2018)04-0080-07
胡秋冉(1987—),女,安徽安庆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主要研究叙事学。邹淑君(1994—),女,贵州安顺人,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民族中学语文教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卡夫卡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之研究”(17AWW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