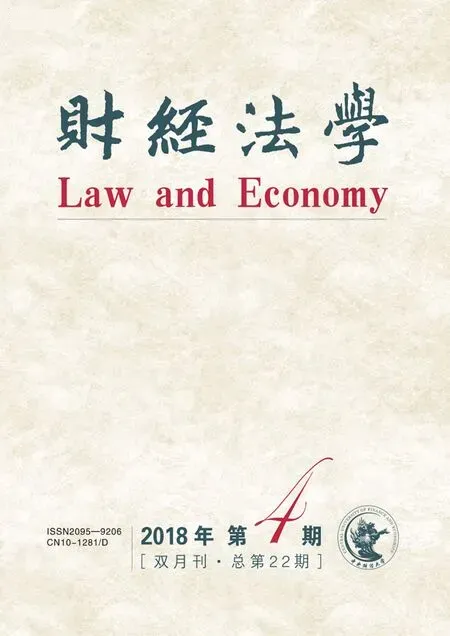“知假买假”的二元请求权基础及价值分野
吴逸越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95年“王海事件”发生以来,“知假买假”成为法学研究中一个持续的热点,争论也从未停止。“知假买假”并非法律术语,而是对一系列社会现象的口语化称谓。这些社会现象之所以会被归为一类案件,是因为“知假买假”的行为主体具有相同的目的——索赔。[注]“知假买假”实际上可以分为以消费为目的和以索赔为目的两种类型。前者指,消费者因为低廉的价格而购买假货,如购买盗版书籍。在以消费为目的的“知假买假”案件中,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一般不会发生关于赔偿的纠纷。相反,在以索赔为目的的“知假买假”案件中,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频繁发生纠纷。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案件范围仅限于以索赔为目的的“知假买假”。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符合一定的前提条件时,消费者可以获得超过实际损害数额的惩罚性赔偿。[注]参见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12页。而可以作为“知假买假”后进行索赔的依据的惩罚性赔偿条款主要存在于两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第55条第1款和《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因此,法律语境中的“知假买假”指:购买者明知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或者所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购买,之后分别依据《消保法》第55条第1款或《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行为。
关于法院是否应当认可“知假买假”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一直以来都存在激烈的争论。很多人将关键问题归结于一点:“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2013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食品药品规定》)第3条规定:“食品、药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不得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指导案例23号“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其判决认为,只要在交易中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是为了个人或者家庭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经营或职业活动需要的,就应当认定具有消费目的,属于《消保法》调整的范围,经营者认为“知假买假索赔”不是消费者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六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4]18号)。《食品药品规定》和指导案例23号试图将关注的重点从“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的问题怪圈[注]参见税兵:“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构造——以最高人民法院第23号指导性案例为中心”,《法学》2015年第4期,第102页。中带出来,回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笔者认为,即使认可了“知假买假”者的消费者身份,也不能一刀切地决定案件的最终走向,而应当综合考察是否具备相关请求权基础所要求的要件。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着重进行两方面的分析:第一,根据我国现有的相关立法和法律解释,并结合司法实践案例,认可一般情况下“知假买假”者的消费者身份。但是,这仅为法律适用的前提,并非解决“知假买假”相关问题的决定性因素。第二,沿用法教义学的路径,以《消保法》第55条第1款和《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为基础,分析作为请求权基础的两个条款在前提条件和保护目的方面的差异,从而将“知假买假”区分为两类不同的案件,尝试寻求各自的解决之道。
二、消费者的身份:法律适用的前提
除《消保法》以外,《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中也使用了“消费者”的概念。也就是说,“消费者”的身份是适用《消保法》第55条第1款与《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的前提条件。如果可以否定“知假买假”者的消费者身份,则上述惩罚性赔偿条款不能适用,其索赔目的也无从实现。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消保法》第2条往往被认为界定了“消费者”的概念。这一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其中突出了“为生活消费需要”。有观点认为,要具有“消费者”的身份,则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服务的行为必须完全是为了生活消费的需要。但在“知假买假”案件中,行为人“买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活消费的需要,而只是为了索赔获利。因此,该观点认为,“知假买假”者不具有“消费者”的身份,不能适用《消保法》与《食品安全法》中的相关条款。[注]参见程欢欢:“知假买假人诉请十倍赔偿不应得到支持”,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5月3日,第7版。但是,这一观点的立足点存在问题:《消保法》第2条并非对“消费者”进行定义。一般来说,进行概念界定的条文,其行文方式应当如《食品安全法》第150条中的各句。[注]例如,《食品安全法》第150条第1款规定:“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即定义性条款应当采用“……,指……”的表达方式,或者其他明确具有定义性质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语言表达上来看,《消保法》第2条显然并非定义性条款。《消保法》第2条没有采取定义性的条文构建方式,而只是进行样式描述。换言之,此处并非进行概念界定,而是通过描述主观目的来展示消费者的行为范式,即“为生活消费需要”是“消费者”的一种典型的主观状态,是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因此,从逻辑上来说,“消费者”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此。如果严格要求具有“生活消费需要”,则在无形中缩小了消费者的范围。
与我国《消保法》第2条的规定明显不同,德国《民法典》第13条真正对“消费者”进行了概念界定:“消费者指不以营利活动或者独立的职业活动为主要目的而从事法律行为的任何自然人。”荷兰《民法典》中没有一体化的、适用于整部法典的“消费者”概念,而是在“合同分则编”(第7编)中对不同合同类型中的“消费者”进行各自定义。例如,第7编第1a章规定了“分时使用、长期度假产品、协助交易和交易系统合同”,其中第50a条规定:“本章中,下列概念是指:a.消费者:并非在商业、经营、手工业或职业活动中实施行为的自然人;……”第7编2a章规定了“消费者信用合同”,其中第57条规定:“本章中,下列概念是指:a.消费者:为从事经营或职业活动以外的目的而实施行为的自然人;……”可见,无论德国《民法典》还是荷兰《民法典》,在定义“消费者”的概念时,均采用了排除法。排除营利活动、职业活动等之后,从事活动的自然人即为消费者,而并不限缩式地规定一定要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这种排除法的定义方式,维持了消费者概念的开放性,有助于避免对消费者身份的过分限制,也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相契合。
《食品药品规定》公布以后,刘俊海教授认为,第3条的规定对20多年来知假买假者是否是消费者的争议有一锤定音的作用,表明最高人民法院支持消费者知假买假。[注]参见刘俊海:“法院应热忱支持‘知假买假’”,载《经济参考报》2014年2月11日,第8版。但是,《食品药品规定》第3条并未使用“消费者”的概念,而代之以“购买者”,没有正面回应“知假买假”者的身份问题,而是避开了这一争论。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食品药品规定》中并不要求购买者具有“生活消费需要”的目的,实际上淡化了“消费者”身份对于主张权利的影响。
指导案例23号认定,购买者没有将商品用于再次经营销售,就不属于为了生产经营活动,应当认定为“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消费者,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范围。[注]参见前注〔3〕。但是,这一论证过程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这一论证过程只考虑到“营利目的”和“消费目的”两种类型,而忽视了处于灰色地带的“索赔目的”。[注]参见尚连杰:“‘知假买假’的效果证成与文本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88页。笔者认为,对于“索赔目的”需要具体分析。一般情况下,“知假买假”者是偶然发现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或者发现其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自知有利可图,从而“买假索赔”,所获得的惩罚性赔偿也是意外所得。此时,没有明显背离典型消费者的行为范式,仍然应当认可其消费者的身份。但是,如果出现特殊的情况,即有人将买假索赔作为职业,甚至成立打假公司,索赔所得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则应当认定是为了营利目的或者职业活动的需要。[注]“中国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于1996年成立第一家打假公司。到现在,已经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开设了四家职业打假公司,并通过打假获得高额报酬。成立打假公司之后,王海的打假行为的性质已经不同于其1995年因北京某商场出售假冒品牌耳机而索赔的行为,而成了职业活动以及营利活动,早已超出《消保法》规制的范畴。其在职业打假活动中也不再具有消费者的身份。参见王蔚佳:“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的20年”,载《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3月15日,第A11版。此时,其不具有消费者的身份。结合指导案例23号的案情来说,该案判决瑕不掩瑜,认可“知假买假”者的消费者身份是正确的。综合上述情况,除非极端情况,“知假买假”者的消费者身份已被确认。
也有学者认为,虽然“知假买假”者的消费者身份已成共识,但是保护“知假买假”有悖于《消保法》的立法宗旨。因此,提出将“知假买假”的消费者与《消保法》特别保护的消费者区别开来。例如,郭明瑞教授认为,“知假买假”者因其“知”也就不存在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除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外,不能受《消保法》的保护。[注]参见郭明瑞:“‘知假买假’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吗?——兼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当代法学》2015年第6期,第71页。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立法者认可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在法律规范层面对消费者进行保护,已经超越了具体情境中买卖双方强弱对比的范畴。[注]Hans Micklitz & Kai Purnhagen,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7. Auflage,Verlag C. H. Beck,2015,§ 13 Rn. 4.也就是说,只要法律行为人具有消费者的身份,则不论其事实上是否处于弱势地位,都一概适用保护消费者的条款,无须考察交易双方在现实中的强弱力量对比。比如,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消费者,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而前往小商铺购买商品。客观来说,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实力要强于经营者,但是依然适用《消保法》来保护消费者。况且,除信息获取能力之外,消费者相对于经营者的弱势地位体现在很多方面,如经济实力、谈判能力等等。[注]参见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55页。“知假”只能说明消费者辨别出了经营者的欺骗行为或者商品的瑕疵,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或者力量不对等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更不能说明“知假买假”的消费者不再需要《消保法》的保护。
经过《食品药品规定》第3条以及指导案例23号的认可,“知假买假”者也属于消费者逐渐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是,合理解决“知假买假”案件,才刚刚完成第一步,即法律适用的前提:“知假买假”的消费者也适用《消保法》、《食品安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而判断其惩罚性赔偿请求是否应当得到认可,则需要考察其是否满足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消保法》第55条第1款或者《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的前提条件。
三、二元请求权基础:“知假买假”的类型划分
在以往的文献中,以索赔为目的的“知假买假”往往被当作一类案件来看,试图寻求通用于这类案件的解决方法。[注]参见熊丙万:“法律的形式与功能 以‘知假买假’案为分析范例”,《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第300~339页。这些案件虽然具有相似的外观,但是其请求权基础呈现二元化模式——《消保法》第55条第1款和《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这两处请求权基础的保护目的不同,决定了其各自构成要件的不同,因而出现了两条不同的主张权利的路径。如果强行将其作为一类案件来看待,并试图寻找到一种适用于两类案件的处理方法,则只会顾此失彼,徒劳无功。
因此,应当将“知假买假”案件划分为两类并分别进行研究:以《消保法》第55条第1款为请求权基础的案件和以《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为请求权基础的案件。
(一)以《消保法》第55条第1款为请求权基础的案件
这一条款规定的前提条件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因此,核心问题在于对“欺诈行为”的认定。放眼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民法通则》等多部法律都涉及欺诈行为,而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对于“欺诈行为”的明确定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1.“欺诈行为”的概念同一性
虽然《民通意见》第68条明确界定了“欺诈行为”的概念,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能否运用《民通意见》中的认定标准来解释《消保法》第55条第1款中的“欺诈行为”。因为,“欺诈”本身在《民法通则》和《消保法》中发挥的功能并不相同:在《民法通则》中,欺诈是撤销法律行为的法定事实,以保护受欺诈者的意思自由;而在《消保法》中,欺诈是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一种法定事实。[注]参见朱广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适用”,《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106页。
笔者认为,虽然两处的欺诈具有不同的功能,可能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但这是同一法律概念的不同侧重点,即一个欺诈行为有可能造成损害意思自由和损害履行利益两种不同的后果。两种后果之间并不相互排斥,不影响“欺诈行为”概念的同一性。在德国《民法典》中,第123条第1款规定了欺诈行为,作为撤销法律行为的法定事实。[注]德国《民法典》第123条第1款规定:“因受到欺诈或者不法胁迫而做出意思表示的,可以撤销该意思表示。”但是这一条款位于总论部分,其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概念以及构成要件也适用于合同及侵权领域,作为请求损害赔偿的依据。[注]Ansgar Staudinger & Thomas Ewert,Täuschung durch den Verkäufer,Juristische Arbeitsblätter,Vol. 4,2010,S. 241ff.正如梁慧星教授所言,按照民法解释学,同一法律或者不同的法律使用同一概念时,原则上应做同一解释。既然《消保法》没有对“欺诈行为”进行定义,那就应该按照《民通意见》第68条进行解释。[注]Christian Armbrüster,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7. Auflage,Verlag C. H. Beck,2015,§ 123 Rn. 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1996年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2条对“欺诈消费者行为”进行了定义,与《民通意见》第68条基本一致。[注]《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消保法》第55条第1款规定的是“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只强调了经营者的行为方式,因此只需要考察经营者的行为,对于实际案件中的消费者是否受到欺诈在所不论。[注]参见刘保玉、魏振华:“‘知假买假’的理论阐释与法律适用”,《法学论坛》2017年第3期,第69页。这种观点实际上混淆了“单纯的欺诈行为”和“受欺诈的法律行为”。前者如经营者的欺骗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的事实表示,属于事实构成,不可能出现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而只有“受欺诈的法律行为”才是民法上所谓的“欺诈”,会导致承担民事责任。[注]参见徐志军、张传伟:“欺诈的界分”,《政法论坛》2006年第4期,第93~94页。而且,如果单方面考察经营者的行为,则实际上放宽了“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消保法》第55条第1款中的欺诈行为是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前提,而惩罚性赔偿是通过提高赔偿的数额来实现惩罚、威慑的功能,并非通过放宽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
因此,认定《消保法》第55条第1款中的“欺诈行为”时,也必须遵照《民通意见》第68条的认定标准。
2.“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
德国民法学者Dieter Leipold教授认为,欺诈行为有三个构成要件:第一,欺骗,指引起、加强或者维持对方对事实或者其他客观可以证明的情况的错误认识;第二,恶意,即欺诈人知道或者认为可能会给对方造成不真实的认识;第三,欺骗行为和对方做出的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至少是与其他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而因果关系的认定,则单方面从被欺诈人的主观认识来判断。[注]Dieter Leipold,BGB Ⅰ Einführung und allgemeiner Teil,9. Auflage,Verlag Mohr Siebeck,2017,§ 19 Rn. 2.我国《民通意见》第68条虽未明确列举“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但是从其文字表述中可以清晰地识别出几个构成要件:第一,“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这符合德国民法理论上的“欺骗”,主要强调欺诈一方的欺骗行为;第二,“故意”,这是规制欺诈者的主观状态;第三,“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表明对方当事人的错误意思表示必须由欺诈者引起,即规定了欺骗行为与错误意思表示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见,无论是德国的民法理论,还是我国《民通意见》第68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基本相同。
在“知假买假”案件中,因果关系的构成要件有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德国民法理论,关于“欺诈行为”的因果关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经营者的欺骗行为和消费者的错误认识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注]Andreas Feuerborn,In ,,Nomos Kommentar zum BGB“,3. Auflage,Verlag Nomos,2016,§ 123 Rn. 42.如果消费者对于所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的错误认识是由经营者的欺骗行为引起的,并且与之相符合,第一阶段的因果关系才构成。第二阶段,消费者的错误认识与所做出的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注]同上注。如果不是因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该消费者完全不会做出这项意思表示,或者不会在该时间做出包含该内容的意思表示。只有当两段因果关系均构成时,才可以认定欺诈者的欺骗行为与对方当事人的错误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经营者才能构成“欺诈行为”。在以《消保法》第55条第1款为请求权基础的“知假买假”案件中,经营者对消费者进行了欺骗,消费者最终也做出了看似受到欺骗的购买行为。但是,首先虽然经营者有欺骗行为,但被消费者识破,因此并没有导致消费者产生错误的认识。其次,消费者做出意思表示也并非由错误认识引起,而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通过索赔而获利。因此,在“知假买假”的情况下,欺诈者的行为虽然符合“欺骗”和“恶意”两个构成要件,但是因果关系并不成立,因此经营者不存在“欺诈行为”。
3.欺诈条款的保护目的
关于欺诈条款的保护目的,德国法学界的通说认为,是为了保护法律行为领域的意思表示自由。[注]Christian Armbrüster,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7. Auflage,Verlag C. H. Beck,2015,§123 Rn. 1.“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根源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法治思想。[注]Manfred Wolf,Jörg Neuner,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11. Auflage,Verlag C. H. Beck,2016,§ 10 Rn. 27.而保护意思表示自由则是“私法自治”原则的直接体现。虽然欺诈行为导致的后果是消费者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但是这种错误并非源于自身的误解,而是经营者在外部的误导,实质上属于意思表示缺乏自由。[注]参见前注〔21〕,徐志军、张传伟文,第92页。也就是说,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影响了消费者的自主判断。受到欺诈而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人,在自我决定以及做出意思表示之时,并不处于真正的、完全的自由状态。在“知假买假”案件中,购买者识别出了对方具有恶意的欺骗行为,其意思表示自由没有受到限制,所以,不属于欺诈条款所保护的特定的法益。而且,经营者的恶意欺骗行为往往只针对特定的消费者,因而这一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限制在交易双方之间,不宜夸大其不利后果。
因此,在以《消保法》第55条第1款为请求权基础的“知假买假”案件中,经营者确实有单方面的欺骗行为,但这是一种事实构成,不会独立引起民事责任的承担。消费者识破了骗局,其意思表示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因果关系的要件不存在,因而经营者不构成“欺诈行为”。此时,消费者如果“知假买假”并索赔,则不满足请求权基础的前提条件,其惩罚性赔偿的请求不应当受到认可。
(二)以《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为请求权基础的案件
《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法律责任的建构上类似于《消保法》第55条第1款。但是,该款中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是“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不同于《消保法》第55条第1款的规定。构成要件的不同实际上反映出两个条款在保护目的上的巨大差异。如前所述,惩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意思表示自由。但是,《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的规定与保护意思自由无直接关系,而是基于其他的保护目的。
食品药品由于其特殊属性,与不特定的大多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如果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进入市场,会对众多人的生命健康产生威胁。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如骇人听闻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注]案情参见“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09年第4号。“地沟油事件”、[注]案情参见“袁一、程江萍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地沟油’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0期。“瘦肉精事件”等。[注]案情参见“孙建亮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14年第4号。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普通消费者很难识别市场上销售的食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因此,法律规定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必须承担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定义务。《食品安全法》第4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法定义务在具体的条文规定中也有所体现。例如,第54条第1款规定:“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定期检查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结合上述条款可以看出,作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基础的《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的保护目的是保证进入市场的食品符合安全标准,保护不特定的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权益。
只要生产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即使并未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实际损害,《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的前提也已经满足。至于消费者购买食品时的主观状态如何,并非此时需要考察的因素。如果消费者明知某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却仍然购买,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明知食品已过保质期仍然购买,虽然其身体健康并未遭受损害,但是经营者或者生产者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其法定义务,威胁到了不特定的消费者的重大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认可“知假买假”的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指导案例23号中,法院依据修改前的《食品安全法》第3条和第28条第8项规定,认定食品经营者应当履行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定义务。[注]参见前注〔3〕。没有履行该项法定义务,即可以认定经营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虽然《食品药品规定》的公布与《消保法》的修改间隔很短,但是《食品药品规定》中明确说明,其依据《侵权责任法》、《合同法》、《消保法》、《食品安全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因而并非是《消保法》具体适用的细化规定。而且,第3条非常明确地将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限定为食品药品质量问题的纠纷,并不是广泛地适用于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一切纠纷。有学者指出,《食品药品规定》第3条允许食品药品领域“知假买假”适用《消保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只是一个特殊的规定,不应当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商品和服务。[注]参见李仁玉、陈超:“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法律适用探析——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的解读”,《法学杂志》2015年第1期,第53页。这一条规定应严格限制于食品药品质量问题的适用,而不适用于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案件。因为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定的保证食品安全的义务,威胁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权益,民事可罚事由已经构成。此时无论消费者是否“知假买假”,均不会改变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违反法定义务的事实,因此不得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在整部《食品安全法》中,无论消费者是怀着何种目的与动机,也不考虑是否存在意思表示的瑕疵,只要是购买了不安全食品,即属于该法规制的范围。[注]参见前注〔4〕,税兵文,第103页。
(三)两类案件的区别与联系
根据请求权基础的不同,“知假买假”案件可以分为上述两种类型。但是,“假”的表述难以涵盖两类案件的情形,还容易引起误解。如果将“假”理解成为通常意义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则与《消保法》和《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格格不入。因为“假冒伪劣”的日常含义可能横跨了两个不同的请求权基础的范畴。确切地说,在以《消保法》第55条第1款为请求权基础的案件中,“假”指的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该条款主要保护消费者的意思表示自由;而在以《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为请求权基础的案件中,“假”指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该条款主要保护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权益。虽然两个条款均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后果,但是针对不同的民事可罚事由,也适用不同的前提条件。
下面,笔者将利用一个案例来说明“知假买假”的两类案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A为某著名食品品牌,市价远高于普通品牌B的食品。某食品经营者在A品牌散装称重食品中混入部分B品牌食品,试图迷惑消费者,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某消费者发现了这一事实,仍然购买了食品若干,随后起诉要求惩罚性赔偿。经鉴定,A品牌、B品牌的食品均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在这种情况下,食品本身并无安全问题,经营者没有违反法定的保证食品安全的义务,因而不符合适用《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的前提条件。同时,虽然经营者有欺骗的行为,但是被消费者识破,其意思表示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因此经营者并不构成欺诈行为,消费者也不能以《消保法》第55条第1款为由请求惩罚性赔偿。这种情况下,该消费者只能以经营者未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为由,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通过买假索赔而获利的目的无法实现。
四、结论
“知假买假”案件自从出现以来,就不断成为争议的焦点,导致了法律适用上的很大困扰。法学界和实务界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却将重心放在了“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的讨论上,对消费者的身份展开了拉锯式的争论。但是,消费者的身份只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并非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性因素。真正决定“知假买假”者的索赔请求能否得到认可的,只能是其是否满足法定的请求权基础的前提条件。
“知假买假”并非一个严谨的法学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均十分模糊,缺乏法教义学上的梳理和研究。明确“知假买假”的二元请求权基础,明确各自的前提条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由于不同请求权基础的立法目的和保护法益的重大差异,“知假买假”实际上涵盖了以《消保法》第55条第1款为请求权基础和以《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为请求权基础的两类案件。前者针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保护消费者的意思表示自由;后者针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保护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权益。
明确两个请求权基础的各自前提条件之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消费者明知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骗行为而仍然购买,经营者不构成欺诈行为,消费者根据《消保法》第55条第1款的惩罚性赔偿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生产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已经违反了法定义务,即使消费者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而仍然购买的,也可以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请求惩罚性赔偿,法院应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