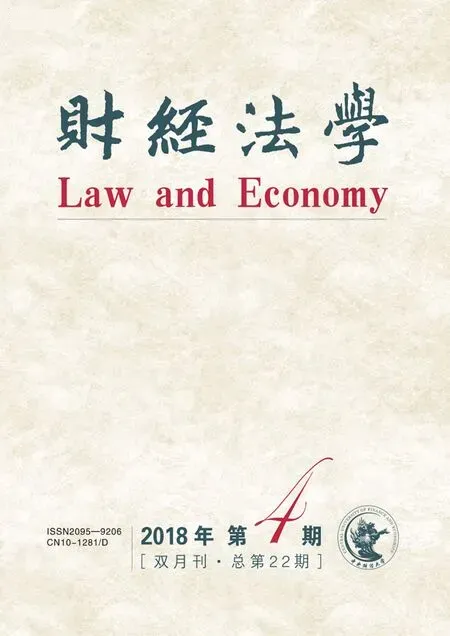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现实困境及其消解
杨 慧
当今社会,很多艺术品都已不再局限于单纯满足人们的鉴赏和收藏需求,而进一步衍生出实用功能,从而产生了同时具备艺术性和产品实用功能的实用艺术作品。[注]也有学者称之为“实用艺术品”。上述两个语词的产生主要源于学者对《伯尔尼公约》中“Work of Applied Art”一词在翻译和理解上的偏差,但这两个语词在理论和实务中并没有被严格界分。由于“实用艺术品”并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故笔者在本文中采“实用艺术作品”的称谓。从更好发挥其功用的目的出发,该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给予实用艺术作品最有效的保护。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学者主要从著作权视角思考对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此外还有若干从外观设计专利权、商标权、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对其予以保护的研讨。在著作权的研究视角下,实用艺术作品的概念、[注]参见管育鹰:“实用艺术品法律保护路径探析——兼论《著作权法》的修改”,《知识产权》2012年第7期,第55页。特征、保护路径比较[注]参见杜颖:《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等理论问题是学者们的中心关注,而鲜见立基于司法实践之上对实用艺术作品独立纳入著作权保护对象的充分论证。于此背景下,本文重点从司法实践出发,结合《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第5条第9项和第29条第3款的内容,探讨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路径并化解这一路径中的潜在风险。
一、实用艺术作品的内涵与外延
(一)实用艺术作品的内涵
纵观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实用艺术作品”一词最早出现于国务院1992年9月发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注]《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第6条规定:“对外国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期,为自该作品完成起二十五年。美术作品(包括动画形象设计)用于工业制品的,不适用前款规定。”该规定的出台主要是为了履行《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的义务。中,但该规定并未释明何为实用艺术作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编写的《著作权与邻接权法律术语汇编》一书中首次明示了“实用艺术作品”的含义:是指“适于作为实用物品的艺术作品,不论是手工艺还是按工业规模制作的作品”。[注]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著作权与邻接权法律术语汇编》,刘波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中的“实用艺术(作品)”:适于作为实用物品的艺术作品,不论是手工艺还是按工业规模制作的作品,著作权法可以确定其本身在多大范围适用于这类作品。实用艺术作品概念的英文原文为Applied art (Work of-)An artistic work applied to objects for practical use,whether handicraft or works produced on an industrial scale.Copyright laws may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apply to works of this kind.在我国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首次明确阐释了实用艺术作品的概念。该草案几经修改,最终在2014年6月6日的《送审稿》中将“实用艺术作品”定义为“玩具、家具、饰品等具有实用功能并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并将其与美术作品一道作为作品的子项目予以规定。从表述上看,我国沿袭了国际上对于实用艺术作品的定义。
(二)实用艺术作品的外延
从上述概念中可以看出,实用艺术作品具有实用性(实用功能)和艺术性(审美意义)的双重属性,正是这种双重属性使得其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存在着受“著作权保护”和“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的两种可能性。从两种属性的结合方式上可将实用艺术作品分为三种类型:其一,只有在实用艺术品的艺术成分与实用成分可分离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实用艺术作品。[注]参见前注〔2〕,管育鹰文,第57页。常见的方式如将美术作品印制在实用品上,或者直接将雕塑等立体美术作品制作为实用品等。这种观点以美国《版权法》的规定为代表。[注]美国《版权法》第113条在提到绘画、刻印和雕塑作品的专有权利的范围时,都将该作品与实用艺术作品区分考虑。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Chapter 1,∮113(2003).郑成思教授也曾在其著作中强调:实用艺术作品保护的着眼点在实用的“艺术品”而非“实用”的艺术品,因此其艺术性成分必须能够独立于产品的实用功能而存在。[注]参见郑成思:《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其二,只有艺术成分与实用成分不可分离才构成实用艺术作品。[注]参见谢渊:“论实用艺术作品双重保护的正当性——兼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第一稿涉实用艺术作品相关内容”,《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68页。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外形、色彩、线条及其结合融合在一起的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实用品,才能构成实用艺术作品。其三,只要兼具艺术成分和实用成分者均为实用艺术作品,不考虑两者是否可分离。该种观点认为,采这种认定方式不仅有利于激发创造者的创作积极性,而且还可以促进版权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参见孟祥娟:“实用艺术作品宜为著作权独立的保护对象”,《学术研究》2013年第3期,第47页。
尽管上述对实用艺术作品外延的分类均是从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结合方式出发,但从其表述中可以看出,三种分类方法实际上各有侧重。第一种分类侧重于实用艺术作品的核心是艺术性,实用性只是代表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种可能性。易言之,艺术性是实用艺术作品的本体特征,实用性相对于艺术性来讲是第二性的特征。第二种分类强调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同等地位,两者都是第一位的特征,且紧密结合、不可分割。具体而言,这种分类方法要求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成分本身具有实用性,实用造型就是其艺术性的载体。不过,这种分类方法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倘若遵循该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将实用艺术作品与美术作品予以区分。第三种分类则强调最大限度地保护实用艺术作品。按照该种分类方法,只要具备了实用艺术作品所必需的实用性与艺术性,不管两者以何种方式结合,都可以将其认定为实用艺术作品而加以保护。但该定义有过分扩大实用艺术作品的外延之嫌,同时其实用性与艺术性不可分离的部分在实践中亦存在认定上的困难。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一种分类方法较为适当,即只有当艺术性成分可以从实用性成分中被识别和分离出来时,才能构成实用艺术作品。理由在于,首先,该种分类强调了实用艺术作品的核心是艺术性,这是其定义之根基;其次,该种分类弥补了其他两种分类在可操作性上的不足,更加有利于实用艺术品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实现;最后,该种分类兼顾了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既不会不当减少当事人寻求救济的途径,亦不会显著增加当事人举证上的困难。
二、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现实困境
(一)路径之争: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路径尚未统一
笔者以“实用艺术作品”为关键词在无讼案例网上进行检索,剔除无关和重复样本后,共获得131件关涉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案件。[注]参见无讼案例网:http://www.itslaw.com/bj,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2月31日。从这些案件的裁判文书中可以窥见,尽管我国现行法律中缺乏对“实用艺术作品”的规定,但“实用艺术作品”这一语词在司法实践中已得到了广泛应用。具体而言,当事人均试图通过证成自身产品属于实用艺术作品而得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法院也普遍认同将实用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的保护范畴是对其予以周全、妥适保护的必由之路。不过,在进一步阐明实用艺术作品缘何应受《著作权法》保护时,由于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法院的论证思路出现了分歧,分别为实用艺术作品选择了美术作品保护路径和作品保护路径(也即下文的单独保护路径,容后详述)。
1.美术作品保护路径
为了使自身的诉请和裁判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前述大多数案件中的当事人和法院都试图将实用艺术作品涵摄于美术作品的概念之中。早在世纪之交,于“胡三三与裘海索、中国美术馆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即认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美术作品不仅限于纯艺术性的美术作品,亦可以将实用艺术作品囊括在内。[注]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二中知初字第145号。循此思路,对服装艺术作品的保护可以准用对美术作品进行保护的相关规范。近十年间,于“菲维亚珠宝有限两合公司与中山众华堂工艺品有限公司、珠海众华堂珐琅首饰研发中心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中,两审法院均认为,菲维亚公司的涉案饰品是实用艺术作品,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实用艺术作品可以归入美术作品项下而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注]参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20民终1574号。亦可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苏民三终字第0115号。宜充分关注的是,对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采上述保护路径的法院在具体展开论证时往往以美术作品为参照对涉案实用艺术作品进行审视,[注]参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厦民初字第963号。要求其在具有因承载实际使用价值而产生的实用性基础上,还需达到足以匹配美术作品的艺术高度,[注]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粤高法民三终字第504号。即具有因审美意义而产生的艺术性。[注]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5号。
2.作品保护路径
随着实用艺术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类型日益多元,围绕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而产生的纠纷不再鲜见,司法实践中也应运而生了另一种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路径,即作品保护路径。这种保护路径直接从作品的应有内涵出发,论证实用艺术作品符合作品的基本定义,尤其是能够满足作品的独创性要求,进而可以归属于作品的范畴而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注]参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厦民初字第962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浙知终字第122号;亦可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深中法知民终字第415号。如在“泉州丰泽正月娇工艺公司诉东莞梵歌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著作权归属、侵权纠纷上诉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正月娇公司主张享有著作权的“大象头壁挂”是具有实际用途的艺术作品,其所采用的艺术设计在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创作程度,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创作者的智力成果,故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注]参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19民终6961号。值得注意的是,对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采这种保护路径的法院不再将实用艺术作品与美术作品进行比照,而是追本溯源,透过涉案实用艺术作品的有形载体,对其中的艺术加工从意思传达、风格手法、表现形式等方面予以综合考量,[注]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107号。进而就其是否满足了作品之所以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性特征给出判断。[注]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川民终字第627号。
(二)对象之辨: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对象仍不清晰
显而易见,在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对于实用艺术作品应当同时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已初步达成了共识。与此同时,法院在认定涉案作品是否为实用艺术作品时也主要参考实用性与艺术性两个衡量指标。[注]参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中法知民终字第41号;亦可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号。一般认为,所谓实用性,侧重于强调物品的用途、功能等,即其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而所谓艺术性,则侧重于强调物品的外观造型、色彩装饰等,即其能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人们的鉴赏需要。由前述实用艺术作品的内涵和外延可以推知,艺术性是实用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和内在属性,实用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艺术创作是其得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为,在将实用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时,其受著作权保护的对象仅为实用艺术作品中的艺术性表达部分,而不及于纯实用部分。[注]参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甬知初字第142号;亦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3)民申字第1350号。
然而,在具体界定著作权的保护对象时,虽然不同法院均承认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成分可以与实用功能剥离开来而独立存在是其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前提条件,[注]参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19民终8368号;亦可参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益法民三初字第14号。但它们对于实用性与艺术性“可分离”的理解却存在显著差异。如在“MGA娱乐公司与温庆浩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产品将艺术创造与实用造型紧密结合,其艺术性承载于产品的实用造型之上,透过该产品的整体、局部设计和颜色搭配而表现于外,故其属于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实用艺术作品。不过,二审法院却认为,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涉案产品的艺术性,但这种艺术性是依附于产品的实用功能而存在的,倘若变更该产品现有的艺术设计,则其实用功能亦将受到影响,故其不属于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实用艺术作品。[注]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粤高法民三终字第74号。在上述案例中,两审法院均强调一种产品欲构成实用艺术作品,其艺术性所呈现的艺术美感必须能够与其实用性所呈现的实用功能分离开来,当然这种分离既可以是物理上的也可以是观念上的。不过,两级法院对实用性与艺术性是否“可分离”的判断方法和标准却并不相同,这种差异最终使它们对涉案产品是否属于著作权保护对象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具体而言,一审法院主要是从社会一般公众的鉴赏视角进行判断的,即考察涉案产品中的艺术成分能否在公众的头脑中被独立地欣赏,这是一种较为主观的、注重受众心理感受的判断方法;而二审法院则主要是从产品生产者的设计视角进行判断的,即考察涉案产品中的艺术成分是否在事实上承担了实用功能,这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注重产品实际效用的判断方法。一般而言,法官在运用上述两种方法对实用性与艺术性是否“可分离”进行自由裁量的过程中,使用前一种方法对“可分离”的标准要求较低,多见于支持涉案产品构成实用艺术作品的判决中;[注]例如“无锡市海谊工艺雕刻公司与李嘉善著作权侵权纠纷上诉案”,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苏民三终字第0115号;又如“美高品牌有限公司诉汕头市顺胜玩具实业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参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汕中法民三初字第107号。相反,使用后一种方法对“可分离”的标准要求较高,多见于否定涉案产品构成实用艺术作品的判决中。[注]例如“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广州冠以美贸易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上诉案”,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73民终537号;又如“张翔、中山市飞图服装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上诉案”,参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20民终4505号。
(三)独创性之断:实用艺术作品的独创性标准较难界定
承前所述,证成实用艺术作品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在物理上或者概念上相分离仅仅是其得以获得著作权保护的第一步,关键则在于阐明其艺术性达到了作品的“独创性”要求。毋庸置疑,独创性是作品的根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实用艺术作品欲作为作品的一种而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当然就必须符合“独创性”的要求。不过,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具体把握实用艺术作品的独创性标准时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裁量思路,每种裁量思路下具体的裁量标准也有较大差异。诚然,这种实用艺术作品独创性判断思路和标准的不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所解释,但亦经常会面对“同案不同判”的质疑。
具体而言,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以一般作品的独创性判断标准对涉案产品是否具有独创性进行判断。如在“黄炳登与中山麦杰婚纱有限公司、袁选贵、郑素莲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产品中创作者所选择的创作元素虽较为常见,但其对于创作元素的选择、组合、排列却付出了体现自身智力成果的劳动,其最终所呈现出的产品是有别于他人的原创成果,故应当认为具有独创性。[注]参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中一法知民初字第14号。类似的案件又如“宁波巨扬日用品有限公司与宁海金昌文具厂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参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甬知初字第142号;“欧可宝贝有限公司诉慈溪市佳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二中民初字第12293号。事实上,一审法院的上述观点亦与部分学者对实用艺术作品独创性判断标准的论述暗合,即对实用艺术作品是否予以著作权保护不应考虑其艺术质量的高低,只要其中的艺术成分是独创的,就应当予以保护。[注]参见丁丽瑛:“实用艺术品著作权的保护”,《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38页。不过,有相当数量的法院对此持有反对态度。如在“Joby Inc.与余姚市辰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艺术作品必须能够清晰、确定地传达一定的情感并使受众能够有效感知,这需要其能在思想与表达方面达到一定艺术高度,而非通过简单的线条和动态变化就能实现,故涉案产品不具有独创性。[注]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浙知终字第122号。类似的案件又如“上海澳托克数字仪器有限公司与罗托克控制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5号。与法院的此种独创性判断思路相对应,由于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中并无对实用艺术作品的直接规定,亦有部分法院以美术作品的独创性判断标准为参照对涉案产品是否具有独创性进行判断。有法院认为,实用艺术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应适当低于纯美术作品而定位为“具有一定的审美个性”。[注]该案件为“华斯实业集团肃宁华斯裘革制品有限公司与无锡梦燕制衣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上诉案”,参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7)冀民三终字第16号。事实上,先前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阐发,认为这种审美个性可以体现于产品设计中的外观形状、空间结构、色彩搭配、人物或动物的脸部或动作造型等诸多方面。[注]See Tina Hart,Linda Fazzani & Simon Clark,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Palgrave Macmillan,2003.不过,亦有法院认为,从实践趋势可以看出,实用艺术作品中艺术性的独创性标准应远高于一般作品,可以匹配美术作品通常能够达到的高度。[注]该案件为“厦门华海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与厦门瑞川复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其他著作财产权纠纷案”,参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厦民初字第963号。类似的案件又如“上海盈扩实业有限公司、黄德宏与刘伟传侵害作品复制权纠纷上诉案”,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333号。
(四)侵权认定之困:实用艺术作品的侵权认定标准有失规范
紧承前述,在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中,当涉案产品的实用艺术作品属性被法院认可,也即法院同意给予其著作权保护后,自然会产生侵权认定标准的问题。事实上,法院对于这一标准的把握将决定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会在何种程度和范围内受到保护,也即关乎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制度的最终实现。
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采取与一般著作权侵权判定类似的“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定标准。如在“英特—宜家系统有限公司与台州市中天塑业有限公司侵害其他著作财产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原告销售的涉案产品属于投放在市场中的、大众可接触的产品,故被告具有接触该产品的可能性,即以接触可能为侵权成立的先决条件。所谓接触可能,是指依社会通常情况,被告有“合理机会”或“合理可能”阅读或者听闻、了解或者感受到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注]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87号。在肯定具有接触可能之后,该相似部分是否达到“实质性相似”就成为案件审理的关键。上述案件中,法官将诉争产品进行对比后认为,“原告购买并经公证的被告公司的涉案产品在整体外形上与自己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相似或基本相同”。但令人遗憾的是,法院并未就进行对比时所采用的标准进行清晰而详尽的说明。须为注意,“实质性相似”具体标准的缺失使得法官通常在仅仅进行简单对比的基础上即依据自己的内心确信来判断被告是否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注]例如“美高公司诉陈岱光其他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参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汕中法知初字第19号。又如“斯平玛斯特有限公司诉蔡杏川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案”,参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汕中法知初字第80号。此种做法的盛行不仅会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张,而且有碍于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制度之本旨的实现。[注]参见吴汉东:“试论‘实质性相似+接触’的侵权认定规则”,《法学》2015年第8期,第69~70页。
三、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单独保护路径的原因分析
(一)实用艺术作品本质上显著区别于美术作品
综据前述,当前司法实践之中存在两种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路径,此两种路径的并存对实用艺术作品实用性与艺术性之“分离”、独创性的判断等具体问题的解决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欲消解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困境,必须统一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路径。近年来,主张应对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采单独保护路径的观点逐渐为立法和司法所接受(容后详述)。透过现象究其本质,单独保护路径的正当性基础即在于实用艺术作品与美术作品存在根本性质上的差别。
1.两者在概念上有重叠之处
《送审稿》第5条第8项规定:“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法律并没有明定美术作品只能为观赏存在而不能具有某种实用价值。因此,仅从概念上来看,实用艺术作品和美术作品似乎存在着某些重叠,并不能对两者进行完全的区分。有学者认为,美术作品既包括纯美术作品,也包括实用艺术作品。前者指纯粹为表现个性与美感而创作的美术作品,一般专供陈设、欣赏、收藏使用;后者指不仅为表现艺术美感,而且还为满足生产或生活需要,并投入产业制作、销售的艺术产品。[注]参见丁丽瑛:《知识产权法专论》,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这种观点一度成为学界通说,也正是前述司法实践中多援引美术作品的规定对实用艺术作品纠纷进行裁判的理论基础所在。
2.两者在本质上相互排斥
尽管我们无法通过文义解释的方法对美术作品与实用艺术作品予以泾渭分明的界分,但通过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的。第一,从著作权法律体系之角度考虑。美术作品作为纯艺术作品,属于文学版权领域;而实用艺术作品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其功能性,属于工业版权的范畴。由于二者从属于不同的领域,故其在制度设计上亦有着各自的偏向性。美术作品在创作之初主要是为了鉴赏和收藏,艺术性特征是其本质特征。正因如此,美术作品的原件具有特殊的收藏价值,其意义远大于复制件;而实用艺术作品的创造动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其实用性,其价值往往通过吸引消费者购买并加以使用的方式得到实现。因此,实用艺术作品往往要进行批量生产,原件和复制件区别甚微。[注]参见吴伟光:“中文字体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国际公约、产业政策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影响与选择”,《清华法学》2011年第5期,第67、76页。这种差异也会在司法实践中对两类作品在保护上的不同侧重点中得到体现。第二,从立法目的之角度考虑。根据法律规定,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是特别规定的,只有25年;而美术作品的保护期则为作者生前加死后50年。倘若实用艺术作品是美术作品,25年的保护期就会被50年保护期所涵盖。这种涵盖将导致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制度被“架空”,立法上显然是排斥此种假设情形发生的。
(二)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单独保护符合立法趋势
纵观世界各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对实用艺术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具体保护方式上,既有将其作为单独对象加以保护的模式,也有将其归入美术作品行列加以保护的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通常根据是否具有实用性将艺术品分为纯美术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并同属著作权保护的范畴。[注]法国《知识产权法典》(2016年4月25日合并本)L.112—1条规定:“本法典的规定保护一切智力作品的著作权,而不问作品的体裁、表达形式、艺术价值或功能目的。” 同时,该法典L.112—2条第10项将实用艺术作品单独列为“被视为本法典意义上的智力作品”。参见黄晖译:《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3页。与此相对应,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国家则明确将实用艺术作品作为美术作品予以保护。从美国《版权法》第101条的规定中可以窥见,美国将实用艺术作品作为图案、图形、雕塑作品这一类别的一个子项予以明确规定,它们均归属于美术作品的范畴。[注]美国《版权法》第101条规定:“绘画、图形和雕塑作品,包括平面的和立体的艺术作品,图形作品,实用艺术作品,摄影作品,印刷和艺术复制品,地图,球体,图表,图解,模型,技术草图,以及建筑设计等作品。这类作品应当包括工艺美术品,但只涉及他们的外形而不涉及他们的机械的或功能的方面。” 参见李明德译:《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页。与之类似,日本《著作权法》第2条第2款也明文规定:“本法律中规定的‘美术著作物’包括工艺美术品”。
由上文所述可见,无论对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采美术作品保护路径抑或单独保护路径均是符合国际趋势的。此时,应将其置身于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寻求最优路径。尽管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并无实用艺术作品的规定,但在《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中却有保护25年的规定。[注]《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第6条规定:“对外国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为自该作品完成起25 年。美术作品(包括动画形象设计)用于工业制品的,不适用前款规定。”此种超国民待遇的规定主要是为了完成《伯尔尼公约》规定的义务,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质疑。[注]参见国家版权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2012年3月,第7页。为与上述规定相适应,并考虑到实用艺术作品与美术作品的诸多差异,多年来我国一直有将“实用艺术作品”明确列入《著作权法》的建议,但由于存有下述若干技术和理论上的疑难而一直未能实现。这些疑难包括:第一,实用艺术作品同纯美术作品不易区分。有些美术作品创作出来的时候属于纯美术作品,但亦可以应用在工业产品上。例如齐白石的画最初是纯美术作品,以后可能印在茶杯上。假使印有美术作品的茶杯也由《著作权法》保护,就会混淆文学艺术作品与工业产品的界线,而工业产品本应由工业产权调整,不应由著作权法调整。第二,实用艺术作品同工业产权中的外观设计不易区分。工业产权保护在手续和保护期方面显然不具备著作权保护的优势,如果都用著作权保护,将会严重影响工业产权保护体系的发展。[注]参见中国人大网:“中国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第一章关于“美术作品”的释义,载http://www.npc.gov.cn/npc/flsyywd/minshang/2002-07/15/content_297588.htm,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2月12日。事实上,以上两个疑难均可以通过全面理解实用艺术作品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并对这两个特性予以恰当的分离来解决。诚如前述,兼有实用性与艺术性是实用艺术作品得以存在的前提,而《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仅限于其中的艺术性成分,对于其实用性部分,则需要诉诸工业产权的保护。通过对以上两个疑难的释明,学者们有效论证了将实用艺术作品单独作为作品的一项内容进行规定的合理性,而这一共识也在《〈著作权法〉三次修改稿》与《送审稿》中均得到了体现。[注]《〈著作权法〉三次修改稿》第3条及《送审稿》第5条中,都无一例外地将实用艺术作品作为作品的一个分类单独进行了规定,仅在具体表述上有所区别。笔者认为,以上所述可充分证成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单独保护符合立法趋势,《送审稿》中第5条第9项和第29条第3款的规定实现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向前迈进的重要突破。
(三)实用艺术作品单独保护契合司法需要
紧承前述,当前司法实践中同时存在对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采美术作品保护路径和作品保护路径两种观点。应当承认,面对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规范长期缺失的现实,对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采美术作品保护路径一直是当事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及法院处理类似案件的首选,其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保护路径所存在的诸多理论不完善、论证不周延的问题日益暴露,最突出的有以下两个:其一,大部分判决中均未论证美术作品与实用艺术品的关系。倘若实用艺术品的艺术成分无异于美术作品,那么实践中产生实用艺术作品这样一种新的作品类型的动因是什么?若两者不同,那么实用艺术作品与美术作品的边界何在?其二,并非所有的实用艺术作品都属于美术作品,但实用艺术作品一定属于作品。因此,采用这种保护路径时,对于那些属于实用艺术作品范畴,但又无法落入美术作品之列的作品该如何保护就会留白。[注]参见杨利华:“我国著作权客体制度检讨”,《法学杂志》2013年第8期,第26~27 页。
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司法实践中有相当数量的法院对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采用了作品保护路径。前已述及,该种保护路径从作品的含义出发,论证实用艺术作品符合作品的基本定义,故其可以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显而易见,这种保护路径不仅可以解决上述两个问题,而且其论证思路更加清晰,省却了多余的逻辑推演。不过,由于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规范的缺失,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需要在判决中花大量篇幅证明实用艺术作品属于作品范畴,这显然增加了进行司法证成的工作量。随着实用艺术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类型日益多元,上述问题将更加激化,现有保护模式将难以适应司法实践中权利人诉求多样化以及纠纷复杂化的趋势。因此,宜尽快落实《送审稿》中第5条第9项和第29条第3款的规定,对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予以单独保护。
四、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单独保护路径的具体构建
(一)明晰实用性与艺术性“分离”的适用标准
前已述及,实用艺术作品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分离”包括物理上的可分离和观念上的可分离两种情形。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用艺术作品是可以在物理上对其实用性与艺术性进行分离的,其艺术成分往往是本就独立存在后来被应用到实用品上的美术作品。例如,印制有山水画的餐具、寝具,外观上附着有立体卡通形象设计的文具、玩具等即属于这种情形。有学者提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保护的实用艺术作品首先应当是实用成分和艺术成分在物理上不可分割的艺术作品,《著作权法》不保护物理上可分离的实用艺术作品。[注]参见吕炳斌:“实用艺术作品可版权性的理论逻辑”,《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3期,第76页。不可否认,物理上可分离的实用艺术作品其艺术成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美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但此时其实用成分就不能获得工业产权保护,显然不利于作品的全面保护。更加重要的是,从实用艺术作品的概念、本质和制度价值上看,其并不排斥前述类型的实用艺术作品存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给予权利人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不建议将物理上可分离的实用艺术作品排除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之外。
而对于后一种情形,也即实用艺术作品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在观念上“可分离”这一问题,美国在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注]美国采取“分离特性与独立存在”之标准将实用艺术作品类型化为“物理上的可分离”和“概念上的可分离”,其中“概念上的可分离”就相当于我国学者所称的“观念上的可分离”。这一标准主要源于“Mazer v.Stein”案。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一身着长裙的女子头顶圆盘起舞的灯座造型享有版权。而在后来的1975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终审判决美国一家制造街头灯具的公司设计出一种像阿拉伯数字“7”的街头灯座造型不享有版权。其理由是:前者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具有观赏性,后者的灯座显然是“实用物品”,其内在功能仅仅是实用性,而不具有观赏性。美国学者戈德斯坦(Paul Goldstein)曾说过,“在版权法的诸多精细界分之中,最为棘手的莫过于可保护的图案、图形、雕塑作品与不可保护的工业设计实用成分之间的界限。”[注]Paul Goldstein and Copyright,Principles,Law and Practice,Vol.1,§2.5.3,99.在“布兰德”一案[注]该案涉及的是关于用管形物制作的彩虹雕塑形状的自行车支架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争议。案情大体是这样:设计人用管形物制作了一些彩虹形的雕塑品,起初并未想到以之用作停靠自行车的支架。后来,设计人的一个朋友向他提出了以该雕塑品做自行车支架的建议。据此建议,设计人又对彩虹形雕塑做了一系列修改,以期增加实用性,达到实用目的。第二巡回法院裁定,这种装饰性的彩虹形自行车支架不受版权保护。中,奥柯斯法官采纳了邓尼考拉教授的观点,其对于观念上的可分离之理解可以表述为:“如果外观设计的因素体现了美学上的考虑和功能上的考虑之混合,作品的艺术部分就不能被认为可以与实用因素在观念上分离。相反,如果外观设计的因素可以被认为体现了设计者的艺术判断,并且设计者在进行艺术判断时未受功能性因素的影响,则存在观念上的分离特性。”[注]转引自丁丽瑛:“实用艺术品著作权的保护”,《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第135~141页。此外,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还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判断方法和标准,主要包括:其一,“主要/次要判断法”(primary/subsidiary test)。在该标准下,如果作品具有在观念上区别于“次要的实用功能”之“主要的装饰性方面”,则满足观念上可分离。其二,“可销售判断法”(marketability test)。美国学者尼莫(Nimmer)认为,在去除某作品的实用功能而仅保留其美学特征的情境下,若该作品仍有很大可能适于向社会中的一定群体销售,则为观念上可分离。其三,“注重设计过程的判断法”。该判断法关注设计的过程而非设计的结果,若作品的设计成分反映了创作者有独立于功能性考虑之外的艺术判断,则该作品满足可分离性要求。其四,“临时置换判断法”。如果一个具有实用功能的作品可以在普通观察者的头脑中被临时置换为一件观念上的艺术作品,则满足可分离性要求。[注]参见前注〔45〕,吕炳斌文,第73~75页。
笔者认为,在对无法做出物理上分离的实用艺术作品进行“观念上的分离”时,上述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判断方法可兹借鉴。承前所述,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参考了“注重设计过程的判断法”和“临时置换判断法”。事实上,此两种方法并无科学意义上的孰优孰劣之分。不过,前一种方法可以通过技术还原等方式予以清晰、直观地呈现出来,而后一种方法则主要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前一种方法的视角观之,如果一个造型精致美观、图案绚丽多彩的艺术作品同时具有家居用品的实用功能,但假使设计者在勾勒此件实用艺术作品的线条、形状、图案并填充其色彩时根本没有考虑赋予这些设计以任何特别的功能,而纯粹是为了获得审美意义上的艺术效果,那么即可认为这件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是与其实用性相分离的。此时,由线条、色彩、图案、造型、元素搭配组合及修饰而形成的整体艺术表达就成为作品独创性判断的唯一对象。[注]参见丁丽瑛:“实用艺术品纳入著作权对象的原则”,《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43页。为了使这种判断方法更具可操作性,司法实践中可以模拟改动实用艺术作品在艺术部分的设计,如果改动后影响了其实用功能的实现,则艺术成分与实用功能就是无法在观念上分离的;反之,则是可分离的。[注]参见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5~77页。而对于统一使用此种判断方法可能会在事实上不当缩小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对象之弊端,可以通过辅之以“可销售判断法”来缓解。在某些较为特殊的情况下,倘若某一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成分虽具有微弱的实用功能,但即使去除该作品全部的实用功能而仅保留其艺术美感却依然不影响其向特定受众销售,则也可以认为其实用性与艺术性是可分离的。
(二)统一实用艺术作品独创性的判断标准
有观点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上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更加强调创作的“独立性”而非独立的“创作性”。换言之,作品具备何种艺术高度并非《著作权法》的中心关注,只要作者的创作过程中有不可或缺的智力投入而非简单和重复的体力劳动,体现了作者对创作元素的取舍、选择和安排即可。[注]参见冉崇高、赵克:“著作权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竞合与冲突——以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为视角”,《人民司法》2011年第21期,第91页。诚然,上述判断标准对于一般的作品并无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当的可适用性,但却并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有着自身特殊性的实用艺术作品独创性判断之中。
具体而言,在生活品味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许多实用商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艺术气息,这些艺术成分往往亦是设计者独立创作出来的。但显而易见,不能因为这种创作的“独立性”而对这些实用商品均予以著作权保护。事实上,如果对美感较低的实用品都给予著作权保护,设计者将不再有动力去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权,这不仅将导致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制度设计落空,同时也会使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泛滥。[注]参见张伟君:“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法保护与外观设计专利法保护的协调”,《知识产权》2013年第9期,第53页。因此,前述多数法院均将实用艺术作品达到“一定创作高度”作为予以著作权保护的条件,而这种“高度”通常是高于一般作品的。司法实践中,S型牙刷、放置沐浴用品的器皿、胶带切割机等独立创作且具有一定特殊造型的实用商品被排除在了著作权保护范围之外,即是这种独创性判断标准的直接体现。不过,为避免矫枉过正,应当强调实用艺术作品需达到的“一定创作高度”并不等于纯美术作品通常所体现的艺术高度,而是酌情降低为具有“一定的审美个性”即可。倘若要求兼有产品实用功能的实用艺术作品在艺术性上与纯美术作品相匹敌,恐怕是其难以承受之重。
(三)规范实用艺术作品领域“实质性相似”的判定标准
对于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中如何细化“实质性相似”的侵权认定标准,美国、日本等国家普遍适用“一般理性人”标准。具体而言,由于实用艺术作品的消费对象为普通公众,故在比较两部作品时应当使用“一般观察者”的标准来感受两部作品之间的相同与差异。[注]参见前注〔49〕,丁丽瑛文,第140页;亦可参见梅伟:“民法适用的理性人标准”,《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54页。易言之,如果以一个可能购买该实用艺术品的普通的、非专业的消费者的观察目光,将对比产品各自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评判时,倘若发现除非在主动去寻找差异性的情形下二者是相似的,就可以认定二者达到了实质性相似的程度。具体操作时可将被告产品与原告产品进行对比,以一般理性人的认知确定两者相似部分是否属于原告独创、受著作权保护的内容,而不能简单以某个人或某些特定群体的判断为依据。不过显而易见,这种判断实质性相似的“一般理性人”标准与前述判断实用艺术作品实用性与艺术性是否在观念上“可分离”的“临时置换判断法”存有相同的弊端,即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且难以直观地呈现出来。[注]参见谷永超:“英美刑法的理性人标准及其启示”,《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4期,第135~138页。亦可参见梁鹏:“保险法之‘理性人’标准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81页。在美国,这一问题往往通过当事人或者法院聘用的私人组织进行专业的数据统计与分析来解决。但在我国,目前并无权威的第三方机构能够承担这一职能,自然也就不能将“一般理性人”的判断以相对准确、有参考价值的数值呈现出来供法院参考。因此,这一判断标准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官的自由裁量予以指导,但如何在我国的法制土壤中提升其可操作性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