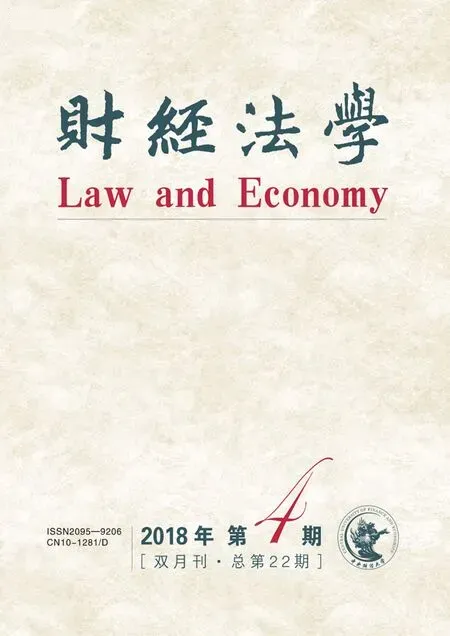《商标法》“不良影响”条款研究
——基于“叫个鸭子”商标案的思考
宋亦淼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11月19日,味美曲香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提出第15740333号“叫个鸭子”商标的注册申请,指定使用在第43类“住所代理(旅馆、供膳寄宿处)、饭店、汽车旅馆、旅游房屋出租、旅馆预定、酒吧服务”等服务上。2016年4月23日,商标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第30条、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驳回了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味美曲香公司不服上述裁定,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评委”)提出复审申请,商评委以“诉争商标格调不高、易产生不良影响”为由,驳回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味美曲香公司不服该裁定,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鸭子’一词在非主流文化中有‘男性性工作者’含义,尤其是诉争商标文字又由谓语动词组成‘叫个鸭子’短语,会进一步强化相关公众对此含义的认知和联想,易造成不良影响”,故维持了商评委的复审裁定。[注]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京73行初2359。味美曲香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指出,“按照社会公众的通常理解,‘叫个鸭子’并无超出字面的其他含义,未产生不良影响”,故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商评委就“叫个鸭子”商标提出的复审申请重新做出决定。[注]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京行终3393号。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将“叫个鸭子”商标注册使用在酒吧、旅馆等服务上,是否因违反《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而具有“不良影响”?[注]本文将《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简称为“不良影响”条款。笔者无意加入“叫个鸭子”是否具有不良影响的争论,因为《商标法》“不良影响”条款本身就是一个概括性条款,其内涵及条款所适用的范围都具有极大的抽象性,且目前学界和司法实践对“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尚存在诸多分歧。因此,与其就个案探讨“叫个鸭子”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还不如通过该案审视“不良影响”条款的内涵及适用规则,这或许具有更大意义。
二、“不良影响”条款的内涵解读
判断“叫个鸭子”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的前提,在于正确理解何为“不良影响”。这倚赖于法律的合理解释,因为法律适用始终是法律诠释的问题,[注]参见〔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只有通过法律解释,“承载”意义的法律文字才能变得可以理解。
(一)“不良影响”条款的意义脉络解释
正所谓“建构概念清晰、逻辑一致、位序适当的法律体系,对于所有法学家都有难以抵御的魅力”[注]舒国滢:《法哲学:立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法律内部有前后和谐贯通的体系,绝大多数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意义脉络解释予以解决。意义脉络解释首先要考虑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法条的内容界限,构成了法条解读的重要基础。[注]参见孔祥俊:“论商标可注册性要件的逻辑关系”,《知识产权》2016年第9期,第3页。此外,意义脉络解释也意指规整脉络中条文间事理上的一致性,对法律的外部安排及其内在概念体系的考虑。[注]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7页。
“不良影响”条款的性质为何?其在《商标法》中的定位又为何?对此,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良影响”条款是《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的兜底条款。理由在于这一条款前7项控制的都是与伦理道德有关的要素,即“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的情形,第8项理应为兜底条款,这样既可以兜住第1款前7项及第8项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以外的不良影响,又可以控制第1款没有列举但欠缺独占适格性的标记。[注]参见饶亚东、蒋利玮:“对《商标法》中‘其他不良影响’的理解和适用”,《中华商标》2010年第11期,第34页;李扬:“‘公共利益’是否真的下出了‘荒谬的蛋’?——评微信商标案一审判决”,《知识产权》2015年第4期,第32页;汪正:“此‘不良影响’非彼‘不良影响’——关于‘其他不良影响’禁用条款及诚实信用原则”,《中华商标》2007年第3期,第47页。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良影响”条款是《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兜底条款。原因有二,一是如果前述第一种观点成立,则应当将“不良影响”条款单列为一项,而非放在第8项之中;二是第1款前7项调整的是商标的商业意涵,第8项调整的则是商标的文化意涵,基于不重复原则,“不良影响”条款不宜被扩张适用。[注]参见孔祥俊:“论商标法的体系性适用——在《商标法》第8条基础上的展开”,《知识产权》2015年第6期,第10~11页;李琛:“论商标禁止注册事由概括性条款的解释冲突”,《知识产权》2015年第8期,第8~9页。第三种观点认为,“不良影响”条款是商标不得注册绝对理由的兜底条款。理由在于,《商标法》与其他知识产权制度相比,特别强调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其权利保护范围的划定是综合考量诸多公共政策的结果,而这又集中体现于商标注册制度之中。[注]参见〔英〕史蒂文·D.安德曼:《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梁思思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页。因此,将“不良影响”条款理解为商标不得注册绝对理由的兜底条款,有利于为《商标法》应对不测事项预留空间。[注]参见黄汇:“商标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保护——以‘微信’商标案为对象的逻辑分析与法理展开”,《法学》2015年第10期,第76,80~81页。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首先,从条文逻辑方面考量,《商标法》第10条第1款前3项是与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关的标志,第4项是与官方标志、检验印记相关的标志,第5项是与红十字会相关的标志,第6项是与民族歧视相关的标志,第7项是与商品质量或产地相关的标志,第8项是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相关的标志。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前7项条文并非完全并列,而且不都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将“不良影响”条款解释为《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的兜底条款,显然行不通。其次,从立法技术方面考量,《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是一个典型的例示性规定,符合“一个典型事例+或者(和、与、以及、及)+其他+上位概念”的基本样式。[注]所谓例示规定,是指立法者在面对欲调整的事项难以穷尽时,先列举几个典型事项,再连缀助词“等”或代词“其他”,最后加上抽象的上位概念以做全面涵盖的法条形式。参见刘风景:“例式规定的法理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95~96页。其中,“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标志是“一个典型事例”,具有“不良影响”的标志则是“上位概念”。将“不良影响”条款解释为第1款第8项的兜底条款,有利于保持条文间事理的一致性。最后,从法律实施效果方面考量,如果将“不良影响”条款解释为《商标法》第10条第1款乃至商标不得注册绝对理由的兜底条款,有扩大商标行政管理机构在商标注册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之嫌,这不仅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商标注册和使用行为,也与当前国家机关“简政放权”的理念相左。[注]参见章凯业:“商标法中的‘不良影响条款’研究”,《行政与法》2016年第6期,第117页。
(二)“不良影响”条款的目的论解释
法律的意义脉络解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通常只有追溯到法律的目的,才能真正理解法律的含义。[注]参见前注〔7〕,卡尔·拉伦茨书,第207页。因为任何法律条文的制定都有特定的目的,故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应尽可能贯彻立法者的目的。而且,当其他各种标准不能获致毫无疑义的解答时,许多立法者借法律追求的目的,同时也是法律的客观目的,就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注]同上,第211页。
1.“不良影响”条款的调整范围
法律的调整范围是指法律调整和规范的社会关系,此即法律条款创设之使命。厘清“不良影响”条款的调整范围,是研究其适用规则的基础。我国采取的是商标注册制度,《商标法》规定了申请商标注册需满足的条件,包括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而根据商标法理论界的通说,注册商标的消极条件又可分为绝对事由与相对事由。[注]参见孔祥俊:“我国现行商标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知识产权》2010年第1期,第19页。其中,前者涉及申请商标固有的不可注册性,主要关注申请商标是否具有识别性以及是否符合公共政策;后者主要涉及申请注册人与他人之间的权利冲突。[注]See Guv Tritton,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Europe,Sweet & Maxwell, 2008,p.272.“不良影响”条款是有关商标可注册性的法律评价要件,即便某标志具有事实上的可识别性,但因具有“不良影响”也不能注册为商标。[注]参见前注〔6〕,孔祥俊文,第7页。这种限制是极为严格的,不受主体和时间的限制,且不存在任何例外情况。
2.“不良影响”条款的保护法益
法益即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每一部法律,乃至绝大多数法律条款,都有其自身所保护的法益所指。作为一种最高法律原则,法益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规则得以明确化的前提。[注]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对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检视”,陈璇译,《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第53页。根据参与《商标法》修正讨论的学者的意见,“不良影响”条款旨在规制某些本身具有反动、色情等不良影响的标志的情形。[注]参见黄辉:《商标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将该条款的立法目的限定在“维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以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2013年版),载http://www.npc.gov.cn/npc/flsyywd/minshang/2013-12/24/content_1819929.htm,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8月25日。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商标授权确权意见》)第3条明确规定,仅损害特定民事主体权益的情形应由《商标法》其他条款规制。由此,“不良影响”条款保护法益指向的是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如果商标注册行为仅侵犯个体利益,应依据《商标法》的具体条款寻求救济途径;如果行为同时侵犯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在公众利益受损是源于侵犯个体利益的情况下,仍应依保护个人利益的具体条款禁止商标注册;[注]参见马一德:“商标注册‘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230~231页。只有在行为仅损害公共利益时,才考虑“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由此,“不良影响”条款旨在禁止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属于最严厉的商标禁用条款,不能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注]同上,第231页。
(三)“不良影响”条款的比较法解释
知识产权是一项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立法实践,应善于对比研究域外法上的成熟经验,以借鉴先进之国商标法之良规,兼采其最新之学说。因此,在前述标准仍有未足的情况下,可运用比较法解释,参考域外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以妥当理解我国《商标法》上“不良影响”条款的内涵。[注]参见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0页。
1.国外“不良影响”条款相关法律规定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商标法,都对旨在维护道德或公共秩序的禁止商标注册或使用的理由进行了规定。通过比较各国相关法律规定,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国《商标法》上的“不良影响”条款。美国《兰哈姆法》第2条(a)款规定,“包含不道德的、欺骗性的或毁誉性的事物或由其构成;包含贬损或不当暗示与生存或死亡的自然人、机构、信仰、国家象征有某种联系,或使其受辱、名誉受损;……”的商标,不得在主注册簿上获得注册。[注]参见杜颖译:《美国商标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其“不道德”与“毁誉”之含义与我国《商标法》上的“不良影响”极为接近。[注]参见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90~493页。《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第7条第1款规定了13项驳回商标注册的绝对理由,其中第(f)项规定“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商标”不得注册。《法国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商标法》第3条规定“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标记,不得用作商标或其组成部分。”《英国商标法》第11条后半句规定,“违背法律、道德,或属于丑恶形象,此种事物作为商标或商标的组成部分注册,应属违法”。日本为防止商标注册制度之滥用,在《商标法》第4条第1款第7项明确规定“有可能危害到公共秩序之商标”禁止注册。[注]参见〔日〕田村善之:《日本知识产权法》,周超、李雨峰、李希同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127页。
可见,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都对违反公序良俗之商标不得注册做以规定,有些国家直接表述为“违反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有些国家则对违反公序良俗之具体所指进行了解释。为此,我国“不良影响”条款与国外“公序良俗”条款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表明国外与“公序良俗”条款相关的立法与判例对我国具有可借鉴性。同时,在对违反公序良俗之具体所指做以解释的国家立法中,可尝试从其“不道德”、“毁誉”、“贬损”、“丑恶”等核心词汇中,窥视我国“不良影响”的内涵。
2.国外“不良影响”条款相关司法实践
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在“不良影响”条款适用方面具有丰富的判例,并形成了一定裁判规则。本文即以美国为例,介绍其“不良影响”条款相关司法实践。
在“灰狗”(Greyhound)商标案中,商标申请人申请将一只飞奔的狗的形象注册为商标,指定使用在衬衫等商品上,灰狗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异议人灰狗公司的商标即为一只飞奔的狗的形象,且核定使用在帽子、枕头、行李箱等商品之上。两商标唯一的不同在于,申请人商标中的狗正在排泄粪便,而异议人商标中的狗没有。对此,美国商标评审与上诉委员(Trademark Trial and Appeal Board,简称TTAB)认为,“申请注册的商标形象不同于正常的狗的形象,其排泄粪便的行为冒犯了社会公众。而且,社会公众都已认可灰狗公司之狗的形象,申请人截取异议人商标中狗的形象,且将其设计为正在排泄粪便,易使公众联想是灰狗公司的狗在排泄粪便。因此,申请注册的商标是丑陋的、带有贬损的意味,违反了《兰哈姆法》第2条(a)款之规定,不得获准注册。”[注]See Greyhound Corp.v.Both Worlds, Inc, 6 USPQ 1635(TTAB 1988).再如在“麦金利”(McGinley)商标案中,商标申请人想要将一个包含“一双裸体男女拥吻且男性生殖器官外露”的照片标志注册为商标,使用在“致力于社会与人际交往关系的小报”(Newsletter Devoted to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opics)和“社交俱乐部服务”(Social Club Services)上。TTAB认为,“申请人的商标有悖于礼仪和道德,冲击了社会成员的道德感情,是丑陋的”。而后,美国关税与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简称CCPA)进一步指出,可借助以往判例和《兰哈姆法》颁布时的字典理解何为“丑恶”。根据1942年《韦氏新国际词典》,“丑恶”是“冒犯了良知或道德情感,引起谴责,对声誉造成负面评价”[注]英文原文为:“Giving offense to the conscience or moral feelings; exciting reprobation,calling out condemnation……Disgraceful to reputation……”之意。根据1945年《方魏新标准词典》,“丑恶”则是指“冲击了真实、体面和礼仪的感觉”[注]英文原文为:“shocking to the sense of truth,decency,or propriety……”。据此,CCPA认为,“申请注册的商标是丑恶的,不予获得注册”[注]See Inre Robert L.McGinley, 1981 CCPA LEXIS 177.。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与我国一样,美国司法也是通过判例的发展在不断对“不良影响”条款予以解释。各国对于“不良影响”条款内涵的解读虽受本国国情影响而具有一定特殊性,但仍有诸多共通之处,具有相互借鉴的价值。而且,如在“麦金利”(McGinley)商标案中CCPA借助以往判例和权威词典斟酌条款中核心词汇的做法也可供我国法院参考。
三、“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规则
“不良影响”条款本身的立法技术,决定了其只能为纷繁复杂的个案提供一般性行为模式,而无法提供量体裁衣的妥当保护。[注]参见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82~84页。欲探究“叫个鸭子”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还需从该条款的适用规则入手,以增强认定标准的客观性。[注]See Anselm Kamperman Sanders,Unfair Competition Law,Claredon Press,1997,pp.22~23.从该案一二审判决中,可以发现法院主要从“不良影响”条款的判定对象、判定主体、商标所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类别、商标使用及知名度情况等四个维度,探究“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规则,下文将逐一分析。
(一)判定对象是标志的主要含义还是其他含义?
《商标授权确权意见》第3条指出,在判定商标标志是否因违反“不良影响”条款而不能获得注册时,应考察该商标标志本身的含义,判断其是否会让公众产生消极、负面的感受。那么,当某标志可能具有多重含义时,应考虑该标志的主要含义还是所有含义?是否只要其中一种含义可能存在消极、负面影响就被认定为具有不良影响?聚焦于该案,问题即为“叫个鸭子”在非主流文化中是否具有“男性性工作者”的含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在判断其是否具有不良影响时,又应否考虑该种含义?目前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争议很大,有观点认为,在判断标志是否具有不良影响时,考察其主要含义即可。如在“黑尾巴”(Black Tail)商标案中,马维缇是成人娱乐杂志《黑尾巴》的出版商,其想要将“黑尾巴”(Black Tail)申请注册在杂志类商品之上,但遭到美国专利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简称PTO)的驳回,理由是根据1981年《韦氏新国际词典》,“tail”有“性交”之意,是不道德和丑陋的标志,不得注册为商标。但是,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简称CAFC)对此进行了纠正,以“‘tail’一词具有丰富的含义,‘性交’只是其含义之一,且足以被其他更受欢迎的含义所覆盖”为由,认定“tail”一词非不道德和丑陋。[注]See In re Mavety Media Group Ltd., 33 F.3d 1367 (TTAB May 5, 1993).也有观点认为,对于具有多种含义的标志,如其所具有的一种含义具有不良影响,则该标志就应被认定为具有不良影响。如在“城隍”商标案中,法院则认为“虽然‘城隍’具有‘护城河’等含义,但其也被用来指代道教的特定神灵。在此情形下,将‘城隍’作为商标加以使用,将对信奉道教的相关公众的宗教感情产生伤害,并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高行终字第485号。。当然,如果采折中说,则会认为在判断具有多种含义的标志是否具有不良影响时,应以其主要含义为主、其他含义为辅予以考察;如果其他含义已为社会公众广泛接受或认可,则应纳入“不良影响”条款的考量范畴。
(二)判定主体为社会公众还是相关公众?
关于“不良影响”条款的判定主体,目前争议主要集中在相关公众抑或社会公众上,这在“叫个鸭子”商标案的一二审判决中也有所体现。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和司法实践也未达成共识。有观点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不良影响”条款的判定主体应为相关公众,因为商标能否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消费者心理,而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也完全取决于相关公众的认知。[注]参见前注〔13〕,章凯业文,第121~122页。也有观点认为,“不良影响”条款的判定主体应为社会公众。如在“THEWALKINGDEAD”商标案中,罗伯特柯克曼公司向商标局申请注册“THEWALKINGDEAD”商标,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应当就文字本身的含义,以中国境内相关公众对申请商标整体含义的理解为标准”。[注]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73行初2049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进行了纠正,指出“《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属于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绝对禁止使用的情形,是从保护‘公序良俗’的视角出发的,故此处的判断主体应为‘社会公众’,而非‘相关公众’。原审判决将该条款的判断主体限定为‘相关公众’存在错误。”[注]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京行终874号。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理由在于将“社会公众”作为“不良影响”条款的判定主体,有利于严格贯彻其作为禁止商标注册与使用绝对事由的价值导向。
(三)是否考虑商标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类别?
根据《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解释,判断“不良影响”应考虑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注]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因此,判断标志是否具有不良影响,不能将其狭义地理解为只考虑符号的构成而不考虑商标所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类别。[注]See Kerry L.Kester, Standing to Oppose Scandalous or Immoral Trademarks,Neb.L.Rev. 58,1978,pp.249~270.如在“国人福”商标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申请商标‘国人福’在汉语中通常理解为‘国人的福气’等含义,其申请注册在灭鼠剂、杀害虫剂、灭蝇剂、烟精(杀虫剂)、小麦黑穗病化学处理剂、土壤消毒剂等商品上,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来判断,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反感或负面联想。”[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2)知行字第14号。该判决的审理逻辑即商标标志本身具有积极、正面的含义,但由于指定使用在特定商品上而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是目前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也为笔者所认同,因为商品和服务类别是标志使用的具体环境,而对词语的理解离不开语境。[注]参见姚建宗:“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41~143页。比如“二人转”、“中央一套”等词汇本身是中性的,不带任何情感偏向,但如果将其注册在避孕类商品类别上,可能就会给人带来不适之感。[注]参见袁博:“论《商标法》中‘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规则”,载《中国工商报》2015年12月1日,第7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另一起“叫个鸭子”商标案中,判定其使用在第35类“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系统化、将信息编入计算机数据库”等服务上不会产生不良影响。[注]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京行终395号。但如果在判定是否具有不良影响时需要联系商品或服务类别进行综合判断,则即使两案诉争商标同为“叫个鸭子”,既有判决也并未有太多参考借鉴的价值,因为两案商标指定使用的服务类别不同。一审法院认为两案“叫个鸭子”商标指定使用的服务类别会直接影响公众对商标含义的理解,这一思路值得肯定。
(四)是否考虑商标经使用而具有知名度?
在“叫个鸭子”商标案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了诉争商标在广告宣传、商品销售等方面的16份证据,用以证明诉争商标的使用及知名度情况。那么,在判断某标志是否具有不良影响时应否考虑其使用及知名度情况?有部分观点认为,商标的使用及知名度情况应作为其是否具有不良影响的考量因素。如在“酒鬼”商标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酒鬼”一词虽然有“酗酒且经常喝醉的人”之意,但该商标申请人已使用多年且获得诸多荣誉,其在消费者中不存在不良影响。[注]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9)高行终字第1384号。但绝大多数观点还是对此持保留意见,笔者亦表示赞同。因为“不良影响”条款是禁止商标注册和使用的绝对事由,这种限制不存在任何例外情况。换言之,“不良影响”条款是禁止性规定,在诉争商标违反该条款的情况下,即使其经过长期使用具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也不能因此而损害法律规定的严肃性和确定性。在本案中,法院的态度即是如此。其虽未明确针对原告的上述证据展开论述,但也未在判决论理部分对此予以正面回应,这就说明了法院并不认为诉争商标经使用而具有一定知名度,就可突破“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标的功能由最初的标示商品来源功能,逐渐延伸出品质保证功能、广告功能甚至是文化功能。商标文化功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商业标志可以带有某种美好的寓意、增加大众交流和文化传播中的语汇、演化为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象征性社会符号等方面。[注]参见杜颖:《商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但是,相比于商标所发挥的识别来源功能、品质保证功能与广告功能,商标的文化功能充其量只是附属功能,过度关注商标对文化领域的引导和影响作用可能不甚妥当。如何正确判定相关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确实是一个极难把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