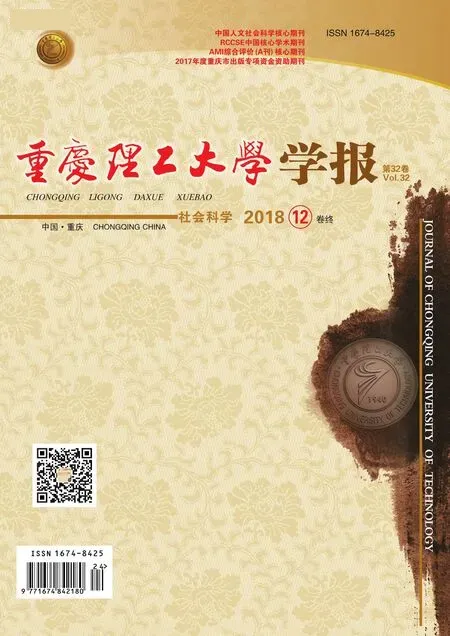规范行为:生物本能vs.社会实践
——兼论维特根斯坦的“遵守规则”理论
樊岳红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一、规范行为的两种解释
当哲学家们对感官知觉进行反思时,他们通常把焦点放在我们的经验信念和知识是如何由经验事实来合理辩护的问题上。神经生理学家通常是通过分析发生在我们神经系统中的因果关系,来最终阐明感性经验。与神经生理学家不同的是,哲学家通常所追问的是对感性经验的辩护理由。而还原论者又试图通过把感知的哲学理论还原为科学事实,但还原论者的这种方法面临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对经验事实及其关系的辩护包含一种内在规范性因素,但这种内在规范性因素又无法由科学语言来解释。科学的终极目标是要形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理论,因此我们会期望科学理论至少在原则上能够解释我们的心理事件,正如能够用科学来解释物理上的黑洞、分子或电场一样。另一方面,还原论者还要解释心理规范是从何而来的问题。毕竟,人们对感知经验和信念的把握也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但还原论者认为,人们的心理事件可以看作是他们的大脑功能,而大脑的运作又是通过神经生理学来解释的[1]。
人们对还原论的期望是,它能够从科学视角来解释人们的规范行动,并且还能阐明这种规范行为是如何从因果层次产生的。或者说,人们期望还原论者能提供一种纯粹物理规范来解释规范行为与因果理论之间的关系,亦即用物理论来解释人们遵守规则行为的原因或理由。通常来说,自然科学所关注的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关注人类的理性。但自然科学的这种方法所存在的潜在问题是,它忽略了如何用人类理性来说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讨论了自然主义者和还原论者的观点之后,那么维特根斯坦又是如何来思考规范行为与外在原因之间的关系呢?事实上,后期维特根斯坦更加关注的是具体事例,如孩子(儿童)是如何被同化到受规则(规范)支配的社会实践之中的。基于此,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所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他首先对“教学”和“训练”进行了鲜明的区分,如新生儿被训练得以特定的方式对外在刺激做出反应,然后获得概念,进而学习如何遵循规则或规范;其次,维特根斯坦主张通过训练使孩子们成为特定共同体的成员,该共同体的规范又是由群体成员的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外在的社会实践又进一步受规则或规范支配。
当然,维特根斯坦不是要为因果层次与规范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是想要改变我们的常识观念。“这就像是我们的生活形式。”[2]559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的哲学不是发展理论,而是为了解释规范领域是如何从原因领域发展而来的,并且他也承认理由和原因都是我们日常世界生活形式的一部分。
二、社会规范行为来自于训练
后期维特根斯坦使用了语言习得的事例来说明他的立场,但他并没有形成关于语言学习的系统性理论。有人主张维特根斯坦所用的这些事例只具启发性,如威廉姆斯(Meredith Williams)所指出的,研究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大部分二手文献只是把学习作为一种启发式的工具,因而往往忽略了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学习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威廉姆斯还指出,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理论中,他把培训过程视为“在创造逻辑空间时的关键区分是语法和经验,而学习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阐明规范性的本质”[3]。维特根斯坦对语言习得的评论表明了我们是如何从本能模式支配的行为转向了自觉遵守规则的行为。从《哲学研究》的评论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在教学和训练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区分。维特根斯坦写道:“当小孩学习说话时,他们便开始运用这样的原始语言。在此,语言教学绝不是一种解释,而是一种训练。”[4]5
维特根斯坦在谈到学习者建立刺激-反应模式过程时并不涉及任何一种智力活动。人们在建立刺激-反应模式时并不是基于语言教学,而仅仅是基于行为的加强模式。在“训练”一词首次出现时,他解释道:“虽然我是以一种严格类似的方式来使用‘训练’一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动物被训练去做某些事情,但训练是通过各种实例来说明的,如奖励、惩罚以及诸如此类的。”[5]因此,当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教学过程是一种训练而不是一种解释时,他所坚持的是语言习得最初是通过建立刺激-反应模式来解释的;而刺激-反应模式发生在本能模式支配的行为层次中,而非发生在自发遵守规则的行为中。在语言游戏中,我们让孩子们从成人的言说方式出发,而不是从孩子自身的观点出发,因此这包含着一种规范性因素。
维特根斯坦提醒我们注意这种差异性,即“我已经被训练得以一个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标志作出反应,而现在我就对它作出如此反应。但那只是给出一种因果关系;它告诉我们现在只是根据路标走,而不是说明这路标是由什么构成的。相反,我还表明,只有这存在着路标的习惯用法、存在着习俗时,人们才能按路标的指示前行”[4]198。只有当共同体中的其他成人都以特定方式对路标作出回应时,那么他们才是在遵守规则,如果孩子们都只是以这种方式来行事,那么他们是被训练得如此行事。因此,训练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只能解释孩子的行为,而不能解释成人的行为,因为成人会作出不同的反应。然而,孩子也是由已经参与社会实践的成人来训练的。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详细讨论如何把孩子的行为理解为在“遵守规则”的,以区别于孩子们条件反射式的行为。“老师不能说:‘当学生在说这句话时,也许学生已经学会如何阅读。’因为学生所说的话是确定的,但学生何时才开始真正的阅读,正如说这是学生阅读的第一个字词,这样的表述是没有意义的。”[4]157这也是我们判断孩子们在遵守规则的方式,但这并不能清楚地说明孩子们最初是在哪一次开始真正遵守规则的。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开篇以奥古斯丁图像论为例进行了详细说明。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哲学中突出强调了语言习得的方式,尤其介绍了奥古斯丁式的语言习得图景。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描述:奥古斯丁认为孩子们通过倾听成年人说话的方式来习得语言。儿童通过观察成人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或眼部表情、观察到字词与对象之间的直接关系等来习得语言,因此孩子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会了如何理解字词的意义。
但维特根斯坦对奥古斯丁的这种观点进行了三点批判:
首先,他对奥古斯丁式的意义原子论进行了批判,意义原子论认为意义可以基于单个字词与单个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来加以解释。如我们可以孤立地学习诸如“红色”“黑暗”“甜蜜”这样的字词,这些字词是独立于其他语言的。事实上,后期维特根斯坦用意义整体论来取代了奥古斯丁式的意义原子论。意义整体论是说一个词的意义取决于语言使用者在整体环境中是如何使用它的。
其次,维特根斯坦不仅批判了意义原子论,而且他也反对奥古斯丁式的语言习得图景。维特根斯坦认为,奥古斯丁没有解释儿童是如何习得第一语言的,而只是解释了儿童如何习得第二语言。换句话说,孩子必须在已经掌握了一门语言的情况下,他们才能独立思考对象,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已经拥有概念了,他们才能来学习第二语言。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阐释:“现在,我想我们可以说:奥古斯丁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了人类学习语言的过程,语言学习就好像一个孩子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她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但好像她已经掌握了一门语言,但不是这个国家的语言。或者,又如孩子已经会思考,但只是还不会讲话一样。并且在这里,‘思考’意指像‘与自己说话’一样。”[4]32
再者,维特根斯坦认为,奥古斯丁没有区分孩子们的行为是由模式支配的还是在遵守规则的。如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会大哭,从而向她父母发出了饥饿的信号。成人可以对这个信号作出不同的回应,因为孩子父母不清楚孩子哭的原因,他们只能通过试图满足孩子的需求来进行猜测。生物学机制在新生儿的这些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机制保证了孩子的生存,但这种生物学机制并不包含一种规范因素,例如一个10岁大的孩子与新生儿表示“她饿了”的方式是不同的,而且10岁大的孩子在被社会同化的过程中,他对这种推理方式是开放的,孩子可以从渴求过渡到想要吃饭,从而表明孩子的行为是遵守了规范的,而这种遵守规范的行为同时也构成了我们社会实践的生活形式。
综上所述,维特根斯坦认为,当奥古斯丁主张孩子们是在成人话语和环境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直接联系时,他预设了太多的事情:(1)他必须坚持孩子们已经明白一个词的指示定义是什么,也已经知道该词在我们语言游戏中起什么作用;(2)在孩子们成为一种语言游戏的玩家之前,他们必须已经了解了语言的指称功能;(3)他们已经处于某种立场中来感知对象,例如感知椅子是椅子。维特根斯坦认为从第三点来看,奥古斯丁把孩子看成是好像能够思考的,“‘思考’在这儿意味着像‘与自己交谈’的事物”[4]32。
为了分清物体,孩子必须能够将对象划归为某一范畴。为了辨认面前的事物是绿苹果,孩子们必须能够在苹果的概念下对它进行分类。
因此,在奥古斯丁的语言习得图景中,孩子在学习语言之前,似乎已经拥有或掌握了一门语言概念。因为,如果孩子在学习一门语言之前,还没有掌握任何这方面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无法通过解释字词意义的方式来教给他们言语,我们也无法通过非口语的实指定义方式来教会他们语言,我们的语文老师也不能用中文中的“痛”来表达英文中的“pain”。因此,在奥古斯丁的语言习得图景中,这就意味着孩子们必须已经拥有了一门语言,掌握了一定的概念;或者至少他们已经掌握了非语言解释的能力。但奥古斯丁的这种方法并不是通过训练来使孩子们习得语言的。
通常在学习语言之前,孩子们的行为是由自然神经脉冲导向的,但这并不包含外在规范因素。当然,在本能模式支配的行为和自发遵守规则的行为之间的界线并非那么严苛。因为有人会说,新生儿的行为也可以被描述为遵守规则的行为,正如新生儿用哭来发出饥饿信号来保证他们的生存一样,新生儿所遵循的规则可以表述如下,“如果你觉得你饿了,那么应该大哭”。甚至规则也允许出现误差:我们可以想象孩子以这种哭的信号来表达饥饿,但是这种信号却失败了,这样一来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大大降低了婴儿的生存能力。这也表明新生儿的本能引导行为包含了一种规范因素,它遵循某些我们进化生物学中的规范。
我们是从科学机制中知道这些生物学规范的,但科学中的生物规范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由社会实践所构成的规范。在科学规范和社会规范中必须有一种独立的标准来进行评判。然而,这些标准在科学理论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同于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适合方向”(direction-of-fit)上的明显差异:一方面,物理论致力于真理这一理想,如果物理论不能满足这一理想的话,或者说如果世界不是按物理论预测的方式来运行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改变理论,而不是改变世界。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实践致力于遵照共同体的规范,如果某个人不能满足这些社会规范的话,那么他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改变他所遵守的社会规范。
进化生物学的规范起到了一种综合作用:一方面,就物种来说,虽然进化生物学理论无法全面反映人们的行为,但人们的行为在描述层次是规范的;因此,如果人们只根据进化生物学来行事的话,那么就大大降低了其生存能力。规则对生存没有例外,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并重新制定规范理论。另一方面,如果就我们自己物种的生存能力而言,我们可以考虑改变我们的行为,例如我们可以考虑停止建造原子电站等行为,以增加我们物种的生存能力。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将生物学标准转化为道德标准。但这种转换破坏了还原论者的观点,还原论者想要把由我们社会实践支配的规范行为还原为由进化生物学支配的规范行为。因此,进化生物学理论表明了新生儿本能引导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生存能力,但却不能被描述为拥有一种规范性,也就是说,无法说明他们的行为是在真正遵守规则。
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理论在描述层次是规范性的,它们遵循如真理般的认识论标准,而我们的社会规范包含了一种外在规范性因素。当世界无法以理论预测的方式来运行时,我们不仅可以选择修正理论,而且也可以拒绝观察陈述。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中,我们会改变或拒绝语言实体,但不会改变或拒绝所描述的事态。同样,当我们指出某人违反了规范时,他可以改正自己的行为,当然他也可以挑战规范或标准[1]。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在训练的过程中,孩子们才能成为语言游戏的玩家,而语言游戏本身又是受规则支配的。当孩子们的行为从自然神经脉冲过渡到遵守外在规范域时,他们就成为共同体成员所完全接受的成员了。孩子们的行为不再是靠自己的直觉来引导,而是受外在社会规范的指导,此时,孩子们可以通过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行为来矫正自己的行为。
三、生物规范行为来自于本能
维特根斯坦的“训练”概念表明,孩子们是如何按照成人共同体所提出的规则来行事的。然而,这并没有解释儿童自己是如何进入规范领域的,换句话说,这并没有解释孩子们自己是如何应用概念和遵循规则的。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思路,为了理解如何从本能模式支配的行为转化为遵守规则的行为,我们必须首先阐明概念和能力之间的关系。在《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主张学习一门语言并不要求孩子事先具有一定的知识,而是要求孩子们拥有一定的能力:“但是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即‘一个已经掌握了一门语言游戏的孩子,他必定知道某些东西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是必须拥有做某些事情的能力’,那这将是一种重复,而这正是我想反对第一句话的地方。”[2]534
为掌握一门语言游戏,一个孩子必须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呢?很明显,这会涉及各种不同的能力。掌握一门语言需要孩子有天赋的能力或与生俱来的能力,如果孩子们不能够对刺激做出类似成人的反应或不能模仿成人行为的话,那么我们无法训练他们。维特根斯坦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试想警犬饲养员做出一些手势和动作来让警犬执行搜救任务,但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对这些手势做出如警犬般的反应,如猫就不会做出如此反应甚至猫会错解这些手势。正如孩子们如果不会对我们的鼓励做出正面回应的话,那就如同人们想教一只猫来执行搜救任务一样,孩子们也无法对成人的话语做出正确的回应。
这说明训练预设了受训者必须具有先天的能力,也就是说,由于受训者的生物结构而先天拥有这些能力。除了这些与生俱来的能力,孩子们也必须拥有向社会共同体中其他成员学习的能力。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通过模仿成人的行为来学习,这是孩子们与环境中的对象互动所产生的行为。通过模仿成人的行为,孩子们学会如何行事,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这是我们的行动,它位于语言游戏的底部”[2]204。在《对数学基础的评论》一书中,维特根斯坦指出在“概念”(concept)和“领会”(grasping)之间有一种相似性:“概念帮助我们领会事物。它们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的情况。”[6]16
儿童通过学习如何在世界中行动,并且通过学习如何操控世界中的一些对象来习得一门语言,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学会了如何认识世界中的某些结构。维特根斯坦给出了一些启发性的事例:“孩子不知道书的存在、扶手椅的存在,等等,但他们学会了如何去取书、如何坐在扶手椅上,等等。”[2]476因此,孩子在习得诸如“扶手椅”“杯子”等词汇之前,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坐在椅子上、喝着杯子中的牛奶。基于这些能力,孩子习得了诸如椅子和杯子等概念,而这些概念又成为了习得其他单词的前提。
由于概念和能力之间的密切联系,维特根斯坦勾画出了一幅世界和语言之间的图景。我们只能通过控制世界中的对象来习得语言。此外,如果世界是不同的,或者说从根本上它会改变,那么我们不会甚至不能使用相同的概念来描述它。“某些事件会把我们置于某一立场,因此,我不能继续进行旧的语言游戏,如此我们就失去了游戏的确定性。事实上,难道语言游戏的可能性不是由一定的事实来制约的吗?”[2]617
因此,维特根斯坦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鸿沟,而这种鸿沟又只能由意义或意向性以某种神秘方式来弥合。维特根斯坦宁愿坚持,语言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而生活形式是由世界中的事物和事实通过实践所构成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世界中的相关事实是我们语言的一部分。如“气温在零度以下时,水会结冰”这是一种事实,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这一事实融合为我们语言游戏的基础”[2]558。
但是,到目前为止,维特根斯坦并没将概念等同于能力。因为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所告诫的一种简化。他后期哲学的特点是研究语法,并反对还原论者的理论。他指出:“‘概念’是一个模糊的概念。”[6]70当孩子们第一次受训从事某种行为时,他们还没有完全拥有这个概念。在《哲学研究》§2中,维特根斯坦介绍了所谓的语言游戏,但在语言游戏中所发生的每一种事情,不能都称为一种概念,那在§2的语言游戏中有概念吗?如“板”“砖”“柱”等概念。当然,在参与语言游戏的这些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更为重要的是,‘概念’是指在语言游戏机制中的一种权宜之计。”[6]71
在§2的语言游戏中只涉及2个玩家和4个词:“砖”“柱”“板”和“梁”。当玩家张三喊出其中一个词时,他的助手李四就会递给他相应的对象,这些对象是李四在对话过程中学会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孩子们也是被训练得做出此类行为。在§2的语言游戏中,李四还没有说出一门语言或拥有一种概念。因为这只有4个字词可以使用,李四也只能按张三给出的命令行事,他没有办法来反思他们的语言游戏。只有当语言游戏得到扩展,达到了某种复杂程度时,才能使李四反思语言游戏中某种语词的用法,从而指出其错误,此时才能说李四拥有了该概念。
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解释语言游戏是如何扩展或者由谁来扩展的。是由玩家张三和李四他们来扩展语言游戏的吗?或者是由掌握了更复杂、更丰富语言的言说者来扩展的吗?对维特根斯坦而言,这种语言游戏的扩展既不是由张三和李四,也不是由受过训练的孩子来完成的,而是由他们的教练、成人言说者来完成的,因为成人已经开始了解规范领域,而且他们也已经掌握了一门语言。维特根斯坦认为,孩子通过这种训练参与到社会实践之中,并且这种训练是由已经掌握一门语言的成人来进行的。
此外,维特根斯坦还认为像真理、知识这样的规范概念,从来不是从因果领域发展而来的,但它们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实践之中,在实践中孩子被训练如何来玩语言游戏。当他们第一次在语言游戏中学会某些概念时,他们还不能做出超越训练立场的行为。例如,儿童不会怀疑与语言游戏相关的对象。“孩子学会相信成人,怀疑是在有了信念之后。”[2]160怀疑意味着孩子在语言游戏中尚未习得相关立场。例如,在§2的语言游戏中,玩家张三只能给出命令,但不能提出疑问或做出讽刺性的评论等。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教孩子说‘这是你的手’,而不是说‘这也许是或可能是你的手’。这就是孩子如何学习关于他自己的手的无数语言游戏。这里的问题是,一方面,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是否真有一只手’;而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学习,他知道这是一只手。”[2]374
在§2的语言游戏中,只有当李四或孩子们习得并掌握了语言游戏时,才允许他们谈论命题的真值,或者说允许他们知道这个或这个是那个时,他们才有能力在理性的逻辑空间里做出更复杂的行动。当成人言说者认为时机适当时,他们可以将知识归因给儿童。只有当“知道”“真理”或“与现实一致”这些词是属于语言游戏的一部分时,它们才是有意义的。在这里,“与现实一致”一词似乎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应用。儿童习得像“知识”“真理”这样的概念,与他们习得其他语言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们是通过训练来参与到复杂的社会实践之中。只有达到这种复杂程度时,他们才有能力去反思。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的话,那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就整体语言来说,我们不能用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当我们试图这样做时,我们就失去了做出修改所需的工具。如果我想把门打开,铰链必须不动。
总之,维特根斯坦认为,在解释语言习得的过程中,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儿童需要具备一定的先天能力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受训者。然后,他们开始模仿成人的行为,通过这一过程开始构建自己的世界形式,并开始应用相关概念。成人对儿童的持续培养,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能力,使孩子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词汇,而且使他们能在语言游戏中做出相应回应,直到可以把他们称为合格的语言言说者。
四、遵守规则行为来自实践
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他发展了一种以自主性为特征的语言习得图景。在§2中,维特根斯坦对训练的评论已经表明孩子是被成人同化,从而参与到受规则支配的复杂社会实践之中。但维特根斯坦几乎没有讨论过这样的社会实践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说,他没有讨论人类最初是如何形成一个社会群体,并且是如何参与社会实践的。他也没有讨论规范领域是如何从原因领域演变而来的,而仅仅说明了孩子最初是如何进入规范领域的。维特根斯坦设想在语言概念和能力之间有密切联系,那二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当然,维特根斯坦反对将真理和指称当成是语言习得图景的基本概念,“他反对这一观点,即语法规则镜像了实在的本质”[7]。然而,维特根斯坦对概念和能力之间关系的讨论表明语言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由我们的生活形式来确定的,也就是由我们所参与的社会实践来确定的。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把规则支配的行为与原始本能引导的行为进行了类比:“我想把这里的人类当作一种动物;正如原始人类拥有的是本能,而不是推理能力。正如在原始状态下的生物。任何逻辑能力足够好的原始人则不需要类似于我们的沟通方式。语言并不是从某种推理中产生的。”[2]475
原始人类包括新生儿,他们只是受本能驱使而行动,而不是出于某种原因或推理。因此,人类所从事的第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并不是来自推理的结果,它们只不过是被动产生的。“这种游戏被证明是有价值的,这是人们玩游戏的原因,而不是推理驱动人们玩游戏。”[2]474这些评论表明,人类通过实践发展了语言,这是合乎理性的,但还没有涉及因果规范方面。世界所施加的约束限制了我们能参与哪些实践。只有在证明这种实践是成功的情况下,才能培养孩子参与实践之中。在其他文化中,他人所发展的实践不同于我们的实践是有可能的,但所有这些实践活动必须要适应这个世界。世界并没有强迫我们进入一种特定的实践,它排除了某些来自可能领域中的实践。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语言习得是自主性的,原因在于:(1)它独立于心理事件和心理表征;(2)词和对象之间具有指称关系;(3)语言习得过程是自主的;(4)实用的目的。对于这种语言习得图景,维特根斯坦反对用还原论者的方法对规则进行解释,即反对用我们物理世界的因果律来支配我们的语言游戏。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语言是独立于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的。无论是个体发生还是整合到目标导向的人类实践中,语言对规则的构成都产生了影响。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指出,我们语言游戏的具体形式是没有理由的,“你必须记住的是,语言游戏就是说不可预知的事物。我的意思是说:语言游戏是不合理性的。它就如我们的生命”[2]559。
语言自主性的论题决不能被误解为是完全脱离物理世界和我们生活形式的。我们的社会实践,包括我们的语言游戏是深深植根于物理世界的。此外,我们规则支配的行为同时也是基于本能引导的行为,这一点与动物无异。因此,世界通过对实践的限制来塑造我们的生活形式,包括我们的语言,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都是合乎理性的。如果我们想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最初在发展一门语言时,是采用这种规则集,而不是另一种规则集时,我们只能引出原因,因为没有理由来说明这一过程。如果我们试图来解释语言的复杂实践,那么我们发现自己无法从因果律得出规则,而因果律是支配物理世界的规律,我们的语言规则是自主的,它们属于规范领域,不属于原因领域。
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图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原因和规范。他认为,在两者之间可以画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因为两个不同的领域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他坚持认为两者都是我们天性中的一部分。“指挥、提问、讲述、聊天,就像我们散步、吃、喝、玩一样,都自然历史的一部分。”[4]25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维特根斯坦的立场称为自然主义。然而,关键是要看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自然主义是如何不同于还原论者的自然主义,并且还原论者的自然主义立场在当代心灵哲学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如果概念的形成可以用自然事实来解释的话,那么概念和一般事实之间应有某种对应关系。但“我们并不讨论这些概念形成的原因;我们也不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研究自然史,因为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目的而发明虚构的自然史”[4]230。
在后期哲学中,维特根斯坦还阐明了世界中的规范问题。他认为,科学所描述的世界和根据规范来解释的心理现象与生活世界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用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话来说,科学和显象(manifest image)之间是有区别的。维特根斯坦告诫说,我们处在世界和共同体之中,我们在世界和共同体中是受理性和原因支配的。科学图景是从理性层面抽象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形成一个全面的因果律形式,如果没有这些科学图景的话,那么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科学就不会取得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然而,尽管科学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决不能忽视科学只能是基于抽象的显象而发展起来的。根据塞拉斯的观点,显象是“一种框架,这种显象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世界中的人”。“这是一个所谓精细化或复杂的‘原始形象’。”[8]另一方面,科学图景是通过科学理论来推断出“不可观察物体和事件,目的是为了解释可被感知事物之间的关联”[8]。塞拉斯清楚地表明,尽管显象是直接的,但更应优先考虑科学图景,并且我们不应该完全消除显象,而是应该把科学图景和显象都囊括在内。此外,塞拉斯还根据显像的不可还原特性发展出一种人类的概念框架,但这种概念框架需要使用科学图景来解释,从而获得解释上的优势。
当代心灵哲学中的主要立场是采用塞拉斯的观点,即把显像与科学图景之间的区分作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也有一些还原论者追随塞拉斯的脚步,通过科学语言所提供的方法来解释规范性。但还原论者所设想的这个策略可能是行不通的,因为只有当科学理论的假设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时,这才是有效的,而且还原论者的选择完全取消了显像。科学的运作不可能获得关于人及其在世界立场中的全部理解。科学图景忽视了人类自身的形式,当用科学图景来理解人类生活形式时,我们要退回到现象层次来解释相关现象。
五、结论
维特根斯坦不是要将人类的框架与科学图景进行调和,而是认为我们错误地将诸事实看作为一个原型现象。科学图景表明我们专注于特定的、明确定义的现象是卓有成效的,但当科学涉及到建构一个更全面的抽象规范图景时,就会有太多的局限性。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处在一个人与物交织的因果关系网之中,生活在一个由各种原因和规范所支配的世界和共同体之中。世界对我们来说是开放的,用抽象的理论无法来把握世界全貌,但是我们可以更详尽地分析和描述它。当然,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试图把规范还原为原因,他也不认为科学理论可以证明规则的合理性,而我们的实践和语言游戏正是由规则所支配的。虽然维特根斯坦把原因和规范设想为一个实体的两个方面,但他并没有讨论理论如何描述不同层次的实在,他想要做的是把物理学和心理学的问题都可以统一到一个包罗万象的通用理论中,即发展一个完整的、连贯的世界图景。这样,我们通过由规则支配的社会实践就可以获得对语言更全面的理解并获得一种生活形式,从而获得规范概念来指导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