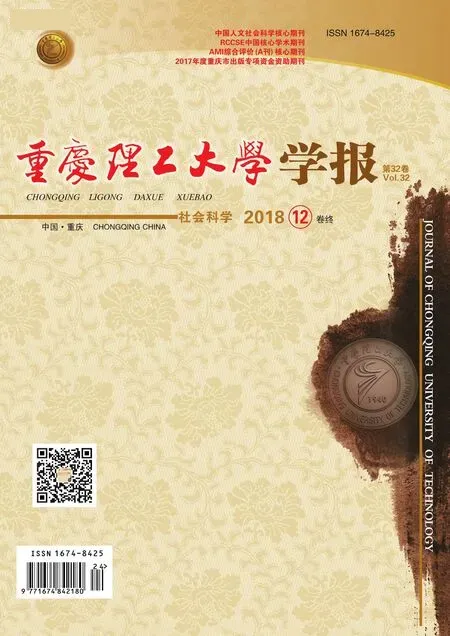关于悖论“三要素”定义的问题
胡义昭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一般来说,对于一个主题的探究并不是从一个完美的定义开始的,而是从一个不完美的定义开始的。而起初不甚完美甚至还有严重瑕疵的定义,一般来说都会随着探究的不断深入逐渐朝着更完美的方向发展。但是很有可能,尤其在面对经验主题的时候,譬如因为主题的边界模糊或者语言的精度不足,无论我们的探究达到何种精细程度,一个完美的定义也始终是我们无法企及的。对于这种语言上的局限,我们可以像接受不允许人类制造出永动机的物理规律那样坦然接受。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进行有意义的探究并且取得有意义的成就。
对于悖论这个主题来说,缺少一个完美的定义可能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因为在对这个主题的探究当中,相比于要为“悖论”寻找一个恰当的定义来说,对于“悖论”这个名字之下的某一个或者某一些悖论给出合理理解或者有效消解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甚至完美的定义,对于我们的探讨必定是更好的事情。
大约30年前,张建军教授因为对当时他所接触到的悖论定义不满,提出了自己的“三要素”定义。这个定义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定义,本来是有利于促进国内学术界对悖论的探讨的,而它本身也可以在更进一步的探讨当中获得实质性的改善。但是,从国内学者的反应来看,早期几位学者基于辩证法或者辩证逻辑的立场对于这个定义有一些不得要领的批评①可以参见张建军教授收录在《矛盾与悖论新论》中的《再论悖论是一种逻辑矛盾》这篇文章了解相关批评。,后来一些学者在相关文章中是未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定义,而几乎仅有的例外是陈波教授,10多年间,他从《逻辑哲学》到《悖论研究》,一直保持着一种轻微批评的态度:
我基本上赞同张建军关于悖论三要素的说明,认为它是深刻的,但有两个严重保留:(1)不太赞同把“悖论”仅限制于“由两个互相矛盾命题构成的等价式”,因为有许多公认的“悖论”,例如有关上帝的全能悖论和全知悖论,各种连锁悖论,各种归纳悖论,许多认知悖论(如摩尔悖论),都不表现为这样的等价式,勉强把它们划归为这样的等价式也不太自然。其次,在我看来,悖论意味着思维在某个地方出了毛病,但张建军的定义中很少有这个意涵,“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这些字眼容易给人造成误导,似乎导出悖论的过程中一切正常且正确。[1]6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建军教授直到今天还坚守着他的“三要素”定义。或许,这个定义早就在等待一个详细的评论了。跟陈波教授的简短评论不一样的是,本文基于对张建军教授的“三要素”的分析,认为 “三要素”定义并不是一个好的定义。
一、 “三要素”定义的基本脉络
张建军教授在1991年12月向首届全国科学逻辑讨论会提交的《悖论的逻辑与方法论问题”》论文当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悖论“三要素”定义①[2]10。第二年,也就是1992年,这篇论文发表在张建军教授和黄展骥先生联合出版的《矛盾与悖论研究》中,逐渐在国内学术圈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这篇文章当中,他是这样说的:“悖论是指这样一种理论事实或状况,在某些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之下,可以合乎逻辑地建立两个矛盾命题相互推出的矛盾等价式。”[3]51稍后,张建军教授从他的定义当中进一步明确提炼出了“三要素”的表述方式:“①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②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③可以构成矛盾等价式。”并且特别强调“构成悖论必须具备三要素”,“三要素构成悖论的基本逻辑结构,缺一不可”[3]56。
自此以后,张建军教授的“三要素”定义就这样被固定下来,除了他后来更愿意用“逻辑悖论”代替这里的“悖论”以及因为之前对于“命题”的使用不符合学术主流而改为“语句”这两点之外。他说:“(逻辑)悖论指谓这样一种理论事实或状况,在某些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之下,可以合乎逻辑地建立两个矛盾语句相互推出的矛盾等价式。”[5]“逻辑悖论指谓这样一种理论事实或状况,在某些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之下,可以合乎逻辑地建立两个矛盾语句相互推出的矛盾等价式。”[2]7,[6]而他相应的“三要素”表述则除了第三要素当中的“构成”改为“建立”而外没有任何变化。
公正地说,张建军教授的这个定义对于当时的国内学界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首先突出了悖论是一个产生矛盾的论证过程而不是作为论证结论的矛盾,其次明确地指出是哪些因素在一个悖论的论证过程当中起作用。张建军教授后来回忆他在“三要素”定义之前使用的定义时说:“悖论就是从某些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的等价式。”①[2]10然而,他忘记了他之前的表述当中其实还有“看起来合理”[4]30这样的字眼,而对这样的模糊表述的不满恰恰是张建军教授提出和坚持“三要素”定义的一个关键动机,也正是他接触到英国哲学家赛恩斯伯里(R.M.Sainsbury)在《悖论》这本书当中的悖论定义之后视为“模糊三要素”而没有充分认可它的原因。他说:“各种主要定义实际上都可视为英国学者塞恩斯伯里[注]张建军教授后来改译为“赛恩斯伯里”了。(R.M.Sainsbury)模糊性三要素结构(‘明显合理的前提’‘明显合理的推理’和‘明显不合理的结论’)的明晰化和精致化。”[5]
赛恩斯伯里的《悖论》第一次出版是在1988年,还稍早于张建军教授第一次公开提出的“三要素”定义的时间。但是,由于当时国内跟西方世界学术交流的时效性还比较差,等到张建军教授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他提出自己的“三要素”定义之后好几年了。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如果赛恩斯伯里的这本书第一时间流传到国内,或许张建军教授的“三要素”定义就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了。值得注意的是,赛恩斯伯里的这个定义其实是在他的那本书的引言当中顺便提到的。下面我们照着张建军教授给出的、更方便我们这里理解的翻译形式,将“apparently”翻译为“明显”的这个词改译为语义稍弱的“看起来”之后,给出这个定义:
我所理解为悖论的东西就是:从看起来可接受的前提,经看起来可接受的推理,得出了看起来不可接受的结论。[6],[7]1
至于赛恩斯伯里的“明显不可接受的结论”是否可以完全理解或者转化为矛盾,虽然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不过因为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就不在这里详细讨论了。本文对于悖论范围的理解基于一个稍加修改但是仍然被相同对待的赛恩斯伯里定义:从明显可接受的前提,经明显可接受的推理,得出了矛盾的结论。
在我们今天看来,赛恩斯伯里定义是一个更好的定义,也是这篇文章要推荐的一个定义。首先,它从论证结构的角度更清楚地展示了一个悖论从前提经过推理得到结论的过程和结构。而张建军教授的“三要素”定义因为避免“前提”而选择“背景知识”则可能造成如何在前提和推理这两个论证要素之间确定哪些是“背景知识”这样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也导致了下面还会谈到的一个麻烦:他起初把前提理解为“背景知识”,而后来又把推理规则甚至“认知共同体所使用的逻辑”[5]塞到“背景知识”当中从而不得不修改对于“逻辑推导”的正常理解。其次,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张建军教授一向反对的模糊性表述,赛恩斯伯里定义可以将那些对于逻辑和哲学来说有意思的悖论涵盖其中,而张建军教授的“三要素”定义尽管同样宣称有这样的涵盖范围,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从一开始,他就认为“三要素”定义“可以很好地涵盖所有已知的集合论——语型[注]原文如此,后来张建军教授改为通行的“语形”。悖论和语义悖论,刻画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并进一步认为“以此定义加以衡量,悖论又远不局限于这两类对象。”[3] 56接着,他就把譬如“追光悖论”“波粒二象性疑难”[3]59这些物理学家叫做“悖论”的一些现代理论疑难囊括其中。到后来,他出于区分论域的需要给出“狭义逻辑悖论”“具体理论悖论”“广义逻辑悖论”这些概念,更明确地描绘出了“三要素”定义统辖的各种范围:“‘狭义逻辑悖论’不仅可以涵盖集合论悖论和经过严格塑述的语义悖论,而且可以涵盖上世纪后半叶所严格建构的‘认知悖论’与‘合理行动悖论’(我称之为‘语用悖论’);凡符合三要素界说但不同时具备上列两个特点的悖论,我又根据其‘背景知识’不同划分为‘哲学悖论’和‘具体理论悖论’两大种类,并将三大类悖论统称为‘广义逻辑悖论’。”[6]张建军教授在将他的“三要素”定义的覆盖范围尽量扩大的同时,也注意到某些“逻辑悖论”不能直接套用这个定义,而需要进行他称之为“塑述”的一种解释转化以符合“三要素”的要求。但是,他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在“广义逻辑悖论”范围内,张建军教授对于那些物理学“悖论”的理解有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忽略了现代物理学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物理学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只是在构造更完美的理论假说符合更广泛的实验证据。那些物理学“悖论”不过是对应的理论假说遭遇的矛盾而已,从逻辑和哲学的角度并不适合被理解为一个纠缠理智的悖论,更别说是“逻辑悖论”。即便是回到相对安全的“狭义悖论逻辑”的范围,对大多数悖论的“塑述”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张建军教授通过下面两种方式规避了这样的困难:要么把以理发师悖论为代表的显然不符合“三要素”要求的那些悖论排除在“悖论”之外而安置在“拟化悖论”之下,要么是在“塑述”一些悖论的过程当中有意无意地丢弃那些不符合“三要素”的因素(对于这种方式,我们将在第二节以对意外考试悖论的“塑述”为例简要介绍)。这些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三要素”定义的刚性过强(引起的“定义过窄”[6])跟它要覆盖的悖论范围过宽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张建军教授那里一直保持着,尤其是在他受到赛恩斯伯里的《悖论》影响要在“三要素”定义当中引入悖论度概念[5],以及把在悖论推理用到的逻辑规则转移到“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5]当中以来,更是达到了空前的强度。然而,这并没有引发张建军教授在“三要素”定义上的自我革命,他依然采取之前一直在对“三要素”定义的解释当中增加柔性来缓冲它的表述刚性的策略,只是要比之前增加更多柔性的解释罢了。
下面,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将张建军教授的“三要素”定义发展分成两个阶段,在他明确引入悖论度的概念和将悖论相关的推理规则移动到“背景知识”当中之前视为前期,之后就是后期。由于张建军教授使用“逻辑悖论”这个名字仅仅基于“‘逻辑’主要指谓悖论推导过程的‘逻辑性’”[8]这样一个不太恰当的命名理由[注]在逻辑和哲学的圈子外,“逻辑悖论”往往是用来模模糊糊地指称那些因为富有推理的逻辑趣味而应该交由逻辑学家来管理的悖论。但是对于这个圈子之内的学者来说,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凡是悖论都是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得到矛盾的,那么凡是悖论都可以按照张建军教授的这种理解称为“逻辑悖论”,因而“逻辑悖论”没有它应当具有的区分能力。,我们下面除了引用原文的地方之外都直接用“悖论”来代替张建军教授的“逻辑悖论”用法,也算是恢复到了他初期的正常用法。
二、 “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
“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是“三要素”定义的表述刚性的主要来源。张建军教授可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对于“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的解释始终包含着另外两个因素:“导致悖论的‘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既可以是人们公认的明晰的知识,也可以是人们不自觉确认的共同直觉;既可以就普通人的人类思维而言,也可以就某一学科领域而言,落实到具体的悖论,便是明确的而非含混的。”[3]51仅仅从这样的解释表述来看,既要让“公认”覆盖“不自觉…… 的共同”,又要让“知识”覆盖“直觉”,难免让人觉得有点勉强。
单从“公认”来看,它似乎至少意味着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公开宣告。如此强烈的语气,张建军教授一直试图用“不自觉确认的共同直觉”来缓和,但是他又觉得后者的刚性不足,立即补充以“明确的而非含混的”来表述。以罗素悖论或者说谎者悖论为例来看,用“不自觉确认的共同直觉”来描述它们当中引发悖论的前提原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再加上“明确的而非含混的”这样的限定就会出现问题,因为这些前提更应该被看成是一些位于边缘地带的模糊直觉,它们在被发现可以引发悖论之前一直是未经审查的,仅仅因为跟另外一些更明确的直觉的相近关系才被引入悖论的前提当中:譬如对于罗素悖论来说,“日常世界当中的红色个体可以构成一类”是一个明确的平常直觉,而跟它相近的“所有红色的东西都构成一个类”这个直觉并不是那么明确的,因为之前并没有认真发生过从“红色个体构成的类是否也是红色”开始不断超越日常世界的扁平层级的思考。
张建军教授也多次提到“将‘公认’置入悖论定义是受罗素的论述启发而来”。他引用了罗素在1959 年回顾罗素悖论的发现时写的一段话:“无论哪一派的逻辑学家,从他们所公认的前提似乎可推出一些矛盾来。这表明有些东西是有毛病的,但是指不出纠正的方法是什么。”[6]然而,张建军教授遇到的是一个糟糕的翻译。查看罗素的原文[注]Bertrand Russell,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George Allen & Unwin,1959年,第58页。,其中翻译为“公认”的“accept”更应该翻译为“接受”。“正确”(和“知识”一起)的表述刚性更强,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上面说过的把理发师悖论当作“拟化悖论”排除在外。坚持“正确”的要求,这也是张建军教授从起初放弃“看起来合理”到后来拒绝“看起来可接受的”这样的模糊表述的根本原因。但是他始终没有注意到的是,即便对于兰姆塞(F.P.Ramsey)的比较狭隘的悖论范围来说,在排除了在赛恩斯伯里那里悖论度非常低的一些悖论以后,除了悖论度非常高的罗素悖论和说谎者悖论可以基本符合软化处理的“正确知识”的要求之外,其他悖论都很难符合“正确”的要求,譬如对于按照理查德的方式定义出来的理查德数(Richard’s number),我们事先并没有什么关于理查德数是否合理的明确“知识”或者“直觉”,只是等到推出矛盾的结果后我们才发现这样的定义方式其实是不合理的。但是,这样的问题都被相关的“严格塑述”通过语焉不详的方式给掩盖过去了[2]15-16,89。
还有张建军教授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发现一个悖论的出错原因,不妨按照“三要素”的说法,是一个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譬如罗素悖论当中的朴素概括原则,那么对于这个悖论的合理消解就是否认这个背景知识,这样一来它就不再是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按照张建军教授的“三要素”定义要求,这个悖论就不再应该被称作悖论了。而对于赛恩斯伯里的“看起来可接受”来说,我们则可以通过引入在它的模糊性范围之内的因素,譬如“相对于那些还没有深入了解罗素悖论的人来说”,用来放在“看起来可接受”前面加以限定,从而避免这种命名合法性丧失带来的尴尬。
在张建军教授后期尝试引入悖论度的情况下,“正确”的过强刚性的问题更加突出。因为“正确”在一般的学术使用当中,很难被赋予程度上的差别,而基于一个像赛恩斯伯里那样允许模糊性的悖论定义,悖论度谈论的是悖论构成因素的合理性或者可接受性的程度。对于张建军教授来说,他必须将当初放弃的“看起来合理”的模糊性重新带回到同时保持“明确而非含混的”的“公认”上来,从而引起更大的张力:“由‘公认’的模糊性可以自然引出‘公认度’与‘悖论度’的概念,而如果悖论的其他两要素经得住推敲,那么它由以导致 ‘背景知识’的 ‘公认度’就决定了其 ‘悖论度’。”[5]张建军教授对于这种张力的感受,最近达到了顶点:“如果我们能够就上述基本意涵达成共识,则‘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也可以改述为‘特定认知共同体的公共信念’这一不会引发歧义的表述。”[6]但是,即便软化到“特定认知共同体的公共信念”这样的解释,“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还是没有摆脱另外一个重要的弊端,那就是把从看起来合理的假设前提推出不合理的结论的那些悖论排除在外。奇怪的是,尽管认知悖论、“合理行动悖论”都是这样的悖论,按理是不应该出现在“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的覆盖范围内的,但是张建军教授的“狭义逻辑悖论”还是将它们全部收录。认知悖论、“合理行动悖论”以关于认知或者行动的合理假设为基本前提,因为看起来合理但实际上不合理的其他前提或者某个推理细节,却推导出了不合理的结论。以意外考试悖论为例,其中一个基本前提是假设老师在下周三天(这里依照张建军教授在文献[2]第165页做出的简化)的某一天举行一场考试,这种可能性是我们当然可以接受的,而且老师还希望这次考试的举行日期对于学生来说是意外的,这也是一个合理假设。那么老师在考试日期上有3种选择,学生看起来没有办法提前预测。就是针对这样一个悖论情景,张建军的“严格塑述”基于认知逻辑的形式工具展开,先是把老师的预告形式化为P1开始[2]166,然后强调学生推理依据的“关于知识的两个合理的假定”,还有其他认知逻辑公理,最后推出矛盾。但是,他既忽略了P1不是一个“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而只是合理假设,也没有明确地把同样重要的3天之内必有一场考试这个合理假设明确展示出来。因此,张建军教授在别的地方批评赛恩斯伯里的悖论定义当中的“看起来可接受的前提”当中的模糊性,而在意外考试悖论当中显然应该接受这样的模糊性的时候却视而不见,这多少有点让人不好理解。
三、 “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
尽管张建军教授在“三要素”定义的前后期在对“逻辑推导”的理解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是他一直都在“合乎逻辑”的指引之下坚持“严格无误的逻辑推导”这一表述:“任一悖论都是从某些背景知识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4]“‘严密无误’是对悖论的推导的‘本质要求’:若推导不严密,就不可能构成真正的悖论。定义 I 的‘严密的逻辑推导’要素,就是用从第(1)要素到第(3)要素之过渡的合乎逻辑性,取代定义II的‘看起来可接受的推理’及其他定义的类似模糊说法。”[6]初看起来,张建军教授这样的坚持没有什么问题。首先,我们最不能容忍的论证谬误就是推理错误。其次,在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悖论当中,导出矛盾的推理步骤都不复杂,如果导致的矛盾是其中的推理错误,那么这样的推理错误应该也很容易识别出来,我们早就应该发现这样的错误而把这样的论证称之为逻辑谬误而不是归为悖论了。这样一来,我们应该只把那些满足“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的论证称作悖论了。但是,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在前期,张建军教授还没有将推理规则(或者逻辑[注]一个推理过程用到的逻辑在这个推理过程当中的作用都可以通过推理规则表现出来,譬如一个逻辑规律可以看成是一个空前提的推理规则,那么我们就可以只需提及推理过程当中用到的推理规则。)移入第一要素的时候,他的“逻辑推导”其实就是赛恩斯伯里和其他大部分学者使用的“推理”。此时张建军教授强调“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尤其强调“严密无误”的刚性,就是不允许一个悖论因为推理错误而导致矛盾。但是,这又一次造成了他的定义表述难以覆盖他想要的悖论范围这种局面。而与之相反的是,在对悖论的关注范围大致相同的条件下,赛恩斯伯里(和其他学者,譬如苏珊·哈克和罗伊·A·库克[注]可以分别参见苏珊·哈克的《逻辑哲学》(商务印书馆,1993年),172页和Roy A.Cook的Paradoxes(Cambridge,2013),9-10页。)对于悖论的理解没有这样精致化的要求,而有的只是“看起来可接受的推理”这样的模糊限定,但是不会遇到张建军教授一再遇到的这种局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张建军教授在前期忽略了一个悖论因为错误推理而导致矛盾的两种可能性。其一,一个悖论之所以推导出矛盾可能只是因为依循惯例选取了不恰当的逻辑框架从而提供了不恰当的推理规则,譬如说谎者句子在经典二值框架下导出矛盾的推理是有效的或者“严密无误的”,但是非经典的三值框架才是刻画说谎者句子的恰当框架。其二,一个悖论在一个恰当的逻辑框架当中之所以推导出矛盾也可能是因为一个推理错误,一个要么使用了看起来正确但实际上错误的推理规则,要么看起来正确、实际上错误地使用了推理规则(尽管后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的推理错误。第二种可能性在前面谈到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没有提到的是,在一个推理过程当中,是否能够轻松识别其中的推理错误取决于是否对它有一个足够细致的逻辑刻画,而在某些即便看起来简单的推理当中,譬如在意外考试悖论的推理当中,这样的刻画也可能不是那么轻易得到的,这就导致我们很难发现其中的推理错误。
而到了后期, 张建军教授因为“面对各种使用非经典逻辑的理论系统及解悖方案”[5]的需要,也就是要摆脱某些悖论的症结根源于不恰当的逻辑框架这种情况对于“严格无误的逻辑推导”的威胁,而将推理规则从“逻辑推导”当中转移到“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时,实际上他改变了对于“逻辑推导”的正常理解,相当于从推理当中抽走推理规则而只剩下几乎空洞的对于推理规则的正确使用。他说:“诚然,其中‘推理规则’的正确性当然也可质疑,但是对‘推理规则’的质疑并不等于对‘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的质疑,这里的‘严密无误’只是指其推导乃从‘公认’前提根据公认‘推理规则’所作,即没有出现违反逻辑规则的‘谬误’。”[6]
张建军教授仅仅为了在表述形式上继续维护“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而把“逻辑推导”交给一个特设性的解释,这样做不仅没有带来额外的好处,而且还要因为抵御他从未注意到的第二种推理错误的可能性对于“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的威胁,造成一种不必要的理论需要,就是把一些可能更应该理解为错误使用了正确的推理规则的情形都统一归结为正确使用了错误的推理规则的情形——至于这种归结是否总是合理,也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些麻烦在赛恩斯伯里那里都是不必要的。
四、 “可以建立矛盾等价式”
张建军教授坚持“可以建立矛盾等价式”作为他的悖论定义的“三要素”之一,起初可能只是因为他在“悖论是一种特殊的矛盾”的观念诱导之下对于悖论和矛盾之间关系的一个误解:“悖论之区别于逻辑矛盾的形式方面的特征,就在于前者可以建构矛盾命题互相推出的矛盾等价式。”[3]51而这个误解又跟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这么一个简便的说法带来的困惑有关。而后来,他一直坚持强调矛盾等价式,大体上只是基于对于矛盾等价式默认可以表述矛盾这个认识对自己的思想传统的坚持:“… … 只要由第(1)(2)要素得到矛盾,就意味着‘矛盾等价式’的获得,后者不必再表达出来。拙著之中对大部分悖论的建构,也只是到‘得到矛盾’为止,没有再施行矛盾等价式的建构步骤。”[6]一般情况下,对于一个悖论来说,强调“可以建立矛盾等价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但是强调矛盾等价式没有语义上的实质意义。
矛盾是一个语义概念,而矛盾式(“p∧ ﹁p”)和矛盾等价式(“p↔ ﹁p”)则是两个语形概念。我们知道,矛盾等价式是在说谎者悖论和罗素悖论当中推导出来的矛盾的经典形式,而且一般情况下,矛盾式和矛盾等价式是可以互相推出的。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要检验一个推理的结论是不是矛盾的,尽管矛盾有时候倾向于以矛盾式的形式出现,有时候倾向于以矛盾等价式的形式出现,但是推出的结论只要能够被我们在语义上确认为矛盾就可以了,而不必事先规定一个特别的语形形式来作为验证标准。如果说“可以建立矛盾等价式”并不要求实际建立一个矛盾等价式,而是建立任意一个在语义上等价于矛盾等价式的矛盾形式,那么为什么要绕着“矛盾等价式”转一圈再回来,而不直接用赛恩斯伯里定义(当然是修改版的)的“推出矛盾”呢?而在特殊情况下,就是像在说谎者悖论当中需要引入非经典逻辑这样的情况下,矛盾等价式“p↔ ﹁p”不能再继续表述矛盾,那么这时候还要求“可以建立矛盾等价式”就是错误的了,正如下表基于常见的三值语义展示的那样:

p﹁pp↔ ﹁pTFFFTFNNN
“p↔ ﹁p”不再能够表述在各种语义赋值之下都达到假的矛盾。而赛恩斯伯里定义当中的“推出矛盾”却是在语义层面上提出的直接要求,可以避免在这样的非经典框架下因为语形跟语义之间的微妙变化出现失效的情况。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非要坚持“矛盾等价式”的要求不可,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引入真值谓词(譬如“… 是真的”“… 是假的”“… 是不真不假的”[9])的方法将非经典框架当中的矛盾带回到经典框架当中来刻画,从而恢复“p↔ ﹁p”表述矛盾的能力。特别对于说谎者悖论来说,这个方法是非常自然而且合理的。不过,张建军教授一直没有注意到非经典情形对于矛盾等价式的直接反驳,也就从来没有考虑到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挽救关于“矛盾等价式”的要求。并且,即便张建军做了这样的挽救,那也不过是将我们重新带回一般情况,再一次面对“强调矛盾等价式没有语义上的实质意义”这样的批评而已。
五、余论
30年前,张建军教授研究悖论的时候国内逻辑研究起步未久,他们那一代人可谓筚路蓝缕。他当时能接触到的那6个悖论定义当中,前4个非常糟糕的定义(譬如“定义II:‘一命题B,如果承认B,可推得非B,如果承认非B,又可推得B,称命题为一悖论’”[3]49)都是来自当时国内出版不久或者计划出版的专业辞典或者综合辞典的专业分册,而最后两个定义虽然好一些,但都是来自国外20年前的文献了[3]75。可以想象当时国内的学术环境跟现在相比真是云泥之别。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张建军教授在悖论研究领域一路奋进,成果斐然,令人敬佩。作为一个后来的评论者,我真心希望这篇文章是张建军教授一直在等待的一篇要求认真商榷的文章,尽管可能来得有一些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