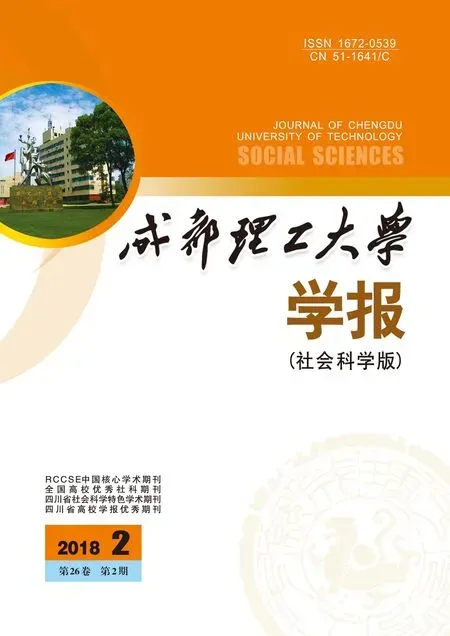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问题探究
高正旭
(昆明理工大学 法学院,昆明 650504)
中立帮助行为是指外观上无害、不追求非法目的的日常行为或职业行为,而客观上对他人的犯罪却起到促进作用的情形。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在我国过去的刑法研究中属于一个较为冷门的问题。最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了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该规定的出台引发了关于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问题的讨论。如有学者指出,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规定是将网络提供商日常服务这种典型的中立帮助行为正犯化,使得刑法可罚和不可罚的边界变得模糊,缺乏立法上的严谨性[1]。如何理解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规定和合理划定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边界,成为刑法理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拟从分析中立帮助行为的概念入手,由此搭建问题讨论的平台,梳理现存的中立帮助行为理论,寻找该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中立帮助行为的概念界定
明确中立帮助行为的概念是对其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基础。从外观上来看,中立帮助行为似乎是与犯罪无涉的日常行为或者业务行为,此类行为的特点是由行为人在日常行为中予以反复实施,一般不会产生社会危害性,但又在偶然的情况下被犯罪人利用于犯罪活动[2]。
所以仅从外观上来看的话,所谓的中立帮助行为与我们每个人的普通日常行为并无区别,因为每个人生活中的行为都可以被用于促进他人犯罪。如父亲给儿子的钱可能被儿子用于日常消费也有可能被利用于实施犯罪,农药店卖给他人的农药既有可能被用于农业生产也有可能被用于毒害他人。所以如果仅从客观方面判断的话,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几乎都可以称之为中立帮助行为,如此则无法将中立帮助行为予以类型化并进行讨论。主客观相一致是我国传统理论评价犯罪行为的理论基础,要判断一个行为是否为中立帮助行为,还需要进一步对行为主观进行认识。
中立帮助行为的“中立性”特征来源于其客观上的日常性和职业性,因为缺乏具体的犯罪实行行为,如果要将中立帮助行为入罪化,只能将其作为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是指在犯罪过程中对实行犯的犯罪行为起到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帮助犯的帮助行为可能发生在犯罪发生之前或者犯罪发生之际,也有可能存在事前通谋并于犯罪之后提供帮助的帮助行为,但是无论其行为表现如何,帮助犯在主观上是有积极促成犯罪的故意。所以如果要将中立帮助的行为定为某犯罪行为的帮助犯,也需要帮助者主观上存在着帮助他人实施犯罪的故意。犯罪故意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结合而成,在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可以说认识因素是意志因素的基础,无认识因素则无所谓意志因素。在许多中立帮助行为中,帮助者只是实施了其生活中反复实施的日常行为或职业行为,其对犯罪结果的促成往往有偶然性,难以肯定行为主体存在有成立犯罪故意所需要的认识因素。如引起诸多讨论的“出租车司机容留他人吸毒案”,吸毒人员坐上出租车并在车内吸毒,出租车司机未作阻止[3]。首先,在本案中难以确认出租车司机对他人吸毒的行为是否有明确的认识,因为毒品属于国家严令禁止流通的物品,普通人难以接触也不太可能对其有所认识,即出租车司机的认识因素并不明确;其次,即使出租车司机明知他人在车内吸食毒品,但是出租车司机运载他人的行为是其正常的营业行为,只要乘客支付相应的对价,其就有义务为他人提供运输服务,其未放弃正常营业行为去阻止他人的违法行为,是否就可以肯定其具有促成犯罪发生的意志因素,这很难从案情中做出判断。如果将此类行为认定为帮助者具有主观的故意,则有可能使案件的审理陷入仅仅依靠当事人口供判断的不利境地。所以正如外国学者指出,中立帮助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只能认为其存在着一种“未必的故意”[4]。
进一步讨论,如果在中立帮助行为中,帮助行为人具有积极促成犯罪的故意,即同时具备了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则此时中立帮助行为就呈现出一种片面帮助犯的状态。片面的帮助犯以片面共犯理论为基础,片面共犯是从国外刑法理论中引入的一个概念,指两个人共同针对同一犯罪对象实施犯罪行为,但仅有一方存在共同犯罪故意,另一方无此犯意的情形[5]。众所周知,过去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一直不承认片面共犯理论。但近年来,即使是我国的通说理论,虽然仍不赞成片面的实行犯和片面的教唆犯理论,但也开始承认“单方面帮助他人犯罪,他人不知道的情况,在社会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并认为对于此种片面帮助犯的情形“比较起来,还是以从犯处理为宜”[6]。
对于片面帮助犯,帮助者在主观上明确知道他人将要实施犯罪行为,客观上实施了促成他人犯罪的加功行为,虽然其主观上与实行行为人并不存在通谋,但是其行为已经产生了值得刑法规制的社会危害性,对其进行处罚是合理的。但是笔者认为,在片面帮助行为中,由于帮助者并没有办法掌握或者左右整个犯罪流程,其对犯罪的实施只有辅助的作用,所以即使中立帮助行为处于片面帮助犯的情况下,如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将其行为正犯化,则其可罚性取决于正犯的犯罪实行行为,只有当正犯犯罪行为进入到实行行为阶段,对法益产生紧迫的威胁时,才能说帮助行为具有可罚性。
所以,中立帮助行为的行为人,其在主观上至多是对犯罪行为产生的一种放任态度,其是否在客观上促进犯罪结果的产生,取决于犯罪人是否利用了其提供的帮助,即中立帮助行为的性质其实在犯罪实行行为发生以前都处于一种待定的状态。如商店老板看见门外有人在争吵,其中一人怒气冲冲地进入店内要求购买刀具,商店老板即使具有促进伤害发生的故意,将刀具出售,其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还要取决于购买者是否使用该刀具侵害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权利。如购买者未使用该刀具,则该买卖行为只能被评判为一次普通的民事购买行为,无需也不存在刑法上的评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立帮助行为对犯罪结果的促进具有偶然性,对其概念的定义也应当反映出这种偶然性,所以有学者将中立帮助行为定义为:基于偶然原因与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联结并在客观上为他人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便利,但却是社会个体为保障社会存续发展以及公民正常交往所需而承担所负之社会职责的行为[2]110。笔者认为这种定义是合理的。
二、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理论评析
(一)全面可罚性说
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在理论上有全面可罚性说和限制可罚性说不同观点。
全面可罚性说认为,只要中立帮助的行为在客观上促进了犯罪结果的产生,就应该肯定此种帮助行为具有可罚性,并且没有必要将中立帮助行为与其他类型的帮助行为作区分[7]。如德国刑法理论中就有观点认为,如药店的药剂师如果了解他人购买安眠药将会实施犯罪,仍向他人出售安眠药,随后他人的确将该药品用于犯罪活动,出售药品的行为客观上促进了犯罪结果的产生,可以对药剂师以帮助犯论处[8]。全面可罚性说的提出,可能与提前刑法介入以全面保护法益等思想有关,但是其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文所述,如果仅仅从帮助行为与犯罪结果发生的因果关系上来看,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实施的几乎所有与外界发生联系的行为,都有可能对他人的犯罪行为有或大或小的促进作用。如餐厅老板为几个看似形迹可疑的人提供了食物,而这几个人后来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餐厅老板提供的食物则成为他们实施犯罪行为的体力保障;又如商家将化学原料出售给他人,售出的原料如果被他人用于制作毒品,那么出售行为客观上为他人制造毒品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助力。因此,如果采用全面可罚性说,那么刑法的处罚范围就有失控的危险,我们每个人都将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小心谨慎,以防止被他人利用,如此人们的行动自由也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全面处罚说并不可取,在目前的刑法理论中也鲜有赞同者。
(二)限制可罚性说
目前,认为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应采取限制处罚说是刑法理论的主流观点。但是,在以何种路径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问题上,学界存在着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的观点。
1.主观说
主观说注重从中立帮助者的主观方面来探究其行为的可罚性,即以促进犯罪结果发生的故意的有无来判断是否成立帮助犯。如过去德国刑法理论中有观点认为,如果在帮助行为中行为人具备了实现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观故意,则其行为就很难被称为一种日常的、职业的不可罚行为,应认定帮助者成立帮助犯。但是主观说的观点还认为,对于中立帮助行为中存在的直接故意和未必故意应当区别对待,出于未必故意实施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只有当帮助者出于直接故意对犯罪人提供帮助,其行为才成立帮助犯[9]。主观说是限制可罚性说中较早出现的理论,但是如果采取主观说的观点,就有可能导致帮助犯成立的判断脱离因果关系的危险。对犯罪行为的认定需要坚持主客观一致,无论帮助者持何种主观态度,其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还要看客观上的帮助行为是否对正犯的犯罪行为有促进作用,所以帮助者的主观方面,并不是划分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关键。故笔者认为主观说的观点过于片面,并不可取。
2.客观说
客观说则主要从行为的客观方面来划分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边界。由于判断角度的不同,客观说理论中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1)以社会相当性理论来判断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可以构成帮助犯。社会相当性理论最初由德国刑法学家韦尔策尔所倡导,社会相当性理论认为虽然某些行为在客观上本属于侵害法益或对法益造成危险的违法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只要符合历史形成的国民共同体的秩序而与社会生活相当,就可以否认该行为存在违法性[10]。受到社会相当性理论的影响,采取社会相当性为判断标准的客观说认为,就算中立帮助行为具有成立帮助犯的要素,只要其行为符合社会相当性,就应该否定其具有违法性[11]。
(2)以中立帮助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的原因力作为判断标准,认为中立的帮助行为并不一概构成正犯的帮助犯。是否构成正犯的帮助犯,应当将“有该帮助行为”与“没有该帮助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判断该帮助行为是不是对正犯结果的引起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不能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来分析[12]。
(3)职业相当性观点认为,只要是帮助者实施的行为属于其职业范围内的行为,就应该被排除于帮助犯的范围之外[13]。
客观说从客观角度对中立帮助犯的可罚范围进行判断,具有其可取之处。但是无论何种类型的客观说观点,都受到了其判断标准模糊的质疑。例如,根据职业相当性说的观点,很难说明为何普通人在知道他人要实施犯罪的情况下,开车将他人送至犯罪地点就构成帮助犯,而出租车司机在知道他人要实施犯罪的情况下将他人送至犯罪地点就不构成帮助犯。另外,社会相当性的判断标准为何?对犯罪结果的原因力如何判断?这些理论在具体标准上存在的模糊性导致在实践中难以对其进行把握。
3.折中说
折中说提倡结合行为的主客观两方面来对中立帮助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进行判断。
如有学者指出,“所有中立的帮助行为是否构成帮助犯的案例,都可以说其行为促进了结果的发生,因此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因果关系,而在于帮助行为与帮助故意的认定,由于这种行为的日常性、业务性,所以原则上只要该行为在其日常、业务的通常性范围之内,未达到一般人都能明白其必然会被用于犯罪的程度,行为人对于法益侵害的紧迫性也没有认识,就不应将其作为帮助犯处理。”[14]该论述可谓是从折中的观点出发,对帮助犯的成立做的消极的判断。而从积极判断的角度来看,有观点认为“日常生活行为是否可能成立帮助犯,要从客观上行为是否有明显的法益侵害性,即日常生活行为对于正犯行为的物理、心理因果性影响、行为本身给法益带来的危险是否达到了可以作为帮助看待的程度;从主观上看行为人是否对他人可能实行犯罪有明确的认识,即是否存在片面的帮助故意”[15]。
折中说的观点基本克服了主观说与客观说存在的缺陷,符合犯罪行为评价上主客观相一致的要求,在目前理论当中较为可取。
刑事责任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是指一个行为经刑法评价为犯罪后,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要承担的否定性评价和后果。故我国的刑事责任是以犯罪成立为前提,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在兼具成立犯罪所要求的所有主客观要件基础上,我们才能使行为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故判断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也需要从具体犯罪构成所要求的主客观要件入手。而依照我国通说理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判断应遵循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判断位阶。故在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进行判断时,首先进行客观性的判断,分析行为是否具有成立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其次,在客观判断的基础上还需要对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进行判断,从而确定行为是否齐备了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而明确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三、《刑法》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评析
自《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关于帮助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定之后,在刑法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除有学者质疑该规定在立法上将中立帮助行为正犯化而缺乏立法严谨性以外,另有学者也指出该规定是立法者在面对“一对多”这种新型帮助犯模式所造成的困境时,通过“司法造法”的方式扩张处罚范围以实现对帮助犯的处罚,这种方法固然解决了帮助犯处罚的形式合法性,但其扩张处罚范围的目的是不足取的[16]。下文将对该规定略作解析。
立法研究的一般进路,应当围绕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也可以以必要性为进路,但必须既说明可行性又说明必要性[17]。从立法必要性上看,面对网络犯罪带来的新情况,不难理解立法者对于严格网络服务者监管责任的用意:“一方面,网络犯罪通常具有跨地域特点,主犯往往分散在全国各地,甚至境外,抓获主犯十分困难。在主犯不能到案的情况下,对帮助犯追究就会陷入被动。另一方面,传统共犯一般是‘一对一’的关系,而网络共犯通常表现为‘一对多’的关系。由于帮助对象的数量庞大,网络犯罪利益链条中的帮助行为实际上往往成为获利最大的环节,按照共犯处理,也难以体现其独特危害性。鉴此,《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九条创设性地提出了网络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处理规则。”[18]
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规定,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时,其就应该终止对他人的帮助行为,否则会有构成犯罪的可能。面对网络犯罪泛滥的事实,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严格的监管责任的确是解决途径之一,其立法的必要性应该得到肯定。但是在设立新的犯罪时,需要对该立法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严密论证,如果仅仅是简单地将帮助行为正犯化,正如一些学者所言:“这个规定,比各种司法解释更进了一步,将本来还存在理论争议的中立帮助行为,一下子提升为正犯处罚了。”[19]忽视了网络犯罪区别于其他传统类型犯罪的特点,对复杂问题简单处理,只会使刑法理论不能得到自洽,该立法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例如网络支付平台的运营者,其平台客观上会被他人用于实施网络诈骗或开设网络赌场,而且由于这类犯罪活动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因此很难否认运营者对这些犯罪有主观的明知和一种放任的态度。如仅从形式解释入手,网络运营商则很有可能构成帮助网络犯罪活动罪。既然立法如此规定,那么网络运营者似乎就得肩负起对其网络平台监管责任,重视查找其平台上所有的违法犯罪活动,以规避构成犯罪的风险。但是网络平台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交易行为发生,如要求运营者严格的监管责任,必将严重增加运营者的负担,也使其在经营行为上畏首畏尾,最终的结果便是“刑法的规定”阻碍了网络科技的进步,使刑法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效用。如放弃对网络领域的刑法介入,则有可能使网络领域成为犯罪的“法外之地”,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合理界定网络帮助行为的入罪标准,除了要遵循犯罪评价主客观一致的要求,还要充分考虑网络领域的特殊性。根据日本刑法理论中网络帮助行为“全面性考察”原则的启示,有学者指出中立帮助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罪,其判断标准应为:“第一,中立帮助行为的提供者必须对于该中立帮助被现实利用实施具体犯罪存在认识、默认,且实际上发生了该具体的犯罪;第二,对照该中立帮助的性质、客观利用状况、提供的方法等要素,获取该中立帮助的人当中,存在非例外范围的人利用该中立帮助实施犯罪活动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而中立帮助行为人对此有认识和默认的前提下提供该中立帮助行为。符合这两个要素之后,中立帮助行为才存在成立帮助犯的可能性。”[20]在我国,由于帮助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已经出台,出于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持,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限制,只能依赖于对刑法条文的语义进行合理的解释,从主客观两方面限制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入罪。
从客观方面而言,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依赖于正犯的实行行为,因此是否有主犯实施的实行行为应是客观判断的第一步骤;其次,应从客观方面肯定帮助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发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以肯定帮助行为对犯罪有促进的作用。中立帮助行为的主观判断向来是中立帮助行为定性的一大难题,但是笔者认为有学者提出的“大半数规则”,应该是判断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否有主观故意的一种合理标准。例如,关于互联网金融平台是否对其平台上存在的犯罪成立帮助犯的问题,“大半数规则”的判断应该是:“司法机关应当查证互联网金融平台在提供合法服务与帮助犯罪活动之间的客观分配比例,分析、判断、计算其中有多少是为合法行为提供信息网络服务,有多少是为犯罪活动提供信息网络帮助。当其服务的众多对象中,大于半数的对象系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时,便可据此推定互联网金融平台对融资端的犯罪活动属于应知。”[21]
四、结语
网络时代带来的新的犯罪形式是刑法理论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出于保护法益的目的,刑法需要积极介入并规制网络中存在的犯罪现象,但是同时又需要保持刑法的谦抑原则,合理划分处罚的边界。在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问题上,首先,要否定中立帮助行为具有全面可罚性的思想,以保持刑法谦抑,为网络产业的发展留下应有的空间;其次,在对其可罚性边界的划定上,要充分认识到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相对于一般帮助行为的特殊性,坚持从主客观两方面全面考察的原则。
犯罪的本质是一种行为,因此在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界限的划定问题上,应以客观行为为判断起点。由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入罪路径只能通过将其认定为片面帮助犯来实现,故从客观方面上看,需要确定中立帮助行为对实行犯的犯罪具有助力,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才可进一步考量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以实现对结果的归责。
主观判断是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判断的重点。因为即使从客观上来看,实行行为人利用中立帮助行为实施了犯罪,但仅有客观上的事实并不能完成对中立帮助者的归责。中立帮助者主观上是否具有可归责的罪过,是确定可罚性的关键。中立帮助行为者是否成立片面帮助犯,其主观方面应限定为直接的故意。当网络运营者明知他人利用其提供的网络服务进行犯罪,并且继续为该犯罪行为提供所需要的网络技术支持,其主观上即存在明确促成犯罪的故意,认定其行为成立片面的帮助犯应无疑问。相反,认为在间接故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对网络运营者进行片面帮助犯的归责,则无疑是过分加重了运营商在网络监管方面的责任,也使其时刻面临着构成犯罪的风险。如此的结果只会使刑法的规定束缚了网络产业发展的空间,其合理性值得质疑。在无法确定网络运营商是否对其网络服务对象的犯罪行为存在明知的情况下,可以援引上文所述的“大半数规则”,通过对其主要服务对象性质的了解,来推定其是否对帮助他人的犯罪行为具有故意。当该网络运营商服务的对象,有大半数在利用其服务从事网络犯罪活动时,应确定该运营商有片面帮助这些犯罪行为的直接故意。运用该判断标准,不至于过分加重运营商的负担,也使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边界可以得到合理划分。
参考文献:
[1]刘艳红.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之批判[J].法商研究,2016,(3):22.
[2]曹波.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6):108.
[3]时延安,韩晓雪.出租车司机容留他人在车上吸毒应否追究刑事责任[J].人民检察,2008,(6):35-37.
[4]陈家林.外国刑法-理论基础与研究动向[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287.
[5]赵秉志.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41.
[6]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66.
[7]王鑫磊.帮助犯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4:128-129.
[8]孙万怀,郑梦凌:中立的帮助行为[J].法学,2016,(1):145.
[9]陈洪兵.中立的帮助行为论[J].中外法学,2008,(6):934.
[10]于改之.社会相当性理论的体系地位及其在我国的适用[J].比较法研究,2007,(5):23.
[11]张伟.中立帮助行为探微[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5):25.
[12]黎宏.论中立的诈骗帮助行为之定性[J].法律科学,2012,(6):151.
[13]张明楷.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424.
[14]林维.共犯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17.
[15]陈兴良.刑法总论精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523.
[16]阎二鹏.法教义学视角下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省思——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J].社会科学辑刊,2016,(4):79.
[17]曾粤兴.刑法学方法的一般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28.
[18]胡云腾.谈《刑法修正案(九)》的理论与实践创新[J].中国审判,2015,(20):23.
[19]车浩.刑事立法的法教义学反思-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J].法学,2015,(10):13.
[20]刘艳红.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流变及批判——以德日的理论和实务为比较基准[J].法学评论,2016,(5):48.
[21]刘宪权.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刑事风险及责任边界[J].环球法律评论,2016,(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