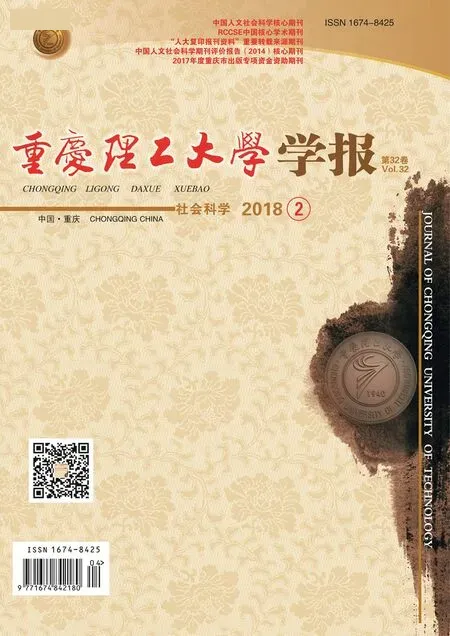试论罗素和弗雷格在真语句指称问题上的分歧
——从3个弹弓论证谈起
胡中俊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真语句*关于真值载体,罗素认为语句表达命题,命题才是真值载体,而弗雷格认为语句是真值载体。由于罗素和弗雷格对“语句”这个词的理解不一样,为方便讨论,在文中的“语句”这个词指的就是真值载体,在罗素那儿,可将其替换为命题来理解。的指称问题,是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罗素和弗雷格,他们的观点并不相同,前者认为真语句指称事实,而后者则认为所有的真语句都指称真。本文试图在分析丘奇、戴维森、哥德尔等关于真语句指称与弹弓论证关系的基础上,厘清罗素与弗雷格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一、丘奇的弹弓论证
真语句指称“真”是弗雷格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弗雷格说:“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一个句子的真值看作它的意谓。我把一个句子的真值理解为句子是真或句子是假的情况。”[1]103同时,他又说:“如果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意谓,那么一方面所有真句子就有相同的意谓,另一方面所有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意谓。”[1]104而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在《语义学导论》中则认为语句的指称是命题[2]。对于这二人的争议,丘奇(Church,A)遵循卡尔纳普关于“同义性”和“逻辑等值”的假定,使用类抽象的方法给出了一个形式化的论证,并表明“最终除了真值可以成为语句的指称外并没有别的可能性”[3]。除了形式化的论证,丘奇在《数理逻辑导论》中提出了一个更为大家所熟知的日常语言论证,该论证由4个语句构成:
S1.斯科特是《崴弗利》一书的作者。
S2.斯科特是那位总共写了29本《崴弗利》小说的男人。
S3.斯科特这个男人写的《崴弗利》小说的数量是29。
S4.犹他州县的数量是29。
丘奇认为,S1、S2、S3、S4将有共同的指称。他的推理有两个前提:(1)每个语句都有一个指称;(2)如果我们将一个语句中的项用另一个与其具有相同指称的项来替换,那么得到的新语句与原来的语句仍然具有相同的指称。由于“《崴弗利》一书的作者”和“那位总共写了29本《崴弗利》小说的男人”指称同一个对象——斯科特,并且S2是用“那位总共写了29本《崴弗利》小说的男人”去替换了S1中的“《崴弗利》一书的作者”而形成的,因此根据假定的原则,我们可以推出S1和S2具有相同的指称。由于 S4不过是将S3中“斯科特这个男人写的《崴弗利》小说的数量”的替换为“犹他州县的数量”, 而“斯科特这个男人写的《崴弗利》小说的数量”和“犹他州县的数量”指称同一个对象——29,二者替换后不会影响句子的指称,因而S3和S4具有相同的指称。“那位总共写了29本《崴弗利》小说的男人”和“这个男人写的《崴弗利》小说的数量是29”同样是对斯科特的指称,因而S2和S3也具有同样的指称。至此,我们知道 S1和S2有共同的指称,S3和S4有共同的指称,S2和S3也具有同样的指称,因此S1、S2、S3、S4都将有共同的指称。
根据卡尔纳普的看法,S1和S4都各自指称不同的命题,然而丘奇的论证却表明“斯科特是《崴弗利》一书的作者”和通过转换得到的“犹他州县的数量是29”会有共同的指称。这里出现了矛盾,因此卡尔纳普的观点是不能够成立的。如果语句指称真值,尽管S1转换到S4内涵发生了变化,但是其真值却是不变的,都指称“真”这个真值。若我们将S1、S2、S3、S4中的“是”改为“不是”,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得到S1、S2、S3、S4将共同指称“假”这个真值。显然,丘奇的这个论证支持了弗雷格的观点。
这个论证就好比一个弹弓一样,虽然小但是有着强大的威力,因此巴维斯(Barwise,J.)和佩里(J.Perry)将其称为弹弓论证(Slingshot Argument)[4]。注意,弹弓论证并不仅仅是这一个论证,因为在丘奇之后,一些哲学家如戴维森和奎因等人又以不同形式提出了这样的论证[5]。如果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家族”(family)概念来讲,这些弹弓论证构成了一个家族。弹弓论证有以下的特点:从一个语句开始,通过一步一步的转换得到新的语句,在每次转换的过程中,保持转换前的语句和转换后的语句具有相同的指称,这样第一个语句和最后一个语句也将具有相同的指称。
二、戴维森批评符合论的弹弓论证
真理符合论尽管符合人的直觉,但是却饱受争议。真理符合论至少有两个理论困境:第一,符合关系的标准无法确立;第二,事实概念模糊不清。可是戴维森并没有直接在这两点上对真理符合论进行批判。在戴维森看来,如果真理符合论是正确的,那么真语句符合个体化的事实。反过来说,如果真语句不能符合个体化的事实,那么真理符合论是不足为信的。我们知道,说一个真语句符合一个事实和说一个真语句指称一个事实,这二者并无实质差别。
戴维森对将命题的“真”定义为符合事实是不以为然的。他存在这样的怀疑:如果一个真命题符合一个事实,那么它将会符合很多事实,甚至所有的事实。根据戴维森的想法,语句“北京比南京更靠北”不仅符合事实——北京比南京更靠北,同时符合事实——南京比北京更靠南,还符合事实——北京比江苏的省会更靠北,还符合事实——北京比中山陵所在的城市更靠北,等等。
要验证这个怀疑,戴维森实际上只需证明两个任意真语句符合同一个事实。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在一个语句符合一个事实p的情况下,该语句还会符合事实q呢?戴维森认为不外乎两种可能:“或者p和q逻辑等值,或者p和q的差别仅仅在于p(q)中的一个单称词项被q(p)中另一个共外延的单称词项所替换。”[6]这实际上构成了戴维森弹弓论证的两个推理原则,在此基础上,戴维森认为以下的s 和t会符合同一个事实。
① s
② (ιx)(x=D)=(ιx)(x=D·s)
③ (ιx)(x=D)=(ιx)(x=D·t)
④ t
其中D代表第欧根尼,s指某个真语句,t指任意真语句,ιx表达限定摹状词, (ιx)(x=D)指唯一的x(x=第欧根尼)。假定①②③④分别符合事实f 1、f 2、 f 3、 f 4。由于s和(ιx)(x=D)=(ιx)(x=D·s)是逻辑等值的,根据上述第一个原则,②符合f 1。再来看 (ιx)(x=D)=(ιx)(x=D·s) 和(ιx)(x=D) =(ιx)(x=D·t),这二者的差别仅仅在于(ιx)(x=D·s) 和(ιx)(x=D·t),它们是限定摹状词,都指称第欧根尼(共外延)。再根据上述第二个原则,可以知道,③符合②所符合的事实即f 1。t 和(ιx)(x=D) =(ιx)(x=D·t)是逻辑等值的,因而④符合③所符合的事实即f 1。又由于①符合f 1,因而①和④也即s和t都符合f 1。
若s代表“苏格拉底是一个哲学家”,而t代表 “长城是中国的”。按照真理符合论,一个命题是真的,当且仅当存在一个事实与其对应,s和t将分别对应事实。然而,这两个语句对应的两个事实中具有不同的成分,一个事实中含有个体“苏格拉底”,另一个事实中有个体“长城”,因此这两个事实并不是同一个事实。可是戴维森却迫使我们承认,s和t只能对应着同一个事实。可以说,这个精心设计的弹弓论证对真理符合论是致命的。如果仍然要坚持真语句与事实对应的观点的话,戴维森认为所有的真语句只能对应着同一个“大事实”(The Great Fact)[6]。这个事实足够大,实际上它就是现实世界。对此,形式模态逻辑的创始者刘易斯(Lewis,C.I.)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所有的真命题将有同样的外延,也就是,这个现实世界。”[7]
三、哥德尔的弹弓论证
正如斯蒂芬·尼尔(Stephen Neale)指出的那样,哥德尔与弹弓论证的关系是长期被忽视的。确切地说,哥德尔并未正式地给出一个弹弓论证,而只是表明若提供一些假定,就可以构造出一个严格的证明。哥德尔(Godel)这样说:“一个人想要获得一个严格的证明,仅需要的更进一步的假定是:[G1 ] ‘Φ(a)’和命题‘a是那个具有性质Φ并且和a 同一的对象’表达着同样的事和[G2 ]每个命题‘说些什么’,这也就等于说每个命题都可以转换为Φ(a)这个形式。”[8]
尼尔对哥德尔的这两个假定进行了阐释,并添加了哥德尔在文本中表达过的一个更为基本的假定,将其概括如下:其一,F(a)和a= (ιx)*此处及后面的ιx的含义和戴维森的弹弓论证中(前面文中第二部分)的ιx一样,(ιx)(x=a·Fx)表示唯一的x,x是a并且Fx。(x=a·Fx)有共同的指称;其二,任何一个语句若指称事实,则都可以转换为与其等值的具有形式F(a)的语句;其三,一个复合表达式的指称仅仅由其组成成分的指称所决定。根据哥德尔的这3个前提,尼尔构造了如下的一个弹弓论证[9]:
(Ⅰ) Fa
(Ⅱ) a≠b
(Ⅲ) G b
由于(ιx)(x=a·Fx)、 (ιx)(x=a·x≠b)和a等同,(ιx)(x=b·Gx)、 (ιx)(x=b·x≠a)和b等同,我们进一步可以得到如下4个表达式:
(Ⅳ) a= (ιx)(x=a·Fx)
(Ⅴ) a= (ιx)(x=a·x≠b)
(Ⅵ) b= (ιx)(x=b·Gx)
(Ⅶ) b= (ιx)(x=b·x≠a)
因为或者a≠b或者a=b,只有这两种情况,我们可以先分析a≠b的情况。对a而言,根据第一个假定,我们可以知道(Ⅰ)和(Ⅳ)的指称相同,(Ⅲ)和(Ⅵ)的指称相同。对于(Ⅱ)a≠b而言,注意到a≠b实际上是a的一个性质,因此可以将(Ⅱ)转换为H(a),其中的H指a≠b这一性质。这样一来,根据第一假定,H(a)和a= (ιx)(x=a·x≠b)的指称是相同的,也就是(Ⅱ)和(Ⅴ)的指称相同。复合表达式 (Ⅳ) 和(Ⅴ)的差别仅仅在于限定摹状词(ιx)(x=a·Fx)和限定摹状词(ιx)(x=a·x≠b)的不同,然而 (ιx)(x=a·Fx)和(ιx)(x=a·x≠b)都指称a。根据第三个假定,我们可以推出 (Ⅳ) 和(Ⅴ)的指称是相同的。至此,(Ⅰ)和(Ⅳ)的指称相同而(Ⅳ)和 (Ⅴ)的指称又相同,因此(Ⅰ) 和 (Ⅴ)的指称相同。再根据上面得到的“ (Ⅱ) 和(Ⅴ)的指称相同”这个条件,可以推出(Ⅰ)和(Ⅱ)的指称是相同的,也即Fa和 a≠b的指称是相同的。
对b 而言,由于a≠b同样是b 的一个性质,因此我们同样可以将 a≠b改写为H(b),那么根据第一个假定,H(b)的指称和b= (ιx)(x=b·x≠a)的指称相同,也即(Ⅱ)和 (Ⅶ)的指称相同。由于限定摹状词(ιx)(x=b·Gx)和限定摹状词(ιx)(x=b·x≠a)都指称b,因此根据第三个假定,(Ⅵ)和(Ⅶ)的指称相同。至此,可以推出(Ⅱ) 和(Ⅵ)的指称相同。于是根据第一个假定,G b和b= (ιx)(x=b·Gx)的指称相同,也即(Ⅲ)和 (Ⅵ)的指称相同。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推出(Ⅱ)和 (Ⅲ)的指称相同,也即a≠b和G b的指称相同。又由上面的证明知道Fa和 a≠b的指称相同,因此这3个语句Fa 、a≠b 和G b的指称是相同的。再考虑a=b的情况,我们会发现论证过程和上述a≠b的情况是一样的,Fa、a=b和Gb的指称仍然相同。这表明,不管a=b还是a≠b, Fa和Gb的指称总会相同。由于Fa和Gb是任意的真语句,上述的论证实际上表明,所有的真语句都将有同一个指称。哥德尔的这个弹弓论证和戴维森构造的弹弓论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若真语句指称事实,那么所有的事实不过是同一个事实。关于“事实”,罗素曾这样说:“当我谈到一个事实时——我并不打算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作一种解释,以便让你了解我正在谈论的是什么——我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10]这里,罗素强调了事实和命题之间的关系:一个事实决定了一个命题的真假。罗素的这段话表明他持有的是个体化的事实理论——真语句指称个体事实,而不是“大事实”理论。
四、真语句的指称:罗素和弗雷格的分歧
一般认为,专名和限定摹状词都是单称词项,如果专名和限定摹状词指称的是同一个对象,那么是可以将二者替换的,比如“《阿Q正传》的作者”可以替换为“鲁迅”。又由于“《朝花夕拾》的作者”也可以替换为“鲁迅”,因而“《阿Q正传》的作者”可以替换为“《朝花夕拾》的作者”。上述的弹弓论证中,“《崴弗利》一书的作者”可以替换为“那位总共写了29本《崴弗利》小说的男人”,“(ιx)(x=D·s) ”可以替换为“(ιx)(x=D·t) ”,“(ιx)(x=a·Fx)”可以替换为“(ιx)(x=a·x≠b)”,以及“(ιx)(x=b·Gx)”可以替换为“ (ιx)(x=b·x≠a)”,都是以这一观点为基本前提的。
在尼尔看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可以使罗素真语句对应事实的观点免受弹弓论证的攻击。罗素在《数理哲学导论》中说:“包含一个摹状词的命题和以名字替换命题中的摹状词而得的命题不是相同的,即使名字所指的和摹状词所描述的是同一个对象,这两命题也不一样。”[11]在罗素那里,摹状词是不完全符号,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并不具有意义,它与专名是不同的。根据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我们以“《阿Q正传》的作者”为例,来简单说明为何限定摹状词不是专名。假定“《阿Q正传》的作者”是一个专名,那么它将代表一个对象O。因而,“鲁迅是《阿Q正传》的作者”就变成了S——“鲁迅是O”。由于O要么是鲁迅,要么不是鲁迅。如果O是鲁迅,那么S就是同义反复;如果O不是鲁迅,那么S就是假语句。我们知道,S既不是同义反复,又不是假语句;因而,这反过来证明,“《阿Q正传》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专名。如果我们接受罗素的摹状词理论,那么上述弹弓论证的替换都是无法进行的,从而都是失效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罗素关于真语句指称事实的思想是以他的摹状词理论为基础的。陈晓平认为语句的指称是事态[12],一个语句是真的则意味着该语句所指称的事态是存在的。由于事态存在是事实的另一种说法,因而可以认为,这一观点与罗素的主张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避免了上述3个弹弓论证是否就可以接受真语句指称事实(RF)这一观点?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真语句指称事实这一观点本身还将面临别的理论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戴维森提出的另一个弹弓论证。该论证有两个假定:“一个假定是,逻辑上等值的单称词项具有相同的指称;另外一个假定是,单称词项在它所包含的一个单称词项被另一个具有相同指称的单称词项所替换的情况下并不改变其指称。”[13]
D1 S
D2 (ιx)(x=x∧S)=(ιx)(x=x)
D3 (ιx)(x=x∧R)=(ιx)(x=x)
D4 R
注意,戴维森和弗雷格一样,将句子看作为复杂单称词项的特例,也就是说,该论证中的句子也被看作单称词项的一种。其中S和R的真值相同,(ιx)(x=x∧S)读作“那个和自身等同并且S的x”,(ιx)(x=x)读作“那个和自身等同的x”,因而D2是在说“那个和自身等同并且S的x”和“那个和自身等同的x”等同。同样,D3是在说“那个和自身等同并且R的x”和“那个和自身等同的x”等同。若S真,则(ιx)(x=x∧S)=(ιx)(x=x)为真;若S假,则(ιx)(x=x∧S)=(ιx)(x=x)为假。
这意味着D1和D2是逻辑等值的。根据戴维森的假定,D1和D2具有相同的指称。同理可得,D3和D4也具有相同的指称。接下来,如果我们可以证明D2和D3也有相同的指称,那么上述4个语句也都具有相同的指称。观察(ιx)(x=x∧R)和 (ιx)(x=x∧S)这两个表达式, R和S真值相同,只有两种可能:(1)R和S都为真,(2)R和S都为假。在第一种情况下,(ιx)(x=x∧R) 和 (ιx)(x=x∧S)都是大全集,它们指称相同;而在第二种情况下,(ιx)(x=x∧R)和 (ιx)(x=x∧S)都是空集,它们指称仍然相同。因而,不管在哪种情况下,(ιx)(x=x∧R)和 (ιx)(x=x∧S)的指称总是相同。再观察D2:(ιx)(x=x∧S)=(ιx)(x=x)和D3:(ιx)(x=x∧S)=(ιx)(x=x), D3不过是用(ιx)(x=x∧R)替换了D2中的(ιx)(x=x∧S)。上一步已经得出(ιx)(x=x∧R) 和(ιx)(x=x∧S)的指称相同。再根据替换原则,我们可以推出D2和D3的指称也是相同的。至此,可以看出D1、D2、D3、D4具有同一个指称。如果我们假定S和R都是真语句,那么S和R具有相同的指称,又由于S和R是任意的,这表明所有的真语句都只有一个指称。
戴维斯设计这个弹弓论证的初衷是借助这个论证彻底反驳那些认为语句的意义是其指称的观点。这是因为,如果语句的意义在于它的指称,那么这个弹弓论证表明了任意真语句的意义是相同的,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注意,戴维森的这个弹弓论证并不依赖限定摹状词可以替换为专名这一前提。(ιx)(x=x∧R)和 (ιx)(x=x∧S)共指称,是因为在R和S真值相同的情况下,这二者要么都是全集要么都是空集。只要我们认可戴维森的那两个假定,我们就无法不承认所有的真语句都有共同的指称。真语句唯一的共同点就在于它们的真值都为真。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反驳这个论证,那么我们就应该接受弗雷格真语句指称真(RT)的观点。
第二个困难,否定性真语句的指称问题。一般来说,事实是指个体具有某属性或者个体间存在某关系。语句“长城不在美国”是真的,如果该语句指称事实,那么它将指称否定性事实。然而,否定性事实是否存在,争议是很大的。第三个困难,复合事实的引入。根据RF,“长城在中国或者长城在美国”指称一个析取事实;“长城在中国并且长江在中国”指称一个合取事实。然而,这些人为设定的事实分类既不合乎我们的直觉,也不满足本体论的经济原则。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将RF的适用范围限制为原子语句,换言之,复合语句并不指称事实,就可以避免这个困难。真的析取语句表明至少有一个析取的原子语句指称事实;真的合取语句表明合取的各原子语句都指称事实。但是,如果我们考虑“所有的人都会死”这样的真语句指称什么的时候,便会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个语句的逻辑形式是∀x(Hx→Dx)。反观RT,不管是简单语句还是复合语句,或者是特殊形式的语句,只要是真的,它们都指称真。相比于RF,RT的理论优势是明显的。
我们知道,弗雷格关于真语句指称真的思想和他的专名理论是密不可分的。与罗素不同,弗雷格并没有区分限定摹状词和专名,他将“《阿Q正传》的作者”这样的表达式也看作为专名。但是在弗雷格看来,“《阿Q正传》的作者”和“鲁迅”的涵义却是不同的。弗雷格认为,对一个真语句而言,其中的限定摹状词被共指称的专名替换后,尽管语句仍然指称真,但替换后语句的涵义是发生了变化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弹弓论证对弗雷格真语句指称真的观点构成了有力的支持。此外,弗雷格的这一思想使得他不会遇到让罗素头疼的否定性事实[14]问题,更不会面临复合事实的争议。
[1] 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证选辑[M].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CARNAP R.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2.
[3] CHURCH A.Carnap’s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J].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43(52):300.
[4] BARWISE J, PERRY J.Semantic innocence and uncompromising situations[J].Midwest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81(6):387-403.
[5] QUINE W V.Three grades of modal involvement[G]//Ways of paradox.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6] DAVIDSON D.True to the facts[J].Journal of Philosophy,1969(66):752-753,753.
[7] LEWIS C I.The modes of meaning[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43(4):242.
[8] GODEL K.Russell’s mathematical logic[C]//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44:129.
[9] NEALE S.The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godel’s slingshot[J].Mind,1995,104(416):777-778.
[10] 罗素.逻辑与知识[M].宛莉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19.
[11] 罗素.数理哲学导论[M].晏成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4.
[12] 陈晓平.论语句的涵义与指称——对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的一些修正[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4):14-20.
[13] DAVIDSON D.Truth and meaning[J].Synthese,1967,17(1):305-306.
[14] 胡中俊.罗素的否定性事实思想及其转变[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5):3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