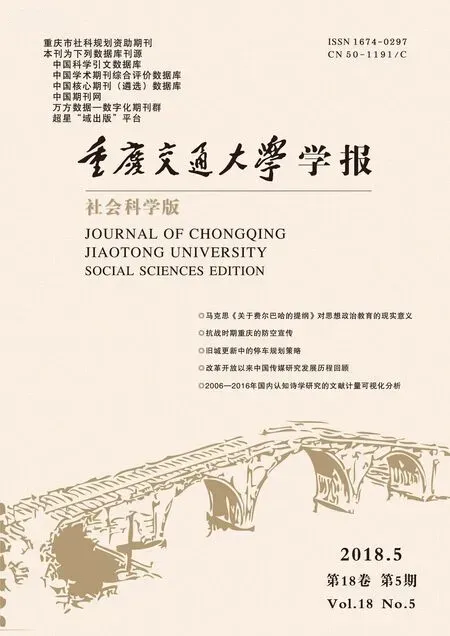挥之不去的梦魇:保罗·奥斯特《黑暗中的人》的创伤叙事
魏 婷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清 350300)
在人类文学史上,书写战争的作品不胜枚举,可以说战争书写一直以文学形式超越真实,反思战争与人性,探究战争的残酷本质。“9·11”事件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个深重的灾难,带来的是恐慌和迷茫、传统价值观的质疑和幻灭。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美国之后的外交政策,而且对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影响也愈发凸显。在文学领域,作家们适时作出回应,“催生了一种具有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文学文本,或称之为后‘9·11’文学”[1]。美国后“9·11”文学将这次恐怖袭击事件放到广阔深远的历史与伦理空间中进行审视和想象,或对全球化时代暴力、仇恨和恐怖的隐秘与逻辑进行批判,展示了遭受恐怖袭击后美国普通民众的恐惧记忆、心灵创伤和救赎轨迹。保罗·奥斯特的《黑暗中的人》就是这类作品的一个代表。
保罗·奥斯特是保持旺盛写作活力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同时拥有诗人、剧作家、电影导演等多重职业身份。奥斯特擅长在现实叙事中搭建出时空错落的文本迷宫,作品以充满悬念和思辨而著称,在各项国际文学奖项上屡有斩获。自其成名作《纽约三部曲》开始,这些带有卡夫卡和加缪式荒诞色彩的存在主义寓言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和评论家的注意。他的作品艺术手法多样,既运用蒙太奇、零散化和时空交错等后现代叙事技巧,也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针砭时弊。他本人曾在采访中声称自己是十足的现实主义者,是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反思并向现实主义回归的新现实主义。唐·德里罗(Don Dellilo)认为奥斯特的作品“具有高超的智慧和原创性……把现代社会面貌与十九世纪的内涵相结合”[2]。奥斯特关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社会现实状况,并对后工业时代的美国社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予以观照。他的作品刻画了一个个平凡的角色凭借自身的力量来因应历史的流变;这些角色历经了情感、道德或意识形态的考验,体现人与社会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
美国本土在“9·11”被恐怖分子袭击之后,奥斯特的作品自然转向描写反映“9·11”后人们的心灵创伤和精神痛苦的问题,以写作来疗伤,以作品来宣泄、消解战争带来的阴影与创伤。2008年发表的小说《黑暗中的人》出版之后倍受好评。在这部小说中,奥斯特以多层次、多视角、非线性、碎片化为叙事特征,将事件、记忆、狂想并行,来呈现“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给美国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对于《黑暗中的人》的叙事技巧及反战思想的研究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Paolo Simonetti认为对奥斯特小说的分析“将强调从后现代主义的感性转向新历史主义,比如《布鲁克林荒唐事》(2005),《密室中的旅行》(2006),以及《黑暗中的人》(2008)”[3]。Aliki Varvogli认为《黑暗中的人》和《密室中的旅行》之间具有特殊关联的原因在于,这两本书都蕴含政治寓言和元小说结构,表明奥斯特通过描述“9·11”事件后的政治气候,可能找到了一种方法来调和他对形而上学和存在主义问题的兴趣[4]。近年来,国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多集中在后现代叙事特点方面,而对于作品中呈现的幻想与现实边界模糊的特质、创伤源头以及创伤症候等重要问题则缺乏深入研究。因此,笔者在创伤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来解读《黑暗中的人》的主题内涵及其对历史的反思。
一、失语与逃避:难以弥合的伤痛
20世纪80年代,美国精神病研究学会将越战老兵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确定为一种可独立诊断的疾病——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此后研究者们开始对各种创伤经历及创伤后症状进行专门研究。著名的创伤理论家卡鲁斯认为创伤是“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 当中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性的方式定时地、无法控制地反复性出现”,并将它理解为一种严重的历史危机和“不能掌控的历史症状”[5]。可见,心理创伤是一种无形的伤痛,会对受害人的精神和心理系统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并以不同的形式如梦境、闪回、癔症等,反复出现侵扰创伤受害者。奥斯特没有用大篇幅的战场描述来呈现战争的残酷,而是将关于战争的反思体现在民众遭受创伤后的症状上。这种创伤不仅是战争对生命造成的创伤,更是严峻的现实生活对个体所造成的创伤。灾难带给人们的是心灵的黑夜,正如书名所暗示,《黑暗中的人》的主人公们都是身处在黑暗中的人。72岁的书评家奥古斯特·布里尔遭遇丧妻之痛,又遇车祸致残,在女儿家休养,内心世界感到孤寂与压抑,夜夜无法入眠。他将自己沉浸在文学创作中,以此来麻痹自己,逃避伤痛记忆。在他编织的文本世界里,200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造成国家分裂,促发了新的内战,“9·11”事件没有发生。女儿米丽亚姆因为离婚之事深感挫败,靠写霍桑女儿的传记疗伤。奥古斯特的外孙女卡佳无法摆脱男友泰特斯死亡的阴影,从纽约电影学院退学后,无法言说的创伤迫使她每夜在黑暗中看经典电影来寻求慰藉。
奥古斯特和卡佳通过看电影来打发漫漫长夜,刻意遗忘创伤细节,以期减轻或者忽略痛苦体验。在观影中,他们探讨电影运用“静物”表现人类情绪的方式。奥斯特嵌入了四部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大幻想》《阿普的世界》和《东京物语》,它们的共性在于描绘了二战后整个社会都处于灾难边缘的图景。随着时间流逝和空间转换,在回忆和忘却的记忆危机中,二战所造成的“历史性创伤”并未随着历史的远去而远去,必然凭借代际传递的方式逐渐提升为集体记忆,形成个人、民族和文化的记忆框架,继续在现实中发挥着它的影响。
二、直面创伤:虚伪的表象真实
奥斯特不仅将电影文本自然融入其互文写作,达到主题上的完美契合,还将“故事嵌套故事”的叙事结构与小说的创伤主题形成结构上的巧妙呼应。小说中历史、现实和想象错综复杂,杂糅在一起,虚实难辨。奥古斯特虚构故事的主人公欧文·布里克(Owen Brick) 是位魔术师,可是一觉醒来,布里克惊奇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不知名的处所,四周不断传来密集的枪炮声和喊杀声。一个自称瑟奇的中士派遣布里克前去刺杀奥古斯特,只有这样才能终止战争,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奥古斯特的大脑。然而布里克对自己的处境困惑不已,认为自己从未签字入伍。而瑟奇中士回应道:“没人签过字。……前一分钟你还在过你的生活,下一分钟你就在打战了。”[6]8布里克莫名地被卷入战争,又要被迫完成一个任务。从故事表层来说,通过虚构战争中的“误入者”映现作者的反战情绪,同时从另一侧面影射了普通美国人在战争中的被动处境。即使他们有幸能从灾难中脱身,却已经支离破碎,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模样。奥斯特的故事灵感源自他对“2000年美国大选的失望和厌恶”。在一次采访中,奥斯特表示:“戈尔赢了,他应该当选,可政治和法律耍花样剥夺了他的总统资格。从那时起,我有种怪诞的感觉,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另一个平行的世界存在。在平行的世界里,戈尔连任两届总统,美国从未入侵伊拉克,可能连‘9·11’也从未发生过。因为克林顿他们快制定出了对策,只有继任的布什那帮家伙无视所有警告,而这才是‘9·11’发生的根源。”[7]奥斯特积极对现实作出回应,通过真实与虚构的并置,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将“9·11”事件归咎于布什政府,尤其谴责了伊拉克战争。他尝试用照相机式的记忆方式,不断寻求对这段历史“真相”的接近。
《黑暗中的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由单一主人公主导的故事世界,如果把奥古斯特的故事和布里克的故事视为两个可能世界,那么他们各自存在的可能世界并行存在, 具有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虽然“欧文·布里克”存在于奥古斯特虚构的文本世界,但它看起来同奥古斯特居住的佛蒙特州布拉特博洛镇一样真实,同时奥古斯特和布里克又是处在更高层级的真实作者奥斯特虚构出的文学形象,这突破了传统小说中壁垒森严的时空界限,使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不再清晰。奥斯特借助故事人物弗里斯克之口,阐述了他对多个平行时空并行的看法:“没有单一的世界。有许多个世界,而且它们互相平行运行,世界和反世界,世界和影子世界,每个世界都被另一个世界中的人梦到,想象到,或者写到过。每个世界都是一个思想的产物。”[6]71平行世界是浩瀚的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无数多个平行宇宙。奥斯特以“虚伪”的形式打造了一个反表象的平行世界,在曲折离奇的叙述中以感觉和幻想拆解了现实存在,对历史的可能性进行了多层次的审视。布里克被无辜地卷入一场战争,并被指派去刺杀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人。无奈事与愿违,布里克逃脱多次未果,最终被炸死在空袭中。布里克的故事反映了普通美国人面对伊拉克战争的无力感,隐含着巨大的荒谬和非理性。布里克被炸死的场景也具有象征意义,“远处有飞机低空飞过,然后是直升机引擎的轰鸣声……厨房的窗被炸得粉碎,地板在他脚下震动,接着开始倾斜,好像整幢房子的地基在移位……”[6]121这一情景可谓真实地再现“9·11”袭击的恐怖场景。烈火、警笛、烟尘、坠落的人体重现了一幅鲜活的地狱图景,将不同时空串联起来,使读者直击恐怖袭击事件,就像电影镜头让人们的目光永远定格于飞机撞击纽约世贸大楼那个画面,再次亲历人类的悲哀。布里克不是历史的殉道者,只是被卷入历史洪流的卑微个体,他不仅见证了历史的浩劫,也承受了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在某种意义上,布里克是美国社会普通民众的缩影。奥斯特将历史存在的真实和虚伪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从普通民众视角着手,书写了硝烟炮火中他们的苦难命运和生存实态,以暴力叙述为历史“证言”。
三、个人视域:挥之不去的伤痛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灾难的亲历者们往往对创伤性的体验记忆深刻,选择遗忘是遮蔽痛苦最好的方式,然而受创者们仍然深受“复现创伤”的折磨,相比较而言,正视伤痛更能得到心灵的救赎。奥古斯特渐渐向外孙女卡佳敞开心扉,讲述自己荒唐的婚外恋,也触及泰特斯遇害的真相。“在对抗个体损害和精神绝望方面,叙事对于维系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生态平衡具有本体价值及生理兼心理调节意义的治疗作用。……让读者在文本阅读中和作家、文本,以及支持文本生产的话语权力之间达成相同的对‘创伤’的认知,通过展示、控诉、批判的一系列仪式化程式,完成对人们内心普遍恐惧、压抑的泄导来使人们精神和心灵的伤痕淤积得到释放和治疗。”[8]
主人公奥古斯特的讲述梳理出不同时期的“我”,将历史时间的流逝,对其间发生的人和事的感知、理解和所要传达出来的意义,转换成对历史事件的空间组合形态而呈现,外在历史事件多方位地渗透进“我”的生命历程。“我”的姐夫吉尔是纽瓦克市政府的企业律师,两人碰巧一起见证了美国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种族骚乱。自那时起,以底特律、纽瓦克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工业化城市开启了由盛及衰的坎坷岁月。如同姐夫吉尔,自这次灾难之后,他的事业和健康日益恶化,最终英年早逝,即便死后也不得入土为安。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场骚乱仍是一些美国人不愿直面的伤疤,种族主义仍是美国社会的顽疾。“我”的叙事聚焦于宏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特定的历史境遇造就了这些人物特殊的充满灾难的命运。奥斯特把叙事文本植入历史脉络中,使读者在现实与叙事之间思索,旨在重新理性并审慎地思考创伤产生的缘由,而非仅仅呻吟或愤怒。
杰弗里(Jeffrey Alexander)在其著作中论述:“来自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共同遭遇某些可怕的事件并因此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烙印在其族群意识之中成为永远的回忆,若是遭受创伤的群体将其遭遇的事件重新整理并加以诠释、述说、传播,形成一个集体的记忆、集体的苦难,就是文化创伤。”[9]。奥古斯特回忆性叙述的主题是战争,这些故事包括纳粹集中营骇人听闻的分尸事件,纳粹对犹太人的驱逐迫害,冷战的牺牲品双重间谍杜克洛的坠楼事件,话题足够沉重,充满令人作呕的暴行。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泰特斯遭恐怖分子绑架并残忍杀害事件。奥斯特将泰特斯行刑的血腥残酷的场面刻画得淋漓尽致,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不得不睁着眼面对这份恐惧和伤痛。奥斯特凭借为历史作证的勇气,直面并再现伊拉克战争真实的面相,它为美国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精神健康”问题,更多的是良知的谴责和追悔的梦魇。
奥斯特回溯历史,将看似混乱的不同历史碎片拼贴在一起,再加以汇集,构成了一个创伤链条,书写“创伤的重复”。小说的叙事都是出自主人公奥古斯特第一人称回忆性叙述,从叙事理论角度来看,第一人称叙述带有某种过来人对以前经历反思评论的味道,其中潜存两种视角:一是叙述者“我”当下叙述的视角,二是被追忆的“我”的过去的视角。叙述视角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转化交叉,其间的经历,加上诸多样的人生况味,会对同样的事件形成不同的感知方式、叙述的形态。奥古斯特的“伤痕”有时代的共同记忆,也有他个人的烙印,他的创伤经验源于丧妻之痛。奥古斯特与索妮亚的婚姻以背叛告终。他的第二段婚姻也没有善始善终,第二任妻子乌娜为了一个画家离他而去。虽然他后来和索妮亚复合,然而索妮亚之死和车祸在其心底重重地刻下了创伤性印痕。奥古斯特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讲故事,而创伤记忆如梦魇般挥之不去,索尼娅犹如一位“缺席的在者”,始终存在于奥古斯特的记忆中。弗洛伊德《超越唯乐原则》中提出了“强迫重复”原则,自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要求重复以前的状态,要求重新体验某段早已忘却的生活。“我”的回忆性叙述并不只是怀旧,而是企图获得宽恕和谅解,也是一种疗伤和自我拯救的过程。但是索尼娅的死不仅使他赎罪的愿望无法实现,自身创伤的修复也永远无法完成。就像文中重复了七次罗丝·霍桑的一句诗“当这怪诞的世界继续向前”[6]187,历史虽无法改变,但必然过去;即使创伤无法祛除和修复,我们也须裹挟伤痛和记忆,勇敢面向未来。
当下,全球范围的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暴力活动呈升级趋势。反思潮正在美国社会和民众中间蔓延,其中美国知识分子阶层对美国社会文化自身的批判尤为尖锐。《黑暗中的人》运用纪实的手段,以一个战争局外人的视角叙述了一幕幕暴力血腥的场景,通过细节描写带给读者最直观、最强烈的画面冲击感,将人类本性中的暴力本能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并通过文字营造一种极度的恐惧、压抑和窒息感。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相比,这部后现代派小说看似零碎残缺,但这样的叙事模式使战争以其特有的方式被记忆、阐释、反思,同时也作为一段历史被记录;在见证历史的同时提供了情感宣泄的通道,旨在引起疗救的效用;在对过去的缅怀中,抚慰备受创伤的心灵,累积起担当苦难和行动的勇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及个人的创伤性叙事并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充满着伤感甚至梦魇般的气息,直接和间接卷入战争都会给人带来无法消弭的心理阴影,心灵上的伤痛将永远无法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