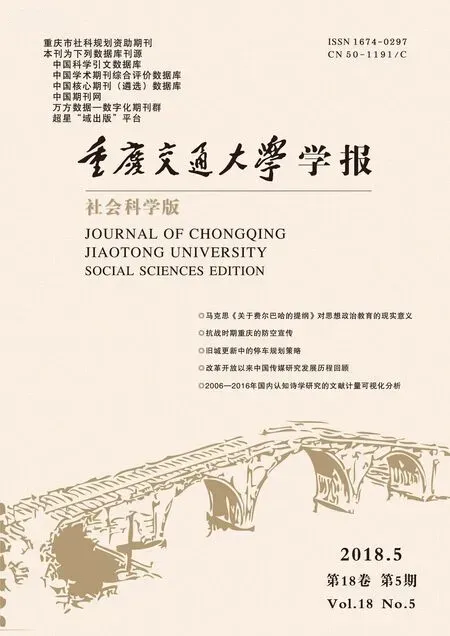古铁雷斯《解放神学》对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回应
奚 望, 张 航
(1.四川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31;2.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西方语言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的胜利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为拉美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受此鼓舞,拉美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之一——天主教会发出了社会变革的呼声。60年代,拉美天主教召开了多次会议,在对贫穷、正义、社会压迫、教会责任等现实议题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被称为“解放神学”的思想。秘鲁天主教神父古斯塔夫·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1928—)1971年出版的著作《解放神学》被普遍认为是解放神学的总纲领。古铁雷斯认为教会应该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摧毁不合理的制度而建立新社会,将天国带到人间;即使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有消灭宗教的倾向,但马克思(包括恩格斯)本人并没有直接消灭宗教的意思,而是要通过宗教批判来改造现实和历史;如果将宗教当作现世和历史批判的武器,宗教完全可以达到解放的目的。他抓住马克思社会和历史批判的实质,站在天主教信仰的立场,主张在圣言的引领下通过阶级斗争消灭异化的罪,使人能脱离异己力量而得以在完全开放的历史中实现自由创造,达到人类互爱一体的终极解放,使天主教的“拯救”与马克思的“解放”二者完全统一。为此,古铁雷斯首先对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作出回应,试图把马克思的宗教批判转变为拉美社会和历史批判的起点与动力。
一、现实层面的回应:用阶级斗争消灭罪
马克思认为宗教产生于人因无法自我觉醒而依赖于宗教主体,是现实世界中人的自我异化反过来导致的自我崇拜,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因此,他把宗教看作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1]。如同劳动异化那样,工人创造产品时,产品成了主体,而劳动本身则变成产品的附属物,使工人失去现实性。“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宗教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2]可见,马克思认为产生异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私有制,而私有制又起源于原始的资本积累。马克思认为:“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3]这个对罪的解释把偷吃禁果看作是亚当在并不缺乏物质资料的情况下,背着上帝把禁果当作私人之物而偷吃。
古铁雷斯觉察到的则是这个故事中的罪性:亚当因为私欲背叛了上帝。因此人离开了上帝,私欲也就产生了异化。古铁雷斯更多认为罪产生于制度化的私欲,即社会的罪。“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让人类治理大地。人只在转化自然和与他人的联系中实现自身,通过劳动成为自由创造的、拥有完整自我意识的人。贫困中的压迫和剥削使劳动成为屈从和非人化的。异化劳动代替了自由人,奴役着他。”[4]295如果人只在原始状态中改造自然,所有人都处于对自然当家做主的地位,也就无所谓异化。问题在于产生了剥削和压迫,一部分人夺走了另一部分人对自然的主宰,将其奴役。这就是人违反了上帝的旨意,古铁雷斯将其视为罪。“罪是压迫结构的证据……作为根本的异化,罪是不公正和剥削的开始。”[4]237可以看出,古铁雷斯更多把罪界定在社会的不平等、制度的不公正导致的异化上,正因为私欲导致社会不公正的制度把上帝与人隔离。因此,异化就是一种有罪的状态。站在神义论的角度,上帝给予人的都是善好的,罪并不源于上帝。穷人物质匮乏却拥有富裕的心灵,而富人物质充裕却只有贫乏的心灵。罪阻碍了人和上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罪也是一切属灵和物质贫穷的原因。
人的贫穷使人丧失自我意识而依附于产品,国家的贫穷使国家丧失自我意识而依附于发达国家。这种依附使国家社会丧失稳定,政治缺乏自主,经济缺乏独立性。这种依附造成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和异化,庞大的国际资本市场又咀嚼了这些贫穷国家,使其成为能控制资本市场的发达国家的附庸,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半殖民地”,“外部统治体系, 从依附框架切入而渗透到一个又一个国家。在这种程度上,外部结构的效果等同于内部结构”[4]120,实际上是穷国国民跟自己的国家一起受到发达国家的奴役。基于神义论,上帝赋予人一切善好,但罪导致贫富不均,贫穷就是一种罪带来的耻辱,是“侵害人类尊严的可耻情形,因此与上帝的意志相抵触”[4]369。拉美不可否认的残酷现实是:“六百万万社会金字塔顶层人口与1.5亿底层人口分享相同的收入。每天收入只有25美分的农民有六千万人。”[5]在天主教徒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拉美,这一现实带来的问题是:如何告诉穷人,上帝爱他们。
古铁雷斯认为,要消灭罪,就要将上述颠倒的关系重新恢复;解决罪的问题就是要获得现实解放,而这种解放要建立在通过斗争消灭罪的根基之上;只有消灭了不合理制度下的异化,人才能重获尊严,人的创造工作才能成为真正进行改造的劳动。鉴于此,他认为马克思是将单纯的宗教批判(也就是对与世俗分离的彼岸世界的批判)进一步发展为以此世歪曲的现实为基础,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本身进行批判。古铁雷斯将天主教信仰本身作为实现消灭异化的途径,主张教会必须“主动而有意识地参与阶级斗争”[4]356,在当下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如果教会拒绝进行阶级斗争,它就会堕落为马克思所谓的鸦片——麻痹人民的统治工具。因此,宗教不能再是无声的叹息,也不能再剥夺人的现实性;宗教应成为“人民的警号,起到把被压迫者从沉睡、被动和宿命论中唤醒,从而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力量和前途的作用”[6]85。古铁雷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可马克思所指的宗教异化。他认为拉美教会从拉美政治中获得了支持,教会就成为拉美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就成了维系拉美社会秩序的工具[6]83。同时,国家需要从发达国家的半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通过斗争打碎富国的统治后,穷国自身的发展才会到来”。但古铁雷斯在此将贫穷的原因仅归于剥削制度,似乎有点狭隘。
阶级斗争是一种敌对关系,天主教的博爱精神如何能在敌对关系中得到显现。古铁雷斯认为阶级斗争要努力使剥削者懂得什么是爱,最终目的是用爱消灭罪,而不是消灭剥削者本身,也并不将阶级斗争当作目的。这种认识包含的解放对象更广泛,不仅解放穷人,还要解放富人,富人也是被罪蒙蔽的人。“活在罪恶的客观状态中的人,我们因为爱的要求而努力对他们进行解放。穷人和富人的解放,是同时进行的。”[4]357这种表述是《解放神学》不同于《资本论》之处,它合乎耶稣“爱一切人”的高度。与罪作斗争,而不是与罪人作斗争。古铁雷斯的阶级斗争主张博爱,这是《解放神学》最具宗教人性的一面。但是古铁雷斯在这个问题上也赋予暴力革命以道德大棒,导致斗争泛滥。罗纳德 ·H.纳斯比认为:“古铁雷斯使几乎所有的斗争都跟风,称自己是为基督的工作提供道德保证而进行的解放斗争。”[7]当时拉美各种游击队、暴动、反政府武装泛滥,似乎印证了这个观点。
但问题是消灭异化是否跟消灭罪等同。对于天主教传统来说,罪更多是指个人之罪,即使是社会之罪,也是源于个人堕落。拉辛格认为:“罪是最大的恶,因为它从内心中驾驭了人的本性。解放的第一要素,作为其他解放的参照,就是从罪中解放。”[8]把消灭罪看作消灭社会异化的观念与传统教会有很大不同。古铁雷斯把罪更多归结于制度而非人性,罪与私欲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而消失。但即使能把罪解释为异化,在消灭罪时仍限于制度的罪,而不涉及个人的道德。考察个体人性难免触及人本身的个体私欲,这不是通过消灭制度能解决的,古铁雷斯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另外,如果将救恩赐予通过革命而得解放的穷人,拯救似乎会超出教会而与是否信教联系不大,这也与传统天主教的救恩理论不一致:一般认为教会有赦罪的权柄,“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9]20,非信教者难以获得这种神恩。不过,《解放神学》不分天主教徒与异教徒或不信教者,只以被压迫者和压迫者来区分,这种解放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二、历史层面的回应:以耶稣为终向的拯救史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抽象共同体看作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法逃脱的形而上学的牢笼,它将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共同体成为最高统治集团,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种社会单元都必须成为共同体的奴隶,原有体系将被摧毁。“那些成为共同体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10]人完全依赖于货币共同体,无法取得人本身的独立、自由,也丧失了创造性和历史性。同样,传统宗教的神的超验安慰、彼岸式的光芒都是一种静态的形而上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的,只会将眼光放到永恒的来世,而把现世看作偶然、转瞬即逝的,也缺乏存在的意义。静态的形而上学没有历史,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历史的创造力必须从形而上学的牢笼中挣脱,并且重新获得创造和发展的力量。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这就要求人打破形而上学的桎梏,消除异化,在历史规律中寻求创造和发展,以自由人的身份实现“将世界和关系还给自己”。通过第一阶段的现实解放后,不合理的制度和异化状态得以消除,人从形而上学中解脱,有了动态创造的机遇。
对于真实的苦难,古铁雷斯不能无动于衷。他的信仰并不仅仅是每日按时诵大日课或玫瑰经,还要为拉美找到通往“真正祈祷”[4]272的路径。从福音角度反思人们的信仰,人们要“在拉美受剥削与压迫的土地上将自己交付给解放的进程,……思考这改变本质的展望,和关注这种交付的新问题的基督徒生命的伟大主题”[4]17。他认为神学是为人类共同体实现解放的批判和反思,而这种批判和反思是“圣言在信仰、历史和实践中的实现”[4]34。把神学界定为圣言训导下信仰与历史实践的批判性反思,这似乎是在神学中加入了一种历史性因素,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社会的历史性解释”[4]130。
要建立历史的人必须着眼于人的现实性,人是开放的、未完的历史创造者。古铁雷斯认为上帝并非仅仅是超越理性的存在,而是活在人类现实中。因此,彼岸思辨的神学必须转换为现世实践的神学。历史的解放意味着“人被视为拥有能对自己命运负责的意识”[4]68,这是人类对成为自己命运的工匠的渴望[11]56。上帝通过历史启示人类,人类对上帝的回应也在历史中。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拯救史,当劳动的人类没有得到与上帝的真正合一,罪仍然随时可能割裂人神的联系。因此,历史的最后导向是“基督终向的拯救”[4]200,包括创造与拯救、末世承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将解放理解为创造和拯救。依撒意亚的歌咏中,上帝创造和拯救的面孔同时出现:“因为你的夫君是你的造主,他的名字是‘万军的上主’;你的救主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将称为‘全世界的天主’。”[12]。古铁雷斯认为拯救并非仅仅等待来世的审判,同时也在现世的历史中,创造和拯救构成历史的跨越幅度,通过创造和拯救,上帝在历史中显明了自身。更为重要的是人还有自我创造的过程,人的特性是劳动创造,通过劳动对社会的改造即在拯救进程中。“劳动,改造这世界,因而成为人,建立人类社会,这同时也是拯救。同样,与贫困和剥削斗争而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也是朝向完满拯救的一部分。”[4]10古铁雷斯从梅瑟出埃及的历史中找到上帝消灭异化的依据,犹太人“迁徙是朝向应许之地的漫长征程,在那里能建立摆脱了贫困和异化的社会”[4]206。人们用劳动改造社会,但埃及被剥削者的劳动被异化了。梅瑟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即打破了这种异化,从社会的罪中得到解放。人类在历史中的自我拯救也就是创造过程,“历史是人类奋斗的长征,是不断地出离埃及,向应许之地进发”[13]。最终,上帝将人类召回自己的怀抱,来实现拯救工程的完成。梅瑟出埃及为人类在圣言带领下的自我拯救与解放提供了一种范式:在上帝的带领下,人类自我实现历史创造从而得到解放。犹太复国运动、马丁·路德金的黑人解放、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无一不是在这种范式之下进行的。所以,上帝的创造与人的自我创造形成拯救中的协同。
第二个层次,既然基督的救恩是上帝许诺给世人的永恒保障,并且尚未完成,那它将继续在历史中不断呈现。“它不断把自身映射向未来,创造一个持续的、历史的流动性。”[4]213永不停止的创造是人得以成为人的方式,也是一种“持续的文化革命”[4]62。因此,历史是开放的历史,末世承诺既在历史又在未来,这种开放性甚至不受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历史规律所限制。“救恩只能来自上主的一个新的历史行动,这将以人所不知的方式重启以前对他子民的干预。”[4]216先知的预言是末世论,先知仅仅是上帝预言救恩的基础,真正的拯救却是“未知”的,因为必须靠新的历史来完成。救恩并不受限于任何历史规律或预言,“末世论思想的魄力在于这种紧张指向将要到来的东西,指向上帝新的行动”[4]217。上帝的意志是纯然自由的,未来也就充满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由上帝赋予人类,人有充足的空间去创造未来。
古铁雷斯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神圣历史和一个世俗历史,“上帝的拯救带来人类的存在”[4]200,一切历史都是同一个拯救史。旧约之后,历史已经在耶稣诞生之日被革新而翻开新的一页,新约的历史正在期待耶稣再临。可以认为历史是以耶稣基督为终向的拯救史。人与耶稣一样将经历死亡与复活,这既是一种危险又是一种希望。因此,只有对末世拯救的希望能战胜死亡,而这种希望的意义则是引领当下。“一种超越式的基督宗教不能替换另一种未来的基督宗教,因为前者将遗忘世界,而后者有忽略苦难不公的现实和忽略为自由斗争的风险。”[4]284历史的终极意义赋予现世以价值,直到基督再临,耶稣基督为终向的历史拯救也只有在现实中不断实践才有意义。古铁雷斯的历史观已经是一元论。丹尼尔·贝尔认为古铁雷斯还取消了世俗—神圣二分论,将世俗世界看作全部的世界。上帝对历史的引领要求世俗化,历史和拯救要通过世俗过程来完成[11]58。拯救并非必须在彼岸世界才能被赐予世人,天国就降临在现世中:“天国没有到来,解放的进程就不能战胜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4]240这其实与“圣言成血肉”(道成肉身)是一回事。逻各斯凝结为血肉,以使不可见的上帝成为现世可见的耶稣[9]9-14,并且从上往下撕裂了上帝与人之间的帐幔[14]38。古铁雷斯是用历史的方法打破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以形成“一”的历史和“一”的现实。
通过历史解放,古铁雷斯试图打破马克思的敌人—资本拜物教、货币共同体,进而打破思想牢笼,这将从根本上抽掉现实批判对象的基础,使现实中的不公正源头消失。
三、属灵层面的回应:爱神爱人
经过现实与历史解放的铺垫,古铁雷斯最终要考察作为人的本质的解放,也就是属灵的解放。斗争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彻底的自由和解放。根据罗伯特·麦卡菲·布朗的观点,新的社会结构并不是解放的全部,而内部(自身)的解放与外部(社会、历史)的解放需要同时进行[15]。解放也就意味着除了阶级斗争和历史革命外,还要重新审视和改造灵魂。这种解放成为属灵的、最高的解放,即“真正和完全的”解放[4]64。在这个问题上,古铁雷斯持一种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人拥有自我本能,而资本拜物教剥削框架的压迫使人丧失自主性,也就失去本能。解放就是使人恢复本能,这就是古铁雷斯所谓的属灵解放。什么是人的本能,马尔库塞将其界定为“爱欲”,这种爱欲的解放要求一种非压抑文明。人以快乐的原则生活,劳动“完全服从于人和自然的自由发展的潜能”而成为纯粹的创造力;人们之间因为爱欲而结合,非压抑性秩序借助爱欲自身的本能,“在成熟的个体之间形成持久的爱欲联系”[16]。古铁雷斯所言的人的本能则是教会训导中的“爱”。
古铁雷斯引用圣保禄,昭示人们基督拯救的进程“从旧人到新人,从罪到恩典,从被奴役到自由”[4]66。他认为罪是一切奴役的根源,从罪中得拯救和解放就能拥有自由,人就可以开放自己,走向他人,成为“自我实现”[4]52的新人。罪切断人与上帝的纽带,使人变成以自我身体为中心,陷于个人的、身体的奴役,而非属灵的自由。这还是源于私有制导致的人类的异化,这种异化更导致属灵的贫困。但基督并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与众人联系在历史的纽带中。基督有着人类的面容,也有着上帝的神性。古铁雷斯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基督通过人重新建立人与上帝的联系,使人成为与他人、与上帝合一的人,以打破罪的桎梏。他认为要“在基督内,通过灵魂,与分离和反对团结作斗争,人在历史的最中心成为一体”[4]210。人是历史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成了理性觉醒的、现实的自由人,而历史要求人与他人建立政治关系,走向人类一体。“人的理性已经成为政治的理性”[4]76,政治和宗教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互不相干,宗教则将陷入个人化。“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17]515,而合一的人类则是最大的发展。
如果我们认为人的本性中善恶并存,人的自我努力即使达到高度文明,也不能取得真正的自我原则和道德概念,最终只有走向全善的神,与基督合一,才能到达纯然的善。这样,人就可以并且应当从这种合一中迸发出彼此的爱,使整个人类凝结成一体。学生时代的马克思在自己的宗教论文中也想到通过基督到达人类互爱合一。马克思的思路同样是从人与基督的合一出发,论证人要敞开心扉成为互爱的人。马克思写道:“葡萄枝蔓不仅会仰望栽种葡萄的人……它会感觉到自己与葡萄藤和长在藤上的其他葡萄枝蔓最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可使人内心变得高尚,在苦难中得到安慰,有镇定的信心和一颗不是出于爱好虚荣,也不是出于渴求名望,而只是为了基督而向博爱和一切高尚而伟大的事物敞开的心。”[18]452-453马克思在这里虽未论及解放,但从属灵角度将最终的爱置于最高地位,从人性改造到人类凝聚、最后到博爱的思想构架,可以说是古铁雷斯所谓属灵解放的思想源头。
在古铁雷斯看来,属灵的解放代表着终极关怀意义上的自由,属灵的解放意味着人可以不受自身或社会的限制,从而真正进入自由王国。古铁雷斯强调“新人”的概念。新人的概念本身来自于圣经:“所以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19]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也有精辟论述。马克思说:“解放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新人’”[18]242,新人是脱离了束缚而得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并且“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0]。
怎样成为新人?古铁雷斯认为,内心接受了基督的人必须与遭受苦难与不公正的人们形成真正的团结,而不仅仅是内心的信仰和灵修,人才能成为新人。“人并不真正透彻地知晓上帝的审判已经来临。人的生活也并不是孤立于他人和上帝。人同样不能放置自身于基督之中而又试图避免人类凝聚的历史。”[4]205也就是说,上帝已经降临,人与上帝在同一个现世。人们因为上帝而结合为一,一个新人必须是敞开心扉与众人成为一体的人,而这也是博爱的要求。“不求回报的上帝撕光了我,让我赤裸,把我的爱不求回报地普施给众人。”[4]271这让人想起耶稣在审讯中被撕光衣服的情景,赤裸的耶稣似乎只剩下对全人类的爱。圣言成血肉造成的事实是:人因耶稣的牺牲而赎罪,重新获得成圣的机会;因罪被驱逐的人类重新回到上帝身边,人类也因此与上帝合二为一。属灵的自由不是造成孤立的人,人要敞开自己的心扉走向他人,如同上帝无偿的爱一样,作为回应,人应当通过人而到达上帝。这就是耶稣对诫命的总结:“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上帝”和“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14]30-31,也就是天主教“爱神爱人”的训导。
这种号召人类大同的思想可看作是古铁雷斯对保禄六世《民族发展》通谕的回应。保禄六世认为应当关注穷人所遭受的社会不公,从现实的需求中真正帮助穷人,从而形成“基督内爱的团体,使所有人分享生活的上帝的礼物”[21]。同样可以认为,《解放神学》所言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共同体关系与马克思所谓自由人共同体如出一辙,二者笔下的人们也将摆脱异己力量,国家将成为服务工具。人们为他人服务并不是出于被统治,信仰也不是像《游叙弗伦》一样仅仅服侍神,而是“用服侍同胞来传播上帝的爱,如同基督一样”[22]。圣言通过启示带领穷人寻求解放,历史的终点救恩将赐给万民,上帝之国降临,终极拯救彻底实现,到达解放神学的最高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古铁雷斯认为属灵的解放是最高的解放。
四、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解放神学》对马克思宗教批判所作的三个回应,前两个是关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后一个混合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交往等理念,但最终是上帝公义的实现。古铁雷斯的上帝是一个虚化的本体,它是三重解放的起点和终点,其中的历史则由人自己努力完成。这三重解放都是在上帝指引下的一种人的自我解放,即没有上帝,解放就没有方向,但上帝只会指引这种方向,而其中的内容,《解放神学》采用了马克思的模式。《解放神学》将二者合二为一,用马克思的理论重新构建了教会。
上帝和人的能力各自在什么样的尺度范围之内?由此可以看到,解放神学在根本的立场上有两种可能性倾向:第一种,经过一番周折,《解放神学》所言的最高解放还是回到了神义论,即作为至善的上帝为了实现普世公义,它带领人类在历史和现实中实现拯救。如果从这个终点来看,马克思的思想对于《解放神学》来说只是一个过程,而保禄六世的通谕才是古铁雷斯的目标指向。抵达这个终点,也就回到了传统天主教教义。这种倾向中的解放神学虽然在社会批判和历史创造层面有历史唯物主义倾向,但它的神义论必然是拒绝真正的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情况下得以实现的是目的论式的历史,而不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二种,严格限制上帝的影响,把历史完全归结于人。上帝在此几乎只有精神引领的作用,一切事务都由人来完成。这种情况下上帝也就成了伊壁鸠鲁的神,与世间不发生关系,人们也不从他那里获得超验的力量。这种解放必然是人类的自我解放,解放神学在这个意义上就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已经占有了一元历史,而上帝的作用只是在拉美“放手发动群众”。以大众最具有感情的教会为载体,是走人民路线的最佳方式。实际上,《解放神学》文本本身更类似于第二种倾向,但从后期访谈和著作来看,古铁雷斯似乎想又转向第一种倾向,但他却始终没能清晰地论述到底应该站在哪种倾向上,或者说他本身在此问题上也陷入了困境。在古铁雷斯之后,这两种倾向一直存在于解放神学的各个神学家和革命者中。
巴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并不损害基督教活生生的上帝, 只是损害到‘观念上的偶像’罢了。”[23]为了消灭成为新偶像的资本拜物教,他甚至提倡“真正的基督徒必定是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基督徒”[24]。从思想本质来说,《解放神学》并不是一部原创性很强的著作,而是融合了大量前人思想创造出的新的“实践神学”,将认识转化为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6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解放神学因拉美政治、经济、军事等格局的变动而逐渐走入低谷,甚至有人说“解放神学已经死亡”。再后,从全球政治格局来看,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也从大环境上让解放神学更加难以立足。但解放神学本身走向衰落的同时却影响了世界其他教会,形成了旨在寻求解放的黑人神学、大众神学、妇女神学等。今天,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2013年登基的“人民的教宗”方济各(Papa Francesco)显然对解放神学充满好感。方济各与古铁雷斯同是拉美贫民窟出身,深切知晓最底层人民的苦难。他发布《福音的喜乐》通谕,把资本拜物教当作圣经中的金牛犊崇拜而予以痛斥[25],邀请古铁雷斯到梵蒂冈参加会议,他甚至在墨西哥接受了一个铁锤镰刀形象的十字架礼物。解放神学陷入衰落后似乎又因方济各的上台而重焕青春。方济各成为穷人的教宗,古铁雷斯也再次声名大噪。他旋又提高音调,将方济各看作是自己的支持者,声称教廷从未批判解放神学[26]。
为实现马克思号召的终极解放,古铁雷斯写出史诗般的《解放神学》,他既要与劳苦大众一起在阶级斗争中失去锁链而获得整个世界,又要走出红海,去向没有剥削和异化,只有奶和蜜的应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