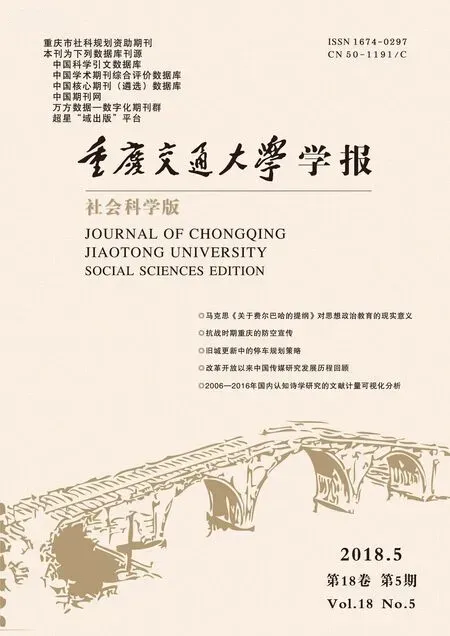时代转弯处的逃离与迷津
——对电影《塔洛》的现代性阐释
杨有庆
(兰州交通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70)
如何使艺术面对它的时代,以既不躲避也不屈从的姿态获得某种程度的现实性?这是每个艺术家都必须自行解决的首要问题。真正的艺术家拒绝充当评判者,往往通过对个体存在状态和境遇的呈现,来思考并试图解释那些将个体卷入时代的现实问题。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电影《塔洛》就是面对当代现实,以影像来思考、唤醒当代藏族人生活现实,进而阐释现代性的杰作。
一、伪装成爱情悲剧的城市体验
万玛才旦是第一位使藏语电影获得了真实地位的中国导演。在《静静的嘛呢石》(2005)、《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1)、《五彩神箭》(2014)、《塔洛》(2015)等藏语电影中,万玛才旦以纪录片风格的影像民族志方式唤醒现实,从内部呈现了现代藏地人们的生活世界。他在镜头中凝视个体、族群与时代的复杂关系,讲述藏人在时代洪流中所遭遇的冲击、焦虑与抉择等种种新的历史经验。万玛才旦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审视现实时往往“瞥见光中隐秘的晦暗……将这种黑暗视为与己相关之物,视为永远吸引自己的某种事物”[1]。这种独特性产生于某种试图以地方性知识阐释现代性的企图。电影《塔洛》无疑是此类阐释中最具有野心和力量的尝试,通过对逃逸在历史之外的个体如何被现实质询、规训这一主题的影像化表达,来楔入当代与时俱进的历史神话,进而爆破关于进步的历史幻象。
2015年,万玛才旦执导的电影《塔洛》改编自他本人的同名小说。相对于《塔洛》小说文本的简洁留白和致力于荒诞感的营造,改编后的电影文本显得更有现实的质量和现代性张力。本片于2015年被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提名并最终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又于2017获得第17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之最佳导演奖。这些奖项某种意义上确证了本片对现实的阐释、思考和唤醒方面的力量与贡献。
电影《塔洛》讲述了牧羊人塔洛由于错过身份证照片拍摄时间,到县城的照相馆去补拍证件照,在此过程中认识理发店女孩杨措进而陷入爱情,为了爱情堕落却被抛弃而幻灭的故事。影片通过这样的情节,探究在现代社会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牧羊人如果进入城市的可能性后果:他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又会获得何种新的体验?本片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乡下人进入城市最终堕落乃至幻灭的现代寓言,其中蕴涵着对城市的某种现代性焦虑和想象:城市是诱人堕落的罪恶之地,是一切诱惑和欲望藉爱情、自由等美好事物之名而行的渊薮。
影片中,当塔洛身处城市,画面总伴随着大量难以描述的噪音,让人烦躁压抑;而当他回到山野里牧羊时,出现的是羊的叫声、深夜的狼嚎,铁壶在炉子上发出的“滋滋”声、木材燃烧的噼啪声等自然的声音,虽然孤寂但却静谧自在。这种鲜明的对比隐含着对城市的现代性体验与审美批判。
当然,影片中对城市的现代性体验主要通过塔洛的爱情追求与失败加以表征。塔洛为什么会爱上理发店女孩杨措?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表面看起来似乎因为他是一个长期处在与世隔绝的孤独状态中的成年男子。这孤独使得他错误地理解了杨措别有用心的示好举动,比如夸赞他英俊,给他买雪糕以及邀请他一起去卡拉OK唱歌等。但杨措并非塔洛在县城遇见的唯一的女性,另外还有其他比如照相馆的女老板德吉、小商店的女老板等。为什么塔洛没有爱上这些女人,而是对那个怂恿他卖掉主人家的羊携款私逃的“坏人”念念不忘呢?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女人是他习以为常的传统藏族女人的样子,而杨措则是不一样的,是城市与现代的化身,是时尚而魅惑的。因此,虽然塔洛觉得杨措穿牛仔裤、留短发、抽烟、与男人打情骂俏等行为对藏族女孩来说不好,与传统藏族女孩行为不符,但还是身不由己,一步步陷入了其所设置的爱情陷阱而欲罢不能。对塔洛而言,时尚女孩杨措犹如一个现代版的贝雅特丽思——一个引导他感知和体验城市的女神。正是在杨措的引导下,塔洛生平第一次领略了干洗、卡拉OK、啤酒、女士烟、Rap等城市日常生活的物之震惊。这些沐浴在商品光芒中的物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方式给塔洛带来了震惊体验,同时其本身所具有的“物化的力量”也在逐渐冲击和瓦解着塔洛的生活习惯和原则。在卡拉OK歌舞厅里,塔洛手持话筒唱起拉伊的场景,完美地呈现了这种冲击。拉伊是在青海、甘肃与四川等安多藏区流传甚广的藏族山歌,内容涉及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塔洛一手持话筒唱起本应在高原牧场或旷野中咏唱的情歌,同时又把另一只手张开放在耳旁,似乎在聆听回声。这个场景荒诞之中又有反讽的悲凉。此处自然歌唱与现代技术的矛盾似乎表明甚至放大了塔洛和杨措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是乡村与城市的差异,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差异。这种矛盾与差异在那一刻似乎被爱情的力量或幻象所和解。随着剧情的发展,塔洛为了他所理解的爱情,不断妥协退让,比如在歌舞厅里不抽自己卷的旱烟,用话筒唱拉伊,甚至铤而走险卖掉主人家的羊,计划携款和杨措一起私奔。结局却是杨措趁塔洛睡着的时候,自己带着塔洛卖羊所筹的16万元巨款逃之夭夭。这样的结局,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城市与现代相对于乡村与传统的胜利。
可以说,塔洛的爱情追求与失败,呈现的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牧羊人进入城市的种种历险、震惊体验和传统生活方式面对现代城市生活时的可能命运。他追求的是一种建立在感官、感觉基础上的情感关系,因此他在家里跟着收音机里的歌声学习拉伊,在激情驱使下试图通过传统的方式去获得爱情。但杨措喜欢时尚,向往外面的世界,只是想从他身上获得走出大山的金钱。虽然她在塔洛拿出钱的一瞬间似乎被感动了,但随即很快就恢复了冷酷的理性态度。詹明信说:“物化的力量驱逐了那个古老的、象征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使语言和文化的经验中出现了新的关于外在的参照物的观念。”[2]285在此,金钱作为新的经验和参照物打败了对爱情的浪漫想象,某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物质占据主导的现代文化击败了传统。
塔洛为了爱情的追求、堕落和被欺骗,与其说是一个男人一厢情愿地陷入伪装成爱情的陷阱,铤而走险而不自知乃至最终幻灭的悲伤故事,毋宁说是一种本能冲动驱使下注重感情关系的传统罗曼司想象被奉行金钱原则的“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和“用头脑来代替心灵”的都市理性所淹没的现代寓言[3]187。
二、丧失的记忆与主体的崩塌
电影中主人公塔洛超群的记忆力及其丧失是贯穿全剧的一个重要线索。在影片开头长达12分钟的长镜头中,去派出所办理身份证的塔洛用“念经的语调”背诵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汉语全文。同时,他也能够记得所放牧羊群的总数、多少只公羊、多少只母羊、多少只羯羊,以及羊群每年增加的数目。这个富内斯般的人物,其惊人的记忆力让派出所所长多杰瞠目结舌,叹为观止。后来,当杨措席卷塔洛卖羊所得的16万元不辞而别时,塔洛再次来到派出所准备自首。多杰所长要求塔洛在其他民警面前背诵《为人民服务》,以展示其超强的记忆力。但这次塔洛背诵得磕磕绊绊,不到一半就难以为继了。塔洛的记忆力及其丧失暗示了现代社会中有关主体构建和崩塌的真相与秘密。
影片中的塔洛从小失去了父母,为别人放了大半辈子羊。他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从外表和行为判断大概四五十岁。他读过小学,认识一些汉字,从小就背诵《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作品,也稍微能了解其大概意思。直到成年以后,他对《为人民服务》的记忆仍然可以达到连正文之外的发表时间都丝毫不差的程度。语言并非客观之物,它通过词语沉默的存在将观念“铭刻”在人的内在生命和行为之中。福柯论及语言对主体的构建时说:“人在一种成片段的语言的空隙中构成了自己的形象。”[4]从塔洛和多杰所长的谈话中可以发现,塔洛误以为司马迁也是现代的人。这一错误表明:他并不能理解此文所涉及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政治内容。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其道德规训的接受和践行,甚至将古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与现代具体政治道德规训相结合,进而从此类政治文本中汲取并生成了基本的价值观和实践标准:为他人服务就是好人,其死亡就会有意义;反之就是坏人,就是无意义。正是在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价值观框架中,塔洛相信自己为村里人放羊,即使有一天死了,也是像张思德一样的好人。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其功能“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5]。在此片中,《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政治文本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表述的正是个人与现实之间的想象性关系。塔洛将生命的意义交付给以“为人民服务”为标准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可以说,塔洛是一个被政治意识形态“召唤”成功的典型政治—道德主体。在好人/坏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塔洛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与此相对应,电影通篇的黑白影像世界象征了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是简单的非黑即白。而塔洛这个连自己年龄和名字都记不住的人,居然对《为人民服务》的汉语全文,以及与放羊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相关事宜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这一细节表明在进入县城之前,在塔洛身上由二元对立式政治意识形态构成的主体与其生存条件之间的想象关系是牢固的。
塔洛去县城拍证件照,“好人”的主体身份认同遭遇了两次冲击。一次是他在照相馆门口给小羊羔喂奶时,被巡逻的警察怀疑是小偷,后经照相馆老板解释消除了误解;另一次是杨措怂恿他卖掉羊拿钱和她一起去拉萨,塔洛落荒而逃。这两次冲击震荡了塔洛对“好人/坏人”的认知和判断标准,使他耿耿于怀。因此他再次来到派出所向多杰所长请教如何区分好人与坏人。这个情节设置表明塔洛据为己有的那种非此即彼的价值观和主体身份认知在现代城市理性的冲击下动摇了,他开始怀疑自己一直相信并践行的原则。但多杰所长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于塔洛的重要性,而是以俏皮话的方式打发了塔洛。
此后,塔洛回到山上继续放羊。某天晚上他醉酒照看不力,羊被狼咬死了十多只,甚至连他最喜爱的小羊羔也难逃狼吻。闻讯赶来的牧场主辱骂并且扇了塔洛耳光。这是塔洛建立在“为人民服务”原则上的好人信念崩塌的直接原因。那个由语录召唤和构成的政治—道德主体轰然倒塌。塔洛卖掉了所有的羊,带着16万元再次来到县城,打算与杨措一起私奔。他在杨措的建议下,剃掉了标志性的小辫子。从小辫子到光头这一形象的巨大转变,虽然影片中杨措解释是改头换面,为了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客观上却表达了塔洛弃旧从新的潜意识愿望。但杨措最终欺骗了塔洛,在他睡着的时候携款逃走。因此,当塔洛来到派出所准备自首时,他再也不能流畅连贯地背诵《为人民服务》,这标志着他内在的政治—道德主体终于在现代城市理性的冲击下不复存在。
总之,塔洛超群记忆力的丧失并非由于遭受欺骗的打击所致。影片在情节设置上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曲折地呈现了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个体之政治—道德主体的建构过程,及其在新的经验——城市理性与金钱冲击下崩溃的可能性命运。
三、个人命运背后的民族寓言
电影《塔洛》不仅仅是一部关于个人在现代社会生存状况的作品,也是关于现代社会中藏地生活与现代性进程之复杂关系的表述。通过塔洛的经历,影片叙述的是有关藏地人们在现代社会可能会遭遇的冲击和困境。换言之,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了一种对现实的现代性阐释,正如詹明信所说的,在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中包含着整个族群社会生活受到冲击的寓言[2]523。
加缪说:“艺术家不负责任的时代已经过去。”[6]在他看来,在现代生活中,艺术家的智慧必须在与现实的对峙中才有机会重新挺拔和得到尊重。本片在对塔洛个人生存状态、处境和命运的叙述中,也包含着对藏地其他人,或者说整个民族在现代生活中状态、处境和命运的叙述与反思。
作为民族寓言的叙述和反思,在影片中主要呈现当代背景下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撕裂与妥协。首先,万玛才旦在电影中呈现的藏地并非汉族艺术家以游客心态想象的“最后的净土”,而是其不断遭受现代文化冲击、渗透和撕裂的状态与处境。电影《塔洛》中塔洛在照相馆拍照时遇见了一对藏族新婚夫妇,他们在拍摄新婚照,都穿着隆重的藏族服饰,背景装饰画先是拉萨布达拉宫,然后是北京天安门。但布景换到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时,摄像师德吉觉得“有点别扭”,并将原因归结为他们所穿的服饰与背景不配套。当他们依照摄影师的要求换上西装,摄影师又始终觉得不自然,却不知道原因何在。新娘子灵机一动,要求抱着塔洛随身带着的小羊羔一起拍照。最后,镜头里这对夫妇穿着西装,丈夫拿着奶瓶,妻子抱着小羊羔,在纽约城自由女神像背景下完成了照片。这一场景极具张力,一方面表现了当代藏地人们生活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不适以及杂糅景观。穿上西装的藏族夫妇被规训得与到藏地旅游的汉族男女并无二致,唯有手里的小羊羔表明了传统微弱的在场。这幅犹如游客的照片颇具后现代的滑稽模仿意味。另一方面不断切换的布景隐喻了遥远的北京、纽约已经像幽灵般渗入了藏地人们的日常生活想象,甚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所以后来当杨措问塔洛如果有钱想去什么地方时,塔洛自然地说出了拉萨、北京和纽约。这表明图像、文字等媒介带来的对这些遥远而陌生之地的想象,已经成了人们经验的一部分。他们以此作为经验和参照,对当下的生活进行感受、判断和质疑,结果往往会产生逃离的欲望。
其次,塔洛的爱情追求与失败极富象征意味。他对杨措的爱情,深层原因在于杨措是现代和城市的某种肉身象征。换言之,塔洛爱上杨措,隐含着藏人对现代和城市的向往与追求。他选择了两条通往爱情的道路——拉伊和金钱。但相对于象征传统的拉伊,杨措更喜欢代表时尚和现代的Rap。金钱是杨措靠近塔洛的根本动力。当她听说塔洛所放牧的羊群价值十几万元时,才开始别有用心地向他示好,后来邀请他去卡拉OK,把醉酒的塔洛背回理发店。这一系列行为都是因为金钱的缘故。等塔洛酒醒时,杨措骗他说要一起私奔去大城市,怂恿他卖掉主人家的羊。这时他进城时带着的小羊羔叫唤的声音唤醒了塔洛。此时,羊叫声象征的传统生活暂时抵御了来自城市的诱惑。随着情节的发展,小羊羔被狼咬死了,羁绊塔洛留在乡村的力量消失。塔洛最终卖掉了羊,企图用金钱去追求爱情。对杨措而言,虽然在交往过程中有被塔洛打动的瞬间,但金钱才是她的最终目的。正如西美尔所说,在城市生活中事物的质的差异性被中性的中介——金钱所掏空,“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飘荡”[3]190。相对于金钱,爱情、情感与浪漫等事物无不显得黯然失色。在影片中,金钱成了唯一真正维系塔洛和杨措关系的媒介。塔洛爱情的失败表征了藏人在现代性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以及都市理性摧枯拉朽的力量。尤其是对金钱的追求,使得人的生活和精神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工于算计。在此过程中,“金钱是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压力和焦虑,引出了新的灾难和欢乐”[2]299。
塔洛对《为人民服务》的失忆,则象征在特殊时代所建构的革命经验和主体在金钱这一新的历史经验冲击下失效的事实。在金钱占据主导地位、凌驾于精神之上的物质文化与城市理性的冲击下,传统的价值观念、信仰与生活方式都面临着崩塌的危机和可能。导演万玛才旦在访谈中谈到了这种困境:“我觉得藏地的年轻人,还有塔洛那个年龄段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但可能塔洛那个阶段的人更激烈一些,因为过去的年代迫使你放下自己的个性,在你心里建立起另一个信仰的体系,随即这种体系又坍塌了,但你得在别人的侧目中重建原来的体系。”[7]在这场后革命时期的爱情追求与失败中,塔洛原有的价值体系逐步坍塌。革命时期锻造的价值体系和主体在城市理性冲击下逐渐式微,乃至于最终崩溃。这样的遭遇不仅是塔洛个人的命运,也表征了藏地人们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现代性焦虑和困境。在影片结尾,剃成光头的塔洛将摩托车停在一个公路的拐弯处,远处是雪山。这个场景意味深长,象征传统的雪山与象征现代的公路,塔洛究竟如何选择呢?他在沉默中独自饮酒,最后将原来用来驱赶狼的鞭炮捏在手里点燃。影片至此戛然而止。塔洛要驱赶的是什么?传统的重负,抑或现代性的冲击?很明显,导演没有替塔洛作出选择。影片保持了开放的结局,保持选择的诸多可能性意味着藏地现代性的未完成,成为杨措、万玛才旦是塔洛未来的可能性选择,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可能性。
总之,万玛才旦在电影《塔洛》中通过对牧羊人塔洛日常生活状态、处境的叙述,用影像图绘了藏人当代以来在政治话语和以金钱为原则的城市理性轮番规训下的不适、逃逸与豹变,以其生活与爱情经历为线索呈现了当代藏地人们在现代社会冲击下所不得不面对的身份焦虑、价值体系崩溃与主体裂变等现代性体验。影片选择叙述个体在现代社会中遭遇的不适、震惊与裂变来真诚面对现实,凸显身份焦虑、价值体系崩溃与个体裂变等背后的传统与现代之冲突,进而在唤醒现实的同时阐释现代性。这不仅是对当代藏地人们生活的叙述与反思,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现代生活中“各种占支配地位的虔诚提出质疑、作出抗辩”的叙述与唤醒[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