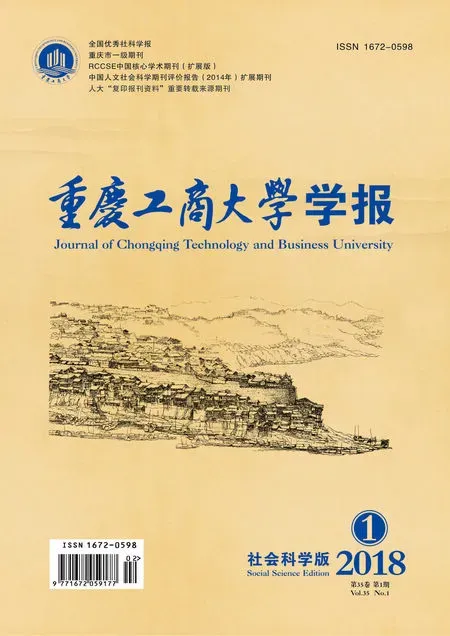雨王亨德森:浮士德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卢 婕
(1.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2.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雨王亨德森:浮士德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卢 婕1,2
(1.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2.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歌德以浮士德在知识、爱情、政治、艺术、事业等领域的探索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西方知识分子追求生命意义的过程。《雨王亨德森》对浮士德精神进行了传承与发展:尽管亨德森沿袭了浮士德对人生意义的五条探索道路,但他为西方知识分子找到的人生价值并不雷同于浮士德的既有结论。通过将“观念小说”《雨王亨德森》与“哲理诗剧”《浮士德》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洞察西方知识分子几个世纪以来追求人生价值的心路历程。
《浮士德》;《雨王亨德森》;贝娄
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以浮士德在知识、爱情、政治、艺术、事业5个阶段的探索为主线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人士不断追求和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诗剧结构宏大,作为歌德毕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结晶,与“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起被誉为欧洲文学四大里程碑,对后世欧洲文学的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郭沫若评价《浮士德》为一部灵魂的发展史,一部时代精神的发展史*见郭沫若著《浮士德简论》,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郭沫若译《浮士德》第一部。。本文从精神探索道路的角度分析20世纪美国作家索尔·贝娄《雨王亨德森》中的主人公亨德森对“浮士德”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亨德森沿袭了浮士德对人生意义和人类前途的五条探索道路;另一方面,亨德森在否定浮士德的探索道路之后为西方知识分子找寻到了新时代语境下全新的救赎之途。
一、亨德森对浮士德精神的传承:相似的探索道路
宗白华说:“近代人失去希腊文化中人与宇宙的协和,又失去了基督教对上帝虔诚的信仰,人类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得到了自由,但也就同时失所依傍,彷徨,摸索,苦闷,追求,欲在生活本身的努力中寻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歌德是这时代精神的伟大的代表”[1]66。《浮士德》正是歌德为近代“信仰危机”的西方人探索的救赎之路:“在我的心上堆积全人类的苦乐,把我的自我扩展成人类的自我”[2] 82。但是,随着历史前进到二十世纪,西方信仰危机并没有得到缓解。相反,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等因素导致西方人在精神上更加惶恐不安。价值观断裂、精神空虚、理想破灭、道德沉沦使西方文学出现了“荒原观念”“迷惘的一代”和“伤痕文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索尔·贝娄在创作的中后期反省和反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悲观格调,以自己“新浪漫主义”风格和“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创作了《雨王亨德森》。可以说索尔·贝娄笔下的亨德森是继浮士德之后的另一个西方精神探索者先驱。他们都以追求生命真谛为人生要义,都渴望灵魂与肉身、小我与大我的合一,都向往超越现实的存在以达到灵魂的永生。二者在精神探索之旅中,都在知识、爱情、政治、艺术、事业等方面经历重重阻挠,但他们都像西西弗斯一样在挫折中不断接近生命的真相,寻找“存在”的意义。
(一)知识探索之旅
《浮士德》第一部以浮士德深夜在书斋中抒发苦闷为开端。“唉!我到而今已把哲学,医学和法律,可惜还有神学,都彻底地发奋攻读。到头来还是个可怜的愚人!不见得比从前聪明进步;……别妄想有什么真知灼见,别妄想有什么可以教人,使人们幡然改邪归正”[2] 23。浮士德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以书本和知识为第一阶段,但是长期困守书斋不仅没有让他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反而使他对禁锢心灵的书斋感到如同监牢一般的反感。他呐喊“这么活下去连狗也不肯”[2] 24。在欣欣向荣的大自然和自由愉快的人群的感染之下,他决心抛弃从知识中寻找生命意义,转而投入生活的激流中,希望有所作为。
在《雨王亨德森》的第一章,亨德森也遇到类似的精神危机:“各种事儿开始纠缠我,很快在我心里造成一种压抑”[3]1。然后,名牌大学毕业的亨德森试图在书本中寻找解救自身危机的良药。他的父亲为他留下成千上万册书。亨德森常常暗自翻阅书本以便找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字句。但是他查了几十本书,却找不到他奉为信仰的箴言“罪过总会得到宽恕,善行不必非要先修”[3]1,翻出来的只是父亲当作书签的旧钞票。“我闩上书房的门 ……搭着取书的梯子去抖动书页,抖出的钞票纷纷扬扬飘落到地上。可是我却始终没有找到那句关于宽恕的话出自何处”[3]2。索尔·贝娄用飘落的钞票这一意象象征性地表达了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书本和知识所提供的精神慰藉远远不能抵抗现代社会人类所普遍感受到的虚无感。《贝娄书信集》的编辑本杰明·泰勒认为,“贝娄笔下的主人公都是些知识分子,但他们在遭遇现实生活时,却发现自己掌握的知识微不足道,甚至徒劳可笑”[4]XIII。亨德森与浮士德以知识寻找生命意义的失败如出一辙。
(二)爱情探索之旅
浮士德在知识悲剧之后接受了靡菲斯特的赌约,在返老还童之后与葛丽卿坠入爱河。但是他的爱情为葛丽卿带来一系列灾难:母亲被毒害,兄弟被杀,孩子被淹死,葛丽卿本人也身陷囹圄。浮士德在对爱情的追求中不但没有救赎自己,反而因为给无辜者带去灾难而加重了对人生意义的质疑。靡菲斯特又把浮士德带到“瓦卜普吉斯之夜”,让各种疯狂淫荡的女人腐蚀浮士德的灵魂。但浮士德对各种诱惑无动于衷,并没陷入酒色的泥沼而沉沦。
索尔·贝娄笔下的亨德森也有类似的爱情悲剧。亨德森的第一任妻子弗朗西斯漂亮、高大、优雅、矫健,与亨德森一起生活了二十年,生育了五个孩子。然而由于二人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心灵默契,亨德森在退伍以后仅和她有过一次亲热。他在心烦意乱的时候来到马德伦教堂附近,端详着那一带游来荡去的妓女的面孔,但是他却说“没有哪一张能够平息我内心可怕的喊叫——我要!我要!”[3]14在结束了与前妻的婚姻之后,亨德森最初对第二次婚姻满含期待,以为第二个妻子莉莉可以给他一个开始新生活的机会。但是,第二次爱情和家庭生活也没有让亨德森寻求到人生的真谛。他很快就对之感到失望和厌倦。“和莉莉结合的家庭生活,完全不像乐观者所预料的那样”[3] 28。他开始当众吵她,私下骂她,利用各种机会弄得莉莉叫苦不迭。在第二次婚姻后的一天,亨德森穿着红绒睡衣,室外是殷红的秋海棠,深绿和鲜绿的草木,沁人肺腑的芬芳,悦目的金黄颜色,但在这一切良辰美景中他感到的只是“悲哀”。亨德森没有能在爱情与家庭生活中寻求到他渴望的“有意思的生活”,他和浮士德一样在经历了知识悲剧之后,试图以爱情来拯救自己的愿望也落了空。甚至在潜意识中,他并不指望以爱情来赋予生命意义,而是恐惧爱情的满足会阻止他求索生命意义的脚步。即便在两人感情最浓之时,他也朝莉莉喊:“你休想迷住我,休想把我扼杀掉,我壮实着呢!”[3]28亨德森对莉莉若即若离的态度以及无缘无故的恼怒,都证明了“爱情”这一剂良药没有解除精神危机为他带来的巨大的痛苦。浮士德和亨德森都通过爱情悲剧认识到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必须克服“小我”,走向“大我”。跳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向更高的境界靠近。他们分别对文艺复兴和现代社会一味追求官能享受的现实提出批判。
(三)政治探索之旅
在《浮士德》的第二幕,靡菲斯特把浮士德带到宫廷,希望官场生活能羁绊他不断追求意义的脚步。起初,浮士德雄心勃勃想通过发行纸币来缓解经济危机,但当时的帝国政治昏暗,诸侯割据,官员腐败成风,军队巧取豪夺,人民生活困苦。皇帝无心国政,只把浮士德当作供人消遣的魔术师。浮士德想要通过从政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梦想以破碎告终。杨武能在《走进歌德》中提出之所以不把从政的经历纳入事业悲剧是因为剧中浮士德在宫廷为昏聩的皇帝贵族的骄奢淫逸而效犬马之劳是谈不上事业的。
亨德森也曾试图以相同的方式寻找生命意义:他在自己年龄已经不适合战斗的情况下非要去参加战斗为国效力。甚至赶到华盛顿说服人们允许他上前线。然而在战争中,由于军事长官的无能,蒙特卡西诺修道院被炸毁,许多在意大利战场参战的德克萨斯州人丧命,这让他打消了军事冒险的热情。在意大利萨莱诺滨水区部队长毛虱时,他被人当众剥得精光,涂上肥皂水将腋毛、阴毛、胡须、眉毛剃得一干二净,成为渔民、庄稼汉、小孩子、大姑娘、妇女和大兵的笑料。这些戏谑性的回忆说明亨德森战前“为民主和自由而参军战斗”的理性主义和英雄主义被战争中荒诞的现实彻底颠覆。虽然他在战争中因踩到地雷受伤而获得一枚紫心勋章,这让他的内心在短时期中获得一种“巨大而真实”的感受。然而这种短暂的充实感很快被揭穿了的战争谎言和平庸的战后生活消磨殆尽。于是,他一方面在表面上采取一种老于世故、纵酒自娱、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来逃避社会和家庭赋予他的责任,一方面在内心里拼命挣扎以寻求能拯救自己免于堕落的“有意思的生活”。亨德森所处时代是没有专制帝王的美国现代社会,因此,他的政治探索之旅在浮士德的基础上有所变异。但是尽管他不是“从政”为皇帝效力,而是“从军”为政府当局卖命。这段经历却同样具有荒诞色彩,其结局也都以深重的挫败告终。
(四)艺术探索之旅
浮士德在宫廷为国王效力时,用魔力变出古希腊美女海伦的幻影,他为海伦的美而倾倒,因而意识到自己应该在古希腊艺术创造的美的国度去追寻生命的意义。他说“用不着老是考虑独特奇异的命运!存在乃是义务,哪怕就这么一瞬”[2]456。他在艺术的国度极视听之娱,沉迷于主观的美的感受中,意图以对艺术的追求逃避污浊的现实。但是他与海伦结合生下的儿子欧菲良酷爱自由,在上天入地的自由驰骋中从高空坠地身亡。海伦悲伤不已返回古希腊,浮士德对古典艺术的追求破灭,他不得不回到现实世界继续自己的精神探索。
亨德森也有以艺术逃避现实的经历。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对音乐的追求上。在众多的解脱办法中,他选择了拉小提琴。他把在储藏室里发现的一把父亲的旧提琴送去修理后,跟着匈牙利老头学习拉琴。尽管他奏出的声音像是在摩擦装鸡蛋的塑料泡沫壳,他却希望只要悉心练习,终会奏出仙乐般的调子。通过拉琴,亨德森达到了接近逝去的父亲和母亲的心愿。他虔诚地演奏,带着激情,充满渴望和热爱,直演奏到感情崩溃的地步。亨德森试图通过演奏古典乐曲、歌剧和圣乐曲来寻求“与内心那个声音之间的平衡”[2]30。然而,对艺术的追求并没驱散亨德森心头的欲望:在琴谱架前的荧光灯下练习塞维西克的曲子时,亨德森听见那些尖锐聒耳的可怕滑音,不禁暗想:“啊,上帝,生与死的主宰!我的手指尖都损伤了……我的体内仍然发出那个声音:我要,我要!”[2] 31。可见,对艺术的追求并没有解答亨德森对生命意义的质问。他心中升腾的“我要,我要!”正是对生命意义的强烈质询,对现实世界芸芸众生不求甚解、随波逐流、信仰丧失的畸形的生活形态的彻底抗拒。
(五)事业探索之旅
浮士德在对艺术的追求失败后,决定从幻想的美的国度回到现实世界进行移山填海、造福人类的事业。在失明的状况之下,在被靡菲斯特欺骗之下,浮士德误把别人为他挖掘坟墓的声音当作人类移山填海的劳动之声,因而心花怒放地说出:“你真美呀,请停一停!”[3]556此语一出即意味着浮士德对生命的最高限值和全部奥秘的追求得到满足,因而他输掉他与靡菲斯特的赌局。
《雨王亨德森》中的亨德森本是一个继承了三百万美元的富翁,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曾祖父当过国务卿,几个叔伯父当过驻英、法的大使,父亲是著名学者。但是在五十多岁时,他还梦想进医学院,然后可以当一名医生减轻他人的病痛。在遭到前妻的嘲弄之后,他办了一个养猪场。他把自己漂亮的旧式农场、马厩房,建筑精美、屋顶上有观景台的旧粮仓都养起了猪仔。他把自己漂亮的庄园变得俨然成了一个猪的王国,无论是草坪或是花圃,到处立起猪圈。除此之外,他还亲自干粗重的活计,试图以繁重的劳动将自己对生命之虚无的感觉排挤出思考空间之外。他试着全心全意地劈柴、举重物、犁地、砌水泥板、浇混凝土、煮猪饲料,像囚犯一样袒露着胸臂,抡起大锤把石头块砸碎。但是最后亨德森的感受是:“这样干的确有帮助,但还不够。粗暴产生粗暴,撞击产生撞击……还不止是产生而且是增加,火上浇油”[2] 23。他总想干些什么,尽管有那么多的财富,他问自己拿着这些钱有什么用?自己可以制造什么呢?“我要,我要!”的呼唤在每天下午出现,亨德森越想抑制它,它就变得越强烈。他自我反思到:“美国的幅员如此辽阔,每个人都在干活:制造呀,挖掘呀,推土呀,运货呀,运载呀。我想受苦者受苦的程度都是一样的,虽然每个人总想奋发振作。我试过了一切能想到的解脱办法,没用”[2]24。浮士德在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事业中寻求到了生命意义的满意答案。尽管他输了赌局,上帝却因为“凡自强不息者,终将得到拯救”,仍派天使下来把他的灵魂从魔鬼手中解救出来带到天上。但是亨德森即使是在忘我的工作和造福他人的事业中仍然没有得到解脱。那个“我要”的声音不断在他的灵魂深处呐喊,把他逼迫到疯狂的边缘。在小说前四章交代亨德森非洲之行的动机时,短短39页篇幅竟然重复出现了七处“我要,我要!”以表达亨德森内心的强烈诉求。冯至说《浮士德》的主题是我国《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5] 156。 亨德森不断呼唤的“我要”正是浮士德永不停步、寻求生命意义的精神在二十世纪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延续。
二、亨德森对浮士德精神的发展:不同的探索结果
恩格斯指出:“歌德只是直接地——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预言式地’——陈述的事物,在德国现代哲学中都得到了发展和论证”[6] 652。《浮士德》尽管没有给西方人关于完满人生的答案,但是它被看作是“近代人的圣经”。它对人生意义和人类前途的思考对《雨王亨德森》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现代美国毕竟不同于文艺复兴时的德国,索尔·贝娄的创作不可能是对歌德的简单模仿而必须是创造性地继承:尽管浮士德和亨德森都经历了在知识、爱情、政治、艺术和事业等领域的探索以找寻意义的精神之旅,歌德以整本书的篇幅,按历时性的顺序在知识、爱情、政治、艺术和事业各个领域逐个“试错”,直到浮士德把造福人类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索尔·贝娄把亨德森的精神探索之旅安排在同一时间轴上共时性地展开,仅以前四章的篇幅让五条不同的探索道路相互交织。作者的叙述夹杂着顺序、倒叙和插叙,让亨德森不同领域的探索在极度有限的叙述时空中全部遭遇失败,以“雪崩”式的各个方面的毁灭性打击促使他远赴非洲寻求精神的解脱。理查德·斯登认为该小说的“头四十页已经溢满了足够写两至三部小说的素材,包括夫妻间、父子间、雇主和佃农间的关系,以及所有令人焦虑不安的内容,然而这些内容都通过作家以诙谐、简单、机智的方式进行处理,并都展现在该小说的开篇部分,这些都最先带给读者们惊喜。而之后的三百多页从素材到领域的跨越更是让许多小说家望而却步,不敢涉猎”[7] 102-107。可以说《雨王亨德森》的前四章是以《浮士德》的探索作为亨德森踏上非洲寻求生命真谛的前传。亨德森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美国式”的探索是从第五章才开始。
(一)关于人生意义的结论
浮士德从孤独封闭的书斋开始,“从一个人的梦想式的世界到两个人的(恋爱)世界到官场生涯到美的精神世界到广阔的发现自然的群体世界,在不断的否定中实现精神的攀升”[8]145。在移山填海改造自然的工作中他最后说道:“它是智慧的最后结论:只有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者,才配享有自由和生存”[2]556。阿克尼斯特说浮士德的生命意识就是在于明知“有限永远不能成为无限的伙伴,也依然要走向生命毁灭的终点”[9]136。亨德森身上延续了对生命荒诞性的抗争精神。在非洲薇拉塔勒女王那里,他向女王请教最好的生活方式。女王说对一个孩子来说,世界是奇怪的。亨德森已不再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对世界感到惊奇,而成人则主要感到恐惧。因此最好的生活就是“朗格—图—摩拉尼”,意思就是“人要活下去”。要保持赤子之心才能令死亡显得遥远。不考虑人生最终的归宿,只为当下的生活而奋斗。女王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与浮士德几乎一致。亨德森认同女王的观点。他说“我不仅为我自己摩拉尼,而且要为大家”[3]81。他全心全意制造炸弹为部落消除蛙患,甚至在极度亢奋之下在黎明时分见到了阳光在白土墙上映现的西瓜汁一样的粉红颜色,这是他五十多年以来难以看到而又一直渴望的象征着“希望”和“意义”的颜色。
然而,索尔·贝娄并没有让亨德森的探索止步于此。如果亨德森的探索以“朗格—图—摩拉尼”为终极答案,那么索尔·贝娄只能沦落为歌德思想的简单复制者。索尔·贝娄本来以“层进法”安排亨德森一步步接近完满,但是却在读者以为的完满结局处为亨德森的命运来了一个“突降”:亨德森在炸死青蛙的同时也炸毁了阿纳维的蓄水池,在愧疚与自责中黯然离开。最后他领悟到“满足于存在的人气运亨通,追求变化的人遭尽厄运”[3] 152,他决心仿效女王过一种以“存在”为满足的生活。然而,当他来到瓦里里与国王达甫成为莫逆之交后,国王却指出仅仅是“摩拉尼”并不能赋予生命以深度。人的心智有权对事物抱适当的怀疑。在讲真话的前提下,国王对亨德森说:“格朗—图—摩拉尼是挺不错,但它本身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东西”[3]206。国王引导亨德森和狮子交流,排除体内郁积的悲伤,涤尽恐惧和绝望。在国王的点拨之下,亨德森开始不再恐惧自己体内不断冒出的“我要”的呼声,他认识到这神秘的呼喊是藏在体内催他不断向上的东西,他明白他这一代的美国人注定要周游世界以寻找生命的真谛。在国王遇害后,亨德森最终意识到人生的意义不仅需要“现实”,还需要常被人们看作“非现实”的崇高的思想和高尚的品质。用亨德森的话来说,就是:“包藏宇宙的胸怀,包容世界的海量,与永恒的事物结盟,为追求永恒的价值而努力”[3] 301。由此可见,亨德森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既继承了浮士德“自强不息”实现个人价值和为大众造福的现实的部分,还蕴含了对二十世纪西方信仰迷失的现实的反思,在浮士德精神的基础上增加了精神追求等非现实因素。这是现代主义经历精神创伤之后向古典主义理性与秩序的回归和螺旋式上升,也是二十世纪的索尔·贝娄对十八、十九世纪的歌德思想的发展与补充。
(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结论
在《美学》中,黑格尔称《浮士德》为“绝对哲学悲剧”[10]320。关于人与自然这一哲学问题的思考在《浮士德》中占有重要地位。歌德通过浮士德表达了他那个时代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浮士德在书斋翻译《新约圣经》时把“太初有道”改译为“太初有言”“太初有意”“太初有力”[2]59,最后创造性地翻译为“太初有为”。希伯来原文中“道”为“Logos”一词,按照基督教教义的理解本是“神的理性”“创世的原则”和上帝的肉身及耶稣基督*《圣经·新约》中《约翰福音》写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浮士德否认‘太初有Logos’,就等于否定了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就等于否定了基督教关于上帝是造物主的说法”[11]308。浮士德“太初有为”中的“为”字德文为“die Tat”,表示人的行为、行动与实践,生物的生存或进化,或者自然以及社会的运动和发展。浮士德对“Logos”的翻译“宣示了一种无神论的、强调自然界本身的运动、进化、发展的宇宙观”[11]309。在事业悲剧中,浮士德率领民众移山填海,变沧海为桑田的奇迹充分印证了他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信心。歌德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他见证了荷兰围海造地和美洲巴拿马运河的开掘。歌德眼中的自然是与人类对立的、需要被驯服的对象。但歌德在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奇迹感到振奋的同时也感到惶恐,因此他笔下的浮士德被忧愁吹瞎了眼睛。浮士德的命运正体现了歌德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态度:自然是宏大的,但它却应该臣服于人类脚下;人类是伟大的,但在挑战自然的同时却难免不受惩罚。
然而,二十世纪的亨德森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当亨德森来到非洲,发现周围群山环绕,土地贫瘠枯裂,一连几天都见不到人时,他感觉到“单纯”“静穆”,他觉得那些石头与他“存在着联系”;后来他又觉得自己艰苦旅程中遇到的斑马的嘶鸣、太阳的升落、牛群和悲伤的人们、黄色的水池和青蛙,每桩事内部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在他把手放在微拉塔勒女王的胸脯上时,他感到她的心跳节奏像地球的转动一样有规律,他觉得自己触到了人生的秘密;在非洲他了解到阿纳维人把牛像自己的亲人一般眷爱,瓦里里人把狮子当作楷模;在搬动姆玛神像之后,经历疯狂的祭仪后,他竟然真的求雨成功成为“雨王”;达甫的“失败者的残余被埋进坟墓,泥土重又吞没自身,然而生命的洪流仍滚滚不息”说法对他产生很大震撼。达甫的“大自然也许具有心智”[3]254的说教起初让亨德森不太明白,但是之后他发现“人类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像国王这样的人”[3]262。种种奇特的遭遇让他最后领悟到大自然可以与人类进行交流,而不应只是向人类俯首称臣。亨德森不再把自然当作人的对立面,而是接受了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奎厄姆在《索尔·贝娄与美国超验主义》中提出索尔·贝娄深受惠特曼、艾默森、梭罗等人的超验主义思想影响,主张个人与自然及社会等诸多对立面的融合[12]。二十世纪的科学理性和现代化生产使群体和谐分裂为个体冷漠,使精神统一分裂为内心异化,使人与自然的亲密分裂为对立敌视。在见证了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掠夺,自然对人的惩罚与报复之后,索尔·贝娄为了克服这种分裂而将和谐与统一重新植入人类心灵,他提倡超验主义自然观,提倡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反对自文艺复兴以来把万物当作被人主宰和征服对象,将神当作虚妄之物而丢弃的“技术性栖居”。亨德森在非洲与自然共处,由社会的人向自然的人回归。他的感受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结束对立,走向统一。浮士德和亨德森都是历史沧桑的艺术缩影。他们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体认正是歌德与索尔·贝娄在不同的时代对世界本原、对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思考。
(三)关于死亡哲学的结论
在《浮士德》中,书斋中的浮士德回顾自己无所作为的一生,感叹道:“活着对我已成累赘,我渴望死,痛恨生”[2]74,然后他饱含热情歌颂死亡带来的幸福。在浮士德输掉自己的灵魂,仰面倒下死亡之前,他说:“我有生之年的痕迹不会泯灭,而将世代长存。——我怀着对崇高幸福的预感,享受着这至神至圣的时刻”[2]556。蒋承勇在《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中》指出:“康德可谓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勇敢不懈探索的‘浮士德’。正是他对人的内心宇宙之复杂奥妙的倾心探索,深深地吸引着歌德”[13]248。事实上,歌德对“死亡”的看法受到德国同时代哲学家康德的深远影响。康德说:“当一个人不再能继续热爱生命时,正视死亡而不害怕死亡,这显得是一种英雄主义”[14]167。因此,浮士德在书斋里的自杀念头和对死亡的颂扬不是“软弱和怯懦”,而是“壮烈的绝望”。但是康德作为一个近代哲学家,在对死亡的思考时更多地把理论中心放在“生”这一层面。他提出“想得越多,做得越多,你就活得越长久”[14]136,“劳动是享受生命的最好方式,无聊则是人生最可怕的负担”[14]134。因此浮士德在移山造海的事业中感到了生的无限意义,他领悟到只要他是在为人类幸福进行创造性工作,哪怕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他也毫无畏惧,他把死亡的瞬间看作至神至圣的时刻。
在《雨王亨德森》中也有多处关于亨德森的死亡意识的描写:亨德森由章鱼苍白的肌肤及布满斑粒的头部,和它被困玻璃缸无助的神态联想到了自己正日渐衰老,被平庸的生活窒息的处境。他心里暗想:“这是活着的最后一天,死亡在向我发出警告了”[3]18;当他与莉莉吵架把家里请的一个老处女钟点工吓死后,他感到她的灵魂像一股气,一丝风,一个泡,飘出了窗户。他意识到“这就是一切,原来这就是死亡——永别?”[3]28;在去非洲之前,亨德森还多次以自杀来威胁莉莉;当他在瓦里里看到布纳姆带来的干瘪的首级时,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巨大潜力,几乎陷入崩溃:“为什么死亡总追随着我——为什么!我为什么不能离开它一会儿!为什么!为什么!”[3]237。 在当晚的祷告中,亨德森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希望他能宽恕自己的罪恶和愚蠢。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15] 315。只有获得一个充分的“死亡概念”,人们才会对“此在之存在所可能具有的本真性与整体性”有一种“源始的”认识。亨德森正是在“死”的震撼中意识到他自己的“在”,促使他努力保持自己的个体性和具体性,推动他从日常共在的沉沦状态中超脱出来。可以说,《浮士德》和《雨王亨德森》都非常重视对死亡哲学的探讨,但前者主要受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的影响,而后者主要受到现代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影响。后者的哲学思想是在现代语境下对前者的批判性继承与反思。
三、结语
歌德被认为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作家、思想家,为整个西方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浮士德表现的世界观、人生观是歌德留给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是“对西欧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在德国民族形成中加以艺术概括,并根据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展望人类社会的将来”[16]34。索尔·贝娄被哈罗德·布鲁姆认为是“同时代中最强劲的一位小说家”[17]1。他继承和发展了歌德的创作特色与核心精神,把对哲学、神学、神话学、文学、音乐、人生的思考与作品本身熔为一炉。西方评论家把他的《雨王亨德森》定位为“观念小说”,“最令人费解同时也是讨论最少的一部贝娄创作的小说”[18] 309。但是,通过将《雨王亨德森》与《浮士德》进行比较研究,在“浮士德精神”的观照之下,结合二十世纪美国的具体文化语境,读者可以较容易地解读这部看似令人费解的“观念小说”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可以洞察到西方知识分子从18到20世纪追求人生价值的心路历程。
[1]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 歌德.浮士德[M].杨武能,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3] 贝娄.雨王亨德森[M].蓝仁哲,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4] Taylor, Benjamin,SaulBellowLetters[M].New York: Viking, 2010.
[5] 徐保耕.西方文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 恩格斯.英国状况[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 Richard, Stern, “Henderson’sBellow”,TheCriticalResponsetoSaulBellow[M].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1995.
[8]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9] 阿克尼斯特.歌德与浮士德[M].晨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
[10]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1] 杨武能.走进歌德[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12] Quayum M. A.SaulBellowandAmericanTranscenden-talism[M]. New York: Peter Lang, 2006.
[13] 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4] 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16] 董问樵.浮士德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17] Bloom, Harold.Introduction:SaulBellow(ModernCriticalViews) [M].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6.
[18] Michelson, Bruce.TheIdeaofHenderson[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1981(4).
HendersontheRainKing: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Faustus’Spirit
LU Jie
(The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ChengduUniversityofInformationandTechnology,SichuanChengdu, 610225,China;TheCollege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SichuanUniversity,SichuanChengdu, 610065,China)
Goethe summarized the pursuit of life’s meaning made by western intellectuals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early 19thcentury through Faust’s exploration in knowledge, love, politics, art and career.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Faust’s spirit: though he followed the suit of Faustus’ five roads to approach truth of life, he drew a different conclusion for western intellectuals. Throug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ovel of idea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and the poetic drama of philosophy “Faust”, western intellectual’s journey to discover value of life in several centuries can be better perceived by readers.
“Faust”;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Bellow
10.3969/j.issn.1672- 0598.2018.01.014
2016-10-22
2017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网络文化研究中心资助科研项目(WLWH17-41)“网络环境下本土文学经典化案例SWOT分析”
卢婕(1978—),女,四川广安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研究。
I106.2
A
1672- 0598(2018)01- 0117- 07
(责任编校:杨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