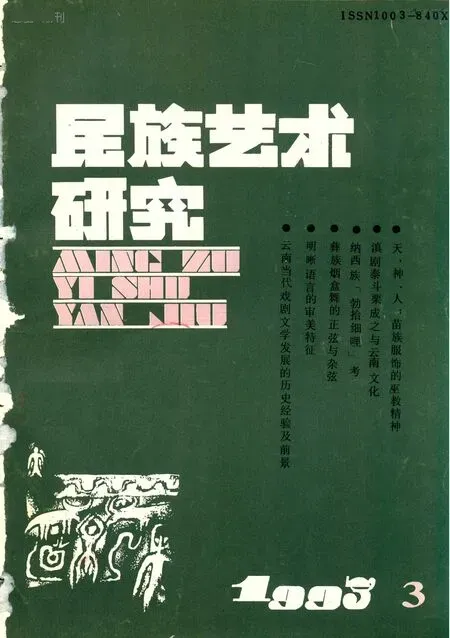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民族纪录片”的历史演进、“国家传统”与美学创新
森茂芳
英国学者休·希顿——沃森在其著作《民族与国家》中说:“民族,民族国家”已成为如今“撼动我所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力量。”*[英]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1页。著名的挪威人类学学者弗雷德里克· 迈特更不无感慨地说:人类学、民族学及人类学民族学影视创作,是当今世界“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事业。*[挪威]弗雷德里克·迈特:《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前言》,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页。这是就世界范围来说的。而对于自古以来民族问题就命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多民族的中国来说,民族学研究、包括影视在类内的民族文化艺术创作在我国虽不敢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那也是在所有人文学科、文化艺术中位列“重中之重”的大事要题。就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党和国家伟大的民族政策的照耀下,在中华文化复兴工程的感召下,在民族文化大省强省建设工程的推动下,凭借多民族大国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民族学、民族题材的文艺作品大量涌现,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时代主题话语之一。其中借助电视这一被历史“提升到权威地位”*王逢振主编:《西方学术大师讲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的最具大众传播优势的媒体而创作的“民族题材纪录片”或称“民族纪录片”,在我国更是以数以万计的巨大的创作量、以其社会意义的重大、文化内涵的深刻、人文风致的醇美、艺术样式的丰富、民族特色的鲜亮而成为当代中国最为重要而独特的影视片种。
一、民族志写作的两大历史背景
美国民族志诗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说:“民族志从来都是在国家体系形成和世界政治经济进展这一历史变迁之背景下写出来的”。*[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等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09页。他认为“人类学电影”“民族志电影”直至如今的“民族纪录片”,诞生于这样两个“历史变迁”的时候:(一)“国家体系形成”的时刻;(二)“世界政治经济进展”的节点。当然,这两者之间又是互为表里关系的,因为历史的事实是:“世界政治经济进展”往往引发一系列甚至成批的新兴“国家体系”的诞生。
影视史学界一致公认美国弗拉哈迪于1922年摄制的《北方的纳努克》为世界“人类学电影”的开山之作,弗拉哈迪因此被誉称为“世界人类学电影之父”。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到爆发前夕,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一个“民族被买进和卖出,被分割和合作”*[德]恩格斯:《德国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卷第641页。又见杨生茂等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上册第187页。的时代。为配合这一“民族被买进和卖出”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目的,或国家派遣,或应殖民者的驱使,许多武装有各种学科知识与技术设备的殖民官员、商人、探险者、记者、旅行家、冒险家、传教士、科学家,走向美洲、非洲、亚洲、澳大利亚等殖民地,对所谓“原始民族”进行社会、文化、历史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英国学者奈杰尔·拉波特等在其《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将之定义为“殖民上升时期的学科活动”。*[英]奈杰尔·拉波特等:《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当时又正值电影技术诞生并趋向成熟的时刻,所以他们配合人类学的文字记录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与作品,学界称之为“人类学电影”。同样弗拉哈迪也难逃“殖民上升时期的学科活动”的宿命。他是美国的采矿工程师,受雇于一家在加拿大修建铁路的美国公司,远征找矿,他来到了爱斯基摩人(意为“吃生肉的人”)的部落。出于对域外“异文化”的关注,他们拍摄的第一部人类学电影《北方的纳努克》诞生了。步其后尘,大批的后继者们,也应各自帝国殖民探险、拓张的需要,走向亚洲、非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亚各地,摄制了大量的作品,于是构成世界纪录电影史上的:“人类学电影”奇观。
二战后,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诞生,史学界将之概括为“去殖民化的民族解放运动”。自此“民族主义”“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民族国家”成为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进展历史变迁”的最炽热的关键词与历史主题。应运而生,“民族志电影”被大批的新兴的民族国家呼唤而出。为回避当时“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之争,与“人类学民族学”这个二合一的概念相对称,称之为“人类学民族学电影”,后来又厌其概念叠加之弊而以“文化”置换“民族”,改称“文化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电影”。也许是出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强烈的文化情怀吧,中国学者刚开始只接受了“民族学”的概念,就称其为“民族志电影”;后来接受了“人类学”的概念,因而就有了“影视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电影”。这给人的印象是在有意或无意淡化与忽略“民族志电影”的独立价值。但从“人类学电影”到“民族志电影”,再到“民族纪录片”的“创作运动的延续过程”来看,我以为作为民族志写作内容之一的“民族志电影”是一种上承“人类学电影”,下启“民族纪录片”的重要片种。尤其是“民族志电影”作为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产物,更是不宜回避与忽视的。关于这一点,国外学者也有人注意到。如有一种意见认为,“民族志”是“人类学”的应用,其具体表现形态就是“田野民族志”,并对其进行区别:“田野民族志是关于民族的写作实践”,而“人类学家通常更多地研究异文化而不是自己的文化。”*[英]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这里虽给予“民族志电影”以地位,但是却只局限在所谓的“田野写作”上。另一种意见是“把民族志,而不是理论推崇为人类学的真正基础”。*[挪威]弗雷德里克·迈特:《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前言》,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84页。“民族志”在人类学上“应用”也好,是人类学的“基础”也罢,从这其中我们已看到“民族志电影”已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存在意义。不仅如此,学界还将“人类学电影”到“民族志电影”的变迁称作“范式转换”或“程式跳转”,即:“一个现实的研究程式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很多从业者可能会转而投向另一个程式——一种作品的新方向”。*[英]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这一“程式跳转”最重要的意义是使原来的人类学电影找到“一种作品的新方向”,被人们用一个意味深长的“志”字加以定义,名曰“民族志电影”。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哈佛大学电影研究中心的创作。如他们拍摄的《猎人》《恩鲁姆·特柴》《一场婚姻的争论》等20多部作品记录下了非洲卡拉哈里大沙漠的布须曼人的狩猎生活、降神仪式、婚姻习俗等等,后来的研究者虽将其定义为“人类学片”*张江华等:《影视人类学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但原创者在其与之同时出版的配套著作《未受损害的民族》一书中却将布须曼人当作“未受损害的民族”即“原始民族”来观察、记录、研究,是一批有别于以往“人类学电影”的“民族志”片。这给人的印象是,学人们在理论上不愿放弃宏大的“人类学”概念,而作品创作用的却是“田野民族志”的方法。面对这种人类学理论与“田野民族志”创作实践的脱节,怎么办呢?这就面临寻找“作品新方向”的又一次“程式跳转”。其间为“人类学电影”“田野民族志电影”寻找“作品新方向”,其中创新了“民族纪录片”成就最为巨大的是中国。
中国“民族纪录片”如今之所以如此繁荣众多,我以为原因是其遇到两大“国家体系形成”的“历史变迁”的关键时刻:其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二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1949年,这是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体系形成”的伟大时刻。经百年的历史苦难与革命斗争,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中走出,从东亚病夫的民族委屈中站起,一种油然而生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促成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作为新兴“国家体系形成”的一项重要工程,刚成立的中央政府为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发展,先后派出了多个“中央民族访问团”“民族调查组”奔向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跟团随组同时拍摄了相当多数量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仅1957年到1967年间,共拍了15部,它们是《佤族》《黎族》《凉山彝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独龙族》《景颇族》《西藏农奴制》《新疆夏合勒克乡农奴制》《苦聪人》《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大瑶山瑶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从其涉猎的民族之多、地域之广,可以看到在新兴“国家体系形成”之时,人类学、民族学及人类学电影、民族志电影的兴盛。其强烈的“民族志”叙事意识,是“人类学”三个字难以精准概括的,甚至可以说这些作品“人类学”的意义,只是其次生价值,其直接而现实的意义是民族文献、民族志记录。
历史来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来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又一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兴“国家体系形成”的更为伟大的历史时刻,这是“民族纪录片”再次得到巨大发展的历史节点。事实也正是这样,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话说长江》《黄河》《舌尖上的中国》《乡愁》《走遍中国》以及大量的中国各少数民族纪录片引发的巨大反响,在某种程度上远超同期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人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大地、民族风情的记录,已不只限于过去“民族志纪录片”“人类学电影”中的奇风异俗、花花草草、唱唱跳跳、古寺古庙,而深化为对民族文化、人文情感的深层叩问,诗意情怀细腻到“舌尖”的体悟、“走遍”中华大地,充分表达出一种悠悠“乡愁”。这些作品有如“风信子”一样,昭示我们可以远瞻预设的未来,伴随“中国梦”的伟大征程,“民族纪录片”大有希望、天地广阔。
二、“民族纪录片”的“国家传统”
《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的作者阿兰·巴纳德说人类学或民族志电影写作一般沿着这样两条线路发展:“按照截然不同的国家传统间发散的和汇聚的影响线索发展”“基于国家的传统的因素”发展。*[英]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我国繁荣如此的“民族纪录片”之所以取得今天如此巨大的成就,并有如此极具民族特色的面貌,正是它不但广泛吸纳了“国家传统间发展的和汇聚的影响”,更是对我国4000年古国、古老的民族书写的“国家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到陕西的蓝田田人、周口店的北京人、广东的马坝人、湖北的长阳人、山西的丁村人、北京的山顶洞人、广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资阳人等等的发掘,这是考古学描绘下的中华民族相沿170万年的发展图谱。中原的炎帝族、黄帝族,北方的狄人,东方的夷人,南方的九黎、三苗等等,这是中华民族神话记忆中的民族世界。族群聚居的地区称为“方”,甲骨文中留下了上百个“方”字,这是远古族群聚居的地缘态势。商周以拥护“天下共主”的联盟的形式,举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面“民族团结”“民族统一”的旗帜。巨大的历史惯性、文化认同,使中华民族超稳定性地始终保持“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就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传统,酿成中国特有的、数千年一脉相承的、代代修史的“历史书写”传统。其中“民族书写”始终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二十四史》的《四裔传》《魏书》《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元史》直至《清史稿》等,都记述了众多少数民族建立王朝的历史。《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蛮书》《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地方史志,以及数量大得惊人的历朝历代文人的笔记、文集、诗词、戏剧中都记载了少数民族的历史、民俗、文化、宗教、艺术等等。周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史官中更设有专事“民族书写”的所谓“掌邦国之志”的“小史”(《周礼·春官·小史》)。这部小史书写的“邦国之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志”……这一切做法不但保留了珍贵的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文献资料,更结晶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书写”的“国家传统”——“史志”。
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使中国陷入落后挨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为救中华,针对中国所面临的民族问题,借助西方以研究欧洲民族为对象所产生的民族学思想,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五族共和”的主张。1926年,时任国民政府高官的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第一次将“民族学”这一学术概念、人文思想写入中国的辞典。1928年调任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长的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专设民族学组,组织人员对广西的瑶族、台湾的高山族、黑龙江的赫哲族、湘西的苗族等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进行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推动其他省区以及燕京、清华、云南、四川等地的大学也开展了民族研究。其间,配合民族学田野调查,同时摄制了不少影像资料,编成了中国影视民族学片史上的第一批作品,中国本土的第一批装备有电影摄影设备的民族纪录片艺术学家也应运诞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个:其一是人类学博士凌纯声。1933年他与同事芮逸夫、勇士衡等受中央研究院派遣,前往湘西,后又到云南进行苗族、瑶族等民族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学电影拍摄。他说:“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欲知苗族生活的真相,非借标本影片不足以表显,多方采购标本,及摄制影片,正所以求真而保存其特质也。”*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其中给出这样一种重要的创作思想:科学求真,应摄制标本电影。很明显这是科学家的眼光。与此同时的另一条创作路线是由以郑君里为代表的电影艺术家开创的。1939年4月,为抗日救亡,郑君里作为国民政府派遣的“西北抗日救亡宣传队”的成员,来到西北,沿途拍摄了意在报道西北和西南地区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彝族的风土人情、宗教活动、支援抗战为内容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其在《我们怎样制作“民族万岁”》一文中阐释自己的创作思想是在“保存被摄对象的真实神韵”的前提下,“对实际事物加以创造的戏剧化”。*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又见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就这样,凌纯声以“科学求真”为目的的“标本电影”的品相,郑君里的“对事物加以创造的戏剧化”处理,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继二十四史“史志写作”后的又一影响巨大的民族志电影的“国家传统”。这是我国后来的“民族纪录片”最早的母本。
1955年配合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摄制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云南就有《佤族》《独龙族》《景颇族》《苦聪族》《纳西族》《永宁纳西族阿注婚姻》《怒江——一条迷失的峡谷》。很明显,这些作品虽也强调“科学目的”,但是更偏于民族“社会历史”的宏观透析,所以大多数作品的视野落在对整个“族”的社会性质、历史发展、人文特征、信仰倾向等的实证性发现与记录。就是由于这一原因,使这些作品至今仍为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所珍重;而且作为一大“国家传统”来说,这批作品有如一座桥——一头血脉相连的是从《二十四史》时代的“史志实录”,凌纯声的“标本电影”的“传记式民族片”,郑君里的“创造的戏剧化处理”的时政纪录报道;一头是今天的“民族纪录片”。从中我们看到要真正过渡到今天的“民族纪录片”,光靠上述的“史志实录”的“纪实”、“标本电影”的“求真”、“戏剧化处理”的“求艺”还不够,还欠一大后来才真正完善强化起来的“大众传播”的“新闻性”元素。
有人统计说,仅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以来“共摄制长纪录片239部、1506本,短纪录片2007部、共3632本,新闻期刊片3528本。”*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尽管其特点被不无片面性地概括为“形象化的党报”,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些作品在歌颂新中国、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事业中起到了极为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为我们认识一个“新国家体系的形成”留下了不朽的“时代的日记”“民族的相册”。是的,到了电视技术在中国大地大普及的20世纪80年代,电视纪录片成为影视世界“天下第一”的片种。其作品题材遍及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其作品类型多得只能用“风起云涌”来加以泛化表达。其核心品质与文化力量来自作为“时代日记”的新闻性,源自“民族相册”的庄严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点——国家日记的新闻性,民族相册的庄严性,构成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纪录片”新的“国家传统”。如云南纪录片导演范志平在拍摄《甲次卓玛和她的母系大家庭》时跟踪多年,记录下被人誉为女儿国的云南丽江泸沽湖摩梭人的一个家庭的生活变化与村寨变迁。郝跃进的《最后的马帮》、孙曾田的《最后的山神》将记录视点切在一南一北两个民族进入现代社会这一“历史节点”时刻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心理的、文化的、信仰的变革上。其具有人类学、民族学“标本电影”的品质,更具有强烈的新闻纪录片的冲击力与时政意义,其“两栖性”,使这些作品既为“影视人类学”点赞,又为新闻纪录片世界所推崇。
三、“民族志诗学”的建立与我国“民族纪录片”的艺术创新
1984年10位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志电影的学者、艺术家会聚美国新墨西哥州召开题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的研讨会,最后汇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民族志诗学”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
何谓“民族志诗学”?西方学者将其定义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等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代译序第6页。面对我们在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中壮势发展的民族纪录片,我以为对国外的“民族志诗学”进行积极的梳理与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志诗学”,或说是“民族纪录片诗学”,这对推动我国民族纪录片的发展应有着积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其一,“写文化”意识的确立。《写文化——民族志诗学与政治学》一书,将“写文化”置于主标题位置,而“民族志诗学”倒只作为副标题出现,这一“词位”排列,给出这样一个信息:“写文化”是“民族志诗学”的首要精魂。持这一观点的不只是这10位提交论文的学者,而是当时学界的一大“历史共识”。英国学者奈杰尔·拉波特等在其《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提出人类学的本质就是“写文化”。*[英]奈杰尔·拉波特等:《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如何写文化?“殖民主义上升时期”的人类学或民族志基本上将西方殖民者的“他者”眼光,在他们的学术眼光里,或“电影眼睛”里,看到的是殖民地的原始、落后、愚昧。1974年,美国学者斯坦利·戴蒙德出版了《寻找原始人》一书,提出要拯救“西方世界的危机”,只有“向原始人学习”。*叶舒宪等著:《人类学关键词》,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原始人的挑战》的作者罗宾·克拉克等更把“高贵的原始人”看作照见西方文明危机的一面“高尚的镜子”。*叶舒宪等著:《人类学关键词》,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但不管怎么说,上述这些还是“他者”眼光。相比之下,真正以平等科学的眼光,很好地建构“写文化”的是中国。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影视人类学研究室,自组队伍,自主创作,如赴贵州摄制了苗族文化系列片《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苗族的工艺美术》《苗族的节日》《苗族的舞蹈》。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1983年拍摄的《白裤瑶》以及17个民族的近40集民族纪录片,其“文化志”特征异常鲜明。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八九十年代摄制的《白族》《迪庆藏族》《泸沽湖的母系亲族》《阿佤山纪行》《独龙掠影》,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瑶族壮族纪录片,云南电视台摄制的《走进独龙江——独龙族及其生存环境》《甲次卓玛和她的母系大家庭》《山洞里的村庄》《最后的马帮》《澜沧江》等明显以“写文化”的哲学意识、“文化志”的历史情怀来把握题材。有意思的是,尽管科研所与民族大学的“学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作品冠以“学术”的名谓:人类学电影、民族志电影,但电影厂、电视台、音像公司的编导们却把原先的“民族志”片的“志”字换了个新闻体裁命名,称作“民族纪录片”。两股力量都在“写文化”,都或多或少共用影院与电视台这一平台播映。“写文化”的传统源起20世纪80年代,至今30余年,已铸成中国“民族纪录片”的一大“国家传统”,已酿为中国“民族纪录片”的一大文化奇观。
其二,“文学转向”的美学选择。英国学者拉波特说 :“文学转向”成为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写作的“一项当务之急”。他观察到通过“文学转向”,人类学、民族志写作出现了这样一些新变化:“人类学逐步摆脱了埋头于对‘他者’进行天真的不偏不倚的分析的企图”,从而表现出一种大别于以往作品的“创造性和美感”,为此,他甚至把这种作品称作“文学人类学作品”“乡村的牧歌”。*[英]奈杰尔·拉波特等:《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这一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写作的“文学转向”在中国引发的反响,如下:一是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文化人类学小说”。如贾平凹的乡土小说《晚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高行健的《灵山》,姜戎的《狼图腾》,赵宇共的《走婚》《炎黄》等等。另一“文学转向”即影视纪录片中明显的文学意趣的强化。且不说《话说长江》《黄河》《话说运河》等的文学散文式的解说词的引入,就是“民族纪录片”也常以散文、散文诗或戏剧化、故事化的方式构筑作品。例如纪录片导演乔丹,为拍好藏族题材录片,这位艺术家长期深入西藏,自学藏语,她创作的《贡布的幸福生活》(1999年)和《老人们》(2002年)的浓郁的“文学性”,被评说家誉之为有一种西藏圣地赋予的“赞美诗气质。”*朱靖江、梅冰:《中国独立制片档案》,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再如云南电视台导演魏星编导的《学生村》,记录的是一个云南民族山村小学的生活,作品以兄弟两个小学生为主要记录对象,以极为平常的校园读书生活记录,让人看到云南少数民族孩子的求学之路的艰辛。该作品几如一部“纪实性电视剧一样”,有人物、有故事、有戏剧矛盾,有如一部“人间悲喜剧”。
其三,新闻化走向。人类学,民族志是拒绝“新闻性”的。但是一方面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所给出的内容的神奇、情景的神秘、人文的惊艳,其本身就具有某种程度的 “新闻性”。另外再加上一位美国评论家所观察到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作家“要保住地位就得写出新奇的小说——不但要‘新’,而且要成为‘新闻’。”*[英]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译序,范景中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事实也正是这样,人类学、民族志只有走出大学的讲堂,走出科学院的大门,走向大众,才可能真正获得新生。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学理指引的方向在西方未真正得到广泛采纳,倒是在我们中国找到了另一种集“写文化”“文学化转向”为一炉的“新闻化走向”。最为典型的例子如西藏的“民族纪录片”,其“新闻化走向”已然构成一大传统:1942年出品的大型纪录片《西藏巡礼》,以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吴忠信1939年12月赴藏参加班禅坐床大典的事件为记录对象,展现了西藏的地理风光、风土人情、宗教文化,以及作为抗战后方的西藏人民的活动,其“新闻纪录”的“当时性”十分撼人。《光明照耀着西藏》出品于10年后的1952年,这是随军进藏记者,以积累了几年的镜头素材,最后编辑成功的作品。该作品以巨大的政治热情为西藏的解放、农奴的翻身留下了不朽的影像文献,是人类学、民族学中的“史记”,更是“新闻纪录”在历史第一时间留下的伟大场景。1959年出品的《百万农奴站起来》,记录了平息西藏叛乱和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情况。其片名就有如一个“历史性定义”一样,标明这一作品展现的“历史节点”:西藏农奴制灭亡的时刻。1976年的《西藏高原大寨花》,其中虽多有时政记录的历史局限,但其可贵的新闻记录,同样值得珍视。198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西藏——西藏》《五十年代西藏社会纪实》《西藏今昔》,组合为半个世纪西藏解放、社会变革的“新闻记录”史。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西藏的诱惑》《雪域明珠》,到新世纪独立制片人摄制的《喇嘛藏戏团》《青扑——苦修者的圣地》《天主在西藏》《八角街》《拉萨雪居民》等,尽管其间多有独立制片人特有的“作者人类学”的叙事品格,但是其“新闻记录”的报道功能仍溢于画面。是的,尽管西方学者对中国如此的新闻纪录片走向不一定赞赏,但人们不能不承认,这在中国纪录电影史上,甚或世界人类学电影、民族志电影史上,都是不可忽视的创新。
其四,叙事模式的创新。学人们将人类学,民族学写作分为四种模式:“经验的、解释性的、对话性的、复调的”。说虽然“经验的和现实的,解释性的模式”是长期以来人们公认的“权威模式”,但是随着民族志写作艺术的发展,其“逐渐让位于话语的,对话的和复调的范式”。“对话”是“一个体现了两个主题间的话语交流的文本”,“复调”“是一个不仅给予合作者以独立的陈述者地位,还给予写作者地位的多重作者的乌托邦”。*[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等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96、298页。更有学者说“未来人类学将是各种方法的混合”,是一个“再本土化”即“对本土知识的维护,再发现或创造”*[英]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80页。的创新过程。美国纪录电影史家尼柯尔斯认为世界纪录片叙事模式经历并积累了这样四大模式:“格里尔逊传统的直接表达”;“无须添加含蓄的或直率的解说”的“真实电影,又叫直接电影”;“常以采访的形式进行直接表达”的“以访问为主流的影片”;“把评述和采访、导演的画外音与画面上的插入字幕混杂在一起”的“自省式”,即“个人追述式”或叫“自我追述式”,并说这是“当代纪录片的标准模式”,其特点是“把直接谈话(人物或解说员直接向观众讲话)结合于访问会见中”。*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537页。又见任远编译:《海外名家谈电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第四种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以“主持人”或“嘉宾主持”,甚或以记者的谈话为叙事主体的作品,也即是实施上述“对话”“复调”“混合”“文本策略”的作品。美国的埃里克·巴尔诺没有专门为纪录片定义叙事模式的发展轨迹,但从他为定义纪录片创作者的创作动因与历史贡献而给出的一系列关键词中,可以窥见其对“纪录片义叙事模式”、“结构策略”与“文化战略”的描述,他点赞纪录片作者是“预言家、探险家、报道、记者、画家、拥护者、喇叭手、揭发者、诗人、编年史作者、观察者、触媒者”*[美]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目录。等。
从上述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纪录片”其结构模式与叙事策略既坚守了人类学电影、民族志电影所特有的长期的田野观察记录、历史文献的运用,更集“预言家、探险家、报道记者、画家、拥护者、喇叭手、揭发者、诗人、编年史作者、观察者、触媒者”等的功能于一身,再加上少数民族的“人文秘境”的神气,更使这些作品有着别样的文化色彩与美学情调。如对独龙族的记录,早自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科学文化纪录片”《独龙族》,到80年代的《走进独龙江》《最后的马帮》,2016年的《一步登天》等等,是对独龙族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第一时间的观察与记录。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独龙族》用的是解说加画面的“格里尔逊式”,那么《走进独龙江》则是有解说、有访谈的直接电影式;《最后的马帮》几为“以访问为主的影片”;《一步登天》可视为运用“混合方式”的。
“民族纪录片”的发展于新中国“国家体系形成”之时,定基调于在我中华文化的“国家传统”之中,汲取世界人类学电影、民族志电影的“民族志诗学”的美学沃润,以开放的胸怀、创新的理念,拥抱这一全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国“民族纪录片”天地更为宽广,作为将更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