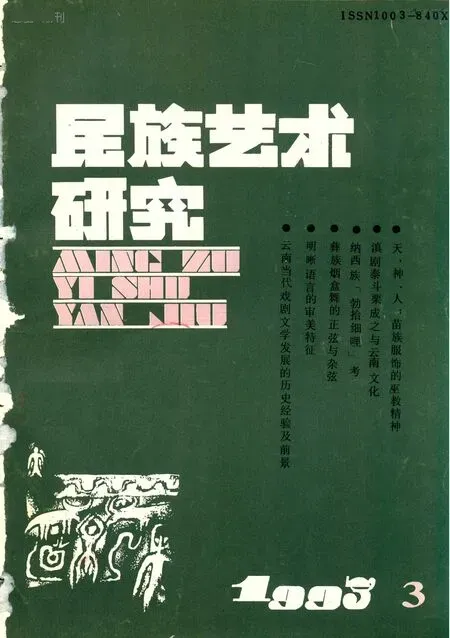单点民族志与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塑:《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的审视与启示
罗 锋,王诗颖
2017年11月1日,首期周播纪录片《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于上海纪实频道开播,每期时长约26分钟。《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延续上海纪实频道的传统与特色,每集择取一个公共空间,采访不同人群此时此刻出现在此地的原因,邀请他们分享各自的人生故事。作为首个以“纪录片”命名的电视栏目,《纪录片编辑室》由上海电视台创办于1993年,在开播之初采用周播模式,直到2002年上海纪实频道成立时改为日播模式。时隔15年之后,《纪录片编辑室》再次推出周播节目《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该栏目采用日播嵌套周播模式。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围绕纪实美学展开的激烈讨论,中国纪实影像的修辞策略与话语形态经历了革命性变化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讲,《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的出现则在时空双重维度上拓展了纪录片的创作边界。这档被外界誉为“中国版《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的周播节目在所采用的影像方法上究竟有何特色?又是如何运用镜头语言赋予上海这座城市以“人文温度”及唤起关于上海的城市记忆的?而与之极为相似的日本版《纪实72小时》,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一、“单点民族志”与公共空间的“细描”
1995年,在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发表关于“多点民族志”一文后,*Marcus, G.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5,24: 95-117.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多点民族志”,其影响力逐渐从人类学走向更为广阔的学科领域,并对纪实影像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周浩的《棉花》、贺照缇的《我爱高跟鞋》这样的独立纪录片,还是中央电视台出品的《舌尖上的中国》和《航拍中国》这样的大型纪录片,都呈现出明显的“多点民族志”特征。然而,在越来越多的纪录片采用多点民族志手法的语境下,《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并未“与时俱进”,而是抽身回归颇具“原初意味”的单点民族志,这使得影像具有浓郁的“怀斯曼”风格同时兼具人类学色彩,而“时间”与“在场”是建构《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人类学风格的两条基本路径。
采用单点民族志手法的优势体现在影像的“深描”功能的发挥上,即通过长时间段的聚焦某一特定时空,从而完成对拍摄对象历时性的建构。但《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将传统意义上无限的历时性压缩至72小时,力图使固定的拍摄时长与从公共空间里生长出来的生活节奏形成一种角力,并不漏痕迹地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捕捉充满戏剧性的情感张力。72小时这一固定时段的设定,无疑在逻辑上给予影像以开放而又多义的结局和想象空间。没有固定的结局,没有人为设定的情感宣泄点,《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的这一特征也使其与其他类型纪录片有了显著区别。如《街角便利店》一集,在便利店角落安静等待孙女的那位奶奶,你不知道她明天会不会来,你更不知道奶奶的孙女明天会不会来,人性中所期望的“大团圆”式的结局没有“上演”,但又绝无悲剧性的遗憾,因为在拍摄的72小时之外,还有明天。这种开放性的期待成为温暖观察的“结局”。
“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结构。”*Kevin Lynch. The Image of the City. MIT Press&Harvard Press,1960: 1.公共空间作为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社会切片般将城市复杂的社会交往划分为一个个“隔间”。生活在具体社会关系中或拥有相似生活经验的人,为满足其一定的生活需求,往往会依托于固定的地理空间形成“类”的划分,从而进一步产生社会性的“类活动”和“类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公共空间往往具有“类属性”。摄像机则如一把切入现实生活肌理中的手术刀,拾取当代生活的一个个样本和切片,从而使人们更加了解一些社会现实背后的深层寓意。*韩鸿:《民间的书写: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对准日常社会交往频繁、具有“类属性”的城市公共空间,蹲点拍摄,在尽显纪录片空间风格的同时,给予观众散文般的观影感受。通过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的镜头呈现出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和最本真的一面。像《我的年终小结》的镜头就记录了一位正在捡拾路边纸盒的阿姨。她已在去年给儿子买房买车。当编导问她明年的期望时,她答道:“18年想给媳妇买家具、买项链,我们就不想了,我们这个年代已经过来了。”再如《培训广场的超级周末》这一集,镜头捕捉到补习班外家长们的焦虑和无奈,“生活刚摆脱贫困,现在生活基本花费都在孩子身上。”因此,像地铁站、便利店、面馆、美甲店、健身房、菜场、理发店、复兴公园、宠物医院、上海书城等这些特定的公共空间,恰似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个“切片”。当众多的城市“切片”集聚在一起时,其影像便折射出社会的多维面相,同时给予观众复杂多元而又充满意味的解读空间。
与单一民族志影像书写通常采用的旁观视角不同,《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采用的却是充满主观色彩的第一人称视角。记录者以提问者角色直接介入公共空间,通过对生活场景并置式的记录,触及城市最为丰富的“神经末梢”,形成对各种事件、各类人物累积式的印象,由此“为观众书写在中国语境下繁华都市中常常被人忽视和遗忘的一角”,从而以影像还原出充满生命张力和现实感的社会空间景观。
二、影像里的城市温度与集体记忆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智利导演顾兹曼这句被无数次援引的话语,凸显出作为历史记忆载体之一的纪录片之厚度与温度。
作为城市的一种镜像,影像勾连起城市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就像巴赞论述的那样,人的潜意识中存在一种“木乃伊情结”,这种情结驱使人们记录自己的生活,把某一时刻的生存状态固定下来,并使之得以再现,即“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 崔君衍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从这个角度来看,《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旨在用影像重塑城市空间,通过展现流动在公共空间中人群的生活剖面,观众得以窥见不同阶层人群的生活百态、人生困境和精神状态,从而感知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与温度,而这均建立在对穿行于公共空间里“人”的关注之上。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对《纪录片编辑室》一贯秉承的价值立场的回拨与重新确认,即“重视呈现生存于不同社会现状中的主体及其生活世界,这些主体不仅包括上海本地人口,也包括跨地区边界的人口。”*徐亚萍:《〈纪录片编辑室〉的口述历史生产与上海的世界主义重构》,《传播与社会学刊》2017年第42期。于是,那些残障人群和外来务工人员的日常生活被平静、不带任何色彩地真实记录下来。
如在《小面馆的美味人生》中,镜头记录下一对特殊父子的生活轨迹。晚上9点,父亲牵着智障的儿子出现在面馆中。面对镜头,这位父亲不断重复的语句是,“要听话,要遵纪守法,让他少吃些苦头”。最后一晚8点,这位父亲再次独自出现在镜头中,“少吃苦头”仍是父亲对于儿子所使用的关键词。《驾校人生》中,镜头捕捉到一位考“C5”驾照的残疾人。面对镜头,他侃侃而谈年轻时追求女生未果的经历。《菜场的日与夜》中,镜头记录了一位晚上9点仍在收拾墨鱼的鱼贩的回忆,“我17岁就来上海了,没本事,一直赚不到钱,干什么都不容易。”《我的年终小结》记录下捡拾路边纸盒的阿姨,“我们来的时候,还没地方睡,就睡在那个公园里。来的那年下大雪,就是刘德华唱歌那年。”另一位裤腿上沾满泥土、从事旧楼翻新的务工者感叹,“17年让我懂得一个道理,人生走到每一个地方都不容易。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带着钱回家见大人和孩子时,人生在世就是为了孩子而活着。”而作为沟通工具的沪语方言在《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中的频繁亮相,则赋予影像独特的审美趣味,这也在本质意义上完整地复活了沃尔特·翁所谓的“生活世界”,即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未经异化的交往体验。*Ong, W.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Some prolegomena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1:295.无论是被访者还是观众,都能够迅速以乡音为基础形成对某城市的认同感。
在拍摄层面,《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主动放弃炫技手法与繁复的镜头调度,而是采用手持设备、平视视角、长镜头、同期声等一系列“返璞归真”的创作手法,关注并还原公共空间的固有温度。作为社会交往和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场所,公共空间早已超越物质空间的定义,而具有场域性的多重符号意义。其自身的空间功能、建筑风格和文化属性等都可成为一种“情境符号”,参与影像叙事,渲染情绪氛围。就像戈夫曼所言的“前台”现象,在特定公共空间中,人们往往会呈现出特别状态。如《城南的渡轮》中,镜头在深夜和凌晨记录下都市人与理想的缠斗和对其的迷茫、放弃与坚守,多种情绪在他们那平静的叙述中流淌出来。《街角便利店》中,一位照顾患癌母亲的青年人面对“工作要紧吗?”的提问时。直言“我妈妈要紧”,镜头随后静默、被拉平、延宕。《菜场的日与夜》中,一位在这买了20年菜的70岁老人,用上海话如数家珍般为摄制组介绍菜农,亲切地叫着他们的各种绰号。《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正是用这些朴实无华的镜头使观众在影像中与另一个“自己”相遇,城市的温度也由此得以升华。当然,《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给观众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温情,还有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
关于集体记忆,法国学者哈布瓦赫跳出传统的生理学与心理学框架,开启了记忆研究的社会建构框架。在哈布瓦赫看来,我们的记忆是“外在唤起”的,我生活于其中的群体、社会及时代精神氛围,能否提供给我唤起、重建、叙述记忆的方法,是否鼓励我进行某种特定形式的回忆,才是至关重要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 、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69页。城镇化浪潮已经将每一座城市裹挟进急速转型与空间重构的洪流中,由城市速度引发的都市焦虑症无不影响着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个体。空间的寄居性和生存状态的不稳定性促使人们更加渴望进行自我价值的确认,而这种确认又往往是通过对于集体记忆的回溯与分享来进行的。大卫·林奇对于城市的观察同样印证了这点,“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印象。它是许多个人印象的叠合,或者有一系列的公共印象,每个印象都是某些一定数量的市民所共同拥有的。”*Kevin Lynch. The Image of the City. MIT Press&Harvard Press,1960: 41.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观照和行走其间的“人”的记录,不啻为观众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印刻着集体记忆的视觉档案。
通过对精心选取的一系列独具上海风味的地理空间的影像建构与城市空间的符号化,《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不断强化其城市集体记忆“寻根处”的社会功能。百年的复兴公园、自1942年开始运营的城南渡轮、27年的富民面馆、20年历史的上海书城等这些老上海的遗迹,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公园里玩”,这句话在《复兴公园》不断地提及与重复。记忆的回溯、建构与传承便在这句话中完成。“我17岁刚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还都是菜地”“以前小时候我妈妈带我渡江,这个摆渡才6分钱”。在这些最平常的交谈中,镜头不仅记录下个体对于旧时光的追忆,记录下城市的变迁,也赋予了其对观众集体记忆的强大的“唤起”功能。《街边的理发店》中,一位从4年级就在这家老店理发的大学生面对镜头谈道,“总觉得这家理发店和外面不一样,毕竟从小就这儿剃了。高中每次月考完一定来这儿剃头。大概觉得月考完,来这儿剃头成绩会好一点。”“我结婚的当天,一大早来这儿定定位,吹好弄好面修好,该结婚就去结婚了。”对于他们来说,理发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它在生命中已具有某种仪式感,并与人生的历史性时刻一同成为无法抹去的个体记忆。《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正是通过讲述这些公共空间里普通人的点滴故事,通过其故事片段式的重组,不断拼凑成一幅关于城市印象的完整图谱。影像的唤起功能无疑为观众调动个体获得记忆深度参与影像解读、形成城市集体记忆提供了某种可能。
三、尚未获得的“沉静”精神
坦诚地说,《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在固定时空内运用单点民族志拍摄手法,是对以往纪录片创作边界所进行的富有想象力的突破与创新。不论《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是否直接模仿日本NHK《纪实72小时》,但两者创作模式上的高度相似,为中国版与日本版的《72小时》对比分析提供了可能,也由此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反观和审视我们自身的创作实践。
从栏目定位与纪录片形式来看,《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主要借鉴直接电影理念,即在拍摄中“尽量使被拍摄对象忘掉摄影机的存在,摄像机像墙上的苍蝇一样等待非常事件的发生,在剪辑时,尽量不暴露剪辑点”。*罗伯特·C·艾伦:《美国真实电影的早期阶段》,李迅译,转引自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作为一种被动的客观叙事,纪录片影像的张力往往取决于题材本身,如若题材本身缺乏故事性,影片则会显得平淡冗长,这在《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24小时宠物医院》中,大部分采访因缺乏故事性而过于平淡,且又因采访对象同质化而显得冗长。但一只被汽车压断腿的流浪猫却成为贯穿始终的“故事点”,镜头在3天中记录下流浪猫被市民送诊、朋友圈众筹手术费到逐渐康复的过程。人性的温暖经由这次突发性事件得以戏剧性地展现。但《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中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采访屈指可数,充满故事性的突发性事件又“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为拯救镜头语言的叙事性,该栏目扛起“上帝之声”的大旗,使用解说词人为拔高主旨,评判人物命运,意图将画面未能渲染到位的情绪,通过“配音+解说词”模式直接强加给观众。但其解说词的生硬运用,使得画面意蕴与解说词形成错位,因声画关系导致的生硬割裂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观众对城市空间与人物命运的阅读与思考。
日本NHK《纪实72小时》则以固定空间中穿行的长镜头和摇移镜头,促使观众以“第一视角”紧随画面不断靠近拍摄对象,倾听他们的故事。大量长镜头的使用维持了其影像时空的相对完整性,再加之记录拍摄现场全景镜头的运用,《纪实72小时》以娴熟沉静的手法为我们呈现出直抵人心的生命质感与真实感,从而引发人们对命运的感叹。反观《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大多直接使用固定镜头,以静态人物采访的形式建构观点,通过多组采访与空镜头的组接完成影像叙事。某种程度上,这给予受众的观感更像是26分钟的新闻片,而非纪录片。
于是,尽管《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与日本的《纪实72小时》在形式、题材,甚至立意上均颇为相似,但前者镜头没有最终“沉静”下来,使得其在情感处理上缺乏足够的表现力,难以将人性中温暖的闪光点提炼出来。无法“沉静”,问题可以归结为拍摄选址上未过多考究、人物性格塑造不饱满,以及影像叙事节奏未能触及情感的自然宣泄点。例如,同样聚焦街边的吃食店,《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选取的是上海老城区的两家面馆,除开店时间较久和面临拆迁以外,并未挖掘出这一空间中其他深层次的含义,而《纪实72小时》却能够经由店中招牌食物,探寻出食物背后的符号意义。“猪排”在日语中与“胜利”谐音,所以去炸猪排店的客人多是希望在“悲喜交加的一年”中迎来好运。《黄金炸串店》中,因炸串店开在神社旁,且店名中有“黄金”二字,来此地的客人大多希望拥有更多财富。在《荞麦面自动贩售机》一集中,一位单亲妈妈经常带着儿子来吃荞麦面。这位曾经因年少不经事、饱受人情冷暖和生活磨难的母亲,在这里却能感到温暖,因为这里曾在她无处可去的时候接纳了她,正是这里曾给予了她坦然面对困难、坚持梦想的力量。
就人物塑造来讲,《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虽采访众多对象,但其沟通在整体上不够深入,因此无法展现个人独有的性格特点,难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与此同时,众多采访对象的并置,影像叙事节奏过快、无重点,从而影响整体情感的渲染与传达。《纪实72小时》则基于对人物命运的好奇,通过“沉静”的镜头语言,以及对只言片语和生活细节的耐心记录,呈现了一个个鲜活而饱满的生命个体与其独特的精神世界,展现出人性中的复杂性,从而激发观众关于生命丰富性与可能性的思考。如深夜到便利店买打折面包的老渔民,“味园”地下酒吧寻找接纳感的“女装癖”,笑着说出从小被母亲抛弃的“牛郎”等人物,无不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此外,再以时间节点选择为例,《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标注的时间往往只是一个准点时间;而在《纪实72小时》中,时间会精确到具体某一分钟。这虽仅仅是一个细节上的区别,但足以显示日本纪录片工作者的“沉静心态”与“匠人精神”。
结 语
毋庸置疑,《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以颇为新颖的单点民族手法为我们重塑了公共空间,用影像重拾一座城市的温度;但透过影像,我们并未感受到一种“沉静”的美学风格。“沉静”之缺席与电视节目急速市场化的逻辑脱离不了干系。其实就《纪录片编辑室》而言,早在2006年左右,采用观察式和参与式拍摄方式、忠实于现场的美学观念已不再具有优越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有效率、更具组织化的制作模式的出现,即强调拍摄前的筹备工作和叙述上的戏剧手法。于是,在提倡效率、生产线化的观念引导下,《唐山大地震》等系列纪录片生产出来,整个制作周期不超过两个半月时间,而《纪录片编辑室》此前单集节目的时间成本会高达一年左右。*徐亚萍:《〈纪录片编辑室〉的口述历史生产与上海的世界主义重构》,《传播与社会学刊》2017年第42期。
置于传媒市场化语境中,我们完全可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心态来观察《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但我们依然应以严苛的眼光来“逼视”它,其本意并非一味指责。作为中国第一个专业化纪录片栏目,《纪录片编辑室》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留存着难能可贵的、纯粹的纪实精神,《人间世》的创作过程便充分体现了小川绅介关于纪录片的经典判断。“时间是纪录片的炼金术”,而在创作手法上试图有所突破的《纪录片编辑室·72小时》,恰恰在“时间”这个要素上失去了耐心。然而,这在另一个维度上给予我们的启示则是,或许在这个愈发推崇技术为王、制作豪华的纪录片“大片化”时代里,饱含丰富生命体验、兼具“沉静”美学风格的纪实影像给予了我们更多的视觉慰藉和心灵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