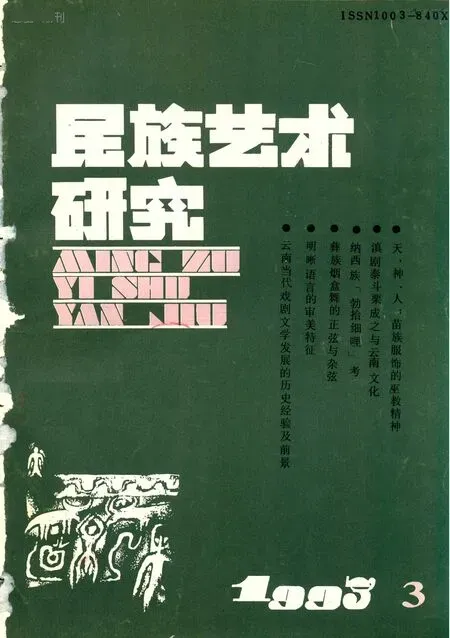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
李世武
艺术人类学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能确认其为科学意义上的艺术人类学。首先,艺术人类学必须在艺术民族志的基础上建构理论;其次,艺术人类学建构的理论必须与艺术考古学、艺术哲学、艺术史、艺术社会学等牵涉艺术研究的学科所建构的理论有所区别。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舶来学科。对艺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回顾与反思,其目的在于推动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建设。
一、 艺术人类学的历史与研究方法回顾
在19世纪的欧洲学术界,艺术科学由作为记述角度的艺术史和作为解释角度的艺术哲学组成,艺术批评被认为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缺乏客观性而排斥在艺术科学之外。尽管19世纪的人类学家已经将艺术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但那时的人类学家被建构文化进化论的宏伟目标所吸引,并且他们的艺术观念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艺术的人类学研究在古典人类学时期被人类学家们边缘化了。人类学起源于西方学者对西方帝国殖民统治下的原始部落的研究。从广义上而言,尽管19世纪的人类学家忽视了对艺术的专门研究,但是,来自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的原始艺术研究,却从学科交叉的意义上填补了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空白。比如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首次强调将人种学方法用于研究艺术起源的重要性,以他人调查的原始艺术资料为依据,提出了艺术起源的若干规律。*[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19页。再如英国生物学家哈登,在英属新几内亚岛民社会中进行艺术民族志研究,论述了图案进化的生命史。*[英]哈登:《艺术的进化:图案的生命史解析》,阿嘎佐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一位艺术史家和一位生物学家,前者借鉴人种学方法研究艺术起源,后者则亲身调查,用生物学的方法探索了活态的部落艺术。尽管他们有各自的学科立场,我们却可以将其归入艺术人类学家的范畴。学科是人为建构的,各学科之间不应强调壁垒,故步自封,而应当互通有无。古典时期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在论述文化传播时也涉及了艺术传播的问题。传播学派将世界艺术的起源归因于西方,忽视了非西方民族的艺术创造力。
现代时期的艺术人类学,逐渐由人类学的边缘走向中心。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开拓者马林诺夫斯基从功能主义的立场研究艺术,*[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弗思注重原始艺术的社会结构。*Raymond Firth,Elemen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London: Routledge,1963,PP.156―159.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中也有不重视艺术研究的学者,如拉德克里夫-布朗,在研究安达曼岛人时,将那些明显具有艺术特性的文化样态归入技术文化的范畴。艺术首先是技术,但并非所有的技术都是艺术。现代人类学中真正对艺术持有浓烈兴趣并作过系统化研究的人类学家,是美国历史特殊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博厄斯以实地调查的丰富材料为基础,对古典人类学时期夸大文明民族与原始民族之间思维过程的差异性观点进行有力地反驳,并且强调对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视。*[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古典时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是将原始艺术作为艺术不发达阶段的产物来研究的。当时的学者之所以研究原始艺术,目的在于以文化进化论为参照,建构出艺术进化论的理论模型。然而,现代人类学家发现,那些殖民地的所谓原始艺术,并不能代表西方最早的艺术。博厄斯的研究,用艺术相对论的观点,有力地驳斥了艺术进化论。必须肯定不同民族的艺术所具有的创造性和价值,不能用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歧视非西方艺术。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研究,突出表现在对面具的结构主义分析方面。*C.Lévi-Strauss,The way of the masks,trans. S.Modelski, London:Cape, 1983.
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于1981年出版的《艺术人类学》,是人类学历史上第一部以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名义确立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著作。莱顿主张,艺术人类学的学科目标是研究小型社会中的艺术。*[美]罗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靳大成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实际上,艺术人类学还有更大的野心,就是在跨文化的范畴内研究艺术,从非洲部落到西方大型工业社会,都有艺术人类学家在做研究,如美国人类学家马凯对视觉艺术的研究,几乎涉及了人类社会的主要类型。20世纪晚期的艺术人类学界,开始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产生了强烈的反思意识。特别是关于艺术的跨文化审美研究问题,更是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James F.Weiner,“1993 debate Aesthetics is a cross-cultural category”,Key Debates in Anthropology,Tim Ingold (eds.), New York:Routledge,1996,P.225.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西方艺术人类学界开始意识到现代西方美学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话语殖民。如果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不过是由那些有意或无意地携带着西方美学观念的人类学家在非西方社会中开展田野调查,并用西方现代美学观念解读非西方艺术,那么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不过是在扩展现代西方美学的经验,不过是为现代西方美学增加更多的个案式注解而已。艺术人类学走向了反思的时代,这种反思意识使艺术人类学界对自身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这种焦虑除了来自西方现代美学的话语殖民之外,还来自于人类学家对地方知识的理解困境。吉尔兹提醒我们,人类学家并不能和当地文化持有者拥有共同的感知,只能拥有一种游离的,近似的感知。*[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5页。如果说我们不能在艺术研究中和当地人拥有相同的感知,那么我们如何能准确地描述出当地人的艺术经验呢?当我们为他者的文化样态贴上“艺术”的标签时,即意味着我们是在用自身的经验描述他者的文化样式。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推演下去,未免过于悲观了。因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类的推论结果,*庄子:《庄子》,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8页。撼动的不仅仅是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论基础,而且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如此推论将陷入不可知论。艺术人类学必须明确自身的立场,他者的艺术经验并不是不可知的,而是必须通过深入的田野工作才能准确加以描述。所有的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都是在不断接近事实。如果事实已经被彻底揭示,那么科学研究也就走到了尽头。实际情况是,科学研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0世纪晚期以来艺术人类学界的方法论反思,开始表现出对现代理性的怀疑和超越。这场学术反思已经拉开序幕,即意味着艺术人类学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期。事实证明,反思是促进创新的必经之途。英国人类学家盖尔的遗著《艺术的能动性:一种人类学的理论》,即是这场学术反思过程中产生的重要成果。*Alfred Gell,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Oxford: Clarendon,1998,PP.1-7.盖尔为了避免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成为现代西方美学的附庸,主张彻底摒弃美学传统,转而研究艺术与能动性的关系,在艺术人类学乃至艺术史的研究中,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盖尔的观点也受到了资深人类学家的批评。莱顿和墨菲都不认同他的观点。很明显,盖尔是因艺术人类学长期受制于现代西方美学的束缚之中,是在几近窒息的状态下提出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视角。在艺术研究中,无论是西方艺术研究还是非西方艺术研究,彻底摒弃美学视角或以审美为中心,都是极端而不符合事实的。因此,艺术人类学有必要向现象学的视角转向,摒弃那些在特殊背景下建构起来的艺术理论,比如西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确立的现代美学理论,让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回到人类的生活世界,深描人类社会中丰富而多样的艺术经验,应当成为艺术人类学方法论转向的突破口。
二、 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一)打破学科壁垒,走向学科交叉
艺术人类学不应成为西方艺术概念和范畴的附庸,而应该不断向这些概念和范畴发问,揭露其语境化的本质。*Howard Morphy,THE ANTHROPOLOGY OF ART,C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Tim Ingold (eds.), New York:Routledge,1994,P.678.按照学科发展史,人类学分化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因文化范畴细化研究的需要,又分化出法律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因此,艺术人类学处于人类学学科的第三层。艺术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然而,因细化研究文化有机组成部分而分化出来的学科之间,不应形成壁垒。在艺术研究中,尤其是非西方艺术研究中,审美中心主义是一种亟待超越的误区。大多数传统艺术与宗教、医疗、历史、认同、道德等都发生了联系。“人类学家所建构的现实不是零散的现实,而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类的活动与创造不是被视为互不相关的个体。”*[美]马凯:《审美经验:一位人类学家眼中的视觉艺术》,吕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页。因此,艺术人类学必须与宗教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族群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等学科形成交叉关系,才能建构出整体性的艺术经验。除此之外,人类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亦可加以借鉴。艺术人类学是自由而开放的现代学科,随时准备吸纳新兴的知识体系,以拓展自身的研究视角。
(二)回归语境,探索艺术多样性
艺术人类学面临的一个核心理论难题,是艺术的定义问题。欧洲艺术的定义主要是体制论(institutional)的定义、以事物属性为依据的(in terms of attributes of the objects)定义和以目的(intent)为依据的定义。*Howard Morphy,THE ANTHROPOLOGY OF ART,C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Tim Ingold (eds.), New York:Routledge,1994,P.651.实际上,目前根本不存在跨文化意义上公认的艺术定义。首先,很多传统社会中不但没有艺术的概念,更没有将某类形象定义为艺术的习惯。其次,即使在有艺术概念的社会中,艺术的定义也是受语境约束的。在艺术学理论非常发达的西方社会,对艺术定义的争论依旧喋喋不休。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不必纠缠于艺术的定义问题。艺术人类学要认清的基本事实是:艺术概念是学者建构的;我们必须警惕将某种既成的艺术概念作为权威概念强加到研究对象上。以目前学界对艺术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还不足以建立一个跨文化意义上公认的艺术定义;艺术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样态,将不断挑战既有艺术定义的准确性。因此,只能在特定的语境中确定一个特定的定义视角。必须特别警惕将某种审美中心主义或形式主义的艺术观念强加到研究对象上。对事物的定义,其实隐含着我们的研究视角。例如,我们所定义的神话和传说,在很多无文字社会中,都属于历史的范畴。文化持有者相信这些口头传统叙述的内容是真实的。但对于我们而言,这些叙述是虚构的。因此,我们将其列入文学的文类之中。艺术的定义亦如此。当我们用某种纯审美的、形式主义的或者感性、虚幻的视角将他者的文化样态界定为艺术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文化样态是神灵的象征,是沟通鬼神的方式,是记录历史的媒介,是建构道德的途径,是一种传统医疗手段,是完整的劳动过程的一部分,是古代统治者的政治谋略……始终认识到艺术是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采用经验实证的方法研究艺术,是艺术人类学存在的合法性依据。艺术人类学理应在人类艺术多样性研究方面贡献出自身的力量。
尽管艺术人类学有研究世界艺术的学科追求,并且像马凯这样的人类学家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可喜的成就,但是,艺术人类学面临的更为紧迫的任务是研究那些被其他学科忽视的艺术现象。艺术人类学承担着保护艺术多样性的使命。保护艺术多样性,就是将艺术相对论作为基本原则,反对在各民族艺术之间划分出等级,反对在艺术研究中持有包括西方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精英艺术中心主义和都市艺术中心主义等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必须平等地看待各民族、各时期的艺术。在艺术人类学的视角下,艺术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因为艺术经验是不可复制的,是依赖于语境的,作为艺术理论呈现的艺术经验,则是学者建构的。古典时期,甚至在现代和后现代时期,一直存在从形式角度评价艺术优劣的传统。这一评价机制在跨越文化语境之后,就面临很多问题。不仅不存在没有艺术的民族,而且没有一个民族的艺术是简单的。局外人之所以认为某一民族的艺术是简单的,要么是在跨文化比较过程中忽视了语境的重要性,要么是割裂了艺术形式与艺术意义的密切关联。在跨文化比较中,不能被表面的相似所迷惑,必须对文化差异进行深度解读。被西方艺术哲学贬斥传统民族艺术,应当成为艺术人类学优先研究的对象。这些艺术往往是不为了审美静观而创作、流通和接受的,对传统民族艺术的研究也就不仅仅具有美学价值。社会、历史、宗教、心理、民族、审美、伦理、医疗等都可能与传统民族艺术相关。建立自由而开放的艺术人类学,用艺术人类学独特方法研究传统民族艺术,就是对其他学科的一种贡献。
(三)继承文化整体观,坚持世界意识、跨文化比较研究和田野工作方法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经验性极强的学科。无论是古典时期注重第二手资料的研究,还是现代以来对田野民族志方法的运用,都表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不是某种玄思,而是一门从事实中建构理论的学科。理论的阐释力取决于事实的可靠性。因此,艺术民族志应该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尽管后现代时期的艺术人类学已经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起陷入了表述危机;尽管在艺术人类学内部,盖尔的能动性理论依旧不乏拥护者,莱顿依然坚持视觉交流的视角,墨菲等依然专注于跨文化审美、本土美学的研究,甚至审美人类学已经自成格局。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总结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人类学研究所留下的遗产。
古典人类学留给后世人类学的两种遗产,其一是文化整体观的确立。人类学文化整体观要求人类学研究将文化视为一个复合体,强调文化各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西方现代美学最为致命的缺陷在于将文化经验化约为艺术经验,再将艺术经验化约为审美经验。这种不断化约的方法,固然可以细化研究对象,不断接近微观研究;但是,割裂了艺术经验、审美经验和文化经验的联系,忽视了艺术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联,使现代西方美学走向了远离人类生活世界的狭隘境地。唯美主义、泛审美主义、形式主义等思潮的出现,其源头即此。当代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必须注重在文化整体观的宏大视角下研究艺术。古典人类学留下的第二种遗产,是世界意识与跨文化比较研究。古典人类学在全球范围内搜罗资料,在人类进化史上思考问题,使得人类学的学术格局非常大气。尽管后现代人类学反对宏大叙事,但走向地方主义、琐碎叙事的艺术人类学,是无法对世界性的人类学艺术经验研究做出贡献的。艺术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原始艺术、部落艺术、无文字社会中的艺术、小型社会中的艺术或乡村艺术,艺术人类学必须具有世界意识,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美]马凯:《审美经验:一位人类学家眼中的视觉艺术》,吕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6页。
现代人类学留给后世人类学的遗产,主要是田野工作方法。田野工作方法是艺术人类学家撰写理论研究之基础——艺术民族志的科学方法。我们始终相信,只有通过实地调查才能获得真理。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艺术和他者的艺术中,都蕴含着丰富的艺术经验,无论他者的艺术经验与我们的艺术经验之间有多大的差异性或相似性,艺术人类学的首要任务是作为他者艺术经验的翻译者。艺术人类学家在开展田野工作之前,一定要尽可能地将自身成长经历中通过书籍、数字媒体或闲谈获得的艺术经验清零,摘掉有色眼镜,谦虚地进入他者的生活世界。把那些从经典书目中阅读而来的中西方艺术学理论悬置起来,面向他者艺术经验本身。如此,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中,深入观察当地人创造艺术、接受艺术的全过程,以当地人的身份体验这一切,才能融入当地社会,出色地完成艺术翻译者的使命。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中,自以为是的观点、对家人的思念、当地人的态度、突发事件的降临等,总会干扰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但是,艺术民族志的成功撰写始终作为一个目标在远方等候我们。学习当地人的语言,是深入研究艺术本体的第一步。不少艺术人类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绝大部分非西方社会并没有艺术或美的概念,但却可能存在一些相似的概念。我们不应该被这些表面的相似性所迷惑。我们始终承认,概念是受语境限定的;而人类的艺术经验,不但受语境限制,而且具有情境性。例如,持审美中心主义者主张,艺术美的特点在于艺术家在创造艺术品的过程中伴随着愉悦感。这种观点显然不适用于绝大部分非西方艺术。艺术品创造和接受的过程中,所伴随的情感,有无限种可能。对于艺术人类学家而言,在语境和情境中描述他者的艺术经验,至关重要。首要的是艺术持有者的观念和感受,而不是研究者的感受。用研究者的经验替代他者的经验,再将此种越俎代庖的经验扩大为普遍经验,是不可取的。
(四)重视书面文献研究
艺术人类学不应当排斥对书面文献的研究。这是因为:1.书面文献记载了人类学家无法超越时空去从事田野工作的时代所存在过的艺术现象。有的古代艺术至今依然遗留在乡村社会,但大部分古代艺术已经消失。艺术人类学研究完整的历史语境中的艺术,就必须涉及书面文献研究。很多书面文献,在广义上,属于古人写作的艺术民族志。尽管缺乏现代人的学术意识,但此类文本亦是对古代艺术进行的描述,甚至还经常带有评论性和考据性。2.不少无文字社会中的艺术,实际上曾经流行于文字发达的社会中,研究文献,是梳理不同社会中艺术交流史的有益途径。比如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如果不进行书面文献研究,就可能陷入文化沙文主义,认为很多艺术现象都是某一民族所独创,忽视了艺术交流的历史。仅仅依赖文献,又可能被古人所误导。那些带有民族中心主义的描述,必须加以辨析和反驳。中国各民族的艺术不是一座封闭的孤岛,而是多元一体的。3.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冲击,无文字社会将退出历史舞台,文字传统将代替口头传统,成为描述艺术、记录艺术的主要方式,文献研究是未来艺术研究的必经之途。因此,田野工作方法不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唯一方法。当然,我们反对文献田野这种提法。这种提法认为阅读书面文献也是在做田野,混淆了人类田野工作方法与书面文献研究的本质和具体操作过程,是都市学者忽视对第一手资料的获取所持的托词。书面文献和口头传统,都需要比较和辨析。
(五)在主位与客位的交互之间探索艺术事实
艺术人类学主张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研究他者的艺术,但并不意味着摒弃研究者自身的价值判断。相反,后者必须占有重要的位置。问题是,首先这种判断必须以艺术民族志所描述的较为准确的艺术事实为基础;其次,这种判断必须注重历史语境。例如,对于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类学家而言,像巫术这样明显的非理性的信仰,是不应该在现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蛊惑人心的。但是,人类学家的文化批评并不是简单、粗暴的批评,他必须证明,在巫术作为普遍信仰的社会中,其作用为何?巫术又在何种程度上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起作用?再比如宗教人类学对萨满教的研究,当然不是为了在现代社会中推行萨满教,而是将萨满教作为宗教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的宗教形态来加以研究的。在人类历史上,“萨满是世界上第一位医生,第一位精神医生,第一位心理治疗师,第一位宗教职员,第一位魔法师,第一位表演艺术家以及第一位故事的讲述人。”*Christina Pratt,An Encyclopedia of Shamanism,New York: 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7,P.xxiv.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亦是如此。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牵涉大量明显的非理性的信仰,比如神话、鼎、门神、傩、秧歌、端午节画天师、悬艾虎等艺术现象,都是巫术、宗教的副产品。当研究者在乡村社会调查到巫医依靠舞蹈、咒诗、绘画、击鼓、摇铃等可以识别为艺术的文化样态为病人治病时,首要的目的仍然在于描述出巫医以艺术治疗疾病的事实。将艺术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其实践形式就是撰写客观、真实的艺术民族志。然而,研究巫医艺术疗法的研究者并不是巫医本身,亦不信仰巫医建构的价值体系;研究者在研究结束之后,必须返回现代人的理性立场。简单、粗暴地否定明显的非理性的信仰,是机械唯物主义,而非历史唯物主义。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过程就是一种在主位与客位之间不断转换视角的过程。
结 语
研究的范围并不是确定艺术人类学科学性质的关键所在,“因为要断定一种研究是否合乎科学性质,并不取决于它的范围的大小,而是根据它的方法来决定的。”*[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页。无论艺术人类学研究是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研究史前艺术、古代艺术、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还是从地理的维度研究亚洲艺术、欧洲艺术、非洲艺术、美洲艺术、大洋洲艺术,抑或是从社会分层的维度研究民间艺术、精英艺术,艺术人类学的研究都必须严格遵守该学科得以相对独立于学科之林的基本方法。第一,在文化整体观的视域中研究艺术。在表演艺术的研究中,注意艺术整体观的视角。将仪式中的雕刻、绘画、音乐、舞蹈、诗歌孤立地抽离出来,贴上某种“门类”艺术的标签,不符合表演艺术的真实存在形态。此种混合型存在形态,对研究者知识结构的要求极为苛刻。第二,尽可能坚持将艺术民族志作为建构理论的基石。不坚持田野工作方法的研究,即使贴上了艺术人类学的标签,其实质却依然属于其他学科的范畴。在史前艺术研究中,学者们使用民族志类推法来重构史前艺术的意义。在古代艺术的研究中,则可对古代艺术在当代社会的遗留进行民族志研究。第三,在涉及书面文献的艺术研究中,实现书面文献研究与田野民族志研究的互动。第四,始终将尊重、理解他者的艺术传统为首要目标,始终明确人类学研究作为文化翻译的追求。在此基础上进行主场经验的描写。第五,悬置作为艺术研究话语殖民的西方美学理论,直面艺术经验本身。第六,与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或人类学之外的学科保持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