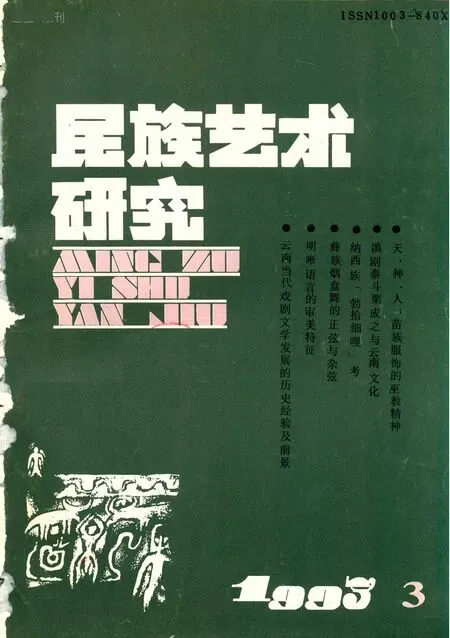舞蹈戏剧构作在中国
田 湉
戏剧构作一词来自德国剧场理论。作为一种手段,它正在被舞蹈编导有意识地引入到作品的创作中,尤其是在舞蹈剧场和当代剧场的创作中。
一、戏剧构作
关于戏剧构作的定义,中央戏剧学院李亦男教授在《戏剧构作:一点回顾》一文中谈道:“戏剧构作(die Dramaturgie)观念与德语戏剧的启蒙主义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不主张孤立地看待文本,将之视为经典而束之高阁,而是强调剧场作品与当下社会的关系,主张从发生在当下的演出的需要重新架构已有文本,或从纪实材料出发自己编创舞台文本,以期用艺术介入现实,在剧院引发关于社会话题的讨论,从而完成戏剧的启蒙任务。”*李亦男:《戏剧构作:一点回顾》,微信公众号:中戏戏剧构作,2016年1月4日。由此可见,戏剧构作强调文本的开放性意义,它的展开往往从概念、构思或是现象开始,体现作品与当下社会的紧密关系,并期冀观众在剧场观演之后能够展开对该社会话题的讨论。就其方式,包括两种:一种是对文本进行重新地架构;一种是从社会采风、纪实和调查出发,编排作品所需的文本。
另外一位对“戏剧构作”有所论述的是上海戏剧学院孙惠柱教授,他曾在《剧作法、戏剧顾问学及其他——论Dramaturgy的若干定义、相关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意义》一文中,谈到对dramaturgy在历史上的三个定义:戏剧评论及理论、剧作法*另外可以提到的是威廉阿切尔的《剧作法》一书,这里的dramaturg几乎和playwright是一样的意思,即为剧本提供意见,或说为经典剧本提供翻译和修改意见的人。、戏剧顾问学。文中作者对这个词的定义趋向于“戏剧顾问”,并指出“戏剧顾问是主要为剧本服务的高级顾问,在中国从事剧本工作的人,就是中国的戏剧顾问。”*孙慧柱:《剧作法、戏剧顾问学及其他:论Dramaturgy的若干定义、相关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意义》,《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他们主要“协助全团的艺术总监或单个剧目的导演,挑选剧目或者找人翻译、改编经典,或者和当代剧作家讨论修改,做研究找材料,还要受导演之托为全剧组的人诠释剧本。”*孙慧柱:《剧作法、戏剧顾问学及其他:论Dramaturgy的若干定义、相关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意义》,《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而另一个词dramaturg则主要指从事“戏剧构作”的人。
对dramaturgy的界定,不论是“戏剧顾问”还是“戏剧构作”,其意义都围绕着剧场“创作”和“管理”在进行。“戏剧创作”包括了创作前期的话题选定及由话题展开的剧场性因素等;亦包括文本、肢体、声音等及其创作过程;而创作之后的“剧场管理方式”又包括了协助导演、艺术总监与外界的沟通交流、组织演出活动等诸多方面。所以,可以看出,戏剧构作者存在于创作前期的筹备、创作过程中以及上演之后的三个阶段,贯穿始终并发挥作用,他既帮助剧场作品探索表达、参与整个创作过程,同时也承担着类似演出经纪人的工作。随着国内对戏剧构作的认识和实际应用中其职能的不断变化,它的概念还在不断被定义的过程中。
追溯“戏剧构作”的起源,第一个明确以“戏剧构作”身份工作的人是18世纪德国戏剧家、美学家莱辛。1976年,德国汉堡国家剧院曾聘请莱辛担任常驻剧院的评论家,莱辛用“dramaturg”一词来指称自己的工作,以此来区别那些不在剧院,通常为报刊做评论的评论家。在汉堡剧院,剧院总监和剧院编剧两者在当时是分开的。戏剧构作在那时被认为是“智者”(wiseman),即智慧的男人。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和剧院院长一起,负责选择戏剧节的剧目、选定剧目的文本修改和翻译、舞台上演员的合理调度和排演,以及与观众、新闻界的沟通等。此后,这个职业延续了两百多年。18世纪到19世纪,戏剧构作的方式连同德国的启蒙主义一起流传到了东欧、北欧等地,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很多剧团诸如柏林剧团,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剧团式的戏剧构作工作方式,戏剧构作人给剧团、剧院提供围绕剧目产生的方方面面的支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戏剧构作也传播到了美国,“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戏剧构作专业均以德语国家模式为蓝本,极力提倡戏剧的社会责任感与教育启蒙意义,对美国主流剧场的普遍商业化倾向进行反抗。”*李亦男:《何谓戏剧构作》,微信公众号:中系戏剧构作,2016年10月13日。戏剧构作向亚洲的传播与发展,直至两年前开始有了热度:“2016年,亚洲戏剧构作协会(Asian Dramaturgs’Network, ADN)成立。在同年4月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年会上,这个词的汉译成为了第一个议题。”也是在这个会上,由于几种不同的汉语翻译方式都无法涵盖Dramaturgied 含义,所以一致同意直译为“戏剧构作”。*李亦男:《何谓戏剧构作》,微信公众号:中系戏剧构作,2016年10月13日。
如果说莱辛的戏剧构作在于反映现实社会和启蒙思想;那么现代意义上戏剧构作的开创者是布莱希特。德国国家剧院戏剧构作者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方式的定性及其沿用,也是在布莱希特之后。现在德国的各类型剧院中,“戏剧构作承担着参与剧院管理、负责剧目安排,根据排演的具体需要确定导演人选,也直接参与剧目的排演创作并代表剧组在演出期间与观众和新闻界交流。”“戏剧构作者是剧场创作中的研究者和理论家,是剧院院长和导演的重要合作者与对话伙伴。”*李亦男:《何谓戏剧构作》,微信公众号:中系戏剧构作,2016年10月13日。
二、舞蹈戏剧构作
(一)舞蹈剧场的界定
1949年库特·尤斯(Kurt Jooss)建立了福克旺舞蹈剧场工作室;20世纪70年代皮娜·鲍什(Pina Bausch)将舞蹈剧场推向高潮。伴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后现代”艺术的风靡,皮娜·鲍什舞蹈剧场创作中与戏剧构作人的大量合作,才使戏剧构作逐渐成为舞蹈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首先需要对舞蹈剧场进行一些论述。*参见欧建平:《舞蹈剧场:从德国来到中国》,《艺术评论》2012年第2期,“舞蹈剧场,德文Tanztheater,英文dancetheater,这是一种手段高度综合的剧场演出形式,1970年中期开始出现在德国这个有着深厚哲学传统的国度,并与美国后现代舞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慕羽:《中国现代舞者的“舞蹈剧场”意识初探》,《艺术评论》,2012年第2期,“舞蹈剧场既有用某种跨界、跨艺地利用一切剧场表演手段的介于表演艺术、视觉艺术乃至文学的综合剧场方式,也会延伸涉及舞者的身体和剧场空间探索的肢体剧场,他们都强调身体在不断的形式实验中,崭新的表达可能;而且涉足社会话题,关注对人本身的考察、质疑和打造。”
本文尝试对“舞蹈剧场”进行界定:舞蹈剧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与媒体社会形态的确立出现的一种新的剧场形式,代表人物是德国舞蹈家皮娜·鲍什。舞蹈剧场围绕“剧场性”展开不同元素的话语形式,肢体、声音、装置、光影、多媒体投影等一切元素都围绕剧场展开,其中肢体表达与声音、说话、装置等元素在舞蹈剧场中处于同等的地位,而非高于它们或像传统舞蹈、舞剧表达中的以专业舞者身体为主体。展开舞蹈剧场的方式多是“多元”(diversity)且“跨界”(cross-boundry)的;各种跨界剧场元素被调用,同时为剧场服务。这里的剧场是一个空间(theater)概念,而非一种戏剧(drama)艺术形式的概念。
如前所述的“舞蹈剧场”这一概念的确立和使用打破了传统舞蹈作品的创作思维模式。就目前来看,当一个作品演完,观众对照过去的观看传统舞剧和舞蹈作品的经验,产生“这是舞蹈吗?”的质疑,那这个作品很有可能是“舞蹈剧场”或说是带有剧场性质的舞蹈作品;反之,观众仍在欣赏其中优美的肢体表达,作品仍在传统舞蹈创作路径中发展,这个作品则不是“舞蹈剧场”的作品。皮娜·鲍什所改变的,就是把从前我们认为不是舞蹈的那些东西放进了舞蹈创作和剧场空间中。正如“后戏剧剧场”中对“后戏剧”的定义那样:“只有在语言之外的剧场手段跟文本处于平等地位的情况下,从每个系统而言,没有文本也是可以想见的情况下,才朝着后戏剧剧场迈出了一步。”*丁柳:《论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去文本倾向》,《中国戏剧现状论坛》2016年第1期。所以,只有在传统舞蹈语言之外的剧场手段跟肢体(传统舞蹈概念中的肢体)处于平等地位,围绕“剧场”这一空间概念展开创作,并运用其他各种手段进行表达的情况下,“舞蹈剧场”才会出现。
由此,舞蹈剧场的特点大致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舞蹈剧场中的舞蹈/肢体与其他“非舞蹈”因素并存,且地位一致。文学、说话、唱歌、肢体、哑剧表演、影像、材质、行为、灯光等元素,在舞蹈剧场中是平等的地位。有人将舞蹈剧场的特点总结为“多元”或是“跨界”,就是说多种艺术形式在剧场中会同时被调用。比如,活跃在国内的纸老虎戏剧工作室就将其宗旨定位在:打破常规剧场的界限,使剧场对舞蹈、音乐、装置、行为艺术、民间表演、社会实践、个人问题、流行时尚等方面更加开放……将表演、角色、人物的定义推延到更大的范围内。
第二,不再执着于用专业化的舞者身体,而是转向“戏剧性”的身体和行为性的表演。舞蹈剧场诞生的时代是在“后现代”舞蹈阶段,后现代舞是对现代舞限制的反抗,所以时常用的是非专业舞者、不会跳舞的日常身体。也因此,舞蹈剧场中的舞者常常是非职业的,肢体动作也常常是非专业的,以此区别于传统的、专业化的舞蹈肢体,身体不再以展现技巧为目的。
第三,文本、声音、肢体等元素的出现,是为了打破舞蹈中的限制而存在,并非为了借鉴那些不是舞蹈的艺术形式而存在,即那些非舞蹈的“其他东西”应当具有自身存在的必要性。
第四,舞蹈剧场承担起了对社会现实、社会问题发声的艺术使命,其重要路向之一是将“作品包含于社会行动中”。*丁柳:《论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去文本倾向》,《中国戏剧现状论坛》2016年第1期。舞蹈剧场中所使用的肢体、声响、装置、说话等元素所具有的间接性特征,往往充满了隐喻和暗示。于是,舞蹈剧场中的“场”,便成了社会生态和社会现实的体现,在这些看法、表达和争论的背后,最现实的社会形态,包括不同社会阶层间互相观看的视角都极为真实地呈现出来。剧场中所发生的一切,代表了某种社会行为,每次对观众的演出也都是开放和生动的。
第五,通常情况下,舞蹈剧场的舞台环境设置具有多样性,作品结构方式倾向于碎片式拼接。不是所有舞蹈剧场都依托一个既定的“文本”展开。从皮娜·鲍什的舞蹈剧场建立之后,不同的实践者对舞蹈剧场都有发展和变化。比如中国台湾林怀民的“云门舞集”,它的英文Cloud Gate Dance Theater,如果直译过来就是“云门舞蹈剧场”;而内地的纸老虎戏剧工作室(北京)、组合嬲(上海)、二高表演(广州)等,也都有自身的发展方向,即本文中对“舞蹈剧场”概念的界定。*除了“舞蹈剧场”之外,还有另外两个概念:身体/肢体剧场(physical theater)、动作剧场(movement theater),比如陶冶、段妮的“陶身体剧场”,从身体出发尝试不同的舞动方式,探索不同的创作观念。
(二)舞蹈剧场与戏剧构作
从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来看,莱辛将戏剧构作的名称及其方法在德国建立起来,且作为行之有效的系统在德国剧院创作中不断沿用,而皮娜·鲍什生活在这样一个艺术环境中,两者之间必然是有紧密联系的。也正是欧洲舞蹈剧场的出现,才使舞蹈戏剧构作的功能和身份慢慢得以确立。
也许可以这样厘清舞蹈剧场和戏剧构作之间的关系:舞蹈剧场并不是和戏剧构作同时出现的,舞蹈剧场的鼻祖是皮娜·鲍什(20世纪70年代),而戏剧构作的鼻祖是德国的莱辛(18世纪),但舞蹈戏剧构作这一名称及其工作方式,是经由皮娜·鲍什建立舞蹈剧场之后,才逐渐明确起来的。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皮娜·鲍什的舞蹈剧场与戏剧构作人展开了大量的合作,将舞蹈戏剧构作的作用以及对舞蹈戏剧构作人职业身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又由于德国舞蹈作品剧场性的凸显特征,戏剧构作很快发展为德国舞蹈剧场中的一个专门职业。
与皮娜·鲍什合作最为频繁的是德国戏剧构作雷蒙德·汉格(Raimund Hoghe)。因此也有人认为,雷蒙德是第一个明确地以“舞蹈戏剧构作”参与舞蹈剧场创作的人。在与雷蒙德的合作中,皮娜·鲍什将舞蹈素材收集、铺开,并通过戏剧构作的方式将其重新建构到编舞过程中。所以,狭义的戏剧构作主要指的就是对舞蹈作品进行结构处理。
目前活跃在欧洲的舞蹈戏剧构作人,如德国的托马斯·邵普、凯·图赫曼*托马斯·邵普,曾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戏剧学和舞蹈理论。现为柏林ada工作室常驻评论家,柏林校际大学中心舞蹈部的客座教师。作为舞蹈戏剧构作,他与很多舞蹈编导合作过,并被邀请参与欧洲与加拿大等各大艺术节和会议。凯·图赫曼,本科就读于柏林恩斯特·布施戏剧学院导演专业。自2003年起,他分別在马克西姆高尔基剧院、魏玛德国家剧院等剧院工作。在美国、印度、中国作为驻地艺术家,图赫曼发展和实践了纪录剧场的工作方式,并形成了自己对纪录剧场的新理解。他尤其专注于探索通过纪录剧场开拓替代性类历史编纂(alternative historiogra- phies)的可能性。等,他们大部分人出身于舞蹈理论领域,以戏剧构作的身份参与到舞蹈作品创作中,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断层,使理论和实践产生实际的联系。鉴于欧洲舞蹈理论大部分源自于戏剧理论,多数戏剧构作人会通过对戏剧理论的学习,深化对戏剧构作自身的认识。2017年12月22日,由易卜生国际委员会主办、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承办,在北京德国文化中心举行的“舞蹈戏剧构作的本土化”主题工作坊中,托马斯·邵普指出了舞蹈戏剧构作在参与创作时的两个主要工作内容:第一,结构舞蹈作品,整合编舞中不同段落和碎片式素材;第二,综合其他艺术因素,参考音乐、视觉艺术和当代艺术等多种形式,将其有机融入作品中。*2017年12月22日,由易卜生国际委员会主办、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承办,在北京德国文化中心举行了“舞蹈戏剧构作本土化处理研究”主题工作坊。这是一个有关舞蹈戏剧构作理论与实践交流的内部工作坊,自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1月4日,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举行,德国戏剧构作人、当地舞蹈领域的艺术家、学者们共同参与,就舞蹈创作及其戏剧构作等问题进行交流。北京站由德国舞蹈戏剧构作人托马斯·邵普担任主讲人。
在美国,戏剧构作主要围绕“保留(经典)剧目剧场”存在。它们活跃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剧院和剧场中。戏剧构作人主要承担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内容:第一,“剧目选定”。戏剧构作与剧场艺术总监一起制定每个季度的演出计划。戏剧构作人需要依据2018年可能或潜在的参演群体、观众的观演状况,来考虑剧目的选择。第二,“文本处理”。与导演、演员一起,处理选定下来的剧目“文本”。这需要戏剧构作人充分考虑到合作导演的风格。不同的导演风格,对戏剧构作人的要求会有很大不同。在讨论剧本的时候,戏剧构作人还需要点出导演遗漏或缺失的环节,从而妥善处理剧本的前期翻译、修改、编排。第三,“排演助理”。当创作前期工作完成后,演员在舞台上开始进行排演,戏剧构作的身份就像是导演助理,要配合导演进行场上调度,考虑到声、光、电等与作品本身的配合。第四,“交流与延展”*交流与延展(communications and outreach),这里是针对演出内容本身与观众的交流,而不是与市场的对接。。作品排练完成,将要上演之前,戏剧构作需要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撰写节目册,用自己的话归纳出导演和剧团重现这一保留剧目的意图,需要把这些信息交给观众。而当作品有“演后谈”的时候,戏剧构作人需要主持演后谈,并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熟悉度和理解深度,把观众提出的问题接过来,递给场上的导演或是某个演员,就好像是递球一样,要选对选手。同时,当场上的导演、演员没有回答出观众的问题时,戏剧构作人需要补充这些没有被回答或是没有被回答清楚的问题。*根据2018年1月11日,笔者与舞蹈戏剧构作人庄稼昀就“舞蹈戏剧构作”议题的访谈内容整理。庄稼昀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于洛杉矶加州大学 (UCLA) 获戏剧和展演研究博士学位,Andrew W. Mellon基金获得者。北卡罗来纳教堂山大学戏剧系助理教授;北京舞蹈学院创意学院特聘教授;美国职业剧团 Play Makers Repertory Company 戏剧构作。为文慧的《红》(2016)、江帆的《流量》(2018)等中国多部舞蹈剧场作品担任戏剧构作。也可以说,戏剧构作人是一个全能选手,他们不仅要全程参与作品的创作过程,是创作团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又随时跳出团队之外,在团队之外观察反思,介于两者之间,像镜子一样照出整个作品。
舞蹈戏剧构作在实际参与团队创作时,需要遵循三个工作原则:“激发问题”“抽离与间离”(强调构作过程的流动性)和“普遍性”。这三个工作原则通常由戏剧构作人组织创作组内部成员来完成。“激发问题”是指就创作者的创作意图或某一社会话题,通过戏剧构作人激发提问和小组流动提问的方式,将该问题的核心不断发散,再提炼,最终将其内核显现出来。“抽离化”是指通过小组内部包括提问、回答、干涉等角色的不同分工,来探讨作品问题的各个方面,这种流动式的角色转换,给创作者、创作团队带去不同的思考维度和方式,从而使创作者的创作保持陌生化。“普遍性”原则,是由于创作者总是会强化自身个性的部分,但作品最终是大众在接受,因此需要创建一个共通的东西,即普遍性的东西。
三、中国的舞蹈剧场及其戏剧构作
(一)中国舞蹈剧场
舞蹈剧场在中国的开端,是在20世纪90年代;舞蹈戏剧构作在中国的引入,则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有的,而且它正在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从中国舞蹈剧场和当代剧场的创作现实来看,一部分导演和编导已经清晰意识到与戏剧构作之间合作的意义。比如纸老虎戏剧工作室的田戈兵与克里斯多夫·莱普奇,生活舞蹈工作室的文慧与凯·图赫曼,三种碗合作社的江帆与庄稼昀等。舞蹈编导与戏剧构作人共同完成材料选择、调研、有效问题筛选、文本翻译修改等工作。而另一部分导演和编导,在作品创作的过程中,虽然没有明确地与戏剧构作合作,但实际上是由自己承担并完成了戏剧构作人的工作内容。所以,戏剧构作在中国舞蹈领域的应用还非常新,它主要的生存环境就是在现当代舞蹈作品和以肢体语言为主的舞台剧中,并较为明确地应用于那些被称之为舞蹈剧场的作品中。
作为一种职业,“舞蹈戏剧构作”(dance dramaturgy)在国内尚未形成气候,但可以观察到,有很多导演、编舞和舞者,在作品中都自己承担了“舞蹈戏剧构作”的身份,做着类似“舞蹈戏剧构作”的工作。由于中国舞蹈尚处在“现代”“后现代”“当代”同在、共融的阶段:一方面,一部分先锋实验者们致力于剧场探索,尝试打破传统,用不同的剧场元素对传统剧场模式进行反抗和反思;另一方面,舞蹈戏剧构作在这时也悄然进入到实验戏剧和舞蹈剧场的创作中,推动编导的思考,参与编排过程,辅助作品创作的完成。
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中央戏剧学院李亦男教授翻译的德国雷曼的《后戏剧剧场》一书,这本书对中国剧场导演和致力于做舞蹈剧场的编导产生了一些影响。她在中央戏剧学院为戏剧策划与应用本科生开设了几年的“戏剧构作”课程,其教学成果和作品也以文献剧的方式呈现在舞台上,如《家》(2016)、《水浒》(2017)、《黑寺》(2017)等,在实验剧场创作中独树一帜。戏剧构作理论及其方法被渗透到了舞蹈领域中,被舞者、编导和学者们共同关注和认同。舞蹈编导们开始思考,戏剧构作如何才能参与到中国舞蹈剧场中,使剧场作品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随着舞蹈剧场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戏剧构作的参与性,不少人开始关注戏剧构作的职能以及戏剧构作人这一职业。细数中国舞蹈剧场的艺术实践,很多艺术家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1994年吴文光和文慧的生活舞蹈工作室(北京)、1997年田戈兵和王亚男的纸老虎戏剧工作室(北京)、1997年李凝的“凌云焰肢体游击队”剧团(济南)等;新世纪以来,2005年张献的组合嬲舞团(上海)、2007年何其沃的二高表演(广州);近年来活跃的小珂×子涵的当代剧场(上海),以及2017年江帆的三种碗合作社(上海)等——这些创作团队都致力于舞台表演形式的多样化探索,并带着对社会问题的反思精神,因此,他们接近于,或说就是本文对“舞蹈剧场”概念的界定。在他们的创作手法中,已或多或少地涉及舞蹈戏剧构作本身。
(二)中国舞蹈剧场中的戏剧构作
上述中国舞蹈剧场的创作中,明确与戏剧构作人进行合作的是文慧、田戈兵和江帆。
20世纪90年代生活舞蹈工作室创办,他们探究历史,关切当下,以“报告”“记录”和“回忆”为创作中心,2008年创作了8小时长的关于“文革”个人记忆的多媒体剧场《回忆》;2009年开始围绕“民间记忆计划”创作了5部剧场作品和11部纪录片;2014年以《红色娘子军》为蓝本,整合文献资料、访谈资料,创作剧场作品《红》。在《红》的创作中,导演文慧与德国戏剧构作凯·图赫曼,文本兼戏剧构作庄稼昀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舞台上最终呈现出了具有“文献性”的身体,从舞蹈角度剖析作品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技术创新和审美取向,也对它在特殊意识形态支配下所建构的阶级叙事和这套叙事逻辑下的集体认同进行解读。同时,《红》也将“文革”时期与今天进行对接,一方面探讨那些曾被政治化的文化符号于当下的复制和消费,另一方面也探索隐藏在宏大阶级解放叙事中的女性解放意识在今天的实际意义。*参见《红》场刊内容。由于《红》是以记录剧场的方式对《红色娘子军》的重访,戏剧构作在其中不仅承担着与导演不断碰撞出合理的文本结构的作用,同时,也需要对作品进行文献资料和访谈资料(文字、图片、视听资料)的充分整合。
再有田戈兵导演的纸老虎戏剧工作室,他本人是戏剧导演,他的爱人王亚男是位舞者,两人一人导、一人做舞蹈编排,配合协作,擅与国内独立舞者、演员们通力合作,创作与肢体相关的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剧场作品:纸老虎“装傻”表演展(2012)、《非常高兴》(2013)、《铁马》(2014)、《十诫》(2016)、《从前有座山》(2016)等,他们擅长将现实生活作为材料和剧场表演的结构,把戏剧作为一种进入生活现场的按钮和口实,使剧场表演获得更大的自由和空间。尽管他们的创作并不是用肢体主导舞蹈剧场,而是剧场作品,但他们却明确与戏剧构作合作进行创作。2017年8月,纸老虎在中国首演了剧场作品《500米-卡夫卡、长城、不真实世界图像及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该作品的创作,是由导演田戈兵与戏剧构作人克里斯多夫·莱普奇(Christoph Lepschy)*克里斯多夫·莱普奇(Christoph Lepschy),德国自身戏剧构作人,曾任德国慕尼黑肖伯格剧院、弗莱堡剧院、杜塞尔多夫剧院、斯图加特国家剧院、巴塞尔剧院以及萨尔斯堡艺术节的剧场构作。合作,在对朝代史和港口专家进行社会调研和采访的基础上完成的。戏剧构作人克里斯多夫在了解导演田戈兵创作意图的基础上,给出整体结构和文本编排,使导演和文本之间实现有效衔接。最终,《500米-卡夫卡、长城、不真实世界图像及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由8位中国舞者和3位欧洲演员参演,以卡夫卡小说为出发点,结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大型工程(宁波-舟山港区改造等)的调研,并着力于采访在这些大型工程实施现场的建筑师和工人,记录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通过搜集材料、整理材料、提取材料进而激发问题、结构作品,以剧场表演来探究社会问题。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蹈编导系的江帆,2017年与戏剧构作人庄稼昀(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戏剧和展演研究专业博士)共同创建了“三种碗合作社”,其前身为2014年的前空帆剧场,其团队坚持以充满弹性、开放的创作态度对待剧场创作,该作品中常整合戏剧、舞蹈、影像、新媒体等表现方式,专注社会问题。江帆的舞蹈剧场作品《折影》获2015年上海壹戏剧年度小剧场奖;2016年她将《折影》和《饭桌》共同组成的舞蹈剧场《隔壁》,分上、下两个版本演出于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该作品由肢体、音乐、舞台空间展开,“试图将舞蹈和身体作为过程而非目的,试图让观众不止聚焦于舞蹈动作和演员本身。以非舞蹈化的形体,传达出个体间的关系,以及背后蕴含的社会性。”*好戏mp_cf1.《这部舞台上不开灯的“舞蹈剧场”,又回来了》, http://www.sohu.com/a/114903212_467540,2016-09-22。2018年1月,江帆在“三种碗合作社”中出品了舞蹈剧场《流量》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演出,该作品由庄稼昀担任戏剧构作,运用多媒体投影、直播等结合的方式,触摸了时下流行的直播经济及其展演机制。
《流量》将呈现方式定位在多媒体舞蹈剧场的呈现上,从直播女主播这样一个为大众所熟知的女性符号切入,以多媒体舞蹈剧场和实时直播的方式,触摸直播经济及其展演机制。其作品立意在对直播现象的关注上,为该作品做戏剧构作的庄稼昀认为,“直播现象是东亚小确幸的一种,这种线上的观演模式和表演机制逐渐建立起了庞大的产业链条,作品也是从这里找到了生发点。比如直播一个节目、一个活动、一堂课,或是通过直播推销衣服、鞋子等等,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生产消费系统。国内大量的年轻人选择把时间消耗在直播上,填充无聊的时间,作品中有句词‘无聊就是生产力’,讨论的就是这个现象。”*根据2018年1月11日笔者对庄稼昀语音访谈的内容整理。
作为戏剧构作,庄稼昀一方面要对导演江帆的个人体验有深入了解,做田野调查搜集,进行材料的反思和整理,在此基础上撰写文本;另一方面,还需要对编导江帆的舞蹈语汇有一定的熟识度,了解她的运动方式以及其行动中潜在的动机等,这样在撰写文本的时候,就能较为自如地把舞蹈可以发挥的部分标注出来。比如作品中有关“自拍杆”的段落,前期戏剧构作与导演在排练厅里先进行动作实践,发现它的可能性,进而补充文本,再在反复推敲文本之后返回到排演实践中,两者在互动中推进发展。而最后文本的呈现,实际带着戏剧构作人对作品核心——直播现象的态度和理解。庄稼昀坦言,在作品创作过程中,戏剧构作人作为导演的辅助工作者,常常会与导演发生来自各个方面的矛盾,如果这个矛盾来自导演个人的审美喜好,戏剧构作人就需要将作品需求摆放在第一位,通过客观判断来修正导演个人化的那个部分。所以戏剧构作是一个能够将文本与导演特点衔接的人,也同样是一个擅于徘徊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将编导个性与观众“普遍性”进行调节平衡的人。
此外,小珂×子涵的当代剧场也活跃在上海。2017年的《Dance Deco Co》在上海明当代美术馆上演,这是在2015年剧场作品《Dance Deco》基础上的深入发展。作品“旨在运用舞蹈中的传统元素调制一出不仅仅是舞蹈的身体反思”。*上海明当代美术馆.McaM表演预告/小珂×子涵:舞蹈剧场《Dance Deco Co》[EB/OL][2017-06-08]http://yiker.trueart.com/20115619/article_item_42968_1.shtml?cid=243小珂早期与张献一同做组合嬲,后来才与她的先生子涵合作做舞蹈剧场作品。他们开拓发展肢体艺术,也寻找贴近中国现实生活的话题。子涵更偏重于对视觉、声音、影像、装置的制作,所以他们一边依旧关注个人身体,一边又打开了舞蹈以外多种艺术形式进行表达,探索在中国公众语境下的表达极限。
还有一些身处体制内,在舞蹈作品创作过程中,较早感知到舞蹈剧场的魔力并进行剧场类创作实验的个人。比如在广西艺术学院编导系执教、同时为广西谷舞典点舞团艺术总监的黄磊,他与香港动艺舞团合作的剧场作品《M事件》曾获得2014香港舞蹈年奖最佳编舞提名以及最佳独立制作奖。该作品由马加爵社会事件出发,编舞从中提取出相关要素对舞者进行发问,经由舞者个人经历及身体经验,转化为一套全新的剧场素材,经过编舞精心重组后,在一个半开放式的特殊舞台空间中呈现出来,令作品由一个发人深思的社会议题,发展成了对人性讨论的舞台作品。
国内还有一些始终活跃在做肢体剧场,却并不是舞蹈出身的导演,比如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专业的李凝。20多年前,他就开始做造型艺术、实验舞蹈、肢体剧场,近几年涉足身体影像。李凝本人并不认同被贴上肢体剧场、公共戏剧这样的标签,他说他要做的是“寻找那些经过社会训练的身体,挖掘、激发其各自的特质,然后将其重新组合、精练和典型化,从而产生出作品。而这个作品可能是表演、舞蹈、音乐、装置、影像、科技等等元素的混合体,不区分类型。”*ART-Q.李凝:肢体剧场不等同于广场舞演出空间,http://www.sohu.com/a/123584237_461398,2017-01-06。
小珂、子涵、黄磊、李凝等从事剧场探索的编导、导演,尽管他们的作品中没有明确运用到戏剧构作,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其实已经完成了戏剧构作在剧场中发挥作用的那部分内容。
四、戏剧构作在舞蹈剧场中的作用和意义
舞蹈戏剧构作给了编导更多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打破了传统舞蹈创作中某种既定的格局;另一方面,依托舞蹈戏剧构作本身的工作方式,它又建立起了新的规则和模式。
狭义来看,舞蹈戏剧构作带有戏剧结构(drama structure)的功能,帮助编舞从理性角度梳理和建立起作品的新格局,检验编舞家那些原本分散的素材,帮助编导建立完整的作品形式。广义来看,舞蹈戏剧构作除了辅助结构作品,还承担了搜集材料、文本处理等创作前期的工作;排练中期协助导演完成剧场各方面的实现;以及作品完成之后节目册撰写、对外宣传等与剧场管理相关的工作。
戏剧构作的工作内容,几乎贯穿在舞蹈创作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但他最核心的参与性仍然主要体现在对舞蹈作品主题的发问、引导和对材料的选择性组织上,因此也有人说,戏剧构作人是一个能时刻对艺术创作提出问题的忠友。他们一边提出问题,带领创作团队将问题发散流动起来,将作品前期的思考带入到未知领域里,带给编导一个更为立体的思考角度;一边把在这一过程中曾经设想到的,但又不切实际的那些“可能性”屏蔽掉,留下那些有意思的、足以推进作品结构的部分,并将这些可行性落地下来。在团队创作过程中,戏剧构作人促使创作者和创作团队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也将艺术创作中的合作者,包括观众与创作者本人置放在更为开阔的位置,进而帮助创作者发现那些隐藏着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作品表达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厚度,通过这种不断叠加和流动的思考方式逐渐建立起来。
此外,戏剧构作人既从观众的角度审视作品,也从艺术家角度参与作品创作。他们在一个可以转换于观众和艺术家之间的中间地带张弛有度,始终在两者间择取平衡。当编导产生一个独特的想法时,戏剧构作需要把它放在更为多元的观看角度和更为立体的文化层面中去考量。尤其在对文本重新整理的尺度把握上,戏剧构作人需要具备调和艺术家个性与社会共性、感性与理性、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能力。大部分戏剧构作人都要承担文本的编写,他们要根据作品需求确立排演主题,之后再依据当下社会现实情状及与作品的关系、剧场观演关系等,对作品文本进行重新“翻译”与“修改”,从而把“过去”的材料、资料、剧本和“今天”的鲜活的社会现实、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将舞蹈戏剧构作人参与作品创作的内容分为“内部”与“外部”两部分,在舞台、肢体、美术、制作等艺术生产的“内部生产”过程,以及创意题材的选择、主题提炼、意蕴书写时,都要带着“普遍性”的思考;因为,舞蹈戏剧构作人的工作内容也包括了实现创意、宣传、营销、推广、作品的衍生品等艺术生产的“外部环节”,需要考虑到“对接”艺术生产的结果,所以“普遍性”要贯穿于舞蹈戏剧构作的全过程中。
当然,戏剧构作在国内舞蹈创作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国内舞蹈编导常常专注于身体的探索,不太重视文本本身,这些“去文本”的舞蹈剧场创作,是否还有导演和舞蹈戏剧构作合作的必要性?再者,大部分舞蹈作品刻意回避了社会性表达,而戏剧构作的德国传统恰恰又擅长体现社会问题。因此,戏剧构作在国内舞蹈创作中的参与意义究竟在哪里?这些,都需要在进一步的实践探索中得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