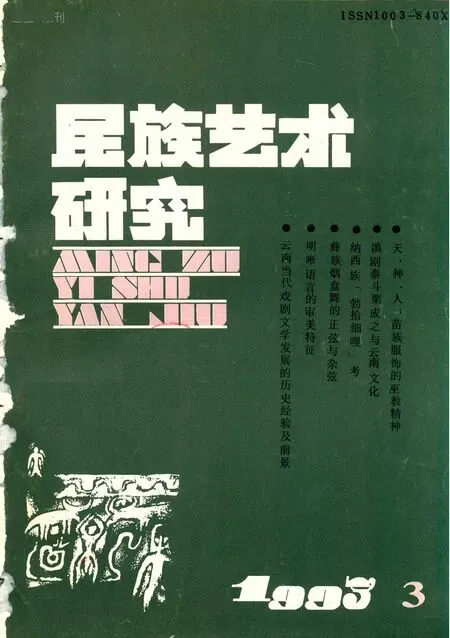从热情到方法:话剧初创期专业化追求对演出水平的提升
徐 煜
爱美剧运动在中国话剧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经过历史的沉淀再度反思爱美剧运动,它的影响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某个阶段、某个群体,而是对现代中国话剧的成型,起了催化和奠基的作用。尽管“爱美剧”的发起人陈大悲等,其本人的戏剧实践未必可观,但其倡导的戏剧的精神导向和艺术标准,却可以看成现代话剧兴起的先声和号角。
五四以后由于爱美剧运动的出现,打破了文明戏的衰败、堕落而导致的中国话剧成长的中断和沉寂,再度激发起人们对中国社会实践话剧这一新型剧种的热情。马彦祥对陈大悲做出的评价,可以看成是对这种开创意义的总结,“陈大悲这个名字,我们已经有好几年不曾听人提起了……但是因为他曾经在中国戏剧的改革上,做过相当大的努力,而且后来中国戏剧所走的途径,和他不无历史的关系,我们是不应该把他忘却的”。*马彦祥:《戏剧讲座》,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
尽管陈大悲的艺术认识对重振中国话剧至关重要,但是容易产生误解的是,他选择的路径却是反对话剧职业化,而依赖业余演剧来完成这一使命的。“爱美”一词本为英语“amateur”(业余)的音译。在《爱美的戏剧》中,陈大悲进行了这样的倡导,“爱美的戏剧,自然不用解释,是爱美的人所演的戏剧了。爱美的戏剧底对应名词就是职业的戏剧;不论哪一国都有爱美的戏剧出现,与职业的戏剧对抗”“但是就目前而论,要把这非戏剧底状态挽救过来,使他走上‘现代戏剧’底路,这个责任和希望,却非加在爱美的戏剧家身上不可。”*陈大悲:《爱美的戏剧》,上海:晨报社,1922年版。
鉴于早期文明戏由于利润驱使,不惜以低级趣味迎合观众,而迅速没落的事实,陈大悲提出了业余演剧的呼吁,这不乏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个提法,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其一是将职业化这一中性的特质,当成阻挠话剧发展的致命因素,从而掩盖了早期话剧衰败的更为决定性的原因,当时的乱象很大程度上源于从事者对方法、技术和演剧规范的生疏,以至于无所顾忌地胡乱发挥而致。而在新兴话剧立足未稳,专业规范、创作观念尚未完整之时,孤立地反对职业化,也模糊了掌握话剧创作所必需的技术方法的难度,业余的“爱美剧”团体初始时往往仅凭热情、兴趣和志向便开始了“剧运”,而缺乏方法的深究,这与其非职业化的导向不无联系。
职业化是否必然会导致话剧的庸俗、堕落;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早期职业文明戏的衰败,以及业余演剧活动是否必然会激发创作的活力和生命——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地将职业演剧一棍子打死可以解决的。事实上,应该看到,“爱美剧”运动后期,大量曾经的“爱美的剧团”的中坚分子,都成了职业戏剧家;即便在以“爱美的”性质为主导的业余演剧时期,一些代表性的团体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其身上体现出的与职业化密切相关的因素——专业化的标准和追求。而创作方式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无疑对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话剧整体面貌发生质变,起到过重要作用。
一、 中国早期话剧“职业化”属性辨
爱美剧运动之所以对职业演剧强烈抵制,在于我国话剧萌芽期竞相展开恶性竞争,以至将新兴的话剧搞得乌烟瘴气的各种文明戏团体,大多打出的都是职业旗号,因此极大地损害了“职业化”这个称谓的声誉。另外陈大悲本人曾经投身于春柳社和进化团的演剧活动,亲身经历了由春柳社引进的严肃的新剧艺术被恶俗的商业文明戏挤垮,对文明戏的反感可想而知。
大多数文明戏的低水准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其暴露出的劣态、弊端是否都应该归咎于职业化,则需要全面地衡量。从表面上看,的确大量文明戏团体都以“职业”者自居,但其中的职业程度与含量却是很值得怀疑的,作为一种职业的必备要素——方法上的专业性,尤为匮乏。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于“职业”一词的解释,就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其二是“专业的,非业余的”,也就是说“职业”不仅仅包含实践的内容和类别,也包含实践的技术和程度。而更多时候,文明戏从业者体现的仅仅是类别的意义,而不是技术的意义。
首先,从许多演出实例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的所谓职业剧团,其在方法上并未真正掌握西式话剧的要领,而时常违背话剧的基本规律和审美特点。例如出于对写实主义话剧生活化的舞台风格样式的误解,普遍轻视人物塑造的难度,而将演员个人的生活状态带上舞台,不做艺术的加工和提炼。以至于当时社会上对新剧表演,往往抱有“化妆之演说派”的诟病,其中包含着暗讽其技术含量太低的意思,“然今之新剧家换易一身衣服(亦有便衣登台者)立在台上,随便说说。于艺术一道,太不注意。遭人鄙视,固亦咎由自取。”*昔醉:《新剧之三大要素》,载《中国话剧百年典藏·理论卷(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其次,演出形同儿戏,更是文明戏的一个显著的弱点。例如:已经为人所熟知的幕表制、抢戏、跳戏只是其中一斑;更有甚者,还有演员直至上台尚不知晓自己所扮演的人物是何身份、来历的。民国初年剧评家钱香如记录的几则例子,反映了当时演出的混乱程度,有在台上哑场的,“有某新剧家上场时,将预备道白尽数遗忘,癡立台口,竟如哑巴,兀立数分钟,始闻咳嗽一声,座客均哑然失笑”;有布景和剧情时代不一致的,“串新剧者大半胡闹,不顾剧情最为讨厌。尝见某社演古代剧,布景用洋式大餐间,已属不伦”;堪称奇闻的居然还有布景堵死演员上场路径的,“某社串演某剧,其布景两旁无门,客来倒茶,饰仆役者不能进内,乃剥开中间彩布之裂缝,挨身攒入,其时但闻台下笑喊曰:攒狗洞,攒狗洞”。*钱香如:《新剧界笑话种种》,《繁华杂志》1914年第4期。
第三,文明戏从业者的来源不纯也成为阻挠其发展的障碍。早期话剧由于样式新鲜,刚出现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再加之其生活化的外观容易让人误解为其技艺简单、容易掌握,因而吸引了社会上的一些胆大油滑的投机分子竞相参与,以博取名利。如洪深所说,“不幸就有许多人,把这种戏看得太容易了。他们看见在文明戏里,既不需要歌唱,而表演又没什么规则成法,可以从心所欲的,他们要加入一试了”。*洪深:《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现代戏剧》1929第1卷第1期。文明戏出现的短短数年间,正规的创作方法尚未巩固,话剧行业就已经畸形扩容,有名无实的“新剧家”遍地开花,极大干扰了新剧的正常发育。有论者对当时沪上文明戏的行业规模进行过估计,“今之所谓新剧家,混称四千人。”*昔醉:《新剧之三大要素》,载《中国话剧百年典藏·理论卷(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尽管其规模庞大,但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甚至社会不良分子大量混迹其间,“流氓、滑头、拆白党之徒,触目皆是。”这样的从业者也绝无社会责任感以拒绝内容低俗、道德败坏的剧目,只要有利可图,无所不为,被有识之士斥为“竟排淫戏,取悦小人”。*剑云:《新剧概论》,载《中国话剧百年典藏·理论卷(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甚至连《珍珠衫》《南楼传》这样在旧戏曲中都被列入禁戏范围的色情戏,都改头换面被搬上了新剧的舞台。
从文明戏的发展过程来看,其败落的主要原因并非职业化与否,而在于其艺术创作方法尚未成型,以及从业者的思想、技术准备均达不到从事戏剧活动所需的素质和条件。如欧阳予倩的评价,“演员在台上一直是自由发挥,没有统一的组织,因此动作前后不连贯,风格不调和……一直没有谁把经验总结一下,保留起精华的部分,去掉它的糟粕,而且正相反,越到后来坏的东西更加发展,好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好的经验,都被湮没至为人所不认识”。*欧阳予倩:《谈文明戏》,载《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洪深对此问题的总结就更为直截了当和一针见血,“说得再透彻一点,‘文明戏’之所以不名誉,并不是因为职业的,而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糟的要不得,就使作者最初曾诚恳的有艺术目的,也是徒然的了”。*洪深:《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现代戏剧》1929第1期第1卷。以此可见,中国早期话剧称不上典型的职业形态,主要原因在于内部要素发育不充分,编、导、演都达不到现代话剧所需的技术规格。因此拿它作为职业话剧的判断样本,难免有测不准之嫌,由此得出职业化导致其畸形发展的结论,也有失草率和片面,不同技术条件和思想倾向下的职业化,带来的结局也是不同的。
文明戏的从业者由于缺乏相应的职业道德和认识水平,无法为早期话剧进化成为现代戏剧样式,创造具有艺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操作方法,而爱美剧的实践结果也未必尽如人意。尽管爱美剧的拥护者,在思想认识和艺术追求上,比文明戏的从业者要进步和纯粹得多,但是其大多数技术水平依然突破不大,造成其尽管有理想化的追求,却欠缺演出应有的艺术价值。仅仅依赖热情、立场和态度对于建设现代的话剧剧种,还是远远不够的;以至于爱美剧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蒲伯英转而呼吁起职业演剧,发表了《我主张要提倡职业的戏剧》一文。文中提到以业余组织松散的状态,企及话剧的艺术标准的不现实性,“单靠爱美的戏剧去承担发展戏剧底责任,实在是力量不够而且为事实所不许……毕竟戏剧界的主力军还是要职业的而不是爱美的”;另外,蒲伯英也意识到职业化本身并非全无弊端,如何引导积极的职业演剧才是关键,“假定戏剧界真没有一个干净人,也只能归咎人底品性不良带累了戏剧界,不能说戏剧是一种使人堕落的职业”。*蒲伯英:《我主张要提倡职业的戏剧》,《中国话剧百年典藏·理论卷(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
受过新文化运动启蒙的知识分子,对参加戏剧活动促进社会觉醒有着高涨的热情。当时兴趣式的话剧团体非常踊跃,在中国话剧领域占据相当比重。石挥曾经言及这种情形:“中国戏剧运动还没有走上正轨本格阶段,一般剧团还是‘爱美’、‘业余’的”;*石挥:《现阶段的话剧:由筹备起到演出止,全面问题的多重解》,《石挥谈艺录——演员如何抓住观众》,北京:后浪出版公司,2017年版。然而在为数众多的爱美剧组织中,真正能把艺术追求和社会理想付诸实现的并不多,“话剧在学校只是游艺会上的点缀,近于玩笑胡闹,剧运受这方面的影响很大”*石挥:《写给爱好话剧的同学们》,《石挥谈艺录——把生命交给舞台》,北京:后浪出版公司,2017年版。;“他们大多是以之为时尚、风头、好玩”*石挥:《古城剧运纵横谈》,《中国公论》1940年第4卷第2期。。
爱美剧的实践者尽管推崇艺术和指引人生的雄心强烈而迫切,但具体到操作层面,却经常不了了之,“爱美的剧团只有‘艺术’两个字的空话”*欧阳予倩:《戏剧运动之今后》,《戏剧》1929年第1卷第4期。。如果不能驾驭有效的演剧方法,即便是凭借热情,也无力使话剧发生根本的改观,并不因为参与者的非职业身份而有所不同,“经过了爱美剧团的一番试验,使人明白靠兴会不能成事”*欧阳予倩:《戏剧运动之今后》,《戏剧》1929年第1卷第4期。。
对于爱美剧组织的弱点,田汉在《我们今日的戏剧运动》中,就已经清楚地总结过,“第一,全凭热情和兴趣来干戏剧是不能坚持的,靠不住的,那种‘乌合之众’一遇困难就作鸟兽散,是不能成事的;第二,戏剧运动不是少数人所能担负完成,必须团结更多的同志,必须训练大量的戏剧的人才”。*赵铭彝:《涓流归大海——赵铭彝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话剧演进的前二十年,无论文明戏还是后来的爱美剧,都没能为中国话剧确立理想的演剧形态。由于职业文明戏的唯利是图,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业余的爱美剧上,尽管初衷和愿望是良好的,但是其业余本身也不足以自发地产生演剧的创造力,相反还可能把演剧活动带入没有约束的散漫状态;后来话剧的发展表明,真正使得中国建立起本土的话剧体系的,正是职业化的作风和对专业方法的探索钻研。“我们的演剧踏上职业化的阶段了,这自然是可喜的事情,因为业余演剧的许多不必要的困难在职业演剧中就可以克服或避免,更重要的是,职业的演剧无疑是会提高演剧艺术水准,使演剧的效果更为加深,更为普及。”*章泯:《目前职业演剧之大危机》,《新演剧》1937年第1卷第3期。
二、 专业意识的觉醒与范例性演剧方法的积累
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话剧,高水准的代表作激增,例如上海戏剧协社的《怒吼吧!中国》、辛酉剧社的《文舅舅》、上海艺术剧社的《西线无战事》、中国旅行剧团的《日出》、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娜拉》、40年代剧社的《赛金花》、中国万岁剧团的《雾重庆》、中国艺术剧社的《家》、中华剧艺社的《屈原》、上海剧艺社的《秋海棠》、苦干剧团的《大马戏团》等等。这种大范围质量提升的状况,当然绝非偶然性可以解释,如果说有什么因素产生了作用,那么业内人士对高层次演剧方法的钻研可谓重要的一方面。
由于受爱美剧观念的影响,新剧运动以来的中国话剧界对职业化一词始终有所避讳,宁愿标明“爱美”的身份,以至于直到1934年中国旅行剧团正式打出职业的旗号,才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职业话剧团的先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名义上的职业化出现的较晚,而话剧的部分中坚分子的技艺早就表现出专业的程度了。很多当时的“业余剧人”的创作状态都起到了范例和引领的作用,并且终身从事的都是戏剧事业或者转入了电影行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艺术生命,甚至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新中国话剧、电影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例如应云卫、袁牧之、郑君里、金山、赵丹、石辉、蓝马、王莹、舒秀文、张瑞芳、白杨等。
这些高水平的非职业戏剧家,之所以达到高端的艺术水平,在于其与一般业余参加者相比,较早地萌发了对专业化的认识和追求。总体来说,中国话剧初创期技术水平和方法运用一直处于比较薄弱的层面,如研究者田禽所说,“当时理论的趋向大多偏重于学术方面,而在技术或方法方面比较欠缺”;*田禽:《中国戏剧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向培良也有过类似的观点,“舞台之不发达,也是戏剧不能发展的一大原因”。*向培良:《中国戏剧概评》,上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年版。这种欠缺在实践领域更是有着清醒的认识。欧阳予倩在《怎样完成我们的戏剧运动》一文中指出过,中国话剧20年来“毫无显明的进步”,究其原因,从表演到舞台装置,处处都有粗糙简陋之嫌。*欧阳予倩:《怎样完成我们的戏剧运动》,《欧阳予倩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曾在日本筑地小剧场担任过美工的叶沉即沈西苓,更是疾呼,“我们现在非得有切切实实的技术上的问题提出和解答的不可”。*叶沉:《戏剧运动的目前谬误及今后的进路》,《沙仑》1930年第1卷第1期。
关注演剧方法,是当时许多剧团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趋势。例如成立于1930年的上海艺术剧社,在演剧实践的同时,连续出版了《艺术》和《沙仑》两本刊物,其中发表的《介绍一个英国工人剧场》《日本戏剧界的最近概况》《舞台效果和音乐》《演剧的技术论》《再述效果》等文章,都很注重推介演出的操作方法。在艺术剧社的公演中,也看得出他们对技术含量的追求。例如,在演出《西线无战事》时,用小灯泡做成信号器调度演员,以减少舞台监督的忙乱;运用转台、暗转等方式换景;甚至第一次采取了将电影片段投影到天幕上的手法。据夏衍的回忆,这些方法对话剧界的触动还是不小的,“艺术剧社的这次公演,不论从剧本到演出,都是一种大胆的革新,而这种革新精神在当时的话剧界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夏衍:《难忘的1930年——艺术剧社与“剧联”成立前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专业化意识的加强,话剧演出普遍对质量有了要求,逐渐摆脱了因陋就简、随遇而安的状态。例如:南国社时期,舞台装置流行以布条作为主体材料,一般以藏青色布条或者灰色布条为背景,再辅以简单的门片、窗片即成一堂景。尽管有人认为这样的布景不失象征、抽象的美感,但是在亲历者胡导的印象中,“当然这样的舞台装置是非常简陋的”。*胡导:《干戏七十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话剧舞台》,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然而,当胡导于1935年观看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娜拉》时,看到的却是一副精美真实、充满北欧情调的场景,屋外的白雪皑皑和室内的富丽堂皇相映生辉,这种效果绝非用布条构成的简易景可以与之相比,“仅从开幕这一刹那创造的艺术效应看,就绝不是灰布条、蓝布条加上门框景片、窗框景片所能达到的”。*胡导:《干戏七十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话剧舞台》,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
《娜拉》的出现并非个例,20世纪30年代以来涌现出一批同样具有完整艺术构思和精良舞台呈现的演出,其艺术效果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应云卫导演的《怒吼吧!中国》,把军舰模型的舞台装置搭上了舞台,堪称那个时代的大制作。章泯导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窗户高达三米半,一张很高的圆顶帐子,帐子下有床,有花绒床罩,左边上场的地方只用一把椅子,其他东西一概虚掉,窗外有鸟吟,整个气氛给人感觉花园很大。而欧阳予倩在《日出》的演出中,极富表现力地将梳妆台放置在舞台前区,卸掉梳妆镜,只留下方框——这一虚实结合的处理,既不失真实感,又保证演员免于背台,可谓神来之笔。
这些例子表明,当时的高水平剧团在话剧演出中,正在摆脱无构思、无设计和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盲目性,而是开始有计划、有设想地争取特定艺术效果。在导演上,重视演出形象与内涵、气氛的统一,意识到场面调度的轻重强弱所能够产生的效果,追求有艺术表现力的处理而不满足于报流水账般的平铺直叙;在空间运用上,则出现了讲究完整、精美和考究,重视风格样式的趋向。这其实也是洪深在1924年为上海戏剧协社导演《少奶奶的扇子》,开创的硬片布景、用实景而非代用景、灯光随着时间氛围而变等正规演出方法,真正得到了巩固和发扬。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话剧舞台出现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范例性剧目,例如贺孟斧导演的《风雪夜归人》、陈鲤庭导演的《屈原》、张骏祥导演的《北京人》、马彦祥导演的《夜上海》、应云卫导演的《雾重庆》、章泯导演的《家》、焦菊隐导演的《哈姆雷特》等。这些剧目得到普遍的反响,不仅仅是由于其思想意义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观众已经开始意识到舞台艺术的美感。例如:发表在《申报》1943年5月1日的名为《“大马戏团”观后感》的剧评中,署名尤青的作者这样写道:“导演佐临可没使我们失望,在大体上是极成功的。尤以第二幕戴三爷的情景能新鲜别致地采用电影的手法,简洁地刻画她妒火中烧的内心,末幕也能把握住悲哀的气氛,此外且能适当地利用音乐的配合,使尽量有弥漫着悲哀的画面,不费极大工力是不易办到的”*尤靑:《“大马戏团”观后感》,《申报》1943年5月1日。。而对1938年2月在重庆演出的《民族万岁》,《国民公报》发表剧评赞扬:“群众场面处理极为成功,灯光置景超过环境限制”“演出换景像电影一样迅速,灯黑过后三秒钟,又一幕景就呈现在观众面前”。*石曼:《重庆抗战剧坛纪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7月。
相对于导演艺术和舞台装置水平的提高,同时期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袁牧之、赵丹、金山、魏鹤龄、陶金、蓝马、石挥、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一批演员的声誉鹊起,表明了表演技艺已经成为并且能够成为话剧欣赏的重要因素。这是自文明戏诞生以来,话剧演员第一次作为群体而备受关注。例如在抗战期间重庆著名的雾季公演中,有人专门撰文概括了演员取得的成绩:
《法西斯细菌》中的静子(白杨饰),《蜕变》中的况西堂和《虎符》中的魏王(孙坚白饰),《金玉满堂》中的祖母(吴茵饰),《风雪夜归人》中的魏莲生(项堃饰),《家》中的瑞珏(张瑞芳饰),《清宫外史》中的寇连材(沈扬饰)等等,可以作为辉煌的例子。他们曾正确地理解了并把握了角色的性格,经历及心理过程,以细腻而不烦琐的,简劲而不粗糙的最真实而又最精炼的细节表现出来,达到了内在情感与外形动作的浑然一体……这样的演技,在今天是该列于前茅的。*刘念渠:《演员行列》,《戏剧时代》1943年第1卷第1期。
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话剧演员,已经形成了稳固而有效的表演创作方法,角色创造已经具备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中国话剧初创期演员艺术上的成长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其表演技艺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就像夏衍曾经指出的,“中国进步话剧有光荣的传统,但也有一个显著的弱点,就是我们过多地重视剧本的‘情节’,过少地注意演员的技巧”。*夏衍:《杂碎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从文明戏遗留下来的做状、虚假、脸谱化的表演套路长期占据着话剧舞台,例如,胡导曾经这样总结自己表演的误区,“当年我的失败正是由于我并不理解什么是性格化创造,完全不理解需要构思形象,要感受人物,要抓住人物感觉,而是直着嗓子吼叫,概念化的表演或模拟人物的粗鲁、粗犷、粗野……”*胡导:《干戏七十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话剧舞台》,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
话剧演员中的一批中坚力量也意识到了现有表演方式的严重缺陷,而自觉地谋求先进、科学的表演方法以改观现状。左翼话剧的骨干金山、章泯、赵丹在排练《娜拉》时的一番对话,就很能体现其方法意识的觉醒,“我们不能总停留在喊几句口号、流出几滴眼泪的表演水平阶段了,我们要提高左翼戏剧的演技水平……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剧场艺术”。*葛一虹:《回忆左翼剧联二、三事》,《中国左翼戏剧家史料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在这种意识的触动下,话剧演员普遍开始对正规、专业的创作方式加以重视,以严谨和细致的态度对待角色,充分理解角色和主题的关系,追求表现方式的美感和艺术性。
中国话剧界较早掌握性格化塑造角色方法的代表性人物是袁牧之。他对话剧表演的贡献,不仅仅是摆脱了徒具其表的虚假做状,或者是把粗浅地品味角色的情绪心理当成体验,而在于开创了内心体验和外部技巧结合的高难度表演的成功范例,为中国话剧表演进入性格化塑造的高级阶段奠定了基础。著名作家张天翼曾经称中国话剧表演经过“做戏”“象”“典型”三个阶段*张天翼:《大雷雨观后》,《大公报》1937年2月20日。。袁牧之无疑是第三个阶段的先行者,他以出色的性格化能力被誉为“千面人”。袁牧之的表演特点在于精心为不同的角色设计或者寻找代表性的造型、体态、行为特征,从而做到每个角色都是独特的个例而不雷同。例如他在《五奎桥》中扮演的老地主从化装、服饰乃至小道具;从体态神情以及小动作,都有精心的设计和构思,入木三分地把一个既贪婪又狡猾,既狠毒又伪善的封建官僚地主,描摹得淋漓尽致、丝丝入扣。其所塑造的角色性格大幅度地拉开了与演员本人的距离,以至于赵丹看后说:“袁牧之已经不是袁牧之,已经完全改换成另外的一个人了”。*赵丹:《表演探索》,《戏剧艺术》1979年第7期。
袁牧之是话剧演员中较早意识到,性格化是由鲜明的外部形象特征传达出的这一重要规律。对于外部形象的重视,袁牧之本人并不否认,例如他演外国人,都会用心寻找参照系,“如我演文勇舅,有地方我直认不讳是模仿Volga,Volga里的侠盗雷森,而有地方是从二三十次的俄国大菜馆的拜访得来的”。*袁牧之:《演剧漫谈》,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版。重视外部特征,往往被当成“表现派”的弊病,因而袁牧之的表演方法也被人称为“表现派”。
其实相较于孤立的体验、动情等等,袁牧之的性格化塑造方法,对于演剧艺术更为重要和艰难,它标志着话剧表演具备了技术含量和美学含量。陈鲤庭是较早认识到袁牧之的表演方法的价值的,对此他这样评价:“我愿意称这样的演技为‘形式’的演技;但请注意并非是形式主义的意思,因为他的方法特征虽然偏重外形,但到底还是以人物的感情内容为依据的,我以为在体验演技如此忽视形式的目前,形式的演技倾向是值得鼓励的”。*陈鲤庭:《演技试论—献给剧友》,《新华日报》1942年6月25日。
将袁牧之归于“表现派”,这种误解来源于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片面理解,认为强调体验就必然反对形式。事实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从来没有反对过角色的性格化,“毫无例外,演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者,应当再体现和性格化,不存在没有性格的角色”。*[苏]格·克里斯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派演员的培养》,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其实体验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塑造与本人跨度大的外部形象。惟其差别大,不容易凭借本能实现,才需要体验,而且是精确地、深入地体验,目的是通达千差万别的人物,而不是貌似心潮起伏的同类人。
袁牧之的演技化追求,对于话剧表演走向性格化、典型化有着重要作用,后来的赵丹、金山、石挥、蓝马等都受到过这种演剧观念的影响。重视把握人物鲜明、独特、准确的形象特点,也成为那个时期现实主义表演经常采用的方法。中国话剧舞台由此出现了大批性格鲜明、生动丰满的经典人物形象。
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话剧在导演、置景以及表演上的大幅度提高,可以看出中国话剧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由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的。一条是作为精神线索的人生、社会、艺术价值观,它把中国话剧导向进步、积极,与社会大众密切结合的正确道路;另一条是方法、技艺不断成熟的线索,在一批从爱美剧、业余演剧起步,但是却充满专业精神和艺术抱负的先驱者的努力下,不畏条件的艰苦和创作的艰难,全身心投入戏剧事业,力图提升话剧的艺术水平。中国话剧演出事业,从几乎没有参照的起点,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完整的创作方法和系统,使得中国话剧进入了现代艺术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