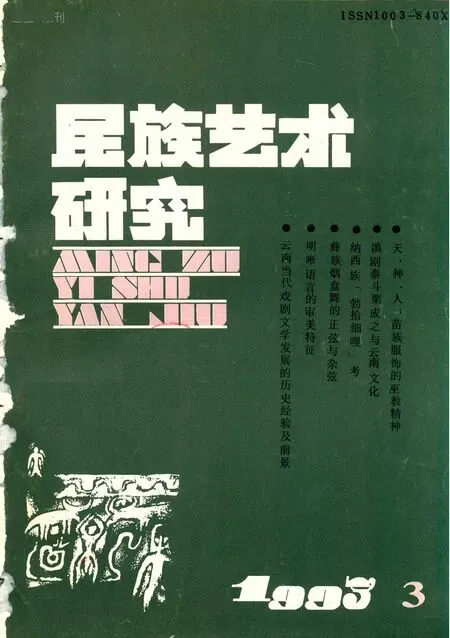写意精神与中国油画的当代性建构
冯民生
写意精神自中国油画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其核心命题。时下,随着中国美术人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和油画民族特色建构的加强,使写意精神成为中国油画发展的当代性命题。写意精神作为体现中国油画民族特色和中国风格的重要理论支撑,是我们思考中国油画现代发展的本土视角和民族文化价值的所在。
在中国油画百余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与探索,使中国油画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和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艺术形式。审视中国油画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不可回避的一个特点是,作为舶来品的中国油画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浸润中国文化精神和吸纳民族艺术基因,使其从总体上渐渐独立,愈加凸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在中国油画由舶来品转变为民族艺术样式的过程中,作为中国艺术表达方式和创作思维的写意精神,在其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中国油画当代性建构的重要精神凝聚和理论支撑。
一、写意的含义
写意,作为中国艺术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范畴,它不但是一种风格样式,而且是一种艺术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中国艺术家建构画面视觉图式的先行意识,也是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表现内容,甚至可以将其看作艺术的系统方法论。尤其在中国油画实践中,写意更为突出地体现了方法论的意义。从中国油画发展的宏观历史视角审视写意精神,它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凝聚和艺术基因的鲜明体现。如果从中国画的风格看,在中国绘画中有“写意”与“工笔”之分,从这方面看,写意就是一种艺术风格,一种画法。但是写意作为一种艺术范畴,它已经超越风格层面成为包含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的具有体系性的方法论知识,承载着民族文化的质地和艺术精神。
“写意”作为传统美学概念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先秦时期,《左传》中的“铸鼎象物”和《周易》中的“立象以尽意”就已经有写意的含义。中国绘画理论中出现“写意”内容的表述是在唐代,张彦远就有:“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宋代的欧阳修也有:“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张彦远和欧阳修则认为写意就是作画的目的。在中国绘画史上直接表述“写意”这一概念则是在元代。其时,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对北宋僧仲仁所画梅的评价中就曾出现过这一词:“以墨晕作梅,如花影然,别成一家,所谓写意者”。夏文彦的写意含义更多的指一种风格。但是从“写意”这一词的本意来看,它包含了“写”与“意”两层意思:“写”是“抒发”和“书写”,有“表达”的成分;而“意”则包含“意志”“意图”“思想”等含意。除此之外,如果从绘画的层面理解,意还有神韵和精神的含义。写意也可以看作写事物的神韵与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写”是“意”的物化和显现,是手段;“意”是“写”的目的和旨归。没有“写”,“意”就无法显现;没有“意”,“写”就没有了生命和精神,因此写意是互为表里的,共同构成不能分割的整体。从其呈现状态分析“写意”正好就是作画的过程与方式。概括地讲,写意主要是指艺术家通过艺术形式表现思想感情和对社会、生活、艺术的感悟,体现精神情怀。从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角度看,写意就是比、兴,是触物生情,借物以起兴。如果从中国油画的实践层面理解写意,它已超越了风格流派的范围而体现为思维方式、表现方式、审美趣味、艺术精神等诸多的文化意义。
写意作为一种艺术的思维方式,它从“观物取象”到“意象表达”都与西方油画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被明显地区分开来。写意所包含的“观物取象”就是中国文化观照事物的方法。正如《周易·系辞下》中所指出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李来源,林木:《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后人把这种“仰观俯察”的观察概括为“观物取象”。这种“观物取象”的“观”,就是一种对客观物象的直接观察和感悟;而“取”就是在“观”的认识基础上,对“象”的提炼和创造,并以形象模拟的方法加以体现,其中也包含了意象化的过程。这种“观物取象”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注重对客观物象的全方位认识和感悟,充分地调动知觉的因素去感悟,讲求直觉。写意就包含了观物取象的内容。唐代晈然在《诗式》卷一中写道:“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其中“取象”就是选择与情、意相契合的物象,从而将思想与情感寄寓于形象之中。写意在艺术思维中充分显现了画家与表现对象的情感交融,以及对物体与对象的理解和直观认识,同时要把表达的情感融入对象之中,使物体和对象成为饱含情感又保持对象特征的意象之物;写意渗透在作画的整个过程之中,包含“心物融合”和“意象营构”以及抒发表达等多个层面的内容,既体现思想、观念等精神因素,也体现表达方式和创作方法等实践因素,是一种整体显现的系统的方法论体系。
二、中国油画的写意性
对中国油画的发展历史进行考察,对其从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加以系统探究,我们发现写意性因素不但存在于表现性油画中,而且也明显地体现在写实油画中。从我国油画家徐悲鸿和吴作人两位画家的写实风格作品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写意因素的存在。在徐悲鸿的油画作品《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尽管画面写实、人物造型严谨、空间效果真实可信,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整体画面在色彩和形体处理上的写意特征,尤其是在主题气氛的表现上,体现出鲜明的感情色彩与审美取向,充满着中国艺术精神和文化价值;而吴作人在油画作品《齐白石》《三门峡》中,虽然以写实的表现手法进行描绘,但是对整体画面的处理和气氛的营造明显体现出写意的特点,在色调和空间处理上已经超越了写实的局限。也有人把中国油画实践中的写意简单理解为与写实背道而驰的随意变形,甚至胡涂乱抹,这样的说法既不符合中国油画实践的实际,也明显歪曲了作为承载中国艺术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写意的含义。
作为系统方法论体系的写意,不仅包含艺术思维方式、表现方式和一系列的思想观念,也包含意象这一范畴。如果说写意是中国艺术表现的旨归的话,那么意象就是实践这一旨归的重要环节。意象也是一种艺术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
从中国艺术的历史去梳理意象,我们发现意象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艺术创造的方式,甚至包括一些艺术观念。意象有着“意”与“象”两部分内容的含义,其中“意”就是指画家的主观情感和思想。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意”还指主体因悟道而产生的一种感觉、感受、思想,体现着主体对客观事物的理解,是一种可以直观把握的精神意识。“象”是指画家对客观对象进行概括与提炼后所产生的形象。是画家主观情感、思想与客观对象的有机结合,并依照艺术规律创作的艺术形象,这既不同于客观对象,又不脱离客观对象而造就艺术形象。从审美意象产生的动机和过程考察,其以象达意,以象抒情,因象而获得感性愉悦。在意象创构过程中,主体起着主导作用,无论是有感而发,还是情不自禁,都是主体受到客观物象触动后的精神状态的一种呈现,这种状态尽管是一种物我交融的状态,但是主体在其中的主动性并没有被模糊化。因此,意象生成的过程是通过主体积极的能动作用来完成的。意象在中国艺术中更为明显地体现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表现方式,是写意的核心内容。作为写意核心内容的意象,是其艺术思维活动中的基本内容,是以艺术化和审美化指代事物,以唤起存在于事物的美感与艺术因素,使得客观对象幻化为艺术形象。意象是外在对象与信息在主体内部依照艺术规律所建构起的精神体,是艺术思维和艺术形象建构的本质所在。因此,意象创造成为写意的关键环节之一,没有意象化的过程写意也就成为简单的概念而无法获得其旨归。
在中国油画实践中,“写意”往往和“写实”“表现”等概念联系和交织在一起,更为突出地体现为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并集中体现出意象化特点。中国油画的写意性能够成为思考和理解中国油画实践历程和发展特点的精神因素,它带有明显的文化质底和艺术基因。在油画表现中,写意与写实成为相对的两个概念,主要是从风格特点上划分的。如果说写实在表现中注重对客观对象的真实再现,使画面空间成为现实空间的真实幻象的话,那么写意则是突出主观与客观融合后的感悟与情感表达,使画面成为表达主观感情和承载文化意义的载体,但在视觉展现上却不失真实的成分。如果说写实是偏向于再现的话,那么写意就偏向表现。需要指出的是,写意在表现中强调主客观融合所生产的新的意象,注重感悟和直觉,它是对画面进行现实和主观理解相融合的改变和处理的,而这种改变和处理符合中国艺术的创造规律,在“似与不似”之间进行取舍,重视“传神”“意境”“趣味”“气韵生动”的体现。另外,在中国油画的发展过程中,写意和写实不是完全对立的,写实风格的作品中也体现着写意的特点。写意在中国油画的创作实践中更为突出地体现在油画表现中对中国文化精神和审美趣味的自觉融入,以其统帅表现的整个过程,使油画表现成为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审美趣味、艺术理想的自然流露和视觉展现。除此之外,在中国油画中,写意不能离开客观对象以臆造形象。
作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体现艺术精神的写意表现手法,也是艺术表现的制高点,不是一蹴而就的浅薄学问。对于中国油画的实践者来说,要达到体现写意精神的境界,不仅仅只是掌握写意的理论知识就可以的,而是要将其化作艺术实践的表现手法加以运用。对于在中国油画表现中体现写意精神,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熟练掌握油画的表现技巧,谙熟油画的创作特点和规律;同时,也要掌握中国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并能将中西艺术融会贯通,在油画表现中自觉体现中国艺术的美学价值和艺术精神。以上两点缺一不可。如果没有掌握好油画的表现技巧和了解油画的表现规律,写意精神就只能是观念而不能转化为油画语言。试想,一个没有熟练掌握油画技巧和油画历史的人,肯定连油画都画不好,何谈在油画实践中体现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相反,如果有良好的油画表现技巧,又熟悉油画的特点和历史,但不了解中国艺术的写意内涵和意义,对中国艺术的特点和规律不熟悉,也不能在油画表现中倾注写意精神。
三、写意与表现
如果从写意的意象化思维分析,它与西方油画表现中的思维方式有较大区别。意象化的思维是一种始终不离具体形象的主体化过程,其状态就是主客融合,将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悟和阐发放在首位,依照对客观事物的感悟进行主体化处理,而这种主体化就是要进行事物的传神写照并营造意境,更多地体现出直觉把握对象的特点。正如元代画家张退公提起画竹的体会时所言:“得之心,应之手,心手相迎,则无不妙矣。”*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下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7页。这种将形象化迹于心、以手托出、心手相应的过程就是一个由意象描绘到写意的过程,充分表现了画家的思想和感悟,也符合“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中国画的创作意旨。就郑板桥的“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绘画理念而言,“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就是注重客观到主观的情感注入,使客观之物变成意象化的对象;而从“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则是由对象意象化到艺术形象客观显现的过程——由此完成由意象到写意的创作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艺术中意象化的思维方式,始终把客观对象作为感悟、阐发的根本,并注入主观情感;在思维方式上体现出主客融合的状态。因此,中国画创作更多地体现为“心识目记”地表现“心中丘壑”,甚至可以“以大观小”,通过知觉感悟抒情达意。正如李可染所讲的:“中国画不只包括视觉,也包括知觉。应包括所见、所知、所想。”*李可染:《李可染论艺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这种调动人的全部身心的感知在一定程度就是一种意象思维。意象化的画面处理是紧紧依附表现对象展开来表达的,就像王履的体验,“我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下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页。始终心物不离,相互交融,成为一体。写意依照主客融合、心物交融后的感悟遵照中国艺术的“传神”“意境”“气韵生动”等审美理想进行表现,其中不乏概括和抽象的因素,但是它绝不是变形和夸张。主客融合思维主导下的写意是知觉为先的整体把握。
从写意的表现特点看,其状态是主客交融的,具有知觉抽象的特点;而西方油画中的表现,主要体现为画家站在表现对象的对面进行审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主客二分的思维特点,在表现中注重画家的主观感情,依照主观情感对客观对象进行概括、变形,甚至夸张处理,具有理念和情感为先的直观抽象特点,其中心和立足点是主体本身。艾布拉姆斯认为,“表现说的主要倾向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件艺术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因此,一首诗的本愿和主题,是诗人心灵的属性和活动。”*[美]艾姆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以理念或者情感为先去表现对象,会以主体为中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对象身上,使对象成为任意变形,甚至夸张、扭曲的形象,与客观对象愈加分离,这其实就是一种主体精神的无限膨胀,是主体精神对自然对象的吞没,完全抛弃感性的自然形象的原始外形,以主体感情为主导的抽象化表现,其主旨就是表现内在的情感冲动。
另一个突出的表现特点就是以表达主体的内心情感为主要特征。首先内心情感是由主体的情绪和思想所驾驭的,在这样的表现中更偏向于自我的表现,其状态是使主体与客体分离。而表现是通过对物象的夸张、变形,甚至歪曲来实现的,包含情感为先的直观抽象化因素,凸显了唯我独尊的主体性。我们看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德库宁的作品,画面上的女人是被丑化的,画面给人的就是恣肆的笔触和强烈的色彩,仿佛主体对客体的有意歪曲,这显然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所致。我们从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作画过程可以感觉到其理念和思想为先的抽象过程。莫奈深有体会地说:“当你出去画画时,要设法忘掉你面前的物体:一棵树,一片田野……只是想:这是一块蓝色,这是一条粉红色,这是一条黄色,然后准确地画下你所观察到的颜色和形状,直到它表现了你最初的印象时为止。”*[英]贝纳·顿斯坦:《印象派的绘画技法》,平野、陈友任译,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他在大自然中写生时,把自然物体看成是粉色、蓝色、绿色等不同的色块,最后依照自然形状把不同的色块画上去,就完成了其画作。可以肯定的是,莫奈在作画前就有一个理性的概念引导其完成画作,而这种概念是设定在对感性物体进行感觉之前的。20世纪初挪威表现主义画家蒙克在表述他创作《呐喊》的体会时写道:“我和两个朋友沿路前行。太阳正在下落。我感到一阵忧郁,——突然天空变得血红。我停下脚步,依靠着栏杆,死一般的疲倦——放眼望去,燃烧的云朵像血和剑一样,悬挂在蓝黑色的峡湾和城镇之上。我的朋友继续往前——我站在那里,恐惧地颤抖着。然后,我觉察到一声巨大的呐喊划破天际。”*[荷]曲培醇:《十九世纪欧洲艺术史》,丁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4页。这种由主体情感引发的对客观对象的抽象表现,使主体和客体分离与对立,是自我意识的无限放大。因此,表现主义画家都是以情绪为主来对事物进行变形和夸张,也进行情感、理念为先的直观抽象。而中国的写意则从主体对客观的感受中观照,把主体融入客体或者人化的自然中,由此进行表现,这与西方的表现又有本质区别。中国艺术的写意始终不离可感的对象,也不以变形来实现写意,而是在心物融合中观照对象;而西方的印象派和表现主义始终使以情感为先的抽象化对描绘对象进行变形与概括甚至夸张。这也就构成了写意与表现的区别。如果说写意在表现对象时,主观与客观是浑然不分的,那么表现则体现出主客观之间的分离与对视。当然中国艺术的写意与西方的表现不是绝对地截然不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如注重对感情的表达和以对象为依据的阐发,都有相同之处。写意与表现的真正区别还是思维方式与表达状态的区别。
四、写意精神与中国油画的当代性建构
写意作为艺术范畴,是由诸多艺术范畴相互凝聚而形成的一种方法论体系。它既包括精神性因素,体现为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包括形态性因素,体现为表现方式、表达方式、实践运用等诸多方面——这为中国油画的当代建构,不但提供精神和思想源泉,也提供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成为中国油画当代建构的主要理论和实践基础。
随着新时代社会文化建设的需要,中国油画的当代面貌的特征无疑是中国油画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这样的写意精神在中国油画的当代性建构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从中国油画的发展历史来看,其无疑把写意精神的体现作为发展目标加以实践。在中国油画的本土化发展历程中,写意成为精神性因素使中国油画在发展中不断向民族艺术回归。可以说中国油画的写意精神追求与20世纪以来中西艺术融合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中国油画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西方油画的知识,同时不断注入民族艺术精神。从20世纪上半叶起,尽管中国油画还在向西方学习,但是有志向的第一代油画人在学习中已经开始思考和践行油画的写意性。林风眠以“中西调和”的观点,把中国民间艺术的趣味融入油画表现中,甚至以彩墨作为表现形式,来体现写意精神和进行意象化表现。刘海粟则以意象化的处理,在表现中十分注重线条和墨色的表现力,使得油画作品更加概括化和富有中国艺术的精神气质,体现出写意精神。我们看他创作于1929年的《快车》和1931年的《雪霁》,画面表现中尽管是色彩和笔触的胶合,但却体现出笔墨意味,写意特征非常明显。正如他发表在1924年12月1日《晨报》上的《艺术与生命的表白》中写道的 :“我常常看见一种瞬息的流动的线,灿烂的色彩,心弦便不惜地潜跃,自己只觉得内部的血液要喷出来一样,有时就顷刻间用了色彩或线条表白出来。表白出来了,自己觉得生机盎然,异常高兴。”*赵力,余丁:《中国油画文献》,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469页。从刘海粟表述的状态来看,这依然是写意的心身体验。既是提倡写实绘画的徐悲鸿,在他的油画作品中,加强线的作用,把中国画的笔墨意味融入油画表现中,以体现写意精神和民族特色。他于1931年创作的《徯我后》和1940年创作的风景画《喜马拉雅山远眺》,其中人物的处理和色彩意味的表现及其空间的营造,已经体现出明显中国绘画的特点,尤其在主题的表达上写意色彩浓郁。当然我们从当时的颜文樑、王悦之、汪亚尘等人的油画创作中也依然能看到写意性因素。当中国油画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油画民族化所展开的实践之路,就是以体现民族特色为追求的,其中所包含的写意精神则是明显的。随着中国油画的发展,写意精神融入中国油画表现之中愈加成为油画家的自觉追求。董希文、吴作人、罗工柳、艾中信、吴冠中、詹建俊、靳尚谊、朱乃正、妥木斯等艺术家的油画作品中无不体现出明显的写意精神。而这种写意精神就是在油画表现中融入民族艺术精神和人文价值。
从中国油画的当代现状来看,无论是具有写实特点的油画实践和表现性油画实践还是在写实与表现之间的油画实践,都不约而同地追求中国油画的本土化与民族特色,而构成中国油画本土化与民族特色的一个主要建构内容就是写意精神的注入。无论是詹建俊、钟函、靳之林、谌北新、戴士和、闫萍等具有表现性特点的油画作品,还是靳尚谊、杨飞云、朝戈、张祖英、郭北平等具有写实性特点的油画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中国的民族审美趣味和艺术精神,具备写意精神的特点。
中国油画的写意性,更多的是精神性体现。以系统的方法进行写意,以凝聚中国艺术精神。但是要在中国油画表现中体现写意精神,画家不但要掌握油画艺术的表现规律,而且要研究民族艺术,谙熟中国艺术的规律,将中西艺术融会贯通。油画的写意精神只能体现在中国油画家的油画表现中,而且这种写意特征的显现是依靠画家的意象化表现来实现的。如果仅仅依靠对油画表现技巧和规律的掌握,而没有对中国文化与艺术的研究,也许能画出较为优秀的油画作品,却不能创作出具有写意精神和特征的油画作品。对中西艺术的全面学习与修养也成为写意性油画实践的基础,尤其是油画家对中国艺术的修养。正如尚辉先生所言:“油画的中国写意性追求首先应当是以书卷气的文静、儒雅和内敛为其审美品格的总揽,这意味着那些完全着眼于形色的视觉冲击而缺乏文化内涵与心性修养的画作被排除在写意性之外,以此,便界定了西方印象派之后的画作为何不可能完全归入中国写意性审美特质的缘由。”*尚辉:《困扰与重返:图像时代的造型艺术》,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其次,油画性写意精神的实现还体现为,油画表现除表现技巧外的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的中国化介入,使表现的全过程统筹在“民族化”的驾驭之中。为什么我们谈起中国油画的写意精神总会与中国油画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实践分不开,总会以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倪贻德、吴大羽、王悦之、董希文、罗工柳等具有本土化实践特征的油画家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作品更加明显地体现出中国艺术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这也成为他们的油画作品更具写意精神的原因所在。
从中国油画的历史来审视写意精神,专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写意性在中国油画中的体现与其历史进程是同步的。中国第一代油画家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等的油画实践就已经包含了写意精神和建构意象油画的实践。尚辉曾在《意象百年》这篇论文中写道:“中国油画历史有多久,意象油画的历史也就多久。”*尚辉:《意象油画百年》,《美术》2005年第6期。其实这种判断是对中国油画总体特点的一种概括,是对其写意精神的揭示。纵观中国油画发展的实践历程,不能否认的是,中国油画写意精神的生成离不开中西艺术融合的时代背景,也是在中西艺术融合的背景中强化的。写意精神地融入一直是中国油画人追求的目标和理想,是凸显中国油画民族特色的有效途径。
写意作为中国艺术的核心范畴,它不但是一种风格,而且更为明显地呈现为出一种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其核心内涵是中国艺术的精神和品格。它不仅有实践层面的整体要求,也有形而上的系统观念,两方面互为表里,相互依存,构成了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因此,在当代中国油画民族特色的构建中,写意将会成为不可或缺的,既包含精神性因素又包含实践性因素的体系性知识深深地融入中国油画的实践之中,也将成为思考中国油画未来发展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