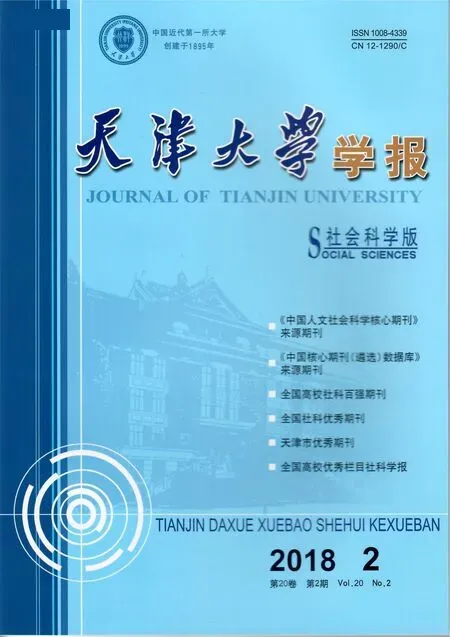孟子诗教视野中的“以意逆志”问题
张大为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天津300191)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经典命题。不过,仅仅在诗学或者文论本身的范畴内讲述这个问题,似乎总让人觉得有些小题大做、言不及质。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放置在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的心性教化意图当中来考量。或者说,只有放置在这一问题格局当中,才能对于这其中的诗学或文论问题,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并进而拓展与深化对于什么是文学的整全认知。这首先需要扭转汉、宋两派的学问家数、尤其是宋代理学兴盛以来对于孟子的解释方式:从心、性的概念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角度解释孟子,恰好与西方现代传统的美学与审美诗学视野若合符节,但这并非孟子的本意及中华文明传统当中所理解的文学性。文学性或者广义上的诗性,作为一种具有丰富价值内涵与复杂文化机理的构成,对于它的理解与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无邪”“止于礼义”的限定性定义方式与否定性问题维度之上,或者对之进行一种宋明理学式的、形而上学化的概念性、割截性理解,这都不可能是客观、全面的。“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文学接受问题,其中必定牵掣着某个更大的问题性格局,伴随着某种更关键、更重要的过程,或者说,它可能是一种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过程的伴生性、衍生性机制或外部体现。
一、 “以意逆志”与孟子诗教的问题性格局
孟子的义理系统,不是从形而上的概念和思辨体系出发,把“道”当成抽象的理念和遥不可及的彼岸性存在,而是要现实地、具体地理解与完成“道体”之整全性和内涵性,以及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实现从“实然”向“应然”层面的越升。具体来说,孟子并未完全否定告子“生之谓性”的人性之原始自然性层面(也即并未完全否定“寡人好货,寡人好色”层面)[1],这类似于董仲舒“道者万世之弊”,或天台宗义理系统当中的“贪欲即道”的思理。这一思路的思维方式,都在于其考虑的是“道”的实存和在体,而非作为形而上学的概念层面的“道”:孟子的“道”具有肯定性、内涵性、价值性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一种限制性、限定性的抽象规范,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汉代诗教。它追求“应然”方面的超越性,但同时正视而不回避世界与人性构成之“实然”的现实状态,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宋儒形而上学的理学思路。在这一交汇点上,孟子学说的基本特征,是中国上古以来诗教传统的体现:“诗教是指以诉诸人们感性的诗歌音乐艺术为媒介的道德品性教育,它既是封建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古代艺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核心内涵”[2]。但孟子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诗教传统的继承者,“王者之迹熄然后《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既能够符合孟子的学说格局与社会理想,又能够具有现实的教化作用,是孟子出于他自己的时代历史条件,综合“王者之迹”体现的儒家政教理想与孔子作《春秋》的现实精神而来的、从个体心性层面上弘扬与重建的诗教传统。
这样,“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孟子自认为自己最擅长的两件事项,就是“知言”与“养气”。综合起来看,或者说孟子之所以把这两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项放在一起来说,就在于无论是“知言”还是“养气”,事实上都是在力求把握人之生命存在实然的自然状态下的现实性,从此出发,是把握捉摸不定的心性问题的某种具体着手之处。这样的义理系统体现在诗教与文论问题上,“诗”与“言”就属于人的心性之实然的自然状态,而孟子“以意逆志”的论诗、解诗方式与方法,由此就具有了存心、养性的修养、教化方面的积极意图。从心性角度看,“性”是“心”之本然、本体,“心”是“性”的实存形式。同时,“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说文解字》),“志”是“意”的统属,而“意”是诗中之义、言中之义,是“志”的具体化。但总体而言,对于孟子来说,只有渊源自“天命”之“性”的道义责任担当,才能称之为“志”。因此,“志”和“性”是同属一个应然层面的东西,而“意”和“心”属于实然的现实具体性,而“志”和“意”又分别对应着“性”和“心”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具体内涵(见表1)。

表1 孟子诗教范畴表
由此,“诗”与“言”,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作为“性”之实然的“心”迹之所存,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志”之具体化的“意”。于是,“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在一定情况下心性教化问题可以转化为诗中之“意”、诗人之“志” 的问题,“存心养性”问题可以转化为“以意逆志”问题。也因此,从诗教的角度出发,“存心养性”当中的心、性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从诗教的层面来“以意逆志”,则心性教化、存心养性易于着手,可以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展开。
(1) 根据朱熹《四书集注》的注疏,“气”与“心”之间是本、末关系,而“心”与“言”之间是内、外关系,因此两者不能简单类比和等同。但无论如何,含“意”之“言”、存“心”之“迹”,虽非道和天性之实体、本体所在,却是“志”与“性”的具体存在方式和体现,要想将其全然泯灭,不仅不符合天道与人性,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因“言”以知“心”,从“心”之形迹入手养“心”之本性、本体。这个过程是一个心性修养与教化的过程,而所谓的“言”和“心”正是孟子诗教的具体实践领域,是诗教展开的基础,也是“以意逆志”的出发点。所以,舍本逐末自然不值得提倡,但“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却是不可以的,因为舍此无从着手或至少是不易着手。
(2)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理出孟子的两条思想线索,“外”(以意逆志):“意”(“诗”“言”)→“气” →“志”;“内”(存心养性):“心” →“气” →“性”(天)。孟子节略性地指示了这两条线索当中的有关内、外、本、末的一些关键之处,而非全部问题。一方面,“志”为“气”之帅,说明“志”高于“气”,是孟子所谓养气的目标与指向;另一方面,如果将“以意逆志”归结于“存心养性”(如上文所说“以意逆志”是“存心养性”的一种方式),其实也只有经由养气的生命化、具体化的修养过程,养性的目标才能实现。所以,“意”与“心”属于“末”的层面,“志”与“性”属于“本”的层面。就道德伦理内涵而言是“意”“志”,就人性的构成与归属而言是“心”“性”。但总体而言,“意”与“志”不是凭空而来的,道德、伦理不是自本自根的,而是“意”“志”在“心”“性”中,道德、伦理在自然性之中。因此,前者表现为外在的道德伦理属性与习得技艺,后者为内在的人性自然基础领域。
(3) “气”因此不仅是这两个过程当中各自的纵向的中介程序,是生命之本末、内外沟通而使以意逆志、存心养性得以实现的中间环节与必要条件:“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同时,它也是横向连接这二条教化进路与思想线索的连通器,“气”是人的现实生命、现实生存的特征,意、志、心、性以及内、外、本、末,统一于以“气”为特征的士人个体生命的现实生存,统一于以“气”与“养气”的循环形式构成的士人生命仪轨。“气”不比“志”“性”更高,却比“志”与“性”具有一个超个体、但却又是具体可触手的自然性底盘——孟子将“养气”与“知言”并列,或许就意味着它们同样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所以才为他自己所“善”长,也正因此,“气”超越生命个体本身,将更加浩大的生命价值格局(浩然之气)包络进来,整合起来。
二、 “以意逆志”与心性的飞跃:孟子的儒学问题关怀
孟子学说的总体取向,是力求将道德伦理内容安置于人性之自然性构成之上,使其变成一种类似生命的准自然本能的东西。人类文明化的生活世界,首先是一个道德伦理的世界,如何处理道德伦理世界与自然人性的关系,这对于古今中外的思想史、文明史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西方的现代之前的传统当中,经常将道德伦理的源头归结为超验性的东西,比如理念、神性等等,这样的思想方式,在现代世界与现代人的世界观面前,面临着现实的、实际的困难。因此,西方的现代性传统将这一切诉诸于具有普遍性的理性机能的自主性个体[3],但问题是,如果这个个体既不自主,也不理性,那将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保证道德伦理世界的实现的可能性。西方现代世界日益趋向的没落、颓废与虚无,恰恰证明了这一康德式的“现代性”思路也未必能行得通。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思想传统的基本特征,在于将道德伦理世界建立在尊重人性之自然性的基础之上,但中国传统所理解的这个自然性,不是一种纯粹物理学、生物性的构成,也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性本质,同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然基质。中国传统将道德伦理世界看成是对于人性之自然性的协调、完善与发展[4]。同时,这个自然性本身也不是恒定不变的,它可以通过培养、教化作用而不断得到升华。自然既是最低的基础,同时也是最高的标准,即道法自然、自然之道意义上的,天道、天命意义上的自然。这样,对于人性来说,道德伦理就不是一种简单的约束性、强制性与外在枷锁,同时,人性也不是完全消极地、被动地应对和符合道德伦理的要求,而是在相互作用、相互砥砺、相互提升当中,符合更高层面的自然之道,达到人性的善性与完善。这是包括孟子在内的先秦儒家、乃至其他思想流派,所努力践行的天道或者道义责任,同样也是直至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参照、借鉴价值的思想文化传统。
于是,孟子的儒家义理系统建构的基本目标,就是使儒家之“意”与“志”,不只是一种后天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意志,而是同时具有天性、天命的自然性基础与根据,能与“天”沟通和建立联系。从儒家士人生命个体之现实存在方式着眼,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所谓养气,就是扩大个体生命的配置与格局,从天道自然的层面找到个体生命的价值根据,从存心、养性的角度守护天性、天道之本然。反过来从“心”之本“性”和本体当中,发现天命之所钟的生存与价值支点,但这不仅仅是为了个体存在意义上的心定、性安,而且是求得以天命、天道来支持儒家的道义实践与政治理想。在这个义理格局当中,“以意逆志”与此协同、平行,是存心养性的一个角度或一种方式,它逆求的威武不屈之志,就是求得性层面上的、由天命与天道支持的人生价值目标的确定性和真确性。“以意逆志”涵括了“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阶段,是对于这一过程的总体概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于知言、养气与存心、养性、事天这个过程的总体描述,或者说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另外一种方式、方法。这就是“所以事天”,只有这样,作为“天吏”“天民”的士人,也才能够做到“仰不愧于天”,完成其道义使命。
因此,“以意逆志”的“逆”虽小,但却是人性或者善性的本质呈现,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或者说,是人本身最为超卓、伟大的力量。一个“逆”字,点明了人心和人性的灵明与高贵之所在,不是任凭生物性的自然随意泛滥,而是凭藉天地赋予人的自然生命,学习自然之道的博大和精微,从更高的层次上接近自然、循顺自然,体悟自然之“道”的境界。《周易》上讲:“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周易·说卦》),道家也有“顺为凡,逆为仙”之说。而就“以意逆志”当中的意与志、“存其心,养其性”当中的心与性之间的关系而言,有点类似佛教“缘生——自在”的关系:心念随外缘、外境流转,善恶不定。在这个层面上,它本身不可能像镜子一样纯净和空明,但如果能够了悟这一切不过是因缘所生的现象和表象(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执着与拘泥于此,那就能得到不空之空、不净之净,得到本然的自性和自在。这样,无论心念怎样流转变迁,也不会扰乱坚定、纯粹的本然之“性”。儒家凭借“以意逆志”方式存心养性,将现象世界的真实与虚妄、理想与现实作破而不破整体理解与把握。“以意逆志”在此就是不被心层面的言辞、意象所干扰,而直探在其性层面凝定的志之所在。
但如果止步于此,则不会超过后世由此取法、追求“明心见性”的个体化修为但却缺乏道义实践、政治实践能力的儒学路径。事实上,孟子所谓“我四十不动心”的“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并非是如道、释两家那样纯粹个体的自我修养境地,而是儒家士人实现与完成其道义职责的过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以意逆志”与知言养气、反求诸己、存在养性,是一个平行、共振的过程,“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是其在个体人格层面发生的现实效应的体现。对于儒家来说,制定某种强制性的规范来约束个体心性,或将心性问题作某种哲学式的形而上学思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个体“顿悟”式的心性修炼,这些都不是其首先要关心的。儒家的首要关怀,是如何对于士人乃至广大民众的心性作某种有效的教化与引导,使其臻于善性,以温柔敦厚之诗性与诗教,来颐养、延伸、升华人的自然天性,使之不断在更高的层次上符合“天命”之善性、符合天道之“自然”,这才是真正能够“不动心”的基础,而“以意逆志”的诗学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就扩充为知言养气、存心养性的大问题与根本性问题。
三、 “以意逆志”与中国传统学术的问题性格局
近现代以来,人们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美学观念与审美主义文论的视野,将文学看成是一个审美客体,一个被观看、被观照的对象,以及通过这种超功利的、内容空洞的审美产品展开的外延化、外缘化、外源化的美育与审美教育过程,并视此为唯一正确的文学认知与理解方式。这样,中国古典诗教传统的文明人类学与文明诗学的视野被肢解了[5]。后者的问题视野与审美化的、美学化的文论有交叉重叠的地方,在具体艺术问题及结论上也不一定与审美主义文论矛盾,但在总体性的问题性格局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孟子并非一定不能关心今天人们视野当中的文学问题,但孟子着实不可能关心一个在作为审美批评及鉴赏方式的问题性组织方式当中展开的“以意逆志”问题。具体来说,在这里,在“以意逆志”的作用机制的具体展开当中,以谁的意逆谁的志其实并不重要,因此像朱自清先生等人的研究结论本身不成问题,不过,“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6],只是一个局部和次生的问题,问题显然不能就此一言而决,如何为“意”?何为“志”?己之“意”与诗人之“志”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吗?对于孟子这样的思想巨人来说,它们只是随意取用的临时性概念或者无关大体的文学批评术语吗?为什么不是“以志逆志”“以志逆意”或“以意逆意”?从己之“意”到诗人之“志”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迎受”是否代表一个与“感发兴起”的诗教效应完全不同的整体性的文学接受格局与效果?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大面积的讨论余地和空间——而这也正是本文这样的探讨所努力的方向。
总而言之,在孟子诗教的问题视野的前提下,“以意逆志”这个命题的关键首先在于,这里发生的个体的诠解和释读过程,其目标指向并非只是文学的、审美的,而同时也是“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的过程,是落实这一目标诉求而展开的心性的具体教化机制。在这个生命修养的过程当中,逐渐将儒家的道德伦理与人文系统化入其中,并使之成为准自然本能。孟子学说并非是一种激进的人道主义与简单的人类中心主义[7],从这样一个心性教化的层面、也只有从这样的心性教化层面上讲,孟子学说当中被人们诟病的所谓乌托邦色彩其实也不是问题。这个意义上,乌托邦并非永远无法抵达的空想天国和乌有之乡,而是可以在每个人的心灵、心性层面实现的“超越”之境。这正是孟子的教化意图的具体实现途径、方式与目标。
[1] 牟宗三.圆善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6.
[2] 陈桐生.礼化诗学:诗教理论的生成轨迹[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1.
[3] [美]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M].刘 振, 彭 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326.
[4] [法]汪德迈.占卜与表意: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M].金丝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7.
[5] 陈 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28.
[6] 朱自清.诗言志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6.
[7] [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M].王重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