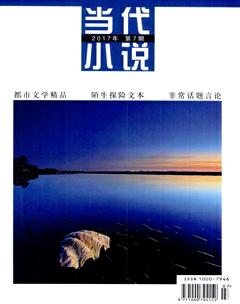耀眼的白光(短篇小说)
阮家国
怪,好怪,怪事好像就是从昨天开始的。
昨天,天好热好热,好像比啥时候都热。昨晚,好像有点儿怪,林又青没睡踏实。他还当晚上酽茶喝多了,可又明明记得,自己根本就没喝酽茶。不过,昨晚没睡好,并没耽搁他早早起床。
林又青是个手艺人,会不少手艺。他会砌岸,砌墙,油漆,简直就没有不会做的活路。他手艺好,自然又是个大工。他的生活也怪有规律,每天早睡早起,一大早骑摩托出门做工,在外边吃过晚饭才回家。做工,他大多在乡集镇的街上做。虽然他在街上做工,可他的家却离街上不近,有十来里路。
做工人家管吃喝,等天黑了才收工吃饭。骑车回家,只见屋里黑灯瞎火,晓得老丈母老丈人已早早睡了。记不得到底有多少年了,老丈母老丈人一直跟他生活。他们是外村人,没儿子,只有女儿,跟嫁到这儿的女儿一路过来过日子,还指望女儿女婿能为他们养老送终。起初一段时间,他们一大家人日子过得像模像样儿,倒还怪像回事。后来好像就又不像回事了,家里人也少些了。记不得是从哪一天起,老丈母他们开始单独过日子,用他家堂屋左侧两间屋生活,一间屋睡觉,一间屋打杂。他跟他们,倒一家不像一家,两家不像两家。他把摩托放进柴屋,来到大门外,开门进屋。做了一大天活路,浑身是汗,就想洗个澡睡觉。刚进卫生间,才开始洗头,他听见屋外好像有人,还喊了他两声。这喊声,好像又熟又不熟,一时却又想不起来到底是哪个在喊他。他也就没吭声儿,继续洗澡,直到洗完澡了才出来。
他穿着裤衩儿,拎把椅子到屋外场子上歇凉,可屋外仍旧闷热,没有一丝风,风都被铺天盖地的热气吸跑了。这一向天太热,晚上,阳光好像仍在烘烤。月亮从对面山上才冒出来,尽管有淡淡的月光,可眼前的东西看起来仍是影影绰绰的。眼下静得出奇,静得好像啥动静都听得出来。刚坐下,他家右边山墙那边好像有点儿动静。他扭头一看,只见朱学仁从屋里出来。朱学仁也穿着裤衩儿,穿着个大裤衩儿,大裤衩儿里边肯定还有个小裤衩儿。朱学仁是他家邻居,他记得,朱学仁差不多就没到他家来过。朱学仁正朝他家走来,边走边说,狗日的,天好热,热死个人。他好像没听见朱学仁说话,觉着朱学仁陡然到他家来,还真有点儿怪怪的。他想,说不定朱学仁嫌天热,出来逛逛,并不是要到他家来。可他又想错了,经过穿过他家跟朱家之间空场地的大路,朱学仁走到他家的场子上来了,大摇大摆地来了。他忙起身,进屋去拎椅子。脚才走过门槛,他又把椅子放到地上,又进屋去找抹布,要给椅子抹抹灰。他也不晓得这把椅子上到底有没有灰,可他还是想拿抹布抹一抹。朱学仁又是村干部,总不能叫人家坐一屁股灰。朱学仁当然晓得他进屋搞啥,说,抹啥抹?你坐过的椅子不早就叫你屁股抹干净了?朱学仁这回说的话,他完全听清楚了,陡然想起来,先头他洗澡时,应该就是朱学仁喊他。朱学仁一屁股坐到他坐过的椅子上,又说,这天好闷人,简直闷死人了。朱学仁这样说,他就又扭身回来,把椅子拎到场子上,在朱学仁身边坐下。朱学仁给他递烟,还递火,这简直就把他搞糊涂了。上门为客,朱学仁到他家来,应该他先递烟,朱学仁倒先给他递烟起来了。朱学仁的打火机喷出明晃晃的火光,自己的烟还没点燃,倒要先给他点烟。这简直叫他经受不起,他不接朱学仁递过来的火,自己把烟点燃了。他边吃烟边想,怪,好怪,朱学仁来找他,到底要搞啥呢?朱学仁说,我有好久没到你这儿来了。到底有好久呢,他也记不得了,只是心里感觉像有好久好久了。朱学仁又说,左邻右舍,还是要常来常往,相互走动走动。他说,那就进屋坐。朱学仁说,不了,屋里热不过,就在这儿坐坐,说说话。他说,我去烧水泡茶,才回來不久,一大天不在屋里,连水都没烧。朱学仁说,我才喝了一大杯酽茶,一点儿都不渴。朱学仁说不渴,他就没进屋烧水,他给朱学仁递根烟。朱学仁拿烟头儿把烟接燃,说,你手艺好,活路做不完吧?他说,还不是有一天没一天?街上的活路马上就做完了,又得等活路做。朱学仁说,呃,李开春给你打过电话没?他这才想起来,早上李开春是给他打过电话,可他当时正撵活路,没心思接电话,加上不晓得是咋搞的,李开春说话的声音又听不好,又没听清李开春到底在说啥。他说,李开春说,好像要做啥活路。朱学仁说,是我叫李开春给你打的电话,村上马上要做个大活路,我想请你来做。他说,做啥活路?朱学仁说,给所有土墙房子涂脂抹粉,穿衣戴帽。尽管他是个大工,可村上的活路他还就一直都没做过。他想,原来,村上一有活路,总是让朱学仁的小舅子魏大银承包,找人做,才怪,这回朱学仁倒要请他这个外人做活路。他说,村上的活路,不是一直都由老人手做?朱学仁说,这做活路,也不能只固定哪一个人做,你要是看得中,过一向就来做做。他简直不敢相信,朱学仁叫他做村上的活路,会是真的,说,看得中,看得中,咋还会看不中?
朱学仁请他做活路,他还是不敢相信。朱学仁起身,又递给他一根烟,才走。看着朱学仁的背影,他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天,林又青又在街上做工,晚上回来的时间跟昨天差不多。把澡一洗,他又坐到场子上吃烟。老丈母从屋里摸出来,说,蒋美菊回来了,你晓得不?他没吭声儿,老丈母又说,她说要找你。他说,她到屋里来过?老丈母说,一大早,她就回来了。这话一说,老丈母就进屋睡觉去了,好像就是要给他透个气儿。
蒋美菊多年不在家,不晓得她到底在哪儿生活,一直要跟他离婚。离婚也不是不行,他只有一个条件,他说,你把你娘老子接走。可她又不能把娘老子接走,再说,她娘老子跟他过日子早就过惯了,又哪儿都不去。这几年,她每年都要回来几回,跟他闹离婚,可他就是不松口。他倒也不在乎,她到底跟哪个男人还是好多男人鬼混,可他就是要叫她永远都离不了婚。她给他戴绿帽子,他也叫她好过不了。今年她还是头一回回来,肯定又要找他闹离婚,他也不怕她闹。
他的电话叫唤起来,果然是她。她问他在不在家,他说还在外头喝酒,吃饭后也不得回去。她又问,他在哪儿吃饭。他说,在能吃饭的地方吃饭。她说,这回回来,还就是想看看你,也不想做啥不开心的事。他说,你也莫给我灌迷魂汤,有本事你就莫回来。他挂了电话,不想再跟她磨嘴皮子。他估摸着,她给他打电话,八成儿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endprint
进山的车路上,晚上也没啥车子,偶尔,会有摩托跑过。刚有一个摩托下去,又有一个摩托上来。摩托的声气越来越大。也不是声气到底有好大,是声气离他好像越来越近。摩托拐弯儿了,一道耀眼的灯光直射过来,一下子照到他脸上,叫他睁不开眼来。
摩托上了他家门前的水泥路,到离他不远的场子边上才停下。车灯熄灭,过一下,他才看得见眼前的东西,猛地发觉,他这辈子最见不得的人骑摩托回来了。蒋美菊穿着连衣裙,在场子上转来转去,看上去,她的腰身倒还细挑。她边转边说,咋的,你也不给我拿把椅子坐?他说,这儿哪儿是你该坐的地方?见场子上没椅子坐,蒋美菊朝屋里走去。屋里没开灯,她带着手电,打开手电进屋。拎椅子出来,她好像又坐不下去,又从摩托后备箱里拿抹布抹椅子。啪啪,见她嫌椅子脏,他朝场子边上狠甩了两口痰。把椅子抹了个够,她才勉强坐下。他说,这椅子,你也坐得下去?她说,这裙子今儿我才穿,糊脏了你给我洗?他说,给你洗衣裳?我还嫌脏。她说,你不是说,还在外边吗?他说,我们又没啥好话说,你还是哪儿好到哪儿去。她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没啥事我还不找你呢。他说,除了离婚,你找我还有啥事?她说,离婚这两个字,可是你先说出来的。说实话,这回回来,我就没打算跟你说这事。他说,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戏?她说,我也晓得,想跟你离婚,没门儿,你那嘴巴,杠子都撬不动。他说,你晓得就好。她说,其实,我心里好想回到从前,好想好想,可我也晓得,根本就回不去。他说,世上后悔药最难吃,你还晓得后悔?她说,我也不是后悔,是觉得我们该心平气和地说话做事,唇枪舌剑,吵来吵去,毕竟不好。他说,你早就连脸都不要了,还管啥好不好?她说,说心里话,我这回回来,就想好好儿玩一回,再就是想跟你缓和缓和关系。他说,莫废话,这根本就不可能。她说,你定个时间,我请你吃饭。他说,吃饭?这辈子不指望,下辈子我也早就想好了,变猪都不跟你同槽。她说,可我还非得请你吃饭不可,这回不跟你在一起吃顿饭,我就不走。他说,那你就试试看。她说,事在人为,我还就不信,连请人吃顿饭都请不动。
林又青才把街上的活路做完,天就下起雨来了。他才起床,朱学仁就来了。猛一下子看见打着伞的朱学仁,他像有点儿恍惚,简直不敢相信真是朱学仁。当时,他才从茅厕出来,连脸都还没洗,本想给朱学仁递烟,可又怕朱学仁嫌他才解手,手脏。朱学仁也不进屋,站在他家大门口,说,走,到我那儿去吃早饭,吃蒸包子。他好像不相信朱学仁蒸了包子,说,咋的,你蒸包子了?朱学仁说,我昨儿晚上发面,今儿天没亮就起來蒸包子,蒸了好多好多包子,有肉包子,菜包子,还有糖包子。早上起来,他还没想起来,自己该不该吃早饭。早上一顿饭,他好像是吃也行,不吃也行。不过,朱学仁叫他去吃包子,他还就想去吃几个,再说,他也想晓得,朱学仁蒸的包子到底好不好吃。他想,朱学仁蒸的包子应该还好吃。他早就听人说,朱学仁的茶饭还怪要得,可他一直都还没吃过朱学仁做出来的饭。他说,要得,我洗脸就去。
朱学仁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女都已在县城成家。朱学仁的屋里人去城里带孙娃儿有好几年了,也就是说,朱学仁是一个人守在老家。
走出自家场子,林又青就闻到了鸡蛋香。朱学仁家,喷喷香的鸡蛋汤已做好了,正等他来喝滚烫的蛋汤,吃热乎乎的包子。
尽管他跟朱学仁是邻居,可他一点儿都记不得自己到底是不是到朱学仁家去过,又像好久好久都没去过,又像根本就没去过。这回好像还是头一回来,他好像就有点儿不自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朱学仁从灶屋里端一大钵子包子出来,放到饭桌上,叫他坐,先吃包子。钵子里的包子个儿不大,椭圆形的肯定是糖包子,同样的圆包子有的点有红点儿,有红点儿的包子要么是肉包子,要么是菜包子。坐到饭桌边,看着这些包子,他好想吃,可他又得等朱学仁来了一起吃。好在朱学仁来得快,眨个眼,朱学仁就端蛋汤来了。朱学仁把一大碗蛋汤放到他面前,说,你咋不吃包子呢?等朱学仁把自己吃的蛋汤端来,坐下来,他才先喝了一口蛋汤。这蛋汤好香,他禁不住又喝了一口,才拿包子吃,拿那种没点红点儿的圆包子吃。他还当这是肉包子,哪儿晓得却是菜包子。蒸包子的面发得好,包子馅儿好,菜包子当然好吃。有红点儿的包子好像更合口,他又吃了两个肉包子。他说,这包子好好吃。朱学仁说,好吃你就多吃点儿,再吃两个。他说,我又只有一个肚子,吃饱了,再也吃不了了。朱学仁说,还有人没吃,莫把你老丈母他们忘了。他没想到朱学仁还把他老丈母老丈人想着,倒还要叫他给他们带包子回去吃,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朱学仁找个干净塑料袋,朝里边捡了十多个热包子,他只好拎上。他正要走,朱学仁又说,呃,反正下雨天没事,晌午我擀手擀面,你过来吃。他说,不了,晌午就不来了。朱学仁说,我一个人吃饭又没劲儿,你就当做来陪我解解闷儿。他说,没事就来。朱学仁说,一定得来,你不来我就不擀手擀面吃。他说,手擀面好吃,我都不晓得有好久没吃过了。朱学仁说,我也有好久没吃,才想解馋。
老丈母正准备弄早饭吃,见他拎着东西来,说,好怪,今儿早上倒有口福,还有热包子吃。他说,快趁热吃。她边吃包子边说,这包子怪好吃,哪儿来的?他说,朱学仁蒸的包子。她说,难怪,今儿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朱学仁还会给我们拿包子吃。他说,莫吃了果子,还说果子酸。
回屋,他也在想,还真有点儿怪,朱学仁咋又要叫他给村上做活路,又要喊他吃饭,倒好像是要求他做啥事。可他又想不出来,朱学仁还会有啥事要求他。朱学仁是能干人,又是村干部,又是村上的一把手书记,咋会求他呢?肯定是正像朱学仁说的,想找个人解解闷儿,这才叫他觉得奇怪。既然想不出来朱学仁为啥要求他,他还只能这样想。
下雨天倒像有点儿烦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不晓得到底该做啥才好。他把昨儿穿的臭袜子洗了洗,又看电视,混混时间,可看电视,好像又看不进去。朱学仁喊他吃手擀面,尽管不是接客,请他吃席面,可也总得在饭前打个电话。要是朱学仁不打电话,他就不过去。正这样想,他的手机就叫唤起来,果真是朱学仁打电话来,叫他早些过去。endprint
雨下得好像小了一点儿,他也懒得打伞,几步就跑到了朱学仁家的山墙外。他没急着进屋,在朱学仁家屋檐下的走道上站了站,听了听屋里的动静。噗嗤噗嗤,好像只听得出像是擀面的声气,他才进屋。
朱学仁正在拿擀面杖在桌上擀面,已擀了一坨面出来。桌边的一个小方桌上放着筛子,筛子里放着切好了的面。正擀的一坨面也擀得差不多了,唰唰唰,只见朱学仁的双手在唰唰唰地擀面。擀面杖被越擀越薄的面皮儿包裹得紧紧的,朱学仁从怀里的桌边把面搓擀到对面的桌边,把擀面杖又收回来,把面皮儿摊开。唰,面皮儿掉个过儿,又擀了起来。
等这坨面擀好,把面皮儿折叠起来,要切了,朱学仁叫他把筛子里的面送回去,给两个老的下着吃。他说,算了,莫管他们了。朱学仁说,拃把远,两步路,你就送一下,给他们安顿好了,我们才吃得踏实。
朱学仁家灶屋里有柴火灶,也有液化气灶。朱学仁用液化气灶炒菜,炒了四菜一汤,又叫他把一个菜一个汤给他老丈母老丈人送去。说来也怪,他把给他们要吃的菜一送回去,雨就下大了。
他还当朱学仁家的晌午饭还有别人来吃,可好像又没有。他说,就我们俩吃?朱学仁说,咋的,你还嫌吃饭人少?他说,那倒不是。朱学仁边朝桌上端菜边说,我们就先吃饭。手擀面也下好了,朱学仁拿大碗捞面,捞了两碗。
菜是好下饭菜,能叫人多吃饭。手擀面吃着香,他就吃了两碗,心想才怪,朱学仁只叫吃饭,简直又不像待客,咋就不提说喝酒呢。他正这样想,朱学仁说,差不多吃饱了,我们再来喝点儿酒。他说,酒就不喝了。朱学仁说,无酒不成礼仪,酒还是喝一点儿,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他说,那就喝点儿啤酒。他想,人家都是先喝酒后吃饭,朱学仁这人才怪,偏偏要先吃饭后喝酒。朱学仁说,这鬼天,下了两天雨,还这么闷热。立体电扇放在朱学仁背后吹着,朱学仁说,要不,把电扇放到你那边去。他说,我不大热,也没出啥汗。朱学仁嘿嘿一笑说,还是你身体好。朱学仁起身,打开冰箱,拿两瓶冰冻啤酒出来,先打开,朝一次性塑料杯里倒。他赶紧嘱咐说,莫倒多了。朱学仁说,要得,喝酒随便,不勉强。朱学仁就只倒了半杯酒,倒了两个半杯。两个人开始喝酒,各自抿了一口。他说,这酒喝着怪爽口。朱学仁拿了两包烟来,给他甩一包,打开一包,递烟给他,还递火过来。火他没接,自己拿打火机点烟。烟是十八块钱一包的软盒黄鹤楼,吃着怪顺口。朱学仁咂两口烟,说,人就是个怪东西,就说这喝酒,一点儿不喝,吃饭好像又缺个啥,喝又喝不了多少。他说,酒还是少喝好,喝多了误事。朱学仁说,今儿下雨,横直又做不成个啥,能误个啥事?他说,那就喝酒。见朱学仁两口把半杯酒喝了,他也喝了。朱学仁要给他斟酒,他叫朱学仁把另一瓶还没打开的酒打开给他。斟酒,他斟了一个满杯。他说,感谢你看得起,我敬你一杯。先喝为敬,咕咚咕咚,他先喝了。朱学仁说,今儿我们不喝敬酒,平着喝。他说,平着喝,我哪儿喝得过你?朱学仁说,看你说的,那是啥话?又不是比酒量,能喝多少是多少。朱学仁说,呃,莫光只顾得说话,吃东西,吃菜吃菜。尽管朱学仁没做好多菜,可菜样样儿都炒得合口,怪有口味儿。他吃几口菜说,没想到你这几年在屋里也成了一个光杆司令,變得跟我一样了,来,喝酒喝酒。朱学仁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说,话说回来,你不当光杆司令,菜也炒不到这好。朱学仁说,要说做饭,年轻时我就在练手艺,那时就想当个厨子,可后来厨子又没当成。朱学仁喝口酒又说,我们屋里自来就是我做饭,自己会做饭怪好,不受憋,想吃啥就能吃到嘴。他说,那倒是,其实我才是光杆司令。朱学仁说,光杆司令有光杆司令的好处,来去自由,无牵无挂。他说,这倒也是,一个人过日子倒也怪好。朱学仁喝口酒,说,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稀奇。他说,啥稀奇?朱学仁说,那天大晌午,太阳像一个大火球,挂在天上,我看见两个熟畜牲,身上根纱不挂,在一个好多年没人住的空房子里做活路,地下只铺着一个床单子,我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事。
呃,怪,好怪,朱学仁咋想起来要说这种怪话?这又是唱的哪一出戏?是不是想套他的话?他愣了愣,不晓得自己的话到底该咋再朝下说才为好。他憋了憋,想了想,还只能就话说话。他说,那是哪两个熟畜牲?朱学仁说,不能说,说不得。他说,刚我只是随便说,到底是哪两个人,你可千万莫说出来。朱学仁说,这事是不能说。他说,宁看狗连裆,莫看人成双,看不得,看了背时。朱学仁说,啥看得看不得?又不是我要看,人家撞到我眼睛了,已经是已经,管它背不背时。他说,背不背时,也只是一个说法。朱学仁说,我看也是,我还就不信,看见那事就会背时。他说,就是,那两个畜牲也是贱,大天白日,咋要偷偷摸摸做那个活路。朱学仁说,呃,你看见过没,就没看见过?他好像想了一想,憋了一下。本来喝酒就上脸,这一憋,脸好像就又憋得更红了。朱学仁的眼睛在逮他的眼神,可又逮不住,他根本就不敢看朱学仁。实在憋不住了,他才说,这就像在路上捡钱,我活了差不多大半辈子了,都还没捡到过一回。朱学仁说,不会吧,你心深,不想说。他说,我眼睛笨,真没看见过。朱学仁说,你是个大工,天天到处跑,就真没看见?猛一下子,他心里好像就有点儿痒痒。实际上,就只差一点点儿,他就会说出点儿啥。他说,我要是看见,还能不说?朱学仁说,莫光说话,忘了喝酒。他说,喝酒喝酒。两个人又喝酒,喝过酒,朱学仁说,没看见就没看见。他说,其实,啥时候都有人做这个活路,可我就没看见人家做过。朱学仁说,你还觉得不该没看见?没看见才好哇。
他去上茅厕解手,心想才怪,朱学仁咋要跟他说这种事。他从茅厕回来,朱学仁又说,蒋美菊回来好几天了吧?他说,你看见那个贱货了?朱学仁说,没看见,只是听说。他说,那贱货回来不回来,跟我一点点儿都没啥关系。朱学仁说,呃,你们又没离婚,你该接她回来吃顿饭,缓和缓和关系,最好能再留她歇一晚上。他说,秃子头上的毛,它不长,我也不想。朱学仁说,你就一点儿都不想?你们既然没离婚,她就还是你的合法妻子,你就是强迫她,也受法律保护。他说,说实话,她就是想跟我睡,我还嫌她脏。朱学仁说,那你到底想不想呢?他说,不想,不做那事,也早就习惯了。朱学仁说,我就不信。他说,呃,你肯定还厉害。朱学仁笑笑说,你呀,是高看我了,我也老了,这两年身体就差多了。他说,谁信?反正我不信。朱学仁哼了一下,好像不相信他的话,又说,这多年,都不晓得你是咋过过来的。大概是酒喝多了,酒撵话出,他说,我是真不行,早就不想那事了。朱学仁说,听说有的女人就因为男人这方面不行,才要离婚。他说,这也不能怪,人能活几辈子?能快活,为啥不快活?朱学仁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你们俩,干脆和好算了。他说,那个贱货,她不叫我好过,我也不叫她好过,反正要叫她离不成婚,就是拖,也得拖死她。朱学仁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他说,贱货没找你说啥话吧?朱学仁说,我既没碰见她,她也没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跟那下贱货,是一辈子的冤家对头。朱学仁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要不,我找她说说?他说,千万莫找她,你找她,她还当我想讨好她。朱学仁说,行,你们的事还是你们自己解决,来,喝酒。正要喝酒,他的手机叫唤起来。是魏大银给他打电话,请他做村上的房屋改造活路。魏大银还是头一回找他做活路,接过电话,他好像还有点儿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说,村上这回做活路,还是由魏大银承包?朱学仁说,胳膊拗不过大胯,不是我要魏大银包活路,是乡上领导指定要他包。他说,魏大银说,天一晴,就开始做活路,我不管乡上指定哪个,也不管到底哪个包活路,有活路做就行。朱学仁说,这活路一做就会做好几个月,今年够你做的。他不大信魏大银,只信朱学仁,朱学仁这话一说,他好像才吃了定心丸。endprint
给村上土墙石瓦房子换瓦刷墙,是今年乡上计划实施的农房改造惠农项目。有项目资金作保障,就是说,谁家符合条件,想改造房子,只要申请,乡上审核批准,要改造房子的人家基本上也不用花啥钱。除了常年不在家的,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要改造房子。村上有五个小组,改造房子,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斧头,从一组最靠近街上的农房改起。魏大银既是包工头儿,又是大工,他跟魏大银负责做油漆门窗,给内外墙涂抹白石灰的活路。
半个月过去,他们改造了八户农房。有一天大清早,他去上工,发现原来的土房子一改造,刷上白石灰的白花花的外墙,看上去倒还怪惹眼,就像看着顺眼的女人穿上了好衣裳,看着更顺眼,咋看都顺眼。他心里还就想到了村上那几个看着还顺眼的女人。
这两年,乡上扩大集镇范围,搞新农村居民小区建设,盖了好多栋两层楼起来,吸引人去生活。房子水电路配备齐全,还做了简单装修,价钱便宜,可就是不走俏,价位一降再降,买房的人还是不多。听说蒋美菊买了一套两层楼,他还就不信。这天,朱学仁又跟他说,蒋美菊是在乡上的新小区买了一套房子,你也不去看看?他说,狗球,贱货还会在街上买房子?朱学仁说,听说是给林克平买的,你不晓得?林克平是他和蒋美菊的儿子。林克平上过县上的技校,技校一毕业就外出打工,打工也有好几年了。平常他跟儿子联系就不多,他只晓得林克平想在县城买房子,还想他拿几万块钱出来。他没答应,不晓得朱学仁说蒋美菊在乡上买房子给林克平成家用,是不是真的。
晚上,朱学仁摸过来玩,跟他坐在场子上歇凉,喝茶吃烟。朱学仁说,明天晚上,我陪你走个人家。他说,晓得你说去哪儿,反正我不去。朱学仁说,不去,你可莫后悔。他说,我能后悔啥?朱学仁说,这两天,我还一直就在想,你要是去那儿,只看你能耐咋样,能不能在那儿歇一晚上。要不,我们俩就来打个赌,赌一条烟,一百八十块钱一条的黄鹤楼,你要是能在那儿过夜,算你赢,我给你买条烟,相反,你就给我买条烟。他说,就那简单?看来,我能吃一条便宜烟了。朱学仁说,莫吹牛,真有那能耐?他说,你也莫激将人,赢家肯定是我。朱学仁说,没想到就为了打个赌,你那想赢。他说,好烟我当然想吃,可也不光是为这,还不是因为你面子大?朱学仁说,那就说好,明天晚上我们一路去街上吃饭。
蒋美菊接客吃饭,屋里并没旁人,好像就只接了他们俩。吃喝在一楼,客厅里竖着一个空调,楼上卧室里也有一個挂式空调。蒋美菊在楼下灶屋里炒菜,用的是液化气灶。卧室还有一个阳台,朱学仁说,这屋住得,又有空调,热天要多凉快有多凉快。朱学仁话中有话,眼神透着一股邪气。
三个人吃饭,随便喝了一点儿冰冻啤酒。晚饭一吃完,朱学仁就说有事要走。朱学仁说他,你就莫走了,反正你们有两个家,这儿一个,村上一个。猛一下子,他又不晓得到底该咋接朱学仁的腔,倒是蒋美菊接腔了。她说,朱书记,你晓得你自己到底有好多家不?朱学仁说,看你个蒋美菊,刻薄话才多。她说,朱书记的家比谁都多,晚上肯定不得回家吧?朱学仁说,不回家,那我在你这儿睡?她说,朱书记,你也莫异想天开。出门,朱学仁边上摩托边说,我想个屁,也不耽搁你们做好事了。
当晚,林又青没回家。蒋美菊的邻居也证明,他第二天一早才走。朱学仁跟他打赌,输了。朱学仁说话算话,真的给他拿了一条烟。
一晃就到了秋天,农房改造改到最后一个组,总算快改完了。紧靠邻村的最后一户人家,屋里的女人姓魏,名叫魏爱云,人长得看着还怪顺眼。越靠近魏爱云家,他越是心神不定。
天下事无奇不有,只是他根本没想到,他会撞见她做那个事。他记得,那一天好像就是今年热天最热的一天。自从那天看见她起,他就再也没碰到过她。
那一天好像就跟做梦一样,鬼使神差,阴差阳错。
那一天晌午,阳光滚烫滚烫,村上满是耀眼的白光,天热得好像比啥时候都厉害。他从外村回来,渴得要死,横直想找水喝。摩托跑进本村,就像是回家了。看见头一户人家,有三间正屋,一间偏厦儿,大门敞开,他就把摩托停在车路边,朝那户人家走去。那户人家,他好像还从没去过,并不晓得到底是哪一户人家。要怪就怪他耳朵尖,尽管无数知了在拼命叫唤,叫得人心烦,可他还是听得出来,哪儿有一点儿动静好像不对劲儿。这儿又没有旁的人家,要说哪儿不对劲儿,还就只有那户人家。怪,好怪,越靠近那人家,他就越觉着怪,就想悄悄看个明白。他像做贼一样,轻手轻脚地摸过去。在大门口,他站了一下,朝屋里看看,确信那怪动静就在堂屋左侧的正屋里。那间正屋又是眀一暗二,也就是两间屋,里边一间,外边一间,里外房门又都敞开着。进堂屋,在外间屋门口,他探头一看,没看见啥。里间屋却又叫他看了后悔死了,屋里的床上好像有耀眼的白光,只见两个人正在做活路。床铺在屋当中,他们头朝门口。魏爱云在上面,眨眼间,她也朝他看了一眼。他愣了愣,赶紧溜走。他当然认得魏爱云,这才晓得她住在这儿。老实说,他并没看清当时跟魏爱云在一起的那男人到底是谁。那人当然不是她男人,听说她男人不在家。他想,就是天再热,也不能敞着门做那事。大概他们俩盼做那事,盼了好久好久,一凑到一起,都急不可耐,根本就不会想到热死人的晌午还会有人来。可那人到底是谁,他还就一直都没想明白。
魏爱云却没在家,她家的屋别人在租住。当然,房屋她还是要改,委托租住人代她招呼改造。租住人说,她出远门了。魏爱云到底在哪儿,啥时回来,没人晓得。
给魏爱云家那间叫他看了后悔死了的屋刷内墙时,他好像又看到了她。猛地一下子,他想,那个他没看清的人会不会是朱学仁?要是,朱学仁又到底明不明白,他到底看没看清,晓不晓得那是谁个呢。怪,他好像这才想明白,可又像还是不明白。
责任编辑:李 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