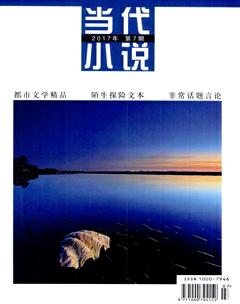你叫什么名字(短篇小说)
郝炜华
1
小高层四个单元,邻里之间素无来往,每户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做什么工作,家中几口人,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所以一单元突然死了人,大家都不知道死的人是谁。
敬修兰夹在几个女人中间,看着一单元门口的男人忙来忙去。他们在两棵树之间拴上白绳,白绳上搭了十几个花圈,花圈前摆了一张桌子,两个男人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个白纸钉成的本子。
一上午,不断有人在桌子前停留,掏出数目不等的钱递到男人手里,男人将钱放进一个黑皮包,然后在本子上写下名字。敬修兰知道那些人是前来送葬的,拿出来的钱叫做“募资”,帮助丧主办理丧事。
敬修兰在农村长大,小时候经常看到村子里死人。一个村百十来户人家,五六百口子人,不管死的是谁,老人、大人还是小孩,村里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多大年龄,长什么模样,年龄大的甚至叫得出小名。
小高层四个单元,88户人家,加起来不到三百口人,死的是谁,大家却不知道。这种情形,怎么说怎么说不过去,敬修兰和几个女人不约而同从家里出来,站在楼底下,猜测死的那个人是谁。
有人猜是那个一头卷发、身体瘦瘦、走路一踮一踮的女人。马上有人否认,“今天上午刚见了她,她突然冲我一笑,弄得我不知说什么好。”
有人说是刚从外地调来的英语老师,英语老师讲课讲得好,死了真是可惜。马上又有人否认,“英语老师是男的,死的是女人。花圈的挽联写着沉重哀悼师母。”
是女人吗?大家都想到花圈前看看,可是花圈前坐着两个男人,她们兴师动众地去看,显得很没礼貌。
这时候,小区的保安走来了,晃晃悠悠的,仿佛被一肚子秘密压得走不动路。小高层偶尔会传出一点消息,比如七楼的男人在商业银行上班,十一楼的女人生了二胎,大家都说消息是小区保安传出来的。有人特意为这事找物业,嫌小区保安泄露业主隐私。
从前,大家都不愿意跟保安多说话,现在忙不迭地打听消息。保安说:“死的是个女人,四十六岁,野外登山时掉下来摔死的。”
野外登山,小高层的人都不陌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城市里的人时兴到野外游玩,哪里偏僻,哪里不好走,就到哪里去。他們还有个难听的名字,叫做驴友。小高层的很多人是驴友。
可是登山掉下来摔死,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有这个可能。”一个女人说:“我们村有座山,山顶有条沟,叫作仙人跳,意思只有神仙才能跳过去。有人偏偏不信,仗着爬山经验丰富,也要跳,一不小心就跳进沟里,沟下就是悬崖,十几层楼高,人掉进去,除了死,没有别的出路。去年冬天,有人掉进去,尸体都捞不上来,家里人趴在沟边,哭了一场了事。”
“出事的,都是艺高胆大的人。”另一个人接过话去,“我们村有个水库,每年都要淹死人,淹死的都是水性好的人。”
围绕这个话题,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一说才知道大多数人都有在农村生活或是户外活动的经历,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类似的故事。听着故事,谁出生在农村,谁喜欢游泳,谁喜欢爬山,谁喜欢打球,也就分析了出来。
眼见的到了中午,太阳晒了起来,她们越说越热闹,声音跟着大起来。
坐在花圈前的男人向她们瞅了无数遍,这时突然站起身,拿起黑皮包和白纸本子往桌上一拍,转身进了单元。一个男人似乎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两手把住单元门,身子一倾,“咣”的一声,将单元门带上了。
2
按照北城风俗,丧事办完,办丧事的人家要在房屋显要位置贴出白纸,罗列送葬人的姓名,以示感谢。第二天,那户人家就在小高层东墙贴出白纸,上面写了很多人的名字。赵钱孙李周武郑王,诸般姓氏都有。可是敬修兰只记住了一个名字——宋茉莉,是那个死去女人的名字。
一晚上,敬修兰都在念叨“宋茉莉”这个名字。
祝季男准备回老家,一边收拾行李,一边骂敬修兰,“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念叨,不怕把鬼招来。”
敬修兰拉开阳台的窗户往外瞧,天色墨蓝,明月高悬,昏黄的路灯照着灰色的水泥路面。一单元的门口没有花圈,没有桌子,拴在两棵树之间的绳子也无影无踪。关于宋茉莉的一切,如同一阵风,呼的一声刮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宋茉莉,宋茉莉。”敬修兰听到有人轻轻叫着,扭过头,看到一个人影站在墙角。人影模糊,仿佛一滴墨滴进水里。“宋茉莉,”人影说:“你叫什么名字?”
敬修兰吓了一跳,“呀”的一声,蹲到地上。祝季男跑过来,到处看,哪有模糊的人影。他点了一下敬修兰的脑袋,说:“你呀。”
祝季男回家是因为他的大表哥死了。大表哥常年在外,极少跟家里人联系。昨天,家里突然接到警察的电话,说大表哥死了,尸体停在医院太平间。
第二天,敬修兰送祝季男去火车站。走到小区门口,遇到那个一头卷发、走路一踮一踮的女人。女人看着敬修兰与祝季男,嘴唇一分,突然笑了。敬修兰习惯了女人的冷漠,乍一看女人笑,一下反应不过来。等到想到应该报之以微笑时,女人已经走远了。
敬修兰拍了祝季男一下,说:“不送你了,自己打车走吧。”
追上卷发女人时,两人已经到了小高层一单元的门口。敬修兰喊了一声:“大姐。”女人停住脚,回头看敬修兰。
敬修兰不知道女人大还是她大。不管谁大,敬修兰都想喊她“姐”,这样才能显出尊重。
女人嘴唇一分,又要笑。趁着那个笑还没出来,敬修兰先把笑堆到脸上,说:“大姐,跟你打听个事。”
“什么事?”
“你是不是数学老师?”
女人自然不是数学老师,但她将职业告诉了敬修兰。她在环保局工作,负责查办企业污染,有时三更半夜跑到郊外的工厂。昨天晚上,去了一家皮革厂,一进门,污浊的气体熏得她差点晕过去。
两个人站在单元门口,一声递一声地说话,身旁就是曾经拴着白绳、搭着花圈的那两棵树。树是小区刚建成时种的,原来只有小孩胳膊粗,现在长成男人大腿般粗细。endprint
晚上,祝季男打来电话,说大表哥死在一个小树林里,警察发现时,已经死一个月了。因为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所以联系不到家人。好在警察负责,将他冻在医院的太平间。有一天,看守太平间的老头闲着无事,翻大表哥的衣服口袋,突然翻到一张暂住证,这才联系到家人。
“看太平间的老头都能翻到暂住证,警察为什么翻不到?”
“我也在想这件事。兴许大表哥想家里人了,弄了暂住证自己塞口袋里。你知道的,大表哥活着的时候,就神神叨叨的。”
这个大表哥,敬修兰有印象,高瘦、白脸、长发,怎么看怎么不像祝季男村里的男人。祝季男村里的男人都长得健壮,农忙时,在家里干活,不忙就在城里打工,春节放假则聚在一起喝酒、打牌,有时也打麻将。祝季男的大表哥不喜欢做农活,不管是不是农忙,都在家里研究周易和书法。别人家的庄稼跟果树一年收入五六万,他家的连一万都收不到。敬修兰与祝季男结婚时,大表哥穷得礼金都拿不出来,给敬修兰算了一卦,当作贺礼。
前年大表哥突然时来运转,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到度假村做形象代言人。度假村寓在深山,锦山碧水,绿树成萌,是个风景优美的所在。
大表哥穿着灰布长衫,脑后扎个小辫,拿把折扇坐在书案前,既有仙风道骨的古人模样,又有风流倜傥的现代艺术家风范。每天不是看书写字,就是给游客看手相、面相,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自从去了度假村,大表哥就极少跟家里人联系,电话没有,人更是见不到。家里人最近一次见他,还是今年春天,大表哥坐在书案前,拉着一个女人的手谈得正欢。
祝季男没跟敬修兰说大表哥怎么从度假村去了小树林,也没说大表哥是自杀还是他杀。只说:“村里人看大表哥活得不像话,其实他心里很苦。嫌村里人没有文化,他苦。到了度假村,遇到真正的文化人了,人家又嫌他没有文化,所以他也苦。”
3
“郑梦龙,郑梦龙。”睡梦中,敬修兰听到有人大声叫着。
郑梦龙是祝季男大表哥的名字,好好的,跑到她梦里叫什么。敬修兰吓出一身冷汗,一下坐起来。影影绰绰中,看到一个人站在墙角,说:“郑梦龙,郑梦龙,你叫什么名字?”
敬修兰尖叫一声,扑下床,打开灯,四下明亮,根本没有人影。敬修兰赤着脚,在房间里乱走。所有的灯打开了,所有的地方找了一遍,包括床底下和橱子里,根本没有人影。
难道真的闹鬼了不成?敬修兰抱着头,坐在沙发上,瑟瑟发抖。突然,她觉得沙发摇了一下,接着墙壁、地板跟着一起摇起来,吊灯、电视、桌子像映在水面上的倒影晃动起来。天呀,地震了!敬修兰拉开房门,跑了出去。
楼底下静悄悄的,昏黄的路灯在水泥地面投下淡淡的光影。敬修兰抬头看小高层。小高层又高又薄,像一块纸片插入墨蓝的天空。天上没有月亮,只有稀疏的星星。
“在宇宙中,地球是孤独的。在地球上,人是孤独的。”不知道为什么,敬修兰想到了这句话。照这样推理下去,在小高层面前,她也是孤独的。
敬修兰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假如她在小高层里突然死去,那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叫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在哪里工作,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手机号码。她会像祝季男的大表哥一样,在房间里躺着,一天、两天甚至三天都不被人知晓。
回到家,敬修兰就给祝季男打电话。凌晨三点,正是人睡得最香的时候,祝季男被吵醒肯定烦得不行。可是敬修兰不管那么多了,她一遍一遍地拨电话,让祝季男的手机铃声一遍一遍地响着。终于,祝季男接了电话,没等他发火,敬修兰就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喊:“祝季男,祝季男,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呀?”
敬修兰决心做一件令小高层所有人都吃惊的事——请大家在楼下聚餐。
祝季男认为敬修兰的神经出了问题,想带敬修兰到医院看病,又怕刺激了敬修兰,因此一看敬修兰就唉声叹气,愁得不行。
敬修兰不管神经不神经,执意要喊小高层的人聚餐。她站在小高层的东墙边,也就是办丧事那户人家贴白纸的地方,挨个问经过的人是否愿意聚餐。因为与小高层的人不熟,敬修兰闹不清谁是住户,谁是访客,所以很多到小高层串门的人就被她打扰了。有人不高兴,冲敬修兰翻白眼,骂她“神经病。”
这声骂恰巧被祝季男听到了,祝季男越发认为敬修兰的神经出了问题,他往家里拖敬修兰,敬修兰不走,蹲下身,突然哭了。
這时候,那个一头卷发、身体瘦瘦的女人从单元门里出来,走到敬修兰身边,说:“不要哭,这个聚会,我参加。”
风吹过来,贴在墙上的那张白纸,发出“刷拉刷拉”的声音。女人死了半个月了,白纸被风吹破了,四角翘起来,眼看着贴不住了。
卷发女人说:“我跟她住对门,好好的一个人,突然没了,我却不知道她叫什么……所以这个聚会我要参加。”
卷发女人决定跟敬修兰一起请小高层的人聚餐。事实证明,站在楼前喊人没有效果,她们决定挨家挨户敲门。敲门遇到的情况各种各样,有人透过猫眼看她们,说:“不认不识的,聚什么餐。”有人将门打开一条缝,一条腿抵在门边,用警惕的目光看着她们,问:“你们是不是骗子或是推销东西的?谁叫你们进来的?”
敬修兰跟卷发女人不敢嫌他们态度冷漠,因为她们平时就是这样对待敲门的陌生人的。有段时间,敬修兰的母亲在她家住,听到有人敲门,母亲不问是谁就开门。到楼下拿奶或是送人,大敞着屋门就出去。为了这事,敬修兰跟母亲谈了无数次,列举了无数件入室偷盗、进门杀人的案例教育母亲。母亲听了,不但不接受,还生气地说:“我们农村的屋门、院门整天开着,也没人偷东西,更不可能杀人。”
小高层的四个单元转遍了,只有三户人家答应聚餐。敬修兰与卷发女人都感觉失败,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
最后,两人决定,即使只有三户人家参加,聚餐也要举行。
突然,卷发女人问敬修兰,“你叫什么名字?”
“是呀,都忘问你了,”敬修兰一拍沙发,“你叫什么名字?”endprint
4
小高层所在的小区狭窄,除了水泥路就是楼跟楼之间的绿化带,绿化带种满草与树。聚会需要地方,水泥路上人来人往,放不下一张桌子。敬修兰相中绿化带,在绿化带中间安一张石桌,既可用来聚会,又可用来平日休闲。
找物业商量,物业一口答应,说:“小区里的人互不往来,我们早就看不惯了。”
星期天,敬修兰发动祝季男,卷发女人发动她老公,四个人在绿化带中间安石桌。石桌是从市场买的,方方正正,又宽敞又平整。敬修兰与卷发女人清理草皮,祝季男与卷发女人的老公和水泥、安石桌。太阳晒得厉害,四个人很快出了汗。敬修兰回家拿凉开水,抬头一看,小高层的很多人趴在阳台上向下看。
开水拿下来,绿化带里多了七八个人。
他们说:“平时窝在家里不运动,除了长肉还是长肉,趁这个机会运动运动。”说完,一齐动手,铲地、搬桌子、和水泥、抹水泥,一上午的时间,石桌安好了,周围还摆上六张石凳。
一个女人说,再铺条石径才好,微雨时节,石径上洒满水珠,草和树的叶子绿得发亮,我们坐在石桌旁喝茶、聊天,那种情形,想想都美。女人话音刚落,一个男人说:“铺,一定要铺。没有石径路,在草地上踩来踩去,不长久。咱们得做长久打算。”
男人说完就去买铺路的石子,石子没买来,买来了广场砖,红的绿的蓝的黄的白的广场砖,比石子还要好看。大家一齐忙活,一条漂亮的小径铺成了。微风吹拂,绿草成茵,五颜六色的小径好像一条彩虹一直连到水泥路上。
聚餐定在下星期六晚上,不管三户人家参加还是五户人家参加还是七户人家参加,一定要如期举行。有人提议一家炒一个菜端出来,邻居聚会就要尝尝各家的手艺,所以这个菜一定得是各家最拿手的菜。
星期六晚上到了,敬修兰与祝季男先端了菜出来。祝季男会做菜,嫁给他之后,敬修兰很少到饭店吃饭,偶尔去一次,也是为了批评饭店的菜做得不好吃。祝季男做了两个菜,一个是肉末酸豆角,肉末是雪花肉剁的,酸豆角是祝季男自己腌的,配了红色的朝天椒,又酸又辣,好吃得不得了。另一个菜是松菇炖山鸡,祝季男特意跑山里买的山鸡,光汽车的油钱就比鸡贵。两人将菜摆好,卷发女人与老公也端着菜来了,他们做的是番茄鱼。白白的鲤鱼肉浸在红色的番茄汤里,上面漂着碧绿的葱段,一看就叫人想吃。除了菜,卷发女人还带来一瓶法国葡萄酒。
陆陆续续,又有人端着菜出来。这些人有的是前几天答应聚餐的,有的是帮忙安石桌的。端的菜有糖醋排骨、干锅豆腐、姜汁藕片、川味鸭块……还有人包了胶东大蒸包,牛肉馅的,大小差不多的肉丁结结实实地压在一起,又香又筋道,咬一口,没等嚼,肉汤先滴到手上。
菜、包子摆到石桌上,气氛一下热闹起来。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才知道,除了敬修兰、祝季男、卷发女人和她老公,其他人都不知道彼此叫什么。有的人看着面熟,便喊:“养吉娃娃的老赵。”“十一楼的短发。”更多的人不面熟,他们不停地问:“你叫什么?”“你叫什么?”“你叫什么?”
敬修兰起身回家,回来时,手里多了红色的硬纸片和一盒大头针。她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写到硬纸片上,裁下来,用大头针别到主人的衣服上。
大家低头看身上的纸片,都说这样好,省得一遍一遍地说自己的名字,省得别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省得老去问别人的名字。为了防止彼此忘记对方的名字,他们建议,这张硬纸片要保留好,只要一进小区的门就别上,就像上班必须戴工作牌一样。
不知不觉,端着菜出来的人多起来。令敬修兰惊奇的是,他们衣服上都别着一张纸牌,纸牌上都写着自己的名字。纸牌各种各样,红色的、绿色的、咖啡色的,还有看不出颜色的,纸牌上的名字也各种各样,“赵永刚”、“王静怡”、“高上”、“花兰兰”……先来的人都念后来的人的名字,也都知道了后来的人叫什么。
菜太多了,石桌上放不下,就放小径上。男人把石凳让给女人坐,他们站在石桌旁或者盘腿坐在小径上吃。很多人感慨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大家常常凑在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大爷”、“叔叔”、“哥哥”、“兄弟媳妇”、“嫂子”地叫着,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都亲得像一家人。就连平时闹了矛盾的人家,这个时候也会脸对着脸说话。
小时候多好啊,农村多好啊。到了城里,住进了小高层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不仅城市变了,小高层变了,现在的农村也变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说:“年轻的时候,我回老家,村里人都请我吃饭,一家接着一家,不去还得罪人。现在回去,没人请了。”
“是呀,是呀,我們村也变了。现在不是时兴修家谱吗?我爸出钱修了家谱,免费送给村里人,村里人连声谢谢都不说,有些年轻人甚至不要,说‘将来还不知道住哪,要这玩意儿干什么。”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在的农村也不是以前的农村了。大家都说,不管现在的农村变成什么样,小高层要保持过去农村的样子。所以小高屋不能叫小高层,小高层得有个名字。什么名字?叫桃花村吧。像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一样,不管外面战火纷飞,朝代更替,小高层都要保持纯洁、古朴的民风,都要鸡犬之声相闻,邻里和睦共处。过年时相互拜年,遇有红白喜事相互来往。为了增进感情,聚餐要定期举行……
“不行,不能叫桃花村。那个女人,死的那个女人,是从桃花山上掉下来的。”
5
桃花山,敬修兰知道的。在城市的南面,山顶有座石头建成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听说是清光绪十一年,一名美国神父建造的。敬修兰与祝季男曾去教堂参观。偌大的院子,只有一名做过兔唇修复手术的男子。男子说:“刚刚做完弥撒,信徒都散去了。”
敬修兰与祝季男驱车下山,遇到两个老年妇人拦车,一问才知道,她们是到教堂做弥撒的信徒,住在更南边的山上。今天早上五点半从家里出发,步行到教堂。弥撒结束再步行回家。走到下午一点半了,累得实在走不动了。
敬修兰叫老妇人上车。老妇人上车便跟敬修兰传道,说她们村有个男人欠了另一个男人的钱,想赖账不还。两人就到村支部评理。村支书怎么问,赖账的男人都说没欠钱。一筹莫展之际,村支书想到两个人信天主教。他找了一张耶稣像挂到墙上,问欠帐的男人:“你敢守着上帝的面说自己没欠钱吗?”男人嘴唇张了半天,终于承认,“我欠他的钱。”endprint
“信主的人还会赖账?”
“信主有信得好的,有信的不好的。这人信得不好,所以受到了主的惩罚。有一次,他到集上买菜,嫌卖菜的秤数不够,从包里掏出十字架,叫卖菜的当着十字架的面再称一遍。卖菜的不光没称,还打了他一耳光。主借着这个事惩罚了他。”
女人是爬桃花山看天主教堂时掉下来的吗?
马上有人否定了敬修兰的猜测。说女人不是爬桃花山,女人爬的是摘星山。摘星山——“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仅仅听名字,就知道山很高。可是,女人不是爬山时掉下来摔死的,是快到山底时,摔了一个跟头,滚到山底的水塘,淹死的。
女人跟着驴友团爬摘星山,下山时,碰到一只受伤的老鹰。一名男驴友抓了老鹰的翅膀,想将它带到山下疗伤。老鹰本来安安静静的,快到山底时,突然挣扎起来,爪子将男驴友的手、肚皮和腿抓伤了。
大家都说男驴友下山必须打狂犬疫苗或者破伤风针,女人却说不用。因为只有被哺乳动物伤着了,才需要打狂犬疫苗;只有被家禽伤着了,才需要打破伤风针。老鹰既不是哺乳动物也不是家禽,所以不用打狂犬疫苗或者破伤风针。
没有人信女人话,女人是什么职业都不清楚,凭什么要信她的话。有朋友在医院工作的打电话向医院咨询,有朋友在防疫站工作的打电话向防疫站咨询。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医院的朋友说狂犬疫苗或者破伤风针归防疫站管理,需要向防疫站咨询。防疫站的朋友说被老鹰抓伤,属于伤口处理,需要向医院咨询。
“有在林业局工作的吗?”女人问:“老鹰是在树林里拣的,树林归林业局管理,应该到林业局治疗。”
聚餐的人笑起来。像女人刚死那天,站在楼前头议论摔死或者淹死的都是艺高胆大的人那样,他们说起各个部门相互推诿,相互推卸责任的事。这些人不是在企业机关或者政府部门工作,就是跟企业机关和政府部门打过无数次交道,所以都能讲出一大堆这样的事。每件事都很精彩,每件事都很热闹。他们一边说一边听,一边听一边说,不时爆发出热烈的笑声。
那个女人怎么摔了一个跟头?怎么就滚到了水塘里?水塘很深吗?女人不会游泳吗?其他驴友没有救她吗?好好一个人,怎么说死就死了?这些问题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问了。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不知谁的手机响了,一开始铃声很低,像条细小的蛇在人群间游走。突然,铃声高了起来,“茉莉花呀,茉莉花。”
四下一下安静下来。所有的人,兴高采烈地说着、兴致勃勃地听着的人全都安静下来。他们想起来了,死的那个女人名叫宋茉莉。这个名字,他们都是从贴在东墙的那张白纸上看到的。因为这个名字,他们才意识到生活在小高层里,如同生活在一片冷漠的大海里。不,不是大海,而是拥挤的地铁。他们相互之间肩挨着肩,胳膊碰着胳膊,腿贴着腿,心却隔得异常遥远,即使坐着高铁也到达不了彼此心灵的一个角落。
他们常常给喜欢的微信点赞,发微信的人有的在国外,甚至远在天边。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晒到微博上,与陌生的和不陌生的人分享。他們常常通过“轻松筹”给遇到困难的人捐款。可是,为什么变得对身边的人漠不关心了?
女人的死将这种冷漠、这种无情、这种漠不关心一下子放大了。他们这样对待女人,其他的人也会这样对待自己的。
敬修兰举起酒杯,说:“我知道大家为什么来聚餐。我的目的跟你们一样,就是为了住在小高层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叫什么,为了有一天,我突然死了,不会像宋茉莉那样没人知道她的名字。来,让我们为宋茉莉干一杯。”
没有人响应敬修兰。这些好不容易从小高层里走出来,从层层的包裹中爬出来,卸掉了一点点盔甲,心变得稍微有点柔软的人呆呆地坐着,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菜、酒、草地、树干、别在衣服上的纸牌和包裹在衣服里的肚皮或者肉滚滚的后背……呆呆地坐着,呆呆地想着什么。
月亮爬高了,挂在小高层的楼顶,好像给小高层安了一盏灯。敬修兰这才发现,石桌的旁边竖着一根灯柱,灯柱上吊着一只水滴样的节能灯。它不声不响、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为聚餐提供了水银一般的光明。
灯不是小高层的人安的。灯是谁安的?
责任编辑:李 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