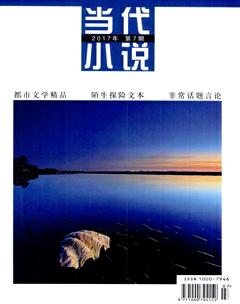胳膊拧不过大腿(短篇小说)
王喜成
1,那一砖头本是打狗的
九常从外边拉麦秸回来,晚饭后仍觉得浑身燥热,从窗台上抓块香皂朝外走。走到路边被瓦兰叫住了,又野哪去哩?九常说他去白沙河洗澡呢。瓦兰说没看小彬在墙角拉屎?给他擦了屁股再走。九常说你不会给他擦,瓦兰说她刷碗哩。
九常又回到窗台上撕下一绺卫生纸,走到墙角问小彬拉完没有,小彬说没有,九常恨恨地说:“屙驴×也没恁难。”
小彬哭着喊瓦兰:“妈,九常说话不好听。”
瓦兰正在厨房刷碗,跑出来用水淋淋的手拧九常的耳朵:“你再给孩子满嘴喷粪,把你耳朵拧下来喂狗!”
九常恨不得在卫生纸上撒把沙,然后再给小彬擦屁股。操你亲娘,凭什么让我伺候你……
九常走到村口,月光里看见丁大牙家的“大黄”正伸着鼻子嗅他家“黑妮儿”的屁股。二八月里猫闹春,二八月里狗打圈,他家的母狗正发情呢。九常恨屋及乌,他不想让丁大牙家的“大黄”上他家的“黑妮儿”,飞脚把“大黄”踹到沟底,那“大黄”岗唧岗唧一路哀鸣朝村东跑去,他家的“黑妮儿”就也朝“大黄”追过去。九常厉声喝斥,“黑妮儿”回来,给我回来,听见没有?可是呢,正处发情期的“黑妮儿”就跟没听见似的。他又骂道,日你妈真贱!骂着也朝那边去了。走着走着,当嗅到河水清凉的气息时,路北边的高坎上,那片芭茅丛里一阵响动把他吸引了。一定是“大黄”把他家的“黑妮儿”引诱到这边跟它粘上了。恰巧路边有块砖,是那种烧变形了的红得发紫的“琉璃”砖,九常弯腰拾起:
“日你姐!”
那一砖又准又狠地投进那片芭茅丛,里边呢,登时没动静了。九常才又想到,刚才芭茅丛里的响动可能是夜风弄出來的。管它呢,自顾朝河上洗澡去了。
这事过去不久,也是在一个晚上,九常搬一箱“元青花”、两条“软云”去丁大牙家。那天他不让丁大牙家的“大黄”上他家的“黑妮儿”,是因为一直对丁大牙怀恨在心。他爹患脑血栓多年瘫痪在床,失去劳动能力。九常多次找丁大牙要求给他爹办低保,丁大牙就是不给办。丁大牙不给九常他爹办低保,却给好胳膊好腿、活蹦乱跳的他岳父办了低保。他岳父家在公路边开草场、开加油站,富得流油,给谁办低保都不该给他办。这不,丁大牙的岳父前天得暴病死球了,村上空出一个低保名额。九常再对丁大牙有意见、再不懂人情世故,求人办事呢,礼多人不怪。
其实你不用眼睛就知道丁大牙家快到了,脚下的路宽了、平了,是水泥路。丁大牙家院里的灯亮得刺眼,他家的房子是仿古式的,上边飞檐斗拱五脊六兽。
丁大牙家的“大黄”可能还记着那天的一箭之仇,汪汪汪朝九常迎上来。不过九常早有准备,从食品袋里掏出一节卤过的“牛鞭”扔过去,“大黄”一见叼着就跑。丁大牙平时应酬多,每次出去喝酒总要带上“大黄”,丁大牙啥都吃腻了,唯独喜食牛鸡巴,久之,“大黄”也跟着喜欢上了。平时乡亲们来找丁大牙办事,都要事先准备好一截“牛鞭”。
佳艳正在平板电脑上玩游戏,面前吐了一地葡萄皮,抬头看见九常,毫不客气地问他来干什么,九常说他来找丁村长,佳艳说丁村长不在家。九常愣了一下,他刚进院子时仿佛看到丁大牙从厕所出来,人影一闪不见了。他跟佳艳说刚才似乎看见丁村长了,头上还戴着毡帽呢。佳艳说你是不是看见鬼了?九常刚才也在想,大热天的又是晚上,丁大牙戴着帽子干吗呢?他不敢跟佳艳说是看见鬼了,只说是眼看花了。接着问丁村长去哪了,佳艳说去外地考察养猪场。他问什么时候回来,佳艳说她也不知道。
九常把酒和香烟放到门口的台阶上。那我走了,等丁村长回来我再来。佳艳对烟酒不屑一顾,让九常把东西搬走。九常装着没听见,自顾朝外走。佳艳厉声道,你再不搬走,一会儿扔到大路上!
这天晚上,九常正在给他瘫痪在床的老爹喂饭,老爹的嘴哆嗦着,吞咽都困难,却断断续续地跟他说,让我饿死算了,不想再连累你们。九常说爹呀,前些天丁大牙不在家,一会儿我再去找他,正给你办低保呢。给爹喂完饭,九常搬着那天的烟酒走到门外,恰遇村文书去“狗蛋”家打麻将,人家问他去哪,他说去找丁大牙,想给他爹办低保。村文书说,丁村长已经把那个空出的低保名额挪给他岳母了。
九常气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上还在气,不行,我得去找丁大牙。这次啥礼物都没带,空手去的,日你妈,要屌毛了给你拔一根。反正低保名额已经给他丈母娘了,要是要不回来了,找他理论一番,出口恶气。
丁大牙正在院里跟村文书说事,见九常进来,虎着脸说,我正要找你呢。九常一惊,说你找我有啥事?丁大牙说走走咱俩到外边说。出大门,丁大牙和颜悦色地跟九常一起说说笑笑走在村街上。村上的汉子们有的开着拖拉机去外村拉麦秸、有的骑摩托去城里做工,看到九常跟丁大牙走在一起,揶揄他道,九常行啊,能跟丁村长一起说说笑笑,平起平坐了。九常竟也飘飘然了,是啊是啊,丁村长给面子!
俩人说说笑笑朝村东白沙河走去,快走到河边时,在那天晚上九常朝里边扔砖头的芭茅丛边,丁大牙站住了。九常也站住了,疑心道,说球个事值得跑恁远?没想到丁大牙说事前先一拳把他揍了个趔趄,他说咋、咋,丁村长你打人?丁大牙说打你是轻的,说着将一把从医院开出的诊断书、住院结算收据、住院费用清单硬塞到九常手里。
九常蒙了半天:“丁村长,你这是干什么?”
“那天晚上朝芭茅丛里扔砖头的是不是你?”
“不是我。”
“敢说不是你?”
“是我又怎样?”
“是你又怎样,你小子问得轻巧。那会儿老子正在里边拉屎,你一砖头砸到老子的后脑勺上了!”
九常一惊,怪不得那天晚上去他家,见他戴着帽子。不过他又疑问道:“那咋没听见你吭一声?”
“当时老子都昏死过去了,半声都吭不出来了!”
“我再说一遍,那一砖头不是我扔的。”
丁大牙又揍了九常一拳:“你刚才还问我咋没吭一声,竟敢耍赖。知道那块砖现在哪里吗?在公安刑警队的档案柜里存着呢,上边有你的指纹,不是看乡里乡亲的挨了打还替你说情,早把你抓起来了!”endprint
九常拿票据的手一抖:“这里边一共多少钱?”
“九千八百七十八块一毛九。”
“还有零头呢?”
“零头不要了,你给个整数。”
九常拿眼在地上搜寻着,看到芭茅丛里那块烧变形的“琉璃”砖,心里骂着去你妈的,嘴上却跟丁大牙说:“丁村长,要不你也拿起那块砖朝我后脑勺上来一家伙。”
“我是村长啊,哪像你们不懂法拿着砖头胡球整,出人命了怎么办?”
“那我没钱怎么办?”
“听白眉毛说你往他草场里送麦秸,一天赚几百块敢说没钱。”
“赚几百块的时候也有,但不经常。再说养着孩子老婆呢,挣一分钱九个窟隆儿等着填。”
“孩子老婆是不是你的你自己清楚,人家有人养。”
九常顿时矮人半截:“丁村长,先给你一半行不行?”
……
2,敢对外人说,酥你
九常的孩子老婆尽管有人养,可他刚盖了房子,老爹又瘫痪在床,手里也没钱。东挪西借凑够了五千块钱,跟丁大牙说好的,先给他一半。谁知还没顾上把钱给丁大牙呢,当晚他被瓦兰“宠幸”了。
瓦兰的漂亮不是一般的漂亮,瓦兰嫁给九常,才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瓦兰是邻村的,她是带着几岁的孩子嫁给九常的。九常只知道瓦兰以前在县城一家大酒店当过服务员,有关她的传闻不少,但他不肯相信,听见权当没听见。瓦兰嫁给九常二年了,平时和孩子花钱如流水,但从来没花过九常一分钱。对九常来说真该庆幸才是,只是到了晚上,瓦兰不跟他干那事。九常干急没办法,姑奶奶、祖奶奶地叫着,索性扑通跪到床沿上。求個够,求一百回人家勉强给他一回,只是还没尽兴呢,就被她从身上推下来了。瓦兰常带着孩子去县城,一去就是三天五天,九常打她电话也不接。
今儿晚上,要说天上的星星还是以前的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不同的是,瓦兰主动要九常了,不但要他了,还让他尽兴了,始终没把他从身上推下来。
九常尽兴后,瓦兰说话了,娘家妈后天过生日呢,要送给母亲一枚金戒指。还有,她的电动车爆胎了,也破旧得骑不成了,想买辆真空胎的。九常正在兴头上,顾不得疑问从来没向他要过钱的瓦兰今晚咋跟他说这些呢?他问一共得多少钱,瓦兰说五千就够了。
九常把钱给瓦兰后就后悔了。
近些天,九常一直躲着丁大牙。丁大牙找不到他,给他打电话,问他把钱准备好没有。他说钱倒是准备好了,不过又被瓦兰要走了。
丁大牙说:“骗鬼去吧,瓦兰能花你的钱?”
“瓦兰是我老婆,她不花我的钱花谁的钱?”
“花城里那个领导的钱。”
“放你妈狗屁!”
“你小子活腻了,敢骂我!”
“骂你是小事,你再诋毁我老婆,咱们法庭上见!”
“哟嗬,你小子飞砖伤人倒有理了,限你三天把钱送来,送不来可别怪我不客气。”
九常这样的直肠驴,对丁大牙说他当时是在芭茅丛里拉屎深信不疑。不过,这天他在村上遇到了老皮的老婆“十三香”,“十三香”对他的态度让他突然联想到什么。
是上午,九常开着四轮拖拉机去外边拉麦秸,还没出村拖拉机熄火了。这时“十三香”牵着孩子从丁大牙的便民超市出来,手里拎着鼓鼓囊囊的食品袋。九常对“十三香”笑道,怪不得呢,拖拉机也恋美人,看到你就不走了。当时“十三香”的表情让九常很难揣摸,人家也没理他,把脸扭到路边,跟倒垃圾的常二婶说句话,趔着身子从他身边走过。咋回事?平时“十三香”见他时总要先跟他开玩笑,说他半路成家,对老婆赛过亲妈,问他最近又吃瓦兰的妈(奶)没有。对于“十三香”的反常表现,九常忽然想到了丁大牙。
丁大牙再打电话,九常诈他:“我最恨这种人:自己有老婆,还在外边攀柳折花。”
“当然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丁大牙话中有话,接着又问,“不过你说这话啥意思?”
“那晚你要真是在芭茅丛里拉屎,我绝对不会给你一砖头。”
“你小子看到什么了?”
“我闻到十三香的味道了。”
“不管你是看到了还是闻到了,敢对外人说,酥你!”
“我才不对外人说呢,管我球事。”
丁大牙的话太恶狠、太欺人了,让九常受不了。酥你是当地方言,是句最恶狠的话。酥与碎近意,酥你就是碎你,让你粉身碎骨,比杀你都狠。说酥你时,那口气劈头盖脑如雷轰顶。说酥你,要么是大人吓小孩,要么是说给最瞧不起的人,是对对方的一种威胁和震慑。日你妈,你睡人家女人让我遇见了,你该求我为你守口如瓶才是,反而威胁我,要酥我,太拿老子不当人了。
按九常的逻辑,丁大牙不让他跟外人说,那我跟你老婆说总可以吧?
午饭后,丁大牙的老婆佳艳扭着屁股去娘家跟她的几个嫂嫂、弟媳们打麻将,九常故意跟她在村街上走一起,说是去她家的便民超市买东西的。
九常说:“丁村长威胁我,那事敢对外人说,酥我。”
“说吧,啥事?”
“能有啥事,臊臭事。”
“跟谁?”
“这不能告诉你。”
“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谁。”
“你也不管管?”
“男人有本事,在外边有个穿红的、再有个挂绿的很正常,哪像你,听说连自己的老婆都收拾不住。”佳艳一句话,把九常噎得半天回不过气儿来。不过,她又笑着跟他说,“要不要我也帮你找一个?”
“我又没本事,又没钱。”
“不是所有女人都爱钱。”
“是啊,比如你,爱美。”
九常对佳艳奉承着,心里却想入非非了……
3,丁村长对我不错嘛
九常经过分析、论证、总结,再经过综合考虑才决定跟佳艳试一烙铁,虽说冒一定风险,但舍不了娃子套不住狼,舍不得金弹子难打巧鸳鸯。endprint
九常想了,丁大牙在外边叨野食儿,怕是还不只“十三香”一个呢,佳艳被荒废在家肯定寂寞,那天她说的话是不是在暗示我?人说有钱的女人寂寞也好不寂寞也好,外边都有“小鲜肉”。自己虽不是“小鲜肉”,可也不是“老腊肉”,才三十多岁,正值壮年,成熟、稳重、威猛、阳刚,正合她口味,她要的就是这些。再说又是一个村的,她什么时候要,他可以随叫随到,丁大牙又经常不在家,多方便啊。
佳艳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城里一趟,到那家桃花坊女士美容店去美容。九常也不去外村拉麦秸了,就去村东离白沙河不远,坐在那片芭茅丛边等佳艳。他朝那片芭茅丛里观察了,几墩芭茅围成一个空间,里边的空间是个长方形,北高南低,宽有一米半,长有两米,正好能躺下两个人。又在路边的高坎上,可以观察周围的动静,路上的人却看不到他们。日他个娘,丁大牙真会选地方,在这儿跟“十三香”野合,几墩芭茅守护着他们,野风吹着,河水氤氲着清凉,奶奶的那才叫个爽。你丁大牙能在这儿睡“十三香”,我就不能在这儿睡你老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想到这儿,九常“哧”一声笑了。
太阳粘在地平线上那会儿,佳艳骑着电动车在白沙河的石桥上出现了。是不是还植了眉?清新精巧,像贴上两片柳叶,刚美容过的脸庞在晚霞里熠熠生辉。
九常从高坎上走下来,站在大路上跟迎面过来的佳艳说话:“这是谁家的妹子长恁漂亮。”
“不认识大嫂子了?”
“咋就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了?”
“扯去吧。”佳艳接着问他,“你今儿个没去外村拉麦秸,站这儿干什么?”
“等你啊。”
“等我?”
“你能不能下車听我说句话?”
佳艳捏住闸,从电动车上下来了:“说吧。”
“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里?”
九常指了指高坎上的那片芭茅丛:“就那里。”
“去那里干什么?”
“当时丁村长就是在那里风流快活的。”
“他在那里风流快活,让我过去干什么?”
“兴州官放火,也兴咱百姓点灯,咱也……”
“好吧。”佳艳笑了一下,面不改色地跟他说,“路上跑一身汗,我回去洗个澡再来,你等着。”
佳艳走多远了,九常又朝她喊道:“不见不散啊!”
佳艳走后,九常又一时想入非非。傍上她,以后她多在丁大牙面前吹吹枕头风,下次再空余低保名额就有我老爹的份了,以后村上有啥好事也能轮到我头上了。丁大牙还想讹我医药费呢,以后他老婆的钱我也可以帮着花呢。他奶奶,这不是一举两得、一举多得吗?
九常正想到得意处,佳艳来了。其实是他听到响动自以为是佳艳来了,其实来的不是她,来的也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有丁大牙、还有他的两个弟弟、三个小舅子,虎狼一般。
九常脱下褂子往肩上一搭,朝他们喊道:“走啊,一起去河上洗澡。”说完转身朝河上跑去,可他吓得两腿稀软,没跑几步就被他们追上了。先是被他们打得满地找牙,接着是丁大牙抄走那块“琉璃”砖朝他劈头砸下。
当九常从昏死中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先看到护士正在给他换水,接着看到瓦兰守在床边。他心里一热,先问小彬呢,瓦兰说送他去外婆家了。接着问是谁把他送来的,瓦兰说是她,人家恨不得把你打死。九常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跟她说:“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你管我干啥?让他们把我打死算了。”
“老公,我以前真的瞧不起你,但是没想到你竟敢勾引村长的女人,啥叫男人,这就叫男人;啥叫汉子,这就叫汉子!”
九常原以为丁大牙他们就是把他打死,瓦兰都不会管他的。没想到是她把他送来的,更没想到她能对他说出这样的话。尤其是一句老公,叫得他心里热乎乎的。登时激动得一骨碌从病床上坐起来,一把攥住瓦兰的手,只见那豆大的泪珠“扑嗒扑嗒”地往下掉,掉到他的胳膊上、掉到瓦兰的胳膊上。
瓦兰抽出手,又扶他躺下:“别动弹,头上缝了七针。”
病房里有四张床,都住的有人。他们来得早,病人和陪护人相互都熟络了,说着话,亲亲热热、热热闹闹的,九常很喜欢这场合。只是有两个老人,看模样可能是退休干部,两人话题最多的是反腐,当说到某某局长双规了、某某县长进去了,登时激动得两眼放光。当他们提到某一个人的名字时,瓦兰顿时神色黯然。九常装着没看见,心里却犯起猜疑。
有人提着礼品来看病人,进来就认出瓦兰了:“怎么,你也在这儿?”
瓦兰头一低:“你认错人了。”
九常看瓦兰在这儿处境尴尬,跟她说咱们出院吧,也没大碍,头上只是缝几针。瓦兰说再住些天吧,还没拆线呢。九常说他在这儿住不惯,先回去,等好了再来拆线。
九常出院的第二天,村文书来找他。要他写一份低保申请书,还要他老爹的照片、身份证、户口本,提供他老爹住院时医院开具的诊断证等,说是丁村长的安排,给他老爹办低保呢。九常问,你不是说那个低保名额丁大牙给他丈母娘了吗?村文书拍了拍九常的肩膀,这个名额是人家丁村长专程跑民政局托关系给你要来的。
九常心里一热,转身跟瓦兰说:“丁村长对我不错嘛!”
瓦兰斜了他一眼:“人说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这是伤疤没好就忘了疼了。”
4,跟我说话足有十分钟
没等拆线,九常出院的第二天就去外边拉麦秸了。以前从没关心过九常的瓦兰,也对他知冷知热了,她说去外边拉麦秸是重力气活,劳作中伤口崩裂了怎么办?九常说咱土生土长的人哪有那么娇嫩啊。瓦兰越不让他去拉麦秸,他越要去;越是关心他,他越干劲足。瓦兰也像个居家过日子的人了,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按时做饭,做好饭等九常回来。九常也不用自己洗衣裳了,身上的衣裳还没穿脏呢,瓦兰就催他,脱下来我给你洗洗。这样愈发增强了九常的家庭责任感。有些天没去拉麦秸了,我得挣钱养家啊、养老婆孩子啊!endprint
村上的青壮男人大多在外地打工,就九常呆在家里。半路成家,那时虽说瓦兰并没有给他温存和体贴,但越是这样越不能离开她。
今年拉麦秸得跑远乡,去最偏僻的地方。土路真难走,沟沟坎坎的。有的农户难说话,死讲着价钱。有时自己也会看走眼,那垛麦秸到底有多重?几次都是那样,拉回来别说赚钱,还赔钱呢。
公路边的草场是丁大牙的小舅子“白眉毛”开的,远望就像《水浒传》里林冲发配时守的那座草料场。九常的车开进草场时,有几辆大车正在往外出,是运往一家造纸厂的。看那车装的,边沿像砌起的墙,有三间平房那么大、那么齐整。几乎跟九常一起进草场的还有同村的“钥匙”和“铜锁”,他倆都比他拉的麦秸多,从驾座上钻出来,头上身上全是麦秸,简直成了麦秸人。他俩问九常跑哪拉的麦秸,九常摇着头说远哪,西北乡白庄,路上全是坡。他俩说比他跑得还远呢,东南乡鹿营,那路简直走不成。
“钥匙”和“铜锁”车上的麦秸直往下淋水,九常也往麦秸里掺水、掺土,但没有他俩掺得多。不掺杂不行,不掺杂不赚钱,有时还赔钱。他俩掺杂掺得多,白眉毛只是象征性地扣点儿杂,却给九常拉的麦秸扣杂扣得多,快扣去三分之一了。九常前后撵着给白眉毛敬烟,求个够,说这一弄不说赚钱了,还赔钱呢。白眉毛说你怕赔钱,我就不怕赔钱?九常说你要赔钱,生意早不做了。白眉毛扬着手像驱赶牲口一样,愿卖就扒车,不愿卖滚球远远的。九常火了,那晚他在河上挨打,就是白眉毛先追上他,把他扑倒在地的,这会儿恨上来一拳砸到对方的鼻子上。
白眉毛开始吃亏了,公路对面是他哥哥“白大肚皮”开的加油站。他又叫来“白大肚皮”和他弟弟“白指甲”合着把九常痛打了一顿。
打完架,九常又拉着麦秸顺公路往南走,把车开到大张庄张瘸子开的草场里,人家倒没扣他杂。
按九常的想法,乡村野汉谁跟谁打一架鸡毛蒜皮小球事,吃亏也好沾光也好,过去了就算过去了,根本没想到白眉毛会报案。晚上,当民警出现在九常面前时,他说:“他们三个打我一个。”
民警说:“他们打你你咋不报案?”
“我不报案是不想麻烦你们。”
“你不报案可人家报案了。”
九常被带上警车时还说:“我就不信,挨了打不报案就输理了?”
“白眉毛鼻子上有血,你鼻子上有血吗?再说,多少人都证着呢,是你先动的手。”
在看守所,连九常自己都不知道呆了几天,在这里白天和晚上几乎没什么区别。感觉中跟老皮说的咋就不一样呢?几年前老皮跟人打架进来过。他说隔几天狱警把他叫出去,说是教育他,其实是打他。通知家里人给狱警送点钱不打了,可是隔几天又说要教育他,家里送点钱不打了,隔几天又打。那次他老婆送钱送错了,送给另一个狱警了,那次挨打挨得狠,人家打着骂着,日你妈,把钱送给别人,算你白送……
九常进来几天了,狱警还没找过他呢。
“李九常!”
说曹操曹操到,狱警在外边叫他。九常腾地从地铺上站起来,接着浑身一抖,禁不得心惊肉跳。从监舍里出来,那狱警对他笑道:“看把你吓的。”
“还不是怕挨打嘛。”
“现在法制社会,不论谁打人都犯法。”
“也不要钱了?”
“正反腐呢,谁敢向你要钱啊!”
走出看守所大门,九常仍不敢相信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让他出来了。看到花坛边停着一辆黑明发亮的轿车,咋就看着眼熟呢?却想不起会有谁来接他。当丁大牙打开车门叫他上车,他呆在那里不动了。丁大牙只得把车开到他身边。
在车上,丁大牙对九常一脸歉意,说他这些天去外地考察养猪场,要是在家,咋也不会让他“进去”。本来要多去几家养猪场的,白眉毛在电话中说起这事儿,才提前回来的。说着摇头叹气,感觉他为这事费了很大周折、转了不少圈子。说话间,车停在那家君悦大酒店门口,九常问怎么不走了,丁大牙说在里边摆了一桌酒席,给他接风呢。
从进门到通过大厅再到房间,感觉就像走进皇宫一般。里边早有一干男女候着他们,丁大牙向九常一一做了介绍,都是县里要害部门的领导,还有两个是公安上的副科级干部。当丁大牙向他们介绍九常时,说你们可能不认识他,瓦兰你们认识吧,他是瓦兰的老公。他们顿时用异样的目光看他,脸上的表情讳莫如深。他们轮番对九常敬酒,敬酒时各自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九常不胜酒力,好在丁大牙替他挡着了,还替他喝酒。可他还是醉了,仿佛记得丁大牙附在他耳朵上说体己话,足足说有十多分钟,都让他荣幸得要死。
感觉都喝得差不多了,有人提议每人讲个段子,以助酒兴。他们特会说,故事异峰突起,且妙趣横生,令人喷饭。丁大牙讲的段子太黄了,但特搞笑。轮到九常了,他说俺乡里人拙嘴笨舌,平时少见多怪。就说说刚才走进这家酒店时的见闻吧,之前我从来没到过这里,这里边的迎宾小姐我一个都不认识,可她们咋一看见我就笑呢?不光笑,进来时还一个个冲我点头,不会是看上我了吧?就他这么一句自以为稀松平常的话,连自己都觉得对不起听众,没想到让一桌人笑得喷饭了。都说今儿晚上就他讲的段子最新鲜、最动听。他都不明白究竟好在哪里。
丁大牙开车把九常送到家门口。
瓦兰已经睡了,见九常走到床边:“回来了?”
“回来了。”
“先去洗个澡。”
九常洗了澡,借着酒兴爬到瓦兰身上做那事。做你就做吧,别扯些不相干的事。可他今儿个太高兴了,也太感激丁大牙了,边做边跟瓦兰说:“……他们说我讲的段子最新鲜,我都不知道新鲜在哪里。”
“这笑话只有你能讲得出。”
九常接着陶醉:“你不知道啊,酒席上丁村长附在我耳朵上说体己话,足足说有十分钟!”
这些天瓦兰已经接受九常了,这会儿真想再把他从身上推下去:“滚下来,你就这么没出息?别说是村长,就是县长趴你耳朵上说会儿话又该如何?”
九常自觉没趣,一骨碌从瓦兰身上滚下来了。endprint
5,我就信你一句话
九常回来的第二天,白眉毛搬箱牛奶来看他,先跟他道歉,接着说以往的事权当大风吹走了,希望他还和往常一样往他草场里送麦秸。他呢,却再不会对他拉的麦秸扣杂了。人家这样说,九常再拉麦秸时,反而不好意思再往里边掺水、掺土了。
九常开着拖拉机从白眉毛的草场里出来,回去的路上遇上“十三香”的老公老皮开着机动三轮往田里送化肥。想他正忙着,跟他打个招呼过去算了,谁知老皮把车停下来跟他说话。老皮问他拉车麦秸能赚多少钱,九常说这说不好,有时赚得多有时赚得少,有时还赔钱。老皮说还不如出去打工呢。他说真想跟你出去,看看,南方没把你晒黑反而白了。接着问他回来多久了,老皮说才回来,種罢麦就走,那边只批半月假。
老皮把车开出多远了,又回头朝九常喊道:“晚上咱俩喝几杯。”
“好哇好哇我请你。”
“我请你!”
天有点冷了,晚饭后,九常不再去河上洗澡,正要去自家的卫生间用淋浴,小彬来缠他。这些天,瓦兰对九常好了,小彬也跟着依恋九常了,九常也对小彬关爱有加。小彬刚才要瓦兰的手机玩游戏,瓦兰不给,说手机伤眼,小彬又来缠九常。九常刚把手机给小彬,老皮来了,手里拎一瓶二锅头。九常有点儿蒙,当时老皮在路上说请喝酒的话,他根本没在意。以前老皮在家时,从来没正眼瞧过九常,他们不是一路人,他请谁喝酒都不会请他喝酒的。当时瓦兰在厨房里腌咸菜,九常让她弄几个菜,记得冰箱里还有肉。老皮说不必了,咱去公路边的酒店里。九常说在家不也一样吗?老皮说我请你,你得听我的。九常有点儿不情愿,但还是勉强跟他去了。
公路边那家酒店,到晚上生意仍不错。顾客大都是邻近村上的,从城里做工回来,或是在附近做什么营生,晚上相约来这儿喝几杯,解解乏。大厅里坐满了人,进去时因为都认识,不少人站起来跟他们打招呼,过来一起喝吧,老皮说自便、自便,各整各的。老板也跟他们熟,问老皮回来几天了,又指着楼梯旁那张桌子说,就坐那儿吧。老皮问楼上有单间吗,老板说有,老皮说我们上楼,想清静清静。老板先上楼给他们开灯,在单间落座后,老板说有卤猪蹄、卤羊肉,还有……九常抢着说,就要盘卤猪蹄,再上个素菜算球了。老皮说太简单了,九常说就咱们两个,菜多了吃不完。
九常扬着筷子让老皮,你也吃、你也吃。但老皮只喝酒,几乎没动筷子。几杯酒下肚,老皮把酒杯很响亮地放在桌沿上,接着问九常,听说不久前你砸了丁大牙一砖头。九常正抱着猪蹄啃,蹄筋卡在牙缝里了,用牙签投也没投出来,才跟老皮说砸丁村长一砖头是真,但他不是故意的……
“当时你到底看到什么了?”
“要是看到了还敢往里边扔砖头吗?”
“后来丁大牙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他在里边拉屎。”
“他说拉屎你信不信?”
“村长说的话,能不信?”
老皮又往嘴里灌了几杯酒,眉头一皱,皱出一脸的阴狠来:“李九常,你知道我的脾气,今晚不跟我说实话,连你一起收拾!”
九常手一抖,杯里的酒溅到桌面上:“我刚才说的全是实话。”
“你别瞒我了,这事乡亲们都传疯了,但你是目击者,我就要你一句证言。”
九常知道老皮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打起架来不要命,出手狠且不计后果。别说是丁村长,就是乡长县长他都不怕。那年就是在大街上打警察,才被关进去的。他知道,丁村长今晚的小命就在他九常手心里攥着呢,人家对他那么好,他不能见死不救。
九常镇静下来,那手不抖不颤,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对老皮语重心长道:“兄弟啊,你在外边打工,‘十三香在家替你上扶老下养小,风里雨里侍弄庄稼,你就忍心端着屎盆子往她头上扣?自己的老婆是什么人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老皮用筷子敲着桌子说:“李九常,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当时我去河上洗澡,瓦兰说小彬在拉屎,让我给他擦了屁股再走。恰好‘十三香来我家串门,跟我说你去吧,我给小彬擦……”
“你再跟我说一遍。”
九常就一字不差地把刚才的话跟老皮复述了两遍。
老皮这才渐渐有了笑脸:“其实我根本不信那些流言蜚语,我就信你一句话,知道你是老实人。”
老皮说完,从怀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隔窗扔了出去,接着只听“扑出”一声,不似匕首落地的声音,感觉是不是扎在哪里了?
九常偷偷朝额上抹一把冷汗。
老皮开始吃菜,看盘里的猪蹄所剩无几,朝下边喊,再上一盘卤羊肉!
菜吃个差不多了,他俩又接着喝酒。当老皮喝酒喝到眼角起一层像脓样的东西时,说话就乱了。一脸猥亵地问九常:“听说瓦兰不跟你干那事?”
“没有的事,其实瓦兰对我挺好的。”
“等种罢麦跟我去南方打工吧,现在都是机械化操作,工地上的活儿也不重。一天几百块呀,那里到处都是按摩店,里边的小姐随便玩,尽你挑,你在家守着老婆又不让你干,撑死眼饿死■有啥用?”
“你进去过吗?”
“几乎见天去,那边便宜得很,才要二三十块钱,一天挣的钱连个零头都花不了。”
九常听了一阵心酸,话中有话地跟老皮说:“等种罢麦,你还是带着‘十三香出去打工吧,这样在外边可以相互照顾。”
老皮一时沉思不语。
第二天下午,九常往白眉毛的草场里送麦秸,没看到白眉毛,给他过磅的是他大哥“白大肚皮”。他问你弟弟呢,白大肚皮说白眉毛去外地的造纸厂要账去了。但又见他一脸阴郁,表情很复杂,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
当田里露出嫩黄的麦芽时,老皮把孩子留给父母照管,果真带着“十三香”到南方打工去了。
6,你先给我带个头
多天后,当九常看到白眉毛出现在他的草场里时,发现他走路有点儿瘸。
九常卸了麦秸,正要开着四轮车回去,丁大牙来了,要拉他去城里玩。其实九常不愿跟丁大牙一起出去玩,他那些城里的狐朋狗友们一个个人五人六的,跟他们隔着一层天呢,可又无法违了丁村长的情面。九常说他先把车开回去,丁大牙说你的车先放这儿,丢不了。九常说你看我拉一天麦秸,弄得身上灰土狼烟的,总得回去洗个澡吧?丁大牙说就是带你去洗浴中心洗澡的。endprint
车行驶到城区时,当走到那家“知足常乐”洗脚城门前,丁大牙临时改变了主意,跟九常说咱先进去洗脚吧?九常此时浑身瘙痒,最要紧的是先去洗个澡,可丁村长说什么,他只有听从的份。
看来丁大牙是这里的常客,老板包括小姐们都亲热地叫他丁老板。老板说,还坐“舒雅阁”吧。给你留着呢。服务员先上瓜果、茶水。接着是两个小姐捧着木桶进来了,木桶里的水热气蒸腾,呈咖啡色。两个小姐勒着一样的印花水裙,年轻点儿的俏眉俊目,年长点儿的胖得有味。
年轻点儿的小姐叫小娴,习惯性把木桶放到丁大牙面前,丁大牙却指着九常跟她说:“今儿你给他洗。”
小娴假嗔道:“丁老板不喜歡小妹了。”
丁大牙又指着九常说:“他是我的贵客。”
九常虽是“贵客”,明显地被小娴轻慢、瞧不起,边给他洗着脚边数落着:“你瞧瞧人家丁老板的脚,光滑细嫩得跟大闺女的屁股一样……”
丁大牙“哧”一声笑了:“操,你咋不比大闺女的乳房呢?”
小娴接着说:“再瞧瞧你的脚,粗糙得跟榆树皮似的。”
九常尴尬一笑:“我哪能跟丁村长比啊。”
洗完脚被放到一个柔软的墩子上捏拿收拾,接着是通身按摩。跟那个稍胖点儿的小姐相比,小娴显然是在对九常草草应付,就跟蜻蜓点水似的。九常倒没说什么,丁大牙发话了:“小娴哪,要不要我跟老板说说,给我的客人再换个小姐?”
小娴这才舍下身来,别看这点儿年龄,看似柔弱得能被大风吹倒,下起手来却那么狠,几次都把他弄疼了,可疼得很舒服,感觉酣畅淋漓,这样的享受还是第一次。以前,九常只知道人生下来就是吃苦受罪的,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去处,这么美妙的享受。品尝着香茶瓜果,听着音乐,有香喷喷的小姐伺候着,纵是神仙日子又该怎样。
九常正这么想着,丁大牙跟他说话了:“九常啊,听说老皮在家时请你喝酒了?”
九常一惊,这他都知道了?他说:“我跟他不是一路人,但他要请,只好随他了。席间他想套我的话,可我……”
“你别说,我啥都知道了……”
九常忽然联想到那天晚上老皮的匕首在窗外落地的声音,又由此联想到第二天白眉毛没在草场出现,不觉又出了一身冷汗。
回家的路上,丁大牙又跟九常说,现在从上到下都在注重培养女干部,我打算在村里给瓦兰配个职务,让她当村妇女主任兼计生专干。九常说她哪行,小家碧玉不是那种泼辣能干的女人。丁大牙说,我说她能干就能干……
吃早饭的时候,瓦兰把前些天腌的咸菜端到餐桌上。那是由芥菜掺炒熟的黄豆、花生腌制而成的。芥菜串味儿,那黄豆和花生也跟着变了味,吃到嘴里辛辣蹿鼻,可很对九常的胃口。九常故意逗小彬,夹粒花生米往他嘴里填,说知道俺彬彬爱吃这个。小彬嚼一口,辣得直挤眼睛,爸爸坏、爸爸坏!九常高兴得哈哈大笑。
九常高兴完又跟瓦兰说:“给你报告个好消息,丁村长说了,准备在村里给你配个职务呢……”
瓦兰撇了撇嘴:“你去跟他说,姑奶奶当妇女主任不过瘾,我想当村长,除非他下来我上去。”
“这怕是办不到。”九常又说,“丁村长还跟我说了,他要在河边建养猪场,是与外商合资,那种上规模的养猪场。但要征用十来户农家的责任田,但他们有抵触,丁村长想让我带个头儿。”
“这我支持你,发展养殖业是正事……”
“那我就率先把咱家的责任田给他了?”
“给他吧。”
丁大牙会造势,在跟九常签订土地转租合同时,请了两个唢呐班。当时是在村部大门外的场地上举行的,一个唢呐班吹奏《好汉歌》、一个唢呐班吹奏《百鸟朝凤》。每个唢呐班还配有演唱人员,且都是些靓姐丽妹,一个唢呐班唱《花木兰从军》、一个唢呐班唱《穆桂英挂帅》。把外村人都给招引来了,那场面一时人山人海。
丁大牙还在签字仪式上讲话,说九常已被聘用为养猪场行管人员,什么叫行管人员?就是干部,每月拿工资。谁接着愿意把自家的责任田转让给养猪场,和九常的待遇一样。按月拿工资,养猪场还给你交三金,这等好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当天下午,施工队就把建猪场的材料:砖、沙石、水泥、钢筋等拉进了九常的责任田。路还没修好,前边有铲车开道,把河边那个高坎、那几墩芭茅、当时丁大牙在那儿“拉屎”的地方都给铲平了。
7,那你先去洗个澡
丁大牙租了一辆中巴车,让九常带着那十来家农户去百里外菊花岭景区旅游。总共有十多个人,但他们说话却是一个调。上车时他们说:“种罢麦农闲了,出去走走也不错,只是别跟我们提征地的事,要提,我们现在就下车。”
九常说:“不提、不提。”
在路上,他们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租车费我们十户均摊。”
九常说:“这是小事儿。”
上山的时候,九常没提征地的事。他们也没提,只问九常,咋不让你家瓦兰一起来。九常说小彬在上学,中午她得接学生,还要照顾俺老爹。
山上有庙,他们在烧香许愿时几乎众口一词:“希望我们的责任田今年长出好庄稼、明年长出好庄稼,后年还长出好庄稼……”
九常听了,心里说这工作怕是不好做。
从庙里出来,九常跟他们说:“都饿了吧?下山吃饭。”
山脚下有家山野土菜馆,店面不咋的,砖瓦土屋。厨房不用煤电,烧的是山柴,离老远都听见劈剥作响。那菜真地道,野猪肉、野兔肉、野生鱼,野生蘑菇,不论荤素菜都是野生的,味道鲜美异常。九常从车上搬一箱“本地造”纯粮食酒。那菜可口如意,那酒醇香浓烈,一个个开怀畅饮。当桌旁扔出几个空酒瓶时,九常觉得时机成熟,该跟他们说正事了。
九常说:“听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斤小麦集市上还卖四毛多钱呢,现在别的物价翻了几十倍,一斤小麦才卖九毛多。粮食不值钱,再扣去化肥、农药,工钱,种地不赚钱怕是还要赔钱呢……”endprint
九常还没说到征地的事,他们立刻放下酒杯,不喝了。他们说:“不是我们难缠,你也不想想,养猪场要是办成了还好说,如果办不成呢?就是办成了过几年倒闭了怎么办?到时再把土地归还我们?那时可是一片废墟啊,好好的田地被水泥硬化成铁板一块,还能种庄稼吗?到时候我们吃什么?喝西北风?”
九常一时哑口无言,半天才说:“这事我也想了,可人家是村长,咱胳膊拧不过大腿。”
他们说:“村长怎么了,他是比咱多长个头还是多长个鸡巴?”
事先丁大牙跟九常说过了,最后不行的话,给他们一个暗示,但要委婉,拐弯抹角不能直说,让他们感觉到,心有恐惧就行了。可他这会儿喝高了,就直说了,他把刚才的一口一个丁村长改成了丁大牙:“丁大牙还有下步棋呢,但我不想看到他走那步棋……”
他们说:“我们倒要看看他走哪步棋。”
九常说:“丁大牙跟外边的黑社会都有联系呢,他说棋要一步一步地走,先礼后兵。”
他们“呼隆”把桌子掀翻了:“丁大牙竟敢来这一手,现在是法制社会,谁怕谁啊!”
他们要立马回去找丁大牙理论。九常赶紧拦挡,有话慢慢说,下午还要去月亮湖呢。他们说别说月亮湖,就是月宫也不去了。问他走不走,你不走我们走了,说着一把拽起中巴车司机。九常没办法,只好跟他们回去了。
九常哪里知道,他走这半天,家里出事了。到家时,他看到瓦兰站在院门外,她脚下是一堆男人的衣裳,那堆衣裳看着很眼熟。她身边还站着赶来的孙乡长。周围人山人海。不过,瓦兰对当前的局面显得沉着冷静,应对自如。
孫乡长跟瓦兰说:“你先把衣裳给他扔进去。”
瓦兰说:“我怕弄脏我的手。”
瓦兰用一根竹竿把那堆衣裳——上衣、裤子、裤头、鞋子一件一件地挑进院墙内。
是这样的,丁大牙早对瓦兰垂涎三尺,只是碍于县里那个领导,最近听说那个领导被双规了,这才没了顾忌。可瓦兰是见过世面的人啊,她哪里看得上丁大牙。再说了,那边没了依靠,她要跟九常过正经日子呢。别说许愿当妇女主任,就是认我当干娘我都不干。丁大牙一时恼羞成怒,开始揭她的短,你他妈做婊子还要立牌坊,你在城里那些烂脏事谁不知道啊。他这么一说,瓦兰暂把一腔怒火强压在心底,表面不动声色装臣服,假意跟他撒娇道,臭男人、臭男人,那你先去卫生间洗个澡。丁大牙说要洗咱俩一块儿洗。瓦兰扭着腰肢说俺不哩、俺不哩,俺得替你看着门。乘丁大牙洗澡的工夫,瓦兰把他的衣裳扔到了院门外,接着给乡长打电话。
当晚,九常一个劲儿地向瓦兰检讨自己的过失,不该为虎作伥,到处替丁大牙说话。瓦兰说人无完人嘛,接着咬着他的耳朵说:“我拒绝丁大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你想知道吗?”
“当然想知道了。”
“我怀上你的孩子了!”
九常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他做梦都想要个自己的孩子,却一把将小彬揽到怀里,失声痛哭:“你是我的亲儿子啊!”
后记
丁大牙还算聪明,没等乡里的领导处理他,主动请求辞职。接着在村里的换届选举中,瓦兰全票通过当选村长,连丁大牙都投了她的票。
瓦兰上任后接着也要办养猪场,可她没有征用农户的责任田。最近村外那所小学搬迁到镇上了,她要在那片校址上开创新的事业……
瓦兰就是瓦兰。
责任编辑:段玉芝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