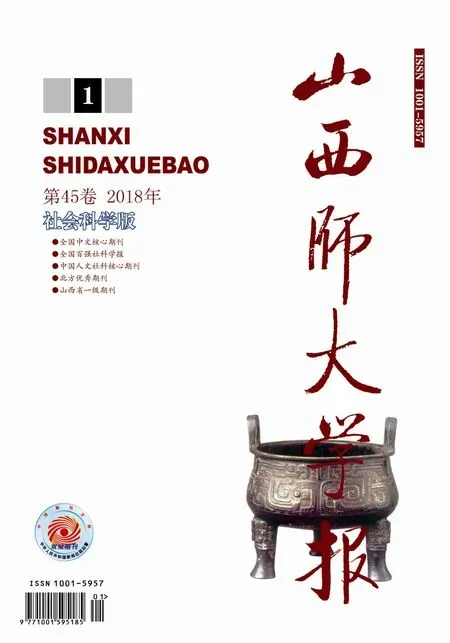论明清书坊与戏曲评点的关系
廖 华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南宁 530023)
明清戏曲评点的兴盛与创作繁荣、演出频繁有关,其实,刻书业的发展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明代戏曲评点集中在明万历至明末,这正是戏曲刊本兴盛的阶段。据笔者初步统计,明刻戏曲评点本约160种,除了徐士范、王骥德、汪道昆、孟称舜等几位家刻评点本外,其余的坊刻本约占评点本总数的90%以上;清刻戏曲评点本近300种,坊刻同样占有较大的比例。朱万曙先生在《明代戏曲评点研究》一书中曾指出书商促进了戏曲评点的发展。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明清书商如何推动戏曲评点,对戏曲评点有何具体影响。
一、书坊以评点作为促销手段促进戏曲评点的兴盛
戏曲插图能够辅助文本阅读,戏曲评点亦有此功效。明清戏曲的评点主要在两个方面帮助读者阅读。
一方面,戏曲评点帮助读者理解文意。一是解释文本内容。凌濛初《西厢记凡例》云:“评语及解证,无非以疏疑滞、正讹谬为主。”[1]175即帮助读者疏通、纠正曲辞。二是体会作家思想。程羽文在《盛明杂剧三十种序》中说:“吾友沈林宗顾曲周郎,观乐吴子,遂先有此举,其点校评论,又一一传作者之面目,而溯之为作者之精神。”[1]189在程氏看来,沈泰校勘和评点戏曲选本,犹如春秋时吴公子季札观乐、评乐一般,很好地传达了作家的主观情感。三是指出作品的精彩之处。如凌濛初《琵琶记凡例》云:“今人选曲,但知赏‘新篁池阁’‘长空万里’等,皆不识真面目。此本加丹铅处,必曲家胜场,知音自辨。”[1]179告知读者哪些才是“锦心绣口”,这就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鉴赏作品。
另一方面,与小说评点不同,戏曲评点具有指导演出的作用。比如提醒演员需要认真对待的关目,像《酒家佣》第十三折《文姬托孤》的眉批云:“此出是通本得力处,演者要留心。”[2]或是指导演员的表情与动作,像《玉茗堂批点异梦记》第二十出《投环》的出批云:“此折乃好关目也,两下惊疑全在投环之际,演者须从曲白内寻出动人之处为妙。”[3]指出演员要抓住情境做戏。此外,冷热场面的调剂,曲律声韵的提示,演员服装和舞台道具的说明,戏曲评点均有涉及。
评点有助于理解文本,也能指导演员表演,对于读者来说具有莫大吸引力。因此,书坊利用评点宣传,促销手段层出不穷:
其一,在书名、序跋、正文中指出刊本附有评点。书名位置显眼,书坊有意识给书名添加“批评”“评点”等字眼,如《玉茗堂批评种玉记》《新镌绣像评点玄雪谱》。序跋也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成为刊本宣传的途径之一,如竹轩主人《歌林拾翠题识》云:“杂曲选本,流传甚繁,本坊博搜古今名剧,细加评选,腔介从新。”[4]另外,乾隆十六年刊本《芝龕记》的正文首页署“海内诸名家评”,作为书籍正文的第一页,过目率很高,同样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其二,在序跋、凡例中夸赞评点内容。谢国《蝴蝶梦凡例》云:“是编评点原有数家,不敢不摘录以借文芜拙,亦不敢尽录以爚溷鉴观。”[1]285意思是该本的评点不会混淆读者的审美感知,而是“借文芜拙”,使作品增色,暗示所选评语都是优秀的,这是对评语的间接肯定。也有直接赞美评语的,如《田水月山房藏本北西厢序》云:“实甫遇文长,庶几乎千载一知音哉!”[5]170称赞徐渭能够深切理解《西厢记》的精神,是王实甫的知音。《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凡例》云:“《西厢》之有徐评,犹《南华》之有郭注也。”[5]212郭象对《庄子》一书的诠释和流传贡献颇大,将徐渭的评点与之相提并论,可见评价之高。又如天章阁本《西厢记》署李贽所评,序跋指出李贽评点的《西厢》为“传神之祖”,而且提醒读者,“毋曰剧本也,当从李氏之书读之”,[1]226这无疑抬高了刊本的价值,起到了促销的作用。
其三,将不同评点家的评语放在同一刊本中,并加以强调。集合多家评语的刊本,也能抓住读者的眼球,所以书坊并不吝啬评语的添设。如起凤馆《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的评点者署王世贞和李卓吾。起凤馆主人在刊本的序言云:“自来《西厢》富于才情见豪,一得二公评后,更令千古色飞,浮屠顶上,助之风铃一角,响不其远与!”[5]152又在《凡例》中指出两位大家各自的评点特色,即王评是“扬扢风雅,声金振玉”,李评是“品骘古今,一字足为一史”。[5]154金陵书坊汇锦堂刊刻的《三先生合评北西厢记》则集合了三家评语,署名汤显祖、李贽和徐渭,还请来王思任作序,强调汤评、李评、徐评的特色分别为“立地证果”“当下解颐”和“雅俗共赏”,将它们合刻能够陶冶性情,利于风化。[5]231言下之意,这样的刊本弥足珍贵,值得阅读。
除了上述三种广告外,还有其他促销方式。比如,以名家评点打广告,即聘请名家评点戏曲;或巧用评语字体,书坊师俭堂的出批就别出心裁,均用书写体;或是集中刊刻某种题材的剧本。郭英德先生曾分析明万历十一年到清顺治八年的传奇作品数量,其中风情剧最多,占45.6℅,其次是历史剧,占19℅,[6]261可知这两种题材是最受读者欢迎的。而署名李贽评点的戏曲文本中,占大部分的是风情剧与历史剧,显然,书商为了提高销量,连评点本也是以大众喜爱的题材居多。
总之,明清书坊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于刊本中增加评点,并以此作为促销,广告形式多样,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戏曲评点的兴盛。
二、书坊组织下层文人评点戏曲引领和推动戏曲评点的发展
书坊与文人关系密切,特别是在中上层文人加入戏曲行列之前,书坊往往需要下层文人编写戏曲,下层文人为了得到经济保障也乐于受雇于书坊。在书坊的组织下,下层文人评点戏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早期的戏曲评点本以坊刻为主,一批下层文人在书坊的组织下成为较早从事戏曲评点的群体。据笔者统计,明初至明万历三十年间,具有明确刊刻时间的戏曲评点本有家刻本:万历八年徐士范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万历十年焦竑合刻《西厢记》与《琵琶记》(已佚);其余全是坊刻本:万历元年建阳种德堂《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万历五年金陵富春堂《校梓注释圏证蔡伯喈大全》、万历七年金陵少山堂《西厢记》、万历十三年金陵世德堂《荆钗记》、万历十七年金陵世德堂《拜月亭》、万历二十年建阳忠正堂《西厢记》、万历二十五年徽州玩虎轩《琵琶记》、万历二十六年金陵继志斋《西厢记》《琵琶记》、万历二十七年金陵继志斋《玉簪记》。那么,刊刻时间不明确的早期戏曲评点本又有哪些呢?
朱万曙先生指出明代戏曲评点本有五种形态:注音间评型、释义兼评型、考订兼评型、改评型和纯粹评点型,其中“注音间评型”和“释义兼评型”属于早期戏曲评点本的形态,前者在《古本戏曲丛刊》中仅发现《麒麟罽》《蝴蝶梦》《红蕖记》三种刊本,后者则集中于世德堂的刊本。[7]32—33《麒麟罽》为陈与郊家刻本,《蝴蝶梦》的刊刻书坊不详,《红蕖记》是继志斋所刻,世德堂为金陵著名的书坊。可知,早期的戏曲评点本主要是坊刻本。此外,据笔者考查,现存最早以“题评”命名的戏曲是徐士范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而最早大量使用的是世德堂,所刊戏曲的书名大多有“题评”两字,如《新镌重订出像附释标注惊鸿记题评》《新镌出像注释李十郎霍小玉紫箫记题评》《新镌重订出像注释节孝记题评》。这是商家惯用的广告手段,其实评语多是随感式的鉴赏性质,缺乏系统与深度。但是,世德堂较早有意识地注重评点的作用,对于戏曲评点发展所作的努力应值得肯定。
在中上层文人评点戏曲之前,下层文人为了生计或为了消遣而加入戏曲评点的队伍,他们甚少在评点本中留下姓名,所做评语也较为稚嫩,但是在戏曲评点的萌芽阶段,实属可贵。
其次,下层文人的戏曲评点也颇具特色与价值。不仅是初期阶段,在整个明清时期,均存在书坊组织下层文人评点戏曲的现象。下层文人由最初不留任何信息,发展至假托名人评点,或者署别号,如快活庵、醉竹居士、丽句亭、画隐先生、西园公子、澄道人、且居、西湖漫史、媚花香史、羊城平阳郡佑卿甫、苗兰居士、明道人。这批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文人,评点戏曲的态度还是比较认真的。因为评点工作不得马虎,要是草率为之,令书商不满,稿费可是大打折扣。对于失意文人来说,评点还可宣泄情感;对于戏曲爱好者来说,评点也是一大快事,如快活蓭评点本《红梨花记》卷首有一篇序言云:“余见《梨花》传奇两种,一为武林,一为琴川”,随之评价了这两种版本的差别,然后说“予以评章如此,不知两家以我为知音否也?”[8]评点者非常自信,得意起来甚至将自己视为作者的知音。也就是说,评点既可赚钱,又可消遣娱乐,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这种心态驱使下,下层文人的评点并非毫无建树。如继志斋所刻戏曲评语十分丰富,像“旌节二句,元人杂剧俗作旌捷,非”“此调今俱作锁寒窗,误矣”“此后旦唱渐高,但以锦被兜身,只当坐定或靠桌上,不可行走”,对于曲辞宾白、曲律音韵、舞台表演等都有点评。又如徽州书坊玩虎轩所刻《琵琶记》的评点者不详,黄仕忠先生指出,晚明各种《琵琶记》评本均以此本为底本。[9]216如果将现存所有坊刻戏曲评语整理归纳,不难发现,他们的评语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谭帆、陆炜在《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中所说:“晚明的戏曲评点还受着书坊的强烈控制,故书坊主及其周围的下层文人也是评点者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对这一群体作广泛和细致的清理和研究,那不仅对中国戏曲评点史的研究颇多裨益,也能对中国戏曲史尤其是戏曲传播史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史料。”[10]49
三、书坊聘请名家评点戏曲提高戏曲评点的水平
根据现存戏曲刊本来看,最早借名家评点来宣传的,应该是杭州书坊容与堂。
这位书坊主人独具眼光,于万历三十八年率先出版署名李贽评点的戏曲,开启了名家评点戏曲的风潮。其他书坊纷纷实行名人效应的策略,涌现出一大批署名家评点的戏曲刊本。比如,起凤馆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正是刻于万历三十八年,评点内容几乎与容本一致;同年,三槐堂本《重校北西厢记》也署李卓吾评点,但评语多为释义,与李评风格不同;紧接着又有两套五剧曲本,一是《荆钗》《明珠》《玉玦》《绣襦》《玉簪》,二是《浣纱》《金印》《绣襦》《香囊》《鸣凤》。除了李贽外,明清戏曲评点本中署名的名家还有汤显祖、陈继儒、徐渭、王世贞、梁辰鱼、王世懋、屠隆、沈璟、袁宏道、王思任、沈际飞、谭元春、钟惺、徐奋鹏、孙鑛、李玉、李九我、周延儒、彭幼朔、李渔、金圣叹、毛声山、毛宗岗等,其中李九我和周延儒还是位列三公的宰相。
当然,所谓的名家,不排除有假托现象。但也不能否认,明清不乏实实在在参与戏曲评点的名家。比如师俭堂所刻戏曲打上“陈继儒”的名号,笔者认同朱万曙先生的观点,师俭堂所刻戏曲确实是陈继儒所评。[7]99而且,笔者还认为,陈继儒是被师俭堂聘请而从事评点工作的。这可从陈氏的生平和思想观念来考察:
第一,名流身份得到商家青睐。陈继儒不贪图荣利,虽屡受朝廷征召,皆以疾辞;对于穷困儒生则尽心资助,人称其为“山中宰相”;且多才多艺,在诗文、书画、古董等方面造诣颇深,是相当有品位的学者。《列朝诗集小传》云:“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籹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无得免焉。”[11]637陈继儒的人格和才华得到世人的普遍肯定,可谓名动朝野,远及酉夷。对于这样一位不耕不宦,却声华浮动的大家,怎么可能不引起商家的注意呢?
第二,具有读者意识和市场观念。陈继儒非常重视读者的阅读心理,如《藏说小萃序》云:“经史子集譬诸梁肉,读者习为故常,而天厨禁脔、异方杂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则说部是也。”[12]指出读者对经史子集已产生审美疲劳,喜欢阅览千奇百怪的小说作品。又如《陈铜梁真稿序》云:“取古人所已言而袭之,读者憎其腐,则更取古人所未言而用之,读者又怪其凿空角险。”[12]指出读者讨厌阅读毫无新意或者情节过于荒唐的作品。出于对读者的关注,陈继儒对书籍市场也有较深的认识,如他曾指导许自昌次子许元恭的刻书事业,在给许元恭的信中说:
小孙经书已完,今读《化书》。字字皆灵,句句皆有益于身心家国。此学士大夫未尝教儿读者,节短转快,此举业之径路,容寄老亲家刻之。盖出于《道藏》,不甚流通也。
《国策选》觉是举业书,非好古者所贪购也。叙文亦同请政,惜此书并惜此序,一笑。
承惠《读书后》,又得闲仲重校跋之,妙甚。但目录须列在前,使读者一览,见所未见,生歆艳心,千万即易之。
久望《读书后》,得教,刻板极精,当走天下。第多刷数千,一日而发之,纸贵无疑。目录悉列于前,观者艳其多,寻者乐其易,跋语姑置后可也。有装订成书者,乞惠二十册,以便寄远,且长其声价耳。
《读书后》以校正差落数次者奉览,乞编前后刻之。……尚可抽其论经、论史者共为一部,则远可行、久可传,只恐翻版耳。[13]369
陈继儒对许氏的建议涉及哪些书籍会畅销,版面安排如何才能吸引读者,甚至对于可能存在的翻版现象也给予了提醒。
第三,以卖文为生。陈继儒本人曾说过他是“卖文为活”的,其《白石樵真稿》有篇尺牍《与萧象林户部》云:“若不肖屏迹佘山,卖文为活,惟有白醉黑甜于茆茨篱落之间。”[14]138清人宋起凤在其所著《稗说》中提到陈继儒,亦云:“四方征其文者,束帛挺金造请无虚日”,“以润笔之资卜筑余山……纵情山水数十载。”[15]37可知,陈继儒常为人代笔撰稿,置身于出版业,润笔之资成为其主要经济来源。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师俭堂为提升刊本知名度而聘请陈继儒评点戏曲。由此可见,明清书坊虽然以赢利为目的,但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不惜花钱聘请名家评点,以致客观上提高了戏曲评点的质量。
四、书坊主亲自评点戏曲丰富戏曲评点的形式与内容
据笔者统计,明清书坊主人评点的戏曲列表如表1。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部分剧目的评点者是经过学者考证的:郑振铎和郑志良两位学者均指出《玉茗堂批评红梅记》为袁于令所评;[16]凌延喜于天启年间刊刻的《幽闺怨佳人拜月亭记》,评语出自凌濛初、沈璟还是凌延喜本人,学界有所争议,笔者认同江兴佑先生的观点,即凌延喜是实实在在的评点者之一;[17]至于《西厢会真传》署“汤若士批评沈伯英批订”,笔者倾向于蒋星煜先生的观点,认为是闵遇五刊刻并评点的。[18]

表1
明清书坊主的戏曲评点有一特色,即乐于刊刻自己的评点本,像臧懋循、凌濛初、袁于令、闵遇五、闵光瑜、凌延喜等所评剧本均是本人所刻。而且,书坊主的戏曲评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丰富戏曲评点的模式,评语的学术含量高。明清书坊主中不乏戏曲专家,他们对戏曲评点有着独特的贡献,如臧懋循是“改评型”评点方式的开创者,凌濛初则是“考订兼评型”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闵遇五等并非戏曲专家的书坊主,他们的评点也不乏真知灼见。如《会真六幻西厢》所附录的《围棋闯局》,其作者题“晚进王生”,但是闵遇五从剧本文辞出发,率先指出“王生”并非指王实甫,而是“另一晚进无疑”,这是很有创见的。[5]112
二是将评点理论付诸实践,深化评点内容。晚明时期,臧懋循、袁于令等书坊主开始意识到舞台表演的重要性,如臧懋循在《玉茗堂传奇引》中说:“夫既谓之曲矣,而不可奏于筵上,则又安取彼哉!”[1]151认为不适合演出的戏曲不会是好的作品。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将戏曲理论融入剧作。比如臧懋循删订《临川四梦》,能结合舞台实际评点戏曲并删改剧本;又如袁于令在《玉茗堂批评红梅记总评》云:“上卷末折《拷伎》,平章诸妾跪立满前。而鬼旦出场,一人独唱长曲,使合场皆冷。及似道与众妾直到后来才知是慧娘阴魂,苦无意味。”[1]94于是,袁于令改写这一出为《鬼辩》,改本中的慧娘一上场就是嫉恶如仇,威严霸气的厉鬼,不断控诉贾似道,将戏剧推向高潮,强化了舞台效果。除了臧懋循、袁于令外,书坊主李渔也重视舞台表演,认为 “填词之设,专为登场”,[19]100创作了不少场上流行的剧作。可见,明清书坊主既评点戏曲,又加以实践,丰富和深化了中国戏曲理论。
五、书坊对戏曲评点的作伪有弊亦有利
诚然,明清戏曲评点的作伪现象十分严重。或假托名人评点,如郑振铎先生曾指出:“颇疑李卓吾只评《琵琶》《玉合》《红拂》数种。其后初刻、二刻、三刻云云,皆为叶昼所伪作。”[20]810或直接抄袭他人的评语,像“李评”本第四折“巧辩”的出批,大都为“红娘是个牵头,一发是个大座主”;或直接摘抄名家言论,如继志斋《重校北西厢记总评》摘录王世贞《艺苑卮言》中有关《西厢记》的评论。书商鱼目混珠,大量伪作充斥市场。陈洪绶在《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题辞》中指出:“读赝本、原本不能辨,往往赝本行而原本没矣。如文长先生所评《北西厢》,赝本反先行于世。”[1]225天章阁醉香主人《题卓老批点西厢记》亦云:“吾独怪夫世之耳食者,不辨真赝,但借名色,便尔称佳。如假卓老、假文长、假眉公,种种诸刻,盛行不讳。及睹真本,反生疑诧,掩我心灵,随人嗔喜,举世已尽然矣。”[1]225的确,盗版猖獗,以假乱真,造成“赝本行而原本没”,以致读者“及睹真本,反生疑诧”,给当时读者添了不少困惑,也给现在的戏曲研究带来不便。
然而,书坊对戏曲评点的作伪也有积极的一面。这是因为假托成名人的文人,他们对戏曲的评点也是有意义的。就像吴新雷先生所说:“尽管明末的书商有假冒伪托的恶习,这些评本不一定全都出于李卓吾等人的亲笔,但作为理论批评的一种建设来看,确是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的盛事。其影响所及,由明入清。”[21]65
综上所述,明清戏曲的评点本以坊刻为主;在戏曲评点发展初期,书坊组织下层文人评点戏曲,带动了戏曲评点的发展;并且聘请名家评点,虽然有些评语并不是真正出自名家,但仍然有利于提升戏曲评点的整体水平;书坊主们还亲自评点戏曲,甚至结合自己的戏曲理论进行创作,有效促进了戏曲的繁荣。由此可见书坊在明清戏曲评点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解书坊与戏曲评点的关系,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戏曲评点发展和传播的认识。
[1] 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2] (明)冯梦龙.墨憨斋定本传奇[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
[3] (明)王元寿.玉茗堂批评异梦记[A].古本戏曲丛刊二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4] (明)竹轩主人.歌林拾翠题识[M].杭州:浙江图书馆藏明刻本.
[5] 伏涤修,伏蒙蒙.西厢记资料汇编(上) [C].合肥:黄山书社,2012.
[6] 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7] 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8] (明)佚名. 红梨花记序[M].北京:国图藏明刻快活庵评点本.
[9] 黄仕忠.《琵琶记》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10] 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 (明)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M].明崇祯间刊本.
[13] 转引自黄裳.梅花墅[A].银鱼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14] (明)陈继儒.与萧象林户部[C].陈眉公尺牍.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6.
[15] (清)宋起凤.稗说[A].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16] 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题识[J].文学评论,1961,5;郑志良.袁于令与柳浪馆评点“临川四梦” [J].文献,2007,(3).
[17] 江兴佑.凌濛初不是《幽闺记》的评点者——兼与赵红娟先生商榷[J].浙江社会科学,2005,(4).
[18] 蒋星煜.论《西厢会真传》为闵刻闵评本——与罗杭烈、张人和两位先生商榷[J].社会科学战线,1981,(4).
[19] (清)李渔.闲情偶寄(插图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0]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 [A].郑振铎全集(第6卷)[C].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21] 吴新雷.中国戏曲史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