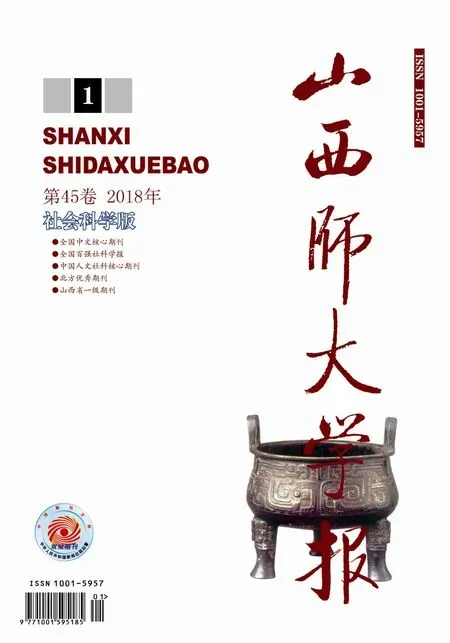农村出嫁女在家庭养老中的角色研究
——以山东省于庄为例
于 光 君
(中华女子学院 女性学系,北京 100101)
一、研究缘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于“女儿”来说,出嫁是身份和角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重要事件。结婚意味着“女儿”从娘家的“自己人”变成了“外人”,同时又成了婆家的“自己人”,“女儿”的权利、生产力、服务转移到了丈夫家庭。[1]619—652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我们这种父系、父居和父权的社会里,女子的生命史和男子有很大的差别:她们一生有两个时期,一是从父时期,一是从夫时期。她们在父母家总是处于暂住的性质,女儿是替别人家养的,泼出去的水,怎能收得回。[2]198结婚前,“女儿”是父系家庭中的“依赖人口”或“家之附从人员”,没有宗祧和家产的继承权,也没有承担家计、赡养父母和参与祭祀的义务,因此,“女儿”在自己的娘家只是一个过渡身份存在,不具有完全的成员资格;结婚后,“女儿”成为丈夫家庭中的正式成员,须无条件向公婆尽孝。[3]169[4]353—375[5]83尽管早在民国时期,法律就已规定了出嫁女儿与儿子一样都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和赡养父母的义务,但是家庭养老实践中的这种性别差异一直以来都是乡村社会的常态,也从未受到家庭成员及其社会主体的质疑。[6]72—81内化了父权制养老伦理的“女儿”及其他家庭成员都不质疑这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因此,“女儿”对于娘家缺乏工具性意义,只是男性继嗣制度的附带受益者。[7]27—33
在生产队时期,农民以社员的身份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家庭是基本的生活单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在社员的家庭生活和生产队的生产劳动中依然存在,生产队按照社员的性别和年龄进行劳动分工,给家庭主妇预留出回家做饭、照料年老公婆和孩子的时间。农闲时节,家庭主妇纺线、织布、拆洗、缝制一家人的被褥、鞋帽等,照料一家人的日常生活。男社员或者参加水利工程建设或者外出做点零活,挣些零钱补贴家用。出嫁女儿只是在父母生日、生病或过年过节的时候回娘家看望父母。出嫁女儿以儿媳妇的身份赡养公婆,而不以女儿的身份赡养自己的父母。家庭养老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同样是没有人质疑这种性别差异的合理性。丈夫作为儿子的角色在家庭养老中始终是“在场”的,基本上没有出现缺位现象,出嫁的女儿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参与父母的养老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女儿养老现象的出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改变。在自然生育状态下,我国农村家庭平均拥有的子女数是7个左右,且大部分家庭都是儿女双全。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农民的家庭规模缩小,并且1/3以上的农民家庭中只有女孩没有男孩。[8]56—58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生育率,致使农民的家庭养老资源萎缩,并且农民的家庭养老资源出现结构性的性别缺失。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明显高于城镇。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资源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是养老资源的萎缩和结构性的性别缺失,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性流动,致使农村家庭养老中出现了儿子缺位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农民工进城的社会问题》课题组调查发现,在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78.64%,女性为21.63%,男性农民工的数量远远超过女性农民工。[9]199—219外流的女性劳动力未婚者居多,而男性则不受婚姻状态的限制,这种差异导致男性严重的角色缺位,已婚女性成为家庭养老的主要承担者。束缚女性的族权、父权和夫权在经历了历次政治和文化运动的打击,又经历了现代性因子的洗礼后已经式微,家庭权力结构由纵向的父子轴向横向的夫妻轴转化,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趋向于平等,已婚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得以提升。丈夫的外出务工使已婚女性对家庭财产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权,在家庭事务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法律知识的普及、女权主义思想的弥漫和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增强了女性的主体性意识,使已婚女性萌发了现代赡养意识,理性地认识到赡养父母是法定的义务。不再将赡养、照顾公婆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在赡养行为中更多地体现出交换色彩;对父母的养老回馈则不仅有情感照顾和精神抚慰,还提供经济支持,并且更富亲情和报恩色彩。[10]25—33交通、通讯设施的现代化,农民经济条件和居住条件的改善也为出嫁女儿赡养自己的父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出嫁女儿参与养老的现象。有研究认为,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角色由边缘走向了前台,其重要性增强和养老行为更为显性化。[11]问题是出嫁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角色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二、研究个案的基本情况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个案的基本情况
不同民族和地区在家庭养老的风俗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比如有的民族一直盛行女儿养老的风俗。本研究选择地处鲁西北的于庄作为个案,于庄一直盛行儿子养老的风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于庄也出现了出嫁女儿参与养老的现象。于庄隶属于德州市陵城区于集乡,是乡政府驻所地,乡党委和政府的机关、乡里的企事业单位和乡中心小学都在于庄界内。此外还有超市、饭店、快递网点、家具店等。改革开放后,于庄就开始发展村办企业,目前,于庄的村办企业已经成长为一个规模较大的纺织企业。上世纪90年代,于庄进行了城镇景观改造,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婚居模式——新户型从妻居。[12]126—130于庄界内的人口由本村人、外村人、外地人和公职人员构成。新世纪以来,由于于庄乡办企业和村办企业效益不太好,于庄本村人外出务工的增多。由于不再审批新的宅基地,以及县城商品房强劲的销售宣传和优质教育资源向县城的集中,父母给子女在县城置办婚房的也多起来。截止2017年9月份,于庄有1400多口人,人均耕地1亩左右,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14人,其中男性2人,女性12人,呈现出高龄老人女性化的趋势。农民没有退休的概念,对于于庄人来说,国际社会认可的60岁或65岁以上为老年人的标准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他们有自己的“老”的地方性标准,只有失去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时候才算是“老”了,成年子女才开始承担赡养义务。而在于庄人的观念中,子女只有结了婚才算是成人了,才成为赡养父母的责任主体。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正在履行赡养义务的出嫁女儿,既包括履行赡养自己父母的义务,也包括履行赡养公婆的义务,既包括从于庄嫁出去的女儿,也包括嫁到于庄的儿媳妇。从于庄嫁出去的女儿18人,最大的67岁(老母亲86岁),最小的38岁;嫁到于庄的儿媳妇14人,最大的71岁(老婆婆93岁),最小的36岁。本研究以于庄为个案,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收集资料。
1.观察法。家庭是观察单位,家庭生活是观察内容。笔者是于庄人,因此笔者具有了“自己人”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既能够置身于自己的家庭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又能够置身事外,对别人的家庭生活进行观察;既能够对于庄人的家庭生活进行整体性观察,也能够对研究对象的家庭生活进行重点观察。
2.访谈法。每一次和家里人、邻居以及村里其他人的聊天都是一次访谈。为了研究的需要,笔者对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和局外人进行了访谈,访谈是以村里人习惯的聊天方式进行的。
最后,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概括、归纳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
三、研究发现
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社会中的人确定社会角色,按角色要求的行为规范活动时,便进行社会角色的扮演。[13]139—148通过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出嫁女儿萌发了现代赡养意识,在履行传统的赡养公婆义务的同时,也开始自觉地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但是,家庭养老中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形式上的性别差异比较明显,但实质上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出嫁女儿在家庭养老中扮演着缺位者、代位者、失语者和权利遗失者的角色。
(一)在自己父母的养老生活中依然扮演着“缺位者”的角色
改革开放前,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农民家庭养老中的性别差异都非常明显,从夫居使得儿子和女儿在父母养老中显示出不同的工具性价值。在农民养老生活的实践中,儿子为父母养老送终,出嫁的女儿则不为父母养老送终。儿子们共同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成为父母养老的主体,轮流赡养父母。出嫁的女儿们则采取季节性地“回娘家”的方式以尽孝心。经济条件不允许出嫁女儿对娘家父母有太多的物质方面的帮助,居住条件也不允许出嫁女儿像儿子那样与父母共居养老。农民养老生活的实践逻辑与“社区情理”*社区情理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及文化相对落后的社区中,存在着由地区亚文化决定的某些为在该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与此相适应的观念,这些规范和观念可能有悖于一定社会的制度和规范,或者与一定社会的制度和规范存在着某种不适应。但因为社区的封闭性且居民文化层次较低,所以这样的社区行为规范和观念仍得以存在并发生作用。而在社区中生活的人在选择自己行为时,则首先考虑自己的行为能否为社区中的他人所接受并把它看作是自己行为选择的主要标准。换言之,只要他们的行为能够得到在同一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的赞成,他们就认为可行。”社区情理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因此,此处所说的“社区情理”其实是有点和涂尔干所说的“集体良心”或“集体意识”相类似,也具有外在性、普遍性与对个体的强制性的。但是它又以规范及与规范相适应的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受到社区舆论的制约,带有十分明显的地区亚文化的特质。参见杨善华、吴愈晓:《我国农村的“社区情理”与家庭养老现状》,载于《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2期。的逻辑是一致的,但与国家法律的逻辑是有差异的,法律规定子女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出嫁女儿置身于国家法律与“社区情理”的结构性张力之中,比照法律逻辑的准绳,出嫁女儿扮演着“缺位者”的角色,但是没有人质疑这种“缺位者”角色的不合理性。而且由于没有出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外出流动现象,儿子的“在场”掩盖了出嫁女儿在父母养老生活中“缺位者”角色对父母养老生活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农村男性劳动力向城镇的集中性流动出现了儿子在家庭养老生活中“不在场”的现象,这造成两种结果,一是已婚女性在自己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上升,能够支配家庭财产。由于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的经常性“不在场”,已婚女性要独立处理家庭事务和打理人情关系,其在家庭生活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并有了更多的实践性权力,出嫁女儿有条件和能力赡养自己的父母;二是在家庭养老资源萎缩的同时出现了家庭养老资源的性别结构性缺失的问题,基于亲情,在儿子经常性“不在场”的情况下,出嫁女儿参与到父母的养老生活中,为父母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来说,法律知识的普及和男女平等观念的增强提高了出嫁女儿履行赡养自己父母义务的自觉性,她们努力改变在父母赡养中扮演的“缺位者”角色。
在于庄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尽管出嫁女儿越来越多地履行了赡养父母的义务,但是依然扮演着“缺位者”的角色。从夫居为儿子和出嫁女儿履行赡养义务提供了不均等的条件,出嫁女儿缺少像儿子那样的“在家资本”,不能像儿子一样履行赡养义务。于庄人有自己评判“履行赡养义务”的民间标准,与父母经常性的“共居”养老才算是履行了赡养义务,有条件的出嫁女儿把父母接到自己家里照料一段时间,也只是在儿子们协商好的“轮养”的基础上,均等地协助儿子们进行照料,不是作为像儿子一样的一个平等的赡养主体。过年过节的时候父母必须要回到儿子家去,不能在女儿家,这既符合农村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也能满足父母和儿子们保持“面子”的要求,这一点要求是出嫁女儿由于缺少“在家资本”所不能给予的。出嫁女儿对父母提供的经济、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甚至把父母接到自己家里进行照料,都是出嫁女儿“顾娘家”和对父母“尽孝心”的表现,而不是“民间意义”上的履行赡养义务。在于庄,为父母“送终”是养老的重要内容,在为父母“送终”的丧礼上,儿子是丧礼仪式“前台”不可缺少的性别角色,这是出嫁女儿不能替代的。身处法律与“社区情理”结构性张力中的出嫁女儿,由于从夫居所造成的“在家资本”的缺失,依然扮演着“缺位者”的角色。
(二)在自己公婆的养老生活中依然扮演着“代位者”的角色
从夫居割裂了出嫁女儿与自己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结婚后,女儿就成了婆家的人,赡养公婆就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从夫居相契合的父权制的养老伦理和养老文化为儿媳妇赡养公婆提供了道德上的根据,但是在法律上儿媳妇只具有协助丈夫赡养公婆的义务,承担赡养义务的主体是作为丈夫的儿子而不是作为妻子的儿媳妇,《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依然在农民的生活中发挥着实际作用,出嫁女儿作为家庭主妇承担着料理家务和照料公婆日常生活的重任,丈夫名分之下的赡养义务由妻子代为履行,出嫁女儿在公婆的养老生活中扮演着“代位者”的角色。在改革开放前的生产队时期,生产队的劳动分工默认家庭主妇赡养公婆的责任,给作为家庭主妇的女社员预留出做饭、照料老人生活的时间。由于当时农村劳动力流动较少,在家庭生活中丈夫经常“在场”,也能帮着妻子照料一下父母的生活,妻子在公婆养老生活中所扮演的“代位者”的角色没有突显出来。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民工潮,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集中性流动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外出务工的已婚男性明显多于已婚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丈夫经常性地“不在场”,赡养父母的义务基本上都转嫁给了妻子,由妻子代为履行赡养义务。在公婆的养老生活中妻子作为“代位者”的角色凸显出来。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行,以及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女性开始摆脱父权制养老伦理的束缚,能够理性地认清自己在家庭养老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赡养公婆不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赡养公婆是丈夫的法律义务,自己有协助赡养的义务,协助丈夫履行好赡养义务,使丈夫安心工作能够增进家庭的利益。妻子作为“代位者”的角色,赡养公婆的质量取决于与公婆的关系以及公婆对自己家庭生活所给予的支持程度。族权的瓦解、生产队体制的消解以及农民生活的原子化,对儿媳妇作为“代位者”的赡养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丈夫的不“在场”既增加了妻子赡养的负担,又减少了对妻子赡养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妻子扮演的是“代位者”的角色,丈夫要对妻子赡养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儿子的“孝”与“不孝”取决于妻子的赡养行为是否得到父母及社会的认可,也取决于是否能够平衡好娘家与婆家之间的关系,太“顾娘家”容易引起公婆的不满,因为儿媳妇和公婆两代人所秉持的养老的伦理逻辑以及对儿媳妇在家庭养老中的角色认知存在着差异。
(三)在双方父母养老事宜的协商中依然扮演着“失语者”的角色
在父母如何养老的问题上,儿子具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儿子出现在“前台”。出嫁的女儿则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决定权,出嫁女儿在“后台”,扮演着“失语者”的角色。因为对于娘家来说出嫁的女儿是“外人”了,不能参与娘家的家务事,娘家的家务事由娘家的“自己人”决定,父母的养老问题是娘家的家务事,理应由儿子们决定。虽然在父母的养老问题上出嫁女儿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但是出嫁女儿具有监督权,出嫁女儿在“后台”默默地监督着儿子们的养老行为,当儿子(或儿媳妇)对父母的赡养行为超出道德底线的时候,出嫁女儿就有话语权了,出嫁女儿以父母利益代表者的角色通过谴责儿子(儿媳妇)的不当行为来维护父母的权益。出嫁女儿这种监督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在儿子们中间的威望,如果出嫁女儿对娘家父母和弟兄们的帮扶较多,或者儿子们(儿媳妇)觉得出嫁女儿婚姻家庭的社会关系资源丰富,出嫁女儿在自己原生家庭的威信就高,反之,威信就低,儿子(儿媳妇)就不会太在意出嫁女儿的态度。
表面上,出嫁女儿作为儿媳妇的角色在公婆的赡养问题上也是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的,同样扮演着“失语者”的角色。作为儿子,丈夫是履行赡养义务的责任主体,在父母的赡养问题上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在协商父母养老问题的时候,儿子们在“前台”,儿媳妇们在“后台”。关于公婆的养老问题,儿媳妇在自己的小家庭是有话语权的,但是儿媳妇是不能走向“前台”的,儿媳妇的话语权是通过丈夫在“前台”实现的。丈夫的意见代表的不是自己的意见而是夫妻两人的意见,甚至是妻子的意见占上风。丈夫往往向妻子妥协,因为以丈夫的名义承担了赡养的责任,实际上是妻子在替代或协助丈夫履行赡养义务。如果妻子的话语权没有通过丈夫得到实现的话,妻子会通过和丈夫吵架或不善待公婆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这是丈夫所不希望的。
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权力发生了由上到下、由丈夫到妻子的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流动又增加了妻子在家庭事务中的实际权力。妻子在公婆赡养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作为女儿的角色对自己父母养老生活提供了较多的帮助,因此在父母的赡养问题上也有了较多的话语权。但是,出嫁女儿无论是作为女儿还是作为儿媳妇,虽然在父母和公婆养老生活中有了较多的实践性话语权,但是还没有走向“前台”。在现实生活中,儿子或丈夫依然具有话语权,出嫁女儿依然扮演着“失语者”的角色。
(四)依然扮演着“权利遗失者”的角色
无论是在原生家庭还是在自己的婚姻家庭中,出嫁女儿都不能实现自己的财产继承权,扮演着“权利遗失者”的角色。改革开放前,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出嫁女儿不能像儿子那样赡养父母,只能以“回娘家”的方式对父母表示孝心。根据“社区情理”,出嫁女儿既不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也不继承父母的财产,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尽管按照国家法律的逻辑这是不平等的。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出嫁女儿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履行了赡养父母的义务,但是由于农村和农民财产形态的独特性以及传统习俗对男性的偏爱,出嫁女儿仍然不能实现自己的财产继承权,这既不对等也不平等,出嫁女儿的权利仍然遗失在法律与“社区情理”的博弈场域中。出嫁女儿作为儿媳妇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实现公婆的财产继承权,只能以丈夫的名义实现财产继承权。《继承法》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也就是说,没有丧偶的儿媳不能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尽管儿媳妇也尽了赡养义务。尽管出嫁女儿在家庭养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父系继嗣和财产继承制度并未因此而消失。[8]56—58
四、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出现了女儿养老的现象,横亘在娘家和婆家两个家庭之间的性别壁垒在慢慢消解,但是出嫁女儿在家庭养老中依然扮演着传统的角色,依然存在着“名”“实”分离的问题。通过对出嫁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角色的研究发现,尽管家庭养老中实质性的性别差异在缩小,形式上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在农村家庭养老中依然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现象,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在双方家庭中扮演着不对等的角色,履行着不对等的义务。已婚女性作为女儿和儿媳妇在家庭养老中扮演着二元化角色,既要赡养自己的父母又要赡养公婆,而且重心一直在公婆——丈夫的父母这方。儿媳妇不积极参与公婆养老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也就是在家庭养老中存在着“差序格局”问题。[11]已婚男性则扮演着一元化的角色,只赡养自己的父母不赡养岳父母——妻子的父母。就出嫁女儿的原生家庭而言,出嫁女儿和儿子在履行赡养义务中拥有的条件是不同的,女儿出嫁,离开了原生家庭,丧失了“在家资本”,儿子却拥有“在家资本”,出嫁女儿不能像儿子(儿媳)那样对父母进行生活照料。而在村民看来,“在家资本”具有无限的价值,是不能替代的。依据这种逻辑,出嫁女儿对父母的帮助和照料更多地是被理解为对父母尽孝心的表现,而不是养老行为,出嫁女儿依然扮演着“缺位者”的角色。出嫁女儿作为儿媳妇对公婆的赡养是依附于丈夫以丈夫的名义进行的,依然扮演着“代位者”的角色。因为家庭代际传承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完全由家庭经济基础和家庭权力的代际转移而引发的自发过程,而是一个融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为一体的过程。[8]56—58在中国农村家庭变迁中,传统与现代并存,一方面,小家庭内部关系趋于平等;另一方面,传统父系家族的文化结构和继承规则仍旧主宰乡村社区,体现出很强的文化韧性。[14]18—36中国传统的以儿子为核心的赡养方式并没有彻底瓦解,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9]199—219
家庭养老中依然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直接原因在于从夫居所造成的男女角色的不对等以及所拥有“在家资本”的差异,父权制的养老伦理和养老文化契合了这种状况。父权制养老伦理和养老文化是建基于不对称的性别关系之上的,依靠性别不平等的泛“孝”主义道德维系着家庭养老。因此,为了实现农村家庭养老中的性别平等,促进家庭的和谐与团结,提高养老生活质量,不仅要改变传统的从夫居以外,还要建构以男女平等为基础的新型养老文化以适应和引领新形势下的养老生活。新型养老文化在逻辑上消解了传统性别制度建构的女儿养老悖论,强调儿子和女儿一样,他们作为养老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一致的,他们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是统一的。已婚男性要和已婚女性一样扮演对等的角色,夫妻合作,共同履行好赡养父母的义务。女性和男性一样成为名实相符的赡养主体。
[1] Monica Das Gupta, Lishuzhuo. Gender bias in China, South Korea and India 1920—1990: The effects of war, famine, and fertility decline[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0, 1999,(3).
[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陈其南.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M].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0.
[4]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M].张建国,李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 Cohen, Myron. Kinship Contract Community and Stat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6] 高华.刍议当前农村家庭养老中的新性别差异——对晋东S村的实地调查[J].人口与发展,2012,(2).
[7] 张翠娥,等.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寻乌县的调查数据[J].妇女研究论丛,2013,(5).
[8] 高华,等.刍议当前农村多子女家庭中的女儿养老现象[J].湖北社会科学,2013,(5).
[9] 许琪.儿子养老还是女儿养老?——基于家庭内部的比较分析[J].社会,2015,(4).
[10] 张小红.农村已婚女性双重身份的养老行为差异—— 基于闽南S村的人类学考察[J].老龄科学研究,2014,(8).
[11] 李鑫宇.女性在农村家庭养老中的角色转变研究——以长春市 Z 村为个案[D].长春:吉林大学,2012.
[12] 于光君.婚居模式的嬗变及其现实困境——山东省于庄个案研究[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13]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4] 唐灿,等.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J].社会学研究,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