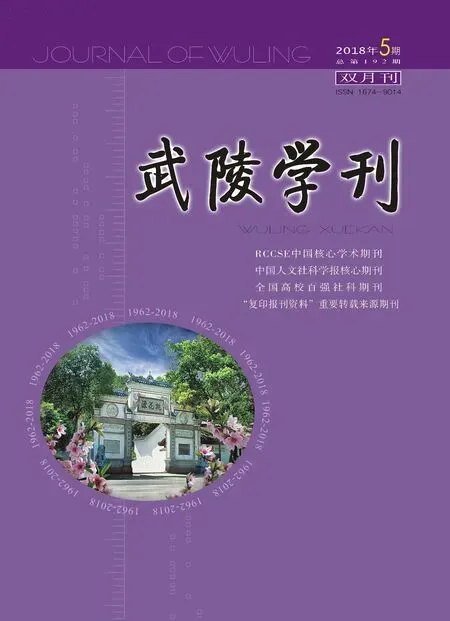经验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化与群体秩序的构建
张东赞
(外交学院 基础教学部,北京 100037)
乌尔里希·贝克睿智地指出,如果说阶级社会的推动力用“我饿”来概括的话,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风险社会,群体的情感反应用“我怕”来概括更加贴切[1]。全球化最初的动力是使西方过剩的商品、资本乃至技术无障碍地在全世界自由扩展,以攫取目的地的人力、土地等资源,获取常规方式所不及的超额利润。由于全球经济互联性的增强,不同生活方式之间互相渗透,打破并超越了传统的同质化和分隔化的文化观念[2]45。因此,全球化一方面带来了物质产品在时间和空间上极大的流通,另一方面也带了一些新的变化,其所到之处逐渐影响并改变着当地人们的文化观念乃至生产生活秩序。同时,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也把风险带到了世界各地。从文化角度看,不断增强群体的稳定性和凝聚力以及成员的群体归属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风险社会带给个人的情感焦虑。
一、生活经验与文化记忆
历史是由日常生活的许多常规习惯和相关行为模式等一些重复结构组成的,并非由众多不可重复的奇特事物以及众多具有威力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构成[3]。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外在环境的关系时,形成了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模式以及重复结构,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人们行为的规范性和定型性。钱穆先生指出,西方文明更看重怎样创造物,即看重如何成物,更重视创新及变化,而华夏文化则更重视如何“做人”,即寻求人与外在世界的稳定性及达到和谐的状态[4]。这种和谐的表现就是人们生活中的“常”,即过去的经验在生活中的现实化。因此,过去不是静止地存在于群体的记忆深处,而是通过某种形式凸显于群体之中。
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过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文化建构和再现的结果。过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具有两个特点:建构性和重现性。所谓建构性,是指过去能反映人们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的认知特点以及相关文化观念。它不同于历史,历史重视客观性且受到各种冷峻的检验,过去则是人们生活的部分或背景,负载着人们的生活导向、意愿以及生活希望等主观性的观念。人们倾向于将某些具有经验价值的重大事件或者人物进行建构,并以一定的形式将其固定保存下来,以便对此进行讲述和传承[5]67。一般来说,有意义、有价值的经历才有被建构成过去的可能性。这种历史感也是人类的重要特征,它与人类创造文化的能力共生并存。过去总是由特定的动机、期待、目标所主导,并且依照当下的相关框架进行建构[5]87。“我们自己的生活史总是被纳入我从中获得自我认同的哪个集体的历史之中。我是带着过去出生的……若是试图脱离这种过去,那就意味着改变我当前的关系。所以我的根本部分就是我所继承的东西即一种特定的过去,它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于我的历史之中。”[6]每个过去都曾经是上一个过去的参照,即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发展,过去不断被新的过去所代替和覆盖,但是人们不可能完全脱离上个过去的影子。当过去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经验。对一个群体而言,过去主要存在于群体记忆之中。因此,只有使文化建构的过去从群体记忆中激活并一直保持活跃的状态,才能保持文化观念的鲜活性,并让过去的经验服务于日常生活。
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旧经验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并逐渐被新经验所代替。比如,在获取食物方面,采集游牧阶段被奉为圭臬的行为在农耕文明中将逐渐被新的方式所代替。那个时候,人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不得不去追捕、战斗、杀戮。到了农耕社会,游牧时期的那些经验、故事已经不再适合人们的生存环境,有利于稳定、团结的传说、故事以及经验反而成为人们所钟爱的[7]。伦理和信仰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将这些过去连接起来形成群体的文化记忆,使过去不再以散点的形式存在而变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链条。一般来说,文字、节日活动、神话、仪式化的活动都可以成为客观外化物,成为群体回忆的载体[5]47。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客观外化物总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于群体成员之间,从而创造出一种文化氛围不断提醒群体成员并传递着相关的文化信息。
当过去负载于一定的客观外化物时,经验就具有了传承的重要条件。离开群体成员的文化体验和反思,过去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以汉字为例,它作为华夏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比如“婚”,《说文解字》:“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从女从昏,昏亦声。”“婚”字透露了古代部落之间的抢婚习俗,抢婚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的是当时人们对于“同姓结婚,其后不藩”这一现象的经验认知。人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已经意识到生命必须繁衍。自然非常钟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抢婚习俗失去了其存在的环境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风俗习惯。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至今仍保留抢婚的习俗。文字作为华夏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一旦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将进入一种接近“冬眠”的状态,需要后人进行一定的阐释才能为人所理解。当社会发展了,某些文本或者文字不再使用时,对于某种经验来说就成为其坟墓。
“过去”若要保持活跃的状态,还需要群体成员的广泛参与。其中,节日和仪式化活动保证了群体成员的广泛体验与参与。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为“重阳节”,又称“老人节”。庆祝“重阳节”一般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节糕、饮菊花酒等活动。这些文化活动阐释了敬老崇孝的文化观念,这与中国农耕社会重视稳定与和谐的经验相吻合。节日或者仪式性的活动作为经验的重要载体,在周期性循环中使群体成员产生了一种被解读的需求。解码过程往往伴随着复杂的感知、情感以及意识形态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群体记忆处于被激活的状态。
二、经验演变成社会生活秩序
文化作为人的一种行为和认知模式的系统结构,它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习得的。文明人之有别于原始人的地方就在于其后天获得的丰富的知识和习俗,习俗乃是文明降生的基本条件[8]697。在一个群体中,习俗本身就是经验的总结,是前人宝贵经验的传承。比如在中国传统婚礼中,新娘子的“红盖头”就从最早的行为经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生活习俗。上古时期,抢婚是部落之间常常发生的行为。在一天之中,傍晚无疑是抢婚的最佳时间。抢婚者去的时候能看清楚道路,回来时为了阻止女方部落追赶,防止被抢女子认路逃回娘家,抢婚一方就用布把所抢女子的头蒙上,这大体就是新娘子“红盖头”的来历。可见,“红盖头”是远古时期抢婚过程中的一种经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原来的经验就慢慢演变成了习俗。当习俗被大家遵守时,就慢慢演变为具有规范性的社会生活秩序。经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拥有的知识和智慧的体现,随着人们实践领域的不断扩展,有的经验转化成习俗被保留下来,从而成为一个群体的精神财富。这个财富越丰富,整个群体的凝聚力也就越强,群体也就越稳定。
社会日常生活秩序是生活习俗的综合反映,而习俗表现在人们生活实践的不同领域。当不同领域的经验被传承并进一步转化成习俗之后,人们的行为活动就被定格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秩序里。在这种秩序下,自然的人性受到一定的压制,习得特性得到进一步发展。习得性特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化。奥尔森(M.Olsen)指出,社会结构的存在需要某种程度的秩序化,这种秩序化包含个体、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其中,个体的秩序化使个体的认知、情感等心理活动过程具有连贯性和稳固性,从而增强个体的安全感,降低个体在面临陌生环境时的恐惧感;社会秩序化就是群体成员在交往过程中共同享有的文化观念、群体回忆形成的带有模式特征的行为。同时对文化行为进行共同的阐释,享有并传承为群体所认同的生产生活秩序[9]。
在汉语里,“秩序”的含义如《说文解字》所说:“秩,积也……序,东西墙也。”“积”字从“禾”以之释“秩”,本来指收割后禾粟储存的一种形态:“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庄子》)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积”有[次第]这样的语义特征,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而“序”所指的东西墙,本是古人室前阶之“堂”左右两边的墙,作为建筑部分的“序”就成了主客及他人登堂、依年龄或者尊卑安排坐席的标记性设施,因而也就有了“次第”这样的语义内涵,并被赋予了认知主体的某种主观意识[10]。在汉语语境里,秩序主要表现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时所形成的习俗规范,即人们在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时的经验总结。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从崇拜自然到天人合一都是经验的总结。人类在其早期,不能很好地把主体和客体分隔开来,面对一种突如其来的不确定和充满风险的未知世界,人们必须作出前行或者后撤的决定。在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人们采取的是保守退让的策略,即对自然的偶像崇拜。人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既定的秩序里面,通过占卜听取所谓神灵的安排也就理所当然了。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运动的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传统的“礼”就是农耕社会中人们生活经验的高度总结。秩序的存在本身就是经验的进一步升华,它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确保了一个群体的稳定运行。
对于整个社会结构来说,它的正常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秩序化。群体成员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带有模式性的行为,对周围环境的阐释达成某种共识,即形成群体共同认同的生活秩序。这种秩序又通过群体成员的具体行为方式展现出来,个体的秩序化使个体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以及在群体生活中更加和谐地与其他成员相处。对一个群体来说,将文化建构的“过去”变成社会生活秩序,并在群体成员中传承下去是保持群体稳定的重要条件。
三、仪式的重复与文本的阐释
秩序是一个群体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具有规范性和定型性的经验。为了抵抗日常生活的无常,秩序需要就凸显出来。从信息处理的角度来说,人们对日常行为的处理主要是自动信息处理,即个体听任情绪反应并按照惯例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内部和外部的诸多信息往往视而不见。对抗这种无视生活中固有秩序的有效行为就是文化观念的重复。重复是凸显秩序的重要方式,也是文化自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所谓文化自觉,是指洞察文化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认识文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思考文化发展的现在和未来的意识和能力[2]34。为了保证文化健康持续发展,文化所建构的生活秩序必须在群体生活中保持一种活跃的状态。
仪式以及节日类活动的重复是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机制。重复让群体成员生活在规范性的社会生活中,使文化观念在时间层面上的叠加得以在空间上进一步凸显,从而保证了文化观念的鲜活性。这种周期性的文化行为一旦成为大众的活动,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媒介作用就更加凸显出来。循环的周期性使人们产生一种距离感,从而产生了对文化解码的需求。文化观念在循环类的活动中也会处于一种被激活的状态。当节日把时间的河流加以结构化和节奏化之后,日常生活就在这种秩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日常生活从宗教生活分化出来并创造了自己的秩序,节日也就变成了一种供特殊的另类的秩序、时间和回忆栖居的所在[5]53。在循环的行为活动中,个体的参与性被凸显出来。节日正如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钟表,它将日常生活进行切分然后传递出一定的文化信息。如果说钟表提供人们准确的时间信息,人们按照这一信息来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么,节日就将日常生活的秩序重新进行编排从而凸显出一个新的计时系统。该文化系统的群体成员一定会看得懂节日“时刻表”的编排逻辑,并做相应的反应。一般来说,这种节日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大多是文化的核心观念。仪式性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重温过去的重要事件,保护与传承社会的核心观念。通过仪式活动,仪式的参与者与过去建立起了关联,重建集体赖以生存的秩序,从而维持群体的正常运行。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阐释是文化信息的再一次编码。在有文本的社会,文本属于一种支配霸权式的编码,解码者完全根据编码者的意图进行信息的接收。文字符号是华夏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的构造之特殊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因此,对汉字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化信息的再一次编码。比如“武”。从字形上看,武“从止从戈”,与战争有关系。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而《说文解字》中也有另一种阐释:“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文甫切。”许慎取了楚庄王关于“武”的阐释,即停止战争征伐乃是“武”。再如“国”字,《说文解字》曰:“邦也。从囗从或。古惑切。”《说文解字》:“或,从囗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从古人对“国”的阐释可以看出,稳定的社会秩序对于农业社会的重要意义。
四、秩序与身份认同
人类不是无私的蚁群,也不是反社会的独眼巨人,而是一种“社会动物”。只有与他人交往,人类才能表现和发展自身的个性,进一步实现个人、群体乃至对整个社会的身份认同,社会则为人类的交往提供了平台[8]665。对于人们交往的平台来说,它需要过去,只有过去才能使群体所在的平台进行自我定义。对于过去的指涉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需要有证据证明过去的存在;其次,过去和当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5]24。过去的确存在,它存在于集体回忆之中,并通过外在表征物凸显出来。过去和当下的差异性源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从而使得文化建构的过去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关于个人分享群体过去进行身份认同的问题,菲尼(Phinney)提出了“三阶段”的模式。在最初阶段,个体尚未对民族群体的观点进行积极或者消极的调查探索,个体只是不自觉地习得载有民族观念的风俗习惯,对这种生活秩序习以为常。第二个阶段是个体寻求民族身份的认同[11]。在这个阶段,个体成员开始从无意识地习得习俗开始转向自觉地学习并理解本民族的文化符号。文化符号作为文化观念的载体,是人们对过去生产生活中所经验的事与物的观察和感悟的固化。符号需求是人类特有的基本需求,人类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总是在积极地将人们的经验转化成某种符号,以实现其载体化。符号转换活动既是思维必不可少的行为,也是思维的先决条件,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12]。群体成员对文化符号解读的过程,也是对生活秩序的一种解码过程,并通过这些活动寻求群体身份认同。意义和经验不单单是个体成员对事与物的认知以及阐释,而是群体成员的一种共同感知,属于群体的共同精神财产。他把意义定义为社会行动者对其活动目的的符号化确认。在他看来,被符号化的意义才是群体成员的一种共识。社会行动者的身份认同是基于某种或者某些文化属性的意义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文化意义的属性较之其他文化意义来源被赋予了优先的地位。第三个阶段则是文化认同的形成,个体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强烈的依附感,对日常生活秩序有较高的认同感。
过去的存在是信息的储存、调取、传承的一种行为。只有这种被文化建构的过去被传承下去即被群体成员所共享的时候,这个过去才是存在的。如何让这种过去保持一种积极的状态,就需要通过外在的表征物。过去和现在的差异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统治者出于对整个群体的统治需要,会将带有自己意志的观念投射到社会生活秩序中。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3]群体成员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分享继承带有集体观念的过去从而不断加深自己的身份认同感。
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本土文化的日渐衰微,民族活力日渐消磨,民族文化失去自己的特性,成为强势文化的附庸。群体的身份认同感因此也在降低,随之而来的则是群体的凝聚力减弱。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华文化跟异质文化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文化必须认清自身,保持自身的特点,不断发掘并弘扬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优点,顺应时代的发展,实现文化互鉴,这才是中华民族所必然要走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