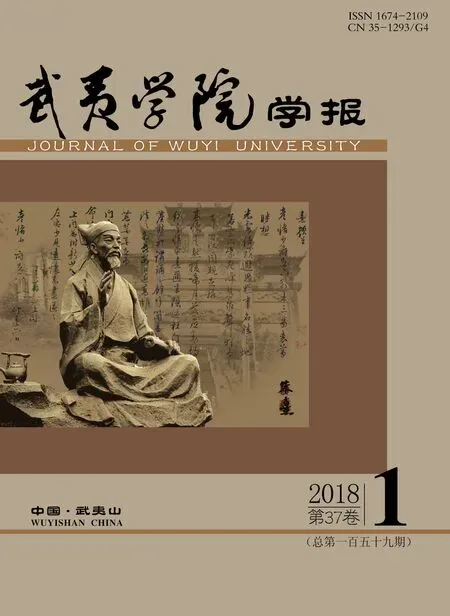定时在线传播行为性质辨析与权利界限
张 轩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定时在线传播侵权的认定始于2008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宁波成功多媒体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成功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时越公司)著作权纠纷案”(以下简称《奋斗》案)①,法院认为“虽然网络用户在其选定的时间不能够获得《奋斗》的全部或任意一集的内容,但却能够获得网站正在播放的那一集的内容。因此,北京时越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奋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二审法院同样认为悠视网未经许可的在线播放行为侵犯了宁波成功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②。而在相似案情的“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其他著作财产权纠纷案”、“安乐影片有限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等案件中,法院认定该行为侵犯的是《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③。显然,不同法院在处理有关定时在线传播行为侵权案件时有不同的法律适用④。定时在线传播行为由于是一种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不同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也非传统的广播权所能涵盖,因而引发了众多学者对该类行为侵权认定与法律适用问题的诸多思考与讨论。
一、定时在线传播行为的侵权认定
出现上述司法判决分歧的原因在于,定时在线传播行为作为新近出现的新的“非交互式”传播方式,由于立法技术的问题,导致这类行为并没有任何一项现有的专有权利进行调整;且与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相似性,因而出现适用上的分歧。对此,司法实践中一般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该类行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二是认为该类行为侵犯广播权;三是认为该类行为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纳入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范围的考量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限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⑤。通过信息网络传输,使得公众能够获得其提供的视听作品是其与定时在线传播行为的相同点,也是易混淆点。但两者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行为方式是交互式传播,目的是“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⑥;而定时在线传播典型的行为是“网络内容服务商按照预先发布的节目表在特定的时间通过信息网络播放节目”[1],公众此时没有个人选择余地。因此《奋斗》案中,法院忽视了《奋斗》只能在特定的时间选择该节目这个定时在线传播的特征而只关注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这一特性。既然两种行为都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那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模型是否可以涵盖定时在线传播行为,予以一体保护?我们尝试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源头寻找答案。
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源头在于WCT(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八条后半句:“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获得这些作品”[2]。该条后半段是在描述网络传播方式中的交互式传播,但是该条前半句:“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限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2],规定了“向公众传播权”(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这就包括了不论采用“交互式传播”,还是“非交互式传播”的定时在线传播行为,也包括了将来可能出现的新的传播方式,即采用了“技术中立”的立法方式。因此WCT第八条前半句正是为解决诸如定时在线传播行为这种新的“非交互式”传播提供法律依据,这也是WCT第八条前半句的使命所在。另外,著作权作为专有权——私法中的“公权力”,对“权力”进行脱离本意的扩大解释,似乎也是对其他私主体的不利解释。因此,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表明该专有权利控制的特定行为方式只能是WCT第八条后半句的“交互式传播”,将侵犯“非交互式”的定时在线传播行为强行运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予以保护,只能导致《著作权法》的专有权利体系遭受破坏。
(二)通过广播权控制的疑问
既然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不能规制侵犯“非交互式传播”方式传播的定时传播行为,那么广播权是否可以规制呢?
有学者认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完全符合《著作权法》第十条关于广播权对于广播行为的规定,该条规定广播行为可以采用“以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进行传播,而广播权的规定中并不要求“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这一要件,因此可以适用广播权的规定[3]。通过“央视国际诉百度案”的司法判决⑥可以看出广播权控制的有线传播或者转播行为包括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行为,这或许让人理解为广播权足以规制侵犯定时在线传播的行为。但是我们从广播权的实质上看,广播权控制的是对于信号的转播权,即先是接收以无线或者有线的方式传出的信号,然后通过以有线或者无线的的方式对该信号进行转播,并不包括对于作品的直接传播。即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权所控制的有线传播只是以有线方式传播无线广播的行为,并不包括通过信息网络这种有线方式直接传播作品的行为。
因此,在现有的《著作权法》对广播权的法律框架之下,我们无法通过广播权这个专有权利对受到侵犯的定时在线传播行为予以规制。
(三)“其他权利”兜底条款的适用
由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定义上的不周延,使得上述的“信息网络专有权”和“广播权”无法对侵犯“非交互式”网络传播的行为进行规制。因此,在实践中,除了少数几个法院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对该类行为进行规制,大部分法院是适用的是《著作权法》的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兜底条款”。
如前所述,WCT对于“非交互式”的定时传播作品是要求给予保护的。2007年6月9日,WCT正式在我国生效,也即意味着我国有义务履行WCT第八条前半句条款,对“非交互式传播”的定时在线传播作品予以著作权法保护。
在“安乐影片有限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 “兜底条款”:“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认定被告侵权。2010年5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第十条:“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信息网络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在线播放的,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进行调整”。所以在我国《著作权法》尚未修订之前只能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兜底条款”对“非交互式”的定时在线传播作品予以保护。这也是学者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定时传播行为版权法保护的主流意见与做法。
二、定时在线传播行为保护的法律模型建构
目前,对于定时在线传播行为著作权法保护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建立如WCT第八条的“向公众传播权”,如美国版权法第一百〇一条“公开表演或者传播作品权”规第(2)项规定:“利用任何装置或者方法向第(1)项规定之地点或者向公众传送或以其他方式传播作品的表演或者展出,无论公众是否可以在同一地点或者不同地点以及是否可以在同一时间或者不同时间内接收到该表演或者展出”[4]。二是适用兜底条款“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予以保护。采用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会带来著作权内容传播技术和方式的增加,“其他权利”这个兜底条款,作为一种立法技术可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的作品使用方式,另外也体现了著作权权利体系的开放性[5]。三是打破交互式传播和非交互式传播的界限,直接设立专有权利。四是对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重构。由于现有的《著作权法》中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立法违背了“技术中立”的原则,使得定时在线传播权行为无法得到专有权利的控制。因此,我国的《著作权法》应当遵循“技术中立”原则,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进行重新建构。学界有三种建构方案,一是对广播权进行重构,使之能够控制非交互式的传播行为[6];二是设立一项广义的“公开传播权”,使之涵盖对于“交互式”或“非交互式”的传播作品的行为,不论该行为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进行传播[7]。三是对“信息网络传播权”重新进行定义,使其能够适用于所有网络传播行为,以适应技术发展和权利保护的现实要求。
若现有的法律框架下的专有权利能够规制侵犯定时在线传播的行为,那么根据奥卡姆剃刀定律(Occam's Razor,Ockham's Razor):“如无必要,勿增实体”(Entities should not bemultiplied unnecessarily),确实没有必要创设新型专有权利对该类侵权行为进行规制,但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兜底条款”,则难以应对因技术进步带来的新问题而给现存的《著作权法》的立法体系带来不稳定性以及造成司法判决的不一致性而产生司法不公正的情形。因而,从法经济学角度来看,因为侵犯一项权利界限模糊难以找到准确法律依据的定时在线传播的侵权行为容易造成长期的经济效益减损程度,要大于一次《著作权法》修订过程中对相关权利进行重新建构的法律成本。因而,既然我国已经加入《WIPO版权条约》,就应当对“非交互式”的“定时传播作品”采取符合WCT第八条的保护水准,应当仿效WCT第八条条约的规定,设立“向公众传播权”,在向公众传播权下再区分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此时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在采用现行法意义上“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这个行为结果的立法技术,而是包含了交互式和非交互式传播的方式的新概念[8]。不论是通过何种传播方式,也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均对其形成的作品予以保护,类似于美国的公开表演及展览权(right of public performance and exhibitions)。另外,“向公众传播权”这种宽泛的、技术中立的立法模式可以减少因技术进步给立法带来的新问题。固然,设立“向公众传播权”需要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等传播权利进行立法重构,于法经济学角度,这样的重构需要耗费大量的立法成本,而诸如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基本不用花费认为司法成本。但是在设立了“向公众传播权”以后的相关司法判决中,可以节省大量司法成本,亦保证了案件的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因此,从法经济学角度,在现有的《著作权法》框架下,为了保证专有权利的体系性,应当采用“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对侵犯定时在线传播的行为进行规制,在对《著作权法》修订时,应当设立“向公众传播权”,以保证修订前的立法、司法成本最小,修订后的遭遇相同或者相似情况的案件司法成本最小,显然从长远角度这是一种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应对方式。
三、结论
《著作权法》作为《知识产权法》一个部门法,自然和《知识产权法》一样,会受到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和挑战。由《奋斗》一案中新的传播方式——定时在线传播行为——给“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立法技术(违背了“技术中立”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水平 (未能准确把握WCT第八条的精神)带来严重挑战。而学者提出的各种模型建构,大多缺少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模型建构的成本收益。从长远角度,显然新设“向公众传播权”,是在短期内《著作权法》修订之前,采用“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规制侵犯定时在线传播的行为,从经济效益上是最有利的保护机制。
注释:
①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8)海民初字第4015号民事判决书;同样采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予以保护的相似案件是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世纪龙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案”。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穗中法民三初字第196号。
②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8)海民初字第4015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民终字第5314号 民事判决书。
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均不认为该行为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详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二中民初字第10396号。
④ 笔者在“无颂网”中输入“定时在线传播”,输出的结果共有十七个,其中有两个案件与定时在线传播行为侵权认定无关,有三个案件重复,余下的十二个案件中(包括一审、二审),全部法院全部认定为定时在线传播侵权行为侵犯《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 “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输入“非交互式传播”,输出四个案件结果,与定时在线传播侵权行为有关的只有一个,亦是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因为该类侵权行为的法律概念尚未统一,因而,笔者无法查清所有涉及“定时在线传播”的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显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定时在线传播侵权行为的法律定性中,法院倾向于适用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这一兜底条款。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
⑥详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海民初字第20573号;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西民初字第16143号。
参考文献:
[1]焦和平.论我国《著作权法》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完善:以“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侵权认定为视角[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6):143-150.
[2]王迁.著作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196.[3]刘军华.论“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行为的权利属性与侵权之法律适用[J].东方法学,2009(1):131-136.
[4]孙新强,于改之.美国版权法[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
[5]李自柱.网络实时传播行为的法律适用[J].电子知识产权,2014(10):91-97.
[6]王迁.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构[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23-28.
[7]顾威豪.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定性:由司法解释对“信息网络”的扩张看“网络传播行为”的扩张[J].中国版权,2013(6):47-50.
[8]靳学军,石必胜.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J].法学研究,2009(6):106-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