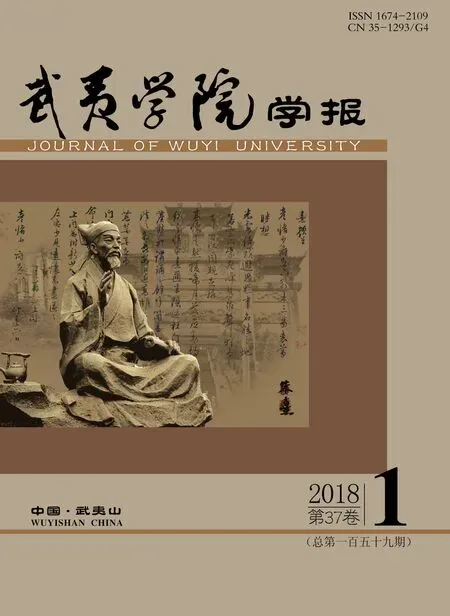古代麻沙书坊商业出版的传播路径
金雷磊
(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古代福建文化产业发达,特别是建阳麻沙,从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术发明,就出现了图书出版业。古代福建所出版书籍又被称为“麻沙本”。“麻沙本”的研究,学者要么从版本学、目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要么就从出版史的角度进行探究。而把麻沙书坊出版作为一种现象,从书籍传播的角度进行研究,考察书籍出版传播从作者、出版商、运输商到读者,这样一种循环模式的传播学研究则是少之又少。本文就是从传播学的角度,以麻沙现象作为个案,来对古代书坊出版业的传播条件进行分析,从而厘清古代麻沙文化产业兴盛的原因。
一、麻沙书坊出版业概况
古代麻沙书坊出版是福建出版业的一朵奇葩,无论是官府出版,还是私人出版,在规模和数量上都超越不了书坊出版。这主要是因为,书坊出版以盈利为主,出版商大都具有敏锐的市场眼光,能够审时度势,出版一些深受大众欢迎的书籍。比如当时就出版了很多字书、韵书、类书、农书、医书、举业书等功利性、实用性强的大众书籍,特别是帮助士子应付科举考试的举业书,更是书坊出版的一大特色。宋初科举考试进行了改革,科举取士不问出身,即使普通百姓,只要努力学习,也能做官,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这样,在麻沙书坊兴起了一个科举考试复习用书的市场。书坊“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1]。从岳珂地描述来看,当时的考试,允许携带参考资料进入考场,这就造就了举业书大规模刊刻的市场。
麻沙书坊出版业在宋代就出现了繁荣,元代持续发展,明代走向鼎盛,清代开始衰落。据地方文史专家方彦寿考证,建阳书坊在宋代有29家。[2]主要集中在麻沙和崇化两地,历史上麻沙的名声高于崇化,因此很多书商也把图书运到麻沙售卖。宋代,麻沙就出版了 《九经》《纂图附释音重言重意互注尚书》《后汉书》等经、史著作。元代沿袭宋代刻书风气,以余氏、刘氏、叶氏、郑氏、虞氏这些刻书世家为代表,主要出版一些面向中下层的书籍。“元代建阳刻书业尽管无经史大部的出现,但其刊刻的大量书籍以中下层民众为主要对象,在传播文化尤其是对庙堂文化以外的民众文化的传播上,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3]元末,麻沙书坊毁于兵火。明代建阳书肆转移到崇化,崇化还有专门进行书籍交易的墟市。麻沙书坊虽毁,但并没有消失,到了明代中叶,出版业又有所恢复。“不过,麻沙书坊的复兴程度十分有限,刘氏是建阳刻书世家,但明代的刘氏书肆多集中在崇化而不在麻沙,张、蔡二氏刻书在建阳坊刻业也没什么地位,因此,麻沙书坊的‘浸盛’只是相对元末明初的凋敝而言,它根本没有恢复到昔日的繁盛,更难以望崇化书坊之项背。”[3]可见,到了明代,麻沙和崇化共同构成了建阳书坊出版业的新型格局,建阳出版业出现了鼎盛的局面。清代,麻沙一带仍有出版活动,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有诗云:“得观云谷山头水,恣读麻沙坊里书。”查慎行《敬业堂集》中有《建阳棹歌》云:“西江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回。”不过,此时规模已十分有限。清代王士祯在《居易录》中说:“今则金陵、苏杭书坊刻版流行,建本已不复过岭。”表明当时全国出版中心已转移到南京、苏州、杭州一带。
古代麻沙书坊出版以余氏最为有名,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且当时官刻书亦多由其刊印。”[4]南宋时期,以余仁仲的万卷堂最为著名。此外,还有余唐卿的明经堂,余彦国的励贤堂等。元代的余氏刻书坊有勤有堂、勤德堂、双桂堂等,其中又以余志安的勤有堂出版书籍最多、影响最大。元末明初,余氏开始衰落。“建安余氏书业,衰于元末明初,继之者叶日增广勤堂,自元至明,刻书最多,亦有得余版而改易其姓名堂记者。”[4]但这种衰落只是暂时的,到了明代中后期,余氏书坊开始复兴,不到几年,又出现了兴盛局面。
二、古代麻沙书坊商业出版的传播路径考述
麻沙书坊出版的图书,主要通过水路、陆路和海路进行运输。 在水路方面,以闽江、晋江、九龙江等河流为主,福建山区和沿海起伏很大,西部武夷山海拔1000米至2000米之间,发源于武夷山脉的河流从山上直接俯冲而下,很快就可以到达沿海平原地区,这些河流水势湍急,从上游到下游顺流而下,可以加快船行速度。但是,从下游到上游则是逆流而上,当时水船全靠纤夫人力拉动,不可运送重物。从武夷山脉下来有一条建溪,也是险要丛生。罗隐在《送沈光侍御赴职闽中》一诗中云:“末至应居右,全家出帝乡。礼优逢苑雪,官重带台霜。夜浦吴潮吼,春滩建水狂。延平有风雨,从此是腾骧。”[5]这里的建水就是建溪,建溪源自武夷上,经建阳,至建瓯北,与东溪会,南至南平。说明了建溪的水势。韩偓有首诗歌名字叫《建溪》,写道:“长贪山水羡渔樵,自笑扬鞭赶早朝,今日建溪惊恐后,李将军画也须烧”,他在这首诗的序中提到:“建溪滩波,心目惊眩,余平生溺奇境,今则畏怯不暇。”[6]可见建溪的险要。因此,福建山区的木材、矿产、粮食、茶叶等物运到沿海,而沿海的食盐、海产品则可以运送到山区,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建山区和沿海的贸易两者可以相互交换,刚好形成互补,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福州又是闽江的下游沿海城市,在福州城内,水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船只来来往往非常方便,从闽江上游驶来的船只都要到达福州,然后运到东南沿海。所以,福州也是沟通山区和沿海城市的中转站。正是这种交通枢纽地位,使得福州当时的贸易兴盛,商业繁荣。福建要与外界取得联系,主要是翻阅西北部的大山,然后出省,从外省进入福建也是一样,要经过西北部山区才能到达。
从陆路入闽,崇山峻岭、怪石嶙峋,山路崎岖难行,地势异常险要,“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7]因此,常常有人叫苦不迭。而且西北山区人烟稀少,使得游人投宿也显得艰难,“古木闽州道,驱羸落照间。投村碍野水,问店隔荒山。身事几时了,蓬飘何日闲。看花滞南国,乡月十湾环。”[7]
在陆路方面,江南入闽主要是经过分水关和仙霞岭二条通路。第一条路线是经过分水关,分水关又名大关,是崇安县八关之一。《辞海·历史地理·历史地名》注释:(1)“分水关,又名大关,在福建崇安西北分水岭上,接江西铅山县界。当闽、赣交通的冲要,自古有‘入闽第一关’之称。五代在此置寨,宋开庆间并置大安驿。元废。明洪武初复置关,设巡司戍守。(2)“在广东饶平东南接福建诏安县界。明代在此筑石城,设巡司戍守。”
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应江西籍同乡陆九渊之邀,他不辞闽山赣水之途的艰辛,亲赴铅山参加由吕祖谦发起的“鹅湖之会”,与主张主观唯心主义的陆九渊学派进行辩论,哲学上称“鹅湖之辩”。朱熹参加鹅湖学术辩论凯旋后,途经分水关,多日论战,身心疲惫,但决胜之快意未尽,他驻足突踞于闽赣两省的漫道雄关,观察两陂分水,咫尺天底下,看云卷云舒,听涧水交响,他获得了心悟。立即口占《题分水关》一诗:“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
分水关位于建阳县温岭场境内,这里是武夷山脉最狭窄的地方,中间几十里山路,两头都是河谷。崇阳溪两岸有宽一里以上的河谷走廊,从崇安场一直延伸到建州城,长达200多里。在福建,这样平坦的走廊极为罕见。崇安至江西铅山县界,路程80里,只有从分水关到车盘一段长10里比较崎岖,西向铅山,一路平芜,成为闽赣孔道。分水关既是古代福建防御外敌入侵的军事关隘,又是闽赣两地重要的交通驿站。中原文化通过这个孔道进入闽地,使闽北成为福建最早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明代王世懋有这样的描述:“凡福之丝绸,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泉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北宋元祐进士、浙江瑞安人许景衡《分水关》诗云:“再岁闽中多险阻,却寻归路思悠哉。三江九岭都行尽,平水松山入望来。”有了关卡,便有了异乡之感,平生了思乡之情。南宋绍兴进士、莆田人黄公度《分水岭》诗曰:“呜咽泉流万仞峰,断肠从此各西东。谁知不作多时别,依旧相逢沧海中。”
分水关,曾被古建筑学家、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罗哲文著的《中国名关》一书列为中国名关之一,分水关古道的起始点,雄踞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桥墩镇与福建省福鼎市贯岭镇交界处的分水岭上。据明万历《福宁州志》记载:“分水岭,与温州平阳交界;叠石关,在十八都,与分水关皆闽王立,以防吴越入侵”,分水关始建于五代时期,后梁开平四年(911)王审知为闽王,为防御吴越国的入侵,让闽中百姓更好地休养生息,在分水岭上建造关隘防墙,关以地名,称“分水关”。北宋统一全国之后,分水关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驿道。
第二条经过仙霞岭,仙霞岭在浦城西北,是福建通往北方最近的一条通道。最初没有商业贸易通道,此路为黄巢进入福建时开凿。“刊山开道七百里,直趋建州。”[8]通道全部在建州境内,而北方移民要进入福建,必然要进入建州境内。因此,唐代建州移民最多,发展也最快,这对当时的建州来说十分有利。宋代陆游《宿仙霞岭下》诗云:“吾生真是一枯蓬,行遍人间路未穷。暂听朝鸡双阙下,又骑羸马万山中。重裘不敌晨霜刀,老木争号夜谷风。切勿重寻散关梦,朱颜尽改壮图空。”
仙霞关位于浙江衢州江山市保安乡南仙霞岭上,地处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为古代衢州往来建州之咽喉要地,仙霞古道又称为江浦驿道,是闽浙官路。素有“两浙之锁钥,入闽之咽喉”之称,是汉、唐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又是海上丝绸之路一条重要的陆上运输线。仙霞古道也是一条古诗词之路,张九龄、白居易、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等历代文人墨客,留下诗文达300余篇。
明代王世懋《闽部疏》认为,闽之货物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仙霞古道),下吴越如流水。《福建省志》记载,汉、唐建都长安,福建各地都以杉关为晋京官道;宋、元移都临安和北京,遂又改以崇安的分水关或浦城的仙霞岭路为晋京大路。可见,分水关和仙霞岭是但是陆上两条主要传播通道。
福建靠海,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山海经》所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9]在海路方面,从福州出发,主要有向北和向南两个方向。向南约200里就可以到达泉州,泉州继续往南,可达广州。这可以说明当时闽粤之间的商业贸易应该是很频繁的。向北则可以通往江南、渤海等地。当时,福建要向中原进贡,也是经常走海路。“审知岁遣使泛海,自登、莱朝贡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10]而且当时福建对外贸易发达,很多海外进口的商品就是通过这条航线把它们运到中原。北方航线是福建商业贸易发展的一条重要航线。北方航线最远航行到渤海一带的契丹国和渤海国。
宋代,福州和泉州成为了重要的航运港口,这两个港口在福建占有重要一席,对外贸易繁忙。泉州在宋代的繁华可用“涨海声中万国商”来形容,到南宋末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港。福州海外贸易也是兴盛,宋代鲍抵的“海舶千艘浪,潮田万倾秋”反映了福州海外贸易繁忙的情景。宋代福建与海外外贸往来的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赵彦卫《云麓漫钞》称,福建市舶司常到的诸国船舶如:大食、嘉令、麻辣、新条、甘杠、三佛齐国、真腊、三泊、缘洋、登流眉、西棚、罗解、蒲甘国、渤泥国、阁婆国、占城、目丽、木力千、宾达侬、胡麻巴洞、新洲国、佛罗安、明丰、达罗帝、达磨国、波斯兰、麻逸、三屿、蒲里唤、白蒲迩国等。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所记的与泉州港有关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而且,对外贸易的结算方式也出现了钱货交易。宋代以前没有国际通货,所以钱货交易始于宋元。开始时也是以铜钱或金银为支付手段。如《诸蕃志》载,与楼国“交易用铜钱,以乾元大宝为文”[11]。这主要是因为宋代出现了被称为交子的纸币。从行为方式上看,私人贸易规模大,人数多。“宋代来往于福建与日本间的福建商人见于记载的就有周世昌、陈文佑、周文裔、潘怀清、李充等等,他们都是属于民间商人贸易性质,并非由国家组织的。”[12]而这些私人贸易在某些方面较为正规,如据日《朝野群载》辑载,李充到日本从事贸易时,曾呈上要求贸易的公凭。[12]
宋代时期,福建海外交通通畅、海外贸易繁荣,主要原因有地理位置的优越、造船技术的发达、官方的重视和对海外海外贸易的管理、丰厚的利润和精于海外贸易的商人等原因。在宋代时候,福建形成了专门精于海外贸易的海商,并且达到了一个高潮。宋代如精通藩汉文字的王元愚,在占城居住十年后归泉州成为大海商;往来海中十数年的北宋晋江人林昭庆也成为著名海商。苏东坡在《论高丽进奉状》所言:“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从事商业被认为是下等的、不入流的工作,而在福建闽南地区刚好相反,经商赚钱反而一件比较光荣的事业。《泉南芦川刘氏族谱》载其二十三世:元壕“为人性宽洪,有大志,少时吕宋经商,利市荣归”[13]。世宙“少时立志经营,往夷邦经商,得大利荣归”[13]。建阳出版的书籍就是通过福州港和泉州港传播到海外,客观上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
三、古代麻沙书坊商业出版的价值概述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民间书坊的功能也逐渐完善,具备了将编辑成书和刻印出版联系起来,并从事图书流通业务的条件。”[14]郑鹤声、郑鹤春在《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中认为,“版本之类有五,而书肆坊为其中坚”,“坊肆本者,诸书坊书肆所刻木也。书籍之流播,全赖有坊肆之雕刻。”[15]麻沙书坊对当时社会文化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其出版价值不容忽视。
首先,普及了大众文化。相对官刻和家刻而言,麻沙坊刻书籍在内容上,以出版科考用书、字书、历书、韵书等通俗读物为主;在形式上,通过改变行款字体,采用上图下文和封面以及正文与注疏合刻等方式不断创新。这些内容和形式上的创举,都更加贴近大众生活,能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随着印本时代的到来,下层民众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书籍,也有机会阅读书籍,对下层民众知识文化地普及和提高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坊刻书籍极大地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更多普通大众参与到文化的创作与交流之中。
其次,保存了古代典籍。印刷术发明之前,图书主要依靠手抄传播,这种方式费力、耗时,重要的是,图书生产与流通的数量有限,提供的复本也是少之又少。雕版印刷发明之后,以书坊为代表的民间出版传播机构,能够及时地、大量地生产图书,图书数量大为可观。随着复本的增多,也为古籍的长期流传提供了机会。坊刻图书和官刻、家刻图书一样,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众多的坊刻图书,通过文字把古代的事件、人物、信息记载和传播下来,使得我们今天分析、研究历史有据可依。可以说,书坊在古代文献的出版和传播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促进了中外交流。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往来频繁,图书一般通过交换或购买的方式传播到海外。赵汝适在《诸蕃志》中就有泉州赴高丽的海船用建本换高丽药材和人参的记载。《二程全书》《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文字正宗》等理学书籍的传播也远至朝鲜。一些书籍如《杜工部草堂诗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传播到朝鲜后,还经常被翻刻。麻沙书坊出版的图书出口到外国,影响了他国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为外国古代图书的跨文化传播和保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了光彩夺目的历史印记。
综上所述,麻沙书坊商业出版作为古代出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同于其他地方出版的特色。麻沙书商对书籍的编辑、校对、刊刻、印刷、装订和发行等环节,也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特色和方法,无论是对建阳出版还是对福建出版,乃至对全国出版事业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麻沙书坊的异军突起,是出版界中的一匹黑马,改变了图书出版格局,形成了出版业中的“麻沙现象”。“麻沙本”作为书籍版本学中独具风格的一种版本,流传和沿用至今,成为当时以及后世学人研究版本学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参考文献:
[1]岳珂.场屋编类之书[M]//愧郯录(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13.
[2]方彦寿.建阳刻书史[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91.
[3]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211,234.
[4]叶德辉.宋建安余氏刻书[M]//书林清话(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57:46-47.
[5]曹寅.送沈光侍御赴职闽中[M]//全唐诗(卷六百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7568.
[6]韩偓.玉山樵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25.
[7]王象之.福州[M]//舆地纪胜(卷一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92:3676,3752.
[8]宋祁.黄巢传[M]//新唐书(卷二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6454.
[9]山海经校注[M].袁珂,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67.[10]欧阳修.闽世家[M]//新五代史(卷六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846.
[11]赵汝适.诸蕃志校释[M].杨博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155.
[12]胡沧泽.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4):102,101.
[13]庄为矶,郑山玉.泉州谱碟华侨史料与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1006,1007.
[14]于翠玲.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38.
[15]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6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