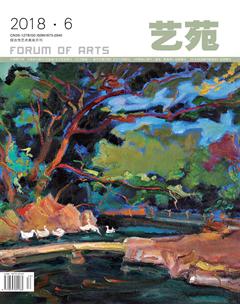《相爱相亲》:凝视·在场·死亡
蒋兰心
【摘要】 《相爱相亲》作为著名女性导演张艾嘉的电影作品,既体现着导演通过女性视点赋予女性“看”之权力的性别企图,同时又渗透出由“摄影机”“照片”等视觉符号建构出来的男性“在场感”。在这样的二律悖反中,不难发现充斥全片的“死亡符号”,乃是张艾嘉以特有的女性智慧尝试冲破父权为女性营造的“相爱相亲”幻象的终极手段,也彰显了其在“主流艺术电影”旗帜下独树一帜的女性主义突围策略。
【关键词】 《相爱相亲》;张艾嘉;女性凝视;男性在场;死亡符号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谈及导演张艾嘉,我们无法回避的关键词是“性别”。一方面,鲜明的女性气质使张艾嘉在当今影坛占据一席之地,从《少女小渔》到《20 30 40》再到近年大热的《念念》,导演均以女性人物为主角,始终保持着对女性情感与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张艾嘉深谙商业电影制作之道,她让女性电影以“主流艺术电影”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影片中流淌的女性意识柔软而温吞。电影《相爱相亲》是张艾嘉首次执导的内地题材电影,这个由“迁坟”引发的故事,让“死亡”成为结构起整部影片的视觉语法:抑或是反复出现的墓冢,外婆的骨灰,姥姥的棺材,外公的遗像;抑或是学生家长在灵堂前表演的哭丧,摇滚歌手阿达躺进棺材之时留下的眼泪;甚至是无处不在的猩红色,乡村逼仄昏暗的老屋,摧毁而又重建的城市等等。這些秘而不宣的“死亡”符号,正是张艾嘉以女性独有的智慧,在父权意识形态框架之中悄然留下的异样印记。
一、女性凝视:主体的指认
帕特里克·富瑞在《凝视:观影者的受虐狂、认同与幻象》一文中解释了“凝视”这一概念:“既是看的行为,也是被看的行为;既是知觉,也是解释;既是眼前呈现的事物,也是事实在光学的物理世界和人的主观世界中的呈现与消逝。”[1]77可见,“凝视”是一种“主体-客体”的观看结构。当我们把“凝视”同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相结合时,“凝视”这一概念便具有了性别意味。正如劳拉·穆尔维所指出的,“男人在看,女人在被看”背后,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权意识形态。因此,赋予女性“看”的权力——即女性视点,成为女性表达的有效途径。电影《相爱相亲》便是由女性展开叙事、控制叙事、推动叙事的典型。张艾嘉以薇薇外婆死前的幻觉开场,姥姥、薇薇母亲与薇薇三代女人的情感生活也就此拉开序幕。薇薇母亲岳慧芳“自作主张”让薇薇外婆与外公合葬,决心要将外公的坟墓从老家迁出。一辈子没等到丈夫只等到枯坟的“大房”姥姥死守着坟墓不放,与岳慧芳针尖对麦芒。薇薇出于对强势母亲的反抗,对老家姥姥的好奇,甚至为了自己所在节目的收视率,在两人中间游移。三个女人虽各自为阵,但导演都赋予她们合理的动机:姥姥的固执源自对丈夫的坚守与深爱,岳慧芳的蛮横是人到中年的恐惧与对自我身份的怀疑,薇薇的冲动行事则是年轻的困惑与成长路上的崎岖。三个女人的种种纠葛最终落脚在爱情与爱情之外的大爱之上,其动机也因此更趋崇高。与此同时,三个女人的“看”在视听语言层面也体现着些许变化:姥姥多是出现昏暗的内景之中,逼仄的农家小屋宛若她被婚约围困住的一生,也暗指衰老死亡的结局;岳慧芳是永远的行动派,自然光俯以宽阔的场景,符合她忙碌又焦虑的个性;薇薇时常出现在酒吧、出租屋等冷暖色调对比鲜明的场所,地下、边缘的场景则是在彰显年轻一代的叛逆与对自由的追寻。在导演的镜头中,三代女人是丰满的、行动力极强的、有能动性的。所以,当三代女人拥有了“看”的能力,与之对应的三代男人便成为了她们眼中的男人:“特别自私”但值得等待的外公、“温吞软弱”但有礼有节的丈夫、“不负责任”但魅力十足的男友。正是这些女人眼中的男人让我们感受到女性主体发出的另一种“凝视”,即便着墨不多也弥足珍贵。
另外,相较于宁瀛等女性主义导演极端反叛的电影编码,张艾嘉镜头下的女性世界更为温柔和煦。影片中反复运用“红色”作为女性情感的载体:悲伤、嫉妒、释怀等情绪都脉脉流淌在女性的凝视之中。薇薇外婆离世当晚,岳慧英在深更半夜做了一瓶又一瓶辣椒酱,厨房里的辣椒、红厨具与客厅里外婆骨灰盒下面的红布遥相辉映,人到中年的岳慧英以含蓄隐忍的方式表达着丧母之痛。其次,薇薇与岳慧英的生活中都有“情敌”介入——谭维维饰演的摇滚歌手朱音与刘若英饰演的王太太。朱音作为阿达的红颜知己,潇洒又勇敢,在薇薇目光的追随之下,她依旧无所顾忌的和阿达唱着“我们的”歌,让儿子叫“阿达爸爸”。女性间微妙的角力,映衬在朱音的一袭红衣之上。岳慧英的丈夫尹效平是驾校教练,王太太既是邻居也是学员。岳慧英数次目睹丈夫在小区里温柔又耐心的“手把手”教王太太开车,不难想象,王太太那辆红色轿车在岳慧英看来是何等扎眼。影片结尾,岳慧英坐上了丈夫的新车,哭泣中,她喊道:“这辆车不许载王太太。”女人的嫉妒与恐惧在此刻一览无余。最后,关于性与身体的部分,张艾嘉自然不会以简单的“裸露”放任女性重回男性的“凝视”之中,导演只采用了一场隐晦的“春梦”表现岳慧英心中的渴求。高塔之上的她孤立无援,面目模糊的男子向她伸出手,光亮透过高耸的烟囱,她在下坠,不断下坠。在轻微的呻吟声中岳慧英睁开眼,看到了学生家长卢明伟。直到岳慧英在老家看到那座高塔,才忆起梦里的人是年轻时的尹效平,这时,岳慧英对身旁的卢明伟说:“晓光最近很乖,你不用再来学校了。”女性对爱的渴求以及婚姻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诱惑,就这样被导演揉进了一场微不可查的春梦之中。
二、男性在场:话语的纠缠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指出了“看”的三种方式:“摄影机在记录具有电影性的事件的看,观众在观看最后的产品时的看,以及人物在银幕幻觉内互相之间的看。”[1]17具体到张艾嘉自导自演的《相爱相亲》,它的性别观看机制更为复杂:电影内部,是张艾嘉饰演的岳慧芳在“看”周遭的男人们与女人们;电影外部,是导演张艾嘉(摄影机)在看岳慧芳,当然也看到了她被“求真”节目逼得狼狈失态。张艾嘉作为具有女性意识的电影作者,她的摄影机不再是纯粹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机器,影片中的女性视角让导演的摄影机具有了性别自觉,以代替女人们去“看”。然而银幕之内,张艾嘉饰演的岳慧英始终处于一种抽象的男权的凝视之下,男权“凝视”的隐喻,依旧来自摄像机。女儿薇薇出于职业习惯用摄影机记录下了整个“迁坟”事件,随之而来的便是电视台的介入,记者主持人们带着长枪短炮围追堵截,祖孙三代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公众视野中。质朴善良的姥姥在镜头里是个揪着女主持耳朵、死守着孤坟的怪老太;兢兢业业的教师岳慧芳在公众视野中是个霸道又不通情理的“二房”女儿;无意间捅出家务事的薇薇,一边要追寻节目所谓的“真相”,一边极尽全力不想让家人受到伤害。正如薇薇男友阿达所言,节目并不在意姥姥究竟想说的是什么,只在意姥姥是不是说了观众们想听的。在“摄像机”的控制之下,所有女人都要接受审判:在村庄里精干的姥姥在镜头前瑟缩成一团,眼里带泪讲着自己的过往,在导播安排的“戏剧性”中被迫迎合观众的期待。岳慧芳克服重重阻力拿到父亲母亲的合法婚姻证明后,被办事人员挖苦,“你可以去告大房了,我在电视里都看到了”;本是为人师表,却在校门口被摄影机、记者围困到无路可退。“摄影机”下的“求真”节目无疑象征男权的“凝视”,它规范了女人们要守贞,要大度,要符合传统礼法,要对没有回音的爱情至死不渝。现代社会中的男权的“凝视”又为女性修建起一座座不可查又不可破的“贞节牌坊”。
若说摄像机下的“求真”节目代表公众领域的男权凝视,那么家庭内部的男性在场则是通过“照片”传达出来。岳慧英家中数次出现离世外公满墙的遗像,在大屏幕的三维空间中大量使用二维平面照片(运动的时间——静止的空间,运动的影像——静止的照片),不难让观众感受到男性与女性之间透露出的奇妙张力。即便是没有丈夫相片的姥姥,也采用传统“女书”绣起外公的名字当做遗像供奉起来,以营造男性的“在场感”。当然,照片不仅是离世“外公”存在的符号,也是三代女人实现和解的契机。“求真”节目之后,姥姥去往岳慧英家中,想看一看“外婆”。在满墙的遗像里,姥姥踮着脚努力辨认自己的“爱人”。她喃喃道:“这是他吗?不像啊……”照片里陌生的男人不是记忆中的爱人;乡村老屋中墙上的女书与岳慧家中的遗像无法重合;她终于亲眼目睹了那个多给她五块钱做棉袄的男人与旁人相伴一生。姥姥维持了一生的幻想终于在此刻崩塌,她开始明白,能够证明她妻子身份的不是家信,不是族谱,不是枯坟;她坚守一生的“妻子”身份只是对女性身份的执念罢了。最后,薇薇与阿达两个年轻人察觉到这一墙照片击垮了姥姥守护一生的堡垒,他们合成姥姥与外公的“合影”,希望给姥姥一个安慰。但在一场滂沱大雨中,照片浸湿,姥姥顫颤巍巍的拿出照片,想用毛巾擦干,可外公的脸越擦越花。在影片逐渐走向尾声之时,老人第一次痛哭失声,最后一分虚假的守候也留不住,老人像孩童一般无助。于是,在迁坟之时,姥姥即便饱含深情地看着那一筐白骨,也释然地说出“我不要你了”。终其一生的守候,最终结束于一张人工合成的照片,个中是导演布下的悲悯与温情、辛酸与怅然。
三、死亡符号:女性的逃逸
女性导演的女性视点赋予了女性“看”的权力;“摄影机”与“照片”则给予男性凝视“缺席的在场”感。《相爱相亲》似乎仍处于女性电影常见的二律悖反之中,但我们仍能察觉到一丝“异样”——死亡符号挥之不去,充斥于整部影片。英国理论家休·索海姆曾将“激情的疏离”视作女性主义电影的核心概念[2]1,这一概念同样出自劳拉·穆尔维:“对传统电影成规的日积月累的第一个打击(激进的电影制作者已经在做了)就是让摄影机的看在时间和空间上获得物质性的自由,并解放观众的看,使他们成为辩证的和超脱的感情。”[1]17我们知道,由于电影指向的是一种理想的观看主体,若想实现“激情的疏离”,则必须使观看主体产生间离的自我意识,并对“看”的行为产生自觉。于是,张艾嘉的自导自演在性别层面上更值得玩味,即打破凝视的幻觉,也就是齐泽克所说的“看见自己在看”[3]190。与之相仿,影片中无处不在的死亡符号也实现了这种“间离”功能。观众无法全身心投入于“相爱”的纠葛与“相亲”的争执之中——总有无数符号在提醒观众,死亡的终极在场。主持人与记者反复询问姥姥,一生守一座坟到底“值不值”,男权意识形态被加上了价值判断,观众看到了归顺男性社会等到的不过是一座枯坟,给予女性莫大伤害的男性到最后也会化作小小一盒白骨。学生家长卢明伟曾是一名话剧演员,现在以表演“哭丧”谋生,他以极尽夸张姿态喊着别人的“娘亲”,葬礼主角——无私付出的贤妻良母,到头来得到的不过是陌生人渲染气氛的恸哭一场。卢明伟生硬的“表演”证明了男权规训的荒诞,以及世间万物逃不掉的仍只有死亡。岳慧英执拗地要将父母合葬,因为她眼中父母“相爱相亲”了一辈子,母亲必须要有一个“名分”。可影片开头岳慧英母亲跟随父亲灵魂而去的那段光影分明在表达,爱情是一种超越现世的存在,绝不仅仅是男权意识形态中的以“洁振纲常”厮守一生。“名分”以死亡为终点,但爱情远不止于死亡。于是,观众开始明白,所有家长里短的背后都是死亡的终极在场,在死亡面前,“真正”的爱情该是什么模样?男权规训下的“相爱相亲”本身是否就是一场幻象?
当然,《相爱相亲》讨论的不仅是性别问题,更是终极命题。若把“爱”视为影片温暖人心的底色,那挥之不去的“死”则是将影片升华到“爱”以上,把“相爱”的终极归宿直指向“死亡”。“生”与“死”“爱”与“死”的碰撞,构成了影片巨大的张力——观众见证三代人爱情的同时,也看到了三代人的死亡观:姥姥身体佝偻、满脸皱纹、行动迟缓,黑暗的小屋以及黑屋中摆放的棺材,好似将她妆点成了“活死人”。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正是这次“迁坟”事件,让姥姥重新有了些“生”的气息:她会拄着拐追打记者,给办事人员递糖寻求帮助,在薇薇脱衣服的时候恼羞成怒地嗔怪薇薇“流氓”。当她重新回到外公的枯坟前,点燃鞭炮送外公“进城”之时,她似乎真正料理好了自己的“身后事”,“死亡”的倒计时,也是姥姥“爱”与“生”的进行时。岳慧英似乎在迁坟事件之后学会了正视死亡。影片开头,岳慧英整理母亲遗骸之时,她还不敢上前拾起母亲的头骨;影片结尾,她熟稔地捧起母亲的骨灰盒,举重若轻准备起合葬。“人都要走那一步”反而给人到中年的岳慧英一些面对现世的力量,退休生活所带来的空虚与焦虑在死亡面前似乎不值一提。充满青春气息的年轻人阿达,在与姥姥的相处中受到了“爱的教育”,他主动要求躺进姥姥的棺材,与其合影。在棺材里的他,啜泣了几声,“好像也没那么可怕”,脸上随即又浮现起一缕笑容。年轻人触碰衰老、死亡等终极命题之时,以稚嫩的勇气让沉重悲苦暂得消解,对死亡的敬畏也融进了对生命的热爱之中。
结 语
毫无疑问,《相爱相亲》中的女性视点让观众真切体会到女性一生之中的爱与乐、苦与悲,其中透露出的女性意识弥足珍贵。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对男性的“等待”以及女性自身的身份困惑,让《相爱相亲》在本质上依旧拘泥和裹挟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然而,贯穿于全片的“死亡符号”则是女性导演在男权意识形态中温吞的生存智慧,那些秘而不宣的死亡符号试图告诉观众,真正的爱情可以超越死亡,生而为人逃不过死亡,在爱情之上的终极命题仍是死亡。如若抱有几分“同情之理解”,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死亡”是张艾嘉试图冲破父权秩序为女性营造的“相爱相亲”幻象的最后方式。
参考文献:
[1]吴琼编.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英)休·索海姆.激情的疏离: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M].艾晓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M].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