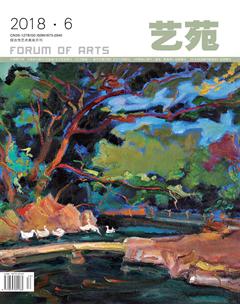《遗传厄运》:密闭空间营造的家庭伦理恐惧
任雨田
【摘要】 作为在2018年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观众与业内人士口碑双赢的恐怖片,《遗传厄运》将恐怖故事建置于密闭空间之中。影片在对传统美国恐怖片进行类型继承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叙事策略的突破,通过故事空间的嵌套与话语空间的转向,进行家庭伦理恐惧的宿命化書写;在对家庭关系和人性本身的双重审视下,突显对人类精神异化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对主流恐怖片的类型范式有所创新。
【关键词】 《遗传厄运》;恐怖片;空间;家庭伦理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北美著名独立制片公司A24成功打造了多部奥斯卡颁奖季热门影片,如《佛罗里达乐园》《伯德小姐》《月光男孩》等等,俨然已成为美国独立制片圈中低成本、高品质的代名词。2018年初,由A24公司发行的恐怖片《遗传厄运》在美国圣丹斯国际电影节展映上获得了良好的观众口碑与业内人士高度评价。美国青年导演阿里·艾斯特通过这部处女作,向人们讲述了密闭空间中发生的家庭厄运遗传事件。影片中家庭伦理、宿命论、宗教隐喻与女性主义的叙事杂糅突破了传统美国恐怖片的叙事类型,亲近血缘间的疏离化叠加成为家庭悲剧命运的现实主义注解,将传统的表层血腥与暴力书写转化为深层的精神恐惧,这些都使其在同类型题材影片中脱颖而出,并拥有直指人心的力量。
一、对传统美国恐怖片类型的继承与突破
美国恐怖片的类型化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恐怖片受德国表现主义影响,吸收小说、戏剧与民间故事中的鬼怪传说,分化为以《吸血鬼德古拉》等片为代表的怪物类型和以《化身博士》等片为代表的怪人类型。前者以吸血鬼、狼人、幽灵、僵尸为主,后者以人格分裂、人性扭曲为主。这一阶段的核心冲突是“人类”与“异类”的显性二元对立,以人类消灭异己的正态结局为多。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恐怖片的类型化取得了重大突破,国内政治动荡与冷战激化使创作者们将目光由传说中的鬼怪志异转向体现个人化风格的现实生活题材。[1]87-91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成为“变态连环杀人狂”主题恐怖片的开端,随之涌现的《沉默的羔羊》《德州电锯杀人狂》《十二宫杀手》《电锯惊魂》系列揭示了自由主义泛滥与后现代思潮裹挟下美国社会面临的犯罪率上升、性暴力、道德沦丧、信仰危机等社会问题。早期的鬼怪形象在70年代后进一步深化为人类自身的妖魔化,即“魔鬼附身”。《驱魔人》《招魂》与《小岛惊魂》等影片中父母、孩童等家庭亲密关系的维系者被魔鬼附身后成为暴力行为的实施者,披着被动化不可抗力外衣的“魔鬼”作恶,将家庭伦理的守望者化身摧毁温暖港湾的邪恶力量,营造出反传统道德、解构伦理秩序的心理式恐惧。
罗伯特·所罗门指出,“艺术恐怖”依赖于对“现实恐怖”的戏说和模仿。[2]有时“艺术恐怖”并非建立在确有其事的真实客体上,但却源于对真实恐惧的思想认知,比如丧尸、哥斯拉、异形等。虚构的艺术形象来源于现代人对超自然力量未知性、科技失控性、信仰失效性、人类自身动物性、死亡与命运无可避免性的心灵危机和经验模仿。“艺术恐怖”与“真实恐怖”并非简单二元对立关系,尽管“艺术恐怖”有时建立在虚假前提上,但却无法割裂恐怖电影表现手法与人们对自我、他人及社会“真实恐怖”的能动反映。对两者关系复杂性更为全面的把握,与恐怖类型电影日益丰富的内涵相吻合。
《遗传厄运》在叙事结构和人物设置上对经典影片《罗斯玛丽的婴儿》《驱魔人》和《闪灵》进行了互文和戏仿。该片延续了现代美国恐怖片的因果式五幕线性结构:发现异常或神秘事件——调查原因——发现真相——展开斗争以暂缓危机——开放式循环结局。影片开始于祖母艾伦的葬礼,孙女查理在祖母去世后开始做出一些奇怪举动,母亲安妮也时常出现幻觉。由于孙子皮特的疏忽,查理被一场车祸夺去生命。安妮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又目睹了丈夫的身亡,平静的家庭生活分崩离析,遗传的厄运成为难以摆脱的黑暗宿命。《驱魔人》的故事同样发生在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母亲偶然发现女儿的怪异行为,请来神父对女儿进行驱魔,最终女儿恢复正常并和母亲在新的城市开启了新生活,但恶魔仍潜伏人间。开放式的循环结局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传达出对寓言式“死亡定律”不可知性的恐慌。《罗斯玛丽的婴儿》中罗丝玛丽的儿子成为撒旦之子的宿主,最终将家人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遗传厄运》中恶魔寻找人类宿主却不是通过随机选择,而是利用女性子宫完成恶灵孕育,使诅咒与家庭血脉紧密相连。外婆艾伦、母亲安妮和女儿查理都成为了地狱八大王之一派蒙王的宿主,与基督教传统的女性原罪形象呼应。影片将不洁的女性身体“斩首”以净化堕落,最终献祭了孙子皮特,隐喻了基督教中的亚伯拉罕杀子,异端仪式的献祭将信仰刻入家庭血脉。
在人物设置上,装置艺术家安妮与《闪灵》中的作家杰克同样是沉浸于自我世界的文艺工作者。杰克由于剧本写作的困难,陷入事业和家庭的两难困境,来到与世隔绝的悬崖饭店,希望完成工作并重拾家庭情感,却最终差点亲手杀死妻子和孩子。人格分裂的父亲被置换为母亲的角色,安妮在母亲死后难以排解抑郁,只能求助于好友而最终误入歧途;她将女儿的死亡现场和母亲的葬礼融入创作,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边界,最终陷入非理性的疯狂。杰克和安妮的故事同样都是发生在密闭空间的一场孤独直播,亲近之人都无法救赎的冷漠与隔离在现代社会物质高度丰富的同时剥夺和扭曲着人类的精神本能。
与大多数恐怖片的结局不同,对邪恶力量的信仰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精神安慰,科学与理性的反抗最终被超现实力量收编,恶魔不再是“类人”或“附体”而与人类本身合体,完成了从视觉恐怖到心理惊悚的过渡。没有大量血腥暴力的视觉冲击,也没有鬼怪形象的直接呈现,模糊心理与超自然界限的描写挖掘出人类自身的危机与心灵深处的恐惧。令人惧怕的从不是赤裸裸的暴力,世界最大的善意和恶意都源自人类本身,问题是人类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法明辨的彼此。
二、密闭空间营造的恐怖氛围
根据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的定义,“空间”作为社会产品,并不是一种固化的静态结构,而是一种与冲突和矛盾产生联系的动态进程。[3]133-136查特曼进一步区分了“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以此阐明故事发生的环境与叙述者的讲述空间,乃至创作者的创作环境。[4]《遗传厄运》在线性的情节发展之下利用“空间”进行了叙事转换与重构,从故事和话语两个维度建构的密闭空间,指向人物特殊的心理反应,同时密闭性的强行打破加强了剧情冲突,有效牵引着观众的紧张情绪。
首先是故事空间的层层嵌套。影片开头对房屋内的家具陈设和环境色调进行了特写,接着镜头拉远,全景显示刚才被特写的房屋只是母亲安妮制作的玩具模型。在正片中数次出现树林掩映中的房屋空镜,“真实木屋”与“玩具模型”形成了对照。“玩偶之家”隐喻着自由意志似乎暗中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所操控。“家”“车内”“教室”等闭合空间与“教堂”“聚会”“校园”等开放空间相互嵌套,并引申出两重矛盾话语:日常与颠覆、真实与虚构。“家”在传统观念中是心灵和身体的栖息地,安妮无法将女儿之死归罪于儿子,到教堂的“失去亲人互助小组”寻找信仰的救赎,原本家人之间敞开心扉的空间形成了闭合,而陌生人却成为愤懑情感的出口;私家车内是逃离聚会嘈杂的私密空间,查理将头探出窗外而惨遇车祸,这个影片中最血腥的镜头成为情节转折点,揭示安全空间下潜藏的不可预知性危险;教室是学生生活中半开放的封闭空间,变焦镜头用于拍摄墙面和窗户上的异常显影,幻觉将沉浸之中的皮特和周围的环境割裂。透过窗户的固定窥探镜头表现出空间的嵌套与叠加,从封闭的私密空间到半封闭的公共空间,不安的情绪渲染逐层深化,从点缀生活的潜伏因素到完全搅乱生活的深度渗透,最终指向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异化”: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成为异己力量,社会人际与亲子关系,甚至宗教信仰最终反过来统治了人本身。日常空间成為超现实想象中的异质空间,区隔了深陷其中的异类和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使现实成为虚化的延伸。
在故事空间的嵌套中,话语空间也开始发生转向。与“话语空间”有关的“此在话语”通常指的是故事叙述者的视角或物理地点。但如果以影片的角色作为“话语空间”的主体,《遗传厄运》体现了两次明显的话语空间转向:由亲情转向宗教,这一阶段是自主并可控的;由正统转向邪教,这一阶段陷入了被迫与不可控之中。“憎恨与原谅”“迷信与科学”在两次转向中互相角力。安妮在家庭中的身份是“母亲”,背负的沉重压力存在于家里的每个角落,悲伤情绪主导了其它所有情绪。参加“失去亲人互助小组”时,安妮得到了个体的集体情感体认,群体赋予她新的共情,她的情感话语空间向家庭疏离而转向主流宗教与陌生的社会团体。影片中被召唤的终极恶魔“派蒙王”有着“男身女相”,一方面掌管灾祸,另一方面主掌科学、艺术与秘法,可以控制魔鬼也能号令天使。善恶俱全的形象暗喻人性本身,影片中的“邪教”成员都是社会中饱受精神创伤、从未犯下滔天罪恶的普通人,每个个体的“话语空间”都相对封闭,没有出口的情绪积累无法摆脱欲望的掌控,只能寻求被邪教赋予洞悉一切秘密的能力。
在话语空间的转向中,对邪教信仰的批判与揭露顺利进入了观众的接受空间,所有角色都淡化了千篇一律的技巧刻画痕迹,成为脱胎于日常生活、真实存在却又脆弱易伤的血肉之躯。就这一层面而言,《遗传厄运》的特殊性在于其所带来的认知愉悦。这种愉悦并不基于传统恐怖类型片惯用的鬼怪志异或完美犯罪,而来自于非客体化的情感满足,叙述的日常化效果给予观众以心理期待。触犯道德和法律的非正常角色一方面让观众感到恐惧、焦虑,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对戒律的逾越激起观众对不合逻辑的叙事产生强烈好奇,而痛苦与愉悦的巧妙叠加便是满足认知好奇所付出的代价。
三、家庭伦理的宿命化书写
《遗传厄运》以人物为导向的家庭剧形式展开,对噩梦的解读根植于复杂的伦理互动之中。影片借用恐怖片惯用的“孩童视角”,从孩童查理和青少年皮特的叙述角度和心理意识重新审视成人生活景观,并与“成人视角”进行多次重复置换,对家庭伦理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认知与描摹。影片的蓝光版本包含一部名为《诅咒:遗传厄运的实质》的短片,短片展现了正片故事的前传,安妮的丈夫斯蒂夫原本是她的精神医生,而在病患关系结束后,斯蒂夫将对她的关心发展为爱慕。导演兼编剧阿里·艾斯特坦言影片情节受到了《魔女嘉莉》的影响,恐怖梦魇并不完全取决于超自然层面,实质源于一个女孩尝试逃脱母系权威施加的宗教压迫与同辈折磨。安妮明显有着两个自我意识的分身,一个是具有权威地位的女家长,另一个是被误解和排斥的精神病人。
《遗传厄运》通过一段拉、定、推的长镜头表现安妮的独白:安妮很小的时候,患有抑郁症的父亲将自己活活饿死,哥哥由于精神分裂症而上吊自杀。也许为了弥补不完整的原生家庭带来的缺憾,安妮冒着生命危险生儿育女,尽心尽力完成母亲的家庭责任,却换来孩子的叛逆与嘲讽。她一面希望逃离代际相承的母系权威的压迫,一面希望成为家庭的真正掌控者,对家庭生活的纯粹追求让步于面对伦理秩序颠覆的无能为力,母亲的心灵危机最终爆发。
女儿查理从小被祖母抚养和安妮日渐疏远,她相貌不扬且沉默自闭,家人的长期漠视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儿子皮特在家乖巧却在外叛逆,他沉溺大麻以逃避对妹妹之死的自责。在安妮与皮特的对峙中,特写聚焦在皮特扭曲的脸上,画外音是安妮撕心裂肺的哭声;安妮在梦游中差点勒死皮特,母亲的动作慢放配上皮特的尖叫,画外音与画面形成强烈对比。青春期是孩子心智与身体成熟的关键时期,母爱的关怀却被强权与责难蒙蔽。在孩子的视角中,母亲真正沦为行为失控的精神病人,母系权威全面分崩离析。不同于传统恐怖片中作为色情观赏物或恶灵象征的女性角色,被颠覆的女性形象开始与男性抗衡,历经悲惨过去的折磨,安妮仍要面对女儿、妻子和母亲身份交叠下的种种抗争。一个家庭慢慢地被未知的诅咒割裂瓦解,无法摆脱的宿命源于亲情的疏离。最亲密的人变得不甚了解,最了解的人在暗中改变。丈夫斯蒂夫充当着家人裂隙的缝合者,在接踵而至的悲剧和母子剑拔弩张的危情下,利用理解和包容纾解家庭矛盾,但这种流于形式的宽慰却无法深入早已千疮百孔的家庭内部。父系权威在影片中一直处于失语地位,外婆对家人的绝对掌控、对孙女的隔代抚养颠覆了传统的家庭伦理,母亲的癫狂又使家长强权与道德权威发生背离。
《遗传厄运》通过解构以合法血缘为单一根基的家庭构建与亲缘霸权,来破除世俗血缘对现世生活的羁绊与操控。在欧洲文化与历史结构中,非血缘伦理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弑父”“杀婴”与基督教的舍亲取义。男性家长的世俗权力通常通过父子或夫妻间的伦理运作加以实现,血缘人伦建制的基础不是亲情而是权威。影片破除亲缘关系而确立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将“非亲缘制”引入一种情感共同体,不断扩大“家”的概念以便产生社会融聚。前现代社会中由血缘维系的家庭关系与社群关系被现代社会的理性关系所取代,这种价值判断使鲜活人性得以从生物学上的冰冷血缘中突围,却也使旧式家庭伦理成为缺少“爱”的躯壳。阿里·艾斯特多次阐释了他的创作初衷:《遗传厄运》最初不是一部恐怖电影,而是有着恐怖内核和运用恐怖片类型手法的家庭片。对格雷厄姆一家的情感创伤的挖掘,使心理式恐惧潜伏于日常生活建置的细节中。在他看来,旧式家庭伦理的解构除了人际关系的法理化倾向,更为本质的是血缘制霸权现代语境下合法性对人伦情感的阻碍。
影片通过极端的寓言式反讽结局在社会学意义上捅破了血缘纽带的幻象。改变人类深陷孤独的处境与探寻和谐重构的可能固然不能依靠极度荒诞的邪教信仰,后现代境况中“新式家庭伦理”的维系需要在更为牢固的情感联系与更为密切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身份再建与归属感确认,而家庭仍不可否认地作为现代伦理重构最基本的单位之一。
四、结语
恐怖类型片的流行一定程度上源于人类对混乱不安、紧张刺激、新奇神秘的猎奇心理,对现实生活的失意表现为对超自然现象、超能力和欲望的渴望与借暴力审美而达到的泄愤。当正统的宗教面临信仰恐慌、至亲至爱陷入信任危机,在极端的精神痛苦中,不恰当的“自救”可能导致陷入精神疾病的“入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球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率仅为9.5%。影片的隐含表达正是亲密关系和社会大众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敌意和冷漠。
“恶魔”源于现代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压力,源于对人身安全与情感关怀的需求,源于对失控、暴力、未知的忧虑。《遗传厄运》突破了近十年主流恐怖片的格调,转向对社会现实问题关注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怀,以叙事为核心,并调动各种视听元素以满足受众的接受特点与审美经验,更加细腻地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困境,将一种家庭伦理式恐怖融合于新的叙事策略之中。
参考文献:
[1]李志强.黑色“梦魇”的足迹--论好莱坞恐怖片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J].当代电影, 2005(5).
[2]Scheuer,Hans Jürgen.Arthurian Myth and Cinematic Horror: M.Night Shyamalans The Sixth Sense[M].The Medieval Motion Picture,2014.
[3]陆扬.社会空间的生产——析列斐伏尔《空间的生產》[J].甘肃社会科学,2008(5).
[4]西蒙·查特曼.故事与话语[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