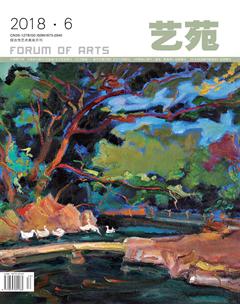宫斗皮囊下权力与爱情的反思
杜怡
【摘要】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如懿传》,作为一部后宫剧,虽身披宫斗外衣,但其叙事主旨与价值诉求却颠覆了以往的后宫剧中的“宫斗”叙事,力图实现对权力逻辑的反思,即以结构宫斗的热闹,投射以解构宫斗的冷眼;同时对后宫的爱情图景进行描绘,戳破爱情幻觉,显露出中国人在日常婚姻之中的幻灭爱情。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与当下生活接榫,探讨这种宫斗皮囊下权力与爱情反思的意义。
【关键词】 《如懿传》;反宫斗叙事;权力逻辑;幻灭爱情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2004年,香港TVB制作的《金枝欲孽》轰动一时,成为当代后宫剧的肇始之作;2006年,香港亚视的《大清后宫》也在内地取得极高的收视率。2008年的《美人心计》可算是大陆最早的后宫剧。2011—2012年的《宫》《步步惊心》《武则天秘史》《后宫》《甄嬛传》相继播出,迎来大陆后宫剧制作与播出的“高峰”;与此同时,迎来了有关“后宫剧”讨论的话题高峰,主流媒体对后宫剧的批评较为严厉,例如人民日报副刊中有关学者评论后宫剧宣扬以恶制恶,崇拜权谋;歪曲历史,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宣扬男尊女卑的封建落后道德,加剧性别不平等恶劣影响;“其中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与封建传统道德严重影响观众对历史的想象与现实的认知”[1];后宫剧影响恶劣“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2]。2012年之后,后宫剧的制作与播出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依旧受观众青睐,2015年的《芈月传》仍旧成为荧屏热点与观众热议的话题。2018年暑期的《延禧攻略》则霸屏,更是创下了单天收视率奇观,而紧续其后的《如懿传》则备受嘲讽与冷落,有人认为女主角周迅面部垮塌、青春不再;其节奏缓慢,不如《延禧攻略》节奏紧凑,未能符合观众“爽”的审美心理机制等等。事实上,后宫剧是本土宫廷剧与外来流行文化的混合产物,豪门恩怨剧与偶像纯爱剧更是其谱系学上不可忽视的源头。而《如懿传》作为一部后宫剧,虽然披着后宫剧惯常的“宫斗”外衣,其中运行着尔虞我诈、阴暗腹黑的宫斗策略,但是该剧的内核宗旨与价值诉求早已突破了“宫斗”的防线,实则是对以往后宫剧中权力与爱情描绘的反思,完全戳破了权力与爱情构筑的可供观众意淫的美好幻象。
一、宫斗皮囊下的反宫斗叙事主旨
《如懿传》的故事线索来源于一个失败的皇后,《清史稿·列传一·后妃》中记载,乾隆的第二位继后,“三十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发,上益不怿,令后先还京师”[3]18917。即在乾隆三十年,47岁的继后自己削发,在满人的文化风俗中只有国丧才可断发,这位皇后的举动惹恼皇帝,被皇帝在南巡过程中遣送回京;随后恩宠不再,在她死后的第二年,其痕迹也被刻意抹去,连谥号、陵寝都一并被剥夺。倘若以令妃为原型的魏璎珞(《延禧攻略》)是屡尝胜绩的草根胜利者,那么如懿则是屡尝胜绩的皇家失败者。在电视剧《如懿传》中回应的便是如懿身为皇后,为何“弃位弃夫弃红尘”成为了故事的母题。《如懿传》编剧流潋紫将这段历史叙述的空白解释为:“与弘历青梅竹马的如懿,在二人进入婚姻围墙外更有紫禁城宫墙、爱情坟墓上更有皇家陵寝,一场场后宫的自卫与反击后,终归情意湮灭,即便贵为皇后,也宁可弃权身死。”[4]1因此,预先知晓结局:夫妻决裂,情义不再,一片废墟;期间便是一场又一场的宫斗,以及伴随宫斗过程中的猜忌、仇恨、离心,都化为日常生活的消磨。然而,《如懿传》的野心却早已峥嵘毕露,在宫斗皮囊下揭开了对宫斗的冷漠感。第一集开始建构男女主角的感情基础;二三集剧情推进迅速,青樱与弘历成婚,弘历登基,成为皇帝。之后到第十八集,如懿完成了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评估:在生存上,她明白了宫廷生活是一个充满争斗与算计的熔炉,争是死,不争也是死,为求自保,自身只能小心翼翼地度活;在情感上,她明白了对爱人的炽热幻想要迅速熄灭,在自己遭陷害之时,爱人丈夫不仅不能保护她,还将她安置在冷宫,并说明这是在保护她。后宫实则只是女性版的官僚战场,皇后不过是傀儡版CEO,负责处理后宫日常事务;而一夫多妻关系中的皇帝,对待母凭子贵的妻妾们使用的是变相的驭臣之术。太后屡次劝导皇帝要“雨露均沾”,而这雨露均沾实则是权力的制衡,而非感情。少女时期的如懿,在情感中对爱人有着盲目预期,对丈夫缺乏基本的认识。夫妻二人早年反复谈论的定情戏剧《墙头马上》,恰恰讽刺了如懿可怜的情感生活:肉眼可见的异性少之又少,倾心容易相知难。而帝王丈夫之所以情感懦弱,缘于对权力的占有与人性的自私。在以往的宫斗剧里,都将帝王形象设置为情感与权力的主动施与者,帝王与妻妾之间的甜蜜互动建立在皇帝单方的“恩宠”,后宫诸女性之间的争斗也是为了争夺恩宠,以及恩宠背后赋予的权力、荣誉、虚荣心。通常“宫斗剧”默认权力规则本身,默认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男尊女卑、长幼有序建构起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其中的女性斗争也不过是在认同权力逻辑下实施的弄权术。但《如懿传》却加入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叙事内容,例如如懿从宫廷画师郎世宁那里得知西方有一夫一妻制,且男女双方拥有平等的离婚权利后,兴致勃勃地与丈夫交心,皇帝却对她进行了一番三纲五常的教育,并立刻收了新宠加以示威。此处,如懿同皇帝谈感情,皇帝却是同如懿谈权力。从此刻起,二人感情的分崩离析只是早晚问题。
事实上,《如懿传》的宫斗剧情非常密集,但对宫斗的诠释角度却有了一致的落脚点:一心当家的皇后,压抑自我,最终被害而死;张牙舞爪的贵妃,最终被弃而死;卖主求荣的侍婢,却被皇帝利用,最终自尽而死;被太后利用、却真心爱慕皇帝的舒妃,间接害死其子,最终郁郁而死……求爱求宠求权求势,互相倾轧陷害,但结局殊途同归,便是女性的集体互害与集体被害。无论是多么翻云覆雨的后宫霸主,在自身命运上也是被动语态。而背后主宰命运的是皇帝以及他所代表的封建权力制度。宫闱间的一丝亮色,便是如懿和海兰的姐妹情谊,在弱肉强食的恶劣环境里,难得地过起了一种现代生活,女人与女人之间的相处,创建了荒凉之外的一种新的家庭形式;这种由女女关系构筑起来的异托邦延展了“爱”的美感:同性之间深切理解的同情、患难与共的信任,似乎比男女之爱更明朗,但是后期,当海兰认同权力邏辑之后,也迅速加入权力操弄的“欢乐场”,姐妹情谊仍在,但人的本质已变,最终成为如懿彻底心死的催化剂。因此,《如懿传》身为一部后宫剧,身披宫斗外衣,用前二十集破题:相信爱,就要被权力吊打;相信权力,就要被更高一级的权力吊打——宫斗,而这些都与爱相反。其他后宫剧,追求的是主角登上权力巅峰的巨大快感,几十集的铺垫,为的就是穿上华服,走进殿堂,享受被万众拜倒时的快感,之前忍受的折磨、经历的龃龉,瞬间都被清空。而《如懿传》却反其道而行之,之前的铺垫,重重的阴谋和争斗、欢笑和陪伴,为的却是最后的解脱。两种瞬间,都有一个画面作为代表。例如《甄嬛传》中的甄嬛,斗倒皇帝,身着华服走上权力巅峰时,深深回眸,其中的野心与沧桑一展而尽;在《如懿传》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如懿在一切幻灭之后,空寂疏阔的表情,与背景中的暗夜融为一体,静谧无声。因此《如懿传》以结构宫斗的热闹,投射以解构宫斗的冷眼,在此种叙述下完成了宫斗皮囊下的反宫斗叙述主旨,也完成了对于宫斗逻辑中对于权力认同的解构,权力是手段、也是目标,也是为了实现自身欲望却以生存为前提旨要的托词;以主动“认输”的姿态实现自我的救赎与超脱,给权力构筑的幻象予以致命一击。
二、宫斗皮囊下的幻灭爱情
《如懿传》的导演曾表示过有意在模仿《红楼梦》,无论是在语言台词、服装道具,还是在环境气氛、审美取向方面,事实上,整个故事的架构与核心仍旧继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这样评价:“《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但这个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在我看来,这是《红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也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间世的最大的悲剧。”[5]79可以按照同样的思路来理解《如懿传》这部作品,《如懿传》主要描写一个理想的爱情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这个兴起是青樱和弘历少年时的相识相知;发展则是迈入婚姻中的如懿和皇帝磨合相守;而最后的幻灭,也意味着二人的爱情终将消逝,夫妻情义终将被世俗的牵累和世故的计算所拖垮。而这个理想的爱情世界自始至终与现实世界分不开,理想、纯粹的爱情与婚姻本身就建筑在这个由封建皇权、等级制度森严建构起来的皇家基础之上,而这个皇家宫廷,是权术阴谋、家族利益、欲望权力交锋的斗兽场。并且在二人理想爱情婚姻的整个发展和破败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承受着爱情婚姻之外的一切力量的冲击,例如妃嫔之间的算计陷害、帝王权术的玩弄、前朝与后宫种种力量的博弈、封建天命的诅咒。因此,这种爱情的真挚与纯洁,既从肮脏中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回到肮脏中去。这种理想世界的幻灭可以说是封建制度本身所带来的,所有人被异化,皇权来自皇帝,但并不代表皇帝可以一味地释放自己的欲望,他同样只能不断地压制,直到皇权吞没自己,将自己变成冰冷的机器,将自己的妻妾均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就算他早已不爱如懿,但如懿也是他的私产,而不是一个具备独立价值的人,所以无论是谁,只要有可能觊觎他的私产,他不能允许。因此皇帝對如懿便可以肆意凌辱,在尊严上进行践踏。在影视作品中,对帝王将相的认同实则并不少,往往会对帝王将相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移情,例如《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记》等,都会认同当权者为了黎民百姓、江山社稷而不得不所作出的选择。而在《如懿传》这部作品中,当凌云彻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乾隆下令从侍卫变成太监后,笔者便无法再从旁观者的角度对乾隆进行批判,伴随如懿痛恨起这个皇帝——乾隆,并且痛恨他所代言的整个封建制度;而如懿用自己断发所反抗的也是封建制度本身,制度让人异化的倦怠与无趣令人厌烦、痛恨。
可以说造就爱情幻灭的是皇权制度,但是在此之外,有着更深一层的缘由,而这种缘由亘古存在,便是婚姻本身的消磨。导演汪俊在这部剧简介里提到一句话:“二人在宫廷里演绎了一段从恩爱相知到迷失破灭的婚姻历程。”这一句化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导演用了“婚姻”这样一个概念,通常情况下,电视剧主创人员不敢也不会将皇帝当成“人”来形塑,“婚姻”二字,也不可能同皇帝联系在一起;但在这部剧,却将皇帝视为一个有权势的男人,讲述他的婚姻故事。实则“婚姻”这两个字,已经说明了这部剧的价值取向。“从恩爱相知到迷失破灭”,承认了皇帝与如懿之间存有爱情,并且是相互扶助、静静相处的“恩爱”;“迷失破灭”则承认他们的婚姻爱情有着正常的走向,以往宫廷戏中,皇帝与他身边的女人,不会有迷失破灭,只有占有者与附属品,没有爱情婚姻发展的轨迹理路。这几个字,有时间的气息,也有伴随着有日常的琐屑。梅特林克在《日常生活的悲剧性》提及:“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悲剧因素存在,它远比伟大冒险中的悲剧更真实,更强烈,与我们真实的自我更相似……生活中真正的悲剧性,这种正常的、深刻的和普遍的悲剧性,只是在人们称之为冒险、痛苦和危险的东西成为过去的那一刻才开始。”[6]75戏剧家梅特林克正是在日常生活中窥伺到了某种悲剧性,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家庭琐事、人情世故、谋划筹算,便是“几乎无事的悲剧”,恰恰是这一种悲剧,于无声处听惊雷,无事中见大事,细流中见江海,直抵生活真相的核心。例如,在《如懿传》中,皇后的丫鬟莲心入水后,这个镜头非常巧妙。灯火阑珊处溅起一小朵不起眼的水花,瞬息即灭。如同历史打了个嗝,将无关紧要的为奴者的叹息包含其中,也不过咕咚一声。权贵的世界灯火继续轰轰烈烈地燃烧着,一千双旁观的眼睛死去,热闹如故。这与《红楼梦》中的世界十分相似,秦可卿去世,各揣秘密的奴婢们死的死,演戏的演戏,没有人活得好,都只有糟糕。如懿则与皇帝两人之间被种种猜忌和彼此的消磨耗尽了夫妻情分,人心在彼此试探中露出狰狞的面貌,皇帝实则是刚愎自用、薄情寡性、自私虚伪、疑心深重的集合体,曾经的弘历已经荡然无存。
如懿与皇帝之间的幻灭爱情建立在相知相守的基础上,完整地写出了一对原本恩爱的情侣——青樱与弘历,他们感情的消逝,这样的消逝自然而无法挽救,也使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感情的浓度可以永恒不变。同时其他嫔妃与皇帝之间的互动则体现了婚姻围城之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对于爱情的幻灭感知,被规定的爱情是这些女性无法摆脱的宿命,她们进入婚姻,便必须敬慕自己的丈夫,当残酷的现实击碎这些女性的幻梦,爱情便开始变质,她们变得委曲求全、小心算计、心狠手辣,此刻爱情早已不是爱情本身,而是苦涩生活的本身。富察皇后身为乾隆的第一任皇后,端庄贤能,她与皇帝之间相敬如宾,然而背后也隐藏着深沉的心机:她在送给如懿的镯子里偷放防止怀孕的香料,在花园里毫不留情地踩海兰的手……但这些恶毒行为并非出于她的天性,而是因为她的地位与家族迫使她这样去做,宠爱与地位是封建时代里女性唯一的救命稻草。《金瓶梅》中,失去夫君宠爱的吴月娘,故意在月下烧香,祝福夫君身体康健,自己能够早日生出子嗣,她所挑选的时间点,恰恰是保证西门庆能看到的时间,结果本来已经生出嫌隙之心的西门庆,认为自己的妻子对自己是真爱;这种心机恰与富察氏一致。高晞月容貌艳丽且多才多艺,前朝又有家族护佑,几乎是宫廷嫔妃所有人的敌人,她的种种谋求算计仍旧有其自身的道理,因为她爱皇帝,她经常在寂寞的深宫里演奏琵琶,在铮铮琮琮之声中默默等待着皇帝的爱。《金瓶梅》里西门庆迎接着层出不穷的新人,潘金莲被冷落,独守空闺,只能在雪夜里独奏琵琶。从魏晋时期开始的“闺怨”主题,穿破时间的雾霭,与此相接。金玉妍则是其中的例外,她是携带着爱情(倾慕北国世子)走进婚姻之城的,爱的对象在远方,内心的苦楚与寂寞始终难以倾诉,留在宫廷之内的是一个空壳。她将皇帝视为猎物,自己身为猎人,她对皇帝有着微妙的征服感,正是因为不爱,所以培养出她的自信,并且越加笃定,以至于近乎狂妄;她在其不露声色的恶毒之下流露出的是种种厌倦感,直到最后被如懿揭穿,自身的爱情也不过是一场幻梦。即使是完全负面形象的卫嬿婉,通过勾引皇帝,在委曲求全之下攀上权力的高峰,但在死亡之际还是惦念自己的初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些被囚禁在笼中的“金丝雀”几乎没有逃离的能力,在笼中做困兽之争,其中的人物行事逻辑均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人性之中的灰色地点成为重点描摹的对象。而这种逻辑也正是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与《金瓶梅》之中的人物逻辑,没有绝对的非黑即白的人事,人性的神性与兽性彼此交织,形成混沌的世界。
三、反思的意义
后宫剧的核心剧情是“斗”,将后宫设置为权术竞技场,人在其中争斗倾轧。后宫剧制造出有关权术的幻想,产生魅惑观众的力量,通过对“恶”的渲染,调动起观众的观赏情绪。在美学观念中,“审恶”也是一种审美,通过刻画人性幽微暧昧之处,达到审美的目的。但是,作为一种美学关照下的“审恶”,是“一种批判性的存在,审恶是为了治恶”[7],即审“恶”是为了惩“恶”,规避“恶”的侵蚀。但是,在大多数后宫剧中的“恶”形成泛滥之势,完全放弃“审恶”的美学原则与批判性。权术的落地生根往往呈现出两种手段,即上位与复仇。前者是普通女性凭借后宫各势力的联盟、陷害子嗣等手段,夺得皇帝的垂青,从而跃居高位;后者是对人事施加给自身情感创伤的一种反抗,通过以恶抗恶的手段,使自己重新获得生存价值。前者代表人物有《甄嬛传》中的甄嬛,少女进入宫廷之后,默认宫廷争斗的逻辑规则、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一步步成长为“皇贵妃”。后者代表人物有《金枝欲孽》中的安茜、《延禧攻略》中的魏璎珞。她们留在宫中的动力便是复仇,安茜留在宫中是为了给死去的奶奶复仇;魏璎珞是为了给姐姐复仇。主人公往往都以生存与情义为前提,行阴暗之事,尽展人性之恶;并在成功之后为所思所做赋予合理性与价值正义。这种“恶”的虚构与叙事,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詹姆逊认为,叙事经验往往由社会制约,“因为它依赖于事件复现和相似的某种节奏,而从起源上讲,这些事件完全是文化性质的”[8]51。因此,电视剧中的叙事经验的形成并非完全由单纯的审美构成,同时折射出社会当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凭借上位与复仇的权术手段构筑出的权力幻觉,不仅是主创团队的主体行为,也折射了社会文化的心态,是二者的共谋;也正如戴锦华所形容的,当下的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逻辑有着深刻的体认,“甚至是对当权者的体认,这种体认不仅是知识性的,而且是身体与情感的”[9]。而《如懿传》中的如懿是权术倾轧泥淖中的一朵“白莲花”,她不愿参与、不愿争斗,只求自保,在剧中呈现出优柔寡断、缺乏行动力的姿态;因为她始终知道自身的爱情世界中的敌人,并非是其他嫔妃,而是皇帝一人。而她最后与皇帝彻底断绝关系,剪发、被废黜,是一种主动的解脱与放弃,解脱是否定,是轻蔑,是对此前种种被灌输的价值观的颠覆,是对结构性力量的最大反动。在此种层面上,《如懿传》通过对权力的反思,实现了对权术逻辑与观众预期审美的一种冒犯,从而迫使观众重新思考权术幻想本身所携带的“恶”,以及以正义之名行惡的悲惨境况。
《如懿传》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节气描绘,伴随着节气的描绘,利用植被花草的兴衰映衬人事的无常。外面无论怎样争斗,里面的人还是一心想过好自己的日子,尽管手上沾满罪恶,但在洗干净手后,日子还是正常地过下去,例如金玉妍,上半场还在声泪俱下地思念情郎,下半场便端出毒药准备陷害其他女性的孩子。《金瓶梅》中,元宵佳节,妻妾们聚集在一起看焰火,看完后走在大街上,每个人竞相表达自己的身段之美,脚步之优雅;潘金莲善妒,讨厌一切新人出现,但也会叫新人宋蕙莲烧一个猪头,供她与孟玉楼等人喝酒玩乐。和睦的生活景象里,埋藏着杀机;而杀机深重的日子里,又有着不甘和无奈,这与《如懿传》趋同。同时,《如懿传》里有着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除了展示时间的流逝之外,还有一个功能,便是显示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态度,即宫廷女性过日子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展示她们的爱恨情仇,而这些,都存有依托,并非是言情小说中的空中楼阁;并且,这也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审美取向:爱中有恨,爱中有琐屑的日常,有委屈,甚至也有绝望,没有绝对纯粹无暇的爱,或者说,没有琼瑶言情小说中那种幼稚的爱。“爱情神话的幻灭从人类深层情感层面显示了启蒙神话的幻灭,从另一角度说,启蒙话语的解体也必将导致爱情神话的解体。”[10]因此,《如懿传》中爱情图景的描绘,不仅写出了国人长久以来的爱情态度与相处模式,更与当下观众的情感世界形成一种精神共振。但又不仅于此,《如懿传》还在追问“爱情”为什么会消失,激情不可控,肉欲会减退,其珍贵亦令人回避胆怯,而它处理的方式是封建权力的异化,以及婚姻围城中的日常磨损。肯追问、肯质疑、肯冒犯,这是理想主义者对生活本身、生存本身的反思;《如懿传》甚至挑战了观众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它的野心就是要“与民同哀”。
参考文献:
[1]颜浩.论“宫斗剧”的文化本质[J].人民日报,2012-7-10(024).
[2]陶东风.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J].人民日报,2013-9-19(008).
[3]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流潋紫.后宫·如懿传[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5]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莫里斯·梅特林克.梅特林克随笔书系[M].孙莉娜,高黎平,译.哈尔滨出版社,2004.
[7]陈进武.“审恶”:当下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J].云南社会科学,2013(4).
[8]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9]张之琪.戴锦华:今天的年轻人对权力有一种内在的体认与尊重[EB/OL].观察者. https://www.guancha.cn/DaiJinHua/2018_07_09_463292.shtml.
[10]邵燕君.在“异托邦”里建构“个人另类选择”的幻想空间[J].文艺研究,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