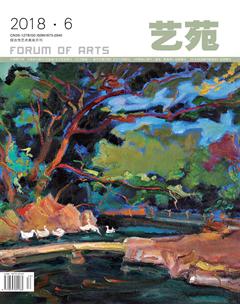从《江湖儿女》中那列火车谈起
周淑红
【摘要】 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中有一场发生在火车上的戏,它以青山环抱中铁路高架桥上一列火车驶过作为开始,本文从这个十几分钟的电影片段入手,从火车的象征意蕴出发分析电影中呈现的对于现代性的审慎的态度。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江湖儿女》和贾樟柯以往一些电影作品的联系。
【关键词】 《江湖儿女》;火车;常人;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
在《江湖儿女》放映到它的三分之二的时候,有一场和火车有关的戏,它以青山环抱中的铁路高架桥上一列火车驶过作为开始,而这时候的女主人公赵巧巧离开三峡,正坐在这列去武汉的火车上。徐峥饰演的克拉玛依忽悠男也在这列火车上登场了,他一上场就非常善于调节气氛,先是问邻座的乘客:“大哥,你去哪儿?”然后问斜对面的乘客:“小伙子你是做什么的?”接着又问正对面的巧巧:“这位美女,你到哪儿去?”忽悠男和周围的人开始热聊起来,他侃侃而谈,把周围的人忽悠了个遍,他说自己在新疆做旅游项目的开发,听说巧巧见过UFO之后马上盛情邀请还没有工作的巧巧加入他探险旅游的团队。巧巧同意了,在转火车去乌鲁木齐的路上,克拉玛依男子伸手试图牵巧巧的手,巧巧递过去手上的矿泉水瓶作为中介物,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去新疆的火车,在车厢连接处,可能彼此顿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幻觉,竟在逼仄的空间中拥抱在一起。当克拉玛依男子告诉巧巧自己在新疆没有什么旅游公司,只有一个小卖部,巧巧表示并不介意,并且也坦陈自己就是他口中的囚徒:刚刑满释放。克拉玛依男子沉默。巧巧在火车停靠的时候,独自下了火车,走进那无边的黑夜。在黑夜中,她真的看到宇宙飞船在天空中划过。
一
在这短暂的持续时间大约十二分钟的电影片段中,可以看到其中的两个人物——赵巧巧和克拉玛依男子从互相不认识到面对面坐在一节车厢上,再到从闲聊中互生好感,好感渐渐强烈,拥抱在一起,最后巧巧独自离开。这个电影片段类似于一个模本,在这个片段中,仿佛也可以窥见整个电影的结构,可以说整部电影是这场火车戏的放大:巧巧和斌斌在山西大同从互相不认识(虽然电影一开始他们就是恋人,但前史中总会有一个相识的过程),之后成为一对恋人,接着中间有一些曲折,聚散离合,最后还是分开了。这个短暂的电影片段似乎也是我们每个观众一生的表征:来到这个世界,经历一番人生的欲望、挫折、争斗、悲欢……之后离开,人生不过是一趟旅程。
巧巧、克拉玛依男子、斌斌,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只是电影以一束烛幽之光将他们照亮了。在这短暂的十几分钟的火车戏中,观众看到了他们,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影片中更多无名无姓的人。也可以想象火车上的其他旅客,有的随便聊几句,有的一句话都没说,彼此只是在一个时间段内在火车车厢这个空间中相遇,有的人在这个站下车,有的人在那个站下车,有的人离去,又有新的人来。除了这些在巧巧回大同的火车上的人,还有片头破旧的公交车上的人以及那些在巧巧去三峡的轮船上的人,这些人和故事无关,也不被注意,但确确实实地在镜头前呈现过,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贾樟柯一直都很喜欢拍人物群像,比如《三峡好人》一开始是一个移动的长镜头,一条小船在长江上漂流着,镜头从船头缓缓移动到船尾,船上几十个民工有的在说话,有的在打牌,有的在看短信,还有的在算卦,不同的人映现在镜头前,流动的水、流动的船和船上的流民构成了流动的镜头。犹如一幅正在逐渐打开的中国长卷画,随着卷轴的转动,视野逐渐展开,镜头中每个人都在镜头划过的瞬间如静物般沉默无语,这个长镜头的背景音乐是地方戏曲《林冲夜奔》。这个镜头悄然无声,却传递出导演的悲悯之情。
贾樟柯的这种白描式长镜头的使用可以让镜头前的事物显得更为客观,他排斥特写镜头,更愿意以中、远景建构影片空间,保持一种有距离的观察,尊重发生于特定时空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让事物不受干扰地自由地呈现,不对观众的凝视进行掌控并且维护观众的观影自主权。白描式长镜头这种电影语言体现的是一种平等、尊重个体,渴望自由的意识。贾樟柯对长镜头的执着和他对侯孝贤和布莱松的崇拜相关,侯孝贤和布莱松都强调和拍摄对象保持距离,同时倡导摄影机“不参与”“不破坏”的旁观态度。贾樟柯说:“带着DV摄影机,在公共场合中会见熟悉的陌生人。隔着人群长久地凝望,终于让我接触到了无可奈何的目光。这令我忽略掉了具体的人物、理由、语言,只留下了动作、声音和飘荡在尘土中的苦闷和绝望。”[1]3这是贾樟柯的创作自白,也是他為自己影片做出的注解。
贾樟柯电影中的这些人物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谓的“常人”。常人,指的并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庸庸碌碌的、不具备主体性质的、沉沦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倒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2]127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也是福柯所说的“无名的人”:“没有什么东西会注定让他们声名显赫,他们也不具有任何确定无疑的,可以辨认的辉煌特征,无论是出身、财富或圣德,还是英雄行为或者天赋英才;他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但除了那些一般被视为值得记录的事情之外, 他们的生存灰暗平凡。”[3]《无名者的生活》是福柯为《福柯文选》撰写的导言,福柯关注那些被忽视的、无力存在的人。贾樟柯电影关注的也是这类容易被历史删除的人。无论是汾阳县城“小武”,还是“三峡好人”以及《二十四城记》的那群“异乡人”,他们多是这种“常人”以及“无名的人”。
也正因为是这样,《江湖儿女》的结尾,是一个监控器里很模糊的巧巧的身影,贾樟柯用这个镜头来做结尾,因为这个形象,就是一个当代无处不在的数码影像。那些个体的鲜活的生命、经历过五味杂陈的情感的人,最终可能就像这个监控里模糊的数码影像一样,终究会被删除。所以贾樟柯在一个访谈中说:可能我这部《江湖儿女》是在拍一些将会被删除的人。
二
火车是现代性的象征,它是流动的、变化的、转瞬即逝的,它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承载了现代、时间、空间、自由、规训、创伤等等经验和想象。
巧巧离开三峡坐的是火车,一路到新疆,从大同来三峡时坐的是轮船,背景声音中的高音喇叭中说,三峡这里移民,这里的风景很快就会被淹没了,成为河底。人口迁徙,流动性,是现代性的意涵,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火车象征着它带来了旧有时空关系与社会等级结构的改变。关于流动性,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说:“尽管在前现代时期,迁移、游牧和长距离奔波已经是平常的事情,但同现代交通工具所提供的密集的流动性比较起来,前现代的绝大多数人口则处在相对凝固和隔绝状态。”[4]90所以,吉登斯用“脱域性(disembelling)”这个术语来表征现代主体脱离空间束缚获得流动自由。而当代文化地理学家约翰·库利则把这种流动性物质化为火车,他说:“火车使大批量人口依靠机械化工具高速移动,是一种巨大创新,火车因此成为现代性的标志。”[5]92-93
《江湖儿女》这部影片可以按照时间和地域的变迁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呈现了山西大同的江湖面貌,第三部分还是回到大同,而第二部分则是巧巧寻找斌斌的过程,第二部分整体上是移动和变化的。变化这一主题在贾樟柯的《小武》《世界》《三峡好人》中都被贯穿了,变化渗透在周遭的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围绕着变化,各种叙事得以展开,故乡正在消失,人们的各种关系也在变异,人物开始寻找那些不变的东西,但是寻找的过程,却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巧巧出狱后,先是去往三峡奉节寻找有了新生活的郭斌,她心灰意冷之后欲回山西,但在回程的火车上碰到克拉玛依男子,又意图前往新疆谋生,最后又改变主意重返故乡山西大同。在这趟距离相当长的旅程中,巧巧被轮船上的乘客偷了钱包,被摩的司机要求“耍一下”……电影用轮船和火车等交通工具绘制了一条从矿区到三峡、再到新疆、最后返回矿区的“江湖”的道路,在这条线路中还可以看到贾樟柯以往电影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如《站台》中的街头文工团、《三峡好人》中的宇宙飞船),可以说是对以前的一些电影作了一场回顾。这条道路也大体描摹出一幅中国中西部地图,这条道路既是电影中的巧巧辗转各地的路径,也是世纪之交中国人口迁徙的路径。
火车的现代性意味在贾樟柯早年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故乡三部曲(《站台》《小武》《任逍遙》)可以看成都是对现代性的反思。《站台》这部电影的开场是一个县文工团下乡慰问演出所表演的一个剧目:《火车向着韶山跑》。“火车”意象显示了人们对现代化的向往,但是这些文工团员并没有乘坐过。文工团团长在电影开头的时候就对崔明亮进行了批评,因为他模仿火车声音不像,而崔明亮则回答说:“我又没坐过火车,我咋知道火车怎么叫?”这其实暗示了火车所象征的通向现代化的这趟旅程可能比较艰难。《站台》的最后,片名暗示的大家苦苦等待的火车出现了,这场文工团成员们“追逐火车”的场景可以被看作是关于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寓言:演出途中,文工团的卡车在一处荒凉的山谷中抛锚,崔明亮坐在驾驶室里,播放张行的《站台》录音带,当“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的歌声响起时,突然“有火车、火车、火车”的喊声也响起来了,崔明亮等文工团成员们跳下卡车,去追逐火车。电影镜头从全景摇成文工团成员们在荒原上奔跑的远景。当他们到达铁道边,呼啸的火车已经一闪而过了,崔明亮、张军、钟萍等朝着远方驶去的火车大喊大叫,他们的喊叫中隐隐混合着兴高采烈和绝望孤寂,然后马上沉寂下来了。这是火车唯一一次出现在《站台》这部电影中,出现的时间很短暂,它没有带他们去任何地方,而且电影镜头所呈现的火车的画面和追逐它的文工团成员在不同的时空中,这一点暗示了当时,即改革开放之后的人们对现代性既试图追寻又隔着很多屏障,暗示这条现代性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片名“站台”所象征的这个连接处的空间,它是过去与现在的连接、乡村与城市的连接、传统与现代的连接,既是一个重要的地点,也是一个尴尬的场域,在这里,人们或许只能等候。
贾樟柯说过:“我学会自行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30里地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这些事情如今在电影中是发生在比我大十岁那些主人公身上。当时对我这样一个没有走出过县城一步的孩子来说,铁路就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6]290
在《江湖儿女》中,也可以看到现代性之于周边环境的隔膜,其中多有裂隙。比如当巧巧到了奉节的潮州商会,她在那道自动门前,自动门却没有打开。自动门内部是一个现代化的企业,还有接待处,但她却进不去,巧巧就这样被象征着现代的林家栋和林家燕的公司阻隔在门外。又比如二勇哥的葬礼,一边是传统民俗中的葬礼仪式,一边则是具有现代色彩的国标舞表演,造成一种强烈的对比与反差,在这种差异中生出了荒诞感。
导演对现代性抱着一种审慎的态度。《小武》《站台》《任逍遥》中的人物是茫然的混混、躁动的青年、卑微的乡镇居民,他们都渴望现代性,但又处在边缘位置,面对时代的变动,他们惶惑地挣扎。现代性往往也会带来道德滑坡,《小武》中的男主人公以偷窃为生,《任逍遥》中的斌斌和小济最后走上抢劫银行的不归路。这种道德崩坏在《江湖儿女》中的很多地方也体现了。麻将桌上,一个青年在用验钞机验一张百元面值的纸币,验钞机发出这样的响声:“这张是假币。”他再验了一次,还是发出“这张是假币”的声音。同样,我们也看到由现代性带来的种种道德问题正在向更深的内陆蔓延。赵巧巧告别潮州商会之后在婚宴流水席上的小小骗局、酒店内的碰瓷等,她轻巧地利用时代的、人心的漏洞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可能,在这时代之中,江湖也褪去了浪漫主义的光晕,变成了穷途末路者无奈的生存伎俩。这让人想到《老子》的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三
火车既是自由和进步的象征,也是束缚和压迫的途径。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第八章“铁路导航与禁闭”中指出火车车厢的一个特点:“火车车厢是个封闭空间,车厢有固定的座位,座位有固定的数目,旅客除了能去休息室和卫生间短暂活动外,就只能被束缚在座椅上。这是多么理性化的乌托邦。这种封闭的空间使秩序的生产成为可能。”[7]112
《江湖儿女》展现了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桎梏。在传统游民社会中,秩序的形成依靠“情义”,或者說,是“情义”建构了一套人们行为的逻辑。某种程度上,情义对人的束缚甚至要高于一个有形的国家机器所给予的制约。在传统游民社会,当情义与国家机器之间发生冲突时,往往前者更为重要,这一点架构出中国社会独特的隐性与显性、有形与无形的社会交往的线索。《江湖儿女》一开头的麻将馆场景中,斌斌调节老贾和老孙之间的江湖矛盾所用的手段是请来山西文化非常重要的代表“义”的关二爷神像,而并非其它——比如“枪”这种武力的胁迫。后来也正是因为“情义”二字,巧巧用“枪”来拯救斌斌,而自己则进入了监狱。监狱则是一套有形的规训与惩罚的机制,但出狱后的巧巧看到了社会上种种道德灰色地带,为了生存也利用了这些,但是她心中仍有“情义”二字在。斌斌试图活得逍遥,对于为救他而入狱的巧巧他表现得并没有多少愧疚,他行为背后的逻辑支撑是——“我的马仔向我耀武扬威,我的小弟没有迎接出狱的我”,所以他追求的是重建他的大哥身份。这种理性的、薄情的逻辑原本可以活得很潇洒,但是讽刺的是,他却被束缚在轮椅上,需要被人推着才能移动。这样看来,《江湖儿女》的主题多少有点呼应贾樟柯早年的电影《任逍遥》,它也探讨了逍遥的可能与限度,渴望逍遥,但又被束缚在有形或无形的枷锁中。《任逍遥》的结尾,抢银行的斌斌被公安抓获。双手被铐、背对墙壁的他被要求唱一首歌,于是他反反复复唱起自己最喜欢的《任逍遥》。这里电影使用了一个长镜头,镜头的角度和位置是完全不动的,只有中景画面中央的斌斌在唱歌,他处于静止镜头框架的中心,这里的镜头框似乎是监狱的隐喻,而斌斌不管怎么做动作也无法打破这一框架。镜头随后切换到小济身上,骑着摩托逃走的小济行驶在马路上,此时的镜头处理和斌斌是一样的。这两个相同模式的长镜头暗示了这两个人物被拘囿的生活状态,在整部电影中,他们一直处于这种被束缚的状态中。他们的“被困”,来自于经济的穷困以及精神的空虚。《世界》同样表现了一群底层人物被束缚在一个地方、无法逍遥的生存状态。全球化虽然令人们能快速饱览全世界不同的建筑,但也将一些人牢牢地束缚在某个角落,并让他们重复做相同的工作。
庄子的《逍遥游》中有:“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庄子提到了可以御风而行的列子,但是列子虽然不用双脚,但是并没有达到逍遥的境界,因为他“犹有所待也”,即仍有所依靠,“风”是列子所仰仗的工具,如果没有风,他就不可以飞行了。
火车上的克拉玛依男子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我们都是宇宙的囚徒。“宇”代表的是空间,它对应的是全球化;“宙”代表的是时间,它对应的是现代性。
参考文献:
[1]贾樟柯.贾樟柯故乡三部曲 任逍遥[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3]米歇尔·福柯.无名者的生活[J].李猛,译.社会理论论坛,1999(6).
[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John Curry.Mobility[M].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7.
[6]贾樟柯.贾樟柯故乡三部曲 站台[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7]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M].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