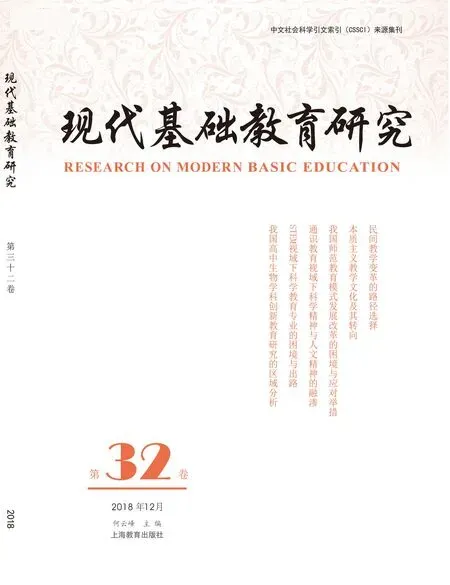福柯自我技术关照下的学习者身份及其形塑
邱德峰,于泽元
(1.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2.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重庆400715)
21世纪是学习者的世纪,学习型社会已初见端倪,并逐步成为一种必然之发展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经合组织(OECD)也多次呼吁:21世纪的关键能力在于学习,提倡把学习权交给学习者。[1]学习型社会愿景的达成不仅需要良好的外在环境支撑,更需要一种内在的身份作为保障。学习者身份(Learner Identity)是个体对自我作为持续学习者的形象和身份的认同,可以有力地推动个体成为终身学习者和自主学习者[2],并最终迈向终身学习型社会。从社会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学习者身份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具或符号,其能够对人自身的学习和发展行为起中介性的作用。同样,从福柯(Foucault)的视角而言,学习者身份也可被视为一种自我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self),即个体如何通过学习者身份这一技术来塑造和改变自我。本研究尝试以福柯的自我技术为研究视角,分析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学习者身份是如何作为一种自我技术来塑造自我的,以及在自我技术的关照下,学习者身份是何以形塑的。
一、自我技术之意涵
福柯的整个哲学思想及研究主题总是与“主体”一词有紧密的关联,可以说福柯毕生都在为“如何塑造主体”而思考和探索。在福柯的三本著作《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词与物》及《规训与惩罚》之中,分别通过对疯癫的历史、人文科学的历史以及惩罚与监狱的历史之考究和讲述,来反映人的主体性是如何演变的,可以说正是在疯癫史、惩罚史和人文科学史的展开过程中,人的形象和主体形象才缓缓浮现。[3]虽然福柯一生都在思考主体性问题,但是其侧重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向。即由此前60年代对知识话语是如何塑造主体的关注,以及70年代对权力谱系学的关注,转向了80年代对伦理的关怀以及自我技术的建构。[4]关注点由“外在权力是如何改变自我并使自我客体化”转向了“自我是如何改变自我的”。从福柯的整个思想进路可发现,他逐渐摆脱了权力与知识论的禁锢式形塑,而转向了基于自身的主体性形塑,以求得自身的知识,恢复主体自由自主的地位。[5]
“技术”是福柯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元素,在关于“技术”问题的看法上,福柯认为,人类所探索的知识(如经济学、生物学、医学等)必须与具体的技术相结合才能成为了解人类自身的工具。而这些“技术”可分为四种[3]:生产技术;符号系统技术;权力技术;自我技术。这里,福柯更感兴趣于后两种技术,即权力是如何塑造人,以及个体是如何管理和塑造自我的。在对自我技术的关注上,福柯进行了历史性的考究,例如古希腊时期的自我技术即学会“关注自我”(the concern with self),能够主控自己的身心问题与欲望,学会与他人相处,也即福柯所谈论的生活艺术、风格与技巧等。在福柯看来,生活技巧、生存技艺及生活风格都环绕着“关照自身”这个核心,所以均可视为自身技术。[6]这里需提及的是,自我技术并不等同于客体管理制度的分析,这是因为:一方面,自我技术并不需要物质条件、工具和手段来产生客体,而是通过一些看不见的、隐形的技术来产生客体;另一方面,自我技术往往同其他治理的技术关联在一起,如在教育系统中,引导他人与管理自我紧密相连,教师教导学生的前提是自己也能够自我管理、以身示范。
总而言之,福柯认为,自我技术即“它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己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纵,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3]较之以往外在的权力技术而言,自我技术更突显“自我”在改变自我历程中的作用,个体的主体性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从福柯对该概念的定义来看,自我技术至少蕴含:(1)对“自我”问题(如身体及灵魂等)的关注,个体通过对自我的主控,从而使其成为自身生存的主人。(2)它是一种生活技巧、生存技艺及生活风格,为个体带来技巧与态度上的修正,有助于引导个体成就自我。(3)可藉由个人自己的方法或是别人的帮助来实施。往往与管理或统治其他人的技术关联在一起,并以隐蔽方式来进行。(4)重视个体的主体性与主动性,和自我修养意涵相近,是美学的主体化。[7]
二、作为自我技术的学习者身份
“身份”是用来区别自我和他者的一种符号概念,用来反映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他者相同或相异的属性。对于自我而言,“身份”关注的是在不同时空脉络下自我的连续性和一致性问题,通过自我来认识自我、形塑自我。而对于他者而言,“身份”则更关注自我和他人所具有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并籍由他人来反观自我、认识自我。这与福柯所指的自我技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来改变自我”的核心理念颇为一致。吉(Gee)将身份分为四种类型[8]:自然身份(nature-identity);制度身份(institutionidentity);话语身份(discourse-identity);亲和身份(affinity-identity),这四种身份能够从不同的视角解释某种“特定类型的人”(certain kind of person)的形成。首先,“自然身份”是个体所固有的一种属性,如性别、肤色、民族、种族、阶层、认知风格、个性等,这些先天属性使得个体具有了某种特定类型的身份。其次,“制度身份”是一种由制度所赋予的身份,即“我们是谁”是由我们所处系统的规范和制度决定的。再次,“话语身份”是一种由话语关系所决定或是在对话中建构的身份,即“我们是谁”与遗传特征或制度运作并无多大关系,而是在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的过程中形成的。最后,“亲和身份”是一种经验身份,即“我们是谁”主要是由我们在某种特定关系团体中的经验和经历所决定的。上述四种身份能够有效地解释:个体如何成为某种特定类型的人,以及个体是如何采用某种具体的理论工具或技术来形塑自我、改变自我,并使自我主体化的,也即福柯所谓的自我技术。
而“学习者身份”是学习和身份相遇后的产物,它是个体在学习活动中逐渐形塑的,能够很好地反映个体是如何在学习活动和经历中认识自我、感知自我的,其本质是对自我主体性的关注,也即福柯自我技术的核心要素。在面向学习与身份的问题上,贾维斯(Jaryis)认为,“人类的学习是一个贯穿一生的过程,整个人的身体(遗传的、物理的和生物的)和心理(知识、技能、态度、价值、情感、信念和意义)所经历的社会情景、感知的内容反过来会转化或结合成个体的人物传记,而这一过程又导致了持续不断的改变的人。”[9]因此,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教育环境不仅是知识建构的场所,也是作为具有丰富经历和经验的人的建构场所,而建构的基础则是通过认知和情感化的过程,将一个社会情景不同方面的经历和体验变成个体自身的一部分。奥斯兰德和卡莱尔(Os⁃terlund&Carlile)的理解也颇有深意,他们强调“我们不仅仅只是获得关于世界的事实,而且还以社会认知方式发展了一种在世界中行为/活动(act)的能力”。[10]而这些认知方式定义了个体是如何通过他人而被感知的,以及个体是如何认识和看待自己的,因此也可被视为主体形塑的一种自我技术。温格(Wenger)对学习和身份也有深远的洞见,他认为“学习不仅是知识、技能和信息的累积,更是一个成为(becoming)的过程。”[11]根据温格的启示,“身份”是学习共同体内部及之间经验协商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学习经历成为构成学习者身份的关键要素,学习经历不仅能够反映个体的认知发展轨迹,也可以映射出个体学习过程中所涉及的情感、态度、意义、信念等诸多元素。同时,温格所持的是一种社会化学习观,共同体反映了个体所处的独特的社会结构,个体在共同体的实践和参与中发展了经验,并创造了意义和身份。
就学习者身份的形成过程而言,辛哈(Sinha)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学习情境使得个体成为一个学习者。[12]这就意味着个体要获得学习者身份需要经历一个情境性的建构过程,正如成为教师、医生、律师、父母或者任何他们所能成为的一样,都离不开相应的情景活动来提供支撑。戈拉德和里斯(Gorard&Rees)也强调,学习者身份是个体社会性经历(主要是指学习经历)下的产物,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历史、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情境的影响。[13]然而学习情境只是学习者身份建构的场域,并不能够作为学习者身份建构的要素。而温格(Wenger)后期的研究也许更具启发意义,温格认为个体对于自我作为某种身份的认知不仅仅是因为属于这个共同体,而更重要的是共同体中的实践和参与的结果。言下之意,个体在某种特定情境中的身份建构主要是由他所从事的以及正在做的事情所决定。法国教育家塞莱斯坦·佛雷内(Célestin Freinet)的名言也许更具深刻性——“人是在打铁中成为铁匠”。这句隐喻至少蕴含两层意思:一是强调活动的情境性,即身处“打铁”活动的情境之中;二是关注动作行为本身,即“打铁”这一具体实践行为。而正是二者的共同作用,个体逐渐成了某种特定类型的人。
综上所述,学习者身份可理解为是,“个体在学习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对自我作为学习者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它是个体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中实践参与及主观学习经历/经验持续不断地建构的结果。”[14]基于学习者身份这一概念,个体可以对学习中的“自我”问题进行反思,如“学习的意义”“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学习中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以及“学习经历和‘成为’(becoming)的关系”等。由此可知,学习者身份既是文化历史学中的一种符号工具,又可被作为一种向内关怀自我的技术。
三、自我技术关照下的学习者身份形塑
学习是一个主体性的参与过程,学习不仅需要充分地关怀学习者的处境(position)、个性(dis⁃position)以及身份(identity)[15],同时更应考虑到学到的东西对于学习者而言有什么意义,这与福柯所指的“关心自己”具有紧密的内在一致性。在关于学习和身份的关联上,莱夫和温格(Lave&Wenger)认为,学习和身份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16]换而言之,学习的过程也即身份形塑的过程,学习的结果则指向了人的改变和形成。在福柯的语境下,学习者身份的形塑实际上也蕴含着“自我成为学习主体”这样一种经历。福柯认为生活技巧、生存技艺及生活风格等都属于自我技术范畴,具体如古希腊时期的节制、记忆、反省(自我检查)、沉思、沉默及倾听他人[17],罗马帝国时期的锻炼、沉思、思想考验、良心检查、对表象的主控等。[18]而后期,福柯在自我技术之实践探究上略有不同,此处以福柯《自我技术》一文中所提到的“自我技术”为依据,并综合其他研究者的分析进行整理,大致归结如下:
1.自我审查之技术及其启示
自我审查(examination of self),也即对良知的审查,意思是人如何看待自己。福柯认为自我审查有三种类型[3]:一是对作为现实的回应之思想的自我审查;二是有关规则与思想之关系的自我审查;三是有关隐秘的思想与内在的污秽之关系的自我审查。从福柯的三种自我审查类型不难发现,其所关注的焦点多趋向于思想层面,也即对良知的审查与拷问,这是一种“向内反求诸己”的过程,与“关心自我”形成了融洽的衔接。作为一种自我技术,自我审查对于学习者身份的形塑具有一定的启示,因为身份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认识自我”及“关心自我”首先应考虑的,因此需籍由一定的自我审查技术来助其实现。在学习者身份的形塑过程中,自我审查可作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学习意义的审查。即学习或学到的东西对于自我而言有什么意义,与自我的认知、先前经验有何联系、如何联系。在学校教育情景中,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加工者”,而是主动的学习者,学生应学会主动思考和质疑学习材料、内容与自身发展的关联和意义。二是对学习情境的审查。通常,我们多倾向于关注正式情境下的学习,如发生在学校内、课堂上的学习,而许多其他有益的学习形式却被忽视了,如日常生活中、同伴交流中、科技项目或休闲娱乐等非正式学习。实际上,非正式学习对于学生人格之健全发展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学生需保持一种高度的学习敏感性,将非正式学习中的情感、信念及意义等也纳入自己的经验范畴之中。
2.倾听之技术及其启示
福柯认为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渐渐形成了一种寂静的文化和倾听的艺术。福柯指出,倾听(或聆听)是一门关于认识自我的重要自我技术,他在阐释倾听时引用了普鲁塔克《关于聆听演讲的艺术》一文中的洞见:“倾听的艺术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在倾听中你才能辨别真伪,人必须学会倾听的理性。”由此可见,倾听对于获得真理至关重要。在学习者身份的形塑中,倾听也可作为一种有益的自我技术,而这种自我技术正是以对自我内在声音的倾听为内核的。例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遭遇不同文化和权力的相互角逐,如家庭的期望、教师的权威、学校的要求等,学生无形中处于一种相对弱势和不平等的状态,学习或对某类知识、规范的习得并非他们的自主意愿,而是外界权威干预的结果。由此,他们内心的声音受到了忽视,内在自我与外在表象实际处于一种割裂和分离的状态,从而致使学生难以获得对于学习意义的感知与认同,也难以实现学习者身份的形塑。因此,作为学习者的学生,应该掌握倾听的技术和艺术,倾听自己内在声音的表达,尊重自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倾听的技术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技巧和学习方式,有利于学习者主体价值的彰显与形成。
3.质疑之技术及其启示
所谓质疑就是不断地对真理和秩序,以及各种道德规范提出疑问,使惯常的规则和样态成为问题。通过质疑,可以思考我们是谁,我们能够或如何做些什么,从而使得自由主体的实现成为可能。福柯不断地思考质疑所需的条件,即个体如何才能更好地对自身的存在提出质疑,也即“主体是如何建构”的问题。在教育层面,“质疑”作为一项关键的品质备受关注,美国21世纪技能联盟(Partnership for 21 Century Skills)所提出的21世纪技能将“质疑”(或批判性思维)视为学习和创新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也明确将批判质疑视为学生的关键品质之一。那么,就学习者身份的形塑而言,哪些质疑的技术可以利用或如何质疑、质疑什么。具体到学生的学习实践中,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是要敢于质疑学习过程中的权威,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即是一种体现。质疑的过程是将自己的疑惑和“无知”敞亮于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及认识自我。二是对学习文化环境、社会规范、学习权利以及学习内容和方式等的质疑,不墨守成规、不人云亦云,避免被一些习以为常的现象所遮蔽。例如通过对学习内容的质疑,学生能够意识到所学之物的合理性及对自我的意义;通过对社会规范的质疑,学生能够领悟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等。
4.写作之技术及其启示
福柯非常注重写作(亦可称“书写”)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写作是自我技术的一种方式,有利于个体关注自我、塑造自我。写作是为了记忆、回忆和审查自己的行为和规则。福柯于1983年发表了“自我书写”一文,他认为写作是探索观念的一种形式,写作使得反思越来越深入和细致,自身的经验在写作的美德下得到了巩固。写作时常关联着“沉思”,与思想本身的训练紧密相关,写作将那些被公认的、真实的话语塑造为理性的行为准则。[3]通过书写,人们可以对自己过去的经历进行审查,并且认识到自己是历史探究的主体。例如,籍由叙事风格的自传,个体能够重组其个人经验,厘清自我思想的发展轨迹和转变过程。书写作为一种有效的自我技术在个体主观学习经历的建构方面也颇具潜力。一方面,通过写作(如学生日记),个体的学习经历能够以回忆的方式得以保存和记录,学习者可以清晰地发现自我学习经历中的主要影响因素,思想、情感及个性的转折点,重要人物和关键事件等;另一方面,书写能够呈现出一幅清晰的自我图像和画面,并以文本文字的方式描绘和呈现出个体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其有助于学习者充分认识自我,从而改变自我。
5.练习之技术及其启示
福柯认为练习(也被称为“自我修炼”)是一种主体化的过程,它包括一整套实践活动,人们可以借此获取、同化真理,并将真理转化为一种永久性的行动准则。[3]练习赋予了个体应对问题和话语的能力。从福柯“伦理自我的形构”观点来看,个体需要在一系列练习中提升或转化自我,练习不仅意味着习惯性的行为,更蕴含一种自我转化的修习活动。福柯认为“默想”和“自我训练”是练习的两种基本方式,默想是将自己置身于一种虚拟的、想象的情境当中,以测试自己对事态的回应。而自我训练发生于真实的情境当中,如练习控制自己的欲望,练习某项技术和技艺。而在学习者身份的形塑方面,练习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身份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对自我某些知识、技能、情感、规范、意义、信念的认同予以持续不断强化。学生要形塑作为学习者的身份,练习也是一项关键的自我技术。例如当面对技能或程序性知识时,适当的练习是一种必要的学习方式(这与行为主义学习观也甚为配合),通过练习,学生能够将技能内化为自身的一种行为或动作方式。同样,当面临其他如信念、规范等学习内容时,练习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其促进了学生对该规范的理解与认同,并使之在思想层面产生效果。
6.越界体验之技术及其启示
福柯认为体验也是形塑主体的一种方式,并将体验视为一种能够且必须被思考的事,一种经由真理游戏而被历史性建构的事。[19]而在体验之中,他尤其关注越界体验和行为,所谓越界体验(transgressive experiences)实际上是一种打破固有传统、规范和惯习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福柯强调越界是生活本身的基本需求,通过越界能够体验个体试图来突破既存的范畴和分类,进而改变自我的认识或感觉等。[20]而学习是一场探索未知的旅程,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学生具有一种越界的体验和意识。通常固有的认知方式、行为模式、规范和信念等使得学生处于一种相对“安全”的舒适地带,而当学生面临新的学习材料、学习环境时,尤其是与已有经验完全相左的时候,个体会感到不适,甚至会产生一种威胁的体验。在本能的驱使下,学生往往会拒绝或抵制新刺激带来的不舒适感。然而,有效的学习恰恰发生在与新事物、新经验的接触之中,这就迫使学生不得不跨越已有传统,打破固有认知习惯,寻求一种新的越界体验。而身份的改变过程总是与学习的轨迹甚为相似,从一种旧有的状态过渡到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状态,而此“过渡”的顺利实现,需要学习者主动寻求并建立多次新的越界体验。对于教育实践而言,这就需要鼓励学生养成“富于挑战、敢于冒险、乐于探究、勇于尝试”的思维习惯,增加学生越界体验的机会。
上述自我技术在学习者身份的形塑中是互为补充、相互配合的,共同为塑造主体、改变自我而助力。此外,福柯还提到了坦白之技术(confes⁃sion)、说真话之技术、默想之技术、节制之技术等,这些技术都能够以不同的视角及方式对自我的改变及学习者身份的形塑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