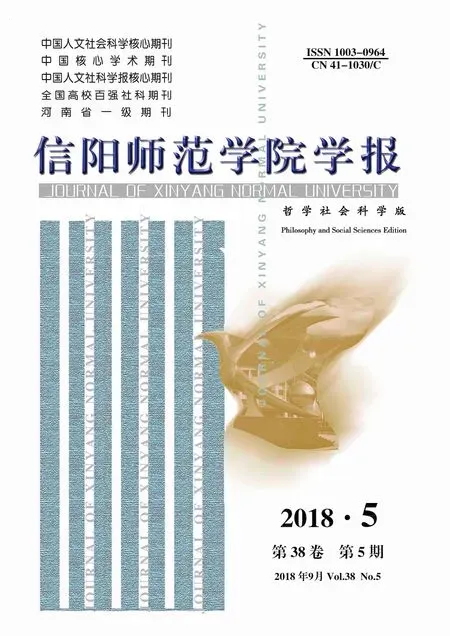“史真”与虚构的界限:17世纪小说观念之变
——以谢小娥故事的“文学—历史”流转为中心
王委艳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谢小娥故事的最初版本是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谢小娥传》,在流传中出现多个版本,历史、小说、杂剧均有。在故事的流转中,文学版本与历史版本显然属于不同的文类系统,其“文学—历史”流转,及故事在不同版本中的细节变动,正好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虚构”与“史真”(历史真实)小说观念提供例证。从对谢小娥故事的文学与历史版本的流转分析中发现,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念与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关联,揭示这种关联可以寻觅到中国小说的深层结构图式。这既是明清通俗小说共同拥有的一种深层结构,也是17世纪通俗小说理论的主要支点。
一、故事的流转与演变
谢小娥故事首先出自唐李公佐《谢小娥传》,唐代牛僧孺《玄怪录》卷二《尼妙寂》篇[1]23与此故事略同,但主人公改为叶氏。宋代《太平广记》卷一二八、四九一分别收录《尼妙寂》和《谢小娥传》,后又被收入《新唐书》卷二五〇《列女传》第130[2]5827。明代凌濛初将其改编为话本小说《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清代王夫之将其改编为杂剧《龙舟会》。
谢小娥故事流转最多的是在“小说”序列中,《新唐书》将其收入《列女传》时做了大面积修改,从文本形式分析,叙述视角更加客观,同时删除一些明显的虚构情节,使一篇传奇转变为历史。谢小娥故事收入《新唐书》卷二五〇的《列女传》第130中“段居贞妻谢”条。全文简略直陈,只有364字,照录如下:
段居贞妻谢,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贞本历阳侠少年,重气决,娶岁馀,与谢父同贾江湖上,并为盗所杀。小娥赴江流,伤脑折足,人救以免。转侧丐食至上元,梦父及夫告所杀主名,离析其文为十二言,持问内外姻,莫能晓。陇西李公佐隐占得其意,曰:“杀若父者必申兰,若夫必申春,试以是求之。”小娥泣谢。诸申,乃名盗亡命者也。小娥诡服为男子,与佣保杂。物色岁馀,得兰于江州,春于独树浦。兰与春,从兄弟也。小娥托佣兰家,日以谨信自効,兰寖倚之,虽包苴无不委。小娥见所盗段、谢服用故在,益知所梦不疑。出入二稘,伺其便。它日兰尽集群偷酾酒,兰与春醉,卧庐。小娥闭户,拔佩刀斩兰首,因大呼捕贼。乡人墙救,禽春,得赃千万,其党数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状。刺史张锡嘉其烈,白观察使,使不为请。还豫章,人争聘之,不许。祝发事浮屠道,垢衣粝饭终身。
下面从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和情节改编、叙述主题几个方面对谢小娥故事的不同版本进行分析。
(1)叙述视角。在李公佐传奇小说《谢小娥传》中,作者采用的是全知视角, 用史传笔法来叙述故事。故事开头即介绍谢小娥姓氏、籍贯、家庭情况,以及故事情节过程。再介绍“余”的情况,即以第一人称叙述其帮助谢小娥解谜的过程,用全知视角介绍谢小娥复仇经过,再转入第一人称叙述“余”和谢小娥的邂逅,最后运用史传笔法“君子曰……”模式对故事进行道德总结。可以说,全知视角和第一人称叙述是李公佐版本的主要叙述特征。这种叙述视角更容易宣扬既定主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李公佐在小说中以“余”的身份成为一种“戏剧化”的存在。它给人一种真实感。
在《新唐书·列女传》中之“段居贞妻谢”,则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非常简明扼要叙述一个孝妇节妇的故事,甚至省去了故事的主要情节,如谢小娥父、夫托梦情节,因为这一情节很明显虚妄不实,不符合史书体例,但将谢小娥作为一个孝妇节妇形象加以描写却符合主流价值规范。
在《玄怪录》之《尼妙寂》中,采取的是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在介绍完托梦、解谜后,叙述者并没有继续叙述妙寂的复仇过程,而是写在泗州普光王寺,妙寂与李公佐的偶然邂逅,借妙寂之口,将她的复仇过程讲给李公佐听。这是一种较少的叙述方式,在古代小说中非常具有价值。这种限制叙述方式使故事更具有传奇色彩,同时,也更具有主观性。
凌濛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且叙述者表现出对故事较强的控制力,使故事的运行服务于“奇”的创作理念和孝妇节妇的主题。王夫之《龙舟会》是杂剧,视角因舞台角色变化而更加游移多变。
(2)叙述时间、叙述情节改编。李公佐传奇小说《谢小娥传》的叙述时间采取的是顺时序,即按照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新唐书》也是按照顺序记录。这种叙述方式给人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对于追求真实性文本来说是必要的。《尼妙寂》采取顺序+倒叙的叙述方式,时序安排比较精心别致,这与故事的限制视角有关。凌濛初的《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和王夫之的《龙舟会》也是按照顺序叙述故事的。
在情节改编方面,《新唐书·列女传》中“段居贞妻谢”对谢小娥故事进行了大量删节,甚至对托梦、解谜、复仇的关键情节也惜墨如金,这符合史书客观化叙述要求,客观化可产生真实效果。
凌濛初的《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改编较大,细节较为丰满,增加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对话。在李公佐的《谢小娥传》文本中,有李公佐参与的故事情节的篇幅占据全文字数一半,而在凌濛初版本中,李公佐则退居次要角色,李公佐的出现是为推进故事发展服务的,其参与的情节所占字数比例大幅度降低,而对谢小娥复仇经过做了大肆渲染,使开篇“千古罕闻”之意在故事中有一个充分的展开。
王夫之杂剧《龙舟会》情节更为丰满,因为要舞台演出,设计了更多适合舞台表演的情节,如托梦一折,增加了小孤神女这一角色,使谢小娥父、夫托梦更具戏剧性,更适合舞台表演,且可借此抒发王夫之对明清易代的悲愤心态。
(3)主题倾向。文本改编成功之处关键之处在于视角、时间、情节的改编均以主题为中心,即主题决定了改编的方向。
谨以一处细节在不同版本中的不同表现为例来说明主题倾向对改编的影响,即谢小娥之父、之夫为何不直接托梦说出强盗姓名,而留下一个哑谜?在李公佐《谢小娥传》和《新唐书·列女传》的“段居贞妻谢”中,作者均没有说明原因。在李公佐版本中,叙述非常简洁:“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3]287而在《新唐书》中叙述更为简单:“转侧丐食至上元,梦父及夫告所杀主名,离析其文为十二言,持问内外姻,莫能晓。”[2]5827且这两个版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宣扬孝妇和贞节观念,《新唐书》把这一故事归入《列女传》中。也就是说,李公佐版本和《新唐书》版本,并不借某一细节来传达主题,而是直接宣扬这一故事是何种主题。
以上两个版本谢小娥之父、之夫托梦的时候不直接说出强盗姓名,而在《尼妙寂》《龙舟会》中则均有说明,这种差异体现了作者不同的创作主旨。
《尼妙寂》虽然把故事的主角由谢小娥改为姓叶,女主人公在报仇之后,遁入空门,法名妙寂。除了姓名改变外,其余皆与谢小娥故事同,因此为同一故事。在《尼妙寂》中,妙寂之父自己说出为何不直接说出强盗姓名的原因:“吾与汝夫,湖中遇盗,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许复仇,但幽冥之意,不欲显言,故吾隐语报汝,诚能思而复之,吾亦何恨!”[1]23很显然,在《尼妙寂》中给出的理由更富神秘色彩。这与志怪小说集《玄怪录》主旨不无相关。
在凌濛初小说中却对谢小娥之父、夫为何不直接说出强盗姓名的原因不置一词。很显然,凌濛初并没有想在这一细节上做文章。在小说入话中,有这样一段话:“而今更说一个遭遇大难、女扮男身、用尽心机、受尽苦楚、又能报仇、又能守志、一个绝奇的女人,真个是千古罕闻。”这是凌濛初改编谢小娥故事的根本所在,即“报仇”“守志”“绝奇”,前两者是宣扬道德,后一个是赞扬谢小娥,也同时宣扬故事的“奇”。
《龙舟会》中这一情节更富有戏剧性,作者虚构小孤神女让谢小娥父、夫托梦给谢小娥,因她“虽巾帼之流,有丈夫之气,不似大唐国一伙骗纱帽的小乞儿”。当谢小娥父、夫问小孤神女为何不直接说出强盗姓名时,小孤神女给出了两个原因:“一则未能明正天诛,一刀还他一刀;一则显不得你女儿谢小娥孝烈,替大唐国留一点生人之气。”然后王夫之还不忘借小孤神女之口对时局和依附清廷的明臣进行旁敲侧击:“做贼称雄也枉然,不见安禄山建国号称天,只羞杀王维与郑虔(此二人均被安禄山授伪职—原注)”[4]120-121。王夫之的改编改变了谢小娥故事的走向,使其融入了更多的家国情怀,并寄托了其在明清易代之际对某些事、某些人的看法。可以说寄意深远,这与其他谢小娥故事宣扬孝、节观念有很大不同。
根据上述谢小娥故事几个版本的分析,可以发现,文学版本与历史版本之间基于叙述目的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叙述策略,也就是说,文学版本更加注重叙述视角、时间、情节的布局安排,并使之服务于不同的主题。而在历史版本《新唐书·列女传》中收录谢小娥故事之前,主题已定,即“烈女”,因此对于一些虚构性情节进行了大面积删减,尤其是为了使故事更具史实性,还将李公佐在《谢小娥传》中上旌表免谢小娥死罪的浔阳太守张公改做张锡。张锡在《旧唐书》有传,且官至宰相。“张锡的仕宦生涯主要在武后、中宗两朝,《谢小娥传》的故事发生在宪宗元和年间,两者已相差近百年,张锡怎么能够嘉奖谢小娥呢?”[5]32《新唐书·列女传》将影响真实的故事情节减到了最低,对托梦、解谜的具体细节进行了删减以服务于史书对真实性的要求。但这里依然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小说《谢小娥传》如何堂而皇之地进入《新唐书》的?文学“虚构”如何成为“历史”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成为历史?而《谢小娥传》的改编进入17世纪又有了新的变化,凌濛初的《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与王夫之的《龙舟会》,虚构成分更多,且在故事的传奇色彩上下足功夫。在凌濛初时代,小说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冯梦龙“事赝理真”和凌濛初“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之“奇”的倡导,已经明确了小说的虚构特性,这与《新唐书·列女传》及之前的时代小说观念有了巨大变化,谢小娥故事最终回归文学。
二、“虚构”成为“历史”的可能性
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与今天有着巨大不同。汉代思想家桓谭在其论著《新论》中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6]这是我国最早和最切近今义的对小说的正面评价。《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列为一家,指出: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或如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里的“小说”是指稗官采集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很显然,“小说”之“小”是和正史相对,并不含贬义,而且有“一言可采”,即作为正史的补充而存在。很明显,这里“小说”概念并不与“虚构”相连,这与西方的“fiction”有本质不同。班固以后直到清代,都把“小说”列为“子部”或者“史部”,这都与虚构没有关系。
唐代刘知几认为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7]246,把小说的功能列为正史的参考。“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己”[7]246。这里明确指出“小说”即为“补史”。“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7]247,即使“小说”也应该“纪实”。到明清时期,小说作者依然延续“补史”观念:“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8]878“若余之所好在文字,固非博弈技艺之比。后之君子,能体予此意,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9]109
“补史说”观念一直困扰中国古代小说作者,直到17世纪冯梦龙主张“事赝理真”、袁于令主张“传奇贵幻”,才打破此观念,使“虚构”理念堂而皇之地进入小说创作中。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由于古代“小说”观念与“虚构”并不构成对等关系,因此,就为“虚构” 理念进入历史提供了可能性。事实上,古代史书采用野史资料并不鲜见,“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7]108。
清代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观点,而六经之首的《诗经》即为文学作品。章学诚提出史家所具备的素质:“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9]205才、学、识,具备三者即为良史。很明显,章学诚把“义”看作史之首,“事”以彰“义”,“文”以纪事。这是一种典型的演绎史观。章学诚还提出:“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9]206“至文”在于“气”“情”。章学诚把人之“气”“情”看成是史之“至文”的关键因素。既然如此,那么就很难排除主观性。
事实上,中国古代正史除从“小说”中采集材料外,合理虚构也极其常见,尤其是人物传记。《史记》对于五帝记载,基本来自传说。《史记·殷本纪》描述契的出生:“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秦本纪》云:“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即使到清代张廷玉修《明史》亦如此,如《明史·本纪第一·太祖》云:“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讳元璋,字国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生四子,太祖其季也。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此描述与志怪无异。不但如此,人物传记中的一些对话等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合理虚构。因此,可以说,历史虽以“真实”为主,但不乏虚构。那么,虚构在何种情况下才能成为历史呢?“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写作和小说写作可以被视为两种不同的叙事话语,但二者的界限有时很难找到。一个非官方的事件记录会显得如此‘真实’,如此有道德意义,它因此会被吸收进官史之中。反之,官修史书中的人物和事件也会变成虚构的通俗叙事中的材料”[10]151。中国历史和小说之间长期以来形成了这种互动关系。
决定历史的不光是历史本身,还包括政治和道德。“历史研究最终是由政治、道德、‘非历史’的标准所决定。史家的最高艺术来自于‘笔削’,那是孔子在公元前6世纪时编订《春秋》时所采用的方法。后代史家的任务就是模仿这一最初的被用以编辑过去事件的‘历史—政治’行为”[10]67。章学诚把“义”放在“事”之前,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反映。《易经》:“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 言、象、意系统是中国符号学思想的起源,所谓得意忘言、得鱼忘筌,其核心指向为“意”,而表达“意”的过程则可以忽略不计。换句话说,所有的“过程”均是“意”的演绎。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关键是“义”,故事只不过是“义”的一种演绎。《春秋》微言大义,所谓春秋笔法,即以表“意”为核心。因此,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开篇往往展现一种宏阔的历史画面和所要表达的“大义”,然后才因文成事、以事表意。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古典小说的深层结构和情节布局,如话本小说,其典型性主题直接影响其故事走向,有时候为了控制故事走向和故事进程,不惜采取非现实情节来改变故事运行方向。可以说,以表意为核心的哲学传统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合法性提供了合理框架。
虚构成为历史,需满足如下条件:一是人物政治等级极高、不容置疑,如帝王将相;二是所欲传达道义不疑;三是形式“史真”:史书文体可以决定写作,也可以决定阅读;四是合理虚构。很明显,谢小娥故事能够被正史采信,满足了第2、3、4的3个条件。
总之,中国正史不乏虚构,满足一定条件,虚构就会成为历史真实。西方《荷马史诗》的历史化也是如此。虚构和“史真”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就是说,中国正史本身已经包含了其一贯反对的虚构因子。17世纪通俗小说理论的发展基本是在虚构和史真之间摇摆,并最终走向“事赝理真”的艺术真实。这是17世纪通俗小说的基本理论走向。
三、写作与阅读:意义建构的多重文化范式
司马迁《史记》所形成的“史传”叙述传统一直影响古代小说的叙述方式。无论是文言小说系统还是白话小说系统,以“纪传体”模式进入叙述,使故事至少从形式层面呈现“史传”效果,并因此获得某种“真实”幻觉是小说作者的追求。从上述对谢小娥故事文学与历史差异的分析可以看出,李公佐的《谢小娥传》之所以能够进入正史。首先,源于其“纪传体”文本形式,以及以第一人称“余”亲历叙述所带来的真实感觉。我们无法考证谢小娥故事是否真有其事,但里面的两个关键情节却毋庸置疑是虚构的,即托梦和解谜,正是这两个关键情节推进了故事发展,谢小娥的孝妇节操得以凸显也来自于此。其次,《谢小娥传》还力图倡导正统道德:即孝妇节妇的操守。这也是凌濛初改编后宣扬的最主要的观念。再次,由于《谢小娥传》对于女性孝道节操的宣扬,使托梦、解谜这些明显的虚构变得合情合理,或者说可以忽略不计。《新唐书》正是以选择性忽略的方式把这两个关键情节进行了闪烁其词的压缩,但并未回避,因为没有它们就无法完成孝妇节操的道德宣传。《谢小娥传》因为具备了“纪传体”几个关键要素,使其穿越“虚构”与“史真”的界限而进入历史。“这篇故事看起来是真实的,叙事者调动了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篇小故事。文本提供了许多‘准确性材料’:具体的时间、真实的地点、主人公家庭背景的细节、叙事者作为参与者和见证人等。另一个支持它成为历史真实记录的事实是结尾的评论”。“通过编入正史,小说实现了它所能扮演的最高角色。经由选择和编辑的程序,小说从卑微的‘小家之言’、非官方历史、补史史料成为历史本身”[10]99。
事实上,作为最高文类规范的“纪传体”文体模式是多种文类的追慕目标,离文类中心越远,其慕史倾向就表现得越强烈。“在文类等级森严的文化中,这种文类模仿,会延续很长时期。某些文类等级低,是文化结构决定的,长期难以变动。因此对某种高级文类的企慕最后成为这种文类中一种必要的表意范型,用以在文化中取得存在的资格”[11]194。中国小说历来地位低下,一直徘徊于“补史”“史之余”“有可观之辞”“有一言可采”的边缘地位,作为历史的补充获得存在资格。诗文亦如此。“如果高级文类都受到史书模式的偌大压力,白话小说那样的低级文类,追慕史书范型几乎是强制性的了”[11]195,并且“慕史”成为小说家的自觉追求,如褚人获在《隋唐演义序》中指出:“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账薄,斯固然矣。第既有总记之大账薄,又当有杂记之小账簿。此历朝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所谓“大账薄”“小账簿”,即把历史演义直接作为史书看待。赵毅衡总结了中国古代小说追慕史书范型的几个叙述学特征:一是非人格化超客观叙述;二是全知叙述角度;三是时间的整饬性[11]203-204。赵毅衡是站在文本形式的角度总结的,从内涵角度来说,还应该包括道德正确性和意识形态的正统性。
小说文本《谢小娥传》的文体演进历史化过程说明,小说文本的慕史倾向和体裁的史传范型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一种体裁的形成既作用于作者,又作用于读者,而这种双向限制作用才使交流的有效性成为可能。中国古代小说长期维持小说文体的“史传范型”,使小说形成一种“史真”叙述效果,虽然这种效果随着小说创作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写作和阅读的“虚构事实”,但不可否认,这种范型带来了“史真”效应,并使其长期影响小说虚构写作的发展,以及影响读者的阅读心理,即他们总是追求一种“真实”效果。这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表达方式和接受方式,并直接影响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传范型”已经构成中国小说的“顺从规范”:
顺从规范迫使叙述稳定其各种程式,以保证读者也加入顺从规范。因此,规范顺从模式也必然是意义的社会共有模式。这样的叙述文本,追慕特权文类范型,与文化的意义等级保持一致,从而加强了这个文化结构。特殊的是,白话小说从文化的下方加强文化结构,它们使社会的下层共享这个文化的意义规范,从而保证了集体化的释义。用这种方式,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者有效地把本属亚文化歧异的中国小说置于中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11]206-207
鲁晓鹏将中国古代小说的阅读分为两种模式:历史模式和寓言模式[10]96。所谓历史模式和寓言模式,有两方面内涵:一是作者在何种体裁序列中组织文本?二是接受者在何种体裁规范下接受文本?即任何文本都会遵循一定的逻辑规范,这是保证写作与阅读符码和释义方向的关键问题。《谢小娥传》被写入信史与其本身的“史传范型”的文体和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是分不开的,虽然不可排除写作和阅读的“寓言模式”,但纪传体文体规范和小说的“补史”“一言可采”等观念也起到了关键作用。鲁晓鹏也承认:“中国叙事确实是一种由历史、意识形态和形式因素多元决定的文本。人们会注意到在中国小说中,或多或少都有以下现象:故事框架与故事本身的不协调,几种不同语言(文言、白话、方言)的并存,情节的章节构成,不同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杂糅,以及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编写、采纳和杂交所造成的语言和文学上的不平衡等。”[10]150这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状况,形成了混合多种话语模式的独特表达方式,这种混合保证了小说这一地位低下的文类在中国文化序列中获得一种生存机会,同时也使得持不同文化立场的人各取所需。上述谢小娥故事的改编情况即是明证。陈平原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概括为“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12]219,赵毅衡把中国小说的文化范型分为“史传范型”“说教范型”和“自我表现范型”[11]193-227,韩南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语态分为“评论式”“描写式”和“表达式”[13]6-7等。学者们的总结各有不同,这都源于中国古代小说所呈现的多重文化景观。
在17世纪通俗文学思潮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小说理论的形成和理论自觉。虽然鲁迅先生说唐传奇是“有意为小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有一变,虽尚不离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4]44。但小说理论一直滞后,直到17世纪,小说评点和序跋等小说理论形式的出现。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所表述的理论思想,“虚构”这时才真正和“小说”联系起来,冯梦龙“事赝理真”的理论倡导和文本实践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重要的一页。正如凌濛初对《谢小娥传》的改编一样,无论是文本形式的俗化还是细节描写、语言方式等都获得了突破。可以说,《谢小娥传》真正是以小说的方式被接受和改编。王夫之在明清易代之际又将《谢小娥传》改编成杂剧《龙舟会》,虚构成分更多,并且从思想上改变了小说的释义走向,呈现了王朝易代之际文人的忧虑和思考。可以说,没有17世纪人本主义思潮在通俗文学领域的贯彻,没有小说虚构的倡导,也许王夫之对此的改编就会是另外一种状况。
明代中期以后,人本主义思潮兴起,思想界对宋代以来的程朱理学进行质疑。而王阳明及其追随者倡导的心学流派,以其推崇的自然人性、满街圣人、民本思想等对中国传统哲学产生重大冲击。人们开始思考“存天理,灭人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国小说创作也由笔记、野史、志怪等转向通俗。与思想界对应,中国经济方式,尤其是东南沿海雇佣劳动和市场经济的出现,市民阶层的壮大,读书人从业方式多元化,所有的这些因素促成了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的大变革。进入17世纪,明朝统治内忧外患,社会动荡,各种思潮泛滥,表现在小说领域,就是通俗文学思潮的兴起,并以大量的创作业绩和理论表述而达到一时之盛。“谢小娥故事”在17世纪之前以笔记、野史、传奇、正史等文类流转,无论正史还是补史,基本可以认作“史传”范畴。进入17世纪,凌濛初改编成话本小说,采取虚构方式对故事进行了大面积改写,而王夫之的《龙舟会》甚至改变了故事历来的释义方式和故事意义。所有这些都与17世纪小说观念的变化,即小说与虚构的结合有着密切关系。
总之,《谢小娥传》在历史中的流转过程也是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过程,“史真”与“虚构”的界限其实是一种观念界限。虽然这种小说的历史观念和历史表达方式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生存赢得了空间,但同时也限定了其发展。这是一种观念化矛盾。直到17世纪,中国小说观念真正接近了小说文体的本质——虚构。中国古代小说才艰难地摆脱了历史观念的羁绊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