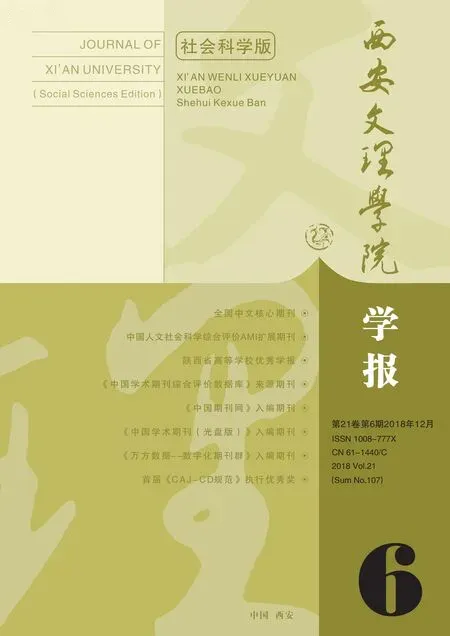《尼各马可伦理学》与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比较
姚丁月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27)
亚里士多德著名的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幸福是人的目的,而密尔的《功利主义》作为西方古典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其高明之处在于:在功利主义的约束力上,着重内在约束,并将这种约束放在人类社会情感的基础之上,因此《功利主义》也对幸福做出了相当有价值的论述。就著作本质而言,《尼各马可伦理学》是伦理学著作,《功利主义》是古典功利主义哲学著作,两者的论述方向莫衷一是,这体现在对幸福本质的探讨方面,促使幸福呈现出不同的理论面貌。
一、幸福本质问题
(一)《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于幸福本质的看法
《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始终强调“幸福是最高善”,而人类的一切知识、一切抉择莫不是为了追求这种“最高善”[1]。追求幸福的手段有很多,亚里士多德只着重提到了两方面——财富和德性。
财富是获得幸福的外在手段,属于外在的善。换句话说,财富对幸福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德性则是获得幸福的内部选择。“德性”是亚里士多德伦理观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它同时包括克制欲望的道德德性和理性指导的理智德性。基于以上分析,“德性”当然是实现“幸福”的重要选择。其次,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于“现实活动”的重视。从“德性”角度来看,道德德性需要社会风尚习惯加以养成,理智德性也需要教导方能实现,所以“现实活动”在德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为善所服务,我们这里谈的“善”与普通的善恶意义不同,我们不是狭义上的善,这种善要从广义上来理解。亚里士多德将“善”的概念以三个层次循序渐进:首先是外在的善,例如吃东西能使我们愉悦,吃东西这个过程让我们获得了快乐,通过外在的善,我们获得了我们想要的幸福。上升到下一个阶段的“善”是人自身追求的结果,通过实践最终获得的价值是我们所喜爱的,这就是内在追求的“善”。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想到是否有真正的善良,即那种本质的“善”呢?亚里士多德的“至善”最后登场,达到了最终的结果,他的“至善”就是幸福,我们对“幸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维度,我们追求的标准不同,自然“幸福”这个概念从古希腊到今天这种自身欲求而不是他物所能影响的目的之目的,所有人所承认的“善”才是普通的“善”,大众之善。
亚里士多德在书中第十卷开始讨论“幸福”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贯穿于他的整部书,幸福就是生活的好或者工作的得心应手。幸福是我们生活中最想欲求的、对于我们来说内心最想获得的归宿,它被作为人们一切实践活动的准则,生活的最终价值归属。
(二)密尔《功利主义》对于幸福本质的看法
身为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认为个人的幸福是他(她)自己的利益,同时集体的利益又称之为公共幸福[2]。但这种利益不只是一种而是人们对多种不同的具体目标,具体欲望的追求,比如金钱、名望、权利,只要能真正促进幸福的,这些行为就是幸福的。
从这一定义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密尔将幸福看作一个具体的整体,这其中可能包含着更加具体的东西,比如健康的身体、美好的音乐,它们都是幸福的来源。二是因为密尔定义的幸福是一种具体的存在,所以密尔眼中的幸福有高低之分—— 一种是本身就是所追寻的幸福的目的,另一种则是用作追求幸福的工具时,同样让人们获得了幸福之感。
他的核心思想是“功利”或者“最大幸福原理”,只要能免除痛苦和快乐,便是最值得欲求的。可是这也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伊壁鸠鲁认为理智的快乐要高于低级的感官快乐,心灵的快乐一直凌驾于肉体之上,心灵上是最永恒、最持久的,快乐是一个综合因素的过程,数量与质量的评判在考量的时候都要仔细寻味,人们往往过于重视数量而忽略了质量,往往质量的优势大于数量时,人们就不会那么在意数量上的多少了。当生活中积极主动的东西多于消极的东西的时候,期望的欲求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满足,心灵深处的情操,不为了那点可怜的私欲而抛弃高尚的、真挚的感情。世界上很多重大的灾祸,可以通过人类安慰沟通得以化解,所有最初的矛盾最终都会消失。在幸福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绝对牺牲自己的幸福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唯有牺牲自己的幸福,才能实现最高美德。
二、两者的差异比较(一)幸福是精神层面的还是实体
《尼各马可伦理学》认为幸福是至善,这就把幸福上升到灵魂的高度,成为一种纯粹的精神。具体说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幸福与德性相关,而德性(特指属于人的德性)是一个人良好并使得他的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这样看来,幸福仿佛近在每个人的身边,但实际上又虚无缥缈,每个人都很难切实地体会到它,或者说,很难笃定地向世界宣布:“他捕捉到了幸福的影子”。
幸福本是抽象的概念,行为实体的存在在密尔看来确实如此,快乐的行为方式是人最本质的内心诉求,追寻美德是为了使幸福可能也可以与德性相联系,但幸福一定是由德性做出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幸福就是那些让我们生活添色、心情愉悦的人、事、物。
功利主义的幸福更侧重于实体性,直接带给人价值的考量,这种考量为人们真正的欲求奠定了基础[3]。密尔在书中从功利主义的含义开始论述,他认为功利的幸福可以作为人们衡量的一个标准,约束人们的行为,他认为幸福不是肆意妄为,功利主义提倡的幸福观的真正目的最高的善,公众的幸福都是对他自己而言最大的善良,功利主义认为追寻美德是为了达到自身善的一种手段,这是其中一种手段,比如金钱是人们追求的本身,我们追求金钱是目的的一部分,权力、名誉也是如此,我们强烈欲求的东西是实体存在,本来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现在变成自己本身的欲求。
(二)幸福是否有高低之分
亚里士多德认为快乐不分高低,但幸福却有高低之分,幸福是一种高尚的快乐,低级的快乐不能称为幸福。消遣时光的快乐不被认为是幸福,这种活动得到的不过是肉体上的沉沦与享受、肉体的欢愉,严肃的工作比享受生活更好,闲暇的消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消遣不是我们的目的。好人对生活的追求都是德性的生活,德性的生活是比别的生活更为持久的、高级的快乐。最终,人的完善的、德性的福祉在于德性的实践活动。
亚里士多德又认为人自身是具有神性的,自身的神性是最高级的幸福。神性的品质优于德性的品质,我们身体别的部分的荣耀都不如神性的那一部分,虽然这是小的一部分,但却是人身体主宰最好的部分,他们总是按照神的关照,神所爱的状态,他们做的是最正确、最高尚的事情,这就是柏拉图“爱智慧”,有智慧的人是最幸福的人,神性的生活是最好、最欢愉的。
但密尔出于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考虑,将幸福区分成高低等级。高级的幸福显然是人们所诉求的东西,它们一方面可以直接作为幸福追求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可以当作追求幸福的工具,低级的幸福则只可以作为工具,只能用来追求幸福,而不能当作幸福的目的,比如:对身体的满足,只能成为获取幸福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幸福追求的根本目的。高级的快乐是自我救赎,当这种德行影响着你自己,密尔的“最终约束力”在不完善的世界里得到实现,他的核心愿想是“最大幸福原理”。功利的世界里是具备约束力的,外在约束力我们可以尚且不说,内在的约束力教育我们做一个好人,当违反道德义务、道德动机不良的时候,产生身心的痛苦,这种情感是综合的现象,很复杂,这种痛苦来自很多方面,道德义务观念的约束力会形成一种情感,只要我们做事违背了道德标准,内心自然会受到约束,感到懊悔,当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为了本心生活,形成良心的生活。
此外,密尔《功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对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关系的看法。《尼各马可伦理学》也许将幸福看作部分个人与社会的共有的德性追求,没有高下之分,但《功利主义》则认为只要能满足更大的利益需求,哪怕牺牲个人幸福也是可取的,这显然是两者幸福观不同的结果。
(三)幸福是否存在实践性差异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书中开篇讲技艺、技术,人们在开始实践的活动,开始有了心理的诉求[3]。他一直认为是某种快乐、财富、荣誉,使不同的人们对世俗的看法有所不同。《尼各马克伦理学》指出每种技艺研究过程,自身追求的完善,他更重视人类内心的道德追求,他想要实现为解释幸福对人们的价值,从概念着手,实现追求“至善”,从一个开始的生活中的例子,最终获得最高善,追寻美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高级的善才是我们真正欲求的,比如我们为了射击制造枪只,又为了战争,我们大部分时候是为了某种具体的活动,我们为了活动本身,通过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欲求的自足的实践活动是实践活动本身,在不断探索中追求内在品德。
亚里士多德一直认为实践的智慧和内在的德性是对于一个理性人的必需品,幸福是我们追求的真正的目的,幸福不存在于外在活动产物中,过程这些行为产生的伴生现象就是幸福,不然就没有办法到达至善[4]。内在的沉思,非逻各斯产物不会存在,当满足了逻各斯,幸福毕竟是实现自我的本身,为了灵魂中的欲求,幸福的终极性为其实践性提供了最好的源动力。
功利主义是以经验作为基础,考察人性并进行道德分析,人们以幸福和快乐作为追求的目的和最终动机,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中,功利主义认为集体幸福是个人幸福的集合,人们在判断或者考虑一个行为或者一个事项是否达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以此作为标准,来评估其是否符合功利主义的最为基本的原则和内核。并主张运用实际的利益作为检验标准来衡量一切的行为,并努力地解释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相关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对美德的追求和坚持是实现功利主义思想的前提,是幸福的源泉之一。
密尔的功利主义是以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和快乐为目的。目的与手段、道德与原则并重,密尔强调个人或集体的良好动机或者品质,是功利主义目的实现的必要条件,结合美德伦理特征,融合进功利主义伦理原则,密尔实践中的智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最终目的,这一目的包含了各方面的内容,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而全面的整体,有幸福、快乐、物质、地位、名声等等,为了实现美德追寻,诉求更稳固的幸福,实现实践的功利主义幸福观。
总而言之,《尼各马可伦理学》体现的幸福观与《功利主义》体现的幸福观虽然有所不同,互有差异,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拥有不平等的价值。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融合,指引着我们更加智慧地生活。
——读《论自由》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