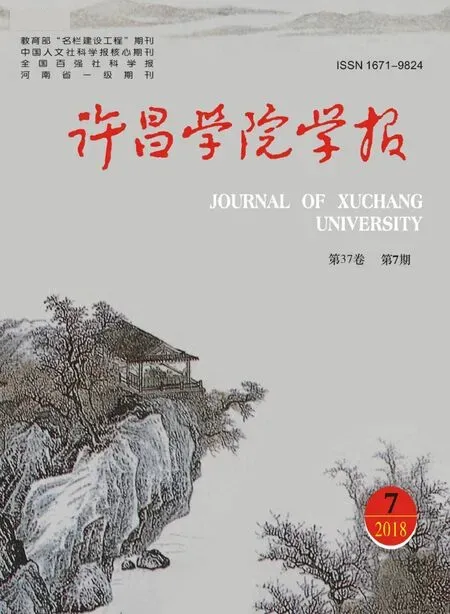东晋南朝侨民的社会融合
——以关中郡姓南迁房支为中心
宋 艳 梅
(常熟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是1966年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研究自杀率时提出的。但它至今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一致认同的清晰定义。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合是指不同个体或群体与某个群体的内聚性,表征的是个体在某个群体中的参与程度和认同程度及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1]。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社会融合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和谐的社会为目标[2]。
总体而言,对社会融合的研究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将某个系统作为整体,关注其社会关系或联系的总体情况,社会融合是影响整体和谐的重要因素;另一类是关注社会融合本身,其特征是考察个体或群体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联系,包括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商业组织之间的社会融合,也包括国内、国际移民与当地社会的社会融合,甚至还有国家之间的融合情况[3]。其中,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不仅是社会融合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移民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关注较多的是国外学者[4],而国内学者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关注的较多[5]。
我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陈寅恪先生说,“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不徙有事发生,徙则有大事发生,南北朝无一大事不与徙有关”[6]129。在大规模移民潮的影响下,侨民与本土士民的关系即侨旧关系问题构成东晋南朝社会的核心矛盾*朴汉济先生认为“侨旧体制”正是东晋南朝时期的社会特征,详参周伟洲:《“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论——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体系》,《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侨民与本土士民的冲突与融合深刻影响至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活动诸方面。侨民在寓居地域的社会参与、社会互动、融入地方社会的意愿和能力及本地社会对他们的接受程度影响着东晋南朝的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因此,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移民问题十分关注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作品如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收入《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胡阿祥师:《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但在诸多移民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多集中于对移民本身或将移民问题置于政治史、文化史视野下的一些讨论,关注侨民群体的社会生活,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他们在迁入地的社会参与、社会互动、融入地方社会的意愿和能力、本土士民对他们的社会接收,以及分析侨旧民众社会生活安定和谐的影响因素等的研究则还很少,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7]。据此,本文将从社会史角度运用社会融合这一社会学理论,对“关中郡姓南迁房支”这一侨民群体在江左是如何进行社会融合的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尝试弥补对士族群体的社会史研究,并进一步揭示家族发展与地域社会的密切关系。
关中郡姓是唐人对魏晋南北朝以来形成的姓族进行分类中的一类,以韦、裴、柳、薛、杨、杜为代表[8]5678。永嘉乱后,除少数家族成员南迁之外,他们大多选择留居北土,后历经胡亡氐乱、晋宋易代,居于北土的家族房支才陆续南迁,进而活跃于江左政治舞台。
东晋南朝的社会群体构成从等级上分士族、庶族两类,从来源上又可分侨人、土著两类,结合言之,东晋南朝社会群体由侨姓士族、侨姓庶族、本土士族、本土庶族四类构成。本文所论的关中郡姓,韦、裴、杨、杜在汉魏时期已是著姓大族,河东柳、薛在南渡时也已有强大的宗族基础和武装势力。但至东晋南朝时期,作为晚渡士族的他们,因为婚宦失类,被江左士人目为荒伧,沦为次等士族,已失去魏晋时期作为高门甲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与早渡江的侨姓高门阶层差异较大,社会距离较远。为了在异地维持家族利益、提高家族名望,他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融入当地社会,来寻求本土庶族、本土士族乃至侨姓士族的社会支持,获得士族身份认同。
一、关中郡姓南迁房支在乡里社会的社会融合
(一)获取乡民的依附和拥护
关中郡姓南迁房支的社会融合首先从居住地开始,除早渡江的河东裴松之父祖、京兆韦泓、京兆杜乂可能居于建康周围以外,于胡亡氐乱、晋宋革命之际南迁的关中郡姓房支主要寓居襄阳、寿阳等边境之地[9]。在这些地域他们逐渐成为乡里领袖,成为乡里社会的名望家族。如京兆杜恽拥有“乡里盛名”[10]220,京兆韦睿被称“乡望”[10]223,睿族弟爱“素为州里信服”[10]226,韦祖征“州里宿德”[11]985,河东柳庆远被举为“州纲”[10]182,等等。
乡里社会是一个地缘社会,地域认同是士人形成乡里社会的基础。关中郡姓作为移民群体,能在迁入地塑造社会名望,一方面与乡里社会的群体构成有关,另一方面缘于他们在地方社会的积极作为。就前者而言,襄阳地域先后接受了大量的雍、秦流民[9],与关中郡姓有着相近的地缘关系,甚至他们在原籍地可能就是京兆韦、杜等家族的拥趸。许多跟随关中郡姓一起南来的流民,往往成为士族豪强的部曲、宾客。在迁移过程中和择地定居后,这些依附民不断增多并强化着对这些南迁大族强宗地位的认同。因此关中郡姓迁移和落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以大族为核心的流民群体对其利益共同体进一步强化认同、形成地方乡里势力的过程。从这点意义上讲,关中郡姓在襄阳的乡里社会很大程度上是故乡乡里社会的移植。不过寓居地域毕竟有着来源复杂的众多流民群体以及当地原生的乡里势力,作为晚渡的异乡人,他们如何在迁入地获取声望?又如何声名远播?这与他们在乡里社会的积极作为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凭借武力才干为流民争取生活资源,保地方社会平安。襄阳所在的樊沔一带分散着许多蛮人,“襄阳以西,中庐、宜城之西山,皆蛮居之,所谓山蛮也。宋、齐以后,谓之雍州蛮”[12]3273,他们“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险”[13]2396。这些蛮人出山,与当地民众抢夺人口、土地。当地居民和外迁来的侨民自然也需要守卫、争取并扩充自己的实力,于是就导致了雍州地域上非常重要的生存斗争——伐蛮。在伐蛮斗争中,那些英勇强盛、战功赫赫的豪强便赢得声望,成为乡里民众、地方政府乃至朝廷统治者的重要保护势力和倚赖对象。河东柳元景年少时即多次随父亲伐蛮,在父辈称颂中以“勇”闻名,再经过人际网络的连接,口耳相传流入士人群体,后来获得荆州刺史、雍州刺史的数番征召[13]1981。
其二,招募率领部曲宾客,组建武装,在捍御外敌、安民保境中建立功业,取得声名。襄阳地处南北边境之地,常受战事纷扰,薛安都南迁后,仍“北还构扇河、陕,招聚义众。……复袭弘农……为建武将军,随柳元景向关、陕,率步骑居前,所向克捷……”[13]2216。久之,关中郡姓的武装力量军功频建,成为江左朝廷经营边事的重要倚重力量,自然也为乡人敬服。
其三,抚恤宗族乡民,为乡里所怀。关中郡姓特别重视抚恤宗族乡民,这一方面是这些世家大族对儒家伦理观念的继承和践行,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在异地培植宗族基础的努力。如《梁书》卷12《韦睿传》载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韦睿不仅对侄子及亲故散施财物,而且对族中宾客友朋、门生故吏等也多有抚恤。天监十七年,韦睿回乡任雍州刺史,客阴俊光路边迎接,韦睿饷其耕牛十头,并“于故旧,无所遗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与假板县令,乡里甚怀之”[10]224。韦睿兄阐,“所得俸禄百余万,还家悉委伯父处分,乡里宗事之”[11]1430。
其四,传承家学,以学识为乡人敬重。关中郡姓南迁后一方面凭借武事铺垫仕进之路,另一方面也非常注重家学传承。在雍、秦士人南迁之前,襄阳一带“率多劲悍决烈”[14]897,民众对礼仪经籍较为陌生。京兆韦氏西汉时期已为衣冠著姓,世代以经史为业,南迁后,仍抱持不辍。例如京兆韦睿“时虽老,暇日犹课诸儿以学。第三子棱,尤明经史,世称其洽闻,睿每坐棱使说书,其所发擿,棱犹弗之逮也”[10]225。其子韦棱、韦黯或“以书史为业”[10]225,或“少习经史,有文词”[10]226。韦睿孙韦载十二岁已熟通《汉书》,长大后,博涉文史[15]249。京兆杜氏亦为三辅著姓,西晋杜预注左氏,杜坦、杜骥在南,仍不忘传其家业,任青州刺史期间,齐地多习之[16]1843。河东裴邃十岁能属文,善《左氏春秋》[10]413。裴忌少聪敏,有识量,颇涉史传,为当时所称[15]317。
在乡里社会,文化学识是树立威信、提高名望的重要途径。“就微观而言,如果一个人在中国社会里能识字,那么对不识字的人而言,他本身就成了一个权威者,因为认识这种难认的图画式的方块字本身就意味着此人是个有文化、受过教育和知书达礼的人……如果谁能掌握和控制言语的表达、书写和传播的权利,谁就是该社会的权威”[17]127。因此京兆韦杜、河东裴氏所拥学识是赢得宗族乡人特别敬重的重要因素。
(二)与乡里士人的社会交往
除了个人才能对家族声望的构建作用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之间的交往、品评对个人乃至家族声名的塑造和传播也极为重要。关中郡姓在乡里的社会交往同样为他们获取仕途进阶和声望提升提供了有利机会。
第一,他们在乡里彼此称扬,相互品评,既利于获得辟召和举荐升迁的机会,同时又密切着相互间的社会关系、保护着他们的家族利益。萧衍镇雍州,问京兆杜恽求州纲,杜恽为之举荐柳庆远。韦祖征为“州里宿德”,河东柳氏家族成员也十分敬重他,“(柳)世隆虽已贵重,每为之拜”[11]985。京兆韦、杜本为同乡,在故乡已有密切交往,《宋书》卷65《杜骥传》:“北土旧法,问疾必遣子弟。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韦华。华子玄有高名,见而异之,以女妻焉。”移居襄阳后,两家仍然关系紧密,彼此联姻,下文将述及。河东薛安都南迁后,常年跟随柳元景出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薛安都从弟道生犯罪被秣陵令庾淑之鞭罚,安都怒欲杀淑之,路遇柳元景,元景责让安都,载之俱归[13]2216,2217。
第二,关中郡姓迁入异地,在联姻对象上也有着明显的身份性和地域性。据文献记载,京兆杜氏联姻家族五例,一例为河东裴氏(杜乂妻[18]2414),三例为京兆韦氏(杜骥妻韦玄女[13]1721,杜恽为韦睿姨弟[10]220,杜幼文为韦睿外兄[10]220),一例为太原王氏(杜龛为王僧辩之婿[10]644)。河东柳氏联姻家族九例,一例为京兆韦氏(柳仲礼为韦粲外弟[10]606),二例为河东裴氏(柳谐为裴蔼之内弟[16]1568,柳玄达与裴叔业姻娅周旋[16]1576),三例为郡望不可考的崔氏(崔灵凤女适柳世隆子[13]1941)、郭氏(柳世隆母郭氏[11]983)、阎氏(世隆妻[11]983),一例为皇族兰陵萧氏(柳偃尚长城公主[10]332),二例为皇族吴兴陈氏(柳盼尚富阳公主[15]129,柳敬言为陈高宗柳皇后[15]129)。河东裴氏南来吴裴房支联姻家族七例*裴松之一房南迁较早,居于京畿一带,较南来吴裴房地位较高。联姻家族有七例,一例为京兆杜氏(杜乂妻裴氏),一例为颍川庾氏(庾楷为裴松之舅父),一例为乐安任氏(任遥妻河东裴氏,裴子野于昉为从中表),一例为汝南周氏(周弘正妻裴子野女),一例为殷氏(裴子野祖母为殷氏),一例为魏氏(裴子野母为魏氏),一例为兰陵萧氏(裴氏适萧齐)。,一例为京兆韦氏(韦伯昕为裴叔业兄女夫[16]1567),二例为河东柳氏(柳谐为裴蔼之内弟,柳玄达与裴叔业姻娅周旋),一例为河东薛氏(薛安都女婿为裴祖隆[16]1354),一例为谯郡夏侯氏(裴植母为夏侯道迁姊[16]1571),一例为安定皇甫氏(裴植姑子为皇甫仲达[16]1570),一例为北地梁氏(北地梁祐为裴叔业从姑子[19]1653)。河东薛氏婚姻家族二例,河东裴氏一例(薛安都女婿为裴祖隆),安定皇甫氏一例(薛安都之女为皇甫肃兄妇[20]460)。京兆韦氏婚姻家族八例,一例为河东裴氏(韦伯昕为裴叔业兄女夫),三例为京兆杜氏(杜骥妻韦玄女,杜恽为韦睿姨弟,杜幼文为韦睿外兄),一例为河东柳氏(柳仲礼为韦粲外弟),二例为吴郡张氏(韦放以息岐娶吴郡张率女,又以女适张率子[10]424),一例为不可考的王氏(韦睿内兄为王憕[10]220)。据此可以看出,他们家族之间的联姻,同出关中郡姓的家族所占比例较高,彼此结成了较为紧密的婚姻圈,从而在地缘关系基础上通过联姻使血缘关系进一步扩展。联姻家族中的安定皇甫、北地梁氏等亦为寓居襄阳一带的豪族,他们同为迁徙家族,地位较低,与关中郡姓有较强的同质性,谯郡夏侯氏为南来吴裴氏所在豫州的同乡。至于韦氏与吴郡高门及柳氏与皇族联姻已是梁以后关中郡姓中央化后对社会名望的进一步谋求了。
不仅如此,韦、裴、柳、薛、杜氏互为婚姻,在血缘、地缘的双重结合下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在雍州,他们之间互相支持,重建家族势力,成为地方社会秩序的领导者;在王朝兴替、宗室斗争的政治、军事纷争中,他们往往共进退,通过联姻,进一步实现了家族声名的塑造和提升。如萧衍以雍州为根据地以梁代齐,韦、柳积极拥护;薛安都北归,裴祖隆、柳光世、韦道福等参赞其事;裴叔业举豫州降魏,柳玄达、柳僧习、皇甫光、梁佑、韦伯昕等姻族同乡集体而动,做出一致选择。
(三)地域认同意识的形成
关中郡姓在寓居地域的社会融合情况还可以通过家族成员的地域认同意识反映出来。东晋南朝,侨姓士族无论寓居何地都世代冠以北方郡望,以彰门第。关中郡姓六大家族虽在江左亦以京兆、河东标榜,但在努力维系家族利益的过程中对居住地和江左社会文化亦形成了一定的认同。如裴叔业盛饰左右服玩向北方族人裴聿夸耀在南方的富贵,轻鄙北方族人之俭陋[16]1565,表明他们对在南方的富贵生活颇为满意甚至得意。裴叔业房支濡染南风,北归后,裴植与母亲诸弟“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16]1571,反映出他们对江左生活习惯的认同。裴叔业一房后被世人名为“南来吴裴”[8]2194,以与北方宗族相别。京兆韦鼎陈灭后入隋,任职长安,却从未返乡,自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绝,自生以来,未尝访问”[14]1772,后在隋文帝御遣下始回杜陵。寓居襄阳的杜氏也逐渐与京兆本宗疏远,号“襄阳杜氏”[8]2423。与籍贯地宗族十分疏离的关中郡姓,在生活习惯和情感上更认同于数代寓居的襄阳以及江左社会。而且,他们仕职南朝期间在任职地域的选择上也多以寓居地为意。如柳元景助刘骏灭刘劭,军功显赫,刘骏问元景事平之后愿任何地,元景表示“愿回乡里”[13]1988。无独有偶,韦睿值齐末,“不欲远乡里,求为上庸太守,加建威将军”[10]220。柳元景侄庆远同样“重为本州,颇厉清节,士庶怀之”[10]183。表明他们对寓居地域已有较明显的地域归属感。
同时,坟茔地的选择是传统中国人乡土意识的最重要表征。魏晋南北朝时期迁移异地或任职在外的士人死后多采用归乡葬的方式回归故土家园。但南北隔绝既久,东晋南朝侨人回归北方故里安葬已不可能,乔迁地便成为入土为安的第二故乡。据《周书》卷42《柳霞传》载,河东柳霞任职雍州主簿时,其父卒于扬州,霞自襄阳奔赴,六日而至。虽路途遥远,风险重重,柳霞仍坚持“奉丧溯江西归,中流风起,舟中之人,相顾失色。霞抱棺号恸,诉天求哀,俄顷之间,风浪止息”。河东柳氏自元景、世隆、庆远等任职中枢后家于金陵,柳霞房支则留居襄阳,“独守坟柏”。梁末襄阳入北,萧詧于江陵称帝,任职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的柳霞辞别萧詧,曰:“陛下中兴鼎运,龙飞旧楚。臣昔因幸会,早奉名节,理当以身许国,期之始终。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太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独守坟柏。常诫臣等,使不违此志。今襄阳既入北朝,臣若陪随銮跸,进则无益尘露,退则有亏先旨。伏愿曲垂照鉴,亮臣此心。”遂留乡里。柳霞眷恋坟陇,凸显着他们家族对襄阳安土重迁的乡里观念。韦爱房支坟陇亦在襄阳,“遭母忧,庐于墓侧,负土起坟。高祖临雍州,闻之,亲往临吊”[10]226。
如此,关中郡姓迁居异地后凭借军功、学识、品行,依靠舆论和联姻逐渐取得了乡里社会对他们家族地位的支持,成为乡里社会认可的表率和社会秩序的领导者。相应地,他们也逐渐形成了对寓居地的地域认同,有一定的地域归属感,在乡里社会的融合程度较高。
二、关中郡姓南迁房支与江左上层社会的融合
东晋南朝时,南迁较晚的士人被目为伧人,为侨姓高门和吴地士族排斥,《宋书》卷65《杜骥传》载:“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关中郡姓南迁后便被视为荒伧,如京兆杜坦曾对宋文帝直言:“臣本中华高族,……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13]1721。弘农杨“佺期沈勇果劲,而兄广及弟思平等皆强犷粗暴。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18]2200。曾在魏晋时早已名著四海的河东裴氏在江左同样难与侨姓高门、吴地士族为伍,如裴松之年二十时拜殿中将军,因“此官直卫左右,晋孝武帝太元中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琊王茂之、会稽谢輶”[13]1698。尽管在魏晋时已属四海望族,但时过境迁,东晋南朝的江左社会名望已非他们所属。裴松之子嗣世传儒史之业,至梁世,裴子野仍“起身下位,身贱名微”,范缜奏请子野代任国子博士位,终因“资历非次”为有司拒绝[10]442。尽管关中郡姓在乔迁地的乡里社会可以树立威望,成为地方领袖,但为家族发展计,南迁后的关中郡姓必须在军功和政治权位的拔助下才能破除上层社会圈的藩篱,融入其中,获得本土士族、侨姓士族的社会支持,进而取得自我身份认同,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一)结缘宗室权贵
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政权的皇族门第不高,甚至出身寒素,且宋、齐、梁皇族同属移民,与晚渡的关中郡姓有着较强的同质性,同样为侨姓士族、本土士族所不齿。南朝朝廷重视雍州、豫州等战略要地,多派宗室王镇守经略,于是侨居在当地的关中郡姓常常是他们积极征召拉拢的豪族势力。史籍记载中可以看到关中郡姓较多家族成员的起家官即于镇守本州的宗室王府任职,他们逐渐围绕在宗室王周围,结识更多的权力人员,扩展社会交往范围,密切着与权力集团的社会关系。随着宗室王在权力争斗中取胜,他们也随即成为军功勋臣,与皇权势力集团有了更多的行为互动。
如韦睿子放、正、棱、黯皆有能名。正起家南康王行参军,棱起家安成王府行参军,放起家齐晋安王宁朔主簿,黯起家太子舍人,韦放子粲起家梁晋安王行参军。
再如裴叔业少便弓马,有武干。齐永明年间,萧鸾刺豫州,叔业任其右军司马,后历任晋安王征北咨议、晋熙王冠军司马。史书载:“叔业早与高宗接事,高宗辅政,厚任叔业为心腹,……叔业尽心用命。”[20]870萧鸾自立,以叔业为给事黄门侍郎,封武昌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后拜持节、冠军将军、徐州刺史。鸾死,萧宝卷自立,迁叔业本将军、南兖州刺史,叔业心不自安,问计于雍州刺史萧衍,终举豫州投北。裴叔业投北,参与其谋者诸如天水尹挺、武都杨令宝、安定皇甫光、北地梁佑、清河崔高客、天水阎庆胤、河东柳僧习等皆为当地豪族。裴叔业危急时刻寻求计策的人选为雍州刺史宗室王萧衍,他对萧衍的信任也反映了关中郡姓与宗室权贵的逐渐融合。
这种融合不仅缘自战事活动中的行为配合以及豪族倚赖权贵的利益驱动,还在于他们两个群体不断加深的情感认同。关中郡姓与彭城刘氏、兰陵萧氏在江左士人看来同样门第卑微,他们在社会心理、文化方面不仅没有较大隔阂,甚至随着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更加深了彼此间情感上的认同。《南齐书》卷24《柳世隆传》载,柳世隆、萧赜任职晋熙王刘燮府,两人“相遇甚欢”,萧道成谋渡广陵,令萧赜同会京邑,欲留“文武兼资人与汝意合者,委以后事”,认为世隆为最佳人选,萧赜即推举世隆自代。河东柳氏与兰陵萧氏在身份等级、文化心理上接近,能够彼此接纳,因此相遇甚欢、志同道合。世隆子惔后为齐巴东王萧子响友,惔弟憕为梁镇北始兴王赏识,任其长史。后始兴王移镇益州,复请憕随任,前后祈请四次,憕复任镇西长史、蜀郡太守[11]990。裴子野在梁武帝时以史才被世人所重,梁武帝深为嘉赏,宗室诸王与其情谊笃厚,“及葬,湘东王为之墓志铭,陈于藏内。邵陵王又立墓志,堙于羡道。羡道列志,自此始焉”[11]867。湘东王萧绎、邵陵王萧纶皆为裴子野志墓,且为之开创了羡道列志之礼制,体现了萧氏对裴子野的深厚情谊。
积极参与宗室集团战事行动并且屡获战功的关中郡姓得到仕途晋升的机会,或者任总一方,或者当选朝官,成为中央化的朝廷勋贵。政治地位的提升为关中郡姓营造了更广阔的多层次的社会关系网。在政治权力的拉动下,韦、柳等家族渐渐在京城立足,逐渐形成了对江左上流社会的心理认同,并自觉融入其中。
(二)交好高门巨族
史文记载,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关中郡姓家族成员在京城活动广泛,社会交往对象中多有高门甲族的身影。如河东柳氏,柳元景在宋前废帝时成为辅政大臣,与琅邪颜师伯等常相驰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13]1990。柳世隆与吴郡张绪、琅邪王延之、吴兴沈琰为君子之交[11]983,齐永明年间,世隆迁护军,为王俭敬重,史书载:“卫军王俭修下官敬甚谨。世隆止之,俭曰:‘将军虽存弘眷,如王典何。’其见重如此。”[11]985王俭还特别赏识世隆子悦、惔二兄弟,谓人曰,“柳氏二龙,可谓一日千里”[11]986,并亲自造访世隆宅,求见悦及惔。世隆子恽与陈郡谢瀹邻居,深见友爱,恽以琴艺为萧子良赏狎,以文才被琅邪王融赏识,并与琅邪王瞻博射[10]331。惔、恽等常预帝宴,赋诗作文,为世所赏。
又如京兆韦氏,韦睿兄纂受沈约推重,“纂仕齐,位司徒记室、特进,沈约尝称纂于上曰:‘恨陛下不与此人同时,其学非臣辈也。’”[11]1430韦睿子“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为婚姻。其后各产男女,未及成长而率亡,遗嗣孤弱,放常赡恤之。及为北徐州,时有势族请姻者,放曰:‘吾不失信于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适率子,时称放能笃旧”[10]424。韦放子粲与颍川庾仲容、吴郡张率,并忘年交好[10]605。韦棱及河东裴子野与沛国刘显、南阳刘之遴、陈郡殷芸、陈留阮萧绪、吴郡顾协等深相赏好[10]443。河东裴子野又与陈郡谢征友善,子野尝为《寒夜直宿赋》以赠征,征为感友赋以酬之[10]718。
京兆杜氏,杜骥子幼文在宋元徽中为散骑常侍,与吴兴沈勃、吴郡孙超之常相从,并与恩幸阮佃夫厚善[13]1722。
可见,柳、韦、裴等家族的朋友圈已由雍州地方扩展至京城社会,无论在交游圈还是联姻对象上都有了侨姓高门和吴姓甲族的身影。这样的社会交往及社会活动既是关中郡姓努力融入江左上层社会的结果,同时也促使他们借助这些家族的社会支持,获取更多的政治社会资源,提升家族地位和社会名望,从而增强同为上层士族的“我辈意识”。
为融入高门士族群体,关中郡姓家族积极主动改变家学门风,改变生活习惯,迎合上层群体的主流文化。河东柳元景以军功起家,位至三公,侄柳世隆文武兼备,助萧氏建齐后虽历任武职,但已积极从文,性爱涉猎,借秘阁书二千卷。晚年“专以谈义自业。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璅,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槊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20]452。在薛道生犯罪被秣陵令庾淑之鞭罚一事上,与薛安都武勇好杀处事莽撞不同,柳元景不仅将其劝回,且对薛氏的言行服细加以批评:“卿从弟服章言论,与寒细不异,虽复人士,庾淑之亦由得知?”[13]2216柳氏主动在文化上改变家学门风的做法曾多被学人讨论,被认为是柳氏在南朝跻身士族行列的关键所在。从社会融合的角度看,关中郡姓在言行服细、文化风尚上积极向高门士族的效仿甚至超越反映了他们对江左文化的心理认同及融入江左社会的心理自觉,这是他们对江左主流社会的情感融合。柳氏对士族高门群体的自我认同,不仅是促发他们几代人积极参与江左政治、军事,不断进取仕宦地位的动力来源和行为自觉,也是政治地位提升、文化风尚转变以后的意识强化。
比较而言,裴(南来吴裴)、薛、杨、杜在融入江左社会的努力方面更多地体现为军事上的活跃,在寓居地他们同样获得宗室诸王的青睐和征召,积极参与了宗室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南北边境的争夺之战,也获得了仕途上的晋升机会。但从他们的社会交往来看,史文可考的多为同质性强的社会关系,大多是在寓居地域或官任地结交一些为高门士族所鄙薄的次等士族或荒伧豪帅,表明他们对江左上流社会融入程度不高。
结合关中郡姓在乡里社会和江左上流社会的融合情况可以看出,晚来的侨姓士族与江左上流社会融合过程比较缓慢,且十分困难。作为原士族高门或地方豪族,在政治地位、武装势力、文化积淀的作用下,他们在乡里社会较易树立权威,营造家族势力,获取社会支持。更因为寓居地域聚居着相当多的北方乡邻,所以他们对乡里社会的地域认同形成较快,具有一定的地域归属感,但在江左上层社会中的融合程度不高,且呈现家族房支之间的明显差异。造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来自社会结构、朝廷政策、家族自身、社会动荡等四个方面。
三、影响关中郡姓社会融合程度的因素
(一)士庶悬隔的等级社会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悬隔、等级森严。东晋南朝时期侨姓门阀与吴姓士族高居主导地位,晚渡的关中郡姓是为其不齿的荒伧。二者无论在仕宦地位、门第等级及家学风尚方面都有着悬殊的差距。在当时的社会,高门甲族操纵着国家政治权柄,身份性的内婚制维持着上流士族的门第血统,家学家教把控着学术文化的传承。正常情况下,寒门家族乃至中下层士族要实现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几乎没有可资凭借的途径,只有在政局动荡、政治集团权力争夺的斗争中,次等士族才有机会凭借武力建立军功求得官职。即便如此,他们仍会由于曾涉仕胡族或与胡族、寒贱通婚而被清途所隔、士人鄙弃。因此关中郡姓在江左上层社会的社会接受度低,很难获取身份认同和士族群体的社会支持。
(二)稳中有变的统治政策
关中郡姓在江左的社会融合还受到东晋南朝统治政策的影响。一方面东晋南朝通过在雍州、豫州等地侨置郡县安抚流民,同时这也是对流民的限制,阻止他们继续南下。因此关中郡姓南迁后,寓居边境之地,虽原是高门大族也只能与江左高门分隔而与次等士族聚居。在寓居地域实行土断后,他们更在当地扎根下来。另一方面,南朝统治者对雍州的着意经营、举用寒人武人的政策为关中郡姓提供了展示才能、创立军功的机会。宗室出镇雍州虽是对日益壮大的雍州武装势力的震慑,但同时又是拉拢当地强宗豪右建立武装根据地的极好机会。因此关中郡姓家族成员多被宗室诸王赏识提拔,征召举用,借机发展壮大家族。宋、齐、梁三朝本为移民政权,刘裕出身寒微,萧齐亦非高门,掌握政权后在官员选用上给寒士武人开放机会,梁武帝时更是寒士荒伧咸被进用,侨姓高门和吴姓士族政治地位逐渐衰落,因此次等士族与高门巨族政治地位的差距逐渐缩小,在众多的政治社会场合中,出现了高门与次等士族甚至士庶共济一堂的场面,关中郡姓从而得以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
(三)家族宗亲的自身努力
如上所述,关中郡姓在江左虽同为次等士族,但在社会融合方面还存在内部差异,不同家族甚至不同房支的社会融合程度不一。这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统治政策有关,也在于各家族房支在融入江左社会方面是否积极。河东柳氏在仕途提升的同时改变家学门风,习学江左上流文化,技艺超群且风韵清远。而河东薛安都虽追随柳元景频立战功,仕阶顺达,但服章言论粗鄙,虽复人士,仍被人轻鄙。此外,江左选官用人看中士人品评、舆论推举,因此攀附权贵、交接名士是获得辟举、征召的重要途径,但河东薛憕“负才使气,未尝趣世禄之门”,连同为关中郡姓的京兆韦潜度都劝他,“ 裾数参吏部”,仍不为所动[21]683。河东裴氏家族中,裴叔业、裴邃房支以军功扬名于豫州,身边团聚着的大多为同乡同僚,与江左高门之间几无社会交往活动,裴松之房支虽难预高门之列,但至裴子野时,因文史之才,结交士人,为世所重,社会融合度提高。
(四)动荡不安的社会时局
对于晚渡的关中郡姓而言,他们在乡里及京城的社会融合情况受到时局的巨大影响。他们因社会动荡而迁徙,也因战乱不断而崭露头角,再因政权交替成为朝廷重臣,又因政治集团斗争北投甚至身死族灭。可见一方面社会动荡给关中郡姓在江左社会立足、发展壮大提供机会,乡里社会、宗族权贵、皇室帝族甚至侨姓高门、吴地大族逐渐对他们认可、接受甚至推崇。另一方面社会动荡也可能使他们辛苦经营的家业化为灰烬,不断增强的社会融合的进程被搁置。薛安都因为政治斗争北投,裴叔业因为被皇权猜忌北归,杨氏一门在政局动荡中覆灭,杜氏家族在政局变化中迎来灭家之祸。生存尚且不易,更遑论社会融合。
四、关中郡姓南迁房支社会融合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融合与家族发展
关中郡姓在寓居地域的融入程度与家族生存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家族依靠掌控地方权威、维系地方社会秩序成为乡里领袖进而猎取朝廷官职,得以提升仕途、彰显门第。如前所述,他们通过军功、学识在地方树立权威,并借助联姻手段结成利益共同体,依靠地方社会支持,相互品评,形成舆论,成为地方名望家族,从而获取征召、辟举机会。
在南朝上层社会空间,关中郡姓也积极融入,一方面借助政治权力,另一方面通过改变自身尚武的家学门风,逐渐士族化、江南化,从而与宗室皇族、侨姓高门、吴姓士族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社会关系,获取了他们在南朝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支持。这种社会关系的构建既是关中郡姓在南朝社会融合的途径,也是他们积极融入的结果。最终关中郡姓在南朝上层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声望得到了提升。
对于晚渡的关中郡姓来说,无论在乡里还是在建康上流社会,积极融入始终是家族发展壮大的必要姿态。而从实际结果来看,河东柳氏的社会融合度最高,其家族人士在服章言论、风范仪态、趋走应对方面也更与江左高门家族相近,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最高。相反地河东薛氏保持着寒细武人的社会生活习惯,很难为江左士人认同。此外,关中郡姓南渡后世代与寓居地土著杂居杂婚,无论主动与否,社会风习、文化观念等方面逐渐同化的趋势是一定的。河东裴叔业房支在齐萧宝卷世北归,在生活习惯上已受南人影响,也正是在江左,河东裴氏濡染佛教文化,虔诚信佛[22]。故此,南来吴裴与诸河东裴氏、襄阳杜氏与诸京兆杜氏之区别不仅仅在于寓居地域不同和宗族血缘的疏离,更在于基于不同地域生活环境之上而形成的不同家族文化、社会风习。
(二)社会融合与多元文化
关中郡姓在南朝的社会融合不仅是逐渐对江左社会主流文化、生活方式认同、接受、采用甚至超越的过程,也是以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对寓居地发生影响的过程。他们是寓居地经济开发的促进者,是寓居地社会秩序的领导者,是寓居地社会文化进步的推动者[23]。他们以武勇胆烈在南朝战争风云中唱响了英勇雄壮的战歌,又以世代承袭和日渐创新的文化成就丰富充实了士人风采。以关中郡姓为代表的北方士人南来寓居多年后,人多劲悍的襄阳一带“稍尚礼义经籍”[14]897。江左上层士人以谈义为重,儒史被视为素业,但河东裴氏之史学、京兆杜氏之经学仍助推了东晋南朝史学、经学的发展。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史记集解》、裴子野《宋略》在东晋六朝的史著中成就卓著,为世人称赞[24]313-330,233-237,135-139。京兆杜坦、杜骥先后任青州刺史,将其家业传至齐地,齐人多习之。
因此,关中郡姓在东晋南朝的社会融合也是与江左社会群体的社会风习、文化观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结果便是多元文化交融,并在江左社会大放异彩、缤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