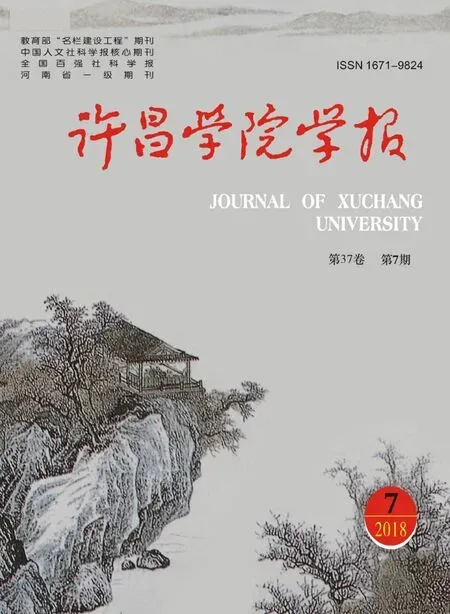曹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修改《日出》深层动因考
靳 书 刚
(许昌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作品出版以后作家们再对原作进行修改在文艺界是很常见的事情,它可以说是一个作家的基本权利。文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原作经过多次修改以后在艺术上变得越来越成熟,进而获得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从而有可能进入经典的行列。但是,对于那些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迎合某种需要而不断修改旧作的特例,则要另当别论了。1949年以后,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诞生于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名作再出版,几乎都进行了修改,并且很多还改了不止一次,有了众多的修改本。其中修改自己旧作比较典型的是曹禺,而尤以他对《雷雨》和《日出》的修改为最。
《日出》自1936年发表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共出现了文字内容有差异的五个不同的版本,每一种版本在思想、艺术、情节、人物等方面多少都有些不同,留着不同时代的印迹,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同时也为展开对《日出》不同版本在思想艺术变化和得失方面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但是,目前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据考察,《日出》的五个版本中,除了1951年开明本改动较大之外,其他几个版本的变动主要体现为剧本艺术的完善和精益求精[1]。相对于初版本来讲,开明本的最大改动在于作者围绕小东西的命运,加进了一条革命斗争的红线,新增了三个人物:小东西的父亲和田振洪、郭玉山,他们的身份是仁丰纱厂的工人。初版本中始终没有出场的金八被作者明确为仁丰纱厂的总经理,其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方达生被改写为一个参加了革命的地下工作者,他和工人们一起,与金八展开了坚决斗争。经过此番删改后剧作的主题、人物和风格都与之前有了天壤之别。曹禺以新中国成立之初获得的半生不熟的阶级斗争观念为指导,对这部名剧做了伤筋动骨的改造,想以此来使作品和人物的阶级性得以凸显,并使整部剧作拥有了乐观明朗的格调,但原作那种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被作者用阶级斗争学说的简单演绎消解得干干净净。
1951年前后,刚刚步入新时代的曹禺正踌躇满志,他为什么要对自己创作于十几年前的经典名剧进行大删大改呢?这恐怕与当时的全新的文学规范、戏剧观众的变化、作者在当时文学场中的复杂站位以及作者本人思想上发生的变化有关。关于曹禺1949年之后的转变,研究者多归结为外因(政治气候)和内因(曹禺的个人因素)两方面。关于曹禺转变的内因,有学者将之归因于他的性格中“胆小怕事、世故圆滑”这一侧面[2]180。关于曹禺转变的外因,也有研究开始指向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不过,两者都没有周延地解释曹禺在1949年后的文学实践。
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确立了后来被命名为“政治—文学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在这一文学格局建立的过程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立为当时文艺的指导方针,成为中国文学遵循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解放中国人民的斗争中,仅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军队[3]9。他提出,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文学是政治力量为实现自身目的可能选择的手段之一。从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开始,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也被要求在总的方向上与现实的政治任务保持一致。
同时,新中国还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统一的组织机构(文联与各专业协会),作家大规模地进入单位。在这样充分组织化的文学结构里,组织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就会疏隔作家的文学身份,特定情况下甚至会遮蔽文学身份。
除此之外,对于剧作家曹禺来讲,新时代观众的变化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在曹禺的戏剧观念里,观众的接受和剧本的演出效果至为重要,他甚至认为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他曾经宣布以观众为“生命”[4]394。因为多年的演出实践使他明白,戏剧只有获得观众的认可才会拥有生命力。他曾反复强调,“一个弄戏的人,无论是演员,导演,或者写戏的,便须立即获有观众,并且是普通的观众。只有他们才是‘剧场的生命’”[4]394。1949年之前,曹禺始终认为他的剧作能够拥有众多的观众,并且一直在给观众以积极的、好的影响。而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一信念发生了动摇。曹禺在发表于1950年的《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的检讨中最让人震惊的是他竟然相信了人们批判他的话:他过去的作品 “客观效果上也蒙蔽了读者和观众”。后来,曹禺在为这个修改本出版写的序言里还在这样检讨:“写字的道理或者和写戏的道理不同;写字难看总还可以使人认识,剧本没有写对而又给人扮演在舞台上,便为害不浅。”可见支配着他的依然是对于他的观众的负罪感。
更为关键的是,进入新的时代以后,创作的接受对象也即服务对象问题愈发成为作家思考的中心。而在新的时代里,观众、读者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面对有了新观念和新意识的读者和观众,曹禺太渴望自己的创作能够与新的普通工农观众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能够为他们所接受,又不致产生消极影响了,于是他必然要对旧作做出修改。
二
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初之所以表现得这么积极,除了他的单纯和热情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极其微妙的现实处境。虽然曹禺在表面上占据着显要位置,拥有众多头衔和职务,但是这并不能彻底改变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
在作协、文化部等单位中,郭沫若、茅盾等人纵然身居高位,但实权也不大。一些细节颇能折射这种现实。1956年,诗人沙鸥前往拜访郭沫若,“(沙鸥)恳切地对郭老说:‘请郭老对周扬同志说说,办个诗刊吧。全中国没有一个诗刊。’郭老笑笑说:‘我说话管事吗?……’沙鸥又说:‘同荃麟、白羽说说也可以……’郭老又说:‘他们听我的吗?’沙鸥心想:如果郭老的话不管用,谁的话管用呢?”[5]1957年,中国作协开展党内整风,《诗刊》编辑吕剑为茅盾鸣不平:“茅盾是个老作家,却未受到重视。(《人民文学》)最初是茅盾主编,艾青副主编,但具体负责的是艾青。”“我接触到许多党员作家,他们对茅盾、郭老都瞧不起,认为这些人只能谈谈技巧。这两位作家都未受到重视,可以设想其他作家的精神状态。”[6]茅盾虽然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周扬是副部长,但由于周扬还是文化部党组书记,故实质上是他在领导茅盾和整个文化部。资历和威望远高于曹禺的郭沫若和茅盾尚且如此,更遑论曹禺。更何况郭沫若、茅盾与革命多少还有些关联,而他对革命几乎没有“尺寸之功”*因为这个原因,对国统区文人的安置曾在解放区作家中引起不满。据傅光明采访可知,当时文艺界“对老舍作北京文联主席不服气”的大有人在。见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曹禺被纳入优待行列,主要是因为他的话剧曾经在三四十年代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再加上有周恩来等老友的格外关照。
曹禺后来对自己的位置也有了清醒的认识,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与周扬、丁玲、夏衍、何其芳等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作家是有着巨大区别的。虽然同被主流看重,但他毕竟来自国统区,没有到过延安,没有加入共产党,在开始创作之初,也没有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创作出一批革命作品,因此自然无法与来自解放区的“丁玲们”相比。
三
曹禺的转变还与他的家庭出身、婚姻状况以及个性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家庭背景、婚姻状况都经不起新社会的考验。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早年曾留学日本,1909年学成回国后,被任命为直隶卫队标统。辛亥革命后,随着黎元洪出任民国大总统,同为湖北籍的万德尊也得到大力提携,当上了大总统秘书,后来还一度做过河北宣化镇守使,一时极为煊赫。这样的北洋军阀官僚家庭出身在新中国成立后火红的无产阶级革命岁月里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它让曹禺有一种强烈的身份的“原罪”感。更何况曹禺当时还有一个让他如坐针毡的个人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他和郑秀没有离婚却早已和方瑞同居。1946年曹禺赴美讲学期间,就曾给郑秀写信正式提出离婚,但郑秀坚决不同意。回国以后,曹禺又一再要求离婚,可还是没有结果,所以他与方瑞之间就只能保持同居关系。而这种暧昧不明的同居关系在新社会就成了个人生活方面的污点,因为它牵涉到那时很敏感的个人作风问题,如果处置稍有不当,很有可能毁掉一个人的所有前程。如果把这桩个人恩怨考虑在内,曹禺在当时文学场中的微妙处境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从曹禺本人的个性方面来讲,他也很容易迅速屈服并对旧作做出过火修改。曹禺自幼养成了敏感怯懦、胆小怕事的性格,这与他幼年时的家庭生活背景有关。曹禺生长在一个畸形的家庭,父亲万德尊宦海几度沉浮,40岁时就下野赋闲在家,从此一蹶不振,整日郁郁寡欢,让整个家里的气氛也很沉闷。曹禺在晚年接受田本相采访时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高兴了,你干什么都行,他不过问;不高兴了,就骂人,甚至打人,还经常发无名火气,搞得家人都摸不着头脑。我就曾在父亲的火头上,挨过父亲一巴掌。……这一巴掌给我印象太深刻了。”[7]81他还亲眼看到父亲将哥哥万家修的腿踢断,所以对于父亲,他很多时候都心存畏惧,时间长了就养成了胆小怕事的性格。此外,曹禺过早地失去了生母,虽然作为继母的姨母将他视同己出,但曹禺还是自幼产生了一种“弃子”情结,他习惯独处,不喜交际,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这样的家庭环境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性格,导致他在为人处事方面胆小谨慎。吴祖光多次坦言:“他胆小,拘谨,不敢得罪人。”[7]207在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以往的作品与新中国的文艺方针之间存在着莫大差距后,谨小慎微的曹禺就愈发不安起来,他迫切地感到自己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来证明自己正在积极追求进步。
四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曹禺很快就明白,要进入新的文学场还要经过一关:思想改造。思想改造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检讨。“检讨”即认错,借用福柯的理论,就是对权力的“驯服”和“归顺”。曹禺于是于1950年10月在《文艺报》上发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一文。在此之前有几位作家比如赵树理已经做过检讨,不过他们多是迫于当时形势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与之不同,曹禺的检讨则是更多出于对党信任的自愿行为,因此曹禺检讨的力度是他们所不能企及的。
曹禺这样解释他写这篇文章的动因:他相信“作为一个作家,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始进步”——他已经认定自己过去的创作思想出了问题,情愿改变自己去适应新的时代。但改变的代价却是十分高昂的,因为只有“多将自己的作品在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才可以使我逐渐明了我的创作思想上的脓疮是从什么地方溃发的”——不仅要彻底、全面地否定自己,而且要不惜用最污秽的语言来辱没自己。仔细研读这篇检讨,不难发现,剧作家自愿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独立思考,向自己的批评者——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家的权威解释全面认同。还有一个地方,曹禺似乎比20世纪30年代的周扬走得更远:周扬曾经肯定,一个作家即使“和实际斗争保持着距离”,也仍然有可能“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现实,把握现实,“在他对现实的忠实的描写中,达到有利于革命的结论”,并且表示对这样的作家“应当拍手欢迎”。但现在曹禺却这样传达了他所服从的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法规:“一个作家若是与实际斗争脱了节,那么,不管他怎样自命进步,努力写作,他一定写不出生活的真实,也自然不能对人民有大的贡献。”[8]
不仅如此,他还接受了人们一再向他灌输的思想:“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你若想作一个人民的作家,你就要遵从人民心目中的是非,你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是非观点写作,你就未必能表现人民心目中的是非。人民便会鄙弃你,冷淡你。”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像他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好好改造自己,就将“永远见不到中国社会的真实,也就无从表现生活的真理”,而且“终身写不出一部对人民真正有益的作品”,为人民所抛弃。对于一个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服务于祖国、人民为天职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因此,曹禺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起终于“投降”了——按当时的说法,叫作“向真理投降”,而且确确实实是自愿的投降,而且以投降为荣[9]230。
思想改造的另一重要形式是修改旧作。为了证明自己已下定决心要洗心革面抛弃过往,作家们纷纷修改自己的旧作,以满足他们“脱胎换骨、自我改造、自我重塑”的愿望。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初,修改新文学作品的更内在的动因是与当时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密切相关的,是知识分子呼应意识形态的召唤、积极投身思想改造运动的结果。曹禺把旧作新改当成了自我改造、自我规训的一种方式。
因此我们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曹禺的心态和思想就已然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于是就不难明白他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作品大加砍削了。他是按照权威理论家周扬的意见修改的。周扬于1937年发表《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批评的批评》一文,在给予两部作品相当高的评价之余,也针对 《日出》提出了如下批评:“历史舞台上互相冲突的两种主要的力量在《日出》里面没有登场。”“金八留在我们脑子里的只是一个淡淡的影子,我们看不出他的作为操纵市场的金融资本家的特色,而他的后面似乎还缺少一件东西——帝国主义。”[10]685以此来对照曹禺的剧作,自然显出根本性的弱点。更何况1949年以后,周扬成了党在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对于作家来说,这不仅仅是来自批评领域的意见,还是上级的指示,是一种权威话语,作家们不得不做出顺从的姿态。这一点曹禺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田本相的采访时证实说:“建国初期,周扬的话,我佩服得不得了,我修改《雷雨》和《日出》,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那本剧作选,我基本上是按照周扬写的那篇文章改的。”[7]37这说明,来自周扬的批评意见始终是曹禺思想上的一个包袱,在他看来,只有用自戕的方式大幅度修改自己的旧作,才能证明自己的思想已得到了改造,从而早日脱掉头上那顶过于沉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尽快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
于是,开明版《日出》的剧情就被曹禺修改为:小东西的父亲被金八杀害,纱厂工人由此展开罢工斗争。小东西被金八卖到宝和下处,方达生和仁丰纱厂工人一起,把小东西救了出来。这实际为剧本加入了一条革命斗争的红线,使剧本的重心由展示陈白露的心路历程转到革命者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展开英勇斗争上来,将历史舞台上互相冲突的两种主要力量演绎为戏剧舞台上互相冲突的两股力量。
这样一来,《日出》的剧情被改造得严重走样,主要人物性格被改得面目全非,《日出》从典型的悲剧变成了一出仅具有宣传教化功能的“社会问题剧”。这一版本自始至终都没有上演过,时至今日,读者和导演们早已忘了它的存在,只有研究者在探讨曹禺创作生涯的曲折和教训时才会想到它。它从一个侧面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曹禺对周扬的批评缺乏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把周扬的个人学术见解全然作为修改的依据,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意见而盲目地全盘接受了,这样就失去了一个作家的独立判断,失去了艺术上的自信,而这对于作家来说几乎是致命的。现在看来,这一版本的价值,一方面在于它向我们证明,曹禺在向自己的过去做彻底的诀别,他已完成了转向,准备以全新的姿态融入新生活,另一方面在于它对于研究《日出》的创作和修改历史,认识作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思想和心态,具有无可替代性。当然至为关键的是,它还告诉我们一个作家的艺术自信和独立判断是多么重要,这也是它为我们今后文学的发展留下的重要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