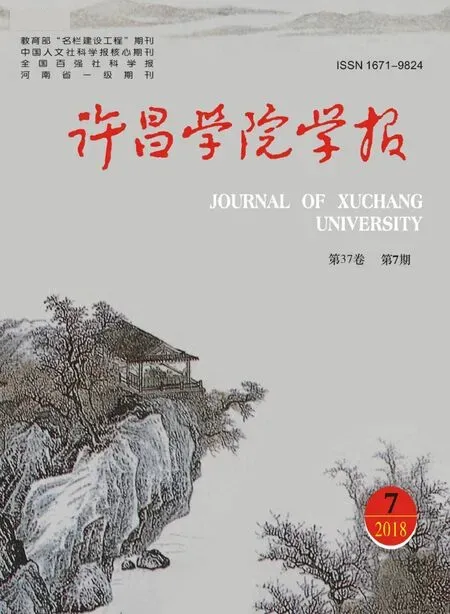王仲荦先生二三事
齐 涛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王仲荦先生(1913—1986),浙江余姚人,20世纪30年代初,为章太炎先生及门弟子。太炎先生去世后,随章夫人汤国梨先生并其他几位太炎弟子共同创办太炎文学院;1942年起,任教于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中央大学返回南京后,任教于文学院中文系;1947年应聘至青岛山东大学。此后至1986年去世,一直任教于山东大学。2011年,我曾应《文史哲》之约,介绍过仲荦先生的学术与学问,故在此仅就仲荦先生之学术精神与人文风范略述一二,可与前篇互见。
一、文史兼通的学术涵养
众所周知,王仲荦先生是著名史学家,从他的学术道路上却可以看到,他属于“半道出家”者,而且他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并未局限于学科制约,而是亦文亦史,左右兼通,融会人文,自成气象。
仲荦先生在史学界以治魏晋南北朝史而闻名,在传道授业中,却并不要求弟子们局限在魏晋南北朝史或某一领域之内。记得考取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后,我们三位学生一起去先生家,先生为我们选定了三个不同方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一个是对韦庄诗词进行校注,一个是以《册府元龟》校勘《史记》,一个是对刘劭的《人物志》进行校注。而且他对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韦庄诗词的校注要仿李善注《文选》的体例,重在明典;以《册府元龟》校勘《史记》要补上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校点中的一个不足;为《人物志》作注则要厘清魏晋时代人才观的进展与变化。
我选了校注韦庄诗词这一方向。先生将他早年所著《西昆酬唱集注》交给我学习。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我历时三年,完成了《韦庄诗词校注》,毕业答辩之时,才明了先生的良苦用心。先生在回忆为《西昆酬唱集》作注时曾不无感慨地对我说:笺注工作“单靠《佩文韵府》是不行的,我就得一部一部书翻检诗句的出处,如《毛诗》、《左传》、《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麟台故事》、《初学记》、《太平御览》、《世说新语》、《穆天子传》、《西京杂记》、《酉阳杂俎》、《庄子》、《列子》、《楚辞》王逸注、《玉台新咏》、《樊南诗文集》冯浩注、《文选》李善注、《全唐诗》等,一天一天地翻检,翻检得很详细,不但解决了注释问题,也充实了自己,打好了基础”[1]590-591。我的最大收获也是打下了基础,对于我们这批“文革”十年中走过来的学生而言,这种基础性的国学训练又更具有特殊意义。先生为另外两个同学所选硕士论文方向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义。
仲荦先生的学术起点是《西昆酬唱集注》和联绵字辞书的编纂。在《西昆酬唱集注》初稿草成后,先生即计划编成一部联绵字辞书。当时《辞通》和《联绵字典》尚未面世,以一人之力,编如此一部辞书,实属训诂学的一项浩大工程。先生晚年曾回忆道:
在朱起凤《辞通》(它是1934年出版的)未出之前,我也想仿明朱谋玮《骈雅》例,编一部书,单收联绵字,每天搞一些,搞了万条以上,《十三经》、《前四史》、《晋书》、南北十史和两《唐书》,都搞了,《楚辞》、《昭明文选》也搞了,当然还有绝大部分书中的联绵字,还来不及辑录,计划是二十来年写成。当时没有卡片,是写在废账簿的反面,大概写满了十七八厚本。
遗憾的是,此稿先是被先生存于余姚故居,后又寄存于亲戚家,待先生1946年重返余姚时,已散失无存。先生曾感叹道:
这一部稿本,我是准备搞到唐五代为止的,工作量太大,收集的资料才十分之三四,倘使手稿存在,还须投入大量工作量,尽管《辞通》与符定一的《联绵字典》行世,我还是能从别一个角度来完成这个著作的。稿已迷失,我也集中精力放在史地方面,就不想从事训诂语言之学了。
尽管如此,这项工作对先生扎实的小学功底的奠定,功莫大焉。
先生史学研究的起点是《北周职官志》的编纂。起初,先生准备编《两晋会要》和《南北朝会要》,后听说泰兴朱铭盘先生已经编成,遂辍笔不编。在章太炎先生指导下,开始了《北周职官志》的编纂。草成之后,又进行了《北周地理志》的编纂。该两书名为《北周职官志》和《北周地理志》,实则是涵括了整个北朝的职官与地理之志,意在填补南北朝诸史中的一个重要阙失。
不过,先生1942年秋应聘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时,却又是师范学院国文系的教席,担任大一国文课。1945年秋,被聘为国文系副教授,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后,进行院系调整,师范学院国文系并入文学院中文系,先生亦转至中文系任教。到1947年夏,中央大学中文系解聘了若干名受进步学生欢迎的教授,有朱东润、吴组缃、蒋礼鸿诸先生,仲荦先生也在解聘之列。当时青岛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闻讯赶到南京,延揽诸贤,先生转至山东大学文学院,次年被聘为教授。
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山东大学成立历史研究所,赵纪彬先生任所长,邀先生至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进行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资料整理工作。不久,历史研究所撤销,成立了历史系,先生转至历史系任教,主要担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教学。自此,先生一直从事历史学的研究与教学。转行不久,便成就卓然,成为国内史学界颇负盛名的史学家。
何以如此?先生治小学所打下的深厚功底,教授国文所积淀的文献素养,加之先生所继承的浙东学派“六经皆史”的传统,为其文史双修提供了良好的根基。先生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浓重的文学情结,使其在历史研究中平添助力,别开生面。比如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大量引入了古典文学的元素,把文学史与文化史作为断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以诗证史、以史论诗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以《隋唐五代史》为例,全书洋洋百万余言,文化史部分占了1/3强,其中,诗史、词史又占了文化部分的2/5,达15万字左右,仅完整引述的唐五代诗词就有千首以上,若单独成册,即是一部完整的唐五代诗史。即便如此,王先生仍然意犹未尽,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
唐代的诗歌文学,是唐代文化的精华。在拙著中,初唐诗只略作介绍,盛唐几位大家,叙述较详。我是喜欢中晚唐诗的,所以叙述中晚唐诗特详。但是受到篇幅的限制,作品是介绍了,对于作品的分析,却只能俟诸异日,另成一书了。
在《隋唐五代史》一书中,讨论史实之时,王先生能以诗为证,引诗入史,解决了若干疑难,在讨论诗人诗作时,则以史证诗,大大加深了对诗作的认识,甚至厘正了诗人与诗作中不少传统问题。
我完成了硕士学业,继续从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时,先生为我确定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韩偓诗校注与研究》,我初时有些不解,先生说:“做韦庄诗词时,以校注为主,研究为辅,做韩偓诗要以研究为主,以校注为辅。”韩偓是唐末重要的诗人与政治家,曾任唐昭宗的翰林学士和宰相,是唐末历史的亲历者,而且,其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注韩偓诗作,必须以史注诗,研究韩偓的时代,又可以诗入史。更为重要的是,在论文的写作中,先生引领我以韩偓为线索,对唐末五代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认识,要求我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唐宋之际作为重点,把握唐宋变革,不要拘于隋唐五代与宋元明清的生硬划分。先生这番鞭辟入里的教诲是在30多年前,惭愧的是,先生曾以金针度我,我却鸿蒙未开,未能持续着力于唐宋之际。
先生虽由文入史,但对于文学之钟爱始终未减,去世前不久,还对我说,待手头工作完成后,要集中精力,编写一部《唐宋文学史》。以先生浑厚的国学积淀,加之俯视唐宋社会变革的历史视角,先生之《唐宋文学史》必当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惜天不假时,未能遂愿。
先生之于文,并非从研究到研究,纸上谈兵,他自己也工于声律,咏唱酬答,清隽自然。记得1985年秋,我购买了一本陈寅恪先生的《寒柳堂集》。先生看到后,颇为感触,在扉页上题诗道:
柳色遥山入梦青,去年今日到江亭。
纵然海底游尘起,还喜流莺隔座听。
一丈红尘浅底扬,白丁香杂紫丁香。
宣南遗事成谈助,盲鼓当年未擅场。
先生说,这是十多年前与周振甫先生唱和之作,用的是陈寅老《和陶然亭女子题壁》韵。先生诗作留存颇多,《华山馆丛稿续编》中收有数十首。先生之诗,清雅脱俗,自然成章,诗人风骨跃然而出。
二、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视野
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初即专注于历史研究,他承担的课程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他的研究重心也同时放在了这一领域,成就斐然。但是,他又从未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这一时期,从未给自己的研究划定专业范围,而是致力于通古今之变。从理论到考据,从先秦到近代,都留下了先生探索的足迹,其探索在许多领域中都能成一家之言;至其晚年,更是达到了孔子所言“从心所欲,不逾矩”。唯此,方成就了国学大家风范。
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尝试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他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4期的《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一文,在国内史学界首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村公社问题。知名经济学家吴大琨先生曾回忆道:
我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研究工作者,是第一次从他那里认识到应当怎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重要性的。那时候,仲荦教授和我都是《文史哲》的积极撰稿者,我们讨论过的一些问题,或者在讨论中想到的一些问题,事后把它写下来,就成了《文史哲》上的文章。在当时王仲荦教授所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我认为发表在1954年4月号《文史哲》上的《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一文,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村公社制度的性质和作用。仲荦教授在文章中说:“许多世纪中,村公社的继续存在,成为古代专制国家停滞性的坚强基础。所有村公社的成员,只能成为土地的使用者——他的占有,也是经由劳动实践过程为前提之下发生的——而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公社社员既不是公社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本身就会变成公社的财产,也就会变成专制君主变相的奴隶。他们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了起来,完成着自给自足的生产,他们要经常地向他们的统治者贡献力役,也贡献物品。这些公社成员们,在身份上虽是‘自由’的,在经济生产上也是独立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公社成员们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就比奴隶或以后的隶农们来的轻,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也许还重得特别厉害。在这种特殊生产形态里,自由人生产还是占重要的地位,奴隶的劳动不能尽量代替自由人的劳动,这样,不但阻碍了奴隶形态的发展,也会阻碍了以后农奴形态的充分发展。”我认为仲荦教授这段话是十分精辟的,他所说的“特殊生产形态”,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以,我认为,王仲荦教授应该说是中国历史学界第一个以他独立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适合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他的这一贡献,在学术上的意义是很大的,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2]75-76
以此为起点,仲荦先生还积极参加了古史分期大讨论,成为魏晋封建说的重要代表学者。此外,仲荦先生还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多次发表论述,先后发表了《从茶叶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的江南丝织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的江南棉纺织业》等论文,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进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先生发表于《文史哲》1953年第2期的《从茶叶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中的重要代表作。文章“从茶叶经济发展这一特殊角度来论证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为什么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得比较久。文章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与封建经济政治体制的强固结合,由于这种结合,更加强了封建阶级对于茶农与制茶手工工人的残酷剥削,阻碍了手工业向工场工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后来更由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保持了封建统治”[3]30。这篇文章被严中平先生誉为研究明清经济史的创新之作,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先生则谦虚地认为:“中平教授是《中国棉纺织史稿》的作者,我受到他的启发和帮助,于是也热情地参加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尤其茶叶经济这篇文章,基本观点受到中平教授的影响很大,他真是我的良师益友。”[4]前言2两位先生的学者风范足垂后世。
宽阔的理论视野使先生的研究视角不断拓展,新作迭出,与之同时,先生仍着力于考据之功,除早年的《北周六典》与《北周地理志》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生还对敦煌文书、鲜卑与代北姓氏、中国古代物价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考证。
先生对敦煌文书的考释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谱牒残卷的考释,包括《〈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五种考释》等。二是对地志残卷的考释,包括《唐天宝初年地志残卷考释》《〈贞元十道录〉剑南道残卷考释》《〈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残卷校释》《〈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考释》《〈沙州志〉残片三种考释》《〈敦煌录〉残卷考释》《〈寿昌系地镜〉考释》《〈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考释》《〈西州图经〉残卷考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考释》《〈西天路竟〉释》等多种。前一部分收录在《华山馆丛稿》中;后一部分则汇为《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一书,经夫人郑宜秀先生整理后,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先生的敦煌文书考释主要是还原式考释。考释以雄厚的文献与史学功底为基础,广征博引,补白祛疑,为敦煌学研究做出了艰巨而有效的基础性贡献。王先生对于自己敦煌文书的有关考释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他曾对收入《华山馆丛稿》中的几则考释评价道:“有关敦煌石室发现的氏族志文章,一共写了三篇……这几篇文章,也有扎实的,如果顾步自怜的话,我是较为满意的。”[4]前言2这是王先生唯一一次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评价。
对鲜卑与代北姓氏的考证属专题性考证,有《鲜卑姓氏考》《代北姓氏考》两文,意在条理北魏、西魏时代,在鲜卑先改单姓又转用复姓的大变动中,各姓氏及相关集团的沿革、变化状况。如先生所言:“自北魏孝文帝改鲜卑复姓为单姓,西魏相宇文泰又改鲜卑单姓为复姓,当西魏、北周之世,庾信有诗云‘梅林可止渴,复姓可防兵’,则改复姓之影响之大,固有关鲜卑化汉化势力之消长,非独一姓一氏之单语复语之变换而已也。荦既写定《北周六典》,于西魏北周复用鲜卑复姓事,虽不得不略一提及,但言之不详,故今复为《鲜卑姓氏考》,别成一篇云。”[5]1在《代北姓氏考》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需要说明的,这两篇考证文章合计10余万字,均作于先生的晚年,无论是从史料的网罗殆尽看,还是从考辨中抉隐索微的功力看,都属考证文字中的上乘之作。先生本人对其也很看重,有几家杂志多次索稿,均未果。他多次说过,这两篇文章要收到《华山馆丛稿》的续编中,一部论文集应当有相当数量的未发表过的有分量的文章,不能只炒冷饭。
先生对中国古代物价史料的收集与考证是其学术生涯的最后一节。至1986年6月先生仙逝前,先后完成了《〈管子〉物价考》《〈韩非子〉物价考》《〈战国策〉物价考》《〈越绝书·计倪内经〉物价考》《〈史记·货殖列传〉物价考》《汉代物价考》《汉晋河西物价考》《魏晋南北朝物价考》《唐五代物价考》《唐西陲物价考》《于阗物价考》,宋代与辽金夏的有关物价资料也大致收集完毕。上述考证或资料已由其夫人郑宜秀先生汇为《金泥玉屑丛考》一书,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
三、学者风范与爱国情操
仲荦先生是真学者,终生潜心学术,固守学术良知,但他又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书斋居士,一生充满爱国情怀,恪守君子之道,报国之志始终如一。
多年来,先生除了研究、教学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爱好,终日在小小的书房孜孜研读,极少下楼,常常每日能完成三千言。而且,先生的所有研究都不找人代劳,从翻检史料、摘录卡片,到以繁体竖排誉录文稿,全部都是亲力亲为。最让人景仰的是先生终日乐在其中,流连忘返。其故交朱季海先生曾寄诗云:
闻道年来懒下楼,书城高筑又埋头。
古城艇子浑忘却,不及卢家有莫愁。
先生答诗曰:
神仙自是爱居楼,惭愧捧心未著书。
风雪连天冰百丈,木兰双桨正愁予。
正是有如此高贵的学术品格,先生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真正做到了视名利如浮云,不伐名,不自矜,固守学术良知,从不以“朴”示人。
先生在生前从不申报任何奖项,也未申报过什么项目,更不彰扬自己的学术与学问;相反,在一些情况下,宁肯学术成果不能出版,也坚守自己的学术良心,不随波逐流。其夫人郑宜秀先生曾回忆先生《曹操》一书修订版的过程:
……《曹操》,1956年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建国后国内第一部有关曹操的著作,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在嗣后进行的关于曹操评价的大讨论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拟再版此书,请仲荦先生加以修订,先生抱病对此书进行了系统的修订,吸取了客观的内容与评价,但没有应景的成分。在再版后记中,先生认为:“替曹操翻案,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使历史真面目还原。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拥护这一新说法,而把曹操那种残酷的性格完全抹掉。如果把曹操所属的那个生活烙痕抹掉,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未能再版。[6]前言2
先生固守学术良知方面最为集中的体现还是“不示人以朴”。前已述及,先生的两部断代史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历时30年才全部完成;其《西昆酬唱集注》与《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更是历时40余载,反复修订,方正式出版。以这三种著作为例,先生的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达到了较高水平。1945年秋,先生申请副教授之职,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伍叔傥在审读了先生送审的《西昆酬唱集注》和《北周六典》后认为,只需将前者送教育部即可,而后者升教授也可以了。只是因为先生执教国文系,不能用此书送审。当时的教育部在请专家审查后,即聘先生为中央大学副教授。尽管如此,先生仍将这些书稿反复修改了30多年。
仲荦先生在学问上特别推崇章太炎先生的“双轨并进”。他认为:“章先生的学问是双轨并进的。他有纯学术的著作,也有和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著作。从这一点看,就也懂得章先生为什么这样向往顾亭林,亭林既有《音学五书》这样纯学术性著作,但也有供国家民族可以借鉴的像《日知录》这样的著作,双轨并进,是并行不悖的。”[1]592
仲荦先生的学术道路也遵循了这样一条“双轨并进”之路,既有纯学术性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等,又有因应时代要求,参与古史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学术大讨论,意在为国家、民族提供借鉴的成果。此外,仲荦先生为了在新中国的建设中贡献一份力量,还进行了若干应用性颇强的研究,曾发表《古代中国人民使用煤的历史》《古代中国人民发现石油的历史》,把历史记载中的煤炭与石油产地进行了系统梳理。先生曾回忆道:“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上,曾发表过《古代中国人民发现石油的历史》一篇短文,曾把中国古代记载石油的分布地区,作一概括的介绍,企图说明只要我国地质探勘工作能展开,迟早有条件卸下贫油国那个帽子。”[7]239
需要指出的是,仲荦先生的爱国情怀与报国之志,来自他对民族历史与命运的深刻洞察,来自他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同气相通。远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仲荦先生由上海辗转香港、海防、河内,远走昆明,投奔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印泉先生,直接效力抗日大业。仲荦先生因环境不适,染上恶性疟疾,在昆明期间,发作了不下七八次,奎宁针、奎宁片成为经常使用的药物,最厉害的时候,体温高到41摄氏度,神志昏沉。无奈,只能离开云南才能解决。恰在此时,重庆中央大学发来聘书,先生决定离开云南,前往重庆。
此时,日军攻下泰国、缅甸后,又进入滇西,攻陷腾冲,进逼保山。龙云所部驻守保山的旅长龙奎垣不仅不抵抗,反而将保山洗劫后,纵火焚城,仓皇后撤。李印泉向重庆国民政府请缨,前往发动民众,配合军队,确守怒江一线。见此形势,仲荦先生毅然收起了中央大学的聘书,投笔从戎,随同直奔前线。对这一段经历,先生曾回忆道:我们一行人行至龙王塘之后,林蔚(时任国民党军令部副部长、入缅军事顾问团团长,也撤至滇西)派人告诉印泉先生,日军一千多人已抢渡怒江,希望印泉先生赶快撤退,印泉先生赶去司令部开会,回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当时许多人多劝印泉先生跟着顾问团撤退,印泉先生沉吟不语。我在天子庙坡受冻后,恶性疟疾复发,到了龙王塘,烧发得更高,正在打针服药,印泉先生派人来请我,征询我的意见,我把我的看法坦白地告诉他。他比我长三十多岁,又是我老师的盟兄弟,我们称呼他为“印老”。我说:“印老出来是抗日的,今天日军进攻滇西,印老来了两三天就撤回去,这绝对不可。如果形势紧急,可以和总司令部(宋希濂任集团军司令)一起撤退。中国的军队在滇西的有四五万人,渡江的敌人只一千多人,一定能够把他们打回去。但保山是前线,支持半个月一个月后,无论印老、无论总司令部都应退到大理,那是滇西后方重镇,居住在那里,比较适宜。还有随从印老来保山的人太多了,前方军事形势瞬息万变,愿意回昆明的,不如让他们回去一些好。”印老模仿《三国志》曹孟德的口吻说:“正合孤意。”后来一一照这办了。渡江的一千多日军,遇到我方坚强的阻击,很快退去。一个多月以后,前线局势转稳,我们随印泉先生退到大理。我在大理又发了一次烧,住了一个月,就回到昆明,由诸祖耿先生前往大理,接替我的工作,我就买车票前去重庆了。
抗战胜利后,仲荦先生虽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但对于国民政府已经失望,采取了不合作态度。国民党政府成立国史馆时,张继出任馆长,他是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想物色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去参加修史,章夫人汤国梨先生推荐了仲荦先生等人,并写信让先生去见张继。碍于师母之命,先生前去一见。见过之后,再也未曾参与国史馆的任何活动。比较一下十几年后先生十分欣然地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真是天壤之别。他在借调校点《二十四史》行将结束之时赋诗云:
十年素榻半凝尘,借调于今又几春。
抖擞风云诚盛事,尔来正愧有闲身。
这种精神状态与先生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学术领域的“双轨并进”,做经世致用之学,是一脉相承的,凸显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救世爱国的人文情怀,这也是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与升华,值得我们尊敬与学习。
先生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说,此文题名是抄袭鲁迅先生的《太炎先生二三事》。弟子懒惰,也借用此意,将这篇缅念文字名之曰:《王仲荦先生二三事》,尚祈先生不责。
WangZhongluo’sPatriotismandAcademicResearch
QI T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Mr. Wang Zhongluo is a famous historian. In his long-term academic research, he was not confined to discipline restrictions. He was distinguished in the research of both history and literature. Mr. Wang also has an academic vision of mastering chang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He has made explorations from the theory to the textual criticism,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modern times as well as from academic issues such as the issue of the period of ancient history,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 Asia, to the sprouting of capitalism. He has created philosophy of his own in many fields. He has also left behind great achievements for later generations, including both the purely academic booksThesixchroniclesoftheNorthernZhouDynastyandTheGeographicalChroniclesoftheNorthernZhouDynastyand achievement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n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Throughout his life, he was full of patriotic feelings, and he followed the way of the gentleman and the dedication of his country. In his later years, he also achieved what Confucius said “do whatever he likes and does not transgress what is right” and made a national study.
Keywords:Wang Zhongluo; historian; both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cademic vision; salvation and patriot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