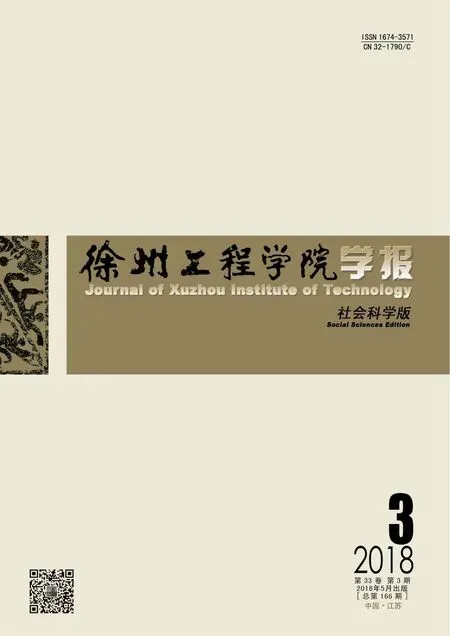屈原《九歌》的礼乐属性和韶舞
黄震云
(中国政法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00)
比较起来,《九歌》和《天问》是楚辞中最难疏解把握的篇章,原因是《天问》涉及天地自然、人文历史的时空过长,难以和其他材料印证;屈原又以带有思索性的语言反问,所以要具体落实其诗义十分困难,争论也就不可避免。《九歌》在学界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愉神之作,纪念为国阵亡的将士,由此引发出多种推测。愉神之说是一个俗语推测,是对作品系统表现的状态的描绘,或者说文心指向,不是一个学术的表达。组诗《九歌》将帝女湘君湘夫人和东皇与“国殇”放在一个平面上,问题就出来了:这些阵亡将士怎么能称为神呢?实在于古无训。为什么选择舜的两个女人而不是女娲或者涂山氏呢?她们也是早期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名气远在二女之上。为什么楚国的《九歌》有黄河之神河伯呢?这也违反传统的礼乐规制。曾经有人想将这些鬼神图画分割成一个模型,怎奈没有学术基础,弄来弄去,落下一个笑话。但是,这是楚辞研究很重要的又绕不过去的问题,需要我们学界作出回答。
一、《九歌》的格局和春享
王逸《楚辞章句》是我们研究楚辞的一个重要门径和坐标。其卷二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错杂而广异义焉。”[1]742-743句中的“祠”一本作“祀”,无“沅湘之间”,无“歌”字。王逸认为是乐神之作,古人乐神的方式有很多,他没有说明是哪一种形式。按照王逸的说明,屈原对《九歌》是改作,改作的内容是《九歌》之曲,表现出三方面的内容: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章句错杂而广异义。这样一来,乐神的祠祭就成了屈原书愤的歌舞了。这些祭神的人会乐意去改变初衷表现屈原的感受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否认,其中加入了相应的成分,只是有限。同时,按照传统礼乐的形制应该是歌乐舞三位一体,那么曲,也就是乐,显然和歌一致,但没有提到舞如何。
《九歌》计11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直觉上和楚国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最后三篇:《山鬼》《国殇》《礼魂》。前面的基本上就是两组:一是天神类,《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二是地祈类,《东君》《河伯》《湘君》《湘夫人》。这是一个直觉的归纳,但归纳以后很容易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天神、地祈和关于楚国的作品《山鬼》《国殇》《礼魂》。看上去,这些神灵的表现亦庄亦谐,譬如《云中君》:“灵皇皇兮既降,焱远举兮云中。 览冀州*按《行书纪年》言:(舜)“元年已末,帝即位,居冀,作大韶之乐。”无疑《九歌》祭祀天神的乐曲出自舜。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2]65不论云中君是雷电还是云彩,他看到的是九州之一的冀州,而不是荆楚,看上去颇为滑稽。虽然冀州位列九州之首,但是荆河惟豫州,《周礼》称“河南曰豫州”。 需要越过豫州才看到冀州,享受楚国人的香火,眼睛却看到冀州或者说跑到冀州去了,是不是很滑稽?又何尝看到屈原改动的痕迹?只能说这个是现成的并且不能改动的礼乐作品。屈原的时代礼崩乐坏,楚国没有自己的礼乐,《诗经》中也没有楚风,毕竟当初西周统治者不喜欢楚人,不与之结盟,楚人也就只好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同,那么当然也不太可能是周的礼乐,而是更早的时侯流传下来的古乐了。
中国的祭祀风气由来已久,商汤灭葛的理由就是葛伯拒绝祭祀鬼神,殷纣王率民以事神,直至亡国不悟。屈原经常提到伍子胥,在那个时代也是巫风盛行。东汉桓谭《新论·言体》上说:“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甚可伤。”[3]14楚灵王祀上帝、礼群神,在社稷坛执羽起舞,这是典型的文舞。到屈原时代这种风气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汉书·郊祀志下》:“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4]702贾谊《新书·春秋》曰:“楚怀王心矜好高,人无道而欲有伯(霸)王之号,铸金以象诸侯人君,令大国之王编而先马:梁王御、宋王骖乘,周、召、毕、陈、滕、薛、卫、中山之君,皆象使随从而趋。诸侯闻之,以为不宜,故兴师而伐之。”[5]211由此观之,楚怀王通过祭祀希望借助鬼神的力量打败秦国,那么这显然不是楚俗,而是楚国的公序亦即战略决策。
这样一个祭祀的格局由来已久。《周易·豫·象传》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6]31以上帝配祖考这样的格局主要形成于西周。《孝经·圣治》说:“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6]2553为什么要祀后稷以配天?按照郑玄的理解,含有礼遇以及引导上帝及其诸神的意思。所以《史记·礼书》总结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7]1167这是指祭祀的形式。但很明显《九歌》中没有始祖,也没有将历代祖先合在一起,不符合禘祫的规格。那么只能是一般的岁时祭祀了。
检《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8]1276又《诗·小雅·天保》说:“禴祠烝尝。” 毛 传:“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烝。”[9]404-405《书·伊训》曰:“伊尹祠于先王。”[10]390陆德明释文:“祠,祭也。” 孔颖达疏:“祠则有主有尸,其礼大;奠则奠器而已,其礼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尊。”[11]202祠可以有纪念、奔丧等多种含义。因此《九歌》体现的礼乐性质是祭享先王,也就是春享性质,以楚先王配东皇太一,礼神主要是大小司命等,很明显,这个和屈原关系最为关联且可成为国殇的先王当然是楚怀王。
二、韶乐的产生和流传与《九歌》的礼乐性质
上古以来,圣贤制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五帝殊时,不相颂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但韶乐是一个例外,昌盛不衰。孔子整理《诗经》,也是以韶武雅颂为标准,韶为正乐标准依据之首,所以《诗经》礼乐上承三代,先周宾商,已是事实。《乐府诗集·卷第五十二·雅舞》说:“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余《韶》《武》。汉魏已后,咸有改革。然其所用,文武二舞而已,名虽不同,不变其舞。故《古今乐录》曰:‘自周以来,唯改其辞,示不相袭,未有变其舞者也。’”[12]753-754韶乐流传久远,为中国古代经典礼乐之最。究其原因,一是韶乐本身尽善尽美,二是本身早期经历了一个增损完善的过程,非单纯的一代礼乐。
(一)韶乐的产生
目前有关资料可以证明韶乐产生在帝喾时代。《吕氏春秋·古乐》说:“帝喾命咸墨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又其卷五曰:“ 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 铸十二钟, 以和五音, 以施《英韶》。”[13]148-149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14]74据此,韶乐最早是黄帝制作,名为《英韶》,而作为声歌则出自帝喾。
(二)舜禹和韶乐
《尚书大传》曰:“惟五祀,定钟石,论人声,鸟兽咸变,于是勃然兴韶於大麓之野。执事还归,二年唠然,乃作《大唐之歌》,以声帝美,声成而彩凤至。故其乐曰:‘舟张辟雍,鸧鸧相从。八风回回,凤皇喈喈。’”[15]3今本《竹书纪年》:“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作大韶之乐即帝位。”韶乐的本质是歌颂,就是说有虞氏即帝位时候用的礼乐是大韶,而不是九韶即帝喾时代的《九招》或《应韶》,故《九歌》中的《云中君》言“览冀州兮有馀”,独独挑出一个冀州,也就对应舜之大韶乐了。屈原作品多次提到九州,这里的云中君,显然是冀州的云中君了。由于用的是舜的韶乐,所以没有改动。 汉代王符《潜夫论》卷八说:“世号有虞, 作乐九韶。”[16]254又《淮南子》卷十三《氾论训》:“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17]719《风俗通义·声音》:“故黄帝作咸池……舜作韶。”注云:“‘韶’,汉志作‘招’,下同。乐记:‘韶,继也。’注:舜乐名也。韶之言绍也,言舜能绍尧之德。《周礼》曰‘大招’。”[18]269显然,汉代人将《九韶》《九招》《大韶》几个混而为一,即韶乐又称为九韶。但根据上引材料看,《英韶》《大韶》《九韶》和《九招》应该有所区别,只有《九招》,后人视为《九韶》,但《九韶》不能说就是《大韶》。至于汉代人将几者作为一部乐来看待,实在缺少根据。
考《尚书·益稷》说:“戛击鸣球, 搏柑琴瑟, 以咏祖考来格, 虞宾在位, 群后德让。下管盗鼓, 合止祝歌笙墉以间, 鸟兽跄跄; 箫韶九成,凤凰来仪。”[10]50箫韶九成的描绘和《尚书大传》中记载的“定钟石,论人声,鸟兽咸变,于是勃然兴韶於大麓之野”内容相似,时间发生在舜禹时期。说明舜确实制作了韶乐,其特点是用钟磬天籁本色之音效法鸟兽之形制作了九成之作,所以帝喾虽然制作了《九招》,但是舜时代制作的是《大韶》,虽然也是九成,但看不出二者是同一部乐。《史记·吴太伯世家》:“见舞招箾。”服虔注曰:“有虞氏之乐大韶也。”[19]1340,1343还是能够分清楚的。至于二者有没有联系和继承,没有充足的资料可以证明,但区别肯定存在。《韩诗外传》卷四:“韶用干戚,非至乐也;舜兼二女,非达礼也。”[20]136由此观之,韶舞干戚,肯定是表现建功的武舞,娥皇女英是舜时代加入的重要内容。如《吕氏春秋》言,韶在殷商时代进行了修订,加入了善的成分,因此孔子说韶尽善尽美。
又《史记·夏本纪》说:“于是夔行乐,祖考至,髃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帝拜曰:‘然,往钦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 ,为山川神主。”[19]73这里提到箫韶九成,舜为之歌的箫韶应该指的是舞蹈,或者说乐舞,表明楚辞《九歌》的仪节如《离骚》所言,歌《九歌》而舞韶,舞不变,但词曲歌的成分有所调整。
百兽率舞最早见于《尚书》,传统以为是恩及禽兽,以至于百兽率舞。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我国的行政体制历史悠久,传说伏羲氏以龙纪,以龙名官;共工氏以水纪,以水名官;神农氏以火名官;黄帝以云名官;少昊氏以鸟名官;周初以天地四时名六卿。司马迁将中国历史从黄帝开始写作。《史记·五帝本纪》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性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19]41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就是有熊氏,熊、罴、貔、貅、貙、虎六师即黄帝的六支军队,熊以外皆是他的盟军。这样的好处和作用是体国经野,设官分职。黄帝不仅对行政系统进行了规范,也对军队系统进行了安排。就有关的典籍称呼看,熊这些动物也有的称为鸟,那么也就是说少昊氏以鸟名官,但是并不是将过去的命名全部推翻。换言之,黄帝时代也应该是这样。但历代的名官系统皆以东西南北中为纲纪,满足五即可,但黄帝的军队却是六师,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而夏代的九,周代的八,皆是各自的特色。
百兽率舞不仅是对和谐天下的一种描述,也是设职分官的需要。和大禹的九州划分一样,皆是人类对世界准确认识和把握的创举。这些创举完成以后就是进一步的推进,政治思维与措施随之跟进,等级、权责也就更加明朗。如祭祀,《礼记·王制》《史记·封禅书》等皆指出: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又《史记·乐书》说:
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
所谓州异国殊,也是指礼乐风俗之差异。这种差异是有意去推动强化形成的。在乐舞时为什么要用百兽?其实这也是求异和变化的一种设计。其原理《周礼·春官》说: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只、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再变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
根据《周礼·春官》的资料我们看出,在周人天人合一的宇宙理论中,乐具有全面的价值功能,所谓六变之象物和以作动物,就是百兽率舞的理论依据。
禹和韶乐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考《史记·五帝本纪》:“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19]39索隐曰:“招,音韶。”根据上面的材料我们看出,大禹是兴《九招》之乐,原因是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无疑九韶并不是大禹制作,大禹时代的韶乐就是舜时代的韶,可称为九韶,后来流传的韶乐也就是舜制作的韶乐。
《山海经·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21]460开上三嫔于天——和尚书宾通,指的是参见礼乐,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郝懿行注云:“盖谓启三度宾于天帝,而得九奏之乐也。”夏后开即夏启,为避景帝刘启之讳,改启为开。所谓天帝也就是已经去世的君王,即禹。禹的《九招》就是舜的《九歌》。又《左传》文公七年《夏书》曰:“‘戒之用休, 蓝之用威, 勤之以九歌, 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22]376歌的特质就是歌功,所以说功成作乐。这里的九歌和我们讨论的楚辞《九歌》不是一回事。现在说的《九歌》十一篇,包括了韶乐和九歌。九歌实际上就是歌颂六府三事的九功之歌。核之现行《九歌》中的《国殇》,正好是十八句,九层意思,显然真正的九歌指的是《国殇》,其余的内容主要是韶乐的内容。
殷商时代,韶乐发生了一些变化。《吕氏春秋·古乐》:“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 以见其善。”[13]153修九招就是说伊尹对韶乐进行了必要的修订,突出了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的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周王室的乐舞时看过韶乐,他赞美韶乐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有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事不敢请已!”[22]921这表明,作为古代经典礼乐,韶乐一直在发挥作用,得到有效传承。韶乐以其至德的品格和尽善尽美的生态,不仅传承,而且还会和其他的礼乐作品配合。从干戚舞到尽善尽美,伊尹起到了重要作用。荀子《乐论》篇第二十说:“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斧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带甲婴胄,歌于行伍,使人之心伤;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邪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23]215-216韶乐也可以分析表演。《庄子· 达生》:“奏九韶以乐之。”舞韶歌武和奏九歌而舞韶兮,祭祀以外,也有的是假日以娱乐之功能。歌乐舞中,奏九歌说明《九歌》还是音乐作品,从名称上看《九歌》应该还是歌,即歌功的作品,因此是礼乐作品无疑。
汉高祖六年, 韶乐“更名文始” 。更名的原因, 据说是汉代统治者为了要表示“不相袭” 前代乐舞的缘故。实际上, 汉代的《文始》在魏文帝黄初二年“改汉文始舞曰大韶舞”,又改了回去。
三、《山鬼》与沉狸仪式
《山鬼》是楚辞中很有争议的一篇作品,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二十年前,我在《江海学刊》上发表了《山鬼漫议》(1996年5期)一文,认为是祭礼,和庭寮有关。后来在《楚辞通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最近几年,在进行楚辞的研究中一直在探讨历代研究楚辞的差异及其原因,发现从东汉王逸开始,《山鬼》阐释的文字中有一点特别一致,就是《山鬼》就是山神,而恰恰这一关键点的解释有误,所以,后来才出现各色各样的分歧。
战国以前,《山鬼》就是山神说于史无征,所以凡言《山鬼》就是山神,皆为误解。鬼,在先秦从来都是指一般人死以后的灵魂,没有别解。甲骨文中,鬼的字形多变,是人戴着面具的样子,大概与巫祝有关,巫祝编演内容不同,故形态出现差异。《礼记·祭法》第二十三言:“大凡生于天地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余不变也”[6]1588。“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6]1589《周礼》说:“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6]757“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以禬国之凶荒,民之札丧。”[6]827显然,《礼记》《周礼》中鬼神还是分得很清楚的,还有等级,不能混淆或者互相替代。就是到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解释为“人神曰鬼,鬼,人之归也”[24]754。这是东汉人的理解。屈原的作品《国殇》说:“魂魄毅兮为鬼雄。”[25]83鬼就是指人的灵魂。因此,《山鬼》就不能说是山神了。
那么,山神如何称呼呢?我国古代的神祇有自己的民族特色。1.天上的神是人的灵魂升天的存在,商周的上帝就是帝喾,因此《关尹子》说人皆可以成为神,神都是人。孟子说人人可以为尧舜是一个道理。2.人和神是一个世界,《国语》和《山海经》明确表示人神本一体,后来分开住而已,所谓绝地天通。3.基于上面的原因,中国的神相当于灵,人对百神可以祭,也可以封。人中强大的照样可以号令百神,如西王母就担任司天神的职务。又譬如周代对无名的山进行封神,土地封神更多,规定二十五家一个社,即一个土地神,目的是祭祀方便。西周的神系是理性的管理学的艺术,与幻想神话无关。国家对神的存废权力一直未断,如明洪武二年封屈原为楚三间大夫屈平氏之神。4.中国人的神定义是哲学思维,即阴阳不测谓之神,异常现象叫做妖,神妖皆不是确定的具象性质。汉以后的神仙、神圣、鬼神合流,神仙只是比普通人长寿、有本事罢了,但像人一样活着。东汉以后妖和西魔合称妖魔,成神仙敌对阵营,那已经进入小说时代了。山之灵概称为山神,决不是鬼,而具体的名称各不相同。历史上经过了几次封神,西周则遍封名山大川。《礼记·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6]1588即人们在山中所见而无法将其识别的生物都是神,如“烛阴”。《山海经·海外北经》云:“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冃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26]1230又葛洪《抱朴子·登涉》说:“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也。”[27]76根据这些资料我们看出,山为本,皆有神灵,各有自己的神形,也有各自的名称。其理由如《尚书大传》等都有解释,就是山中往往风云际会,那是通天的标志,所以认为是神灵。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山鬼》描述的山是什么山。不过,《山海经·中山经》对洞庭湖一带山及其祭祀的描绘,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参考: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柤梨橘□,其草多葌蘪芜芍药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闲,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荣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毛,用一雄鸡、一牝豚(气刀),糈用稌。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尧山、阳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瘗,祈用酒,毛用少牢,婴毛一吉玉。洞庭、荣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瘗,祈酒太牢祠,婴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26]176
根据《山海经》,洞庭湖一带的山神皆鸟身而龙首,这个形象与山鬼形象明显不同。从祭祀看,有的祠用鸡,即扁毛物,有的祠用毛,毛用少牢,就是说用猪羊,猪羊是圆毛,那么鸡鸭等扁毛的就不行了。狸属于圆毛类。埋就是《国殇》中霾两轮的霾,轮指的是玉璧。少牢是大礼,所不同的是天子祭祀天地用太牢。
以这样的格局对照《山鬼》,只能婉约地看出其大致性质过程。按《山鬼》说: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曼曼。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25]79
王逸《九歌章句序》认为:“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之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25]54王逸把《九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认为《九歌》乃屈原根据楚国祭祀巫歌改编而成,这是一篇祭歌,而创作的原因是为了“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即屈原写九歌是为了抒发心中的冤屈和对某人加以讽谏,此可以从其生平与经历见之。王逸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他把《九歌》分成两个部分就是陈事和讽谏,似乎部分接近实情。
屈原《离骚》说:“启棘宾商,九辨九歌。”[25]21“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25]46《九歌》用来祭祀神祇,韶是传说中舜的舞蹈《九韶》。《史记·夏本纪》载:“于是夔行乐……鸟兽翔舞,《箫韶》九成,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28]81说《九歌》皆宗禹之法度,难以落实。但言韶舞和《九歌》二者可以配合使用,符合事实,现存《九歌》就是韶舞和《九歌》的混合体。检《周礼·天官冢宰》说:
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体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举,则陈其鼎俎,以牲体实之。选百羞酱物珍物以俟馈,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鸣,则庮,羊泠毛而毳膻,犬赤股而躁,臊;鸟皫色而沙鸣,狸;豕盲视而交睫,腥;马黑脊而般臂,蝼。凡宗庙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饮食亦如之,凡掌共羞、修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赐肉修,则饔人共之。……渔人掌以时为梁,春献王鲔,辨鱼物,为鲜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宾客、丧纪,共其鱼之鲜槁。凡渔者,掌其政令。凡渔征入于玉府。鳖人,掌取互物。以时簎鱼、鳖、龟、蜃,凡狸物。春献鳖蜃,秋献龟鱼。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6]661
从《周礼》我们看出,周人有禽献之礼,既是朝廷膳羞,也是祭祀之用,而狸是其中重要的禽献。《诗经·七月》也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6]391的记载。根据《山鬼》的叙述“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由象征性的赤豹领路,后面跟着装饰了文采的狸,地点是在山之阿,显然正在从事隆重的祭祀仪式。前引《山海经》言洞庭、荣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瘗,祈酒太牢祠,婴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说明祭山川土地神的时候注重五彩装饰,和狸的行走队伍十分类似。对照《周礼》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6]757。“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6]827,《山鬼》记录的乐舞正是古老的祭祀形式,到周代仍然作为礼的规范的狸沉之礼,时间正是夏天。其内容就是前八句,而后面的文字则以余的口吻叙述参与狸沉的过程及其感受。如王逸所言:“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显然,屈原的《山鬼》既保存了夏代流传下来的诗歌原貌,也通过叙述自己的感受,扩大了《九歌》的篇幅内容,含义也不复杂,表现了楚辞一贯的作风,自比香草,叹息年老,希望得到朝廷重视。至此我们就明白了以下事实:《山鬼》前八句是古歌《九歌》,言述貍沉之礼仪,是为乐舞,而后面是屈原自伤之词。
四、《国殇》《礼魂》和殇祀
(一)楚国关于战争的法律
近年来,我清楚地认识到,研究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甚至文体,都离不开对当时制度的考察,而制度的设计直接全面影响、制约着文学的生态。在屈原时代,楚国发生过一些内乱,对外也有一些战事,但是基本上惨败的都是楚国。怀王死秦,更使楚史蒙羞,因此出现《九歌》为纪念阵亡将士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但是,我们考察楚国当时的王命和法律发现,作为顶层设计的军事法对战败者的惩罚非常的严厉,更不用说去纪念他们了。在大数据环境下,我们不妨让资料说话:
资料一《左传·桓公十三年》说: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资料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楚杀其大夫得臣。正义曰:子玉违其君命以取败,称名以杀,罪之。
资料三《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曰:
薳越曰:“再败君师,死且有罪。此年秋败於鸡父,设往复败为再败。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缢於薳澨。薳澨,楚地。缢,一赐反。澨,市制反。
资料四《吕氏春秋·高义》称:
荆人与吴人将战,荆师寡,吴师众。荆将军子囊曰:“我与吴人战,必败。败王师,辱王名,亏壤土,忠臣不忍为也。”不复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复於王曰:“臣请死。”王曰: “将军之遁也,以其为利也。今诚利,将军何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後世之为王臣者,将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荆国终为天下挠。”遂伏剑而死。王曰:“请成将军之义。”乃为之桐棺三寸,加斧锧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数至也。
上列四条资料告诉我们,战国时期的楚国有战争失败罪的刑罚,非常严厉,战死也是犯罪。但是,如果逃跑则可以免于刑罚。对未战自杀者采取象刑制度,即为之桐棺三寸,加斧锧其上。看了这几条资料我们就知道,《九歌》不可能是纪念阵亡将士之作了。究其原理,楚人认为,死于战事,为恶鬼(包山简考释)。
(二)《国殇》和殇祀
一般认为,《国殇》是纪念楚国阵亡将士的,完全是想当然。为国捐躯,在现当代可以称为国殇,但是,当时的楚国对于战败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当然是不可能的了。那么,这个《国殇》必然有对象,上面我们根据礼制的特点确定作品是属于春享礼,祭祀死去的君王也就是楚怀王。这里,通过《国殇》,我们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昭明文选》卷二十八鲍照《出自蓟北门行》“身死为国殇”,李善注引楚辞《国殇祠》曰:“国殇,为国战亡也。楚辞祠国殇曰。”[29]403李善战亡论也是出自唐代道德观念的判断,不足为训,但称《国殇》为国殇祠是说明唐代流传的版本楚辞依然是祠的特质。而祠并非一般战死士兵所能拥有的待遇,韶乐亦主要是庙堂礼乐,当然不会用在几年阵亡的士兵的场合。
《礼记》有士丧礼,记载士丧问题,《礼记》卷十一有丧服,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
《传》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无受也?丧成人者,其文缛。丧未成人者,其文不缛。故殇之绖不樛垂,盖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无服之殇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殇,殇而无服。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死则哭之;未名则不哭也。叔父之长殇、中殇,姑、姊妹之长殇、中殇,昆弟之长殇、中殇,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適孙之长殇、中殇,大夫之庶子为適昆弟之长殇、中殇,公为適之子长殇、中殇,大夫为適子之长殇、中殇。其长殇,皆九月,缨绖;其中殇,七月,不缨绖。[30]163
按经丧也就是殇,指的是十九岁以下死亡者,十六以上即为长殇,显然和军人的年龄不相匹配。换言之,殇指的是未成年人死亡,带有不幸的意思。因此祭祀不幸死亡的人也会用殇来表示。《穆天子传》卷六说:
天子乃殡盛姬于谷丘之庙壬寅,天子命哭,启为主〔为之丧主〕……天子宾之命终丧礼,于是殇祀而哭,内史执策……敷筵席设几,盛馈具,肺盐羹,胾脯、枣、醢、鱼腊、糗、韭,百物,乃陈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壶尊四十,器,曾祝祭食……祭,祝报祭觞大师,乃哭即位,毕哭,内史策而哭……乐人陈琴瑟,竽,龠。
这是周穆王殇祀年轻的盛姬举行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其主张的实物和楚辞《招魂》中的结构形式非常类似。因此,《招魂》应该招的是楚怀王的魂无疑。这里用的乐器和《东皇太一》中“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也完全符合。尽管这不是绝对的证据,但至少可以看到祭祀的礼乐规格之高,也符合传统的殇祀方式。《礼魂》也是大礼的体现,和《招魂》合为当时的大礼。
(三)《九歌》是祭祀怀王的乐舞
考《周礼·春官宗伯下》云“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31]790-791,“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薺,车亦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31]793。所谓九德之歌,就是《九歌》,是用来礼人鬼的大礼。那么可想而知,《九歌》在当时祭祀可以作为国殇的人,当然是不幸去世的楚怀王了。就屈原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关心的是国家大事,民间祭祀他应该没有什么兴趣,更不会为之出手。以《周礼》宗庙礼乐核之《楚辞》屈原《离骚》:“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乐。” 又《楚辞·九叹·忧苦》:“恶虞氏之《箫韶》兮,好遗风之《激楚》。”那么,与东皇和主神相配的祭祀对象,只有被骗死于秦难不幸的楚怀王了。王逸在《楚辞章句》认为:“国殇,谓死于国事者。”也是对楚怀王而言。又捡《文献通考卷六十八·郊社考一》说:
太史公作《封禅书》,所序者秦汉间不经之祠,而必以舜类上帝,三代郊祀之礼先之。至班孟坚则直名其书曰《郊祀志》,盖汉世以三代之所郊祀者祀泰一、五帝,於是以天为有六,以祀六帝为郊。自迁、固以来,议论相袭而然矣。康成注二《礼》,凡祀天处必指以为所祀者某帝,其所谓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谓配天者亦非一祖,于是释禘、郊、祖、宗以为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盖在於取谶纬之书解经,以秦汉之事为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汉人崇之,六天之说,迁、固志之,则其谬亦非始於康成也。愚尝著《汉不郊祀论》,见所叙西汉事之後。
为什么以东皇为主?《文献通考》给出了答案,以舜为上帝,这是秦汉间的事情,而显然战国末期的楚国就已经这样了。如此看来,东皇太一就是舜,与其相应的礼乐也就是韶乐,其词就是歌功的《九歌》。以此核对与屈原基本同时的宋玉《高唐赋》:
进纯牺,祷琁室。醮诸神,礼太一。传祝已具,言辞已毕。王乃乘玉舆,驷仓螭,垂旒旌;旆合谐。大弦而雅声流,冽风过而增悲哀。于是调讴,令人惏悷惨凄,胁息增欷。
所谓醮诸神、礼太一,也就是这个意思了。《诗经》中的《车攻》是首会诸侯于东都的礼乐作品:
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
田车既好,田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
之子于苗,选徒嚣嚣。建旐设旄,搏兽于敖。
驾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会同有绎。
决拾既佽,弓矢既调。射夫既同,助我举柴。
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驰,舍矢如破。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闻无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记载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於东都。这首礼乐作品类似于《国殇》,以田猎表现威武。又《吉日》说:
吉日维戊,既伯既祷。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从其群丑。
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兽之所同,麀鹿麌□。漆沮之从,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宾客,且以酌醴。
《吉日》也是赞美周宣王的作品,记录田猎礼仪。根据以上两篇作品对比《国殇》看,《国殇》是首表现斗力神武的作品。由于得到神灵的支持,所以在激烈的战斗中,取得了“天时懟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的辉煌战绩。无论如何楚国人不会说他们惹了威灵怒,被敌人杀得很惨这样的话,毕竟他们已经祭祀了太一和众神,所以从顺序上说,《国殇》是在祭祀神灵以后开始表演的军礼。所以“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取得了胜利,他们的信念是“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一副大无畏的样子。这里说的“霾两轮兮絷四马”的霾是沉埋礼的霾,两轮当然指的是玉璧,毕竟霾两轮难以说通。霾两轮和从文狸,构成了沉埋礼。这就是醮诸神、礼太一的殇祀的分界。
虽然楚武王号称鬻子为文王老师,但是成王岐山盟誓以其蛮夷身份拒绝了楚人,否定了其合法的诸侯地位,封其为子爵,名义为楚子,实际上用夷礼,毕竟先秦称男爵的凤毛麟角。因此,楚人对周始终不满。《礼记·祭法》和《国语·晋语》皆说:“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殷商同祭。屈原以帝喾创立的韶乐作为对楚怀王的殇祀,多少应该有楚应获得正统的思维。
参考文献:
[1]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屈原.楚辞[M].汤漳平,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
[3]桓谭.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4]王继如.汉书今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5]贾谊.新书[M].方向东,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6]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
[8]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9]金启华,朱一清,程自信.诗经鉴赏辞典[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
[10]尚书[M].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11]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吕不韦.吕氏春秋[M].陆玖,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14]刘勰.文心雕龙[M].长沙:岳麓书社,2004.
[1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王符.潜夫论[M].王健,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17]刘安.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8]应劭.风俗通义校注[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1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0]韩婴.韩诗外传集释: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1]山海经[M].冯国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2]叶农.左传译注[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23]荀况.荀子[M].杨倞,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4]桂馥.说文解字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5]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26]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7]葛洪.抱朴子[M].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
[28]张守节.史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9]萧统.文选[M].李善,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30]中华书局编辑部.汉魏古注十三经:仪礼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1]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二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