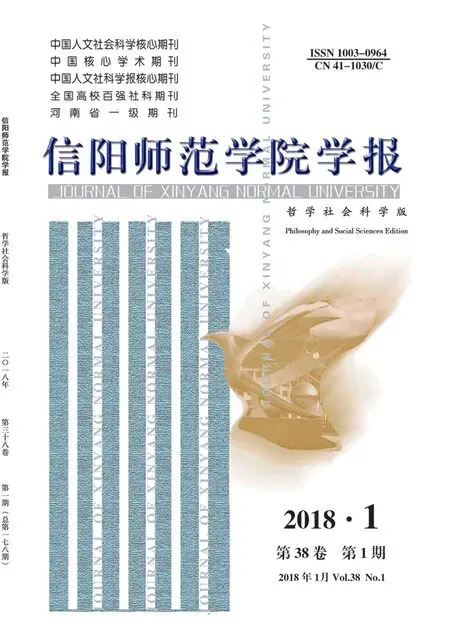乡村挽歌与身份迷失
——解读梁鸿的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
禹权恒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河南当代文学研究·
乡村挽歌与身份迷失
——解读梁鸿的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
禹权恒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梁鸿是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作家,其代表作《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具有典型的非虚构特征。“梁庄”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现实的直接表征,也寄寓着作者对乡土中国社会病症的深层思考。乡民通过“扯秧子”的基本方式进入城市谋生,身份迷失和精神痛苦成为他们永远难以抹掉的印记。“纪实”和“虚构”作为一种“矛盾共同体”,已经有效融入梁鸿的非虚构文学创作过程中,其利弊得失值得进一步探究。
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扯秧子;纪实;虚构
目前,梁鸿已经成为国内非虚构文学创作领域的标志性作家之一,她凭借着《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高度认可。作为一位长期在高校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梁鸿曾经对自己的日常工作充满了怀疑,感觉那种“虚构的生活”并没有和现实世界产生任何关联,“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1]1。于是,她以“故乡女儿”的文化身份,重新回到河南邓州老家梁庄,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和独特感悟,整体呈现了梁庄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常”与“变”,同时也寄托着梁鸿对乡土中国社会病症的深层次思考。
一、村庄:乡土中国的现实病症和疼痛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1]276。作为一个多重矛盾交织的复杂载体,梁庄是梁鸿试图重新“进入”故乡深层结构的重要密码。2008年和2009年,梁鸿怀着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心情,利用寒暑假回到曾经生活20年的故乡梁庄。毫无疑问,梁庄是当代中国社会千百万个乡村现状的基本缩影。梁鸿分别用“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的双重眼光,全面呈现了梁庄在现代性追求进程中整体性的现实图景。她说:“用文学的叙述,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个体情感和社会实证相结合,以情感的态度而非科学的态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当代村庄的存在状态。”[2]但是,梁鸿笔下的梁庄内部却被许多顽固病症缠绕着,各种颓败、黑暗、危机等严重侵蚀着梁庄的生存能力,使乡土中国的缩影——梁庄在剧烈蜕变中不断发出各种痛苦呻吟。
首先,最早进入作者调查视野的是蓬勃的“废墟”村庄。目前,许多村民由于现实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外地打工挣钱,“人去楼空”是梁庄最常见的基本生活图景。正如叶君所说:“城市对乡村的蚕食,以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求生,乡村往日蓬勃的生气渐渐消散,呈现凋敝图景,形成新的乡村现实。”[3]如梁庄的现实图景: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锈着;与此同时,人也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屋前房后的荒草、废墟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1]29
与此同时,原来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成现在的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或者既有权力又有面子的村民沿路而居,不分姓氏,重新形成新的生活场域和聚集群落。梁庄原来的居住格局被有效打破,或者说“村落结构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他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村庄,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盘散沙,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不具有实际的文化功能”[1]40-41。
据老贵叔本人讲述,梁庄砖厂早年为了烧砖取土,平地掘三尺,把将近二三百亩的肥沃土地全部变为凹陷地。假如一旦出现严重水灾或暴雨等恶劣天气,梁庄随时都有可能被洪水淹没,许多村民的身家性命和财产都可能受到严重威胁;早年村庄中间清澈见底的坑塘,如今都已经成为静止的、死亡的、腐败的黑色淤流,没有任何生机和活力,各种废弃物品和生活垃圾随处可见;村庄外面的大片树林早已不复存在,河道中间散发着从化工厂流出的废水,那些经过高温蒸发后的刺鼻的工业味道,让人头晕、窒息、呕吐;加之受到许多现实利益驱动,各种挖沙机在河道中间长期作业,使原来的河道人为地改变,采沙之后所形成的沙窝已经使部分孩子丧命。可以说,村庄内外的现实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严重阻碍了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甚至被人称为“中国的病灶”,这一现实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深刻反思。
其次,梁庄人对学校教育的基本观念逐渐改变,教育现状和前景令人担忧。由于受到“读书无用论”的严重影响,加上农民简单的功利性思想、孩子的年幼无知、教师责任心的下降,直接导致梁庄人普遍对孩子上学不抱希望,一种颓废、失落和涣散的情绪弥漫在村民心中。据梁鸿亲眼所见,曾经辉煌的梁庄小学如今已经闲置起来,杂草丛生,断壁残垣,校门紧闭,荒凉破败,梁庄小学“教书育人”的醒目标语被人抹掉,变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梁庄猪场”。不仅如此 就是国家花费巨资投入的乡村文化茶馆,也几乎沦为村民们打麻将的固定场所,乡村文化前景可谓黯淡无光。根据做过十几年教师的万明哥讲述: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学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学校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1]94
加上受到经济观念和金钱意识的严重冲击,以及许多家长长年在外务工,对孩子们身心发展缺乏基本的关爱,部分孩子就会选择早早退学出去打工。在这一越来越淡薄的乡村文化氛围里,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就相伴而生。比如,长期单独生活的王家少年性格内向,孤独怪癖,在晚上偷看黄碟后不能抑制生理冲动,竟然丧心病狂地去强奸82岁的刘老太,遭到老太太的激烈反抗,最终致其死亡。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凤凰男”梁东,最后也被迫选择在郑州的私企打工,尽管利用贷款在省会买了房,但是仍然由于自身经济条件困难,和女朋友的婚事面临危机。侄子梁磊也是重点大学本科毕业,曾经在深圳一家认证公司上班,但是工资收入微薄,住宿条件非常恶劣,与自己所向往的城市生活相差甚远。他说:“我们这批人比较尴尬。网上不是说吗?让你活不好,但也死不了。我们一个班三十几个人,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我这种状况;那百分之二十比我们强,不是自己强,主要是拼爹妈的背景。干农民的活,你干不了;往高的,你也干不了。我们这种人,是吊在半空上的,上不去,机会很少;下不来,不愿放下身段。”[4]215这些现象深刻影响着农民对孩子接受教育的期待,残酷的现实已经使部分农民对教育失去了基本信心。
再次,梁庄的很多男性长期在外地打工,留守妇女在家里照顾孩子和老人,这就直接导致夫妻之间聚少离多,无形之中给乡村社会婚姻家庭带来了问题。“中国的乡村文化仍然是一种务实文化,踏实地生活,这是第一要义。个人精神需求,夫妻情爱往往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嘲笑、戏谑、回避是最通常的相处方式,很少从容、正面、严肃地去叙说或交流。这种压抑、扭曲精神空间的现象不单存在于家庭内部、夫妻之间,也是邻里交往的基本模式,造成了许多问题”[1]234—235。比如,韩家巧玉背着丈夫明,和梁家万青一起私奔到深圳打工,这一羞耻事情直接把丈夫明气得得了脑血栓,明在中风卧床的第二年就迅速死亡。春梅的丈夫根儿在煤矿打工,竟然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和家人团聚,这就使春梅非常想念丈夫,但又苦于没有联系方式,直接导致春梅胡思乱想,以至造成精神恍惚的可怕现象,最后,春梅竟然因为一桩小错事喝药身亡。王营的一个媳妇儿上吊自杀,直接原因就是丈夫长时间在外地打工,双方不能够过正常夫妻生活,当丈夫回来不久,小媳妇莫名其妙地患了性病,于是,她就怀疑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干坏事,一气之下就竟然选择自杀。正如梁鸿所说:
由于性的被压抑,乡村出现了许多问题。乡村道德观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临时小家庭,它们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有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大肆骚扰女性,并且往往能够成功;有的村干部拥有三妻四妾,妇女们为其争风吃醋,衍生出很多刑事案件。[1]134
最后,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状况出现严重危机。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有机的网络,每个家庭的活动看似不相关联,但却充满张力和布局。费孝通曾经指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就是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5]30通常来讲,在一个村庄里面,大家族的人总能够有较多机会通过各个层面的亲属关系拥有较大的势力空间。但是,那些小姓或者独姓,由于缺少宗族势力,就很难进入乡村的权力阶层并获得认同。在梁庄,老支书梁兴隆、前任支书梁清道以及现任支书韩治景等“乡村政治人物”,都直接或间接进入村民们的“闲话”中间。部分村民就认为,村干部经常损公肥私,甚至享有很多特权,对基层干部极度不满。加上中国乡村内部的传统、文化、道德等因素影响,直接导致农民对基层民主政治漠不关心。实际上,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并非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博弈问题。比如,昆生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贫穷生活,但在前任支书清道哥以及部分年轻人眼中,昆生已经成为一个品德极坏、喝酒闹事、勒索政府、买闺女、故意装穷的人。换言之,昆生在梁庄已经被正常的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排除在外。“他们的存在并非是一个村庄不人道的象征,相反,因为他们的与世隔绝,因为他们的愚笨、怪异,他们已经成为乡村的道德污点,成为被嘲笑的异类,根本不配享受关爱和帮助”[1]160。这种潜规则在乡村社会的正常运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影响着那些处于不同层级范畴的芸芸众生。
“村庄的溃败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1]276。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的现实图景实在让人感慨万千,有些矛盾已经直接引起群体性事件。倘若乡村真正沦落为中国社会的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之时,是否意味着现代化遭遇了现实危机?当乡村在废墟中间散发着恶臭之时,是否验证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是不科学的发展方式?
二、“扯秧子”:从乡村到城市的重要实现方式
《出梁庄记》是《中国在梁庄》的姊妹篇,其详细记录了梁庄在外地务工人员的生活方式、工作环境、身体状况、精神状态等。作为梁庄隐形的“在场者”,这些“进城农民”的生存图景和文化心理结构,是作者进行梁庄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从梁庄来到城市,绝大多数是通过“扯秧子”①方式来实现的。但是,当他们置身于那些陌生城市的时候,客观环境又使其处于一种精神焦虑状态,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打工者”的社会文化身份比较模糊,他们一直在浮华喧嚣的城市边缘游走。
梁庄是一个有机的社会网络,并非只是一栋栋房屋。每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具有密切关联,彼此互为所属。在当代社会,他们也利用这一互为所属的关系以“扯秧子”方式陆续进入城市,并在城市边缘建构一个个“小梁庄”。最后,一个村庄的模式重新呈现出来。可以说,“扯秧子”扯出了一条条城乡之间千丝万缕的根,扯出了那些被现代性、城市化抛弃了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扯出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众所周知,城市的每一个农民工聚集点,几乎都是以老乡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的,比如,龙叔所在的北京市牛栏山镇姚庄村,光亮叔所在的青岛万家窝子,它们几乎都是按照梁庄的既有模式在异地创造、复制的。正如梁鸿所说:“扯秧子,扯出那一地方的一群群老乡、亲戚,沿着最初老乡的居住地,往外扩散,租房子,或私搭私建,形成一个全新的、不被命名却人人知道的聚集地。粗糙、肮脏、简便、毫无章法,内部却亲疏有别,充满着错综复杂的亲密关系。”[4]153
在《出梁庄记》中,贤生是梁庄最早到城市打工的人,也是最早把全家都带出去的人,是梁庄最早出走神话的缔造者。早在1982年左右 ,贤生就毅然离开梁庄来到南阳,后来顺利娶到城市媳妇在南阳安家。紧接着通过“扯秧子”方式,二弟、三弟,之后是妹妹梅花、四弟贤仁、二叔、二婶等直系亲属相继来到南阳。在内蒙古经营校油泵生意的韩家人,也是通过“扯秧子”方式来到城市的,最早的时候是姐姐朝霞的丈夫通过老赵来到内蒙古,后来朝霞、恒武、恒文和韩叔夫妻,以及恒文的姨家表弟向学、小姨夫、舅舅、老丈哥和相关联的吴镇亲戚,前前后后带出来到内蒙古的大约有一百多人,他们的工作性质也具有密切联系。青岛是梁鸿带着悲伤和无奈最后采访的大城市,据在万家窝子居住的光亮叔介绍,原来在青岛的梁庄人很多,梁峰、钱家万俊兄弟、王家一群,加上后来的许多年轻人,至少有四五十人在电镀厂工作过。如今,尽管电镀厂正常作业期间散发的氰化物已经让小柱死亡,现实的工作环境可谓异常恶劣,但是光亮叔、丽婶、瘫子舅舅、邻居老乡新华、秀珍夫妇等苦于没有办法,仍然继续在这里打工挣钱。
然而,在“扯秧子”的过程中,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之间却也经常发生利益冲突,甚至彼此心里隔阂颇深,直接造成相互抱怨、生气、打架以致结下仇恨。比如,贤生在把许多兄弟姐妹们带到南阳的过程中,由于现实利益影响,四弟贤仁就对大哥贤生极度不满。当时,15岁的贤仁在贤生店里帮忙照顾生意,只干活不给钱。20岁之后,贤仁就开始对这一现实状况抱怨,和大哥大嫂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后来,贤仁结婚竟然没有告诉大哥一家人,可见彼此之间心理芥蒂非常严重。在内蒙古,恒文老婆和恒文在姐姐朝霞家中当着许多亲戚的面相互厮打,主要根源在于兄弟姐妹之间在内心都埋怨对方的自私吝啬,是非曲直也实在难以分辨。早年在北京靠校油泵生意起家,如今已经是千万富翁的李秀中就说:“但是咱那儿绝对不行,亲戚不共财,共财再不来。来的亲戚,舅舅、表哥、堂哥、堂妹,还有啥拐弯亲戚,都是我带出来的,到最后全有矛盾,把人搞得很疲乏。我把他们都撵走了,你生气也罢,断亲也罢,也是没有办法。”[4]172
许多长年在外地打工的梁庄人,都深切感觉到自己的社会文化身份处于尴尬境地。比如,在北京郊区的河南村里面的外来打工者几乎占村庄总居住人口的80%,但是河南村的村民和河南村里的河南人之间几乎没有真正的来往。尽管王福姑爷在河南村已经生活了十几年,河南村也成为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家,然而,他们也绝对不了解河南村的内部矛盾和人情是非,彼此之间可谓生活在两个世界。就是在西安的德仁寨、金华村,堂哥、虎子等人和本地村民之间的实际往来,也仅仅限于收房租事宜。“狐狸精”兰子和北京“那个娃儿”之间的爱情悲剧,追根溯源在于兰子实乃外地打工妹,缺乏文化知识和社会地位,没有城市人应该拥有的现实条件,受到男朋友家人的强烈反对,最后以悲剧收场。不但如此,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即使来到城市发展顺利,但内心的身份焦虑感也非常严重。正如在内蒙古白云鄂博做生意的梁庄人张柱子,在和梁鸿深入交谈中说:“要说这些年也算挣些钱,但是,还是觉得不安定,主要是没有身份。光要钱有啥用,你到哪儿去给人家咋介绍,做生意的?自己心里都觉得矮一截子。没有奔头,没有前途,就是住在北京,住在再好的村里,你也不能参与人家啥活动,都没你的份。心里很不美。”[4]126因此,缺乏身份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是外来务工人员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这直接影响着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精神状态。
三、纪实与虚构:非虚构文学创作的基本策略
作为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创作领域中的代表性作品,《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都是梁鸿首先通过实地调查、访谈记录、查阅文献等不同方式,逐渐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然后根据自己对诸多现实问题的深层思考,再集中进行整理剪辑、提炼加工形成的。可以说,梁鸿这种写作方式是非虚构文学创作的基本方式。毫无疑问,非虚构文学创作的应有之义就是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也是作家“在场主义”的现实表征。梁鸿说:“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村庄的过去与现在,它的变与不变,它所经历的欢乐,所遭受的痛苦,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1]2正是怀揣着这些创作动机和希冀,梁鸿才重新回到了那片让她经常魂牵梦绕的土地,以弥补自己的匮乏和缺失,从而试图解决心灵深处的现实困惑。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梁鸿所呈现出来的“梁庄”和“梁庄人”的现实状态,真正就是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吗?显然,许多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生活充满着悖论性和复杂性,这种单向度切入现实的方式有可能带来另一种偏颇。 “梁庄是我的故乡,它不是一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村庄,在强调非虚构的同时也还是不能脱离个人这个维度,我始终是以我的眼光在看待这个乡村”[2]。梁鸿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在文本中间有意识地增加部分“干预性评论”。客观地讲,这可能会给非虚构文学带来一定文学性,甚至也可能会增加作品的思想性。但是,这些主观性评论也存在着诸多盲点甚至偏见。比如,梁鸿和梁庄老人在谈到农村合作医疗、免农业税、土地补贴之时,梁鸿说:“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最容易满足的,给他一点好处就念念不忘。”对村庄附近修建高速公路的认识判断,抑或是对“乡村政治”的臆断性看法,可以说都存在着明显的简单化倾向。因此,梁鸿作品中的“真实”并非“是这样”,它仅仅指向“我看到的是这样”,这些就构成了非虚构文学创作的“真实的限度”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后来,梁鸿也对这种写作方式进行了深刻反思:“我也是一个‘出梁庄者’,当重又回到‘梁庄’之时,我没有资格做任何道德审判,更没有资格替‘梁庄’做出判断。相反,我应该是一个被审判者。”[1]322值得一提的是,梁鸿在呈现梁庄的时候,是把梁庄置于时空倒置的特殊情境下进行关照的,这就有可能对“过去的梁庄”存在着想象性成分,也会在不经意间造成“选择性遗忘”。与此同时,梁鸿在文本里面所呈现的“现实的梁庄”究竟有没有虚构性成分呢?尽管梁鸿自称是以“梁庄女儿”的身份进行采访调查工作的,但是,她已经离开村庄二十多年,对梁庄的现实生活也是陌生的。长期生活在大都市和自身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这些“厚障壁”已经严重阻碍了作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的沟通,许多深层次的现实问题可能会被严重遮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鸿说:“《中国在梁庄》最大的遗憾和缺失还是对乡村生活和乡村生命没有足够深的进入,没有对中国乡土文化和结构有更为深入的把握,因此也没有能把他们的精神状态、表情、言语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这与我调查的深入度不够,知识结构的不完整有关,也与我叙述的穿透力有限相关。”[2]
作为一种“矛盾共同体”,“纪实”和“虚构”已经深深植入《中国在梁庄》的叙事文本中间。梁鸿在后来创作《出梁庄记》之时,已经自觉运用相对理性的写作方式“进入”问题,尽量给读者呈现出“我眼中的真实故事”,至于其和真实存在之间具有何种距离,这可以说是任何作家都无法有效掌控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理非虚构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纪实”和“虚构”?世界各国作家对此也是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形成最终结论。但是,“非虚构写作肯定不是机械记录生活,优秀的非虚构不只是见证、参与和记录。写得再客观,也只是自己角度所呈现的真实。非虚构也需要想象力——想要看到何种真实、所看到的真实又是什么层面的真实,这些都是很考验作者的,非虚构的活力和生命力就表现在这种张力上,我们不是要消解它,而是要丰富和完善”[6]。因此,非虚构文学作家要想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融入了个人化判断,而在于是否真正深入现实生活的核心地带,能够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进行理性描述。
注释:
① 扯秧子,是一项农事活动,这里用该词形象地描绘出了农民凭借亲朋好友的关系,一个带一个地进城务工,在城里形成一个相互交错的存在。
[1] 梁 鸿.中国在梁庄[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2] 刘 莉.怎奈故乡变他乡——梁鸿访谈[J].中国图书评论,2011(6):59.
[3] 叶 君.最后的乡村——论《秦腔》[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125-130.
[4] 梁 鸿.出梁庄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5]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6] 张滢滢.非虚构写作要勇于一步步走进“深渊” [N].文学报,2015-6-23(02).
CountryElegyandIdentityLostInterpretationoflianghong'snon-fictionliterature"ChinainLIANGzhuang" "themakingofliangzhuang"
YU Quanh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 464000,China)
LIANG hong is an important writer in the field of non-fiction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His representative work, "China in LIANG zhuang" "the making of LIANG zhuang" has typical non-fiction characteristics. "LIANG zhuang" is a direct representation of rural reality in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and also conveys the author's deep thinking about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Chinese society.Rural peasants enter the city in the basic way of " pulling the seedlings" to make a living,and the identity loss and mental anguish become their indelible mark. As an"contradictory community","documentary" and "fiction" have been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LIANG hong's non-fiction literary creation process,and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deserve further exploration.
LIANG Hong;"China in LIANG zhuang";"The making of LIANG zhuang";pulling the seedlings; documentary;fiction
韩大强)
10.3969/j.issn.1003-0964.2018.01.022
2017-10-1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BZW15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G031);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
禹权恒(1980—),男,河南泌阳人,文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及鲁迅研究。
J207.42
A
1003-0964(2018)01-0104-05